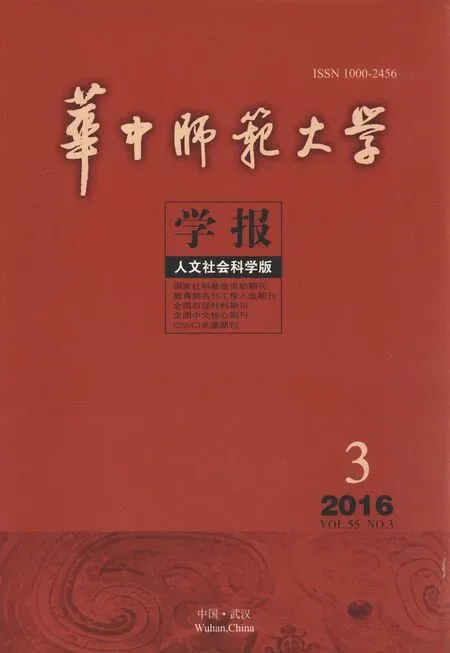反脆弱发展:连片特困地区贫困治理的新范式
李雪萍
(华中师范大学 社会发展与社会政策研究中心, 湖北 武汉 430079)
反脆弱发展:连片特困地区贫困治理的新范式
李雪萍
(华中师范大学 社会发展与社会政策研究中心, 湖北 武汉 430079)
新发展主义基于文化自觉,主张整体的、综合的、内生的新型发展范式。在反贫困路径选择上,新发展主义反思发展主义,并为连片特困地区的贫困治理研究提供参考。先发地区一般采用“先导式发展”路径,基于自身优势,强力推进发展强项,连片落后地区难以遵循此路径。脆弱性交织是连片特困地区的区域特质也是其发展的陷阱。突破发展陷阱,需要寻找到最为脆弱之处,从最弱处着手,反脆弱,从而促进发展,即反脆弱发展。反脆弱发展是指针对区域脆弱性并以此为出发点,以农牧民生计为轴心,促成复合生态系统良性耦合的发展。反脆弱发展是“外助内应”的发展,提倡社会优先发展,强调政府强力作为。反脆弱发展与以往的发展模式相比,它以是否减少了脆弱性作为评判发展的标准;它着眼于未来,注重在当前的社会发展中消减脆弱性,防患于未然;它强调人在减少脆弱性中的主动性。
脆弱性; 反脆弱发展; 贫困治理; 连片特困地区
《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年)》指出,“贫困地区特别是集中连片特殊困难地区(以下简称连片特困地区)发展相对滞后,扶贫开发任务仍十分艰巨”,是国家新十年“扶贫攻坚主战场”。连片特困地区多为“老少边穷地区”,有14个。连片特困地区受制于种种生存与发展的不利条件,仍面临着贫困规模大、贫困程度深、返贫率高的现实困境,减贫之路困难重重。已有的研究和实践更注重以工业化推动产业升级以及效率追求来治理贫困,此路径在连片特困地区举步维艰,连片特困地区的贫困治理及发展应遵循何样的路径?
一、理论与实践的差距:区域性贫困治理路径不清晰
贫困治理的相关学理研究指涉贫困(减贫)理论、发展理论与新发展理论、公共产品理论等。贫困表现在个体、群体、区域层面。个体、群体的贫困,学术界的认知经历了收入贫困——能力贫困——权力贫困的变迁。收入贫困是指人们用于日常生活的物质匮乏,能力贫困是指人们获取生活资料的能力不足,权利贫困是指社会成员应享受的政治和文化权利得不到有效保障。收入贫困是贫困的表现形式,能力贫困是贫困的直接原因,权利贫困是贫困的社会后果和本质,三者总是交织、互补和互动,而不是替代和对立。从收入贫困到能力贫困,再到权利贫困的认知发展,将贫困的外延由物质扩展到社会、环境、精神文化方面。这意味着贫困不只是生产力落后,不只是物质的稀缺不能满足生产生活需求,它与特定的历史文化有关,包含着丰富的社会内涵和心理因素。贫困内涵和外延不断变迁,反映出贫困产生于人类与自然和社会相互影响的互动中。①深入贫困内核,贫困是人与人之间社会关系的总体性表达,只不过这种表达借助物质财富的形式展现出来。②区域贫困的研究中,生态视角与连片特困地区较为吻合。生态贫困论的代表人M·P·托达罗从经济地理的角度来考察地方贫困,他认为地区性的贫困是由自然环境过于恶劣而引发。贫困地区往往具有恶劣的气候特征,暴雨频繁直接摧毁道路、桥梁和建筑物;土壤流失,影响农作物生长;高温和干旱引起土壤有机质流失,土壤结构恶化肥力衰退,诱发虫害、病害,使得牲畜健康恶化,劳动力体质下降从而降低生产率。学者们在M·P·托达罗的分析基础上引入人口压力,从生存空间角度来论述贫困的发生,他们认为,在特定的自然环境条件下,地区所承载的人口容量具有临界点,超过该临界点就会造成人口生存空间不足,生存空间不足就难以保证基本生理需求。生态贫困论者主张反贫困途径是改变生存空间,具体措施是改善土地质量、移民和人口控制等。③
贫困治理研究中,还有社会政策和发展学派的分歧及发展学派内部新发展主义对发展主义的批判。社会政策提倡通过社会福利救助来维持收入,发展学派主张通过经济发展来消除贫困。发展主义认为,对落后地区的扶贫要建立在工业发展的经济增长基础上,也就是期望通过经济援助实现产业结构升级、工业增长来帮助落后地区的穷人。④20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学术界认为社会政策和发展学派都忽视了家庭生计的整体性和复杂性,忽视了穷人自身的能力和抗逆力,并不能保证穷人家庭生计的可持续性。学者们提出可持续生计框架,认为要想促进落后地区穷人家庭生计的可持续性,必须分析他们的整个生计要素:资本、能力和资格以及他们的家庭所在的社会环境,实现家庭生计和外在环境的互动,持续地改善他们的生计。⑤新发展主义是对发展主义的批判的反思。发展主义主张发展中国家复制西方发达国家发展方式与路径。新发展主义针对发展主义的理论缺陷及实践中的失败,主张发展中国家选择一条尊重各民族自己的历史文化传统,符合自己国家社会发展实际的“另类”发展方式和路径。在发展的内容上,发展主义注重经济指标,将丰富而多元的人类需要,化约为单一的向度,仅仅从经济的角度来考量。新发展主义基于文化自觉,主张整体的、综合的、内生的新型发展范式。新发展是基于文化价值的“整体的”发展,是经济利益与文化价值的统一,不只是GDP的增长;发展应当是“综合的”,是国民经济各部门协调发展,是不同地域、社会各阶层之间内聚力的强化,是社会经济整体结构在国家调节作用下的稳定发展;新发展应是“内生的”,是主体力量的动员,是基于历史文化和社会价值的人力资源开发,而不仅仅是物质的丰裕。发展主义与新发展主义之争及其所反映的发展中国家已经历的发展的历史进程,在我国改革开放后的经济社会建设中已有映载。新发展主义理论既适用于分析不同国家经济社会发展道路抉择,也适用于民族国家内部不同区域的发展道路抉择。⑥
在学术之争基础上,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对发展做出了基本规范。1990的《人类发展报告》认为人类发展包括人类的能力形成和能力运用,人的能力包括拥有足够的收入来购买各种商品和服务的能力、延长寿命的能力、享受健康身体的能力、获取更多知识的能力、参与社会公共事务的能力。1991年的人类发展报告增加了环境和居民自有两个因素。总之,发展指的是创造一种能够充分发挥人的潜力的环境,使人们得以按照自己的需求和兴趣,获得富有创造性和丰富多样的生活。人们要有选择生活方式的基本能力,包括获得健康、知识、资源和参与社区活动的能力,没有这些能力,就不可能得到生活中的其他机会。
相关学理研究赋予我们的思考是连片特困地区的贫困治理应是整体性、综合性、内生性的发展,这是否应与其地域性、民族性、文化性紧密联系?贫困治理既要改善生态,更要提升贫困人口的能力,生态治理固然重要而又艰辛,贫困人口的生计改善及能力提高又该如何?与连片特困地区贫困治理的相关思考相映照,我国已有的贫困治理思维定势和实践又是怎样的?发展是我国主要任务,更是连片特困地区的主要任务。⑦连片特困地区在乡村经济还未依赖非农经济得以发展,乡村社区(包括贫困人口)仍未依靠来自非农产业的收入得以脱贫的背景下,作为生态产品生产区域(区域功能划分),工业化前景堪忧,未来减贫路径将怎样选择?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贫困治理的成就得益于制度变革(主要是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等一系列政策和实践)以及迅速的工业化,⑧连片特困地区也惠及于此。当一波波已有制度的减贫效应释放殆尽时,却“缺乏一种有效的替代机制能够保证扶贫政策让贫困人口从中直接受益。由于很多绝对贫困人口集中于极端贫困的地区,所以,单纯依靠经济增长本身(无论它是如何有利于穷人)无法解决这些贫困问题。而且随着市场转型进程的不断推进,各种形式的风险、脆弱性和新的贫困形式以及社会经济差距的扩大将不断产生,传统的以地理区域为扶贫目标的扶贫方式已经不再适合于解决严重的贫困现象了。”⑨
但是,滞后于实践需求,相关研究基于工具理性,连片特困地区反贫困研究不约而同地走上制度化的分析之路,把连片特困地区经济发展道路,特别是现代化实现形式界定在工业化的发展方向上,而对于民族文化传承、特定地域的国内分工等考虑甚少;对于反贫困资源配置、扶贫项目选择、反贫困技术采用等方面,过分倚重国外和其他地区反贫困经验与做法,忽视连片特困地区特殊的地域差异、思维方式、民族文化、政治和历史、传统与习俗背景,以同一性简单推行连片特困地区的扶贫战略,无论在技术推广上还是项目选择上都表现出强制性、机械移植特点;在反贫困力量探讨上,对于政府这一主体,大多研究视其为既定物,抽象而概括地总结其应有的反贫困功能,舍弃了政府在变化的社会、经济机制内部的功能分析和演绎的规范分析,难以揭示出连片特困地区贫困发生的内在实质性。⑩此外,部分减贫研究以“效率”为标准来探讨民族贫困问题,无论是政府扶贫政策实施效果的考察,还是反贫困方式的选择,都非常注重经济效益。这是用简单复制技术性方法来分析复杂的社会性问题,使得减贫工作沦为单纯技术推广机制。


二、脆弱性交织:反脆弱发展的对象物
脆弱性交织是连片特困地区区域特征、发展陷阱,也是反脆弱发展的对象物。
潜藏于各种贫困现象的背后,从脆弱性视角来看,脆弱性交织是连片特困地区的区域特质。依据不同标准,脆弱性可分为多个种类:从复合生态系统及其要素的角度来看,存在着要素脆弱性-复合生态系统脆弱性;从成因来看,存在着结构性脆弱性—胁迫性脆弱性、自然建构的脆弱性—社会建构的脆弱性;从内外部表现来看,累积式脆弱性与冲击式脆弱性并存;从存续时间来看,既有慢性贫困,也有暂时贫困;从脆弱性存在时态来看,有历史范畴的脆弱性、现实范畴的脆弱性、未来范畴的脆弱性;空间形态上,是个体脆弱性、家庭脆弱性、社区脆弱性、社会脆弱性并存与相互渗透;表现形态上,既有显性的脆弱性,也有隐形的脆弱性。
各种脆弱性交织在一起,形成复杂结构,制约区域发展。时空交织是连片特困地区区域脆弱性结构的特征之一。在复合生态系统脆弱的整体性背景下,时间维度上由过去到未来的脆弱性与空间维度上由个体到社会的脆弱性之间相互作用、相互影响,交织在一起,这意味着业已存在的慢性贫困这一最为深刻的脆弱性背景下,历史上脆弱性累积,使得现实中脆弱依然,脆弱散现在个人、家庭、社区和区域范围;历史范畴和现实范畴的脆弱性深远地影响着未来可能的脆弱。内外交加是连片特困地区区域脆弱性结构的又一特征。区域复合生态系统脆弱的环境中,区域内部政治、经济、文化、生态各要素之间难以良性耦合,形成内部结构不稳定,构造“内部张力”;区域之外,政策、经济、社会等风险的冲击,构成外部冲击力,加剧内部张力。内部张力与外部冲击力的“合力”,形塑内外交加的区域脆弱性特征。连片特困地区脆弱性交织可具象为 “PPE怪圈”和“RAP怪圈”的耦合,如图1所示。

图1 PPE怪圈与RAP怪圈耦合机理

“PPE怪圈与RAP怪圈耦合”凸显了相互交织的多重脆弱性,其具体耦合机理揭示了脆弱性交织的复杂性。第一,农村社会发育程度、农业经济结构单一、农民文化素质、贫困、环境退化等多因素之间相互影响,相互作用,形塑了复合生态系统的脆弱性。第二,农民文化素质低且人口过度增长是脆弱性的耦合结点。“PPE怪圈”与“RAP怪圈”耦合结点在于农民文化素质较低且人口过度增长,这意味着,农民文化素质低且人口过度增长是脆弱性的根本点。由这个结点出发,引发农村社会发育程度低、农业经济结构单一、贫困、环境退化等。第三,多种因素形塑了农民文化素质状况及数量增长,这些因素包括农村社会发育程度低、农业经济结构单一、贫困、环境退化等。
三、多主体结构下的生计改善与促成复合生态系统的良性耦合
谁来反脆弱发展?反脆弱发展强调利益相关者(反脆弱发展的主体)在互动中联结,整合各种资源(包括人力资源、物力资源、组织资源等)。先发地区的贫困治理主体一般有当地政府、当地企事业单位和民众。与先发地区不同,连片特困地区贫困治理的主体结构需建构三个支持体系,并形成合力。首先是政府支持体系,它不仅包括本地政府,还包括中央政府、省市政府等上级政府,以及因中央政府通过制度安排设置的对口支援政府机构。其次是社会支持体系,它不仅包括本地企事业单位、社会组织等,还包括通过制度安排建构的对口支援的企事业单位、社会组织,以及区域外的民众等。第三是本地民众支持体系,本地民众是连片特困地区贫困治理最为重要的主体。
反脆弱发展要从哪里“反”起,通往哪里?连片特困地区整体性脆弱中最显著、最直接、最敏感的是农牧民收入问题,而收入与生计紧密相关,反脆弱发展应以农牧民生计改善为轴心。反脆弱发展不仅仅是减少贫困人口的数量和降低贫困程度,终究还需达致复合生态系统良性耦合。


连片特困地区形成了复合生态系统的不良耦合,而公共产品供给可能逐渐将不良耦合渐渐转变为良性耦合。即当公共产品供给增强区域自我发展能力之后,自我发展能力作用于自然、社会、经济三个子系统,可促成期良性耦合。这就是说,改善农牧民生计并促成复合生态系统由不良耦合渐渐转变为良性耦合的关键是供给均衡性公共产品。均衡性公共产品是为落后地区和弱势群体供给的公共产品,它在公共权力的运行范围内,以政治上的均衡手段为经济发展的天然不均衡“解毒”,它体现着民族国家内容分配的公平性以及发展的公平性等。均衡性公共产品供给可使农牧民生计由不可持续到可持续的外力因素,也是增强抗逆力消减脆弱性并促成复合生态系统良性耦合的关键。
四、反脆弱发展的新诠释与新思维
反脆弱发展是一种以重视和减少脆弱性为导向的发展方式。与“可持续发展”不同,它是一种视野更广、直接面向脆弱及其应对的具体路径, 它倡导降低风险性,提高反应力、抵抗力和恢复力的决策与行动,它聚焦于导致脆弱性的各种诱因上。反脆弱发展与以往的发展模式相比,它以是否减少了脆弱性作为评判发展的标准;它着眼于未来,注重在当前的社会发展中消减脆弱性,防患于未然;它强调人在减少脆弱性中的主动性。首先,反脆弱发展是针对脆弱性进行的发展。在复合生态系统脆弱的背景下,反脆弱发展是针对区域脆弱性来考虑发展的内容、路径等等。在国外理论研究中,更多地把脆弱性理解为灾害冲击下的境况,而我们认为,慢性贫困也是极强的脆弱性。其次,反脆弱发展是促进内生性的发展,主要是改善环境,并促进区域民众的福利、机会、能力。内生性发展应该具有地域性、民族性、文化性的发展,即发展与地域特征相符合,与民族需要与民族特质相吻合,受民族文化的牵引。换言之,于发展的考察需要增添区域视角(地方性视角)、民族视角、文化视角等。这是因发展与环境密切相关,一个区域的社会、经济都是区域环境下,即使是农业,也是“地方性的艺术”,田野的秩序永远不会服从于规划人员的理性秩序。再次,反脆弱发展创新了对于发展的判断。于民众,发展是生活水平提高、生计改善、能力提高;于经济,发展主要是绿色产业的发展;于环境,发展是环境改善。反脆弱发展包括社会、科技、生态环境的建设以及居民的生活质量(如营养、衣物、居住、保障、教育、闲暇、安全、环境)全面提高,并重视“人的质量开发”。
由是,反脆弱发展呈现出一些新特征。首先,反脆弱发展是“外助内应”的发展。反脆弱发展不是完全依靠连片特困地区自我力量的发展,应该说,自我发展也包含着利用外部资源。一般说来,先发地区利用了外部资源促进自身发展,如长三角、珠三角等地利用外资等。所不同的是,连片特困地区的发展更需要利用外部资源,利用外部资源的数量更大、程度更深。“外助”的不仅仅是资金资助,还有制度规制及智力支撑等等。“内应”是将“外助”与本地相结合,使得连片特困地区的发展更多地呈现出区域性、民族性、文化性等。其次,反脆弱发展是社会优先发展。我国东西部存在着巨大的人类发展差距(医疗卫生差距、生活水平差距、生活质量差距)和知识发展差距(教育差距、信息差距、技术差距、体制差距)。针对这样的差距,与经济增长式的发展不同,反脆弱发展提倡社会优先发展战略。社会优先发展的基本内涵是民生优先、生态优先,即生态环境更好,民众可行能力更强,生计改善,生活水平提高。如果说,连片特困地区的发展是一种超越式发展,“超越”的内涵更多地指向社会优先发展,而不完全是经济实力的增强,更不是GDP的增加。社会优先发展指向:①发展类型选择上趋于社会优先。发展类型不应再是资产积累型,而应该是长期保值机制及安全网建构战略。②劳动力是民众最重要的资产,就业是民众最基本的生计手段。这意味着增强人力资本,加强教育、卫生医疗等。③社会优先发展指向生计适应性。生计适应性一般由公共服务的数量和质量决定,这就意味着改善民众生计,提高农牧民生活水平,亟需发展的是基本公共服务。再次,连片特困地区的反脆弱发展需要政府的强力作为。连片特困地区实现反脆弱发展,更依赖于政府的规制及投入。政府-社区-民众的力量聚集与整合,是实现发展的内在力量。学术界在基层社会发展的一般性研究中,特别强调政府适当退出,但我们认为促进连片特困地区的发展,政府不应该是退出,而是要不断进入、深入。这是因为在连片特困地区,国家与社会的疆界原本难以区分,甚至不存在,而且从实然的角度来看,连片特困地区尤其需要政府的强力作为。只是,需要进一步深入研讨的是政府作为的范围、程度、限度、方式等。
注释
①杰拉德·迈耶:《发展经济学前沿——未来展望》,北京:中国财经出版社,2003年,第131页。
②刘国虎:《贫困及其现代性话语表达》,云南大学2012年硕士学位论文,第1页。
③⑩郭佩霞:《凉山彝区政府反贫困研究》,西南财经大学2007年博士学位论文,第44页,第17页。
④速水佑次郎:《发展经济学——从贫困到富裕》,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
⑤郭伟和:《“身份之争”:转型中的北京社区生活模式和生计策略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6页。
⑥周穗明:《西方发展主义理论述评》,载于《国外社会科学》2003年第5期;李胜:《新发展主义与后现代解构》,《国外理论动态》2009年第1期。
⑦王珏、吴定勇:《关注民族地区发展进步的视野互动与观点交锋》,《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05年第1期。
⑧学术界认为,正是因为世界工厂-打工经济(由农民工外出就业和打工收入汇款)构成的经济收入循环,是农村减贫的重要因素。参见瑞雪·墨菲:《农民工改变中国》,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6页。
⑨朱晓阳:《反贫困的新战略:从“不可能完成的使命”到管理穷人》,《社会学研究》2004年第2期。








责任编辑王敬尧
Anti-vulnerability Development:The New Paradigm of Poverty Governance in Poverty-stricken Areas
Li Xueping
(Center of Social Development and Social Policy Research, Central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Wuhan 4300079)
In the process of selecting anti-poverty path, new developmentalism, acting as the process and result of developmentalism, is a negation of developmentalism and provides reference for research of poverty governance in poverty-stricken areas. Strengthening regional development, based on their own advantages, is the path taken in regional development of developing areas, and the path is the kind that poverty-stricken areas cannot take. Intertwined vulnerability is not only the regional characteristics but also the development trap of poverty-stricken areas. The most important point of anti-vulnerability is to break the regional development trap through overcoming weakness, take livelihoods of farmers and herdsmen as its core, do lots of efforts to promote a healthier ecosystem. It is the development path of “external assistance—internal response”, which advocates the priority of development of society and emphasizes on strong intervention of governments. Compared with the previous development model, the development path of anti-vulnerability takes reduction of vulnerability as the standard of regional development. It focuses on the future, pays attention to reducing vulnerability in current development, and emphasizes on human initiative in reducing vulnerability.
vulnerability; anti-vulnerability development; poverty governance; poverty-stricken areas
2016-01-16
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甘孜藏区反脆弱发展研究”(15FSH002);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重大攻关项目“新时期我国农村综合改革研究”(12JZD023);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发展报告建设(培育)项目“中国反贫困发展报告”(11JBGP0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