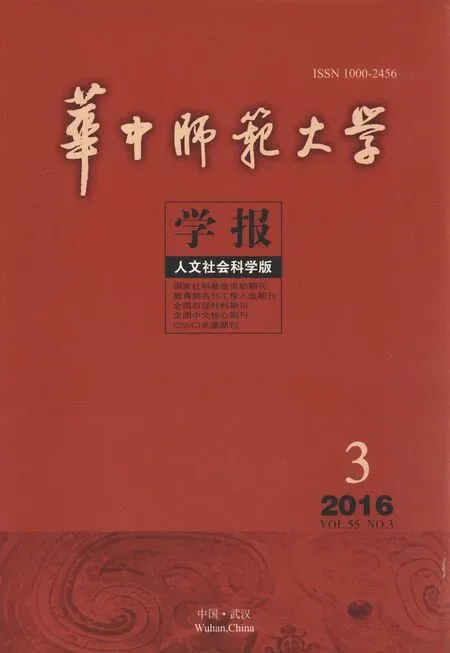古代叙事理论的一对范畴:实录与微隐
王先霈
(华中师范大学 文学院, 湖北 武汉 430079)
古代叙事理论的一对范畴:实录与微隐
王先霈
(华中师范大学 文学院, 湖北 武汉 430079)
实录和微隐是中国古代叙事理论的一对重要范畴,它们从历史叙事中产生,由先秦史家首创并得到后世众多史家继承,在文学叙事中得到发扬和发展。实录包括如实表达欲叙之事和如实表达叙事者的理念,《春秋》更偏重于理念,有时甚至以观念代替实事,造成偏向。微隐包括隐晦和微婉,《春秋》的微隐有一部分出于扩展其适用性的意图,一味从中挖掘微言大义的阐释则助长了牵强附会的索隐之风。《左传》开创了叙事的微婉风格,其后成为中国文学叙事最突出的本土特色。
古代叙事理论; 实录; 微隐; 《春秋》; 《左传》
中国古代叙事理论有一对范畴——实录和微隐,是构成中国叙事理论鲜明特色的两个重要支点。实录和微隐开始是从历史叙事领域产生,更具体地说,是由春秋时期的史官所首创,体现在《春秋》和《左传》中,后来,研究这两部史书的学者对其多有阐说,同时,也被文学叙事所采纳,成为文论家的重要资源,并多有发挥和创革。
一
作为叙事理论术语,实录最早见于班固在《汉书·司马迁传》里对《史记》的一段评述:“自刘向、扬雄,博极群书,皆称迁有良史之材,服其善序事理,辨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这段话为历代史家和史论家以及文论家屡屡称引。应劭《汉书集解》释实录为“言其录事实”,其实,远不是那么简单,实录不能仅从词义上去理解,而应探索、领会其丰富深刻的内涵。班固这一段评述原是采自他父亲班彪的《略论》,而班彪的思想又可溯源于孔子。《左传·宣公二年》在记晋国史官董狐书“赵盾弑其君”之后引孔子的话,“孔子曰,董狐,古之良史也,书法不隐……”不隐就是实录,就是将史事真相如实载之史书,既不隐善,也不隐恶。不隐善相对容易做到,叙事而不隐恶,要更加困难得多,直书恶与丑,往往会引起怨憎而遭遇强大的压力。故此,刘知几说,“若齐史之书崔弑,马迁之述汉非,韦昭仗正于吴朝,崔浩犯讳于魏国,或身膏斧钺,取笑当时,或书填坑窖,无闻后代……以验世途之多隘,知实录之难遇耳。”①他所列举的几位坚持实录的史家的悲惨遭遇证明实录之难于坚守,也表明实录成了中国史学和文学的传统,不是几个残酷的暴君所能扼杀。从孔子到司马迁、班固、刘知几以至其后,实录的第一层意思是,叙事者依自己所认定的理念和所掌握的事实来叙述事件,不因外界的胁迫或利诱而改变。这种实录精神最著名的榜样是春秋时代的两位史官——齐国的太史和晋国的董狐。所以,文天祥《正气歌》将“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作为古今正气的范例,这种正气乃是实录精神的灵魂。
实录为什么需要勇气甚至于需要以命相搏?因为历来许多谋一己及家族私利的权势者害怕实录。《孟子》谓孔子作《春秋》而乱臣贼子惧,《春秋》和上古众多史官之文,其著作之主要目的是要使当政者心存戒惧;无心从善的当政者既有所惧,便想要干预历史和文学的叙事,便要阻挠实录,实录常是在与权势的对抗中进行。《吕思勉读史札记》“毁誉褒贬”条举出若干例证说,当春秋之时,已有掩其实而不书者,有曲笔而乱其实者。②例如,《左传·文公十八年》记襄仲杀惠伯埋于马矢之中,而《春秋》不记此事,隐去了。杜预在注文里说,“惠伯死不书者,史畏襄仲,不敢书。”政治的强权极力掩盖某些人的恶行,千方百计不让它形之于文字,是很常见的现象。春秋时期,诸侯并立,每一诸侯的势力主要限于各自境内,此国史官不记,还有可能为他国史官记之。《左传·襄公二十年》记,卫国宁惠子临死之前,把儿子悼子叫到跟前说,“吾得罪于君,悔而无及也。名藏在诸侯之策,曰:‘孫林父、宁殖出其君’,君入,则掩之;若能掩之,则吾子也。”这是明白而直接地要求儿子替他掩恶,《春秋》在襄公十四年只记下“己未,卫侯出奔齐”,表明宁殖父子的掩盖行为确有效果。不过《左传》则是详细记述卫献公羞辱孙文子、宁惠子,他们发动政变赶走了卫献公,《左传》所依据的,可能就是卫国以外的诸侯之策,或者也可能是得之于故老口述。
到了秦汉以后一统天下,史官对皇帝、对统治集团主要成员的记述,更多忌惮,后代史家要认真做到实录,比春秋战国时期更加艰难,更加需要勇气。刘知几本为史臣,却上书辞官,原因之一就是:“孙盛实录,取嫉权门;王劭直书,见仇贵族。人之情也,能无畏乎!”③唐太宗想要亲览当朝国史,谏议大夫朱子奢上表云,“史官所述,义归尽善,若……庸君饰非护短,见极陈善恶,致怨史官,何地逃刑?”他劝皇帝不要干预史官对本朝的叙事。稍后,魏謩对唐文宗也表示了同样的意思:“臣以自古置此以为圣王鉴戒,陛下但为善,勿畏臣不书。如陛下所行错误,臣不书之,天下之人皆得书之。”“若陛下一览之后,自此文字须有回避,如此则善恶不直,如何遣后代取信?”④大多数皇帝不像唐太宗和唐文宗那样有所收敛,不肯给予史官较大的自主。但是,历代史家、文学家中,都不乏具有董狐精神的人。二知道人说,“盲左、班马之书,实事传神也;雪芹之书, 虚事传神也。然其意中,自有实事,罪花业果,欲言难言,不得已而托诸空中楼阁耳。”⑤他们在文学领域实践实录,凡是在文学叙事和历史叙事上留下辉煌成果的,大多是富有实录精神的作者。
二
那么,历来受到高度赞赏的实录,是否就仅仅是对于实际发生过的事件的如实叙写呢?这就引出了一个理论问题——叙事中主体性与客观性的关系,或者叫作事实与阐释的关系问题。以“赵盾弑其君”为例,《左传》记述道:董狐把“赵盾弑其君”的简文在朝会中向官员们宣示,赵盾说,你这样记载不符合实际,董狐回答,“子为正卿,亡不越竟,反不讨贼,非子而谁!”孔子后来评论说:“董狐,古之良史也,书法不隐;赵宣子,古之良大夫也,为法受恶,惜也,越竟乃免。”同样一个事件,董狐、赵盾和孔子,各有不同的叙述方案,各人有其所理解的实录。赵盾心目中的实录和董狐心目中的实录彼此对立,孔子想要加以调和,他既肯定董狐是良史,又肯定赵盾是良大夫,却更突出了叙事中隐藏的深层的内在矛盾,即主体评价与客观事实的矛盾。三个人都知道不是赵盾杀了晋献公,也没有任何根据说他指使别人杀晋献公。但是,董狐认为,赵盾身为正卿,在伦理上要为晋献公被弑负责,不是他杀的也等于是他杀的,应该记载为国君被他所杀。《春秋》很可能就是沿袭董狐对这件事的记载,其全文是:“秋七月乙丑,晋赵盾弑其君夷臯”。这样的叙述,用叙事者对人物行为的伦理评价,代替了对实际发生的历史事件的如实记录。在他们那里,实录首要是如实地表达叙事者对于事件性质的观点、理解、评价和阐释。《孟子·离娄下》说,《春秋》“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孔子曰,其义,则丘窃取之矣。”可见,孔子修史,把“义”,即他从历史记录中发现和注入的意义,放在最重要的地位。到了近代,陆续有学者对于这种做法提出质疑,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云:“历史的宗旨在于‘说真话,记实事’。《春秋》的宗旨, 不在记实事, 只在写个人心中对于实事的评判。”⑥这样一种对于实录的理解,历来有很大的影响力,且产生一些长久的弊端。
更早,唐代刘知几对《春秋》这种做法也曾有所非议,《史通·惑经》批评《春秋》说,“赵穿杀君而称宣子(赵盾)之弑”。以追责性的评价代替事实,是对实录原则的背离,无论其伦理评价正当和准确与否,都丧失了叙事的可信性。《春秋》重阐释而轻事实的倾向,对后世的叙事有很大的负面效应。胡适说,“《春秋》的余毒就使中国只有主观的历史”,⑦在这种叙事观念体系里,儒家伦理判断可以压倒对事实的尊重。
在历史叙事中,事实应该居于怎样的地位,史家对历史的评价和阐释又应该居于怎样的地位,修史者的主观评价与客观的史实应该是怎样的关系,这是中外史学关注的大论题;真实性和倾向性的关系,也是文学理论关注的大问题。二十世纪以来,西方史学就此发展出彼此对立的学派,文学理论中相关的论争也时常发生。“历史”这个词语(包括汉语的“史”和西文的“history”)具有两重含义, 其一是实际发生过的历史事件,或称历史1;其二是叙事者对于此种事件的叙述,或称历史2。历史1一经发生随即消逝,后人包括史家和文学家,所直接依据的只能是历史2。历史2以及人类所有各种对于客观世界的叙写、记录、描述,都包含有主观和客观两个方面。黑格尔在《历史哲学》导论中说:“在我们德国语言文字里,历史这一名词联合了客观的和主观的两方面,而且意思是指拉丁文所谓‘发生的事情’本身,又指那‘发生的事情的历史’;同时,这一名词固然包括发生的事情,也并没有不包括发生的事情的叙述。”⑧柯林武德《历史的观念》说,古希腊学者区分“两种思想类型”,即“真知”和“意见”,后者 “是我们关于世界的不断流变着的现实之不断流变着的认识”,是不可能被证明的;真知则是永远有效的,“它根据可以证明的推理并且可能通过辩证批评的武器来找出错误和扬弃错误。”⑨柯林武德这部名著所讨论的主题,正是历史的实际过程和史学家的思想之间的关系。晋献公被弑杀,这是确实发生过的客观事实,怎样描述、怎样看待这件事,则可能有多种角度、得出多种结论,从而产生多种文本。董狐注意的重心在表达“意见”,孔子赞扬董狐是良史,因为他主张历史的作用就是训诫,董狐的“书法”警戒所有的大臣负起保护国君生命以维护王权的全责。对于晋献公被弑,对于各种各样的事件,总是存在多种不同的“意见”。史家和作家如果只表达一种“意见”,而抹杀、回避其他的“意见”,并且还抹杀、回避与其他“意见”相关的事实,即便他坚持自己理念的精神颇为可敬,他叙事的真实性必定大大降低,从而他的历史的或文学的叙事的价值也可能就有了重大的缺憾。
叙事不应把意见与事实混淆,更不能以意见篡改事实。清代学者皮锡瑞严辨经史之异,正是这个意思,他说:“故‘春秋’一也,鲁人记之则为史,仲尼修之则为经。经出于史,而史非经也;史以为经,而经非史也。”又说:“经史体例, 判然不同,经所以垂世立教,有一字褒贬之文。史止是据事直书,无特立褒贬之义。”这番话切中儒家叙事观之弊,尊经轻史、重“意见”而轻事实,是长期存在的偏向。


三





实录关乎叙事内容,微隐关乎叙事形式,先秦史家开其端,后来的史家和作家有更多的推进,中国古人就此留下了丰厚的理论遗产和文本典范,需要我们深入挖掘提炼。
注释

②吕思勉:《吕思勉读史札记》,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218-220页。
④李昉等撰:《太平御览》第2718页,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王钦若编:《册府元龟》,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1555-1556页。
⑤二知道人:《红楼梦说梦》,一粟编:《古典文学研究资料汇编·红楼梦卷》,北京:中华书局,1963年,第83-84页。
⑥⑦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年,第84页,第84页。
⑧黑格尔:《历史哲学》,王造时译,北京:三联书店,1956年,第101页。
⑨柯林武德:《历史的观念》(增补版),何兆武、张文杰、陈新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22页。关于历史叙事中事实与阐释的关系,还可参看海登·怀特《历史中的阐释》一文,其中评述了黑格尔、德罗伊森、尼采和克罗齐的观点,也提及马克思、汤因比的看法,见海登·怀特:《后现代历史叙事学》,陈永国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第63-100页。




















责任编辑王雪松
Faithful Recording and Subtle Implicitness:A Pair of Categories in Ancient Narrative Theory
Wang Xianpei
(School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Central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Wuhan 430079)
Faithful recording and subtle implicitness are a pair of important categories in ancient Chinese narrative theory. Emerging from historical narration, they were initiated by the pre-Qin historians and then inherited by numerous followers of later times, thus developed in literary narration. Faithful recording covers not only what the narrator intends to narrate, but also the narrator’s ideas.SpringandAutumnAnnalslays more stress on ideas. Sometimes, it even replaces facts with ideas and leads to biases. Subtle implicitness includes implicitness and subtleness. InSpringandAutumnAnnals, partly with the aim of extending its applicability, it overemphasizes the exploration of deep meanings in subtle words, so as to encourage a tendency of far-fetched interpretation. While withZuoZhuan, an implicit style was started and later becomes the most typical narrative feature in Chinese literature.
faithful recording; subtle implicitness;SpringandAutumnAnnals;ZuoZhuan
2016-03-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