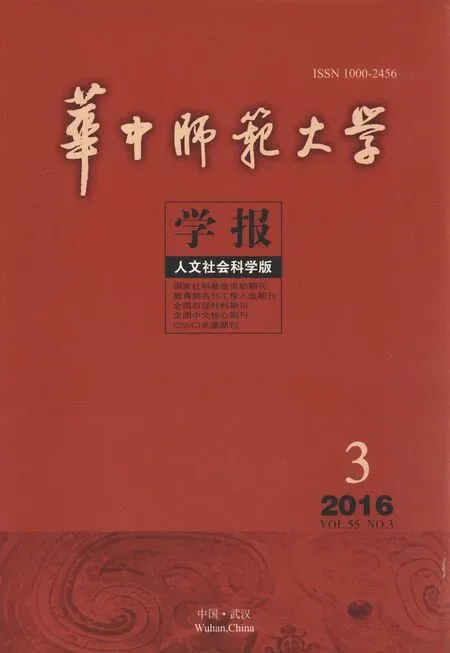小学德育教材中儿童德育境遇的转变及其伦理困境
孙彩平
(南京师范大学 道德教育研究所, 江苏 南京 210023)
小学德育教材中儿童德育境遇的转变及其伦理困境
孙彩平
(南京师范大学 道德教育研究所, 江苏 南京 210023)
本文通过对1981年以来6套小学德育教材的分析,揭示其中体现的儿童德育境遇的转变,并深入分析各阶段的伦理困境。德育教材中的“好儿童”内涵、主要德育资源与设计思路,是决定儿童德育境遇的三个关键因素。从思想品德教材时期到品德与生活(社会)教材时期,小学德育课教材中儿童的德育境遇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好儿童的内涵从“‘五爱’”转变为“过好自己的生活”,在德育过程中儿童由“聆听榜样故事”转变为“学过自己的生活”,教材设计思路由“聚焦儿童良心及其审查机制的建立”转变为“关注儿童现实生活问题的解决”。这两种德育境遇都包含着各自的伦理困境:前者为无思、无我、无生活,后者为自我中心的伦理立场、技术化的生活理路以及功利论的道德逻辑。认识到这些局限性,是深化德育课程与教材改革的重要前提。
儿童的德育境遇; 思想品德; 品德与生活(社会)
1981年,国家教委决定在中小学开设德育课程,开启了中小学德育课程与教材不断革新的历程,迄今,已走过35个年头。教材是学校教育过程的重要构件——尽管学界已有“后教科书时代”的倡议①,但到目前为止, “教教材”是常规课堂中最为普遍的做法——教材的设计思路,是影响教师课堂设计的主导线索与首要资源,进而也成为影响儿童德育境遇的重要因子。本文提到的儿童的德育境遇,是指教材设计中所体现的儿童生命遭遇或者生命境况。本文通过三个相互关联的角度对其进行定位与分析:(1)德育目标关注儿童生命的哪些要素(好儿童的设定);(2)德育教材用什么资源来影响儿童此生命要素(德育资源);(3)德育教材设计是如何对儿童此生命要素产生影响的(影响机制)。
本文尝试通过对自20世纪80年代起至今所使用的6套小学德育课教材的分析,勾勒35年来小学品德课教材中儿童德育境遇的变化,并分析其存在的不同伦理困境,为深化德育课程与教材改革提供新路径。
一、思想品德教材时期儿童的德育境遇
从1981年到2003年,中国小学德育课程的名称为思想品德课。在此期间,历经7次课程改革,小学德育教材也发生了一些变化,但整体而言,德育思路存在着内在的一致性,我们以此时期课程名称称之为儿童德育境遇的思想品德教材时期。对这一时期儿童德育境遇的考察,主要通过分析以下4套教材进行:1983年湖南教育出版社的《小学思想品德教育读本》,1988年人民教育出版社(1990年江苏出版总社重印)、1990年人民教育出版社和2001年江苏教育出版社出版的《思想品德》教材。
“五爱”好儿童1982年,国家教委发布了《小学思想品德课教学大纲》——这是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个德育教学大纲,1986年,发布了其修订版。《小学思想品德课教学大纲》(修订版)提出,小学德育的主要任务,是“通过以‘五爱’和‘五讲四美’为中心的社会公德教育和社会常识教育(包括必要的生活常识、浅显的政治常识以及同小学生生活有关的法律常识),从小培养学生社会主义国家公民应有的思想品德和行为习惯”②。 “五爱”的具体内涵为“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社会主义”,是在1986年9月28日举行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二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上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中首次明确提出的,此后成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基本要求。“五讲四美”具体指“讲文明、讲礼貌、讲卫生、讲秩序、讲道德”和“语言美、心灵美、行为美、环境美”,是1981年2月25日由全国总工会、团中央、全国妇联、中国文联、中国爱卫会、全国伦理学会、中华全国美学学会等9个单位联合发出的《关于开展文明礼貌活动的倡议》中明确提出的。到1997年,教育部发布《九年义务教育小学思想品德课和初中思想政治课课程标准(试行)》,重视德育教学方法的改进,提出要“紧密联系实际,生动具体地”对学生进行教育。在小学阶段,开始重视“文明礼貌、遵纪守法的行为习惯”的养成,但“培养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社会主义的思想感情”,“初步使学生在基本的思想观点与道德观念上具有辨别是非的能力”③,依然是这一时期的核心目标,是教育力图帮助儿童建构的对社会和国家的承诺,或者称为社会良心的主要内涵。儿童作为国家公民的预备人员,德育培养的好儿童必须具备以“五爱”和“五讲四美”为具体内涵的社会公德和社会常识等国家期待的思想道德素质。养成以上述内容为核心的社会良心,是这一时期儿童在德育过程中要实现的思想道德成长。
聆听榜样故事这一时期小学德育课教材的内容,是精心编选的人物故事。这里的人物主要包括两类,一类是榜样人物,即言行符合“五爱”和“五讲四美”要求的人, “五爱”和“五讲四美”的抽象内涵,通过榜样人物的具体言行表现出来;另一类是他者人物,是言行与榜样人物不一致、甚至相反或者相对的人物。课文通过榜样人物在故事中的言行,将抽象的社会善的标准具象化,以便学生理解和把握,为儿童树立“美好自我”的榜样,建立儿童良心中“善”的标准;同时,通过他者人物的形象,让儿童更形象地理解什么是坏的、应该受到批评的或者耻辱的言行,建立儿童良心中“恶”的标准。
这一时期教材中榜样人物,可以划分为三类:一是社会公认的英雄人物。这些人由于对国家在某方面的特殊贡献,已经成为公认的英雄或者杰出人物,在社会舆论中享有无限崇高的荣誉,具体包括革命领袖、革命英雄、各行业杰出的工作者,也包括历史上的杰出诗人、书法家、爱国将士等④。这些英雄人物,因为其突出成就、贡献而被树立为全社会的道德榜样,他们的光荣事迹(包括其童年的故事)被选入教材,成为儿童最主要的学习内容。这些榜样人物的故事在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德育教材中占有主导地位。
二是平凡的好儿童。这里的好儿童,是指在具体的事件中以“五爱”和“五讲四美”为标准指导自己言行的普通儿童,与学习者是近龄或同龄人。好儿童的故事,基本是出于教育的需要而编写,人物的名字多为虚构。由于故事主人公与学习者年龄相同或相近,加上是和学习者一样的普通儿童,因而平凡的好儿童的故事,对学习者具有更强的示范性和可学性暗示。这类故事在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前期常常独立成篇,在1999年苏教版的教材中,呈现方式略有变化:同一篇课文中,前半段讲英雄人物的故事,后半段讲与英雄人物事迹相似的同龄好儿童故事,作为儿童在学习英雄人物故事后的启示性行为,或者作为儿童将英雄人物故事转变到自己现实生活中的样例。这样的编排,显然是希望学习者将榜样故事进行现实迁移,把“好儿童”作为衔接“伟大的榜样”与“平凡的自我”的桥梁,从而缩短学习者与榜样人物之间的心理距离,以产生更有效的学习结果。
三是当代儿童(少年)英雄。这些儿童英雄,是当代的真人真事,因其在某些事迹中表现出了“五爱”和“五讲四美”这些值得赞扬的品质而被社会舆论关注,成为少年英雄。他们的事迹被选入教材,供同龄人学习。教材中出现的儿童英雄包括草原英雄小姐妹、舍身保护公共财物的张志新等。这类故事在教材中的数量并不多,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后,伴随着舆论对鼓励儿童舍生取义行为正当性的质疑,逐渐消失。另外,这些榜样对教室中的儿童产生道德感染力的因素,不是人物本身,而是人物在特殊情境中发生的特殊事迹,教材想突出的,是感人事迹中榜样人物所表现出的勇敢、坚强、机智、爱集体等优秀品质。
在不同时期的教材中,不同种类的榜样人物故事所占比例也不尽相同。整体看来,社会英雄人物与同龄伙伴故事,是21世纪前小学德育教材内容的主体部分。与榜样人物相对的他者人物故事有时独立成篇,有时会出现在榜样人物的故事中,作为榜样人物的对立面存在。不同于榜样人物多有具体而真实的名字,他者人物更多情况下会使用虚拟人物名字,有时也以第一人称或童话故事的方式出现。他者人物的言行,往往针对现实生活中儿童存在的错误言行设计,可以近似看作是儿童道德成长需要避免的现实状态。
形成内在的社会良心审查机制 教材除了通过课文中的榜样(他者)故事将良心的善恶标准具象化之外,也通过故事的叙述语气、情感倾向和氛围渲染,帮助儿童建立起榜样人物言行与光荣(荣耀)等积极的道德情感、他者人物言行与耻辱(羞愧)等消极的道德情感间的联系,为儿童的良心与自我审查机制的建立奠定初步的基础。
这一时期的教材,除了通过课文中榜样(他者)人物的生动叙事外,每篇课文后都配有数量不等的练习,以完成建立良心内在审查机制的任务。课后的练习,可以分为三个层次,对应从浅到深的良心审查机制建立的任务。
第一层次,通过问答练习,巩固良心的善恶标准。这类练习,主要通过提问的方式呈现,答案是课文中明确提到的一些榜样(他者)人物的言行,目的是加深儿童对这些言行的印象,固化学生良知的善恶标准,理解榜样(他者)人物的示范意义。如在《小学思想品德教育读本》(1983年,湖南教育出版社出版)中,《任弼时教女》课文后,“想一想”练习中的问题“任弼时爷爷对孩子们说了些什么话?为什么说‘现在不学将来没有用’”;在《小园画画》一课后,练习题中有“小园一张画也没有画成,你给他找找原因吧!”这些问题的答案就在故事描述中,要求学生通过练习重复学习过的课文内容,作用在于强调与加深“好的”与“坏的”印象。
第二层次,通过判断比较,强(内)化良心的荣辱标准,练习对他人言行的心理审查。这类练习的主要形式是判断,通过让儿童对故事中的他人言行或者是与其相关的、相对的言行进行对与错的判断和评价,引导学生进行深入地思考,强化或者进一步内化良心的标准与是非观念。这样的教学活动,是在引导学生使用刚建立的良心标准,练习审查他人或者案例中的言行,为下一步的自我良心审查活动做准备。
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类题目在教材中有一个从不多见到比较普遍的变化趋势,问题的设计也出现了从简单到复杂和逐步走向细化的发展过程。在20世纪80年代的教材中,这类问题设计比较简单,如在小朋友们帮李大爷扫雪的故事后设计的练习题是:“小朋友们帮助李大爷扫雪,不让李大爷知道,不图表扬。他们这样去做好事,你觉得好不好呢?”到1988年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的《思想品德》教材中,是非判断题就已比较普遍,设计的是非情境也更为复杂与多样化,不仅包括外显性行为的对错,还包括内在的思想状态,如《助人为乐》(雷锋的故事)一课后第二个练习⑤:
二、下面的想法对吗?为什么?
1.张静想:“我帮助别人,做了好事,也没有得到表扬,还不如不帮助别人做好事呢!”
2.宋军想:“我经常把别人的困难当作自己的困难,非帮他解决不可,否则心里不痛快。”
3.赵莹想:“老师教育我们要多帮助别人,我才不那么傻呢,如果别人做好事我也做,别人不做我也不做。”
4.罗明想:“做了好事之后,有人说我出风头,我还不如不帮助别人做好事呢,免得惹是生非。”
这一学习过程看上去更为复杂与精细,实际上是将面对同一事件时人的不同内心状态做了更为详细的分类呈现。但由于课文对所分析与判断的问题有明显而确定的答案,因而,多种状态只是多种错误,正确答案确定而且只有一个。因而,此部分教学的目的不在于让学生进行道德追问和反思,而在于强化和精细化课文中所传递的良心与荣辱标准。
第三层次,自我审查练习,并通过荣辱感进行行为调节。此部分练习的主要任务是引导学生把榜样人物与他者人物的言行与自身的言行进行对照性分析,将自己的言行分为善恶两类,将善的与荣耀感、恶的与羞愧感建立联结,形成个体内在的道德审查机制:当自己的言行、内在动机与善的标准相同或类似时,出现坦然、愉快、自豪与荣耀等感受,实现积极的自我认同;相反,则出现焦虑、内疚、自卑与羞耻等感受,发生消极的自我认同。通过将自己的言行与情感体验建立联结,利用人总是自然地趋向愉快的情绪体验、回避消极的情绪体验的本能,对个体思想与行为做出调节。
在《小学思想品德教育读本》中,在《小玛妮雅(居里夫人)的故事》课文后,设计有“想一想”问题:“和小玛妮雅(居里夫人)对照一下,你在学习上是不是十分专心”;在《雷锋的故事》课文后,设计有练习题:“你怎样学习雷锋从小就乐于帮助别人的好思想、好品德?”“你们班上能不能做到,个个参加学雷锋小组,人人都戴小红花”;在《诚实的小岸英》课文后,提出问题:“小岸英很诚实,你怎样做个诚实的孩子呢?”这类练习,不同于前面两类强化标准与对他人言行的判断,直接指向儿童自我的言行,指向儿童良心自我审查机制建立这一环节。这是道德教育想要达到的最高境界——自律人格必须具备的内在道德心理机制。
更重要的是,这个看上去是个体化的道德心理发生的机制,当其在教师和青年一代中通过统一的课程标准、统一教材、大班授课、同质化教案——教学设计思路相类似的教案,常常通过赛课、提高课堂效率与质量等方式传播——被广泛地、反复地进行时,儿童就形成了同样内涵的价值标准与类似的情感倾向。进一步,这些持有相同道德感的人之间由于价值共契和情感共鸣而自然产生出内在的亲近倾向,从而一定程度上形成群体认同,实现群体范围内的价值团结与统一。在这样的德育过程中,儿童比较容易建立起明确且深刻的社会善恶标准,在社会良心标准与荣辱感间形成鲜明而强有力的内在联系,而且,因为这些善恶标准和情感倾向有较稳定的内在良心审查机制为依托,不容易改变与偏移。
然而,在这一时期,儿童的德育境遇存在着一定的伦理困境,这也是其最终被超越的原因之一。
二、思想品德教材时期儿童德育境遇的伦理困境
无我的良心关注良心,是中国传统文化中进行自我修养的重要内容。孔子在《论语·里仁》中强调,“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王阳明则明确地指出,良知乃“天命之性,吾心之本体”,把良心看作是待发掘的善端,因而倾向于内省式道德建设路线。关注良心及其审查机制的建立,是中国传统道德教育的重要特点,也是巩固传统社会文化统一性的重要而有效的方式。但是,在上述儿童自我良心审查机制的建立过程中,并没有把良心看作是儿童天性中已有的因素,或者说,教材遗忘了儿童具有善的天性,忽视了儿童主体性在社会良心建构中作用。这一时期的德育,立足于社会的期待与国家的立场,课文中的榜样人物多以国家和社会的成人为原型,把现实生活中的儿童的错误言行作为他者人物的原型,这意味着,儿童总是作为杰出与英雄人物的对立面存在,儿童在现实中的言行总是需要克服与矫正的。课文把社会赞赏的善恶标准作为有待儿童接受的良知内容,通过榜样人物故事植入儿童内心,以对儿童的错误言行的改造与放弃为前提,要儿童发出“如榜样般活的承诺”。
无思的判断教材中设计有引导儿童进行对错判断的练习,但这种判断,不是建立在思考、特别是批判性反思与追问的基础上,而是以道德晕轮效应与偶像崇拜心理为基础的。教材采用榜样人物故事进行思想道德教育,不仅是要通过榜样人物言行将社会期待的善恶标准具象化,还因为这些社会榜样人物故事可以产生出道德晕轮效应。因为这些榜样人物在某些方面的杰出表现,社会将其言行崇高化,因而他们在道德上也成为被崇拜的对象,这便是道德晕轮效应。这一扩大化的精神崇拜倾向使榜样人物的生活与工作态度、方式、做法以及童年时代的故事等具有了极大的精神感染力与示范性。教材采用这些榜样人物故事,借助社会精神偶像效应,让儿童不加思索地产生出对榜样人物的向往和追求,而不会去反思和追问榜样人物言行的价值合理性。当然,小学德育教材选用这些素材本身,也生产、助长和延续甚至强化这些精神偶像效应。
无生活的道德课文中讲述榜样(他者)人物故事的目的,并非是为了让学生了解榜样人物的完整生活,而是为了凸显德目,如自立自强、爱祖国等。为了实现凸显德目的目的,故事往往选取比较独特的生活和社会情境,如异常艰苦的环境或者国家遇到特别困难等极端情境,这导致榜样人物言行发生的实际情境与儿童日常生活情境间实现顺利迁移的困难。儿童可能懂得了一个道理,理解了一个德目,可能也承诺在类似的情境下作出英雄式地行为,但他的现实生活中不太可能遇到故事中英雄人物遇到的情境,因而,也就不容易在自己日常生活情境中找到实现这个德目的机会。课文中的榜样人物多为成人而非儿童,这一身份差距,也部分地阻碍了儿童将所学善恶运用到实际生活中,这是德育出现知行脱节的根源之一。所以到20世纪90年代后期,教材在讲述榜样人物故事后,再续讲平凡好儿童的故事,目的就是提供更加接近儿童生活情境的榜样,促进迁移的实现。
综上所述,思想品德教材时期“五爱”好儿童的养成,通过讲述榜样人物和他者人物故事的方式,具象化“美好自我”与“邪恶自我”,以此使儿童接受社会推崇的善恶标准;通过课文与多种形式的练习,将此善恶标准巩固、内化⑥到儿童的精神无意识状态,成为儿童自己的崇高理想与道德标杆——良心;通过德育过程,帮助儿童形成不断将自己与良心对照的审查机制,实现对儿童的精神塑造。在这个过程中,儿童被置放在英雄与杰出人物的宏大叙事中,其自身的现实生活与需要被忽略,不被鼓励进行真正的思,只被要求做出忘我的、如英雄般活的承诺。
自由是道德的前提,在自由的前提下,意志是朝向道德的力量。没有自由的思,没有对现实的生活情境的考量,缺少了对儿童内在向善主动性的尊重,“善”的教育本身的价值正当性就成了需要追问的问题。尼采曾把“驯养一只可以许下诺言的动物”看作是人“为自己提出的两难任务”⑦,可以说,思想品德教材时期的小学品德课便是致力于完成这样一个两难任务。
到20世纪90年代末期,随着主体性教育思潮的滥觞,儿童在德育中的这种“无我”“无思”“无生活”的状况已广为诟病。在解放儿童、尊重儿童的进步主义思潮下,中国儿童的德育境遇迎来了巨大的历史性转变时期。
三、 品德与生活(社会)教材时期儿童的德育境遇
2002年5月,教育部颁布《全日制义务教育品德与生活(社会)课程标准(实验稿)》,2003年秋,依据新课程标准编写的15套《品德与生活》《品德与社会》教材进入课堂,德育教材出现一纲多本的现实局面。我们将这一时期称为儿童德育境遇的品德与生活(社会)教材时期。2003年至今,小学德育课程的名称由原来的“思想品德”修改为1到2年级的“品德与生活”和3到6年级的“品德与社会”,课程的性质由原来的学科课程改为综合课程,相应地,教材的设计方式和指导思想发生了重大转变:生活化、活动性与综合性成为这一时期教材的普遍特点,生活德育成为主导的德育思路。
这一时期,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的教材依然占有半数以上的市场份额,具有广泛的代表性;江苏教育出版社(联合中国地图出版社)出版的教材在教育研究中有较大的影响,其核心编写人员是新课程标准的积极参与者,也是生活德育理论的积极倡导者,更准确地把握了新课程标准的指导思想,更能代表新课程的指导理念。因而,对这一时期的教材分析,以人民教育出版社和江苏教育出版社出版的教材为主要考察对象。

教材内容的编排逻辑,也基本改变了按德目排列的方式,而是依照儿童生活事件的发生顺序和儿童不断扩大的心理视野排列。如人教版教材的第一册,包括4个单元的内容:“我上学了”,“祖国妈妈,我爱您”,“我的一天”和“过新年”,分别对应儿童生活中的重要事件:上学、认识新的生活环境、国庆节、过好学校生活的每一天、过新年——一个重要的节日。在每个事件(单元)下,再分划更细的教学目标,如在上学、认识新的生活环境中,进一步分设认识自己的新角色(我背上了新书包)、辨识学校生活的制度化标志——铃声、认识学校中的新朋友(新朋友,新伙伴),以及认识上学的路及主要的交通标识(上学路上)。同时,“我的不断扩大的心理视野”成为教材中生活叙事发展的线索:我的成长——我的学校生活——我的家庭生活——我的家乡(社区)生活——我的国家生活——我的世界生活。
“过好”生活的好儿童在这次课程改革中,经验论的道德主张得到广泛的认可。通过引导儿童解决自己现实生活中的问题,让儿童过上好生活,从而成为好儿童,这一思路明确而清晰。相应地,教材出现了两个明显的转变:

在人教版小学一年级第一册的教材中,“我的一天”是对学生的日常生活进行引导的主题单元,包括“和钟姐姐交朋友”、“我很整洁”、“我会好好吃”、“我自己会整理”、“看我多精神”5课(本册共13课),这些课文的主题就是在教学生如何整理好自己的书包、图书、玩具、床铺、抽屉等日常生活用品。“整理好”的标准是方便、整齐,策略包括参照课程表整理书包,用完东西放回原来的地方。课文最后用总结性儿歌提示儿童:这样做会得到爸爸妈妈的夸奖。可以看出,教材的主体内容由原来侧重讲道理转向了教生活技能和自己生活的需要。


对话和参与德育过程的儿童改革后的教材,成为儿童文化的世界。改革后的德育过程,不再是单向地针对儿童内在良心的形成与改造过程,而是需要儿童作为主体参与的对话过程。
在呈现方式上,世纪初的教材突破性地采用了图文并茂的叙述风格,成为适合儿童的文化读本。针对中低年龄段儿童,教材呈现方式由原来的课文加插图的方式,转向了通过情境图表达的“图说”方式,教材的主角是包括卡通人物、童话人物、现实生活中的同龄儿童在内的为儿童熟悉和亲近的人物,使得教材成为吸引儿童的学习资源。教材选用了多种适合儿童阅读、深受儿童喜欢的儿童文学体裁。低年龄段儿童教材中出现了大量的儿歌、童谣、谜语,中高年龄段儿童教材中出现了童话故事、美文欣赏、儿童日记、儿童作品等,使教材洋溢着浓厚的童趣和童真,充分体现出适合儿童和为了儿童设计的学习材料的特点。此外,教材中设计的活动也都是儿童喜欢的参与式活动,如猜谜语、唱儿歌、角色扮演、辩论赛、探秘发现、故事会等。通过以上努力,教材为儿童创造了一个自己的文化世界,儿童在学习这样的教材时,就相当于在自己适合并喜欢的文化中旅行。

四、品德与生活(社会)教材时期儿童德育境遇的伦理困境
在上述梳理中,我们看到35年来儿童德育境遇的巨大转变——从“五爱”好儿童到“过好”生活的好儿童,儿童作为受教育对象,在德育过程中由一种“无我”和“无思”的状态,转变为认真思考自己生活并改进自己生活的行动者,这一转变对中国德育和儿童发展的意义是不可估量的。站在深化课程改革的立场上,反思新课程改革中存在的问题与不足,我们发现:世纪初德育课教材“回归生活”的巨大热忱和对儿童权利的极度高扬,放大了教材对“我”的生活的关注,特别是对“我”的生活感受、生活技术与问题解决策略的关注,导致教材在突出“我”时不同程度地忽视了“他者”,在突出“我”的生活感受、生活技能与问题解决策略的同时,存在着对生活事件背后意义与价值挖掘不够的问题,加上以结果为导向的功利论道德思维的普遍存在,使得德育课的教材与现实课堂中非常容易偏向“自我的生活技术”教育,忽视德育课对儿童内在精神世界的关照。这显然不是课程标准中期待的“会过生活的好儿童”。
“自我中心”的伦理立场德育课教材回归儿童的现实生活,是我国德育的一个重大转向,实现了亚里士多德所说的德行是“属人的善”的道德立场。但是,在“回归生活”的旗帜下,世纪初的教材存在着对“我”的关注过度,在一定程度上忽略“他者”的“自我主义”倾向。
毫无疑问,回归自我,相对于关注被树立的道德理想榜样而言,是道德回归现实生活世界的落脚点,或者说支点,是启动属于人的道德与意义的坚实基础,但肯定不是全部。这个基础不是终点,而是走向更完满的“我”的起点,这个完满的“我”,是要通过“我”的普遍性的不断提升而获得的。“我”的普遍性的提升,则需要通过把各种“他者”不断融入自我来实现,各种“他者”不仅包括与自我不同的他人,也包括与个体不同的群体,甚至与人不同的自然,从而实现自我与他人、与宇宙的合一,通过意义的不断找寻,实现对道德价值的超越,从相对的自我出发,走向更为普遍的精神世界。
世纪初的教材中对“自我”过度强调,超过了其只是整个意义和精神世界的支点的限度,有把“自我”等同于“我”,将基础当作了整个目的的嫌疑。这种“过度”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我”是整体教材展开的视线。如前所述,“我的生活”是教材的主题,这是教材中最为明显的一个自我视线锁定,这当然是由于关心“我”成长而采用的一种技术路线,同时,教材的整体线索,沿着不断扩大的“我”的视野展开,从我的成长,到我的家庭、学校、社区、国家与世界,固然可以说遵循了儿童道德心理发展的规律,但这是一个同心圆的扩展方式,“我”是这个图谱的核心。从“我”与世界发生联系的方式与接点理解世界(如教材课文标题“有多少人为了我”),成为教材常见的引导方式,也不可避免地助长“自我中心”的思维,这是后现代伦理学所批判的“我”的伦理思维的典型特点。
在7.26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指出:“我们要按照党的十六大、十七大、十八大提出的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各项要求,突出抓重点、补短板、强弱项,特别是要坚决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精准脱贫、污染防治的攻坚战,坚定不移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动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使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得到人民认可、经得起历史检验。”[1]63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过程中,哪些才是重点、短板和弱项呢?这要分几个层次来看。
另一方面,教材中对各种“他者”的他者化态度,进一步强化了“自我”,弱化了“他者”,也弱化了他者对“我”的普遍性提升的可能。世纪初的教材,在综合课程的概念下存在着把本课程理解成多个学科知识拼盘化组织的倾向,从而使得教材中明显存在着科学课、生活课、道德课、历史课、地理课的分化思路与痕迹。在教材的编写思路中,把生活当作科学认识和把握的对象;把自然当作外在于自我,甚至是安放自我的一个容器;把历史看作过去发生的事件的集合,是在过去的生活中存在过了的客观事实,因而把品德与社会课中的历史课当作历史知识的学习课,将“我”的生活、环境、过去都他者化成一个与“我”相分离的存在体系,是自我了解、认识从而把握与改造的对象,自我是世界的主体,世界是“我”的客体,认识与了解的目的,是以“我”为中心对它们进行改造,而不是自我精神融入意义世界普遍性的提升。
技术化的生活理路虽然世纪初的德育课教材内容主题上呈现了向生活转向的面貌,但这只是回归生活的第一步。要实现儿童从生活中学习,通过学过好生活,实现做个好人的教育目的,更重要的是教会儿童以什么样的态度对待生活,用什么样的思路来看待人与人间的关系、人与世界的关系以及各种生活事件。世纪初的教材,在内容设计的思路上存在着明显地把“生活事件”当作“科学事件”与“技术事件”的倾向,如在上文我们分析过的“我掉了一颗牙”等教材(教学)设计中,表现出明显的科学认识主义倾向;“我自己会整理”课等则表现出对生活技能与问题解决策略的技术主义偏重,这种技术主义的思路,甚至也贯穿在对儿童心理的引导中。如在“做个‘快乐鸟’”一课中,教材分为3个环节:一是回顾生活中的快乐体验,二是总结生活中不快乐的体验,三是寻找让自己和他人快乐的方法。这个思路是把“快乐生活”作为目的,快乐方法是课堂的核心内容,课堂的重点在于引导孩子学会释放和转变消极情绪的方法。从教材中列出的方法看,“听音乐”、“跟爸爸妈妈说说”、“好好睡一觉”、“看动画片”等都属于心理调适的策略,但缺少了对不快乐和快乐本身的反思性辨析,没有引导学生对哪些是值得快乐的事、哪些是不应该伤心的事进行初步辨析。而事实上,这一时期的孩子的不快乐,大概可以分为两类:一是由于自己的某些需要没有得到满足,如想到一个什么样的玩具;二是遇到了自己不能解决的困难,如受到小朋友的欺负。课堂上如果不对这些不快乐本身进行是非判断,不对导致不快乐的原因做初步分析,只教儿童心理调适方法,无疑是一种消极的情绪调节教育,缺少了对学生情感方向的指引。

至今,新世纪的课程改革已经走过了15个年头。回望改革的路,我们为此次改革中儿童德育境遇的历史性转变而自豪。同时,我们也要认真面对改革中出现的问题,在批判性反思的基础上,在未来深化课程改革与教材的编写过程中,进一步引导儿童超越自我中心的狭窄视野,突破功利主义的道德逻辑,建立与他人和世界、与历史和谐共在的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实现对自我的不断超越,学会从日常生活事件中理解意义和价值,过更为完满的生活,走向更为幸福的人生。
注释
①以崔允漷为代表的学者,近年来一直在倡导基于课程标准的教学与课程设计,提出了“后教科书时代”概念,以推动教师在教学设计中的主体性与以学生成长为核心的教育目标的实现。
②国家教委:《小学思想品德课教学大纲(试用版)》,《课程·教材·教法》1982年第3期;国家教委:《小学思想品德课教学大纲(修订版)》,《课程·教材·教法》1986年第3期。
③《九年义务教育小学思想品德课和初中思想政治课课程标准》,《学科教育》1997年第6期。
④这时常出现的榜样人物有:任弼时,周总理,雷锋,列宁,小岸英,卓娅,王羲之,恩格斯,陶铸,夏明翰,吉鸿昌,毛泽东,朱德爷爷,竺柯桢,华罗庾等。
⑤《思想品德》(第10册),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8年,第15页。
⑥在21世纪前,德育中内化论的观点很流行,如在当前德育界很有影响的德育著作《德育新论》中,王逢贤先生将这种内化论发展为双层转化论。
⑦尼采:《论道德的谱系·善恶之彼岸》,谢地坤等译,桂林:漓江出版社,2000年,第37页。
⑧鲁洁:《德育课程的生活论转向——小学德育课程在观念上的变革》,《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科版)》2005年第3期。







责任编辑曾新
The Changes of Textbooks of Child’s Moral Education in China and the Ethical Dilemma
Sun Caiping
(Research Institute of Moral Education, Nanjing Normal University, Nanjing 210023)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6 series of textbooks of child’s moral education in China, this paper reveals the changes of child’s educational conditions and the ethical dilemma of each period. It argues that, from the period of “Ideology and Morality” to the period of “Morality and Life(Society)”, the connotation of “good child” in the textbooks has changed from “Five Loves” to “Living Good Life of Oneself”; the educational topics in the textbooks have changed from the stories of social examples to events happened in child’s daily life; the thinking of the textbooks have changed from constructing child’s mechanism of social consciousness to focusing on the solution of problems in child’s daily life. It also analyzes the ethical dilemmas in the two periods. Understanding the ethical dilemmas is the important premise for child’s moral education reform.
child’s moral education; Ideology and Morality; Morality and Life(Society)
2016-01-06
教育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招标课题“现代生活方式与道德教育”(11JJD880020);江苏省2011计划:基础教育人才培养模式协同创新中心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