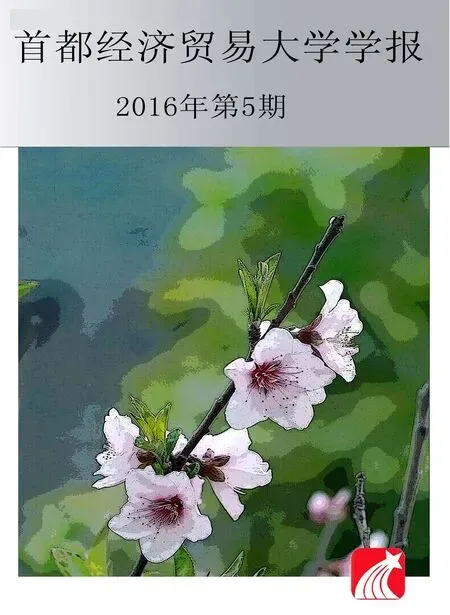不同年龄层次收入与主观幸福感关系研究
刘 彤,胡永健
(天津财经大学 经济学院,天津 300222)
不同年龄层次收入与主观幸福感关系研究
刘彤,胡永健
(天津财经大学经济学院,天津300222)
以中国居民营养与健康调查(CHNS)数据为基础,在恰当的理论假设下,可通过实证分析研究城乡居民不同年龄层次收入和主观幸福感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居民收入对主观幸福感存在正向影响,即随着居民收入的增加,主观幸福感会随之提升;在年龄方面,随着年龄的增加,幸福程度先下降后上升。这些研究结果为政府制定相关政策以进一步增加居民收入、改善人民生活水平并提升居民的主观幸福感提供了依据。
主观幸福感;收入;年龄
一、问题提出
近年来,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城镇化进程的快速推进,构建和谐社会、提高城乡居民主观幸福感已经成为中国政府所追求的重要施政目标。城乡居民对当前经济环境下的生活水平是否感到幸福以及影响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因素有哪些一直以来都是很多学者想要探究的问题。本文致力于从经济学角度研究主观幸福感,并针对其中主要影响因素收入情况来解释不同年龄层次收入与幸福感之间的联系。
关于财富与幸福是否相关这个论题,最早的理论来源于古希腊著名的政治家梭伦,他曾经断言:“很多拥有大量财富的人并不幸福,但很多只拥有中等财富的人却是幸福的”。伊斯特林(Easterlin,1974)也认同此观点。他最早提出“伊斯特林悖论”,认为国民收入与主观幸福感的关系并不强:一个国家中富有群体的幸福水平是要比贫穷群体高的,可是如果进行空间上的跨国比较,富裕国家和贫穷国家的幸福水平相差并不多[1]。
目前,已有很多学者对收入与幸福感之间的关系做了研究。伊斯特林(2010)针对同一国家内居民的收入水平与主观幸福感作出的研究表明:短期内收入的增长与人们的主观幸福感之间存在正相关的关系,但从长期来看(10年以上),收入与主观幸福感之间并无明显关系[2]。曹大宇(2009)利用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数据总结了绝对收入与相对收入分别对幸福感的影响,结果表明,绝对收入并不总是正向地影响幸福感,当收入水平达到某一临界值时,收入增加可能会导致幸福感的下降。当加入相对收入变量参与分析时,绝对收入对幸福感的影响变小,但相对收入效应也会因参考体系的差异如不同地域或不同收入水平等条件而有所区别[3]。张学志和才国伟(2011)也认同此观点。他们认为收入与价值观是影响幸福的重要因素,其中绝对收入与幸福感存在正向作用,并与之呈倒U型关系,但加入相对收入的效应之后,绝对收入对幸福感的作用不再显著[4]。邢占军(2011)针对2002—2008年6个省会城市长达7年的调查数据研究后得出结论:在现阶段,收入与幸福感的确存在一定的正相关关系,而地区富裕程度的不同对两者关系也产生影响,换句话说,高收入群体幸福感程度的确高于低收入群体,但居民的幸福指数与国民整体收入增长并无明显联系,而且地区富裕程度与居民幸福感也基本无关[5]。徐广路和沈惠璋(2015)研究认为,幸福感对低收入人群和高收入人群的影响不一致,由于已经满足了较低层次的需要,幸福感对高收入人群更为重要[6]。此外,刘苓玲等(2015)研究了养老金待遇对老年群体幸福感的影响[7]。
总体而言,无论是伊斯特林的幸福悖论还是之后学者们探讨的各种幸福指数模型,收入无疑是对幸福感影响最大的因素,而且其他相关因素如性别、年龄、婚姻状况等都对二者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毕明和孙承毅(2003)通过对山东省17个城市调研分析,发现居民幸福感存在明显的年龄差异[8]。基于此研究,本文将侧重点集中在年龄层次方面。本文的研究目的,是通过将年龄分层,探讨不同年龄层次的城乡居民其个人收入与主观幸福感的关系,并对其他影响因素做简要分析。本文的研究具有一定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有助于政府针对不同年龄阶段的人群提出不同的政策安排,以提高城乡居民的主观幸福感。
本文剩余部分安排如下:第二部分对核心变量做解释说明;第三部分根据理论分析提出研究假设;第四部分说明数据来源及主要变量;第五部分为实证分析及结果;最后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二、核心变量的概念
本文首先对核心变量进行解释说明,避免后文实证分析中出现歧义。
(一)个人收入
个人收入,指个人以任何形式获得的收入总和。除基本工资之外,通过出租房产、买卖证券产品、申请国家或者社会救助等渠道获得的收益都包含于个人收入的范畴。利用该指标,可以评价个人经济状况和生活水平。
许多文献中,个人收入被分为绝对收入和相对收入。简单来说,绝对收入水平就是“量”的实际增长,即收入越高越幸福。但实际情况是,不同国家,不同时期,不同城市,收入水平的大幅度增长,并没有带来幸福感的提升。如果是相同的经济体,在其他各方面因素对等的情况下,收入高的个体将更具幸福感。罗楚亮(2009)以中国居民住户调查数据为基础,提出绝对收入与主观幸福感具有正向关联,但并不十分显著,而相对收入相比绝对收入对幸福感的影响更大[9]。为了方便研究,本文研究的收入主要包括以下几个部分:居民工资收入和奖金以及其他收入(房租、利息等)。把以上几个部分相加之后,根据家庭的统一编码,按照家庭人口数平均,求得家庭人均收入,作为本文实证研究的自变量之一。
(二)幸福感
对于幸福的理解,不同学科给出了不同的含义,心理学从人格层面上考虑幸福;哲学从道德层面上考虑幸福;生物学认为幸福是化学过程的结果;而社会学则认为幸福是一种社会环境。因此,对于幸福的定义颇为困难。幸福通常可以理解为:人们在经历某事过程中由于从中获得快乐与满足而产生的喜悦情绪。心理学更倾向于这种定义,它表示幸福是人们心理获得满足而产生的主观意识。因此,现代有很多专注幸福研究的学者将幸福定义为主观幸福感,即指个人对自身生活质量作出的主观评价。每个人有不同偏好,因此对幸福的界定不甚明确。但主观幸福感被大多数心理学家和经济学家所采用,本文继续沿用此定义,并将主观幸福感作为本文实证分析的因变量。
三、理论分析及假设
在效用论中,效用是指商品对人的欲望实现的衡量,或者说,效用是指消费者在进行消费时所感受到的满足程度,而预算线表示,在一定的消费者收入和商品价格前提下,消费者所能够获得的商品组合[10]。在经济学中,将主观幸福感定义为“效用”,即个体所感受到的幸福程度。当简化假设时,效用作为因变量,收入作为自变量,收入的增加会使得预算线向右上方平行移动,新的预算线会和右上方更高的无差异曲线相切,切点在更高位上,即个人获得了更高的效用。根据理论进行推断,可以认为当收入增加后,消费者进行决策时会获得更高的效用,即更大的主观幸福感。
以上理论分析只是基于严格意义上的经济学理论分析,然而,主观幸福感毕竟是一种主观上的感受,不能只从狭义角度出发。从广义的角度出发,主观幸福感很难进行准确的量化,并且在不同时期,不同地区呈现出很多变化的维度。主观幸福感作为经济学、心理学、社会学交叉学科的概念,受很多因素的影响。从个体人口特征角度而言,年龄、性别以及婚姻质量均会对主观幸福感的大小产生影响;从社会角度而言,主观幸福感也会因为教育程度、职业高低、法治程度、民主权利等因素的不同而产生差异;从个体心理角度出发,性格特征、生活态度、交际能力则会在主观精神感受上发挥作用;同时历史文化因素也不容忽视,价值观念、传统习俗也会赋予主观幸福感更丰富的内涵和表现形式。
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假设: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个人收入的增加会使主观幸福感上升,但其幸福感增加的幅度会变小;如果考虑年龄因素,那么随着年龄越来越高,个人收入的增加会同步影响主观幸福感的提升,但各年龄阶段,其增长情况未必一致。
四、数据来源与变量选择
(一)数据介绍
本文数据来源于中国居民营养与健康调查(以下简称CHNS)。该数据库是由美国北卡罗来纳大学人口中心与中国营养与食品安全所一起采集完成。CHNS数据采用多阶段随机抽样方法,其样本覆盖了中国9个省的城市和农村地区,内容涉及城乡居民的营养健康、饮食行为、家庭经营活动等微观信息以及经济发展、公共资源和健康指标等宏观信息。在空间跨度上,涵盖的省份分别代表了中国东部沿海、中部、东北和西南四个不同经济发展水平的地区,一定程度上可以反映中国居民的地区性差异;在时间跨度上,从1989年到2011年跨度了20多年,为城乡居民的相关分析提供了有力保证[11]。由于该数据库包含劳动力市场研究所需要的家庭及个人特征等重要变量,因此本文采用CHNS数据进行实证研究。
调查数据中关于幸福感的问题是“你认为你现在的生活怎么样?”,受访者在1到5的数字中选择,1表示“很好”,2表示“好”,3表示“中等”,4表示“差”,5表示“很差”。本文以此问题为依据定义变量happiness用以度量居民主观幸福感。考虑到选项5“很差”选择人数较少,在估计模型的过程中,可能会出现问题,所以,本文将“很差”归到第四个选项的分类。通过将变量关系进行升序调整并编辑整理后,分类如下:1= 不幸福,2= 一般,3= 幸福,4= 非常幸福。
(二)主要变量
影响幸福感的因素很多,也很复杂,任海燕(2012)认为幸福的影响因子包括收入(具体内容包含绝对收入、相对收入及收入的不平等)、失业和通货膨胀、政府支出、城市化进程、环境问题、社会资本和社会规范水平[12]。罗楚亮(2009)则是从城市农村分布情况、人口流动等方面着重分析绝对收入和相对收入对幸福感的影响[9]。李青青(2011)分两个层次讨论:宏观经济层面包括收入、失业与通货膨胀;微观非经济层面分类众多,包括性别、婚姻状况、受教育程度、工作满意度以及社会关系等[13]。樊丹花(2013)综合社会学和心理学等领域的知识,将幸福感的影响因素分为人格及社会人口学因素、经济因素、制度因素、环境因素和社会关系因素[14]。由此可见,幸福感的影响因素分门别类,关系复杂。
本文借鉴这些研究文献的思想,将主要变量分为个体特征变量和家庭整体变量。其中,个体特征变量包括性别、受教育程度、年龄、健康状况、婚姻状况、职业及职业类型等;家庭整体变量包括家庭人均收入,户口所在地(城市还是农村)。
本文研究对象是不同年龄层次收入与幸福感的关系,因此对年龄进行人为分类。其中,以是否可参加工作作为是否具有收入的标准,16岁以下不予考虑,16~30岁作为青年组,31~45岁为中年组,46岁及以上为老年组。
五、实证分析
(一)建模理论基础
本文中,因变量为主观幸福感,在统计上称为“有序数据”,故采用有序Logit模型:
假设存在一个不可观测的潜在变量(latent variable):
y*=x′β+ε
(1)
式(1)中,ε为随机扰动项,x为自变量。
虽然y*是不可观测的,但可以观测到y值;在这里,y*相当于变量happiness。
变量happiness的结构和选择规则为:
(2)
式(2)中的r0、r1、r2、r3为待估计参数,被称为切点(cutoff points)。
假设ε服从Logistic分布,则有序Logit模型可以由下面的方程表示:
(3)
式(3)中,J=1,2,3,4;等式左边,表示发生某一事件(如回答,“非常幸福”)的概率的大小。本文使用统计软件Stata来估计(3)。
本文研究目的在于,基于Logit模型原理,将居民幸福感作为该模型的因变量,选取的各种指标作为自变量,得出一个有序Logit回归分析模型,根据所得模型研究影响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因素,并根据不同年龄层次研究收入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最后提出相关政策性建议。
(二)模型建立与分析
本文将年龄和收入等连续变量分段离散化,表1为有序Logit模型的估计结果。其中模型1为研究居民收入和主观幸福感的整体计量模型估计结果;模型2为从青年组角度研究居民收入和主观幸福感的计量模型估计结果;模型3为从中年组角度研究结果;模型4为从老年组角度研究结果。

表1 居民收入与主观幸福感计量模型估计结果

表1(续)
注:*、**分别代表在95%、99%置信水平下待估参数显著不为零。
1.整体评价
从模型1的估计结果中可以看到,年龄、疾病、职业以及职位类型与主观幸福感的估计系数为负数;城乡、性别、婚姻状况、家庭平均收入及受教育程度与居民主观幸福感的估计系数均为正数。这表明:在城乡方面,与城市相比,生活在农村的人更容易感到幸福;在年龄方面,随着年龄的增长,幸福感先降低后增加;在性别方面,男女差异不明显,但总体来说,女性较男性更容易感到幸福;在婚姻方面,已婚人群的幸福感更加强烈;在患病方面,近期未患病即身体健康的人更容易感到幸福;在受教育程度方面,受教育程度越高,人们越容易感到幸福;在职业方面,与白领相比,技术工人、非技术工人以及农民的幸福感是逐渐下降的;在职位类型方面,与个体经营者相比,长期工、合同工以及临时工的幸福感水平是逐渐降低的。
在收入方面,居民收入和主观幸福感的估计系数为正,说明随着居民收入的增加,居民感到幸福的概率会逐步提升。即在其他条件相同的前提下,同一地区,相同性别并且具有同样教育水平的两个个体,收入水平较高的个体同收入水平较低的个体比较而言更容易感到幸福。袁正等(2013)研究认为,收入增加会使中低收入、中高收入和高收入阶层的主观幸福感都增加,也就是说,收入的绝对数值对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作用依然是存在的,这也同样说明中国还没有达到所谓的“伊斯特林悖论”区,距离拐点的阀值点还有一段距离。同时,这也可以印证之前提出的假设:随着收入增加,主观幸福感在提高,但其幅度在变慢。
2.不同年龄层次收入与主观幸福感的关系
从模型2到模型4可以看出,不同年龄层次人们随着收入提高对主观幸福感的关联程度有很大区别。三个年龄分组中收入相对主观幸福感的系数均为正数,表现出随着收入升高,各年龄段的人们主观幸福感的增强。但16~30岁年龄组和31~45岁年龄组随着收入升高,主观幸福感是逐步提升的,但46岁及以上年龄组在高收入部分却有下降。这也间接反映出不是所有年龄段人群都符合随着收入增长主观幸福感也同步提高的特征。
如图1所示,横向来看,随着年龄的增长,幸福感先降低后增加,可能原因是随着年龄的增长,人们需要承担的责任和义务越多,承受的压力越大,所以幸福感逐渐下降,达到一个极小值之后,随着年龄的继续增加,人们开始步入老年阶段,积累的个人财富越来越多,所需承担的生活压力逐渐变小,幸福感开始上升。由此基本可以证实前文的假设,即不同年龄阶段的人随着其收入增加,主观幸福感也在提高,但各阶段提升幅度不同,且在老年组略有下降。
六、政策建议
基于以上分析结果,并结合中国当前的经济现状,为丰富城乡居民精神生活,加强社会精神文明建设,本文提出如下建议:
第一,提高居民收入,稳步发展经济。中国是发展中国家,绝对收入的变化对居民的主观幸福感发挥着重要作用。立足于当前的国情,发展才是硬道理,在注重经济发展速度和质量的同时,要努力实现居民收入增长与经济发展的同步。居民的主观幸福感以物质条件为基础,对于低收入者来说,收入的增长将会带来主观幸福感很大程度的提升;对于高收入者来说,虽然幸福感提升幅度相对较小,但收入与其依然具有正相关作用。因此,政府应采取各种方式增加居民收入,使他们获得更多的经济来源,提高居民的生活水平,使发展的成果更多地惠及民生,实现国强民富。
第二,提高人力资本存量,注重教育和职业培训。在劳动力市场中,人力资本的高低决定了劳动者可以获取收入的多少,从而获得生活的经济基础。因此,加大教育和职业培训的投入,充分发挥人力资本的作用十分必要。一方面,要强化质量。政府应当实行教育先行的方针,完善基础教育设施,提高教育教学水平,真正发挥教育对人力资本的提升作用。另一方面,要转变观念。应当在快速发展高等教育的同时,加大中等职业、技工等教育投入,这样不仅可以使个人获得一技之长,提升个人价值,增加收入;同时也可以为国家产业结构的调整和经济转型奠定坚实的人力基础。除此之外,提高人力资本的方式还可以通过职业岗位培训,使劳动者能够成为熟练技能的掌握者,在劳动力市场上获得合适的工作从而提高个人和家庭的生活质量,增强主观幸福感。
第三,统筹城乡发展,缩小城乡差距。社会公平是社会和谐稳定的基本条件,但当今社会面临的问题之一就是城乡发展的不平衡。虽然城市的生活水平提高了,但研究表明,其与幸福感的提高程度并不成正比。因此,在城市建设中,政府要注重城市居民身心的健康发展,努力增加就业机会,减小就业压力,增强市容建设,加强道路建设,缓解交通堵塞现状,提升城市居民的幸福感。在农村建设中,可以指定类似招商引资的鼓励政策,把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发展所形成的资本、管理和先进技术水平引入到农业发展中,积极建立新型城乡生产合作体制,加强城市与农村之间的交流,实现城市和农村居民幸福感的平稳提升,向着实现中国梦的道路不断前进。
总而言之,经过了3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各项事业发展迅猛,实现了跨越式的进步。但目前仍然存在很多社会隐忧,还有诸多经济问题需要去解决。发展经济是为了提高广大居民的生活水平,政府的各项宏观经济政策也都是为了实现让居民生活更加幸福的目标。因此,探究经济如何进一步平稳快速增长,提高居民主观幸福感具有重要的经济和社会意义。
[1]EASTERLIN R A.Does economic growth improve the human lot? Some empirical evidence[C]//DAVID P A,REDER M W.Nations and households in economic growth.New York and London:Academic Press,1974.
[2]EASTERLIN R A.The happiness-income paradox revisited[Z].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2010.
[3]曹大宇.我国居民收入与幸福感关系的研究[D].武汉:华中科技大学,2009.
[4]张学志,才国伟.收入、价值观与居民幸福感——来自广东成人调查数据的经验证据[J].管理世界,2011(9):63-73.
[5]邢占军.我国居民收入与幸福感关系的研究[J].社会学研究,2011(1):196-219,245-246.
[6]徐广路,沈惠璋.经济增长、幸福感与社会稳定[J].经济与管理研究,2015(11):3-11.
[7]刘苓玲,王克,任斌.我国养老金待遇对老年群体幸福感的影响研究[J].南京财经大学学报,2015(5):79-86.
[8]毕明,孙承毅.城市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年龄差异研究[J].山东行政学院学报,2003(2):126-127.
[9]罗楚亮.绝对收入、相对收入与主观幸福感——来自中国城乡住户调查数据的经验分析[J].财经研究,2009(11):79-91.
[10]高鸿业.西方经济学——微观部分[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
[11]寇竞,胡永健.城镇劳动者个人和家庭因素对工作贫困的影响分析[J].贵州财经大学学报,2014(6):90-94.
[12]任海燕.经济学视角下的中国幸福研究[D].上海:华东师范大学,2012.
[13]李青青.收入与幸福感相关性的经济学分析[D].广州:暨南大学,2011.
[14]樊丹花.收入与主观幸福感的关系研究[D].上海:上海师范大学,2013.
(责任编辑:周斌)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Income and Subjective Happiness of Different Ages
LIU Tong,HU Yongjian
(Tianjin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Tianjin 300222,China)
Abstracts:Based on China health and Nutrition Survey(CHNS)data,through the theoretical analysis and empirical analysis,this paper analyz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ncome and subjective happiness of urban and rural residents of different ages.Results show that,the income of the residents has significant positive influence on subjective happiness,that is to say with the increase of people’s income,subjective happiness will increase.With the increase of age,happiness first falls and then rises.These findings provide an important theoretical basis for the government to formulate relevant policies to increase people’s income,improve people’s living standard and residents’ subjective happiness.
subjective happiness;income;age
10.13504/j.cnki.issn1008-2700.2016.05.002
2016-01-26
刘彤(1992—),男,天津财经大学经济学院硕士研究生;胡永健(1963—),男,天津财经大学经济学院教授,研究方向为劳动力政策、工资与收入分配。
F014.44
A
1008-2700(2016)05-0011-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