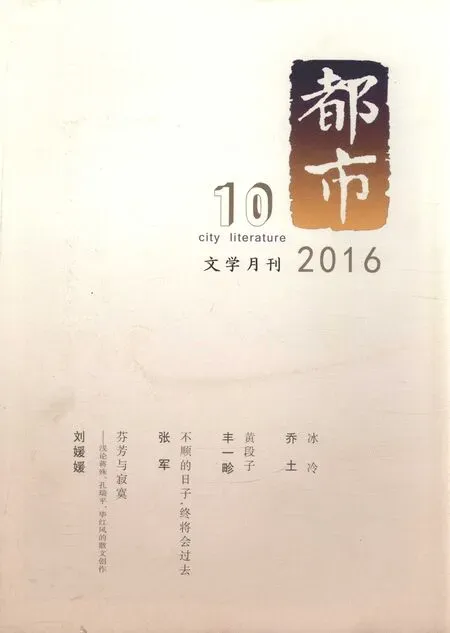难以找寻的“原乡”——评李晋瑞中篇小说《雪噬》
闫东方
难以找寻的“原乡”——评李晋瑞中篇小说《雪噬》
闫东方
乡村,是当代山西作家绕不开的书写主题。从“山药蛋派”的“问题小说”到晋军作家的“寻根小说”,闪耀着黄土高原独特光彩的地域总经常让人读出几分“原乡”的情味,但在世纪之交的社会转型之际,这些“原乡”的色调渐趋幽微。我们也许可以从被命名为“迷惘的一代”的美国作家那里找到一个对照:“在巴黎或是在潘普洛纳,在写作、饮酒、看斗牛或是谈情说爱的同时,他们一直思念着肯塔基的山中小屋,衣阿华或是威斯康星的农舍,密执安的森林,蓝色的花,一个他们‘失去了,啊,失去了的’国土;一个他们不能回去的家。”(考利《流放者归来》第6页)在《雪噬》里,作家李晋瑞也写了一个几户人家的村庄,同样的小山村,然而,他说山村是干瘦的,伏卧在灰蒙蒙的山中,像个毫无生气的老太太,村子里仅剩下三口人,三口人的故事却都是苦事,大雪像是要把村庄吞没,也隐没了他们三人的命运。
对农耕文明的自然之美的迷恋和激赏固然是乡土小说的主要动力,但自鲁迅开始所关注的思想开掘为这一题材奠定了更深远的价值和意义。面对急剧转型中的当代中国,乡土作家已经无法再局限于“原乡”的唯美寄托,也不能再只沉溺于旧有的乡土观念。《雪噬》使用了第一人称叙事的方式,记叙了城市摄影师“我”为了拍摄山村雪景而在隆冬季节借住在一个留守老人家里的故事,塑造了乐知天命不愿给别人添麻烦的“老哥哥”形象。乍一看,小说类似于传统意义上的“原乡”小说,在对乡野风情进行描绘的过程中,淡淡的乡愁萦绕其间,“我”虽非游子归乡,但对老哥哥生活的认同似乎也透露出“我”已将这个村庄当作了自己的精神归属地,但是仔细推究小说情节设置,似乎并非如此,小说在“回乡模式”的外衣之下,放置的是城乡一体化过程中无法调和的矛盾,以“我”的眼看到的幸福,也似乎有些可疑。
“原乡”之难以找寻,首先源于“都市流浪者”或曰“乡土边缘人”的“隔膜”的产生。乡土作家们总是在离开乡土,接受了新的教育之后才能写出乡土小说,而这个时候,他们往往就拥有了知识分子的腔调,乡土往往就成为被批判或者寄托怀念的对象,没见过世面的乡下人本身无法通过文学途径向他人构建乡土社会图景。《雪噬》中勾勒这个仅有三口人村庄相貌的是第一人称叙事者“我”,就使得小说充满了“看”与“被看”的对立,“我”在叙事中的完全介入使得乡村成为了“我”眼中凋敝但是却留有人情味儿的世界。
“我”的回乡之旅确切来说是一趟下乡采风,“我”作为老干部在城里安营扎寨多年,虽然身居城市但是却有着“热闹是别人的,我什么也没有”的孤独,所以“我”哪怕危险也要完成《乡村四季》的拍摄,“尽管人生充满遗憾,可我偏偏不想是这个”。与“我”的孤独相对比的是牛和老猫对老哥哥温柔的陪伴,于是“我”产生了“他并不孤独”的认识,这种认识推翻了之前我睡在暗黑的窑洞中感受到的漫漫长夜。在“我”的视角之下,老哥哥比“我”幸福,他对一切都不是很在意,生活、命运、世界似乎都和他没有关系,他只是活着,尽自己的本分,他有着通达从容的生死观,虽为别人活了一辈子却不愿给别人添麻烦,他在乡村的生活“不闲着”,也就少了寂寞。而我在拥挤的城市之中却无人搭理,儿女双全却各自繁忙,170平方米的房子虽大却只能一个人住,虽然比老哥哥的年纪小两轮,可是注重养生已经十几年,孱弱的同时,不免有了贪生怕死的嫌疑。
老哥哥过继来的儿子有祥的到来撕开了乡村和城市之间隐秘的疼痛。为了生活,为了给儿子买房娶妻,有祥必须进城打工,而84岁的道义上的“父亲”成为了他对故乡最难割舍的牵挂,横亘在他们之间的不仅仅是巨大的经济压力,还有生活习惯和人生观念的差异,这些矛盾常常使得两代人甚至三代人一直处于远香近臭的尴尬境地。有祥“出于责任”,不能丢下父亲坐视不管,他和儿子在大雪天回家对老哥哥软硬兼施,希望带他进城,情急之下脱口而出的“知道的,人家说你犟,不知道的,人家不说我忘恩负义?”成为了促使老哥哥进城的直接原因。面对这个两难的境地,老哥哥没有选择,只能妥协。这辈子他都在为别人活着,年轻时为两个弟弟张罗媳妇耽误了自己,老了又为了避免让有祥背上骂名而进城。篇末,因“我”突发疾病而不得不终止了这次采风,也将老哥哥进城之后的生活悬置。
小说里,老牛成为了乡村仅有了六口活物中第一个死去的,而且它选择了颇具意味的死法——吃尿素自杀身亡,文中为我们讲述了老哥哥和老牛相依为命的过去,现在有灵性的老牛这样死去似乎预示了乡村彻底消逝的开始。老哥哥作为最后的留守者和牛一样,他想决定自己的归宿,“他的墓是自己挖坑,自己从石窝扛来石头自己碹的,他还用石灰泥勾了墙缝,入口的拱门处还雕了花”,他要给自己预留最后一次的体面。史铁生说“死是一件无须乎着急去做的事,是一件无论怎样耽搁也不会错过了的事,一个必然会降临的节日”,在老哥哥眼里,死只是一道门,是“一间屋子向另一件屋子的过渡”,遗憾的是这道门在乡村迅速被吞没的过程中似乎关闭了,他的最后一点理想极有可能无法顺利实现。
“老哥哥强调他只有在这山村才感觉自己是个活人”,“一旦离开村庄,他就觉得自己背叛了”,持有浓重安土重迁观念的老哥哥不愿意离开乡村,但是有祥、向前都劝他去城里“享福”,所谓福分显示出两辈人观念中的巨大差异。古老的山村在老哥哥眼里有传承的血脉,“他每天都走在他们曾经走过的路,每天都使用着他们用过的工具,即使是院门口一块石头,他坐在上面都能感受到父辈、祖辈的温度”,可是一旦当他离开,这一些都不复存在。对于有祥们来说,山村已经不能在飞速发展的经济社会里满足他们生存的需求,农村娶媳妇都要求在县城有房子,所以有祥的离开义无反顾,向前也只是因为被瞎眼老母拖累才被困在山村里。晚辈们决心抛弃的,恰恰是长辈满心留恋的。
尽管小说中一再强调乡村和老家对于老哥哥的价值:“这房子每块石头都散发着亲人的气味,每件器物都渍有着家人的记忆,那些窗明几净的楼房现代、时尚,按平方米作价,尽管这窑洞丑陋、破败、落后,它却无价”,然而也在无意之间泄露出来自城市的“我”对这样的生活避之不及,十冬腊月“和泥打炭”是“我”坚决不愿承受的。正如“我”难以再去适应乡下生活,城乡一体化过程中真正难以解决的矛盾也许并不在于乡村失去了田园诗意,而是让农民进城或者“上楼”让他们按照城里人的生活方式活着是否真的是他们所需要的,。把父母接到城里享福,是否能让他们真正享福?路遥那句“只有享不了福,没有受不了罪”似乎否定了这个问题的答案。
小说结尾处,“我”拍摄的大雪压山、吞噬乡村的照片获得了金奖。其实这只是一张经过“我”的儿子后期加工过的图片,却没有人追究,加之前面“我”曾评价儿子更功利化社会化,似乎将城市塑造成一个无望的冰冷世界,城乡之间,“抑城扬村”的对比十分明显。在这样的写法中,城市和乡村或许都有些失真,钢铁森林的城市在发展中丢掉的太多,作家们把头重新扭向乡村,塑造了不少老哥哥这样的形象,但是老哥哥的行为准则显然也是“我”不能完全赞同的。城乡之间难以平衡的,不仅仅是资源分配,更是价值观念的改换。
乡土作家一唱三叹,在寻找“原乡”路上的精神漫游抑扬顿挫。失去乡村的不仅仅是老哥哥、有祥这些和乡村有着血脉联系的人,更是“我”这样在城市中无根,在乡村里也没有魂的人。现实中,乡村的消逝似乎更加隐秘而难以被人察觉,面对已经发生的消逝,带来一个极大的困惑其实是乡愁今后要指向哪里?提及乡愁,不论是江南水乡还是黄土高原又或者是塞外边疆,首先映入脑海的总归是一个旧时的村庄,若将一本全是高楼大厦的影集命名为“乡愁”,似乎就不太对味,出于文学对我们的熏陶,暂时我们还未能将乡愁和城市的楼宇相联系。然而随着乡村的失落,“故乡”对现代人来说即将成为一个失落的名词,而乡愁本身似乎也将要和游子一样遭遇无处可依的命运。
李晋瑞的小说中,《雪噬》较为特别,以往他写的最多的是城市里没有爱情的爱情故事,他失去了在本体论之上讨论爱情的决绝,而男女之间的情事写到最后好像常常要归结于虚无。在《雪噬》里,他似乎是要为失落了情味儿的城市找回一点光亮,但是这趟寻找就像他的爱情小说一样没有结果,徒增了几分无助:“那铺天盖地的雪,山村显得那么小,那么无力,感觉就像要被大雪吞噬了一般”。小说里说“我”的摄影作品给人归属感,遗憾的是这样强烈的吞噬之感似乎更将人生指向了虚无。
(责任编辑高 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