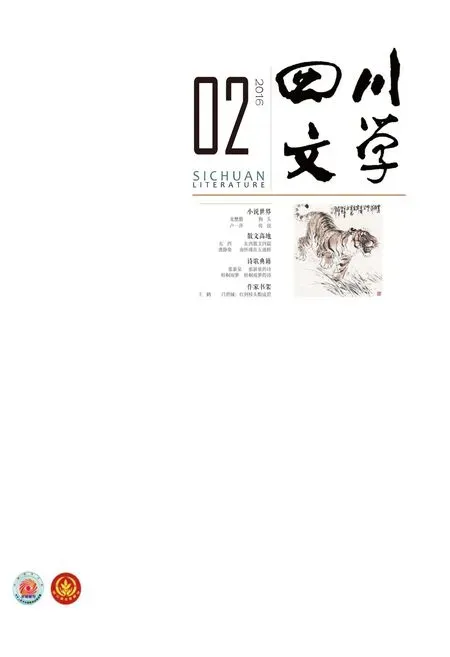四川的回忆录
顾 彬
四川的回忆录
顾 彬
抽刀断水水更流,
举杯销愁愁更愁。
四川,这个中国一个省的名字,我大概在高中学校第一次听到,很可能是1964年。那一年我们学生在德文课上看了布莱希特 (Bertolt Brecht, 1898-1956) 最有名的话剧。这个话剧叫“四川好人”,纳粹时代布莱希特从1938年到1940年在国外写了这部话剧。主人公是一个女的,她名字叫神德。这是一个说明人性格的名字。这女人好像是“神”,她肯定有“德”。布莱希特一辈子受到了中国古代哲学的影响,他会很明白“神”与“德”是什么意思。
话剧里的人把神德看成“贫居窟的天使”。读者或看众也会认为她是很有道德的人。那么,这个女人为什么算四川的好人呢?原来是百神想了解大地上还会不会有仁人。如果有的话,他们认为,这个世界有希望。因此他们从空中下来,到大地上去找。因为神能找到神德这类的人,所以作者解释作品的时候,说因为有她的气质,四川就是世界上唯一个没有受到剥削与压迫的地方。真的是这样吗?从历史来看不一定。社会发展不会这么简单。但是如果我们从儒家来看,一个有独特魔力 (Charisma) 的人可以改变一个社会。也很可能布莱希特受到了儒教的影响。反正他离不开中国文化。也可以说没有德文版的中国哲学,就没有布莱希特的作品。
布莱希特看了卫礼贤 (Richard Wilhelm,1873-1930)所有翻译成德文的中国经典哲学大作。特别是《道德经》决定了他的世界观和写作的路。他文笔的节奏,以及他对水弱不弱、强不强的了解都是从老子那里来的。
再谈神德的名字。我相信女人的魔力,相信诗人的诗意。女人是生命、生活的起源,诗人是空想、幻想的主人。没有女人,就没有爱。没有诗人,就没有爱情。那么,这样看,四川是女人美、诗人诗意的故乡吗?有不少人这样对我说过,也包括现居北京的四川诗人们在内。咱们相信他们吧。
在高中学校时我与四川的关系当然是文本上的。当时因为是“文革”的时代,1973年前我们“西方人”没办法去中国看一看。虽然我们那时候可以去台湾、香港和澳门,但是这三个地区对我们来说不能代表真正的中国。从今天来看,这么一个立场当然会有问题的,这不必多说。
六十年代末,在当时的西德我们学汉学的学生们太需要有人给我们介绍中国,但是我们学到的基本上是书上的中国。我们的老师大部分也没去过大陆,原因是第二大战与冷战。因此介绍中国的教授中到过中国的不多,不过是有的。我的导师是其中之一。他40年代在北京与南京待了好几年。每一次在波鸿大学上课的时候,他给我们三、四个学生讲他当时在当地的经验与经历。他有没有去过四川,我不知道。但是他特别喜欢给我们分析李白最有名的一首诗,“早发白帝城”。 白帝城允许我第二次跟四川有文本的关系。
不过,那一次我听到的好像不一定是一个百分之百纯德国人的声音,我听见的声音听起来是一个中国人的。这是什么意思呢?当然李白最有名的诗好像还是一个德国教授给我们解释的。无论如何,因为我的导师 Alfred Hoffmann (1911-1997) 上过中国老师的课,他就是每一次从他们的角度出发讲的。因此我们觉得当时听到的声音是中国人的声音,是李白个人的声音,是唐朝的声音。
白帝城是我的避难所,我很晚才去过。我在那里碰到过猴子吗?没有。为什么问呢?“两岸猿声啼不住”,我们的导师老给我们讲这行诗。猴子真的能哭吗?如果能哭,为什么要哭呢?白帝城不是很美吗?猴子的美学跟人的美学可能不太一样。
不过,也可能我的导师把“啼”这个字理解成“啼哭”是错的。今天的古代汉语辞典把“啼”解释成“鸟兽鸣叫”,大概是这个意思。很可惜我们今天的人没办法问当时的诗人。但是诗人如果还在的话,他会回答我们的问题吗?我估计李白听我们的问题以后,要把一杯酒吞下笑着说:“你们问猴子吧”。当时的猴子不能问,今天的猴子好像全部跑了。我们怎么办呢?
德国哲学家 Hans Georg Gadamer (1900-2002) 说过一句使人吃惊的话。他说,听很难。我们人应该好好学习听。听,这就是理解、了解。男人听一个女人说话,也可能才听到音素和不太有内容的响声。男人不一定理解女人,人不一定理解动物。能不能了解、理解是一个很大的问题。虽然“啼”不太可能是“啼哭”的意思,不过我们能理解一个猴子的心吗?
我们高中学校的学生们当时上德文课不光看布莱希特的话剧,同时也看他的诗歌。他最有名的一首诗谈老子出关。这个作品也是在国外写的。它最重要的话题不一定是在纳粹时代不得不流亡的问题,它的题目是《道德经》是怎么形成的。虽然这首长诗又让我们学生再跟中国重新打开另外一种书上的关系,但是它主要观点是帮助我们当时的读者,也帮助我们今天的读者理解世界上最优秀的作品是在什么情况之下出生的。除了《圣经》以外,《道德经》是最多翻译成德文的一本书,也可以说它是德国人第二本圣经。
看书的人都觉得作者是最重要的,其他的可以不管,写作的背景不要思考。通过他的“老子”,布莱希特想说明这类传统的、对经典的态度是错的,我们应该重新思考具体情况的重要性。如果当时没有海关要求老子给他留下来“什么东西”,那么我们今天的人大概没办法看到什么《道德经》之类的作品。
老子出关去四川这个故事当然是编辑的。从历史来看不一定有道理,但是从创造来看它就是太有道理的。所有的创造需要一个来源。比如我现在写的这篇散文,如果没有“美文杂志”要求的话,我从来没有开始拿笔。这不光是从来没有开始写的问题,这更是从来没有想出一些思想来的问题。如果没有海关让老子记载他的观点,《道德经》非常丰富的思想会存在吗?因为老子“什么”都知道,所以他不必跟任何人说话。可是我们今天的人不一定“什么”都知道。因此我们需要老子,因此我们需要海关问老子这类的人。
几十年来批评我们所谓的西方人是非常时髦的,特别是批判我们与中国的文本关系。不过到最近,没有批评家思考过连中国人对中国有的时候也才会有这类文本的关系。为了了解白帝城的猴子,他们能够回到唐朝去吗?他们能跟李白见面吗?猴子走了,李白走了。只有我们今人留下来。后代会批评我们,但是我们不知道,因为我们当代人都觉得我们是历史的高潮。白帝城的猴子也可能是这样看自己的。不光时间是残酷的,历史是更残忍的。今天最伟大的,明天变成了历史木乃伊。而我们的后代觉得后天才是历史的终点。我们呢?我们是历史的废物。
I
回忆是一个很麻烦的东西。它跟一个养坏的情人一样,有的时候来,有的时候不来。我脾气多变的记忆说我第一次到成都是1979年。当时我作为导游带一个德国旅行团来中国访问。因为那时候汉学没有太发展,我心里准备好一辈子作为旅游陪同。当然我已经拿了博士学位,但是在当时的西德不少有博士学位的年轻人找不到工作,就开出租汽车,也包括后来获得汉学教授位置的学者在内。虽然我会开车,但我不喜欢开车,我宁愿骑自行车。70、80年代的中国是自行车的天堂。当时我让不少旅客们跟我骑自行车参观北京,我们都很高兴。汽车不多,路好走。人很慢,山很慢,太阳很慢。什么都慢。不光慢,也不太亮,因为电不够。1975年的北京晚上7点后是黑色的。当时我们欧洲来的在今天的北语学中文的人,享受中国首都的黑夜。因为在非常发达的西欧我们看不到真正的黑夜,连夜里也是明亮的。
对欧洲人来说,黑夜算浪漫的,算女人的本身。因此每天晚上在颐和园看日落的时候,我们感觉到我们存在的秘密。老看日落这是说明我们有空,不再受到身心负担。当时我们好像跟其他中国人一样,没事儿要干。当时我临时的故乡是明斯特 (Münster),北威州一个古老的大学城市。在那里我每天感觉到精神压力。原因是读完博士后 (1973) 我看不到前途,拼命地找工作,最后决定作为高中学校的老师,要在我 Rheine 的 母校教德文与宗教。闲暇这个词,我当时根本不知道,更不说能享受什么悠闲。在急急忙忙的情况之下,1973年的春天突然有一个没有想到的机会,我能够来华学一年的现代汉语。1972年当时的西德与中国建立了外交关系。
1974年的11月底,我第一次到北京,北京是灰色的。我第一次到成都,成都也是灰色的。当时大概是1979年的春天,我陪了一个旅行团。除了大雨外,我们当时好像什么都没有看到。不过我的记忆不完全同意我的感觉,它提醒我我们在老城还看了一些老房子。因为我是策勒(Celle) 出生的,因此我特别爱老房子。策勒这个德国北方的小镇第二大战没有受到破坏,它仍然保留它原来中世纪的样子。迁居到策勒郊区的新房子以前,我家住在15世纪的桁木架房屋。好几年以前我带住北京的诗人王家新与住成都的诗人翟永明参观他们两位参观我的故乡,都非常兴奋。
我经常说老房子是一个城市的脸孔。不过,今天不少城市缺少它们自己的面孔。这不光是一个中国发展的问题,这是一个世界上到处都能发现的倾向。对我来说,每一个古老的建筑都有它自己的历史,会讲它独特的故事。拆老房这是拆一个城市的来源,留下来一个伤口。恐怕1979年的雨中我看到的成都老房今天已经都没了。代替它们的很可能也是高楼。住在摩天大楼生活当然会舒服一些。空间多,从上面每天可以看日落,也好。可是,因为高楼大部分一模一样,人很快会觉得缺少什么。缺少一种认同感。因为房子跟书一样,应该作为一个人最密切的朋友。我们真正的朋友们不可能都没有区别。他们是个体的,他们有自己的面貌、语言和手势。看他们的眼睛,我们知道他们是谁,不可能把他们叫错。
因为我第一次来中国距现在已经有四十多年,所以我有四十多年的记忆。我的中国学生,无论在波恩、北京、汕头或者青岛,他们都没有这么长的记忆。我的中国和他们的中国完全不一样,这是正常的。我的中国是蓝天的、四合院的,没有太多车的、小房子的、非常慢的、闲暇的,不一定是不幸福的,没有钱的,简单的。他们的中国是发展的、快的、堵车的、高楼的、让人家疲劳紧张的,不一定非常幸福的,富裕的、复杂的。
成都我几年来去得不少。我在那里上过课,开过朗诵会。那么我跟其他的外国人一样特别喜欢这个城市吗?2005年在四川大学教书的时候当地的人告诉我,外国人爱成都的无所事事。1000块人民币差不多够好好过一个月的日子。那么,1000块当时等于100块欧元在当天的西欧这笔钱可能才允许一个人过一天。我不知道四川的首府今天还是这么便宜,还是让人家入一个颓废的生活方式。我呢?当时我住在一个宾馆,没有时间颓废,我写我的诗、备课、锻炼身体、参观城内外的名胜古迹。那一年我在成都感觉到什么灵魂上的、身体上的烦恼吗?好像没有。我好像非常,睡得好,吃得好,游览也不错。
我了解成都吗?了解是一个太复杂的现象。了解是一种艺术,是一种过程。不可能我们今天的了解跟明天的一样。更不可能我们男人了解一个女人,她不会不要求我们第二天从另外一个角度重新来看她。对所谓异国的了解也是这样。今天的四川不是明天的。如果我们在长江坐船到了万州后要进四川的门,我们跟李白或杜甫一样吗?他们当时来的时候没看到什么高楼。如果我们能问他们你们是乘马达船,飞机或高铁来的吗。他们会听得懂吗?从今天来看他们是中国人,但是连中国人也不一定能全部懂中华的过去和未来。大部分的外国人会比苏东坡或曹雪芹更理解1949那一年。你跟他们说什么解放没用。因此我们的了解都发生在固定的条件之下,这些条件是历史决定的。
最近我在杭州上课的时候,那里的一个教授问我了解杭州吗。他的意思是说我理解多少呢。他以为外国人没听说过这个城市的名字,因此在介绍它的时候该加上“在上海附近”这些字。那么成都呢? 问题可能一个样。不会很多外国人知道它在哪一个省。不过,德国人好一些,因为波恩与成都90年代来建立了友好交流关系。
无论如何,什么都是一个符号。四川的符号比方说是麻辣豆腐、是酸辣汤。我都喜欢吃,我也会自己做。我的儿子们老要求我给他们做。他们多么享受。连我的中国朋友也觉得我的酸辣汤很特别。因为它非常辣,也非常酸。不过它的秘密在于醋。好些年前,大概是2000年的秋天, 我在乌镇听当地的人说他们的醋可以预防癌症。后来我在青岛发现那里的人喝醋,吃饭的时候喝小瓶。那么我学乌镇人、青岛人多“吃醋”。另外准备酸辣汤,我就多加醋。因此我的酸辣汤比不少中国饭馆儿好吃得多。此刻我的酸辣汤是我的符号。北岛写我,他写我的酸辣汤。每一次我的女儿Anna回家,她想吃酸辣汤。顾城歌颂了我酸辣汤的醋,因为我用的是中国的醋。我还记得他1992年的秋天在我柏林房子吃我的酸辣汤时说的话“ 中国醋还是好”。这句话重要吗?已经过了20多年了我还记得。不是奇怪吗?好像不是。如果他少吃过我酸辣汤的醋,也可能他还会在我们中间。
鲁迅说过因为不能忘记,因此他写作。写作与纪念是分不开的。没有回忆,没有文学,应该说没有回忆就没有优秀的作品。中国当代文学的价值问题就在这。这个不多说,因为这不是我的题目。我的题目是四川。谈四川我碰到一个很麻烦的问题。今天的四川跟我书上认识的四川不一样。四川一部分现在不再算是四川。它一部分现在叫重庆,属于重庆市。它有奥地利大,好像是小国。但是因为李白入过四川之门,这就是今天的万州,原来的万县,因此现在属于重庆的这个城市对我来说还是代表四川。要不然来四川的李白不是李白,他是另外一个人。
我谈四川,当然谈我个人的四川,我不谈别人的。我要谈我的四川形象 (image)。当然某一种形象不能代表所谓的现实 (reality)。如果两个人对某一个对象有同样的感觉,他们的现实可能开始形成。不过我一个人创造的形象,那么我的形象没有代表性。如果有的话,那么它只能代表我个人的观点。另外,我们都知道,我们的形象不光能发生变化,它们也会变老了,跟人一样。每一种形象只能告诉别人我们是怎么看的。我们的形象跟我们说的、要的、主张的道理、真理没有什么关系。新约的罗马帝国代表 Pilatus 问得很对“ 什么叫道理、真理呢”。
也可以说每一种形象才是一种建议,允许我们思考要怎么理解什么。因此这种建议是 o开放的(open),根本不是固定的。我为什么主张这个呢?后殖民主义的理论与政治正确的理论都认为有对的和错的认识,比如对中国的认识。如果我们的立场不是非逻辑的,那就没有对的或错的了解。只能存在有意思的、没有意思的看法。这个原来跟后殖民主义或政治正确性都无关,还是应该说我们不要老从这种很有问题的理论来看我们想了解的对象。
最大的问题不一定在这儿。问题在于这两种意识状态不允许人培养什么“错的”、什么“不正确的”观点。大概2000年,我在意大利开会谈忧郁、忧郁症在中国的问题。我原来想说明辛亥革命前的中华不一定有欧洲式的忧郁、忧郁症。那么我很快倒霉了。一个美国人听我的报告后,马上就要求我应该承认中国也有各种各样的欧洲式的悲哀。但是如果我们从历史来看她根本没有,另外忧郁、忧郁症不一定是好的。但是这个美国汉学家为什么非要求我承认中国也有呢?因为美国汉学界讨厌我们欧洲人说“中国没有”的学术态度。按照政治正确理论“西方”有的,中华也应该“有”。虽然那个美国汉学家要求我承认“中国也有”,从思想史来看完全是错的,我为了避免其他的麻烦还是“承认了”传统中国也有忧郁、忧郁症。她就满意了。我只能说可怜的中国,更可怜的美国。
历史是复杂的,因此人家宁愿选意识状态(ideology),从意识状态 看历史、看男人、看写作。意识状态允许我们用最简单的说法来谈中国。这不是一个外国人的问题。这也是一个中国人的问题。也可能更是中国人的问题。因为外国汉学界还会有比较客观的日本、韩国、德国学者谈中国优秀的文化。
中国是一个符号。不光对外国人,也是对中国人。比方说成都出生的巴金把中国传统的家庭看成一种代表压力与剥削的机构。不过他在国内外读者中非常成功的长篇小说《家》对儒教系统的看法太简单。孔子的学说好像全部是压迫年轻人、特别是女人的制度。从五四运动来看,儒教肯定有不得不批判的地方。但是真地可以或应该全面否定它吗?另外,年轻人离开“家”以后,他们会很容易找到一条新路吗?他们不要的是中国的传统,他们追求的是现代性 (modernity)。当然现代 (modern times) 给我们带来好多好处:让人健康的医学,允许我们自己决定我们个人的未来,女人的解放等。都不错,都应该有,不能否定。比方说没有女人解放,就没有现代性。不过,现代性也会有它不太理想的地方。因为什么都可以自己决定,人会越来越孤独。作出要“走”的决议后,人家去哪里呢?鲁迅提过这个问题。他从易卜生话剧的主人公娜拉( Nora) 出发谈这个困境。
现代人老在路上。他的“路上”跟李白或杜甫在四川的“路上”完全不一样。两个诗人离开家想回家,回到具体的家。还是他们希望在四川能看到他们的朋友。有家、有朋友就不要发愁,因为家与朋友给他们需要的认同 (identity)。不过,现代人无家可归。因为社会发展,人老要变。不光是他个人要发生很多变化,他的周围也是、也可能更是。现代城市老在变。为了扩大生活空间、生活方便,要盖好多高楼。高楼里有自来水有暖气,有洗澡间,有地方享受看书、吃饭或看录像等可是高楼跟旧房子非常不一样。在第36层不能看楼下的人什么时候来,什么时候走。邻居也不一定互相认识也可能不要互相认识。
再说,人到了现代不再会有一个“故乡” ,“故乡德文说 Heimat,味道跟英文 home 不太一样。现代性不是一种 终点,它是一个过程,一个从来不会停止的过程。所以人因为不断在过程中没有他的认同,没有固定的认同。如果还有的话,它每天不一样。比马克思早几十年的歌德时代 (1770-1830) ,人已经发现了分工给人带来什么困难。分工的现象把人变成两种人—分工让人失去他原来有的、还是觉得有的整体感。现代的劳动方式才允许他完成部分工作。在传统时代大概是一个人能做一辆马车。在现代时代是好几个人生产一辆奔驰。原来是 一个人需要掌握好几个工序来创造什么,现在一个人才掌握一个工序,就够了。这就是流水线每天给我们讲的事实。
流水线是速度,现代性是速度化。没有速度,没有现代。“文革”的中国没有发达的原因就是在这儿。当时什么都慢。晚上7点后所有的饭馆关门了。人回家看新闻,然后睡去。中午的南京街上没人,郑州的中午谁都在睡觉。恐怕成都当时也是这样。巴金《家》的主人公也都睡去了吗?这个四川来的作家有一次说:“文革”最深刻的话是“你多保重”。保重什么呢?保重慢性吗?思想的慢性吗?痛苦的慢性吗?巴金要求过该建立一个“文革”文献资料站。“文革”结束了快40年了。这类的资料站中国有吗?不能够说没有,也不敢说有。因为汕头市附近有纪念当时、当地死的不少人。我去过,我在那里写过诗。汕头外的纪念馆不是全国的,只是地方的。也好。因为跟一滴水一样。了解水,一滴水够了;了解“文革”慢性的悲哀,一个纪念馆够了。
速度与慢性。它们不得不对立吗?所有的现代化只能破坏传统吗?在传统的废墟上创造一个完全新的时代吗?这个问题难回答。我的回答不一定会有代表性,不过可以思考。德国巴瓦利亚的丁克斯比尔 是小镇,人口可能不超过一万。它是中世纪全部保留下来的城市。原来有火车站,但是居民不要,怕太多旅客们会来。现在只能坐大巴来参观,但是公交车不允许进城,人应该从城外的停车场走路进去。原来日本人多参观丁克斯比尔。现在不来了,因为他们不想走路。过去他们的旅游车可以到城市的中心。现在不行了,日本人就不来了。代替他们是中国人,他们不怕走一点路。路上他们越来越兴奋。因为他们可以回去。回到哪里去呢?回到他们渴望的花园。到处都是花、树、仙鹤。
丁克斯比尔是一个很慢的城市,没有工业,它靠农业,旅游业。它是一个富裕的小城,没有乞丐,没有穷人。不少人整天坐在街上聊天,什么都不做。城里谁都认识谁,谁都跟谁打个招呼,也包括外地来的人在内。我最近在那里的饭馆听一个老百姓谈外国人。他讲得满有意思。他说,谁都可以来,但是他该有道德。如果有道德他是我们的,如果没有他不是。
从丁克斯比尔来看,好像财富与速度不一定应该有关系。我经常带中国朋友到这个小镇去。最近我的一个很密切的中国朋友到了以后说,这里老百姓住的家在中国只有百万富翁能住。好像丁克斯比尔完成了社会主义。它的情况很特别,完全靠它的传统。每年这里纪念几百年前的一个小孩子,这个小孩当时救了丁克斯比尔。三十年战争时瑞典军队原来要占领这个城市。不过,城里一个四岁的男孩儿说服瑞典的统帅不要抢劫它。为了记住这件事情,城市让孩子每年游行表演当时的故事。游行活动时,好像丁克斯比尔所有的孩子在街上。因为这个纪念活动,到外地赚钱的居民都回来参加活动。他们的回乡跟李白与杜甫的回乡一样,是一个很具体的回家。为了欢迎他们,所有的房子安上了花的装饰,不能出来的老人在比较低的窗户上跟他们打个招呼聊天。
这是陶渊明的桃花源吗?好像是,好像。德文有一个说法: 少是多,慢是快。丁克斯比尔是它最理想的代表。
林语堂描写的中国文化是一个慢性的文化。他特别喜欢从北京的老头子来看它古老的文明。到最近我们还能观察老爷爷们在首都的街上打牌、下棋、看热闹。他们当然赚不了什么钱,不过对他们来说财产不是他们生活的目的。他们宁愿跟他们的哥儿们聊聊。他们幸福吗?大概是。我呢?我看他们的快乐,我看丁克斯比尔的小花园,我知道愉快不是能卖的,所有的得意是精神的事情。
北京胡同的老人缺少什么吗?丁克斯比尔 的居民感觉到分工的压力吗?好像都不是,好像。黑格尔说过一句决定现代性特点的重要的话。他认为,人到现代时代只能够有一种自觉状态,这就是不幸福的意识。请看巴金《家》里的主人公,他们都是年轻人。他们想离开成都。因为对他们来说,成都代表中国的传统,一个压迫人的传统。无论我们怎么看他们对儒教的理解,从黑格尔的角度看,他们是矛盾的,因为他们大概觉得自己是这种人,但是想做那种人。走了后他们得到幸福吗,能够做为“一个人”吗?我们只能希望,他们从成都到北京或到上海的路不太悲哀。在“文革”的上海对巴金和他的同行最重要的一句话是“你多保重”。他们当时也许是两种人,是充满了痛苦的人,同时充满了希望的人。1979年后呢?那么,问问他们吧。
II
成都诗人翟永明在第一组诗“女人”中,提出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来。一个人完成了他想作的、他想写的,他想创造的,那么后来还会有什么吗?还会有什么优秀的作品、什么贡献吗?这个女诗人不是第一个思考这个重要问题的人。德国诗人戈弗里德 ·贝恩(Gottfried Benn,1886-1956) 可能比她早30年也问过自己:完成了20世纪最好的诗歌之一,一个作家还会写什么呢?
有些艺术家们也包括歌手在内,虽然才出了一幅图画、一支歌儿、一首诗、一篇散文,他们还是能终生有名,一辈子赚得了好多稿费。丁玲很早就主张一本书。她的意思是说,一个作家能出一本谁都听说过、谁都看过的书,那么就够了。丁玲有这么一种著作吗?她有。反正在国外她写的《莎菲女士的日记》到现在有它的读者。还有成都来的张枣 (1962-2010)。去世前,他在中国、在德国才有一本书,是中文的和德汉双语的。去世后他的朋友出了他的散文集等。无论如何他还在的时候,他已经算新时期最优秀的诗人之一。他去世了后,他的读者不光在中国也在德国越来越多,越来越多买他的一本诗集。
好像张枣出版了他唯一本诗集后,不能再创造什么。我最后一次跟他见过面,大概是2006年的九月份在北大,他坦率地告诉我,他“写完了”。他的意思是,他几年来不能再写什么,未来也可能是这样。当时我想,他原来该翻译。他的创造力量会回来。我从1988年到1994年连一行诗写不出来。那么除了从事我的散文写作外,我当时多翻译,基本上翻译了鲁迅的作品和中国当代诗歌。到了1994年的夏天,我突然能再写诗,到现在没有停笔。我已经出了什么十本一百多页的诗集。
张枣会不少外语。他的德文跟德国人一样,他的英语流利,好像他还掌握基础俄语与法语。因此我原来老希望他能翻译到现在没有中国人注意到的德国当代诗歌。我老鼓励过他这样做,见面时他每一次答应了。不过,基本上除了学李白多喝酒以外,他去世前再没有什么大的贡献。这不是很可惜吗?老实说他浪费了他优秀的才能。
不光张枣这个人可怜,他德文版的诗集也是。这个作者觉得他太了不起。因此他想他在德国出的书应该卖它自己。无论我给他安排什么朗诵会,他不会带他的作品,也不告诉人家有我的翻译。原因大概是他怕他的一个朋友会不高兴。原来是这个朋友应该、也想出张枣的诗集,但是他从来没有。怎么办呢?沉默。沉默是中国人避免问题的好方法。我不太喜欢避免问题,因此也不爱沉默。事实是事实。事实上我翻译了张枣的诗集。不过,他的朋友写张枣的悼词说,附件里有他第一次翻译的张枣一组诗。我为什么提到这个呢?这不是小事儿吗?面对生死肯定是。但是这也说明一个问题。如果连最密切的朋友与同事不知道我们译者们做什么,那么我们的工作是白做的。最可怜的不一定是我们,可能更可怜的是我们的书,是出版社。
听说他还在的时候,他德文版的、设计非常美的诗集才卖了四本。出版社不一定为了张枣而亏本儿了,但是事实是出了我的翻译后出版社很快关门了,卖了他的房子。张枣的书在一个柏林地下室失踪了。幸亏有波恩一个很能干的书店找到了它书的新主人,买了一百本。它们在莱茵河地区卖得很不错。因此该书店又订了几十本。这样地下室的张枣诗集又复活了。我高兴吗?我当然高兴,因为我没有白搞过我的翻译。不过我同时也很难过。四川有很多有才能的作者,但是他们自己知道他们是天才吗?他们大概知道,但是也许他们觉得,自己的天赋是永恒的,跟他们的生命一样。今天不写,那么可以明天写吧。对张枣没有明天,连今天也没有。他已经去世五年了。少一人,多一种痛苦恐怕张枣的早死有象征的意义。听说成都文人的兴趣首先在于玩儿。白天睡觉,晚上出去。玩儿也可能就是一种颓废。张枣最后在北京过的日子是玩儿,白天吃喝,夜里吃喝。什么都不写,什么都不翻译。
一本主义有道理吗?不少1979年后的中国作家,从德国的角度来看不过是蜉蝣,他们缺少很长的呼吸。因此老贝恩与小翟提的问题是非常重要,作者们太少思考这个问题。不过,他 / 她们两位提到的难题不光是一个文学的,也是一个社会的。人类还在梦想自己能够克服所有生命的困境,幻想有一天会入天堂。因此人老在试试看能不能改善社会的情况,能不能提高生活的标准。但是人知道什么时候他够了吗?“More i not enough”( 更多还不够), 这类的口号我最近在北京机场看过。那么,再问什么是 enough,什么算 够呢?第二大战来大部分的国家主张现代化,歌颂现代化。这个态度大概是对的。不过,现代化后会有什么,还会有什么吗?现代化完了,历史也结束了吗?1989年有一个姓 Fukuyama 的美国学者公开宣布了历史的终止。那么,历史真地停止发展吗?原来的梦都会结束吗?那么就问离开四川的老子,写《四川好人》的布莱希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