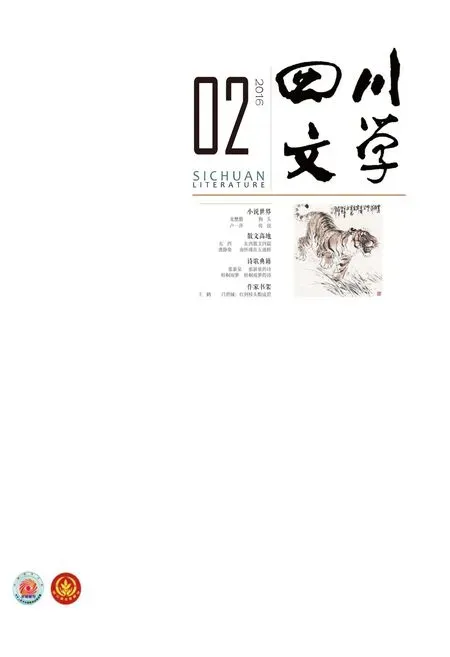酒都
—宜宾
文/罗宾·吉尔班克(英) 译/胡宗锋 马红丽
酒都
—宜宾
文/罗宾·吉尔班克(英) 译/胡宗锋 马红丽
在河流的交汇处,人们总能看到让人心思忧郁的奇特壮观。在合江门处,长江和它的支流岷江以及分别来自金沙江和金河的浩荡水流汇合。宜宾政府也以不同的形式纪念这三条伟大的河流。他们做了一个垂直的静态雕塑画,从下到上,标记了从上海到宜宾的这段河流。沿着台阶拾级而上,通过文字说明,人们可以看到沿途每一个重要的口岸,以及与其贸易史和河道规模有关的不同数据。在模仿竹简的花岗岩卷轴上,雕刻着四川著名剧作家魏明伦的诗句,使这里更加熠熠生辉。他的《宜宾赋》韵文开篇如下:
天下游人,品评万水千山,问何处适宜宾客?
长江重镇,吸引五湖四海,到此城际会风云。
在汉语中,“适宜宾客之处”或“适宜宾客”都是“宜宾”之名的双关语。“宜”取“适宜”之意,而“宾”则有“休息之所”或“宾客”的含义。冬日的清晨,潮湿的雾气漂浮在城市沙洲的上空,细小的雨滴模糊了眼镜,打湿了头发和外衣。这样的景色虽并不能称得上是壮观、适宜的,然而,眼光锐利的人一下就能看到其中独特的水文情况。与满是金色沙粒的事实相反—十九世纪70年代托马斯·白拉克斯顿带着美好愿景匆忙下的结论—金沙江里尽是淤积的泥沙。在和之前被称为清水或“清澈的河流”的岷江汇合之后,这些沉积物在水面之下打旋。魏明伦先生认为,沉积物的形成是由于较小的河流经过了一片“绿色的草地”,而并非是在各种力量的作用下从山上携带下来的。在陕西泾渭两河交汇处,同样的现象也周期性地发生着。只不过,现在的泾河流域水土流失严重,这种现象已经不如以前明显了。
除此之外,一直萦绕在心头的还有“勇敢”的—抑或可称为蛮勇的—“龙头游泳俱乐部”的成员们。一整年里,这些身着橡胶衣服的人都会活跃在这三条河流里。之后,他们会带上明亮的救生圈,这样路过的水路交通管理员就不会在半路阻截他们了。在这样凉爽的清晨训练之后,人们需要补充些能量,来一碗当地的美味“燃面”—字面意思是“燃烧的面条”。在早饭的时候,当地人通常会吃一些混有辣椒油、碾碎的花生和酸菜的食物。在外地人看来,冷配菜中加入如炒蜜蜂之类的食物不是什么好的选择。
虽然千百年来,宜宾以其沿河的地理位置而出名,但它最负盛名的—至少在中国是这样的—是它的饮食文化,尤其是酿酒这个行业。现在,燃面和北京烤鸭、兰州拉面一同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定为“非物质文化遗产”。而单从经济的角度来看,是当地的制造业造就了如今的富裕。在《宜宾赋》的最后一节,魏明伦把这座城市称为“酒都”,并对这个叫法做了如下的解释:
四川酒有口皆赞,五粮液无人不知。高粱红火,包谷金黄,糯米回甜,小麦清香。再配嘉禾大米,合为玉液琼浆。粮为酒之本,曲为酒之骨,水为酒之血,江为酒之魂。前辈秘方,酝酿出浓香魁首;当今绝技,勾兑成白酒状元。
几乎每一个乡镇和村庄都有自己的制酒方法,而且他们也经常向游客展示这种自制精神的魅力。在宜宾,五粮液的总部宏大壮观。有了这样的企业存在,其他的竞争者都只能相形见绌。就最近的估算来看,五粮液的产值占了这个城市GDP的60%或更多。也有迹象表明,它已经取代茅台,成为了中国酒业的领导品牌。
五粮液工厂占地7平方公里,有2万名员工。因其近乎宗教式的热情,它的产品备受称赞。在工厂场地建起来的博物馆还原了如今的整个制酒环境,向游客呈现了史诗般的幕后故事。据称,它独特的香味来自神秘的药草和香料的混合配方。而这种配方也在肯德基及可口可乐的化学成分中使用过。在宣传手段上,五粮液并没有提及有关这个古老配方的信息,从而也就免于受到舆论的指责。有专家学者指出,最早可以称之为酒的是一种名为“姚家雪露”的饮品。或许早在宋朝的时候,它就在宜宾被提取出来了。史料记载,他们和竞争对手陈氏都在蒸馏器中加入了五种谷物,然而直到1909年,才有一个名叫杨惠泉的人将该地区的饮食之乐传播给更多的人。最终,在二十世纪中期,陈氏的后人—年迈的邓子均将这种五谷酿酒法呈给了政府。作为回报,一些窑炉被他的家人保留了下来,以确保能获得一部分的利润。这也为后来的五粮液工厂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五粮液可谓是充分利用了其历史悠久、源远流长的优势。根据史书经典的记载,它建造了一座博物馆,真实清晰地反映了制酒人提取和品尝过程中的精神品质。尽管如此,五粮液也传达了一些让人十分费解的信息。通往工厂的大道如宫殿般华丽辉煌,两侧矗立着金属浇铸的雕塑。这在当今视裸露为不雅的文化中,显得有些令人仓皇失措。因为在艺术方面,中国一直没有比喻象征的传统,工厂的设计师只得从古希腊罗马的雕塑身上找到“美”的内涵。毫无疑问,这些雕塑会让人对英雄精神产生向往,但这也使得它们和粗制滥造的作品没什么区别了。在鹏程广场上,有一个复制五粮液酒瓶的大型雕塑(据说它已成为吉尼斯世界纪录的保持者,高68米,直径26米),底下是翩翩起舞的五位“仙女”。这些高加索少女身上并没有古代希腊三女神的品质,而是分别代表着不同的成分—黍、玉米、糯米、籼米和小麦。她们脚底下的喷泉早已被抽干,而在了解到少部分真正的中国文化是由编造的欧洲神话故事构成后,我们对这件事有了更加浓厚的兴趣。如果这个公司能模仿一下霍去病在酒泉的传奇故事,游客们估计会对这次旅行更加满意。
在宜宾的方方面面,五粮液都有着至高无上的主导地位。这里的每一幢楼房都渗透着该公司红银图案的理念。甚至连西北部在建的新机场都要在命名时加上五粮液的名字,而这一举动也有很大的争议性。大道上华而不实的外表和100年前清王朝衰落时的景象大相径庭。埃德温·丁格尔,一个英国的独立旅行家在被告知他最喜欢的旅行方式—在一群苦力工人的带领下徒步走进宜宾—非常危险的时候,他不得不选择了搭炮艇。这个被他称为“绥府”的有着15万人口的地方,是进行药品、鸦片、丝绸、皮制品、银制品和白蜡贸易的重要场所。一路上,丁格尔由同胞—去往康定的传教士陪同,而他也推测出这个当时熙熙攘攘的市区和出现在汉朝这个问题之间有某种关联:
相似的狭窄小路纵横交错着出现。同时,我的脑海中也形成了这样的定论:这就是这个城市和当地人所向往的潮流趋势。这里也有同样忙碌的机械师、理发师、商人、路边的厨师、流浪的算命先生和健壮的苦力;喋喋不休的医生以非法的手段谋得财富,很多人也因此上当受骗;而轿子和讲官话的随行人员的出现,则打破了这单一的画面。尽管人们行色匆匆,吵闹声此起彼伏,都在为维持生计而奔波忙碌着,这里也很少发生严重的不和谐的事情。但也有人们在书本上读到的浪漫故事—与人们在中国的香港和新加坡的港口遇到的情形既相似,又不同。和我去过的中国西部的任何一个乡镇相比,宜宾的艺术家似乎更热衷于在街道的布告牌上尽情挥洒。他们的书法颇有精美工艺品上的痕迹,故显得十分诙谐有趣。许多作品都刻有伪造的印章,但也有商铺愿意把这些作为自己的店名……
老“绥府”留下的东西没有多少了。就在合江门的边上,一些人还住在庭院里,尽管已经年久失修。四川易发洪涝,许多家庭愿意挤进一个房子里住,但即使是这样,他们有时也不得不穿上大衣或保暖的衣物。透过门上横档的顶部,我们可以看到里面充满绿色气息的墙面和在中庭角落的晾衣绳。主妇们似乎一直在忙着给锅里加水(每家都有自己的水龙头),再把它们放到烧煤的炉子上。过道里因为下雨而拿进来的齐膝的凳子、玩具和小型电摩都成了路障。
毫无疑问,对于宜宾以牺牲传统生活方式及文化来换得经济发展的做法,埃德温·丁格尔是持反对意见的。在出版了《徒步中国》(1911年)10年后,他迁到加利福尼亚的奥克兰居住,开始了别具一格的宗教活动。在如今成为精神意念治疗所的地方,他们一直鼓励人们去拓宽精神上的禀赋,从而更好地使用超感知觉和调息法。丁格尔声称,他曾从西藏僧人那里接受过呼吸的训练。他说,如果再配以严格的养生法(即远离酒肉),那么就可成为在精神上获得很大发展的普救派教徒。而他是肯定不会喝中国酒的。
尽管艺术家们常去的地方大多被拆,模制塑料和电脑生成的字体也代替了职业签字人的创作,宜宾的文化艺术仍存在于如今生活的许多方面。刘火与其他健在的书法家成功地在海外展出了自己的作品。有了像江安县周云和这样的作家,这里的文学依然生机勃勃。
有关丁格尔描述的狭窄小巷,人们应将目光放到这个城市的境界之外,来观察革命前的中国留下的遗产。以合江门作为出发地,我们有很多可选的路线。沿着如水晶般湛蓝的岷江逆流而上往北走,我们最终会走到都江堰市。在这里,公元前三世纪的时候,李冰父子借助水的能量灌溉了成都平原。于是,在中部地区,他们把四川视为农业资源丰富的土地。另一种选择是,我们可以坐船行驶到长江东部的李庄。这个地方我在接下来的部分会涉及到。向西会有一片人烟相对稀少的地方,那里遍布了古镇或是古老的村庄。在这其中,龙华古镇的与众不同深深地吸引了我。这个曾有驻军守卫的古老小镇坐落在屏山县境内。也就是在这个特殊的区域,1861年的时候,当地官员命令托马斯·白拉克斯顿放弃想要在长江上航行的创举。
如果有人想要探寻在太平天国运动时宜宾这里的情况,那么他很有必要来龙华看一看。受地理位置的制约,它的规模较小,住户之间也相距甚远。在村庄的防洪堤坝下,人们可以近距离地发现,有两条浅浅的小溪在此交汇,一条是清澈的,另一条则很浑浊。在这表面的相似之下,对比差异是脆弱得不堪一击的,因为于龙华这个地方本身而言,它的后代子民在相互隔绝中也吸收了外来因素,是一个十分特殊的群体。
甚至连四川当地人都觉得,这个古老的定居点是个很棘手的问题。在码头之上的长廊里,当地的历史学家杜先生在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将家乡历史的重要性传播出去。但是,清晰明了的含义并不总是能表达他的热情。当他拿过笔记本和圆珠笔,笔迹大而干净地记录下从他嘴里说出的每一个名字的时候,我的同伴依次浮现出了惊讶之情—首先是一位来自陕西的教授,接着是来自成都的秘书和司机,最后是宜宾市的记者。我很快就明白了他们无法理解的原因。他不仅有很明显的口音,而且在他的音调中也夹杂着咕哝声和假声。这也暗示着,他的祖先给他留下了混杂多样的文化遗产。随着杜先生的热情不断高涨,我们甚至连他疯狂的手势语也理解不了了。
这里有一些让人轻松的基本信息。龙华古镇大约在汉朝时出现,而后在五代十国时才开始有记载,但直到明清时期,人们才意识到它重要的战略意义。曾有一名叫江玉龙(公元1789-1863年)的将领,奉朝廷之命来到屏山县镇压反抗者以加强边防,并在咸丰三年(公元1853年)时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他的许多士兵都是从福建和安徽调来的,他们使这个古老的小镇重新出现在了这里。同时,他们还吸引了来自不同地方的人们,从而也形成了稀奇古怪的语言特征。因为他的贡献,朝廷册封他为四川省五品军政要员。其死后的谥号为“果”(义同“水果”),十分地接地气。他的坟墓遗址在现在的广元市昭化区。
在杜先生和他的前辈带领下,人们可以凭借现代化的手段去分析龙华的古老特征,从而也可以为以后的保护制定合理的规划。眼下的这块国家保护区,占地面积为3.67万平方公里,周围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地方四分之一已经得到修建。2013年,年代探测学家对一棵有4个人围起来那么粗的菩提树进行了研究。这棵树倾斜着延伸过河,和村边的树梢交织在一起。据估计,此树已有230年的历史。也就是说在美国独立时,这儿还只有树的种子;到法国革命的时候,它破土成了幼小的树苗。当地人受我们这群人的吸引围了过来,他们似乎很喜欢轻拍从树根下长出的一个东西。在我看来,这个突出来的木头块儿像个肿物,没有任何的特色。他们给这起了一个很好听的名字—“龙头”。清朝的皇帝们贪婪地把这神兽视为皇室的标志,并严禁平民百姓使用这个图案。而在民间的文化中,这早已成为吉祥的象征。在四川沿长江一带,每逢新年,人们都会用麦秆缝制怪兽像,在游行跳舞的时候,将它们挑在竹竿上。这就是在电视和西方华人区庆祝上见到的舞狮习俗的淳朴版本。而这似乎真的能带来好运。“龙华”这个名字可以被译为“中华龙”,而这个村庄的名字也来源于一个同名寺庙,怪不得当地人会这么珍惜龙和这个与龙头十分相像的树桩。
去龙华的路上一定要小心翼翼,遮盖起来的石桥正处于维护之中,所以人们在通过的时候必须借助临时用木板搭成的踏板。在主干道右侧的几十米处着陆,迎接人们的是成片的水泥滩和建筑工人用的三色防水油布,以及更多表明正在施工翻新的标志。真正的入口是西侧的大门。之前的围墙早已不在了,而仅能使两人并肩通过的拱门早已失去了军事意义。事实上,由于龙华人的地位谦卑,当地人习惯把这儿称为“扇子门”。如今,新月形拱门的石头上已长满了青苔—镇上几乎所有不是木头的东西表面也都一样。
从上面下来走到主街上,就再也看不到这个地方的全景了。无处不在的绿色光辉为古镇营造了一种阴郁的氛围。因而,每当从台阶或石板上下时,人们不得不小心翼翼。破旧的木房子有的门“开”着,有的“关”着,这完全取决于人们是想为了御寒在家里喝茶,或是蹲在外面和邻居打扑克。第二种场景则是,房子的扇形折门都半开着,一是为了跑烟,二是为了来人进出方便。除了不顾危险、在台阶上活泼地蹦上跳下的小学生,几乎没人能抵住寒冷。在用切肉刀给鱼去鳞的时候,小餐馆里胖胖的老板娘身裹着一件聚酯围裙围裙上鱼鳞斑斑,即使是这样,她的眼神也一直盯着街上来的这个“外国人”。她也许有可能也在准备和杜夫人招待我们午饭一样的乡间美味—甜美的萝卜汤和高蛋白的油炸竹蜂蛹。
跟随杜先生在龙华漫步,每块石头似乎都在讲述着一个故事。先前住在这里的彭氏家族曾经营着一家染坊,房屋建筑的特色是一楼一底。人们在底层做生意,楼上则是温馨的家庭生活。屋子外面,靠墙竖着一块被凿成“凹”字的石头。这是染坊遗留下来的东西尽管并不清楚它当时具体有什么用途。另外一家据说在中国独一无二、没有任何其它地方这样举行祭祀了其祖先的墓穴就在和街道齐平的底层,而后人则在上面一层居住。令人失望的是,可能是主人不在家,也可能是主人家受够了游人那可怕的热情,拒绝应答我们的敲门声。虽然我们透过门缝往里看,但从黑漆漆的前院看不出个什么究竟。突出地面的模糊东西可能是墓堆,也可能是几袋倒出了一半儿的石灰。
跟着杜先生一起旅行,映入眼帘的独特东西不尽相同。虽然对这些东西有点儿厌倦了,但我还是注意到一所马厩似的房门上画着的一个芒果状的心形(或者说是一个心形的芒果)。在心型的中央倒写着一个“忠”字(意为“满是忠诚”或“无限忠诚”)。我第一次看见这个标识是在陕西蒲城的一扇纱门上。那是一座清代的庭院,紧挨着国民党将领杨虎城母亲的住处。在许多窗格下的菱形小窗上,都曾装饰有倒“忠”字。人们推测,这些标识是近些年来被擦干净的。管理员告诉我们,这背后有着不可告人的动机。在“文化大革命”时期,人们曾被积极号召去破除陋习,毁坏象征堕落腐朽的古迹文物。这时就有人用刻印的图案来坚定地支持家人对毛主席和共产党的拥护,以拯救那些古色古香的陈设。当时,对伟大领袖的话语或是中国共产党的标志的毁坏是一种性质严重的冒犯(而且也会被惩罚)。于是, 通过一个小小的有心机的重新装饰,殷实之家才得以保住其珍贵的财富。
在半个世纪前,龙华是否也发生过同样的事我们不清楚。但从木门和墙上毛主席语录的数量来看,这些标语很有可能是为了促使山区人民接受正统的意识形态。如今,出现了有趣的掺假事件。这些昔日的标语现在显得世俗,以至于在匆忙喧闹的生活中早已被人们忽略掉了。虽然在我们来这里参观的那天,写有大字的地方已被各种女式短衬裤和袜子挡住,我们仍能在一处关着的大门上看到“忠于毛主席,忠于毛泽东思想,忠于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等字。在一所破烂的门后面书有“四个念念不忘”(即“念念不忘阶级斗争,念念不忘无产阶级专政,念念不忘突出政治,念念不忘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而在门里面,人们在肆无忌惮地玩着麻将。看到他们玩这,我悄悄地讽刺说:“离经叛道呀!”因为麻将是与赌博联在一起的,故是资产阶级的东西。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这种消遣娱乐方式是最早被打击的不法行为,直到二十世纪80年代,这道禁令才得以解除。
现在这些墙和门上有了另一个字,那就是“拆”。很可惜,这些过去的阴影能够存在的时间已经不长了。确实,不用铅垂线,人们也能觉察出影响龙华古镇的重大建筑问题。好多支撑在木板房屋外围承重墙的椽子,已从垂直变成了与地面成25或30度的角度,让房屋无法再住人了。
杜先生最引以为荣的杰作,比街上那些几十间摇摇欲坠的房屋更为古老而珍贵。在龙华的八仙山,正面有一座32米高的大佛像。这尊佛像是在大约400年前的明晚期雕琢成的,拜见大佛本身就是朝圣。即便是驾驶四轮驱动车,它的坡度还是会使玩得有些厌倦的游客因害怕而吓得大喘气。看大佛要走过长满青草的采石场、茶园小路和废弃的农庄。比起规模和设计,大佛的神圣更使人印象深刻。和乐山那尊71米高的坐佛相比,这尊立佛是有点矮了。给人的感觉是有些平淡或不完整,衣服上少有的褶皱和生动的双手也无亮点。尽管如此,这尊佛像的质地还是很值得一提的。它浑身散发着深红的光:这种红就像是太阳照耀下的西藏喇嘛身上穿的僧衣,比古代英国的红砖略胜一筹。
大佛令人心生敬畏,却又没有得到很好的宣传。我依旧无法想象这尊大佛就在龙华,但也不完全如此。另一处在山坡上的宗教景点,则不是那么仁慈地注视着脚下的小镇。它隐藏在村子一处二十世纪70年代建筑的后面,在一片很古老的建筑中颇有现代社会的色彩。
道教的大禹庙是上了锁的,不出所料,钥匙就在杜先生手里。庙正面发红的石材显然是取之于八仙山,多亏雨水的冲刷,旁边的缝隙里有几片绿叶、遍布青苔和各种各样的其他类似蔬菜的东西。院子的周围长满野草急需清理,有一些参差不齐的建筑物亟待修缮。以前的回廊在过去那个革命年代,很可能被做过车间和仓库。而戏院舞台上的花式设计则依旧崭新,表明不久前这里还经常有演出。
踏入阁楼上的神殿,比真人大3倍的大禹和道教众神的塑像似乎刚被粉饰过。色泽黯淡,有醒目的金箔。我不禁想,这是不是说明这次的修缮不是很到位(这些雕塑在其它工程结束前还需要再润色),或是对大禹本身的迷信一直就是这样?作为一位贤明的仁君,黄帝的第九代子孙—继承父亲鲧的未竟事业—接下了这个工程难题。为了避免黄河洪水泛滥所引发的灾难性后果,当时的尧帝(据说公元前2333—公元前2234年)把这个任务交给了鲧,而鲧因为无法胜任被残忍地绞杀。禹的贡献在于将这泛滥的水变作灌溉之用,重新分流,将其引向农田,而且他也意识到了修筑水利设施的重要性。为纪念这位智慧的君主,人们在长江沿岸修筑了许多寺庙和神龛,而其中的原因不说自明。在像李庄这样的村镇里,墙上都有洪水袭来的水位记录。所有的楼梯井都被吞没了,汹涌的水流冲倒了并不牢固的凉亭,受国家保护的清代房屋的门槛也被冲破。在这样的情形之下,除了这位治水神人还有哪个古人可以去祈求呢?
我们是不是可以这么说,在宜宾,对大禹的尊重是真正的“宗教”呢?这里当然还有另外一个竞争者,那就是鹏程广场塔上的那个大型五粮液酒瓶,它有大佛的两倍大,而且也能瞬间压倒大禹像。如果我们说中国现处于一个唯物主义时代,精神的东西居于下位乃代表经济发展的源泉,那宜宾就是真正的酒都。酒为上,其他一切次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