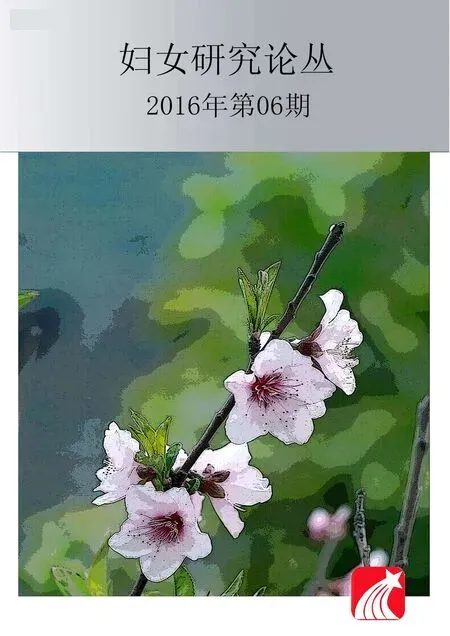妇女贫困的深层机制探讨
金一虹
(南京师范大学 金陵女子学院,江苏 南京 210097)
妇女贫困的深层机制探讨
金一虹
(南京师范大学 金陵女子学院,江苏 南京 210097)
人类社会对贫困根源认识产生的一大飞跃,是从侧重贫困的物质匮乏状况转向更多从社会经济文化和制度性结构中考察贫困和寻找贫困的社会成因。如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马蒂亚·森(A-martya Sen)所指出的,贫困最终不是收入低下,而是获得基本物质福利的机会和能力的缺失[1]。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在2000年《全球贫困问题报告》中,亦指出:人类贫困是指缺乏人类发展最基本的机会和选择。长寿、健康、体面的生活,自由、社会地位、自尊和他人的尊重。贫困具有多元的社会面相、贫困是机会和能力剥夺的产物已逐渐成为国际社会的新共识。
贫困不仅具有多元的社会内涵,且贫困形成是一个复杂的社会过程,是各种不平等社会机制交互作用的产物。因此,单一的解释因子无法准确把握和分析贫困发生的机制。我们特别需要探讨性别、种族、年龄和残疾等不利的人口因素,是如何与资源的不公平配置交叉重叠、使贫困不断发生和再生产的?
贫困与性别是否具有相关性?这种相关性程度如何?国际经验普遍表明,妇女较之男性往往更容易陷入贫困。在发展中国家尤其如此,生活在贫穷中的妇女人数同男子相比不成比例地多。同样,在转型经济国家中,因为产业结构调整带来某些工作岗位的丧失,导致妇女贫穷人数有增多的趋向。即使在发达国家如美国,自20世纪70年代末始,贫困增长最快的家庭是女户主家庭、单亲母亲家庭;另一方面美国贫困人口中的女性也越来越多,出现了具有统计数据支持的“贫困的女性化”(feminization of poverty)现象。这些一方面表明经济增长不能自动惠及贫困群体,也不能自动使男女两性平等受益,另一方面也证实了贫困与性别、性别不平等具有密不可分的关联性。联合国人口基金会在2005年发布的世界人口状况报告中,首次指出二者之间存在明确关联,并断言:性别歧视不成为历史,贫穷就不能成为历史①联合国人口基金执行主任托拉亚-奥贝德在伦敦发布2005年人口状况报告,报告主题为“保障平等:性别平等,生殖健康和千年发展目标”。报告指出,各国领导人如不采取行动终止性别歧视,世界各国让贫穷成为历史的努力将以失败告终。。
贫困之所以与性别、性别不平等具有紧密关联,是因为妇女存在群体性的脆弱性和受到基于性别的社会排斥以及存在男性中心的家庭结构和隐蔽的父权制意识形态(或说传统性别规范、性别角色分工模式)的制约——妇女贫困是这三重不利机制与其他不利因素(生态灾害、地缘政治影响下的地域经济的极度不平衡、资本霸权下的全球秩序等)交叉作用的产物。
在现有社会结构中哪些因素导致了整体上妇女比男性更为脆弱?同时又有哪些因素使妇女比男性更易遭受社会排斥?
1.脆弱性(vulnerability)(也有译作“易受损害性”)②易受损害性最早由世界银行提出并定义,转引自章元、万广华:《贫困脆弱性的预测及未来贫困与社会资本的实证研究》,http://www.crpe.cn/06crpe/index/clinic/2007qnlt/070.pdf,2007。。贫困人群的脆弱性指个人和家庭面临某些风险的可能以及由于遭遇风险而导致财富损失或生活质量下降到某一社会公认的水平之下的可能性。脆弱性分析总是和风险紧密结合在一起,包括环境风险、市场风险、政治风险、社会风险和健康风险,脆弱性高是贫困的重要特征之一。
不可否认,妇女面临各种风险比男子更容易受到损害、更脆弱的原因部分是与她的生理特质相关。比如在灾害来袭和遭受暴力时,妇女因体能较弱会表现出某些劣势,身处孕育哺乳等“四期”时也会表现出种种生理性脆弱;但妇女的脆弱性更多来自性别制度文化等社会性因素。贫困风险在不同性别群体中非均衡分布,与其就业、教育、技能、健康、社会身份等带来的社会资源的差异密切相关。比如,妇女在突发灾难中更容易受到伤害③一些关于灾害的统计表明,无论是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妇女都更容易成为灾害的牺牲品。转引自冯媛、刘大庆:《灾害与妇女贫困》,载于赵群、王云仙主编:《社会性别与妇女反贫困》,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第139页。,不仅仅因体能,更多是与妇女缺少相关信息知识和防护技能训练、优先保护子女家庭的角色期待(妇女在生命受到威胁的紧急关头,第一反应往往是牺牲自己保全子女和家庭)相关,也与政府对灾害风险管理政策缺少性别意识不无关系。比如女童在公共事件中更容易受到伤害,往往因她们更容易受到家庭的忽视。再如老年妇女大多比老年男子更缺少养老保障、卫生保健资源,作为依赖人口的她们,很可能因疾病或丧偶而陷入贫病交加的最不利状况。
女性的脆弱性还表现在经济衰退时期以及经济结构调整过程中,她们更容易失去稳定的工作岗位,被迫采取临时、非全日制就业,因而面临更大的贫困风险;此外,结构转型和经济不景气可能导致的福利削减(比如取消单位托幼机构和家庭供暖等福利),对女性产生的负面影响更大。
2.社会排斥。社会排斥与阿马蒂亚·森所说的“能力剥夺”有关。造成这种状况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某一身份人群由于被隔离于某种社会关系之外,限制了他/她们获得资源和社会公共服务的机会。
社会排斥多用于考察多层次的不利条件如何使社会边缘群体陷入缺乏维持最低标准生活的能力、从而被排斥出主流社会的分析框架。社会排斥是分析女性贫困根源的另一个重要分析维度。基于性别的社会排斥,存在于市场、制度和社会三个层面。有些是结构性排斥,有些正在或可能被结构化。
市场基于性别的排斥通常表现为或直接或隐蔽的性别歧视——劳动市场将女性因生育和抚育子女产生的成本视为影响劳动效率的负担,因此女性被视为次等劳动。这些排斥在不同年龄层和不同职业领域有不同的表现。对处于或即将处于生育年龄的女性则拒绝雇用,如用人单位拒收女大学生;对已经进入职场的女性则设置升迁通道上的“玻璃天花板”等。市场排斥直接影响女性的生计,也造成女性就业的底层化、劳动的边缘化。
制度层面存在的社会排斥。一方面,在以法律法规以保障性别平等的国家,排斥通常不是表现于保护性制度条文的缺失,而更多是对女性平等权利提供的保护性制度资源不足。例如中国农村较长时期存在妇女土地承包、宅基地拥有、集体分配收益等经济权利受侵害的问题,但法律救助途径往往不通畅(例如地方司法部门不受理妇女有关土地权利受侵的诉讼,也没有追诉司法机构失职、渎职的路径);另如对女性平等就业法律法规执行力度不够、单亲母亲家庭救助制度缺位导致部分离异妇女和单亲母亲贫困化。另一方面,社会转型、产业升级、结构调整时期的政策常常是性别盲视的、缺少对政策调整的性别评估。
社会性的排斥还表现在女性因为生育等原因退出劳动市场或离婚、丧偶等家庭变故,将带来原有社会关系的破损和社会支持的中断,造成社会资源的贫乏,表现在失业和女性户主家庭、单亲家庭的贫困化。
3.体现男性中心主义的家庭结构以及与此相应的性别规范、性别角色分工模式的长久存在,是分析妇女贫困发生的第三个重要维度。
家庭资源(包括生产资源、教育资源和健康资源)在两性间分配的不平等,是导致女性贫困的重要原因。比如,在家庭可提供教育资源匮乏的情况下,女童受到更好更高(义务教育之上)教育的机会可能比男童更少④即使在义务教育阶段,男女童的高入学率也掩盖了女童辍学率高于男童的事实。第三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数据显示,城乡女童失学率分别为2.2%、7.8%,农村显著高于城镇。年龄越大女童失学比例越高。17岁女童失学率达22.3%。在失学原因中,女童和男童因家里没钱供、家里需要劳动力、家长认为读书无用的比例分别为21.1%和14.0%。参见宋秀岩主编:《新时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研究》(上下卷),北京:中国妇女出版社,2013,第756-757页。。
在夫妻对家庭资源的支配权方面,男女也远未达至平等。家庭内资源不平等分配既是结构性的,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是一种社会性的内部排斥——对家庭内部成员基于性别身份的排斥性对待(比如很多地区农村女儿不能从父母家庭同等继承财产),家庭生活共同体的现状和以家庭为分配和福利单位的社会制度(例如以户为单位的福利分房制度、最低生活保障、集中供暖等)往往掩盖了家庭内这种个人权利的不平等。妇女一旦失去“婚姻保障”(如离异、丧偶),特别是农村妇女,极有可能陷入无地、无房的贫困境地。
迄今为止,“男主女从”的传统性别规范、“男外女内”的性别角色分工模式还普遍存在,构成根深蒂固的性别文化。这种性别规范为社会提供了对男女两性的不同评价和期待,在农村则限制了女性对非农经济活动的参与,使她们获取收入的机会大大低于男性,而一旦流动产生抚育问题(比如伴随留守儿童产生的一系列问题),往往得到的是对流动母亲“只生不养”、未尽亲职的更多责怪。在都市,“亲密育儿”等要求促使教育母职化趋向越演越烈,也使女性双重角色矛盾加深,特别是缺少社会支持的单亲母亲,面临独自支撑家庭生计和母职的激烈冲突,更容易陷入贫困陷阱。
综上所述,女性群体在应对生态、社会等多重风险中具有更大的脆弱性,在诸如生态环境恶化、社会转型带来的阶层分化,以及变迁中的文化转向等各种外部致贫因素的作用下,基于性别的多重社会排斥、体现男性利益优先的家庭结构和“男主女从”“男强女弱”“男外女内”的性别规范三重因素的交叉作用,成为妇女贫困生成的深层原因。这三维因素之间也是彼此关联的,妇女贫困很可能是这些因素叠加的结果。如因自然灾害不幸丧子的妇女,很可能在“失独”的同时也失去婚姻,因为妇女被寄予为男系家庭生育传续的角色期待。
特别需要强调的是,女性贫困生成和延续还具有劣势积累的效应。如在女童阶段失去了接受更好教育的机会,她将因早辍学、早打工、少技能而较少获得“体面工作”的机会,到老年只能享有低水平的社会福利。这种劣势累积将使妇女一生处于更大的贫困风险之中。
[1][印度]阿马蒂亚·森著,王宁,王文玉译.贫困与饥荒——论权利与剥夺[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
金一虹(1947-),女,南京师范大学金陵女子学院教授。研究方向:性别社会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