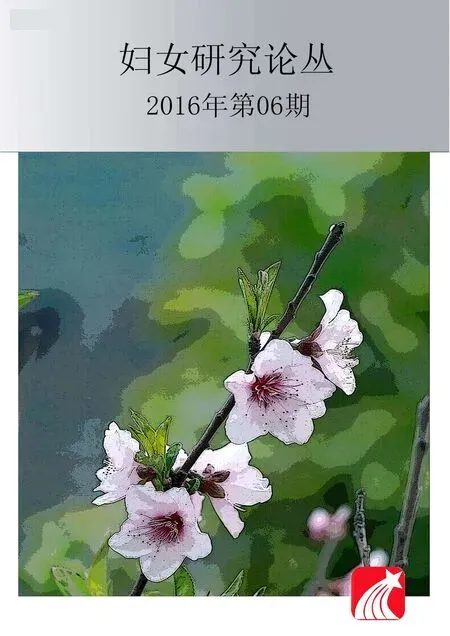农村性别观念的现代性改造*
——以20世纪50年代陕西地区的流动放映为例
郭燕平
(香港中文大学文化及宗教研究系,香港,999077)
农村性别观念的现代性改造*
——以20世纪50年代陕西地区的流动放映为例
郭燕平
(香港中文大学文化及宗教研究系,香港,999077)
农村放映;性别观念;男女平等;女放映员;现代性
新中国成立初期,随着新法的颁布及农业集体化的推进,农村既有的性别观念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取而代之的是对农村女性文化身份的重新想象。其中,被认为是现代宣传工具的电影大规模地进入农村,参与了新中国早期对性别观念的改造。本文以20世纪50年代陕西地区的经验为例,结合电影文本、口述史和档案来分析:流动放映作为多元媒介空间在日常观影中如何作用于性别观念的转换。事实上,在“去性别化”的社会主义性别建构之下,包含着不可避免的“性别化”策略,无论是从宣传技巧还是从女放映员的经历来看,都呈现出了关乎性别的差异化表述。
20世纪50年代开始,新中国的农村经历了全面的社会主义改造。除了经济、政治制度上的彻底变革,国家亦着力于塑造符合现代化想象的农村生活。其中包括在基层建立政治宣传的机制,以便服务于一整套关乎社会主义国家治理的现代话语。流动放映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广泛地进入中国农村。加之放映需配备放映机、扩音机、发电机,这些设备在当时代表着国家工业技术的前沿,电影因而也被称为现代化的宣传工具,在农村用于传播先进的社会主义现代思想。
在电影放映进入农村的初期,男女平等即成为放映宣传工作的重点。虽然国家并没有明确发起宣传“男女平等”的运动,但是随着《婚姻法》的颁布和农业集体化的推进,怎样改变农村旧有的性别观念以及动员妇女参与劳动成为宣传工作的题中之义。前人关于农村放映的研究,基本围绕着放映的形式、制度的建立来展开历史性描述①比较重要的几篇研究包括:李道新:《建构中国电影传播史》,《人文杂志》2007年第1期;刘广宇:《1949-1976年:江津农村电影放映队的历史沿革及运作机制》,《当代电影》2008年第10期;汪朝光:《官营化·教育化·普及化:抗战时期后方电影的发展路径转向》,《江海学刊》2008年第1期;徐霞翔:《“再造”农民:农村电影放映队研究(1949-1966)——以江苏为例》,南京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0年。,放映技术被认为是客观中立的,与性别议题并无直接关联。另外一些电影研究的学者,他们主要关注的是毛泽东时代以农村为题材的电影文本以及对电影中女性形象的分析。但这类研究以文本为导向,不牵涉对文本接收也即放映具体过程的讨论。那么,农村放映到底是如何挑战农村传统的性别观念并作用于新观念的再生产的?这一问题在既有研究中并未获得解答。通过引入性别视角来看待电影放映在农村中的实践,本文得以探讨被忽视的女性经验与现代技术的关系,并且关注在当时依然保守的农村,新的、现代的性别观念如何借助放映技术对传统的性别观念构成挑战。
本文将首先阐明农村的性别观念与毛泽东时代的主流性别建构分别指代什么内容。其后,笔者将聚焦农村放映中与性别相关的实践,以此来探讨以上两者在农村的具体情境中如何展开互动。此处谈及的放映实践涉及两个层次:一方面,它特指因放映而得到展示的主流性别建构。笔者将分析关于性别的主流再现在放映中如何被传播,以及此类再现的生产与本土经验之间怎样相互作用。另一方面,放映实践还包括女放映员的自身经验。笔者将讨论女放映员作为新式的职业女性在进入农村之初,遭受了怎样的挑战以及她们如何改变了妇女在文化中的既有位置。本文主要选取陕西省作为田野调查的地点,结合女放映员的口述史访谈与官方历史档案展开相关论述。
一、历史背景:性别观念的变迁与农村放映的出现
本节将首先简略回顾传统性别观念在中国的变迁。随后,通过梳理新中国政治宣传的理论来源,尝试将性别观念的社会主义式改造纳入政治意识形态宣传的脉络去看待。接着,进一步指出农村放映的出现正是把当时的政治宣传理念具象化为日常实践,从而由此切入讨论性别观念改造与农村放映的关系,为接下来的分析作铺垫。
(一)农村的性别观念与社会主义的性别建构
一般来说,性别观念是指基于两性生理差别而衍生的某些定性思维,它规定了男性和女性各自在社会中的行为规范,并由此确立了相应的道德准则、劳动分工和伦理秩序,等等。进入现代以来,中国的性别观念曾经历数次激烈的变化,其均以重新定义女性在中国社会中的位置为核心。从晚清的“国民之母”到辛亥革命的“女国民”,再到五四时期“出走的娜拉”,对女性的不同想象标记了中国走入现代过程中性别观念的数次转变。但值得注意的是,这些近代以来的中国女权论述,常常指向的是精英阶层(识字阶层),着重于以都市为中心的文化实践。而农村的性别观念却作为想象的他者,被简化为传统的、封建的“男尊女卑”思想,成为需要被改造和清除的对象。而真正的关于农村妇女解放的讨论和实践,则要等到国共合作破裂、共产党移师山区建立根据地之后才发生。
解放区有其特定的自然和历史环境,中国共产党在农村领导的妇女运动也因此发展出了完全不同于五四以来的男女平权实践。两者之间的差异在“四三决定”中得到了突出的表现[1](P65)。1943年,党中央公布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各抗日根据地目前妇女工作方针的决定》(简称“四三决定”),指出目前的“妇女工作中缺少实事求是的精神……不深知她们的情绪,不顾及她们家务的牵累、生理的限制与生活的困难……就根据主观的意图去提出妇女运动的口号……对她们作不必要的动员,浪费她们一些人力物力”[2](P647)。“四三决定”回应的正是当时盛行的“妇女主义”的观点,该观点主要由延安的女性知识分子所把持,沿袭了五四以来城市资产阶级自由女性主义的论述。由于它鼓动农村年轻女性的独立和个人要求,因而与传统的乡村男权观念和宗族结构相冲突,被认为是破坏团结、脱离群众的形式主义工作手法[3],不利于根据地的长远发展。于是,“四三决定”紧接着提出了妇女工作的“新方向”,强调从“经济丰裕与经济独立”入手,原因在于“多生产,多积蓄,妇女及其家庭的生活都过得好……她们也就能逐渐挣脱封建的压迫了,这就是在整个群众工作中广大农村妇女的特殊利益的中心所在”[2](P648)。
从争取女性的“人格独立”转为“经济独立”,五四以来的女性解放论述在延安经历了本土化的改造,妇女权益被完全纳入抗战时期经济至上的话语中。除了囿于战时需要,这一策略一度被认为是遵循了马克思主义的妇女观②受恩格斯经典著作《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启发而发展的妇女理论认为:私有制与商品交换的出现主导了男主外(社会性劳动)女主内(家务性劳动)的性别分工,女性的劳动由于没有交换价值而遭到贬抑,同时她们又被排斥在社会劳动之外,此为性别不平等根源之所在。。如果说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所倡导的经济参与是为了让妇女得以摆脱家庭内部的剥削,那么延安的妇女生产运动为我们提供了另一视角去看待战争时期妇女劳动与传统家庭的关系。正如宋少鹏与周蕾提到的,中国共产党对农村妇女解放的思考不同于恩格斯以降的妇女理论,它没有将性别不平等的根源完全简化为经济关系,而是看到了农村封建宗法社会对女性的压迫,这也即是毛泽东建立的“政权、神权、父权、夫权”的四权压迫理论[4]。然而,在资源和人力都极度匮乏的战争时期,因片面地强调“妇女主义”式的解放而强化妇女与家庭、宗族的对立关系,非但不能很好地实践女性的反压迫运动,反而可能招致新型的压迫和性别不平等。丛小平的文章用翔实的史料回应了这一问题。她通过仔细梳爬20世纪40年代陕甘宁边区婚姻案件的档案,发现并不能将妇女解除婚约简单地解读为女性追求婚姻自主,因为有些案件还牵涉到女方父母故意瞒婚、骗婚以谋取更多彩礼[5](PP139-142)。在这种情况下,进步的婚姻制度反被利用于服务父权制,榨取贫农的经济价值,使得无论女方还是男方都成为了其中的受害者。
“四三决定”的颁布也是基于对这些问题的反思。单一的男女平等制度革新无法完全应对小农意识的缺陷与精明计算,而同样受到地主剥削的男、女农民却有着共同的经济利益和反压迫的需求,这使得延安时期的妇女运动在处理家庭关系时,形成了特殊的“既斗争又联合”的家庭统一战线。一方面,妇女参加生产巩固了她们与家庭的联系,她们以“能干媳妇”的身份获得尊敬[6](P652),这依然遵循着农村传统的“妇德”框架;但另一方面,农村妇女在新的经济关系中寻得了协商与斡旋的空间,同时也潜移默化地改变了农村的性别权力关系。一如王玲珍研究所指出的,并不能据此判定农村的妇女解放在社会革命的宏大目标中被牺牲了,而应将其视为深耕于农村语境的社会主义女性主义本土化实践;妇女运动与传统乡村父权制、社会主义革命之间的多元协商恰恰反映了农村中国的复杂性[7]。
种种协商关系的背后是各方思想之间的碰撞与竞争,即使在新中国成立以后,社会主义式的男女平等与传统性别观念之间的拉扯依旧在农村不断上演。最突出的两个方面分别表现在推行现代婚姻观和动员农村妇女参加生产的过程中,农村都曾经有过强烈的抵制,反对的声音既有来自男性,也有来自女性的。新中国成立之前,大部分地区的妇女(如陕西地区)只在农忙时参加辅助性劳动,“许多妇女思想上轻视劳动,认为下田劳动是耻辱,是命不好才受的苦”[8](P180)。今天我们早已习以为常的婚姻观在当时的农村遭到了强烈反对,一些地方的农民拒绝遵守新法,认为它是“离婚法”“妇女法”,“用来压迫男人的”[9]。纵然,《婚姻法》《土地改革法》的相继颁布已经为妇女权益提供制度化的保障,然而实现男女平等不能仅仅依靠法律强制,它更多的是牵涉到借助宣传教育转变既有的性别观念。
(二)观念改造与政治宣传
反对旧思想、宣传新思想可以说是概括了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践行启蒙教育的主要方法。但新中国的观念改造并不能与此前晚清民国的国民性改造等同而观,它一方面继承了五四的启蒙遗产,但另一方面极大地受到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宣传观的影响,需要被置于启蒙教育与政治宣传的双重脉络下去看待。如全国总工会主席赖若愚在1952年的评论中提到,建国初期虽然改变了封建的经济基础,但新的经济基础和残余的封建上层建筑之间还存在矛盾,“残余的封建上层建筑(封建的婚姻制度、家庭关系、风俗习惯、道德观念等),对新的经济基础起着消极的反作用。因此,在广大农村中,要努力扶植新生的上层建筑(新的关系、民主和睦家庭等),努力宣传这些新的典型”[10]。这类表述主要取径于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理论,强调从两者的相互作用关系出发去看改造观念的重要性。
此外,列宁主义的宣传观对中国共产党早期实践政治宣传有着不可或缺的指导作用。列宁思想在中国的传播有两个关键时期:一个是在十月革命成功后,《新青年》逐渐转为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的宣传阵地;另一个是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安排出版了一系列的列宁著作③可参见王东、陈有进、贾向云著:《马列著作在中国出版简史》,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9年。。列宁的著作中比较系统地谈到意识形态宣传的是他写于1902年的《怎么办?(我们运动中的迫切问题)》一书,虽然这本书主要用以反击当时俄国甚嚣尘上的经济派,批评他们鼓吹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立场,但他在书中对工人阶级的自发性与自觉性的经典讨论,成为后人解读苏联政治宣传的重要理论来源。其中常常被引用的一段表述是:“我们已经说过,工人本来也不可能有社会民主主义的意识,这种意识只能从外面灌输进去。各国历史都证明,工人阶级单靠自己本身的力量,只能形成工联主义的意识……我们应当积极从事在政治上教育工人阶级的工作,从事发展工人阶级的政治觉悟工作。”[11](PP112-114)布尔什维克党认为他们掌握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历史发展的真理,从而得以指导无产阶级革命。不同于马克思的是,列宁认为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意识并不会自发地产生,而是需要党的激发和培养[12](P5),这也是为何社会主义阵营的国家都十分重视政治宣传作用的原因所在。除了马列主义宣传观,毛泽东的文艺思想也深刻地影响了新中国的政治宣传实践。从抗战时期《古田会议》上首次突出宣传工作的重要性,再到后来的《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毛泽东一方面强调“喜闻乐见”的宣传策略;另一方面又以“服务”来联结“工农兵”与“文艺”的辩证关系,凸显文艺创作的群众性和本土性。这些观点恰恰回应了他提到的“对人民要用民主的方法和自愿的方法来教育”[13](P31)。
从这些理论思想出发,我们可以同样地将性别观念的社会主义改造理解为由外向内的政治宣传。为了达成性别观念的社会主义改造,需要有外界的力量经由各式的宣传工作将这些思想带到群众中去。1949年的妇女大会强调了将宣传教育列入工作范畴,以便借此“有意识、有步骤地消除尚存在的各种封建思想和传统习俗”[14](P357)。这在之前的组织工作文件中甚少提及。遗留的父权传统习俗和家庭文化意识亟待重构,取而代之的将是现代的、社会主义式的男女平等观念。宣传《婚姻法》与讴歌劳动妇女也成为20世纪50年代关涉农村性别观念转变最重要的主题。当时的宣传形式十分多样,大部分借鉴了延安时期群众文艺的宣传和动员经验,既利用政策宣传月开展系列活动[15],也出版了大量的群众普及读物④西安的长安书店出版了大量的通俗读物,其中有一个系列名为“劳动生产通俗戏曲唱本”,主要是以普及经济政策为主题。,还包括培训各地的民间艺人在农村说唱相关的快板书⑤可参见西北行政委员会文化局编印:《我的创作和说书经验》,1954年。。但新中国成立以后的宣传方式与延安经验最大的区别还在于流动放映开始大规模地进入农村。
(三)农村放映与电影的现代性
在电影发展的初期,世界各国均普遍地出现过流动放映[16](PP100-102),但在农村地区建立大规模的放映网络,则是社会主义国家特有的现象。虽然国民政府在抗战期间曾经安排了数支放映队在西南地区通过电影动员当地群众,但囿于资源的限制,这些放映活动无论从规模还是持续性来看都无法与毛泽东时代的农村放映相比。1953年,中央政府颁布了《关于建立电影放映网与电影工业的决定》,确立了农村的流动放映作为电影传播的重要路径。这种大力发展全国性电影放映网络的策略,主要来源于两方面的影响:一方面,苏联的电影传播策略影响了包括中国在内的社会主义阵营国家[17](P28)。二战后,苏联力图将国营放映网的观众数量增加一倍,大量向基层供应新放映机、发电机和放映队专用车,以实现农村的电影化[18](PP553-558)。电影被视为最普及最群众化的党的有力的宣传工具,作用于“使先进的社会主义思想在所有的人们中间迅速地成长起来”[19](PP7-8)。另一方面,毛泽东提出的“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指导方针也使发展农村放映成为必然之举,因为让农民看上电影,真正响应了“服务”的号召。那时的媒体经常转述农民的观影反应,如提到群众说“多亏共产党,让穷苦人才能看上电影”[20](P17)。电影放映加强了新政权在基层领导的合法性,凸显了共产党与旧社会民国政府两者在对待农村文化发展态度上的差别,从而也代表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由于毛泽东时代的农村在制度上和文化环境上有其特殊性,使得农村的早期放映与既有的早期电影研究的对象有着很大的差别。随着20世纪80年代电影学的历史转向,早期电影(early cinema)已然成为一个重要的研究门类。以芝加哥大学为核心的电影文化研究群体,将电影与19世纪的都市经验、感觉机制以及时空技术的变化联系在一起,确立了现代性在早期电影研究中的地位[21]。米莲姆·汉森(Miriam Hansen)提出的白话文现代主义(vernacular modernism)将叙事电影视作现代主义的一种文化表现形式,认为其实现了文化的真正大众化,具备民主的特性,使得观众的欲望通过观影活动可以得到实践和言说[22],这也一度成为研究民国早期电影的范式[23]。然而,这种现代性与电影之间的勾连是以大都市文化为土壤的,并不适用于解释毛泽东时代早期的农村观影经验。
毛泽东时代的农村放映区别于民国早期电影的最大之处在于,农村的文化语境不同于都市大众消费文化,它有着以农业社会为基而生发的民间、民俗传统。20世纪50年代放映队进入农村的时候,距离电影传入中国已近半个世纪,民国时期的大城市(如上海)也已经发展出较完善的电影工业了。然而,农村的大部分农民在新中国成立之后才首次看到电影。电影对于农村观众来说,更是一种“现代性的奇观”[24],一方面,电影放映及其设备代表了先进的现代技术,例如很多农村观众是通过电影才第一次接触了“电”⑥根据电影放映员的回忆。此外农村家用电直到80年代才逐渐普及,可参看罗国亮:《中国农村电力发展政策:演变、问题与展望》,《经济研究参考》2011年第51期。;另一方面,电影的镜头语言对于农村观众而言是完全新奇的、不易理解的。这也是为什么放映队的工作包括了让群众“看到”和“看懂”两个大目标[25],即不仅仅要将电影送到最偏远的地区,还要通过现场解释帮助观众理解电影。
这种植根于农村既有文化习惯的早期观影经验指向了电影的另一种现代性,它标记了现代的社会主义政治宣传进入传统乡村社会的瞬间,随之而来的是现代技术的理念和进步的文化思想。在这样的放映空间中,放映员作为文化中介者尝试将全新的观念和再现形式转译为本地观众能够理解的语言。以男女平等这个宣传主题为例,其中的放映涉及怎样借助新式的技术和电影文本,宣传社会主义式的性别观念,取代旧有的封建思想,建立新旧的对照,形成优劣价值的评价。这一转译的过程,既着重于宣传新的思想,更强调要使得新的观念进入既有本土文化的表意系统,并通过挪用既有的文化符号,辅助观众重新理解什么是先进的、进步的性别观念。电影放映作为新的宣传形式,包含了新旧含义的来回往返,它的核心是去协商传统性别观念与社会主义主流性别建构之间的冲突关系。
二、宣传农村妇女新形象:实践多元的放映技艺
20世纪50年代是农村放映发展的初期阶段。以陕西省为例,截至1957年底,全省共有农村放映队157个,基本达到每县5到8个放映队,全年每个行政村可以观看电影2到3次[26](P34),农村放映的影片更新程度因而远远低于城市影院。在这些为数不多的影片中,以农村妇女问题为主题的电影主要可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宣传《婚姻法》,另一类是宣扬能干的农村妇女形象⑦如《儿女亲事》《赵小兰》《结婚》《妇女代表》《小姑贤》《刘巧儿》等。陕西省电影发行放映公司:《电影发行放映统计资料汇编1953-1962》,第70-75页。。通过农村放映的空间,新的农村妇女形象得到宣传,动摇了既有文化中对女性身份的固定想象。通过讨论三类文本及这些文本在农村放映空间中的传播实践,本部分将分析不同的农村妇女形象是怎么经由多元的放映技艺得到宣传的。这其中包括:力争婚姻自主的年轻女性、冲破家庭关系束缚的妇女干部以及进入公共劳动中的女劳模,三种形象的呈现分别涉及了农村女性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如何面对新的婚姻关系、家庭关系以及劳动关系。
(一)《婚姻法》宣传:电影与快板的视听互文
1950年拍摄完成的《儿女亲事》是最早在农村得到大范围放映的《婚姻法》普及教育片之一。这部影片于1951年开始随着放映队在陕西的农村地区巡回播放。它讲述的是农村姑娘李秀兰反对父亲的包办婚姻,坚持婚姻自主,并在《婚姻法》的保护下与恋人王贵春结合的故事。虽然情节并不复杂,但对于从来没有或是依然很少接触到电影的农民来说,电影的镜头语言和叙事逻辑是完全陌生而稀奇的。早期的农村观众会好奇电影幕布上的人是怎么装进去的,电影里的人怎么忽大忽小[27](P11),反而更少关注到影片的内容。放映员在放映中,常常碰到的问题是农村观众注意力分散、行动自由、无法保持安静。为了确保引导农村观众能在看电影中受到教育,放映的管理部门总结了一套关于映前、映中、映后解说的工作规范,一方面用于取悦农村观众,使之形成新式的观影习惯,另一方面也保证了政治宣传的有效性。
刘兆鹤是陕西省当年最早一批放映员之一,他还记得在50年代初下乡的时候,除了放映影片这项技术活之外,他还要现场表演说快板:“那时去西安买的小册子,印的快板,在放电影的时候说。有时放映前会放唱片,当时群众也不是很爱听。但我一说快板人们都拍手。现在还记得快板里头有个是宣传婚姻法的,叫《秀女结婚》。”⑧刘兆鹤,采访,西安,2015年6月27日。为了以喜闻乐见的方式普及政策,50年代初西安的长安书店出版了一系列群众普及读物,《秀女结婚》是其中最流行的快板之一,我采访的好几位老放映员都还记得它的开头怎么说唱。虽然这个快板书并不是特地为影片解说所作,但它的内容跟《儿女亲事》的情节十分相似,因此常常用来作为电影放映的开场表演。《秀女结婚》以第三人称讲述了秀女两次婚姻经历,第一次由于父母包办婚姻嫁给了地主,生活悲惨;第二次由于《婚姻法》的颁布让她可以离婚并与喜欢的对象结合。影片的对白是普通话,而当地的农民习惯听陕西方言,加之影片画面转换对于习惯看戏的农村观众来说并不是很适应[28],这使得放映过程中观众容易被影片内容之外的事物吸引。而快板恰恰是用来引导农村观众把握影片内容的一种有效形式。作为民间历史悠久的文艺形式,快板的节奏、韵律协助调动了群众的听觉注意力,为理解视觉画面提供了基础。
从前的农村观众看戏时对故事的内容早已烂熟于心,而面对电影中多个场景的转换和不同角色的轮番登场,他们常常感觉到不习惯。快板提前告知观众影片的内容,为他们接下来观看影片做准备。而影片中形象化的再现又反过来印证了快板中的口头描述。《秀女结婚》的开头就控诉了包办婚姻的害处:“旧社会、王法瞎,婚姻不能由自家!秀女年长十七八,他大给娃寻下家。别的事情他不管,一心想卖‘两千花’!”[29](P1)短短几句,就概说了前半段的剧情,影片中的爹爹思想封建,瞒着女儿寻婆家,他看不惯秀兰在生产中与队里的青年王贵春过往甚密。快板简明扼要地点出了父亲代表的是旧有婚姻观念。随后,快板解说了秀女第一段婚姻的惨况,并用“有苦难言”来总结。而这“难言之苦”却在电影中得到了具象化的表达,影片以妇女主任之口述说了虹采因包办婚姻投井自尽的惨事,还多次特写了她悲伤的面容。听觉的文本《秀女结婚》与视觉的文本《儿女亲事》之间形成了互文关系,彼此的主题得到深化和加强。影片的结尾,当顽固的老爹看到女儿、女婿在田间欢快地劳动,他终于认可了婚姻自主的好处。《秀女结婚》也通过描绘生产的图景想象了一种美好的夫妻关系:“二次嫁了一农民;自由婚姻自作主,自己选择对路人……欢欢乐乐闹生产,男的耕田女纺线,一天手足都不闲。忙时在家把活做,有空就上识字班。劳动生产是模范,识字班里又占先!农会、妇女做骨干,村里都把他俩的好样看。”[29](PP8-9)据此我们可以看到,新旧婚姻观念之间的矛盾在经济生产的场景中得到化解,而新型的夫妻关系也通过双方共同参与劳动得到构建。
(二)“新妇女”:性别化的解说
以集体生产的大目标化约新旧观念之间的冲突无疑过于理想化,三年后拍摄的《妇女代表》对这个问题进行了更细致的思考。如果说《儿女亲事》讲述了妇女在结婚问题上的自主权,那么《妇女代表》则讲述了妇女在婚姻自主之后依然要面对的生活挑战,它直接触及当时农村妇女在社会变革中遇到的新问题。该影片讲述了一场家庭冲突怎样从爆发到解决的过程,观念保守的婆婆和丈夫因看不惯媳妇张桂容在外参与公家事务,与之发生争吵。面对丈夫和婆婆的刁难,张桂容先是采取忍耐劝说的态度,直到丈夫动用暴力反对她出门为公家办事,她态度瞬间强硬起来,“你凭什么限制我的自由”,并抢过丈夫手中的棍子折断甩到地上。她的丈夫气不过让张桂容滚出去,张桂容跳到炕上拿出地契房契高举着说“两张地契有我一张,三间房子有我一头,这是共产党跟人民政府分给我的”,镜头先是仰拍张桂容义正词严的形象,接着俯拍她丈夫哑口无言的神情。借助夫妻吵架一幕,原来不平等的性别关系被扭转了,一连串的戏剧冲突凸显了女主角冲破了“小家”的束缚,与“大家”/公家建立了联结。
官方介绍资料中强调该片的主旨是宣传“民主新家庭”,建立平等的夫妻关系[30](P92),而这种新的家庭秩序在影片中是通过展示“新妇女”的形象来实现的。如影片的最后,张桂容的丈夫转变态度并让她以后做当家人,但她拒绝了:“我不是想翻过来像你待我那样,我为家里好,你也为家里好,咱们有事商量着办。”根据已有记录,放映员的解说词中特别针对这一幕插入了映间解说:“张桂容是个讲民主的人,她反对别人压迫她,也不愿站在别人头上。”[31](P76)通过解说,放映员强调了新家庭并不是权力关系的逆转,而是平等相待、相互尊重,而民主的含义恰是在讲述私领域的性别关系时得到具现。有趣的是,记录中也解释了这一额外的解说是为了回应当时农村观影中出现的一些问题。夫妻争吵的画面在农村放映的时候,由于视觉性放大,很容易喧宾夺主,反而激化了村里的夫妻矛盾[31](P76)。而影片又为了树立新旧思想的两种人物,对两方的人物进行了反差强烈的塑造,丈夫表现为行为鲁莽、满口粗话,而女主角则是知书达理、不卑不亢,这种夫妻形象是通过夸张化地处理性别差异而建立的。
当我们把电影文本与当年的解说词放在一起对照阅读,可以看到放映员用声音抢夺镜头语言的解释权,引导观众忽略打架的镜头和负面的男性形象,转而认同张桂容这一角色。张桂容行动上具备了传统劳动妇女的优良品质[32],她看到丈夫的裤子破了立即拿来针线缝补,出门学习也不忘照顾孩子,在外劳动的钱都用来贴补家里。张桂容由于以平等民主的方式成功处理了家庭矛盾,她的女性形象又紧密勾连了平等、自由、民主等政治概念。在影片中,平等和民主主要指涉了家庭内部的性别关系,而自由在电影中更多的是意指女性得以跨越小家进入公共空间的自由。然而,放映中也常常会出现转译的内容偏离官方要求的情况,如一个放映队为了让农民更好地理解影片内容,将《妇女代表》的片名解说为“好媳妇”,而被官方批评为庸俗[33](P8)。“妇女代表”作为新的政治性指称并不容易为农民所理解,但“好媳妇”虽是农民观众熟悉的称谓,却又难免落入从属于封建父权制话语的俗套。这个小差错能让我们看到,在放映员转译的过程中,需要不断地协商主流的话语建构与本土化的情境。
(三)女劳模与本土化的幻灯放映
歌颂女劳模是20世纪50年代关于性别议题的又一官方宣传主题。新中国成立伊始,国家沿用了延安时期经济工作的经验,通过发掘在生产运动中有特出表现的个人,将他们树立为典型人物,并授予劳动模范的称号[34]。与此同时,媒体对劳模的事迹进行广泛报道和全国性的宣传,由此形成基层效应,促使群众认同这些平凡又伟大的劳动英雄。50年代中期,随着农业合作化的发展,出现了劳动力不足的现象,因此提出“有必要发动过去不参加田间劳动的广大的妇女群众参加到劳动战线上去”[35](P64)。发动妇女参加劳动,也被认为是实现“真正的男女平等”的必由之路[35](P64)。妇女劳动模范(简称女劳模)的出现与动员宣传的需求一拍即合。尤其在大跃进时期,官方媒体包括电影、报章塑造了一系列女工、女农民的形象[36](P84),旨在大力表彰女性的公共参与,改造以往轻视女性社会劳动价值的观念。
近年来,农村女劳模的个体经验也成为考察毛泽东时代男女平等的切入点,相关学者希望借此来克服此前研究中仅关注官方主流话语的片面分析。贺萧(Gail Hershatter)和高小贤关于陕西采棉模范的研究启发了我们重新审视毛泽东时代农村妇女的主体性。她们结合口述史和历史档案来检视陕西20世纪50年代一位采棉英雄的女性经验,呈现出了她如何通过挪用官方话语来应对农村保守势力质疑的主体性策略[37]。陈庭梅(Tina Mai Chen)将这种个人与官方主流话语之间的协商概念化为情境中的女性能动性(situated female agency)。她在以女拖拉机手为对象的研究中指出,毛泽东时代的农村妇女并不是完全服膺于官方话语操作,她们作为能动的个体懂得运用媒体再现中的语汇为自己在传统的社区中觅得新的文化身份[38](PP270-271)。以上研究为理解毛泽东时代的妇女动员提供了新的思路,但她们关注的主要是官方层面对女劳模的主流再现,而不涉及农村社区中微观的性别再现。流动放映作为呈现农村日常化的视听空间,让我们可以看到另一种对女劳模的再现方式——幻灯放映。
在前两部分关于电影放映及其解说的段落中,我们可以看到政府主导的媒介怎样在农村放映时参与对性别关系的重构,而幻灯放映的不同之处则在于它是植根于本土经验的文本生产。由于农村放映需要紧密配合党和政府中心工作的宣传,而电影的更新速度远远跟不上中心工作的主题变换。电影公司于是发放幻灯机给放映队,鼓励队员自行制作幻灯片及时配合宣传。放映员会在玻璃片上写字、画画做成幻灯片,并把采访到的人物故事编成小调搭配着幻灯现场说唱。在笔者查阅的历史档案中,还能看到零星的关于幻灯放映的记录,讲述农村妇女的劳动经验是其中的重要内容。一份工作会议文件中介绍了一个放映队幻灯放映的优秀经验,他们先收集当地模范人物并编写成材料,在幻灯上写上名字,还配上顺口溜介绍情况,其中有一例谈道:“在紫荆社配合生产、水利、灭七害英雄模范受奖大会,我们编了:女英雄焦玉兰,兴修水利是模范,背米背娃到石马山,挖、担赛过男子汉。消灭七害算英雄,七天七晚没下阵,爬山追赶不懈停,干劲赛过穆桂英。大家很高兴得到表扬,因为上了‘土’电影。”[39](PP66-67)20世纪50年代后期,国家工农业发展需要大量劳动力,动员妇女参加劳动成为宣传工作的重中之重,媒体、文艺创作领域都出现了众多劳动妇女的形象。幻灯放映中对女性模范人物的表彰,很大程度上重复了官方媒体中对女劳模的描写。它强调女性劳动能力的优越性,逆写了女性在生产中的弱势地位。
但与主流媒体精致化的叙事不同,这种宣传虽是粗糙的却充满了民间生活气息。伴随着顺口溜的说唱韵律,农妇焦玉兰与民间传说女英雄穆桂英建立了符号意义上的联系,这也使得本土社区中的平凡妇女在农村的公共空间中变得可见。幻灯放映的特殊性还在于,它营造了农村社区内部的传播空间,注重关照本土的经验。把幻灯称作“土电影”,除了说明它技术还不如“洋”电影成熟,还标识出官方生产与本地创作之分。在不同村子的放映中,放映员通过幻灯呈现具体的人物事迹,这个人物虽不是全国性标兵,却是身边的模范。它所引发的传播者与接收者之间的互动是双向的、即时的。这也是为何在放映中,农村观众得以对放映员提出挑战。有放映员曾经提到她所表扬的对象向她表达了不满:“有时候,我们用幻灯宣传表扬了人家,她倒找上我们来了,说你们怎么把我画得嘴歪眼斜的,还不如不表扬”[40](P25)。在幻灯放映的本土空间中,女性形象的生产与接收是同时的,这是一个不断协商意义的过程,作为创作者和传播者的放映员持续受到本土观众的挑战和质疑。
三、跨越边界:女子放映队的主体性经验
以上部分主要探讨的是流动放映在再现的层面如何转变农村传统的性别观念,而接下来笔者将转向关注放映活动的实践者——女放映员。如果说放映的影像、幻灯曾经给农村的观众带来了强烈的视觉冲击,那么女子放映队在农村中的出现更是极大地构筑了农民观众对现代女性的想象。从这个角度来看,女放映员的在场也成为传达男女平等理念的重要方法。她们的放映经验既同时展现了女性与现代技术的密切联系,更具象化了女性通过流动于公/私空间而实践不同主体性的可能。然而值得一提的是,倚仗国家力量进入乡村并不会天然地赋予女放映员们优势的地位,她们作为现代职业女性的代表仍然必须与农村传统的保守观念作抗争。这些日常化的抗争经验向我们展现了一幅幅复杂的新旧性别观念博弈的图景,既有发生在放映空间内的,也有内置于女放映员生活空间中的。
(一)并置女性身体与现代技术
正如前面提及的那样,20世纪50年代也是社会主义妇女运动开始得到全面推进的年代。无论是农村还是城市,妇女都被动员起来加入公共领域的经济生产中。职业女性的形象得到广泛地宣传,因而越来越多的“女子队”“女劳模”进入主流媒体和公众视野。1953年,陕西省第一女子电影队(以下简称女子队)成立,也一定程度上顺应了上述历史趋势。女子队最初主要由三位中学刚毕业的女学生组成。根据队长卢树坤的回忆,她是被校长安排加入放映队伍的。“我们校长当时也是县教育局的,他说现在放映队缺乏党员力量,所以希望我们能加入。当时我们还是团员。他还打消我们的疑虑说现在是新中国了,女的可以跟男的一样有发展机会。”⑨卢树坤,采访,西安,2015年8月5日。在我的采访中,大部分女放映员加入放映队的原因都是基于学校或单位的安排,她们的讲述中常常提到有一位年长的男领导给予她们鼓励。这样的叙述似乎十分符合五四以来关于女性解放的评价,也即中国的妇女运动向来是由男性开明知识分子最先发起的,女性在其中总是缺席的、被动的。但是这样的观念忽视了历史作为复数的、非线性的可能性,遮蔽了不同群体在推进这一议题的努力,其中的群体包括了早期的传教士、女教师、女工及本土知识分子等。卢树坤的经历很好地说明了这一问题,她对男女平等的理解早在成为放映员之前就已经形成。她的母亲是一位女校的教师,对她的影响很大。访谈中,她拿出自己年少时着男装的相片,谈到“我很早就显现出了反叛,喜欢穿帅气的男装,我母亲对此亦十分宽容”⑩卢树坤,采访,西安,2015年8月5日。。相似地,另一名女子队放映员袁秀英提到,当时的她并不觉得男女差别大,因为从很早开始她就跟男同学一起上课、相互竞争⑪袁秀英,采访,西安,2015年6月26日。。
但是,她们习以为常的性别观念,在当时的非知识分子阶层还没有得到普及。女子队的队员们至今仍清楚地记得她们第一次带着机器走出城门的情形:“我们下乡那天走出城门的时候,看到路的两边站满了看热闹的老乡,他们从来没见过这样的情形。出嫁都没这么热闹。我们就坐在牛车上,车上放着设备和我们的行李,绑了堆得高高的。我们就坐在上面,觉得很自豪。”⑫袁秀英,采访,西安,2015年6月26日。从以上描述中,我们能感受到女子队下乡的过程充满了仪式感,从车上红花到走出城门,放映大队对此特意做了安排。路人之所以感到惊奇,一方面是因为女性集体公开出现在当时尚属罕见,另一方面也是好奇车上这些笨重的钢铁设备与一群女孩子的联系。在这样的场景中,女性的出场与现代机器的同时显露组成了视觉奇观,在当地传播了现代女性——女放映员——进入公共空间的形象。
这种并置女性身体与现代技术的编码方式,在毛泽东时代的主流媒体中曾经反复出现。毛泽东曾在1956年谈到他对男女平等与现代化关系的看法:“只有笨重的劳动都自动化了,农业也都机械化了的时候,才能真正实现男女平等。”[41](P151)五六十年代描绘各种职业女性的海报中,常常呈现女农民与拖拉机或女工人与焊接器的图像,这些符号正是试图去传达新的信息:现代化技术弥补了男女在体能上的差异。当时的文化再现一定程度上挑战了女性的劳动能力不如男性的本质主义观念。学者丘静美曾指出,农民/妇女在毛泽东时代的革命叙述中处于一种矛盾的位置(paradoxical place),他们同为受压迫最深的群体,保守的观念根深蒂固,但同时又更具有革命性[42](PP290-295)。在毛泽东时代的文化再现中,落后性恰恰实现了某种逆转,被表现为先进的、革命的。陈庭梅对女劳模形象的分析很好地说明了这一问题。她指出,作用于女性身体的文化再现暗示了中国生产力的发展,既反映了社会主义男女平等,又反映了中国国家的“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及其社会进步性[38](P278)。这也是为什么女性形象更经常地被用于表现新中国的现代化,而女子放映队也更经常地被指派为特定政治活动的表演者。
1954年,陕西省电影公司和电影大队联合举办了一次科教片展览。科教片作为一种纪录片类型,涵盖了记录和传播现代科学知识的内容。特别是在毛泽东时代的中国,科教片得到大量生产并在农村广泛放映,内容包括种养殖技术、现代机器的操作方法等。在众多放映队中,唯有卢树坤的女子队被选为执行科教片展览的放映任务。在为期一周的展览活动中,一位苏联专家的到访使得女子队的工作变得更加不同寻常。“有一天大队干部通知我们说外国专家要来看我们放映。我们非常紧张。当天晚上还多了很多观众,他们都想来看看洋人”[43](P39),卢树坤在回忆录中提到。她们随后出色地完成了任务,并获得了苏联专家的好评。自此女子队在同行中打响了名声。当我问到为何会选择女子队来应对专家考察,袁秀英谦虚地说道:“其实我们也不清楚为何科教片展览周找我们,苏联专家来的时候也找我们。我估计是因为当时的女子队还是新事物吧。”⑬袁秀英,采访,西安,2015年6月26日。
与其将女子队的工作安排完全看作大队的随意指派,笔者认为更需要细致考察此间的运作逻辑。如果说因为女子队具备某种“先进性”,从而使得她们更容易被官方选择用于代表社会主义中国的进步性;那么我们还应该进一步追问:这种“官方选择”是否也暗含了某种言说的框架,而这一框架把“性别”当作中国现代性得以言说(articulate)的方法。事实上,正如琼·斯格特(Joan Scott)提到的:概念化的语言总需要挪用差异来表达实在意义,而性别恰恰是言说差异的主要方法[44]。同样地,抽象的国家意识形态要在最基层农村获得理解,必须通过具体的再现和言说,性别/妇女的框架恰恰为在农村社区言说国家的现代性提供了语汇。在农村群众层层围观的中心,女子队不仅仅是向苏联专家放映《玉米杂交》《双铧双犁》等科教电影,她们同时也被置于争夺现代性阐释权的场域中。洋人专家的在场提醒着中国的落后位置,然而,通过使用女性身体来操作现代科学知识的传播,实现了权力位置的逆转,社会主义中国的优越性被纳入男女平等的国际性话语中。
(二)流动在公/私领域中的女放映员
在前一部分中,笔者阐述了女放映员产生的历史背景以及“女放映员”的符号化功能。接下来,笔者将考察的对象转向女放映员们在农村的工作经验。
回想起从前的职业生涯,许多放映员感到最辛苦的是必须不断地转点:前一天晚上在村里完成放映,第二天就必须载着设备赶往下一个村庄,一年有两百多天都在不同的村庄之间穿行。除了农村工作之外,他们还要不时地来回到城市租片、还片以及接受培训。基于这种特殊的工作性质,女放映员也不得不穿梭于不同的城、镇、乡空间。官方媒体经常通过描绘放映员的长期流动性(mobility)来表现他们工作的艰辛和为人民服务的精神。五六十年代的《电影放映》杂志刊发了大量类似的报道,其中有许多文章讲述了女放映员的故事,内容基本上围绕两个方面来展开:一方面,它们记录了在山川乡野间转点工作的困难以及女放映员如何排除万难完成任务[45](PP58-63);另一方面,文章还介绍了女放映员具备了出色的放映技术和宣传能力⑭可参看《电影放映》1957年第9期、1960年第4期、1963年第5期等。。但是,这些以“女放映员”为主角的文章与报道男放映员的故事往往内容相似、大同小异,完全没有提及性别上的差异。如果将文章内主人公的性别换成男性,也不会对理解文章意思造成影响。这种写作方法,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毛泽东时代的性别观念,也即“男女一样”。因而,在主流的叙述中,女性的表现必须符合男性的标准才得以被记录,这导致无论是放映技术上还是工作经验上的报道均完全被去性别化。
尽管如此,拨开单调重复的叙事,我们还是能够找到一些不一样的故事。在一篇少有的人物采访中,记者记录了与女放映员陈秀莲的对话。陈秀莲讲述了她感到最难受的事情不是转点工作的辛苦,而是老乡的不理解。她原来以为放映工作很简单,但当她们开始下农村的时候,老乡们口口声声地管她们叫“耍电影的”“女戏子”,有的还叫她们“电影婆”。陈秀莲感到很委屈:“听到这种令人刺耳的‘称呼’,心里真是难受,我们是为他们放映电影的,他们为什么对我们这样不尊重呢?”[46](P25)“女戏子”和“电影婆”的称呼暗含对女性“抛头露面”的指责,也带有贬损女性在公共场合自我展示的含义。陈秀莲的感受并不是孤立的个案,在陕西女子放映队的口述史中也有提到类似经历:“有一天我到乡里街上去贴海报,边走边在路上拿着喇叭大声宣传今晚有电影。刚一喊完,过来一个恶狗,在我腿上狠狠地咬了一下。把我疼死了。结果那群众都哈哈大笑,说这下子把‘电影婆’给咬了。把我难过的!”[43](P17)女放映员在早期工作中的受挫源于群众的不认可,而这种不认可实际上来自于将女性排除在公共领域之外的刻板印象。而在男放映员的故事中,则没有听说过类似的事情。我在采访电影公司的老经理周倬时,他提到了老乡对男放映员的印象,基本上都认为放映员是操作技术搞宣传的,还比较尊重⑮周倬,采访,2015年6月23日,西安;类似表述最早还可参看《西北影讯》1951年第1期,第16-25页。。农村观众倾向于把女放映员当作表演者(戏子),而把男放映员看作技术员、教育者,这种基于性别差异而做出的评价,反映了早期毛泽东时代农村保守的性别观念。女性出现在农村社区的公共空间被认为是突兀的、不合适的,女性在众人面前开展工作(大声宣传、操作放映)随时都可能遭受到异样的眼光。与男放映员不同的是,女放映员在进入农村之初,首先要面对的是如何转换女性在农村原有文化中的想象性位置。
针对这样的挑战,陈秀莲采取的是通过帮助老乡干农活,融入社群,“与群众搞好关系”[46](P25)。女子放映队的队员们则是以更高标准来要求自己的工作。她们保持了300场无过错放映,在当时是最高纪录。通过与群众建立日常化的联系,并以更严格的标准来提升业务能力,女放映员们向农村观众证明了职业女性的工作价值。然而,除了在业务能力上的高要求,她们的行为也被更严格的道德所规范。卢树坤说起早期农村观众对她们的误会:“第一年,我们几个女孩跟另外的几个男放映员一起工作。有个大妈看到我们就说你们几妯娌关系真好。我跟她说我们不是妯娌,我们还没有结婚呢。她就说哪家姑娘没结婚出来干这个。那时候不相信没结婚的女孩敢到处乱跑。”[43](P17)她们为了“减少麻烦”,只跟村里的姑娘相处,并且很快也都各自成家了。有意思的是,在陕西省电影局的报告里,却提到了男放映员在农村的“作风问题”,批评了有些男放映员在农村“乱搞男女关系”“欺骗妇女感情”[26](P11)。笔者访谈男放映员的时候,偶尔也会听到一些风流韵事。放映员在20世纪50年代还是直接隶属文化局管理,属于“吃皇粮”的人,加之较有知识文化,他们因此更容易受到农村女性的青睐。相较于男放映员更宽松的交往环境,女放映员则以一种更严格的性道德规范自己。这也侧面反映了某种女性解放的悖论:为了挑战公领域中既定的女性弱势地位,女性在私领域中对个人欲望做了更为保守的处理。
但是,她们因能力拔萃和“妇德端正”而积累的社会认可,很快又被新的质疑所打破。从家庭到社会,毛泽东时代的妇女为跨越公私领域付出了艰辛努力,其中最大的挑战包括如何平衡家庭与工作中的女性角色。在一份60年代的自述中,女放映员郑义珍谈到了自己的困惑:“当我们初步地掌握了放映技术以后,听到有人说:‘别看她们现在不错,这是花红一时,等她们结了婚,生了孩子,有了拉腿的就垮了。’我们有时也这样想:妇女的确同男人不一样,男人一个家,妇女两个家,——娘家和婆家,顾这又顾那,将来能不能坚持下去呢?自己也打着问号。”[40](P23)如何从小家庭跨越到大家庭,这是毛泽东时代许许多多的妇女要面临的抉择。因为外出工作而减少居家的时间是普遍的现象,而其中以女放映员的例子尤为突出。像郑义珍这样的女放映员,她们每月只能回家几天,一年的两百多天都辗转于不同的村子。而当女放映员要面对的是性别观念依然十分保守的农村社区时,她们的在场持续地引发了关于什么是现代女性的意义争夺战。
如果说出色的技术能力和道德表现曾经为她们在农村的公共空间谋得暂时的位置,那么要将这种暂时性常态化,还需要更进一步挑战农村关于女性在私领域的想象。母亲是女性在私领域扮演的重要角色,生育一度是掣肘女性在公领域发展的“天然”理由。母亲的职能能否脱离私人空间而实现?人民公社时期曾经作过家务劳动社会化的尝试,但最后都无疾而终,如何同时履行母职与公职依然是女性个人层面要解决的问题。今天的我们重读郑义珍的自述很难推断当时的她是否自主地选择了舍“小家庭”为“大家庭”,但与其判断这种选择对女性来说是解放还是束缚,我们还应关注她自我提问的这一时刻。她对“自己能否坚持下去”的怀疑反映了女性从传统进入现代的困惑与复杂心态,她对“哄一辈子小孩”的反问表现出她并没有完全认同一个旧式的贤妻良母形象,反而是开启了自己关于新式女性的另类想象。这一想象不仅仅意指了一个现代的职业女性,还参与了对女性在公私领域的重新划分,改造了劳动之于女性的意义。
四、结语:对男女平等宣传的再思考
20世纪50年代初,大批中国妇女走向就业的新领域,“男人可以做的,女的一样可以”成为当时主流宣传男女平等的官方话语模式[47](P322)。但在广袤的中国农村,这种社会主义性别建构的论述并没有自然而然地为农村群众所接受。值得注意的是,在推行“去性别化”(男女一样)的男女平等观念时,往往需要采用的是“性别化”的宣传方式。例如强调妇女的妇德和温柔,以及这种女性气质与民主家庭的关系,再如建立农村女劳模与既有文化传说中女英雄或巧媳妇的象征关联。虽然主流的性别建构需要塑造“男女都一样”的去性别化想象,但具体的宣传实践包含了一种不可避免的性别化策略。通过回顾女放映员的自身经历,我们也看到她们与男放映员的经验有着很大的差别,这种实际生活中性别化的差异常常被掩盖在当时“去性别化”的社会主义主流性别建构话语中。
通过进入毛泽东时代早期农村放映的历史空间,本文尝试勾勒出这种新与旧、“去/性别化”观念如何借助电影这一现代媒介得以交汇与碰撞。具体来说,笔者从两个层次来理解农村放映中的性别观念如何得到改造。文章的前半部分从再现的层面进入,通过分析放映过程中的意义生产来考察既有的性别观念是怎么被打破或转化的。农村放映作为混杂了传统与现代经验的媒介环境,为我们理解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基层政治宣传与妇女运动的关系提供了本土化的微观视角。在这一放映空间中,新女性的形象在幻灯、快板、电影中得到再现和传播。借助对放映中各种实践形式的铺陈介绍,本文阐明了新的性别观念如何借由多元的放映技艺得到呈现,并指出了关乎性别观念的意义协商是多个层次的,同时也是多种形式的。以《婚姻法》的宣传为例子,笔者探讨了放映的技艺怎样跟电影的文本内容产生互动,以便确保电影的解读可以达成主流性别建构的目标。其次,笔者还考察了幻灯放映怎样参与了本土化女劳模的构造,而这一构造的方式与以往官方主导的性别建构不同之处在于它深植于本土经验,形成了双向的协商交流空间。
文章的后半部分转向讨论女放映员的经验,以及她们自身与放映技术的互动怎样影响、挑战了农村既有的性别定型。在当时依然传统保守的农村,女放映员的在场已然质疑了农村既有的女性想象。但是,女放映员掌握现代放映技术并没有轻易地为她们在农村公共场合的出现谋得合法性。她们依然需要在日常的实践中与传统的性别观念进行不断地斗争。引入性别视角来分析农村放映,不仅仅在于它可以让我们聆听女性的声音和看到女性的主体性,更在于让我们觉察到性别作为分析方法本身,构成了新中国想象现代社会的重要一环。从个体经验的角度来看,女放映员经验让我们看到农村从传统进入现代并不是顺其自然的过程,性别观念的转换牵涉到复杂而微妙的日常协商。从再现的角度来看,“女性”不只是基于性别差异而做出的指称,它也成为农村中国言说现代的策略,新农村妇女、女放映员的形象意指了社会主义中国的进步和解放。
相较于其他的观念(如政治、经济等),性别观念的改变是一个极其漫长的过程。我们也许早已经走出毛泽东时代用去性别化策略宣传男女平等的时代,但是我们似乎还尚未走进性别平等理念已成为主流认识的社会,特别是在广袤的农村。除了制度上的完善,在理念层面推进宣传、促成平等看待两性关系的文化环境亦尤为重要。通过回顾毛泽东时代的政治宣传经验,我们能看到即便在那样意识形态高度统一的社会,性别观念的改造仍是充满着传播者与接收者之间的各种博弈,它启发我们既要复杂化地去看待宣传的过程,也要具象化地去达成宣传实践。
从文化传播的角度来看,政治宣传从来都不是一个单向的过程。即便是以国家的名义宣传具备无比正当性的理念,都不可避免地要受到接收对象的挑战。男女平等的观念不仅仅是一种公共的政治理想,它更触及变革人们生活中最私密的空间和相处方式。而性别观念的展现恰恰属于日常化的生活实践领域,千篇一律的宣传难以达成有效性是因为它无法渗透进人们日常生活的细节中,因而也无法与过往根深蒂固的观念对话,从而达至转变。要在这种复杂化的宣传过程中寻求突破口,以便实现性别观念的改造,就必须借助具象化的策略。这也是为什么毛泽东时代的农村电影宣传十分注重植根于本土的民间文艺形式,发展多元的放映技艺。借助不同的解说手法,同样的宣传内容和电影文本在不同的情境中生产出各自的在地性,观影的受众因此得以与宣传的文本建立连接,从而形成认同和理解。如果说电影中的女性一度为农村的观众打开了对农村妇女的不同想象,那么女放映员的在场则是实实在在地把观念的宣传从再现的层面拉回政治现实。在这一两重具象化(再现的、经验的)的宣传过程中,抽象的理念被转化为可感知的日常经验,从而实现了观念的改造。
[1]罗琼.发动妇女参加生产劳动的基本经验[A].妇女解放论丛[M].北京:中国妇女出版社,1991.
[2]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妇女运动历史研究室编.中国妇女运动历史资料(1937-1945)[M].北京:中国妇女出版社,1991.
[3]贺桂梅.“延安道路”中的性别问题——阶级与性别议题的历史思考[J].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6).
[4]宋少鹏,周蕾.土地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对农村妇女解放理论的开创与发展[J].浙江学刊,2008,(6).
[5]丛小平.从“婚姻自由”到“婚姻自主”:20世纪40年代陕甘宁边区婚姻的重塑[J].开放时代,2015,(5).
[6]蔡畅.迎接妇女工作的新方向[A].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妇女运动历史研究室编.中国妇女运动历史资料(1937-1945)[M].北京:中国妇女出版社,1991.
[7]王玲珍著,肖画译.中国社会主义女性主义实践再思考——兼论美国冷战思潮、自由/本质女性主义对社会主义妇女研究的持续影响[J].妇女研究论丛,2015,(3).
[8]青长蓉,马士慧,黄筱娜,刘宗尧编.中国妇女运动史[M].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1989.
[9]周恩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关于贯彻婚姻法的指示[N].陕西政报,1953,(2).
[10]赖若愚.毛泽东同志的《矛盾论》是解决实际工作问题的钥匙[N].人民日报,1952-04-26.
[11]刘平斋,陈德言编.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论宣传[M].成都: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8.
[12]Kenez,Peter.The Birth of the Propaganda State:Soviet Methods of Mass Mobilization,1917-1929[M].Cambridge UniversityPress, 1985.
[13]中共中央宣传部编.毛泽东 周恩来 刘少奇 朱德论党的宣传工作[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
[14]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妇女代表大会关于当前妇女工作的决议[A].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妇女运动历史研究室编.中国妇女运动历史资料(1945-1949)[C].北京:中国妇女出版社,1991.
[15]中共中央宣传部编印.中央关于群众宣传工作指示文件汇编[Z].1954.
[16]Taylor,Frank J..BigBoomin Out Movies[A].Movie Going in America:A Sourcebook in the History of Film Exhibition[C].Ed.GregoryA.Waller.Wiley-Blackwell Publisher,2001.
[17][前苏联]波尔沙科夫,史敏徒译.战后苏联电影五年计划[M].中央电影局,1953.
[18]Kepley,Vance Jr..Whose Apparatus?Problems ofFilmExhibition and History[A].Post-Theory:Reconstruct Film Studies[M].Ed. David Bordwell and Noel Carroll.The UniversityofWisconsin Press.1993.
[19]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电影局编印.电影放映资料[J].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1956,(4).
[20]西北军政委员会文化部电影处编.西北影讯(创刊)[J].大兴印刷厂承印,1951.
[21]孙绍谊.重访早期电影:现代性理论与当代西方电影思潮[J].当代电影,2012,(12).
[22]Hansen,Miriam.The Mass Production of the Senses:Classical Cinema as Vernacular Modernism[M].Palgrave Macmillan UK,2009.
[23]张真.银幕艳史:都市文化与上海电影1896-1937[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12.
[24]Gunning,Tom.An Aesthetic ofAstonishment:EarlyFilmand the(in)Credulous Spectator[J].Film theory:Critical Concepts in Media and Cultural Studies,2004,(3).
[25]省文化局关于报送陕西省电影宣传工作会议总结报告的函[Z].陕西省档案馆,档案号:232-1-236.
[26]陕西省文化局编.陕西省农村电影会议专刊[Z].1958.
[27]陕西省文化局编.陕西省一九五七年电影放映工作概况及农村放映工作存在问题的报告[Z].陕西省农村电影工作会议专刊, 1958.
[28]延川县农村电影放映工作调查研究总结报告[Z].陕西省档案馆,档案号:232-1-421.
[29]谢茂恭.秀女结婚[Z].西安:长安书店出版,1952.
[30]孙芋.“妇女代表”的写作经过[J].剧本,1953,(6).
[31]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电影局编印.电影放映资料[J].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1954,(7).
[32]屠岸.“妇女代表”的语言和人物描写[J].剧本,1953,(6).
[33]陕西省文化局编.农村电影工作总结[Z].陕西省农村文化工作会议——电影专业会议专刊,1956.
[34]孙云.中共英模表彰制度的肇始及演变[J].党的文献,2012,(3).
[35]全国妇联编.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论妇女解放[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
[36]徐大慰.影像、性别与革命意识形态——大跃进时期上海女劳模研究[D].华东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9.
[37]Hershatter,Gail.Local Meanings ofGender and Work in Rural Shaanxi in the 1950s[A].Re-Drawing Boundaries:Work,Household, and Gender in China[M].Eds Entwisle,Band Henderson,GE.UniversityofCalifornia Press,2000.
[38]Chen,Tina Mai.Female Icons,Feminist Iconography?Socialist Rhetoric and Women's Agencyin 1950s China[J].Gender&History, 2003,15(2).
[39]陕西省文化局编印.陕西省文化工作会议电影会议专刊[Z].陕西省档案馆,档案号:232-1-182.
[40]郑义珍.毛主席著作给了我们无穷的智慧和力量[J].电影艺术,1964,(Z1).
[41]毛泽东.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文集(第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42]Yau,Ching-Mei Esther.Filmic Discourse on Women in Chinese Cinema,1949-1965:Art,Ideology and Social Relations[M]. UniversityofCalifornia,Los Angeles,1990.
[43]陈墨编.花季放映:陕西女子放映人[M].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2015.
[44]Scott,Joan W..Gender:AUseful CategoryofHistorical Analysis[J].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1986,91(5).
[45]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电影局编印.电影放映资料[J].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1954,(5).
[46]何坪.放映姑娘陈秀莲[J].电影放映,1957,(7).
[47]余敏玲.“形塑新人”:中共宣传与苏联经验[M].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15.
责任编辑:含章
Reconstituting Gender Consciousness in Villages: Based on Mobile Film Screening in Shaanxi Rural Areas in the 1950s
GUO Yan-ping
(Department of Cultural and Religious Studies,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Hong Kong 999077,China)
rural film screening;gender consciousness;gender equality;female projectionists;modernity
Thanks to the promulgation of the Marriage Law and the advancement of collectivized agriculture,the existing traditional gender views in rural China were greatly challenged by the promotion of new images of working women led by the state.Films,which were regarded at the time as a modern propaganda tool,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constructing and spreading the ideas of socialist gender equality.In this paper,replying on oral histories,historical documents and film textual analysis,I examine various practices within the multi-media screening space and see how cinematic experiences may or may not have acted upon the transformation of gender consciousness.In actuality,even though the mainstream construction of gender equality emphasized a gender neutral approach based on the idea of"equality between women and men,"this approach was in effect gendered.That is because its gendered nature was reflected through the techniques applied in propaganda and the neglect of the different experiences between female projectionists and those of their male counterparts.
C913.68
A
1004-2563(2016)06-0028-14
郭燕平(1986-),女,香港中文大学文化及宗教研究系2013级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早期电影史、女性观众学、群众动员、政治宣传。
*鸣谢:笔者在陕西调查期间得到了张颖、张正国、樊胜利、刘晖、崔喜奎、周倬的无私帮助。农村放映事业的老前辈周倬、卢树坤、袁秀英、刘兆鹤慷慨地分享了他们的经验,从各方面启发了本文的写作。我还要特别感谢匿名评审和编辑提供的宝贵修改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