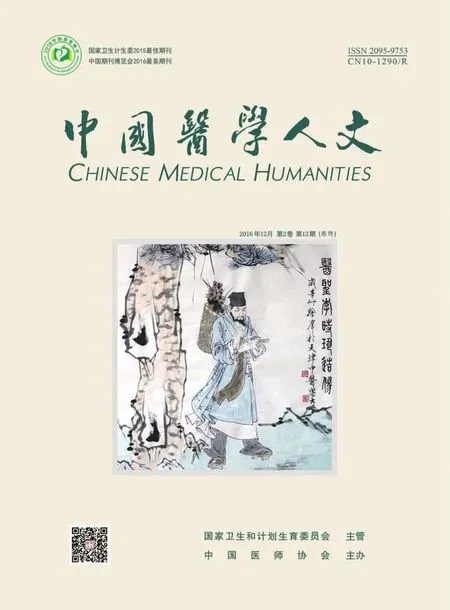聆听疾病背后的声音
文/刘梦苑
聆听疾病背后的声音
文/刘梦苑

“患者悲叹医生不能倾听他们的声音,对他们的痛苦漠不关心……他们也许在技术上得到足够的治疗,但在面对疾病的后果和恐惧时却被抛弃……”丽塔•卡伦在《叙事医学:尊重疾病的故事》的开篇对现代医学做出了如是评价。的确,现代医学的高度发达令人瞩目,但“科学与理性”的背后深藏着“冷漠与麻木”。医生更多地寻求如何提供最先进的医疗技术服务,而忽视了聆听病人对疾病的倾诉,缺乏对病人情感的关注。病人在忍受疾病折磨时,感受不到治疗中的理解与安抚,着实令人唏嘘。
丽塔•卡伦用她丰富的临床经验和广博的人文关怀为我们解开了这个疑虑。这位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内科学教授,用她那诗意的语言向我们展现叙事医学的力量,让患者从自己的讲述中发现躯壳下“自我”的哭诉,让医者在聆听中感受那个孤独灵魂的啜泣,医生和患者的交流超越了医学、生物学的领域,跨越了时空的阻隔,达到的是心灵上的相生与共情。
医学的叙事特征
丽塔在书中这样评价,“医学其实是个叙事性很强的领域。”独特性、时间性、主体间性、因果/偶然性和伦理性,构成了医学的五种叙事特征。我想,这也大概就是叙事医学之所以能填补医患之间的鸿沟、让医患双方得以共情的原因吧。如同本书的题目所言,疾病是故事,是发生在大千世界中形形色色的人身上的故事,不可复制,也难以比拟,这便是疾病的独特性。之于时间性,疾病是时间积淀的产物,将生命的脚步加快并接近远方的终点,而医学企图将时光放慢、停滞,甚或渴望岁月逆流,“医学是一场跟时间的较量”。之于主体间性,就像小说的读者与它的作者所形成的微妙契约一般,医者与患者之间也有着这样的约定,它不是那一纸病历、一张化验单,更不是一条收费凭据,而是两个原本陌生的心灵间真诚的约定。一个人讲述,另一个人聆听,讲述者在讲述中重释自我,聆听者在聆听中走近他者,聆听疾病背后的故事。在某种意义上讲,医学与叙事一直就是不谋而合的。
然而,当医学告别了曾经的神灵主义、自然哲学的医学模式,当哈维的血液循环学说、魏尔啸的细胞病理学等等划时代的研究成果问世,医学似乎从一个极端走向了另一个极端。人们开始一味地强调医学的科学性——可复制性和普遍性:皮肤科医生接诊每日来访的病人就像翻阅一本储存了皮肤科疾病的图册,外科大夫操作精巧的手术如同在流水线上修缮零件。我们太过追求医学之上的共性,医疗活动便成为了在一个个肉体上的重复、重复、再重复。
如今,人们渐渐发现唯数据马首是瞻,视证据为金科玉律,诞生的不过是“为医疗卫生中的科学因素耗尽心血而无暇顾及疼痛、苦难和死亡等人类情感”的一代代专家,医患的鸿沟未被弥合,医患的距离甚至愈来愈远。当人们逐渐认识到现代医学的缺憾,还原医学叙事属性的叙事医学便应运而生。
2001年是文学与医学发展史上重要的一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长老会医院的内科医生、文学学者丽塔•卡伦(R.Charon)提出了“叙事医学”这一新的名词。叙事医学是指具有“叙事能力”的医学实践,而叙事能力是一种吸收、解释、回应故事和其他人类困境的能力,其核心是共情与反思。正是因为医学本身的叙事属性,叙事医学才得以弥补现代医学的缺憾,成为医学发展的美好愿景。
讲述生命的故事
丽塔•卡伦在书中提到,“叙事不只是一种文学形式,它还是一种现象学和认知学的自我体验模式”。叙事般地诉说病情、回首往事,患者开始留意藏在自己身体中的秘密,这个秘密不为人知,甚至连居住在躯壳下的“自我”都并未知晓。叙事给了患者这样的机会,正如心理学家杰罗姆•布鲁纳所说的那样,“正是通过叙事,我们才得以创造和重塑自我。”而在诊疗的过程中,患者并不是唯一的讲述者,医生在聆听,也在讲述。当医生“用第三只耳朵”聆听疾病的故事,用叙事技巧分辨出故事的隐喻、意象与影射,再用深厚的医学经验加以梳理、以独特的文学手段将生命的故事再现,医生是在书写患者的“传记”,却也是在书写自己,更是在书写生命于疾病和死亡面前的故事,这便是共情。
叙事给了患者一次走近自己的机会
如果说“疾病加剧了认识自我的过程”,那么叙事就是让这种对自我的认识、探索得以展现的方式。书中的一个病例很生动地描绘了叙事如何增进了躯壳下的“自我”对身体的感知。一位向来以“我身体很好”而自豪的农产品卡车司机,一直强调自己因腿疾而停止工作。然而,叙事的过程让患者不断回忆起夜间气短、胸闷出汗的细节,一点一滴地透露充血性心力衰竭的迹象。甚至,那个被他的“自我”置若罔闻多年的“枕三个枕头”的习惯,也在不经意间诉说着“端坐呼吸”的秘密。叙事医学的历程很类似自传文学中“自传性分隔”的过程,通过回忆与叙事,“自我”获得了一次与身体的短暂分隔,以叙述者的视角对自己故事中的“主人公”深入剖析,并最终走近身体,了解自己身体的秘密。
疾病叙事的过程不仅是在给医生讲述,更是一个和自己灵魂沟通的过程。在当今,除了病原学明确的传染性疾病以外,疾病很大程度上都离不开那个致病心结和矛盾冲突,这一点很符合精神动力学派的创始人弗洛伊德对“潜意识”的描述,这种被压抑的“潜意识”就像一双无形的手扼住生命的喉咙,在内心积聚、爆发而构成疾病,但是这个深受其害的患者恐怕却并未意识到它的存在。在精神分析治疗中,心理医师会使用自由联想的方法让病人回忆从童年起始的遭遇中的一切经历,想到什么便畅所欲言,从而发现病人压抑在潜意识里的致病情结。
我想,在这里,叙事医学与精神分析疗法殊途同归。叙事医学也是让病人在看似漫无目的的思索中讲述疾病背后的故事,而从中走近自我,发现埋藏在身体深处的疾病之根。就像书中写到的那样,89岁身患多种疾病并伴有长期焦虑的非洲女性通过回忆与叙事,才发现是源于12岁的性侵,尽管吐露心声已无法逆转高血压、乳腺癌在身体上留下的伤痕,但打开了心灵的枷锁,焦虑也随之荡然无存。而叙事医学更为高明之处在于,它将传统的生物学治疗与心理治疗巧妙地融合在了一起,讲述疾病的历程,也是发现身体上的伤痕与心灵上硬痂的过程。
叙事给予医生一种讲述生命赞歌的途径
在临床叙事中,患者并非唯一的讲述者,医生在聆听,却也在讲述。当了解到患者的生存境遇,还原了疾病的社会生活史、传播史,当聆听了患者的感人故事,感受其信仰与观念之后,医生的叙事撰写便是一个关注、反思与再现的过程。医生运用自己独有的医学与文化底蕴,将那有血有肉却又不免逻辑混乱的素材,整理成一曲动人的生命赞歌而将故事重现。王一方教授曾这样评价,“叙事内容再现叙事者的疾苦观、生死观、医疗观,是叙事者信念、思想、意图所建构的另一种真实。”
我想,医生得天独厚地拥有与病人零距离接触的位置,可以记录下疾病的侵蚀、演进以及生命一次又一次相应的挣扎与抗击,这对于患者本人、患者群体、医生乃至整个社会都是莫大的精神财富。因为,“疾病是一扇帮助认识自我的门”,疾病虽然使生活黯然失色,却让患者思考那些不曾思考过的问题,让他们开始考量生命的价值,思索生命的终点意味着什么。身体健康的人视命运与身体为理所当然,唯有经历病痛的折磨后,才能真正体会健康的价值、生命的可贵,才会思索生与死的意义。宗教学者约翰•赫尔因中年视网膜病变而失明,才意识到“肉体完整才是一个人自我之所在”的真谛。史铁生经历残疾、肾衰等一次次折磨才有了“唯爱愿于人间翱飞飘缭,历千古而不死”的生死感悟。但是,不是每个患者都是约翰•赫尔、史铁生,并不是每位经历病痛的人都有着这样清晰的人生理解与感触,那种疾病背后的声音更多是一种朦胧的、若隐若现的存在,等待医生的耐心倾听、敏锐捕捉,并用叙事的手段将故事再现,将微弱的生命之音放大为震撼的生命赞歌。
聆听疾病背后的故事
医学叙事特征中的“主体间性”决定了临床叙事中必然包含两个主体:一个人讲述,一个人聆听。这种叙事本性告诉我们:医学实践本来就是需要一名合格的聆听者。然而,令人遗憾的是,现代医学模式化的诊疗方式使患者的倾诉一次又一次地被打断,“你不用说了,我会问的,你回答我的问题就行。”这样近似冷酷的回答想必每位罹患过疾病的人都有所耳闻。我们这些医学生自进入临床见习之日起,就被一套标准化流程反复、反复而变得“训练有素”。一本本医学宝典教会我们以所谓“专业”的方式问诊,并以主诉、现病史、既往史、社会史、家族史、器官系统回顾、查体等一系列机械化的套路完成病历撰写。毋庸置疑,我们聆听了,并且的确是认真聆听了,只可惜我们企图抓住那些与医学密切相关的细节之后,却忽略了一些也许更为重要的东西。阿瑟•克莱曼曾主张:“将疾病与疾痛区分开来,因为这是两个不同的世界,一个是医生的世界,一个是病人的世界;一个是被观察、记录的世界,一个是被体验、叙述的世界;一个是寻找病因与病理指标的客观世界,一个是诉说心理与社会性痛苦经历的主观世界”。对当下的临床路径而言,这样的比喻恐怕是再合适不过的了。
然而,疾病是有故事的,它展现的绝不仅仅是“头晕、胸闷、喘不上气”这几个简单的症状性描述,它隐含着患者的认识、情感、意志,甚或是患者的人格特征与社会价值取向。患者并不是唯一的讲述者,和他一起讲述的还有他所处的文化。
叙事医学却教给了医生怎样做一个合格的听者。细读、反思性写作的过程,更是教会了医生总结如何聆听,如何走近患者的心灵、与他们共情。书中丽塔在对叙事能力的描述中将叙事过程分为三个阶段:关注、再现和归属。在我看来,关注的过程即体现在医生对患者的聆听过程,也是医疗工作的起始。当绿色的帘子下,一位饱受煎熬的陌生人与我们相遇,倾听过程随之开始。“关注的涵义是清空自己”,聆听也是如此,把自己的思想清空,成为“意义产生的容器”。这个容器接纳病人的疾病故事,捕捉故事中的心灵密码与隐喻,感知患者的灵魂深处,缔结情感和精神的共同体。
当然,我想,丽塔将医生比作“容器”,并不是说医生就是一个接受患者庞杂的诉说的器皿,也不是说医生可以抛弃自己多年的临床知识与医学储备。相反,这是一个有吸引力的“容器”,她不是被动的接纳,而是通过承担见证,主动地将患者疾病背后的故事、体验甚或是难言之隐吸引出来。她是“容器”,她会包容所有庞杂的症状、与之相伴的情感、乃至其背后的医疗观、人生观。
然而,聆听的过程并未就此止步。这个所谓的“容器”会以她敏锐的洞察与深厚的储备,对容纳的信息进行加工,她并没有卸载任何信息,只是以一种专业的方式将它们搅拌、提炼,让它们获得专业的解读。
聆听疾病背后的故事,意味着全面、自然地吸收、接纳与理解,在灵魂深处与患者相遇,与他们共情。而富有专业知识的聆听并不局限于此,因为经过医生这个“容器”的加工之后,患者本人也许会更加清楚认识到自己所处的困境,自己的苦难是从何而起。在这个比喻下,现代医学更像是一个滤器,她缺少“容”的过程,而是过早地对信息进行了过滤,只可惜那些被无情滤掉地信息也就一去不复返了。
尾声
聆听和讲述,是叙事医学中关键的组成成分,也是医疗实践中医患沟通的关键。当然,这两个过程并非截然分开,也并非是单向的听与讲的关系。患者在讲述,他在讲述疾病背后的故事,医生在聆听,她在聆听那个痛苦躯壳下的声音。但同时,医生也是讲者,她将自己听见的声音,与自己的知识、情感融为一体,以诉说、记录抑或平行病历的方式将这个声音重现、放大,让自己听见、让患者听见、让整个社会听见。在聆听和讲述的过程中,医患的角色在调换,这样的过程仿佛正向的循环,聆听方可更好地讲述,讲述才能更好地聆听。叙事医学带来的不仅是融洽的医患关系、改善的治疗效果,更是打通躯体与心灵的阻隔,重建人性的悲悯与救赎。
当然,有人会说,在当今医疗体制之下,医患供需严重失衡,医生应付于日常工作,即便全力以赴尚且感到有所不足,又怎能耐下心来去聆听、品味、再现那一个个感人的故事呢?是的,我想当今中国的医疗环境也许暂时还不是叙事医学的沃土,叙事医学的硕果尚且不能在如今的中国立马扎根、发芽。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就可以抛弃、拒绝这样的理念、信仰和追求。在本书丽塔的描述中,我们知道,即便是在医疗体制发达的美国,也依然没有摆脱冷漠麻木的临床路径:“只有病,没有人;只有技术,没有关爱;只有证据,没有故事;只有救助,没有拯救”。因而,即便我们克服了医疗制度中的一些不合理因素,做到将医患关系转入正轨,唯有“技术前行、科学至上”的理念恐怕孕育的还是一个只会看病不会懂人的机器。我们的社会需要的不仅是柳叶刀、听诊器,更是需要一个有着人性的悲悯与温情的活生生的听者,技术仅仅是工具。
感谢丽塔给了我这样一次洗礼灵魂的机会。作为即将迈入临床实习的医学生,叙事医学给了我一个崭新的视角去重新审视医生这个职业,医生是工程师、科学家,是艺术家,更是牧师、是灵魂的救赎者。叙事医学告诉我们,在褪去了医学的自然科学外壳之后,医学与文学、哲学、艺术殊途同归,因为医学的灵魂终究是属于人文的沃土之上。叙事让医学得以重返人文,在平静的聆听和娓娓的讲述中,获得心灵上的相生与共情,展现人性的温存与美丽。
/北京大学医学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