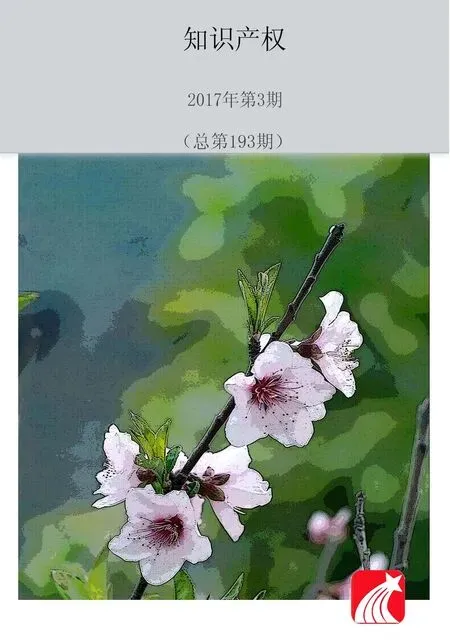禁止专利权滥用原则及其对反竞争效果之考察
于海东
禁止专利权滥用原则及其对反竞争效果之考察
于海东
专利法第四次修改增加了“禁止专利权滥用原则”的规定,其中,有关“不合理地排除、限制竞争”的内容被视为是对反垄断规则——“反竞争效果”的引入,这使得该法有规范反垄断法内容的嫌疑。美国相关司法实践在评判专利权人的行为是否构成滥用时,也考察其是否具有反竞争效果,但其意在严格“专利权滥用原则”的评判标准,而无意规范反垄断法的内容。对于我国专利法中所规定的有关反竞争效果的内容,亦应作出同样的解读。
权利不得滥用 禁止专利权滥用原则 反竞争效果
《专利法第四次修改草案(送审稿)》第14条增加了“不得滥用专利权损害公共利益或者不合理地排除、限制竞争”的内容,此被认为是对“权利不得滥用原则”这一民法基本原则的引入,同时,“不合理地排除、限制竞争”的内容亦被认为是对反垄断规则“反竞争效果”的规定。专利法在第四次修改以前,虽然没有明确规定“权利不得滥用原则”,但是,在相关专利立法与司法实践中却早已有了这一原则的影子。现行专利法中的一些制度安排,比如强制许可制度、权利用尽抗辩制度、现有技术抗辩制度等,就是对“权利不得滥用原则”的具体应用,但是相关立法却缺少能够统领上述各项制度的基本原则。
知识产权具有私权的根本属性,是民事权利体系的一部分,民事制度中的相关学说、理论与规则可以为知识产权制度与规则提供理论上的支撑,并对完善知识产权法律救济体系起到重要的补充作用。①易继明:《禁止权利滥用原则在知识产权领域中的适用》,载《中国法学》2013年第4期,第39–52页。将民事制度中的基本原则“权利不得滥用原则”引入专利法进行明确规定,首先,进一步强化了专利法的民事私法地位和专利权的民事私权地位,强化了“私法自治”在专利法这一部门法中的存在感,民事主体可依其自由意志行使其专利权;其次,有针对性地在专利法这一范畴内考虑行使专利权的行为是否违反了权利设置的目的,也利于建立人们关于禁止专利权滥用的法律观念,②张吉豫:《禁止专利权滥用原则的制度化构建》,载《现代法学》2013年第4期,第99页。强调民事主体必须在合理范围内行使其权利,在追求自己利益的同时,不得对他人和社会造成不利益;再次,作为一项基本法律原则,能扩充现有专利法律规范的覆盖面,填补由于立法活动的预见性不足而导致的规范漏洞,同时还赋予司法活动以创造性和能动性,赋予司法机关以自由裁量权,通过对具体法律规范进行限制、补充和协调,以克服成文法存在的缺乏灵活性和具体的妥当性等缺陷。
一、“权利不得滥用”与“禁止专利权滥用”之内涵
作为一种法概念,“权利不得滥用”起源于罗马法,但其并非与权利概念同时形成,最初只是作为一种法观念而存在,之后才在判例中被解释和运用,并逐渐生成成文法上的具体规则。③钱玉林:《禁止权利滥用的法理分析》,载《现代法学》2002年第1期,第55-67页。1907年,《瑞士民法典》在现代法律上率先确立了“权利不得滥用”之一般条款,以限制私有权神圣和契约自由原则的过分绝对,④龙卫球著:《民法总论》,中国法制出版社2002年版,第59页。该法典第2条第2项规定:“明显地滥用权利,不受法律保护”。此后,大部分大陆法系国家都通过效仿《瑞士民法典》,确立了“权利不得滥用”这一法律原则。而对于英美法系而言,“权利不得滥用”则源自于衡平法上的“不洁之手”(Unclean Hand),是通过司法判例而创制的司法原则,其要求对于实施不公平或不正当行为的当事人,法官不应给予禁令或损害赔偿等救济。⑤闫文军:《美国专利滥用原则评价》,载国家知识产权局条法司编:《专利法研究(2005)》,知识产权出版社2006年版,第445页。
行为哲学告诉我们,权利具有相对性:权利存在着来自外部的限制,权利的行使存在着具体的边界。⑥易继明:《禁止权利滥用原则在知识产权领域中的适用》,载《中国法学》2013年第4期,第39–52页。权利的外部限制是在承认并保障权利的不可侵犯性、权利行使的自由性的前提下,以公法的措施适当限制权利的不可侵犯性,以民法上的诚实信用原则、权利滥用之禁止原则及公序良俗原则限制权利行使的自由权。⑦梁慧星著:《民法总论》,法律出版社1996年版,第251–252页。权利的社会性或公共性,是权利必须承担负担义务的缘由。“权利不得滥用”的要旨,就是要求民事活动的当事人在行使权利及履行义务的过程中,实现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的平衡,⑧徐国栋著:《民法基本原则解释——成文法局限性之克服》,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89–90页。其本质上是法律对私权行使的一种限制,体现了法律追求矫正和分配正义的目标。对价与衡平是知识产权法的立法原则,具有绝对排他性的专利权是近代国家经过周密考虑、充分权衡才创制出来的。在传统专利法的框架下,既然专利权人的绝对排他性权利是以牺牲后续发明人的自然权利为代价,那么,近代国家就应有“正当的理由”保留强制许可等权利限制制度,允许公共利益与私权冲突时,国家行使特殊的衡平职责,根据现代国家的衡平原则,重新修正日益扩张的知识产权制度,是现代国家的法定职责。⑨徐瑄:《知识产权的正当性——论知识产权法中的对价与衡平》,载《中国社会科学》2003年第4期,第144–154页。而在专利法中设置禁止专利权滥用原则,就是现代国家履行这一衡平职责的必然要求。
专利权的特珠性使其相对于其他有形财产更容易被权利人所滥用。专利权作为一种对世权,具有天然的垄断性,与此同时,禁止重复授权制度使得每一项授权专利都是独一无二的垄断权,具有非常低的可替代性,这种垄断性和低可替代性使得权利人对专利的不正当行使更容易构成滥用。知识产权的特殊性给人们对知识产权的认识带来困难:财产法发展史上从不曾出现保护对象没有确定的边界、全赖定义进行指称的“财产”;⑩同注释⑨。专利与公共利益紧密相关,具有垄断性的专利权一旦被滥用,很容易对他人和社会造成严重不利益,并对专利制度所追求的激励创新、促进技术进步这一制度目标的实现造成障碍。为了公平地维系专利权人与他人和社会公众之间的利益平衡、促进专利制度目标的实现,各国立法和司法实践都赋予相对人抗辩权,允许相对人以“禁止专利权滥用”原则来对抗专利权滥用行为。禁止专利权滥用原则旨在弥补成文法的不足,具有使权利范围的外在表述与内在价值体系相一致的“兜底”作用;禁止专利权滥用原则以实现专利权设置的目的为目标,以弥补专利权范围外在要件表述的不足为主要功能,因成文法的局限而具有必要性。1张吉豫:《禁止专利权滥用原则的制度化构建》,载《现代法学》2013年第4期,第96、98–99页。
二、美国法下的专利权滥用原则及其对反竞争效果之考察
在美国的司法实践中,为了防止权利人对专利制度进行滥用,衡平法院通过个案创设了“专利权滥用原则”。1Robert J. Goldman, Evolution of the Inequitable Conduct Defense in Patent Litigation, 7 HARV. J.L. & TECH. 37, 38-40 (1993).该原则是更为基础的普通法原则——“不洁之手”的延伸,意在限制本身可能并不违法,但是却从专利权中获得了反竞争的效果因而被视为违反了公共政策的行使专利权的行为。2Mallinckrodt, Inc. v. Medipart, Inc., 976 F.2d 700, 704 (Fed. Cir. 1992).
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专利许可实践中,专利权人经常会使用限制性许可条件来限制被许可产品的使用或再销售的方式,对限制性许可条款的频繁使用促使了“专利权滥用原则”的创设。最高法院在Motion Picture Patents Co. v. UniversalFilm Manufacturing Corp.案中对该原则进行了首次适用。3专利权人许可被告使用其关于电影放映机的专利技术,但在许可合同中,专利权人又规定被告所销售的每一件放映机都只能使用向专利权人租借的胶片,这种胶片是专利权人的另一项专利,但并未包括在许可合同中。在该案中,最高法院认为,专利权人强行要求购买者必须使用非专利产品胶片的行为是无效的,因为胶片不属于其许可专利的一部分,而专利权人试图将其专利的垄断范围扩充至非专利产品胶片上,这明显已经超出了专利法所授予的保护范围。最高法院认为,专利权是公开授予的一项权利,体现了公共利益,需要在法定授权范围内以合法方式行使。4Motion Picture Patents Co. v. Universal Film Manufacturing Corp., 243 U.S. 502 (1917).此后,法院开始通过此原则的适用来规制那些意图扩充其专利保护范围的、不正当或不公正地行使专利权的行为。
美国法院除了将此原则适用于将专利权垄断范围扩充至非专利保护客体的情形,还将其适用于专利权到期后仍然收取许可费等延长专利法定保护期限的情形。在Brulotte v. Thys Co.案中,法院认为,通过明示合同或者默示行为而限制他人继续使用已经过期专利的行为,剥夺了他人自由使用已进入公有领域的专利技术的权利,与专利法的政策和立法目的相违背,构成当然违法,不具有可执行力。5Walter C. BRULOTTE et al., Petitioners v. THYS COMPANY, 379 U. S. 29 (1964).
随着“专利权滥用原则”的进一步发展,联邦法院在Windsurfing-AMF案中对“专利权滥用原则”的构成要件作出了进一步限定,其指出,被控侵权人需要证明专利权人实施了不被法律所允许的扩充其授权专利的保护客体或保护期限的行为,并且还第一次引入反垄断法原则来对专利权滥用行为进行分析,主张专利权人的扩充专利保护客体或保护期限的行为需具有反竞争的效果,并对相关市场的竞争构成限制。6Windsurfing Int’l, Inc. v. AMF, Inc., 782 F.2d 995 (Fed. Cir. 1986).在随后的十几年中,联邦法院通过适用Windsurfing-AMF案所确立的反垄断法原则驳回了大部分的专利权滥用抗辩。7B. Braun Med., Inc. v. Abbott Labs., 124 F.3d 1419 (Fed. Cir. 1997).
尽管美国法院通过引入反垄断法原则来对专利权滥用案件进行评述,但是并没有将反垄断问题与专利权滥用问题进行等同。在Virginia Panel Corp. v. MAC Panel Co.案中,联邦法院指出,相对于专利权滥用,构成反垄断违法需要更多的确切证据;反垄断法之下的相关市场的定义要比专利权滥用中所要求的标准更明确;一行为如果不足以构成专利权滥用,那必然无法构成对反垄断法的违反。8Virginia Panel Corp. v. MAC Panel Co., 133 F.3d 860 (Fed. Cir. 1997).在Minebea v. Papst案中,法院认为,相对于反垄断案件,专利权滥用案件对反竞争效果的适用要宽松得多;但是法院同时又指出,在专利权滥用原则与反垄断法之间又存在着一个非常明确的亲密关系,即相关市场中的市场力问题肯定是法院在判断滥用专利权行为是否具有反竞争的效果时需要考虑的相关问题之一。9Minebea Co., Ltd. v. Papst, 444 F. Supp. 2d 68 (D.D.C. 2006).
随着司法实践的不断发展,联邦法院开始收紧“专利权滥用原则”的认定标准,与此同时,联邦法院也开始试图将“专利权滥用原则”与反垄断法区别开来。在飞利浦于2002年向全球19家光盘制造商提起的“337调查”中,ITC认为,飞利浦将被许可人并不需要的非必要专利与必要专利捆绑在一起进行一揽子强制许可的行为,剥夺了被许可人自由选择其他可替代技术的权利以及其他可替代技术参与市场竞争的机会,从而产生了反竞争的效果。飞利浦不服向联邦法院提起上诉。联邦法院经审理认为,必须通过“合理原则”对一揽子许可行为进行分析,并指出,一揽子许可并不是要求被许可人实际使用专利包中的所有专利,其主要目的在于确保被许可人不再被起诉侵权,有鉴于此,一揽子许可并不表示专利权人利用一个市场中的市场力去获得另一个市场中的优势。1U.S. Philips Corp. v. Int’l Trade Comm’n, 424 F.3d 1179 (Fed. Cir. 2005).在2010年的Princo panel decision案中,联邦法院认为,就“专利权滥用原则”而言,最关键的是审查专利权人是否通过利用“专利杠杆”不允许地扩大了其专利权授予的客体范围或者时间范围,并且产生了反竞争的后果。2Princo Corp. v. Int’l Trade Comm’n, 616 F.3d 1318 (Fed. Cir. 2010).
虽然“专利权滥用原则”是司法创制原则,但美国也通过立法对专利权滥用行为进行规制。美国专利法虽然没有从正面规定什么是专利权滥用行为,但却以列举的方式排除了不属于专利权滥用的行为。1952年,美国国会修改了专利法,详细规定了几种不构成专利权滥用的行为,具体包括:(1)从某种行为中获得收益,而若他人在未经其同意的情况下进行该行为将构成对专利权的帮助侵权;(2)许可或授权他人进行某些行为,而若他人在未经其同意的情况下进行该行为将构成对专利权的帮助侵权;(3)寻求强制执行其专利权,以对抗侵权或帮助侵权。1988年,美国国会通过了《专利权滥用修正案》,将两种常见行为排除在滥用专利权之外,其在《美国专利法》第271条(d)中补充规定拒绝许可或转让专利,以及提出以接受另一专利权许可或者购买另一单独产品为订立专利许可合同或购买专利产品的条件的行为并不必然构成专利权滥用,除非专利权人在相应的市场上对另一专利权或者另一产品拥有市场支配力。3See 35 U.S.C. § 271(d).由此可见,1988年《美国专利法》似乎也间接支持了联邦法院在Windsurfing-AMF案中所形成的“反竞争效果”这一标准。
美国对专利权滥用行为的规制不仅体现在其专利立法上,而且还通过反垄断立法对专利权滥用行为形成双层立法规制。1995年,美国司法部和联邦贸易委员会共同颁布了《知识产权许可的反托拉斯指南》。该指南首次规定,通过适用“合理分析”原则来对知识产权许可中的限制行为进行分析,并规定适用该原则的具体方法是:调查该限制是否具有反竞争的效果;如果具有反竞争的效果,则需要审查该限制是否为获取某种正当利益所合理需要的,最后还要比较该条款所促成的利益是否大于其所造成的竞争损失,在对诸多因素综合分析判断后,再判定该行为是否违法。4王源扩:《美国反托拉斯法对知识产权许可的控制》,载《外国法译评》1998年第2期。
由此可见,“专利权滥用原则”向公众提供了一种防卫措施,以阻止专利权人寻求超过其专利权保护客体和期限之外的权利。当专利权人企图以违背公共政策的方式主张其权利时,被控侵权人可以通过主张专利权滥用原则来进行积极抗辩。5B. Braun Med., Inc. v. Abbott Labs., 124 F.3d 1419, 1427 (Fed. Cir. 1997).为了抗辩成功,被控侵权人必须证明,专利权人在与专利产品相关的市场中具有市场控制力,并且专利权人的行为可能会导致排挤竞争对手或阻止他们进入相关市场的效果,即具有反竞争的效果。6Christina Bohannan, IP Misuse as Foreclosure, 96 IOWA L. REv. 487(2011).如果两者都能得到证明,法院将拒绝执行相关专利,直至专利权人中止相关行为或者采取补救措施,或者对其滥用行为进行“大清洗”。11See, e.g., C.R. Bard, Inc. v. M3 Sys., Inc., 157 F.3d 1340, 1372 (Fed. Cir. 1998).
三、我国法下禁止专利法滥用原则对反竞争效果之规定及其解读
关于专利权滥用问题,除了本次专利法第四次修改对其进行了规定,2008年8月1日开始实施的《反垄断法》对知识产权滥用问题也进行了原则性规定,体现在该法第55条将滥用知识产权排除、限制竞争的行为规定为《反垄断法》所调整的对象。12《反垄断法》第55条规定:“经营者依照有关知识产权的法律、行政法规规定行使知识产权的行为,不适用本法;但是,经营者滥用知识产权,排除、限制竞争的行为,适用本法。”此外,2016年2月4日公布的国家工商总局《关于滥用知识产权的反垄断执法指南》(征求意见稿第七稿)对何为“滥用知识产权”、何为“滥用知识产权排除、限制竞争行为”也进行了明确定义。11国家工商总局的《关于滥用知识产权的反垄断执法指南》(征求意见稿第七稿)第2条第1款规定:“滥用知识产权,是指经营者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授予有关知识产权的界限和目的,以不正当方式行使知识产权,损害他人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第3条规定:“本指南所称滥用知识产权排除、限制竞争行为,是指经营者违反反垄断法的规定行使知识产权,实施垄断协议、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具有或者可能具有排除、限制竞争效果的经营者集中。”由此可见,与美国类似,我国对滥用专利权的问题也采用了专利法、反垄断法二元立法规制结构。
专利权本质上是一种私权、对世权,专利权人可依私法自治原则自由行使其权利,但专利权人的自治行为要受限于一定的“度”,这个“度”由专利制度所追求的价值目标所决定:当专利权人在这个“度”范围内行使其权利时,即使其行为可能会给他人或社会公众造成不利益,他人和社会公众亦应付有容忍义务;但是,当专利权人跨过这个“度”追求法律并未赋予其的额外利益、并使专利制度所追求的价值目标无法实现时,其行为就构成了专利权滥用,利益受侵害的他人或社会公众也无需再承担容忍义务。知识产权与其他财产权最为不同的一点就是其天生具有垄断性。虽然知识产权和市场竞争都把促进人类社会进步作为其价值目标,但知识产权所具有的垄断性与市场竞争对自由价值的追求之间存在着冲突,知识产权与市场竞争之间天生具有紧张关系。12See Hart, Lznda Fazzani, ”Intellectual Property Law”, Second edition, Palgrave, Houndmills and Basingstoke, 2000, P217.自由、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的维护也存在着“度”的问题,这个“度”是由以反垄断法和反不正当竞争法等为代表的公法所追求的价值目标所决定:竞争主体在这个“度”范围内的私权利益必须给予保护,这是竞争主体进行自由竞争的基础条件;竞争主体超过这个“度”滥用权利的行为则需要通过公法框架下的规制措施进行约束,以维护自由、公平的市场竞争秩序。因此,滥用专利权的行为一般而言具有两方面的可归责性:一是对具有私权性质的专利权的滥用可能会侵犯他人和社会公众的合法权益;二是对具有垄断性的专利权的滥用可能会损害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前者本质上是一种私法意义上的侵权问题,通常可通过私法上的权利救济制度来保护利益受侵害之主体的相关权益;而后者则属于公法所调整的范畴,应通过国家公权力主导的法律规制措施来进行调整,以维护公平的市场竞争秩序。这也就是说,滥用专利权行为所引起的私权保护和公平竞争秩序的维护问题可通过私法和公法框架下的二元救济结构进行解决。这种二元救济结构是互不影响的两个层面,可依其各自所属的法律制度内的运行机制,救济其所要保护的受害之权益,实现各自制度所追求之价值。
通过专利法和反垄断法对专利权滥用问题分别进行规制符合这种二元救济结构的要求。专利法作为一种私法,其所追求的价值目标不仅体现在对专利权人的合法利益给予充分保护,其还承担着实现鼓励创新、促进科学技术进步这一公共政策使命,在专利法维度上对专利权滥用问题进行规制应着眼于考察专利权人行使权利的行为是否不利于这一公共政策的实现。而反垄断法所追求的是公平、自由的市场竞争秩序,其通过预防和制止垄断行为来实现这一价值目标,在反垄断法维度上应当对构成垄断,破坏公平、自由的市场竞争秩序的滥用专利权的行为进行规制。每个部门法都有其要调节的社会关系领域,因而权利设置的目的也主要在于对该领域的社会关系调节和利益分配,反映着相应的部门法鲜明的立法目的和具体的价值追求。13张吉豫:《禁止专利权滥用原则的制度化构建》,载《现代法学》2013年第4期,第96、98–99页。因此,需要注意专利法与反垄断法的分工与协调,不能混淆专利法与反垄断法的目的、无视两者的分工,而将反垄断法规范的内容纳入专利法。14许春明、单晓光:《专利权滥用抗辩”原则——由ITC飞利浦光盘案引出》,载《知识产权》2006年第3期,第37页。
从本次《专利法第四次修改草案(送审稿)》第14条新增加的“不得滥用专利权损害公共利益或者不合理地排除、限制竞争”的内容来看,专利法将滥用专利权的行为归为两类:一类是损害公共利益的行为;另一类则是不合理地排除、限制竞争的行为。而第二类行为似乎属于反垄断法所调整的对象,这是否意味着将反垄断法所规范的内容纳入了专利法范畴来进行调整?由于两法对滥用专利权的行为进行的都是原则性规定,从条文本身无法得到明确答案。
本次专利法修改似乎参考了美国有关“专利权滥用原则”的立法和司法实践。美国最先通过司法判例创设了“专利权滥用原则”,同时,又在专利法中以有限列举的方式对不属于专利权滥用的情形进行了明确规定。1988年, 美国国会在《美国专利法》第271条(d)中补充规定拒绝许可或转让专利,以及提出以接受另一专利权许可或者购买另一单独产品为订立专利许可合同或购买专利产品的条件的行为并不必然构成专利权滥用,除非专利权人在相应的市场上对另一专利权或者另一产品拥有市场支配力。11See 35 U.S.C. § 271(d).类似于美国司法判例中所使用的“反竞争效果”,该规定所引入的“市场支配力”也属于反垄断法范畴内的概念,这使得该法有规范反垄断法内容的嫌疑。
根据美国有关司法判例,专利权人行使专利权的行为只有在具有排挤竞争对手或阻止他们进入相关市场的效果,即具有反竞争的效果时才构成专利权滥用。12Christina Bohannan, IP Misuse as Foreclosure, 96 IOWA L. REv. 487(2011).美国司法实践虽然使用了“反竞争效果”这一反垄断规则,但是并未将专利权滥用问题等同为反垄断问题,并且法院也逐渐意识到“专利权滥用原则”对“反竞争效果”这一反垄断规则的适用,会使人误认“专利权滥用原则”属于反垄断法范畴,法院后期也试图通过各个司法判例来划清两者之间的界限,以尽量明确两者之间的评判标准,避免造成不必要的混淆。如法院在相关司法判例中指出相对于专利权滥用,构成反垄断违法需要更多的确切证据,且对相关市场的界定更严格,同时对反竞争效果的审查也更加严格;一行为如果不足以构成专利权滥用,那必然无法构成对反垄断法的违反;一行为即使构成对反垄断法的违反,如果并非是由于诉争专利所导致的,也不必然构成专利权滥用。13Virginia Panel Corp. v. MAC Panel Co., 133 F.3d 860 (Fed. Cir. 1997);Minebea Co., Ltd. v. Papst, 444 F. Supp. 2d 68 (D.D.C. 2006);Princo Corp. v. Int’l Trade Comm’n, 616 F.3d 1318 (Fed. Cir. 2010).由此可见,美国司法判例原则“专利权滥用原则”下的“反竞争效果”与反垄断法下的“反竞争效果”是两个范围不同、评判标准也不尽相同的两对概念。
由此可见,“反竞争效果”虽然是反垄断法下的反垄断规则,但是司法判例原则“专利权滥用原则”对“反竞争效果”的评价标准和尺度与反垄断法不同,“专利权滥用原则”亦无意规范反垄断法之内容。因此,我国的专利立法,无论是参考美国的专利立法,还是参考美国的司法判例原则“专利权滥用原则”,都不应得出专利法可以规范反垄断法所规范之内容的结论,同时,美国的“专利权滥用原则”的发展历程亦表现出“专利权滥用原则”与反垄断法之间的界限越来越清晰的趋势。
我国《专利法第四次修改(送审稿)》第14条新增加的内容使用了反垄断法下的“排除、限制竞争”这样的反垄断规则,从立法的规范性来讲,这可能会使人得出作为私法的专利法将本应由作为公法的反垄断法所规范的内容也纳入了其规制范围。公私法的划分在于国家对不同社会生活领域采取的法律调整方法不同,公法更多强调的是国家权力的行使,私法则着重社会生活主体的意思自治。14孙国华、杨思斌:《公私法的划分与法的内在结构》,载《法制与社会发展》2004年第4期,第100–109页。反垄断法对知识产权滥用进行规制的基本前提和特点在于维护有效竞争,其所规制的应当是在行使知识产权的过程中不正当地限制竞争的行为,这是由反垄断法的社会本位性和保护竞争的特点以及调整角度所决定的;这既不同于知识产权法针对权利本身进行的限制,也不同于民法的权利不得滥用原则,从更为广泛的角度考虑社会公共利益而并不特别关注竞争所受到的限制,其所进行的限制必然主要运用不同于民法的公法方法,有专门机关的主动介入,即反垄断法对限制竞争行为的控制主要是采用政府干预的方式。15王先林:《知识产权滥用及其法律规制》,载《法学》2004年第3期,第107–112页。因此,具有排除、限制竞争效果的滥用专利权的行为应主要借助反垄断法框架下的规制措施与手段来进行调整。规范排除、限制竞争的行为也并非专利法的主要立法目的和价值目标,基于专利法的立法目的和价值目标所设置的专利法规制措施和手段亦不能有效解决具有反垄断效果的滥用专利权的行为。因此,对于我国专利法引入“排除、限制竞争”这一反竞争效果,应当将其解读为是为严格“禁止专利权滥用原则”的评判标准而规定的,我们应当在专利法的维度下、基于专利法的立法目的和价值目标,而不能基于反垄断法的视角、以反垄断法对“反竞争效果”的要求来对其进行考察和评价。
The fourth amendment to the Patent Law added the doctrine of Patent Misuse, where in the content regarding ‘unreasonably to exclude, restrict competition’ is regarded as an introduction of the antitrust principle of ‘anti-competitive effect’, which places the Patent Law under the suspicion of regulating the content of Antitrust Law. The U.S. judicial practice also examines whether the alleged patentee’s behavior has anticompetitive effect when the judgment on whether it constitutes patent misuse is made, aiming to restrict the evaluation criteria of the doctrine of Patent Misuse rather than to regulate the content of antitrust law. We should also make the same interpretation on the content regarding anti-competitive effect provided by the Patent Law.
prohibition of right misuse; the doctrine of patent misuse; anti-competitive effect
于海东,南京大学法学院博士研究生,北京市立方律师事务所合伙人
——兼评专利法第九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