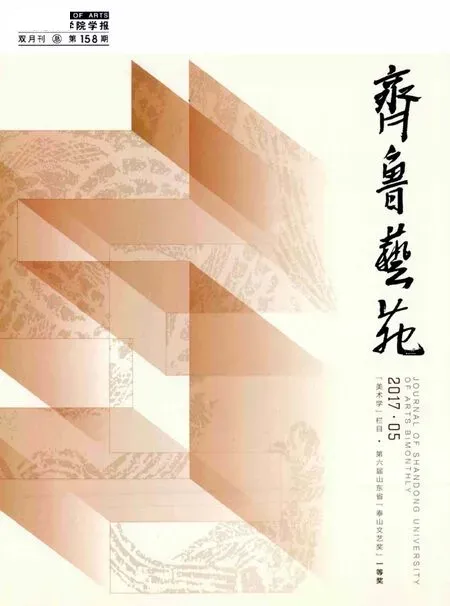儒家文化及乐舞观对海阳秧歌的影响
潘 晶
(山东艺术学院舞蹈学院,山东 济南 250014)
山东地区是中华民族和中国古代文明的发祥地之一,早在旧石器时代,这里就有古人类生息繁衍。山东亦是先秦时期齐国、鲁国所在地,号称“齐鲁礼仪之邦”。齐鲁文化是一种以古代齐国和鲁国为代表的地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成为中华民族的主流文化,其精神作为中华民族的灵魂,至今仍具有强大的生命力。
齐鲁文化发轫于东夷文化。早在四五十万年以前,东夷人的直系祖先沂源猿人面对群山树海,勇敢地开始了从原始森林走向文明的艰难跋涉。“从原始社会至夏商时期,齐鲁的东夷人逐渐形成了两个文化中心。在泰山以北,以今之淄博为中心,是爽鸠氏、季荝、有逢伯陵和季蒲姑氏等活动的地域。泰山以南,以今之曲阜为中心,是少昊、蚩尤、颛顼、后羿、奄国等部落和方国的居地,同时又是中原文化和南方文化联系紧密、便于交融的地区,因而有及其丰富的文化积淀。距今6000年左右,齐鲁的原始居民进入新石器时代,他们被统称为‘夷’或‘东夷’。”[1](P2)
随着生产力的提高,社会分工的发展以及对夏商文化的广泛吸收,东夷文化与中原文化的联系逐渐加强。西周建立后,通过分封建立了许多诸侯国,其中以齐、鲁两大诸侯国为主。齐国和鲁国分别继承了东夷文化和夏、商、周三代的先进文化,但由于两国建国方略的差异和人文环境、地理条件的不同,此后的六七百年中,两国各自沿着自己的轨道向前发展,逐渐形成了两个既有共同点而又风格迥异的文化传统——齐文化和鲁文化。战国时期,两种文化体系开始逐渐融合,形成齐鲁文化。
齐文化具有“重实效、崇功利、举贤才、尚法治、扬兵学、倡开放的文化品格”[2](P4),其精神主旨是“因时变化,与时俱进”,其思想代表是强调“与时移物,应物变化”的黄老学派。鲁文化“讲究道德名节,注重研究传统文化和阐发宗法伦理观念”[3](P4),其精神主旨是“固守传统,强调原则性”,其思想代表是以“天下兴亡为己任”的儒家、墨家学派。齐文化和鲁文化的结合,共同缔造了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源头——齐鲁文化,这使得山东的古代文化既重视人文价值理想,又重视现实国计民生;既注重道德礼仪的建设,又注重行政法规的完善;既保有厚重的传统,又能兼容并包。齐鲁文化所蕴涵的“自强不息、爱国主义、厚德载物、勤劳勇敢、求真务实”的文化精神,也是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资源和理论基础。
一、讲礼之风范
儒家文化重视“礼”,这是种极为森严的仪式形式,且形式大于内容,体现在在乐舞中就是讲究排场和气势,如西周时期的“八佾舞”。“佾”是古代舞蹈阵容的衡量单位,一佾八人,最高级别给天子享用的舞蹈是“八佾”,八八六十四人,场面浩大,讲究排场。古代的礼仪乐舞均讲究祭拜的先后,如祭祀时,需先焚香叩拜,而后祭品呈上,再行叩拜,如此几进几出,彰显对神灵的敬仰。因此,在儒家思想的制控下,华夏成为了礼仪之邦,一个讲“礼”的国度。讲,可视为讲究,礼,可视为礼数,这些礼数也影响着山东秧歌的发展。
孔子作为儒家思想的代表人物,十分重视乐舞的教育作用,强调乐舞为政治服务,还把规范人的伦理道德观念的“礼”与乐紧密结合在一起。《论语·八佾》中记载,孔子因为大夫身份的鲁国季氏僭越,擅自观赏了只有天子才有资格欣赏的“八佾舞”而大声抗议:“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左传》中记录了周人对“礼”的认识:“经国家,定社稷,徐敏人”,其目的是:“民不迁,农不移,工贾不变”。可见周人对“礼”体现出一种追求稳定的保守倾向,对此,孔子是极力维护的[4](P25)。孔子认为礼与乐的配合是统治百姓的有效措施,只强调规范性极强的礼,会造成不“和”,而乐可以“和民声”,但乐也要依靠规范性极强的“礼”来节制。
山东被称为“礼仪之邦”,将社会政治、伦理道德相结合,“敬天尊祖”也渗透到了生活的各个方面,包括舞蹈。无论是上层社会还是底层百姓都自觉信奉。山东三大秧歌之一的海阳秧歌,受儒家传统文化及乐舞思想的影响,对礼仪十分注重、讲究。海阳秧歌中重要的礼仪就属“拜进”,又称“三进三出”,是在祭神、祭祖的“三叩九拜”的基础上演化而来。大年初一,秧歌拜祭本家祖宗,后到各村串演,过程中要向东道村家庙、祠堂祭拜,而祭神的活动也离不开秧歌队,也要行大礼。古时,参拜的礼数更为周全,也更为繁琐,讲究“进门一二三,出门三二一;一回三番九个礼,九回翻番八十一礼[5](P34)”。从进门到出门,过门就拜,鼓乐喧声之中,众目睽睽之下,秧歌队有秩序、毕恭毕敬地表演一整套规范的动作,十分虔诚地完成对祖宗和神灵的祭拜过程。据说参拜仪式能持续两个小时之久,其庄重、虔诚之心,热烈程度可想而知。如今的“三进三出”比过去的“三拜九叩”在形式上简化了不少,但其本质却是相同的。“三进三出”是历代秧歌队必行的礼节,也从侧面反映出齐鲁人重儒尚礼的秉性。两支秧歌队若迎面相遇,不能绕行不能回避,而要行参拜之礼,如若这“三进三出”之礼做得不好,就等于说秧歌队不尊重他人,不懂规矩,就会被人耻笑。正是因为极为重视礼仪,民风古朴,使得海阳秧歌在表演上套路规范、动作整齐。海阳秧歌讲究礼仪,也彰显出山东人重礼尚义的品质,所以说海阳秧歌明显带有儒家传统文化及乐舞思想的印迹。
二、善美之体现
中国古代对舞蹈理论的研究始于春秋战国时代,人们也将这一时期视为中国文化的轴心时期,而有关的乐舞思想也发轫于此。中国古代乐舞不分家,有乐必有舞,有舞必有乐,乐之为用,全在声容兼备,有声而无容,不能称之为乐。先秦诸子百家中对乐舞理论有着比较深刻见解的首推儒家,而孔子作为儒家的创始人,虽然在乐舞理论方面没有留下系统的著作,但是他总结了前人对乐舞的见解,在一些基本认识上,为儒家的乐舞思想观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儒家提出的“美善统一”的思想,要求舞蹈的美必须与善相结合,唯此才能尽善尽美。孔子认为《韶乐》是尽美尽善之作,闻之“三月不知肉味”,而《大武》是歌颂武力取天下的乐舞,尽美却未尽善。唐朝孔颖达对《礼记·乐记》做疏证时指出:“乐之善恶,初从民心而兴,后及合成为乐。乐又下感于人。善乐感人,则人化之为善;恶乐感人,则随之为恶。”[6](P26)这又将乐舞对社会生活、对人的作用阐发得明白晓畅。
依据传统的排列方式,海阳秧歌队中走在最前面的是“执事”,紧随其后的是“乐队”,“舞队”则走在秧歌队的最后面。这三大部分分工明确,各司其职,且配合相当默契。执事与乐队都是为舞队而服务的,分别负责秧歌队的礼仪事务和奏乐、营造氛围。舞队作为秧歌队中重要的组成部分,角色众多且极具个性特色。无论是锢漏与王大娘、丑婆与傻小子带有情节性的双人舞,还是扇女、小嫚的集体表演,都是在乐大夫的统一指挥下,即兴表演,变换队形,无不体现着对美的一种追求。说到海阳秧歌的礼仪庄重、阵势庞大、规范严谨的美,不得不提春秋时期的齐国,这里曾经诞生了被孔子评价为“尽善尽美”“闻之三月不知肉味”的《韶》乐,其气势恢宏,规模庞大,艺术感染力强,体现出一种恢宏壮观之美,这对后世齐鲁乐舞的发展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这种影响也体现在海阳秧歌的表演形式中。
优秀的舞蹈作品总能体现特有的民族审美习惯,倡导特定的时代审美追求。除了外在表演形式的美,海阳秧歌的美还体现着其内在的思想性。海阳秧歌的思想内容积极向上,崇尚对美好的追求,对生活的热爱,倡导人们去追求真、善、美。古时它是祭神、祭祖的仪式,今日它成为广大民众精神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人际交流的重要方式,在历史的每个阶段它都谱写了不朽的篇章。抗日时期它是宣传抗日、激励斗志的重要手段,如今它已然成为海阳市的文化品牌,也成为了招商引资的一种重要途径。
三、真情之流露
儒家乐舞思想的代表著作《乐记》中指出:“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动,物使之然也。感于物而动,故形于声;声相应故生变,变成方,谓之音;比音而乐之,及干戚羽旄,谓之乐。”[7](P26)作者以人心感物而动来探讨乐的本质,认为乐舞是人们思想感情的表现,但并非所有的人类精神活动都是艺术。当人们的思想感情需要表达时,同时又通过特定的形式外化出来时,那才是艺术。如果只是发出自然的声响,并不能算是“乐”,自然之“声”禽兽亦可以发出。这样的表述清晰明了,正印证了“内容决定形式,形式依附于内容,但形式又反作用于内容”的观点。
孔子认为,乐舞是人们思想情感方面的表现,可以通过乐舞观察一个国家的政治面貌和民俗风情。乐舞不仅是人们思想感情的外化形态,它对人们的情感也具有反作用,因而孔子认为乐舞是移风易俗最有效的工具,也是教化民众的有效工具。明代的乐律学家、舞蹈家、历算家朱载堉在继承儒家乐舞思想的基础上,提出“论舞学不可废”,把舞蹈看作一门艺术,看作人文科学的研究对象,他认为:“盖乐心内发,感物而动,不知手足自运,欢之至也。此舞之所由起也”。他站在“天人合一”的角度强调:“天地之命,中和之纪,人情之所不能免也,君子曰礼乐不可斯,须去身此之谓也。”强调人与自然的相互依存、相互和谐的关系,并以此强调舞蹈所起的中介作用和各种功能,充分肯定乐与舞各自独立的艺术品格与相互难以取代的重要作用。
海阳秧歌中的锢漏与王大娘两个角色,是从秧歌剧中演化而来的一对情景舞蹈演员,表演时也是成双成对,不离不弃。他们是海阳秧歌中艺术风格最为突出的一对人物,有着优美的舞蹈动作和丰富的表现手法。二人眼神相互交流、互相挑逗,“你进我退,你拦我去,你去我追,你扑我引”[8](P108),尽情对舞,动感极强。锢漏与王大娘的传说有多个版本,有说王大娘是玉皇大帝的小女儿,名叫旱魃,因眷恋人世不归天庭,危害人间,后被土地神所化的锢漏匠利用情谊将其收服;也有说王大娘是千年狐仙所化,玉皇大帝命土地神化作锢漏将其收服,但土地神最终爱上了这个美丽的狐仙,与王大娘一起演绎了一场终破牢笼的爱情故事。无论是旱魃还是狐仙,无论天兵天将还是土地神,也无论锢漏与王大娘的结局如何,他们都是民间艺人将自己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向往倾心附之的妖、仙、人化为一体的特殊人物,是人们借以抒发情怀,给自己以追求美好生活的希望和信心,同时也体现了对封建社会制度抑制人们情感的鞭挞和痛斥。
吕文斌在《胶州秧歌的特征与形成》一文中谈到胶州秧歌的审美时指出:“社会一方面要求男演员扮演的女角色要用女性动作的优美姿态满足审美要求,另一方面社会又用儒家的观念,要求扮演的女性角色表现出温顺贤惠、含而不露的品德。受这种社会审美心理的影响和约束,在秧歌表演中,男演员扮演女性角色也是在两重心理下完成的,一重是他们为能借助自娱性的秧歌形式,尽力去表达自己生活中不能表达的内心情感而感到欢娱的心情,另一重又受儒教和社会审美标准的束缚,在动作上表现出既激动又沉稳的含蓄美的特征。秧歌中扭、拧、抻、韧的风格特点,就充分表现出了挣脱不了那个时代的妇女们被压抑的内心激情,这一切可以归纳成一个‘曲’字。这个‘曲’,不只表现在女性角色代表的现实生活中的妇女们,
同样也体现在那个时代的男人身上。这种两重心理的艺术体现,形成了胶州秧歌女性动作既有北方妇女舒展奔放,又有内在含蓄、含而不露的风格特点,令人感到别有风情,韵味无穷。”
无论是海阳秧歌中为争取自由的锢漏与王大娘,还是借助自娱性的秧歌形式表达内心情感的胶州秧歌,他们都是人们内心情感的一种寄托,一种表达。人们借助秧歌这一形式宣泄着内心的情感,秧歌又依托着人们的情感得以保存和传承。
综上所述,秧歌作为一种身体符号,代表了农耕时代民众的思想,体现着最朴素的民众情怀。百姓在一年当中最适宜的时候,举行最能表达他们心愿的活动——秧歌,他们在一起欢歌笑语、载歌载舞,用这样一种独特的形式来犒劳辛苦了一年的自己。海阳秧歌在中国民间舞蹈尤其是秧歌类舞蹈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它历史悠久、形式多样、保存相对完好、普及范围广,与其它地区的秧歌(东北秧歌、河北秧歌、陕北秧歌等)有着鲜明的差异,风格亦有显著不同。涨阳秧歌经历了几百年的发展和流变,印证了不同时期民众的精神生活,同时也承载着多元社会文化内涵。它生长在素有“孔孟之乡”的齐鲁大地上,受传统儒家文化思想及乐舞观的影响,带有鲜明的民间祭祀性质,也体现着中国传统文化所蕴含的勤奋务实、勇于拼搏、自强不息、团结奋进的民族精神。随着社会的发展、时代的进步,充满韵味的胶州秧歌、古朴粗犷的海阳秧歌以其自身独特的魅力,越来越多的受到广大民众的喜爱。
[1][2][3]孟祥才,胡新生.齐鲁思想文化史—从地域文化到主流文化[M].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05.
[4][6][7]冯双白,茅慧.中国舞蹈史及作品鉴赏[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
[5][8]于蔚泉.海阳秧歌[M].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07.
———史敦宇艺术作品欣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