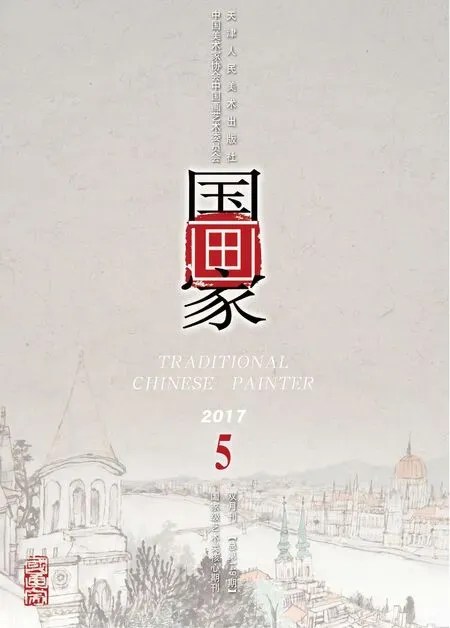论庄子思想对中国画创作的影响
项晓乐
论庄子思想对中国画创作的影响
项晓乐
庄子对后世的影响是深远而复杂的,其美学思想对中国传统绘画的影响更是深刻的。中国画作为中国文化的一部分,浓缩和迹化了许多中国传统思想的特征,从而兼具艺术的高度和哲学的深度,构成了一道独特的人文景观。在从事中国画研究时,人们往往会从哲学思想中追寻其源头,我们尝试从中国画创作角度管窥庄子思想对中国传统绘画的影响。
一、“得意忘言”与中国画创作中对意的重视
据《系辞上》,“象”乃尚未成形之萌兆,“形”乃成形的器物。《象传》中八卦的“象”是:按乾——天,坤——地,坎——水,离——火(明),震——雷,艮——山,巽——风,兑——泽,就是说取自大自然的最常见的八种现象,以及人们的日常生活中无时无刻不在发生关系的现象。[1](118)可见,卦象也是师法自然的。而谈到“意”我们就会想到《庄子·天道》中所感叹的:“世之所贵道者,书也。书不过语,语有贵也。语之所贵者,意也,意有所随。意之所随者,不可以言传也,而世因贵言传书。世虽贵之哉,犹不足贵也,为其贵非其贵也。故视而可见者,形与色也;听而可闻者,名与声也。悲夫!世人以形色名声为足以得彼之情!夫形色名声果不足以得彼之情,则‘知者不言,言者不知’,而世岂识之哉!”[2](213)这段话充分表达了“意”的重要性。书中所记载的不外是语言文字,而语言所贵的是表达的意思,把握意才是最可贵的。在另一段经典论述中,庄子谈道:“筌者所以在鱼,得鱼而忘筌;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2](466)这里,筌、蹄、言都可以说是一种手段、工具。
《易传》中指出“立象以尽意”,魏晋玄学家王弼也说:“象者,所以存意,得意而忘象。”[3]清代文学家章学诚也在《文史通义·易教下》写道:“《易》之有象,取譬明理也,……求道之能喻而理之能明,初不拘泥于其象,变其象也可;及道之既喻而理之既明,亦不恋于象,舍象也可。”[1](208)也就是说,在教化、明理过程中可以不受“象”的限制。晓喻之余,可以更自由以至于放弃“象”。
《庄子·则阳》中写道:“道、物之极,言、默不足以载。”[2](444)即:道和万物的至理,谈说和静默是不足以表达出来的,而绘画则能表现出一种“非言非默”的状态,寄寓“逍遥”超脱精神,可以说,绘画是一种表现“道”的有益形式。在道说不可说这方面,绘画艺术语言有其得天独厚的优势,这种语言恰与庄子的“书不尽言,言不尽意”观点相通,都寓有象外之意,可意会而不可言传。这在中国画具体创作中,可以体现为:作画时,强调意在笔先、笔不周而意周,给人留下想象的余地,余味绵远悠长。若过于刻画雕琢,就有失含蓄、蕴藉,可谓过犹不及。
二、“不敢怀非誉巧拙”与中国画创作的心态
绘画艺术是一个具有哲理性的综合体,汇聚着无形与有形、主体与客体等许多因素的对立统一,正是强调了对立力量的碰撞,使画面更富于张力。庄子思想对中国画家的创作心态也有深刻影响。
庄子重视静,《庄子·天道》中写道:“万物无足以铙心者,故静也。……水静犹明,而况精神!水静,则明烛须眉;平中准,大匠取法焉。圣人之心静乎!天地之鉴也,万物之镜也。”[2](197)可见,静是不受外界干扰的结果,心静下来就像水静下来变得清明一样,过滤掉尘世琐屑才能清亮得足以照见天地万物。庄子说“惟道集虚”,他将虚静的心境称为“心斋”。南朝时宗炳在《画山水序》中提出:“圣人含道映物,贤者澄怀味像。”意即贤德之人澄洁胸怀体味各种物象。苏轼《送参寥师》中说:“静以了群动,空故纳万境”。清代恽寿平《南田画跋》中也认为审美要有虚静的心境:“川濑氤氲之色,林岚苍翠之色,正须澄怀观道,静以求之。”[4](25)可见,画家要保持心灵的澄澈空明,荡涤尘滓,才能深刻地体察物象的内在精神。
《庄子·养生主》讲了庖丁解牛的故事:庖丁从一开始的眼睛所见到的“无非牛者”到“三年之后,未尝见全牛也”,就反映了多次练习以后就能够“以神遇,而不以目视;官知止”,以心代眼,心手相应。“技”可以进于“道”,技术的高度纯熟使庖丁游刃有余,并得到了极大的精神自由。《庄子·达生》中,“工倕旋,而盖规矩,指与物化,而不以心稽,故其灵台一而不桎。”工倕的手指头灵活地随着器物变化,而不需用心去考究,所以心神纯一而不受束缚。庖丁和工倕的故事都说明除了技巧外,必须心神专一。在心境虚静的前提下,庄子还主张要抒发对物象的真实感情。庄子对“真”做了阐释:“真者,精诚之至也。不精不诚,不能动人。故强哭者,虽悲不哀;强怒者,虽严不威;强亲者,虽笑不和。真悲,无声而哀;真怒,未发而威;真亲,未笑而和。真在内者,神动于外。是所以贵真也。”[2](536)这反映在中国画中,就是注重艺术家主观情感的真实性。书法中,颜真卿的《祭侄文稿》就是饱蘸血泪,写了又圈,圈了又写,点画狼藉,愤激的感情和顿挫的用笔形成昂扬的气势。清代杰出画家郑板桥在《题李方膺墨梅图卷》中说:李方膺画梅“日则凝视,夜则构思,身忘于衣,口忘于味,然后领梅之神,达梅之性,挹梅之韵,吐梅之情”。[4](265)郑板桥也以竹子寄托怀抱,对竹子满腔深情:“风中雨中有声,日中月中有影,诗中酒中有情,闲中闷中有伴,非惟我爱竹石,竹石亦爱我也。”[4](264)
除了对物象有真实的感情外,《庄子·山木》中说:“物物而不物于物,”[2](306)主张顺其自然,主宰外物而不被外物所役使。“知大备者,无求,无失,无弃,不以物易己也。”[2](413)主张遵循天道,没有希求,没有丧失,没有遗弃,不因追求外物而改变自己的天性。只有保持自己的天性不变,面对利欲时才能不感到困惑。苏轼曾提出“君子可以寓意于物,而不可以留意于物”的待物态度,而前者是一种不重在物质占有的、审美的态度,能“足以为乐”而“不足以为病”。“这种游于物之外而不游于物之内”的态度使人娱悦自己的神志,使艺术家的心灵多一些洒脱、欢乐,少一些困扰、负重与贪欲。庄子还讲了善于“削木为鐻”的巧匠梓庆的具体事例,意在说明在创作中要把名利、荣辱抛之脑后。梓庆以斋戒来静定心神:“齐三日,而不敢怀庆赏、爵禄”“齐五日,而不敢怀非誉、巧拙”,除了摒弃外物如名缰利锁的诱惑和羁绊,胸无挂碍外,创作者们还要排除内在干扰,“辄然忘吾有四肢形体”,虚以待物,不受任何尘俗琐屑与杂念干扰,殚精竭虑,“以天合天”。在这种精神状态下,画家超越形骸、忘掉了自身的物理性存在,挥毫泼墨于懵懂间,如有神助,笔下幻化出物象的无穷韵致。《庄子·田子方》中,“解衣般礡,臝”的画者没有“受揖而立”,不受外界干扰,保持着放松的、自由自在的创作状态。郭熙在《林泉高致》中所说:“每乘兴得意而作,则万事俱忘”;“庄子说画史解衣盘礴,此真得画家之法。人须养得胸中宽快,意思悦适……自然列布于心中,不觉见之于笔下。”[5]甚至,国画家们还要像《庄子·人间世》中的“若一志,无听之以耳,而听之以心”一样,即不是用感官的耳朵去听,而是以虚寂之心去听,超脱了视觉听觉形色名声。游心于天地之大美,才能体悟“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的大视野、大境界。
三、“庄周梦蝶”与中国画创作中的物我合一
《庄子·齐物论》讲了一个故事:“昔者庄周梦为蝴蝶,栩栩然蝴蝶也。自喻适志与!不知周也。俄然觉,则蘧蘧然周也。不知周之梦为蝴蝶与?蝴蝶之梦为周与?周与蝴蝶则必有分矣。此之谓物化。”[2](45)在梦中,庄子与蝴蝶的界限消解,融化为一。在中国画创作中,画家由于精神高度集中,也会达到物我合一、物我不分的精神层次。
中国画非常重视写生,珍重精诚,忌讳闭门造车和伪饰。在传统山水画创作达到鼎盛的宋代,许多画家久居深山老林,与大自然交融,无论春夏秋冬、昼暮晨昏、风霜雨雪,以山水为师、为友,终得山水之性情,并以崭新的技法、笔墨情趣为山水代言,其中大画家范宽就是突出的例子。唐代画家张璪提出“外师造化,中得心源”,几乎被所有中国画家奉为信条。而清代山水画大家石涛则提出“搜尽奇峰打草稿”,以求描画出山水个性化的面目。
《庄子·达生》中的佝偻者黏蝉时,“虽天地之大,万物之多,而唯蜩翼之知。吾不反不侧,不以万物易蜩之翼。何为而不得?”[2](287)这位黏蝉的老人精神高度集中,他只知道蝉翼在自己眼前,无论什么都不能搅扰他对蝉翼的注视。这种高度专注的精神状态在绘画创作中也很常见,唐代张彦远在《历代名画记》中说:“夫象物必在于形似。未有形不似而得其神者。”嵇康《养生论》中就曾精辟地谈道:“君子知形恃神以立,神须形而存。……使形神相亲,表里具备也。”中国画强调形神兼备,形为肉,神为骨。“神”是抽象的,但能得物象之品质、精神。北宋董逌在品评李成的画时说:“盖其生而好也。积好在心,久则化之,凝念不释,殆与物忘。”[4](21)苏轼在《书晁补之所藏与可画竹三首》中曾评论文同创作说:“与可画竹时,见竹不见人。岂独不见人,嗒然遗其身。其身与竹化,无穷出清新。庄周世无有,谁知此疑神。”这说明画家在创作时忘掉了自己,忘却了“我”与竹子的界限,身心与竹子融为一体,我即竹子、竹子即我,人、竹不分。清代石涛也说:“山川脱胎于予也。予脱胎于山川也”,“山川与予神遇而迹化也”。显然,这些论断与庄子的“物化”异曲同工。中国画家从自然界中汲取灵气,既师法自然而又不强调模仿,在创作中将画家个人主观感受陶铸于对象,从而达到物我交融、合二为一之境。在这种精神状态下,画家混淆了物我界限,不知何者为我、何者为物,物就是我,我就是物。
庄子不仅讲到了“物化”,他还说:“故圣人法天贵真,不拘于俗”。即圣人效法自然贵重本真,在处理与描绘对象的关系时,我们会发现画家们既崇尚自然,又不拘泥于流俗的倾向。苏轼曾将墨竹画为红色,王维画雪中芭蕉,还有一些画家打破了时令、逻辑限制,自由地组织画面。清代郑板桥在谈画竹时也有一段著名的论断:“眼中之竹非吾胸中之竹,而笔下之竹又非吾胸中之竹也。”总之,画家在创作中融入个人深厚的感情,在为对象传神的同时,也使绘画对象融入了个人的人格、精神。
四、“独与天地精神往来”与中国画创作的人文寄托
中国画是具有高度精神性和纯粹性的艺术。言为心声,“画乃心印”,国画家们透过一幅幅意味隽永的画作寄托着他们的精神和气节。作品中仿佛可以感受到他们的心跳和呼吸。正如诸葛亮《诫子书》中说:“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国画家们气度不俗、志趣高迈,在作品中也传递着这种注重精神层次的气质。
在对待功利的态度上,“孔颜乐处”历来为知识分子所称道,《庄子·让王》中讲了孔子、曾子、颜回和原宪的故事。其中孔子与颜回有一段对话:孔子问颜回为什么不愿做官,颜回回答说:“不愿仕。回有郭外之田五十亩,足以给飦粥;郭内之田十亩,足以为丝麻;鼓琴,足以自娱;所学夫子之道者,足以自乐也。回不愿仕。”[2](491)孔子赞同颜回曰:“善哉,回之意!”显然,在这里,庄子重视的是心灵的舒展,自我娱情悦性的乐趣比权位和利欲更重要。像《庄子·让王》中,曾子“三日不举食,十年不制衣”异常贫寒,但仍然有心情去“歌商颂,声满天地”,显然,曾子精神的丰富远胜于物质的贫寒,正所谓“养志者忘形,养形者忘利,致道者忘心矣”。[2](490)即保养意志的人,就能够忘掉形体;保养形体的人,就能够忘掉利禄;得“道”的人,就能忘掉私心。孔子曾“穷于陈蔡之间,七日不火食”,饿得面黄肌瘦时还“弦歌于室”。庄子记述了如“匡坐而弦歌”的原宪等多位物质贫寒而精神充盈的贤人,显然,庄子担忧“道”的穷困远甚于担忧物质的贫穷,神志的愉悦比物欲的满足更为重要。
庄子的人生态度是达观的。在庄子将死的时候,弟子想要厚葬他,他说:“吾以天地为棺椁,以日月为连璧,星辰为珠玑,万物为赍送。吾葬具岂不备邪?何以加此?”[2](560)这种睿智和超脱反映了这位战国时期先哲的大境界。同时,庄子的“逍遥”精神也为历代文人墨客提供了自由的精神空间,尤其是失意的文人更是把老庄思想奉为至宝。元代画家倪瓒曾表达:“居于儒,依于老,逃于禅。”庄子说:“故圣人法天、贵真,不拘于俗。愚者反此。不能法天而恤于人,不知贵真,禄禄而受变于俗,故不足。”[2](542)即圣人效法自然,贵重本真,并不被世俗所束缚。愚蠢的人就相反。他们不能效法自然而体恤人;不知道贵重本真,而庸庸碌碌地被世俗所改变,所以不能知足。庄子注重精神,认为德性的美比形貌的美丑更重要,“生与死、祸与福、物与影、梦与觉、是与非等各种现象,表面看来是各不相同的,但本体上是一致的,都是道的物化现象罢了”。[6]
庄子美学思想已渗透于国画家们的运思方式和观物方式中,许多画家崇尚出于天然,不忧心于人事,抱守本性而不受变于世俗,任由自我抒写性灵,与大自然心神相通,“独与天地精神往来,而不敖倪于万物”,追求“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的大胸怀、大境界。中国画注重情感表现,展示心灵自由,渗透着一代代艺术家的心血,负载着深厚的文化积淀,它以独特的艺术形式展示着中华民族传统的美学精神。
[1]敏泽.中国美学思想史[M].济南:齐鲁书社,1987.
[2]杨柳桥.庄子译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
[3]转引自陈望衡.中国古典美学史[M].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8.第303页
[4]周积寅.中国画论辑要[C].南京:江苏美术出版社,2005.
[5]俞剑华.中国古代画论类编[C].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2005.第640页
[6]曹础基.庄子浅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2.第42页
(作者单位:河南理工大学建筑与艺术设计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