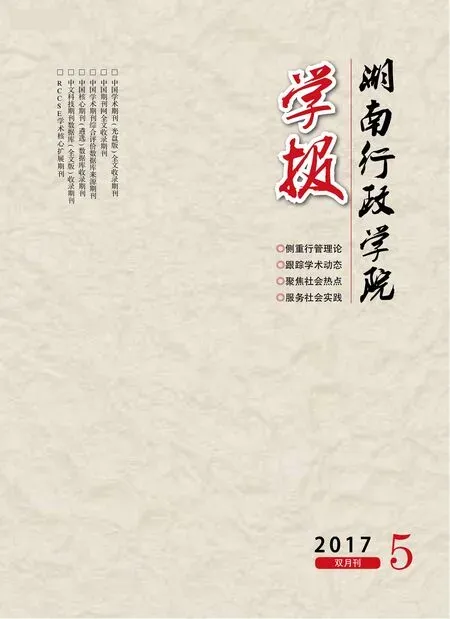历史·结构·情境:神话研究方法论刍议
沈德康
(湖南科技学院,湖南 永州 425199)
文史研究
历史·结构·情境:神话研究方法论刍议
沈德康
(湖南科技学院,湖南 永州 425199)
从宏观层面来看,神话的研究方法是从历时性研究过渡到对横向结构的分析;从字面意义的形态学分类转向对深层结构的揭示;从囿于神话文本转向对社会情境的重视。国内神话研究目前在理论、方法以及范围上都取得一定突破。在此基础上,将神话置于思想史、文化史的宏观背景中,综合利用结构主义神话学、仪式学派、母题分析等方法,将“历史”“结构”与“情境”这三要素结合起来,可使神话研究更具历史性、深刻性与现实性。
神话;方法论;历史;结构;情境
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国内学者引介并采用了不少新方法研究神话,这使神话研究的深度得到提升。在这些方法中,“母题分析”与“故事形态学”的方法尤为显著,得到了广泛使用,学者们首先对中国各民族神话从情节、主题等方面进行了系统、细致的分类。这一工作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因为任何研究都必须建立在严格、系统的分类基础上。“故事形态学”的开创者普罗普(V.Propp)就曾说过:“正确的分类是科学描述的初阶之一。”[1]3此外,学者们利用人类学、民俗学、宗教学等多方面的理论与资料,不断揭示神话的深层意蕴,这使中国的神话研究水平得到极大提升。
然而,学术研究是没有止境的,除了用宏观的思想史、文化史视野考察神话,除了用细致的文献考证以及“母体分析”等方法揭示神话的内涵,更应将神话文本与这些文本置身其中的情境结合起来。在下文中,笔者首先从“文学诠释学”出发,分析普遍意义的文本与情境的关系,然后依次对“结构主义神话”以及“仪式学派”的相关理论、方法进行分析,以此说明将“历史”、“结构”、“情境”三者结合起来研究神话的必要性。
一、文学诠释学
根据“诠释学”(Hermeneutics)的基本观点,文本(神话)、情境(世界)以及研究者(人)这三者形成了一个双向的循环结构。所谓“双向的循环结构”指的是:此三者之中,研究者站在任何一者的立场上去分析第二者,都只有通过第三者才能完成对第二者的分析。换言之,神话研究之所以可能,这是因为处于神话与研究者之间的中介提供了这种可能性。而这个中介就是世界,它是文本与研究者共同的情境。少了这个作为中介的情境,一切都将变得无法理解。
我们知道,研究者置身其中的世界是一个历史性的存在,这就意味着任何时代的观念都是“时代性”(当下)与“历史性”(过去)并存的。因此,尽管任何一个特定的研究者作出的诠释都受到了特定“情境”(观念世界)的限制,但观念的历史性仍为他的研究提供了这样一种可能,亦即——他可以通过文本去建构一个兼具历史性与时代性的世界。马丁·海德格尔(M.Heidegger)说:“话语中我们首先理解的并不是另一个人,而是一个筹划(世界),也即一个新的在世存在的轮廓。”[2]164保罗·利科(P.Ricoeur)说:“世界是一个由文本打开的指称整体。”[2]164这些说法具有相同的含义,亦即:文本分析的最终目的就是通过“视域融合”(the fusion of horizons)建构一个观念世界。这个观念世界是一个历史性与当代性兼具、个体性与集体性共存的世界。故而在神话研究中,“历史”主要指纵向的文化史、思想史进程,它为神话研究提供了一个宏观的时间框架。这个框架使神话在上古(古)与现代(今)、研究对象(客)与研究者(主)之间形成张力。总之,神话是上古社会的一种历史书写,与文明时代的历史书写相比,它更多地是从种群、集体的层面反映早期人类的信仰、文化与思想。
通过上面的分析,我们也不难发现,文本(神话)与情境(世界)的关系十分紧密,没有任何人能抛开情境去解释文本。与之相应,一个人对情境的认识越深刻,那么对文本的诠释也就越合乎情理。而对于“情境”,我们可将其区分出两个层次:一个是观念(意识)层面;一个是实践(行为)层面。因此,在分析“文本”的过程中,由于“文本”与“情境”相辅相成的关系,研究者也多是从这两个层次去进行分析的——这也是“结构主义神话学”与“仪式学派”的方法论根据。
二、结构主义神话学
“结构主义神话学”是与法国学者列维-斯特劳斯(C.Lévi-Strauss)关联在一起的。尽管列维-斯特劳斯对普罗普的“故事形态学”提出了异议,但在很大程度上,“结构主义神话学”的分析方法受到“故事形态学”的启发。[3]
所谓“故事形态学”,指的是一种从情节角度把纷繁的民间故事归纳成“功能项组合”(情节链)的研究方法。普罗普根据故事中人物的行为功能之意义将民间故事概括成“功能项”的组合。[1]17-20“故事形态学”与“母题分析法”十分相近,它们都是从情节角度对故事进行分类,它们之间最大的差异在于“形态学”比“母题分析”所选取的情节单元要小一些。所谓“母题”(Motive),苏联学者维谢洛夫斯基(A.Veselovsk)将其定义为“最原初的不能再分解的叙事单位”[1]11。
总的来说,无论是“故事形态学”还是“母题分析法”,它们都是从情节的层面来分析神话。但神话(Myth)与民间故事(Folklore)有着本质的差异。普罗普就曾指出:“神话与民间故事建立在迥异的形态系统上。”[1]196由此可见,仅仅从情节的层面来分析神话是远远不够的。神话与民间故事的根本差异体现在它们在迥异的情境中发挥不同的功能:(一)神话更多地与严肃的仪式情境关联,旨在唤起神圣的情感,目的是通过其蕴含的观念影响人的实践;(二)与神话相比,民间故事更多地与轻松的娱乐情境关联,其世俗性源自它对情节娱乐性的关注。这两者的差异决定了我们不可能仅仅通过“形态学”或“母题分析”就深入、系统地揭示出神话的实质。
列维-斯特劳斯在借鉴结构主义语言学与故事形态学方法的基础上开创了结构主义的神话研究法。他说:“神话的特征是结构依附于意义。”[4]这就是说神话的实质是体现某种意义,而意义则需要由“神话素”(Mythemes)形成各种结构来显现。他在阐述其方法论时指出“讲述神话”是从左到右、从上到下地逐行阅读,而“理解神话”则是从左至右逐栏进行,把每个纵栏当作一个整体。[5]这意味着,结构主义神话学首先要打破以听故事的方式来理解神话的思路,它要抽掉贯穿在神话叙事中的历时性的时间轴,然后由具有结构功能的“神话素”构成共时性的观念系统。对此,保罗·利科评论道:“结构主义将情节降低到表层结构的水平,这就完全剥夺了情节在叙事中的主导地位。”[2]244但在列维-斯特劳斯看来,要理解神话的深层含义就必须把用时间串联而成的“叙事单元链”(情节链)转换成由对比(相异)、类比(相似)、重复(强调)等关系[15]形成的“观念系统”。
总体而言,“故事形态学”或“母题分析法”与“结构主义神话学”的区别在于:前者只是将故事归纳成了情节链,而后者又在情节链的基础上将其重组为各种观念结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普罗普才说:“列维-斯特劳斯教授是在对我的抽象概念再加以抽象。”[1]191换言之,普罗普的“情节单元”被列维-斯特劳斯转换成了“神话素”。所谓“神话素”,用列维-斯特劳斯自己的话来说即“关系束”[2]116,这意味着“神话素”是从结构关系的层面被定义的,因此,“神话素不是一个神话句子,而是一个由其他独特句子分享的对立价值。”[2]116在列维-斯特劳斯看来,神话的实质是表达观念,因此以叙事(情节)的形式呈现出来的神话仅仅是神话的表层结构(字面意义)。而要揭示神话的深层结构(象征意义),就必须把贯穿在“情节链”中的时间轴抽掉以摧毁情节的线性结构。在打破情节的线性结构后,情节单元将根据自身的属性以及相互之间的逻辑关系重组为观念体系;这个重组的过程也是结构意义逐渐显露的过程。因此,“神话素”不是孤立的情节单元,它是在结构化过程中使神话蕴含的观念凸显出来的结构单元。
总之,“故事形态学”或“母题分析法”与“结构主义神话学”的差异是十分显著的:(一)前者保留了情节,后者摧毁了情节;(二)前者提炼出的是“情节链”,后者分析出的是“观念体系”;(三)前者有时间性,后者没有时间性。
就神话在初民社会中发挥的巨大功能及其表意方式来看,“结构主义神话学”的研究方法值得借鉴。神话绝不是无关紧要的东西,神话中蕴涵着对初民而言极其重要的观念。毫不夸张地说,在神话时代,神话关系到一个种群的存亡、兴衰,影响到初民社会的方方面面。如马林诺夫斯基(B.Malinowski)所言:
“神话在原始文化中具有不可或缺的功能:它表达、增强并理顺了信仰;它捍卫并加强了道德观念;它保证了仪式的效用并且提供引导人的实践准则。因此,神话是人类文明很重要的组成部分,它不是聊以消遣的故事,而是积极努力的力量;它不是理性解释或艺术幻想,而是原始信仰与道德智慧的实用宪章。”[6]244
实际上,以神话为核心的口头传统正是初民社会最核心最重要的教育内容。因此,如果仅仅是从字面意义去理解神话,也就是说如果把神话仅仅是当成一般意义的民间故事来读,那么,我们看到的只会是匪夷所思、古怪离奇的情节,至于其中包含的对初民而言生死攸关的观念是不可能揭示出来的。
列维-斯特劳斯将线性的情节重组为逻辑性的观念体系,以此使神话蕴含的观念凸显出来,这是十分可取的做法。神话以具象的叙事来表达抽象的观念,这是由初民的思维习惯以及语言表达能力所决定的。因此,只有透过神话的表层结构(字面意义),我们才能揭示神话的深层含义(观念体系)。对此,列维-斯特劳斯说:“我主张不是去表明人如何用神话进行思维,而是去表明神话如何用人进行思维却不为人所知……人类心智不管其偶然的信使的身份如何,总是显示出越来越可以理解的结构。”[8]
就对神话文本的分析而言,“结构主义神话学”无疑是目前最具效力的研究方法之一。它的不足之处在于:在把神话文本转化成观念体系后它没有将这些观念放回仪式、习俗等社会情境中进行分析。马林诺夫斯基曾说:
“神话的研究只限在章句上面,是很不利于神话的了解的。”[9]
“文本固然是十分重要的,但是离开了情境,故事也就没有了生命。因此,这些故事植根于土著的生活中,而不是在纸上。”[6]247
这说明神话的存在与特定的社会情境是紧密相关的。“结构主义神话学”的不足之处就在于它仅仅是在“文本”与“观念”之间打转而很少将神话所蕴含的“观念”再放回“情境”中进行说明。正因为这样,保罗·利科曾批评列维-斯特劳斯的神话分析是“无果的游戏和诸成分的滑稽结合。”[2]122利科的批评可能代表了多数读者的心声,但我们不能就此否定“结构主义神话学”的全部价值。对于这个缺陷,我们可用“仪式学派”和“表演学派”的研究方法加以补救。
三、仪式学派
从“仪式”这一“情境”出发来分析神话是另一重要的研究方法。20世纪上半叶以英国学者哈里森(J.E.Harrison)为代表的“神话-仪式”学派(剑桥学派)以及20世纪70年以来以美国学者理查德·鲍曼(R.Bauman)为代表的“表演学派”都注重从社会情境的角度来分析文本。对神话而言,“宗教仪式场”这一“情境”是理解神话的前在框架。
如果说社会是初民生产生活的舞台、情境,那么,仪式场则绝对是在初民生产生活中占据主导地位的核心情境。理查德·鲍曼说:
“社会关系是无形的、抽象的,但是当人们通过仪式聚合在一起,他们采用一系列象征符号和一系列象征性行动时,那么通过这一戏剧化的形式,人们就可能达到对社会关系的理解。所以这些事件(尤其是仪式)就变成了社会力量的象征性威力的象征性展现。所以,按照涂尔干的理解,如果要想了解一个社会中什么是重要的,它是如何结构的,那么最好的办法就是去了解它的仪式。”[7]
对初民而言,宗教仪式是一切社会活动的“轴心”,不仅所有活动要围绕仪式而转,仪式也为社会的运行提供不竭的动力。仪式所具有的轴心地位决定了仪式过程中的语言与行为所蕴含的观念对整个社会都具有极其强大的示范作用。而这种示范作用的真正目的是为了强化社会的秩序,维持生产生活的正常运作。
在现代社会,仪式所具有的典范性已经被制度化的常规教育削弱了。而在神话时代,人们参加仪式活动与现代人完成义务教育有相似之处。从大量民族志中我们可以看到,在初民社会,举行宗教仪式的场合非常多,这些仪式涉及到生产生活的每个方面:祭天、祭祖仪式上要模仿和讲述天神或始祖的创造性行为;在进行狩猎、播种等生产活动前需要举行促殖仪式;诞生礼、成人礼、婚礼、葬礼都需要举行相应的过渡仪式。总之,仪式为一切社会活动确立了极具典范意义的活动模式,哈里森指出:
“仪式旨在重构一种情境,仪式确实是一种模式化的活动,它是实践活动的再现或预期,因此希腊人将仪式称为dromenon,即‘所为之事’。”[10]13
“仪式是一种再现或预现,是一种重演或预演,是生活的复本或模拟,而且尤其重要的是仪式总有一定的实际目的,这些目的指向现实,是为了召唤丰衣足食的季节的轮回。”[10]87
仪式中表现的不只是“所为之事”,这些“所为之事”其实都是“应为之事”。在仪式上,人们不仅要模仿诸神的创造行为,还要歌颂祖辈的丰功伟绩,这些也都是神话的主要内容。因此,“神话”需要放到“仪式场”这一情境中去,才能对之获得恰当的理解。
总的来说,社会的秩序与稳定有赖于外在的社会制度身体化为每个社会成员内在的行为准则。在初民社会中,神话是原始族群保存其观念、价值的主要文化形式。因此,初民社会要确保社会活动的有序进行都必须树立一种典范性的实践模式,而这种具有典范意义的实践往往是通过宗教仪式向整个社会人群辐射的。因此,在仪式中唱诵和表演神话,其实就是用凝结在神话中的观念来规范人们的行为。毫无疑问,这样的神话内容具有展演和垂范的社会价值。
正因为神话能提供这样的价值,所以在神话时代,人们在各种仪式上一次又一次地重述神话。每重述一次,就意味着人们重返诸神创造、发明那些伟大事物的神圣时刻,他们由此再一次回到了时间的源头。神话为他们打开的是一个具有典范意义的原初世界。在这个原初世界(神话世界)中,一切神圣的典范与楷模都值得模仿,因为它们蕴涵着无限的力量(现实意义)。对此,米尔恰·伊利亚德(M.Eliade)指出:
“大多数原始人的行为在他们自己看来,都只是在重复神灵或者神话人物在时间开始之际所做的最初行为。一种行为有意义仅仅是因为它重复了一种超越模式或一种范型。此种重复的目的也是为了确保这个行为的正常,通过赋予其本体论地位而使之得以合法化;行为只有在重复一种范型的时候才是真实的。原始人的每个行为都假定具有一种超越的模式——他的行为是灵验的,只是因为它们是真实的,因为它们模仿了那个范型。一个行为既是一种庆典,也是一种对现实的切入。”[11]
神话中的观念所具有的约束力量十分强大,除了神话本身的典范性,也与初民对神灵以及神话的崇信态度有关。比如,在彝族地区,毕牟(彝族神职人员)在讲唱创世神话时十分严肃、神圣,不能随意出错;在婚礼等场合毕牟要唱诵经典来比赛,记得越多越清晰越受人们尊崇[12];在彝族的一则洪水神话中,马樱花树挽救了彝族始祖的生命,于是,彝族人用马缨花树为新生儿做吃饭用的碗做洗澡用的盆[13];怒族和傈僳族曾争夺一块猎场,相持不下,最终是通过背诵谱系决出胜负的;西盟佤族举行祭天、祭祖仪式,仪式中由最大的巫师为氏族成员讲述创世史诗《司岗里》;新几内亚特罗布里恩德群岛的土著人相信讲述神话会对田野里新种的庄稼有益[6]245;澳大利亚卡拉杰利人的神话中,两个文化英雄在小便时采取一种特殊的姿势,直到今天,卡拉杰利人仍然模仿采用这种小便的姿势[14]。由此可见,在初民社会中,神话的确具有极其强大的影响力,它往往通过影响人们的观念来规范人们的行为。因此,要想对神话有一个清晰的了解,我们不仅要揭示文本中的深层结构,还要结合历史情境来诠释深层结构所表达的社会观念。
综上所述,神话的研究方法是从历时性研究过渡到对横向结构的分析;从字面意义的形态学分类转向对深层结构的揭示;从囿于神话文本转向对社会情境的重视。就目前而言,国内学者在西方神话理论的引介与运用上已做了很多工作,但我们仍然有改进、提升的空间。正因如此,将“历史”、“结构”与“情境”这三者结合起来是很有必要的。只有将“历史”、“情境”、“结构”与这三者结合起来,才能使我们的神话研究更具历史性、现实性和深刻性。
[1][俄]普罗普.故事形态学[M].北京:中华书局,2006.
[2][法]保罗·利科.诠释学与人文科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
[3][法]列维-斯特劳斯.结构人类学(2)[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595-606.
[4][法]列维-斯特劳斯.神话学:裸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700.
[5][法]列维-斯特劳斯.结构人类学(1)[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229.
[6][美]阿兰·邓迪斯.西方神话学读本[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
[7][美]理查德·鲍曼.作为表演的口头艺术[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203.
[8][法]列维-斯特劳斯.神话学:生食和熟食[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20-22.
[9][英]马林诺夫斯基.巫术、科学、宗教与神话[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7:122.
[10][英]简·艾伦·哈里森.古代艺术与仪式[M].北京:三联书店,2008.
[11][美]米尔恰·伊利亚德.神圣的存在[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27.
[12]刘尧汉.我在鬼神之间:一个彝族祭司的自述[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86:153-154.
[13]杨春华.彝族创世史诗中的历史观[J].楚雄师范学院学报,2004(2):68.
[14][美]米尔恰·伊利亚德.神圣与世俗[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2:97.
[15]沈德康.论藏缅语民族洪水后人类再生神话中的生殖观念[J].四川师范大学学报,2014(4):134.
责任编辑:肖 琴
B9
A
1009-3605(2017)05-0091-05
2017-04-12
湖南省教育厅一般项目“中国藏缅语民族文化起源神话研究”(项目编号:15C0605);湖南省社科基金一般项目“中国苗瑶语民族神话的整理与研究”(项目编号:16YBA179)。
沈德康,男,四川茂县人,湖南科技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神话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