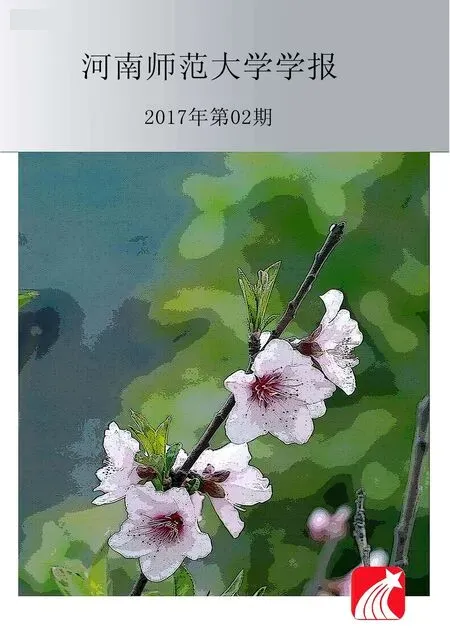论李光地八股文批评中的理学立场
陈水云,孙达时
(武汉大学 文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2)
论李光地八股文批评中的理学立场
陈水云,孙达时
(武汉大学 文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2)
明末清初,正是八股文由全面衰颓到振衰起弊的一个阶段。一方面,科举延至清初,在千余年历史传承的同时,其制度本身的各项弊端也于此时暴露无遗。明末士子为求中式而巧用机法,通过以记诵预先“拟题”之文,或以“程墨”“房稿”等时文范本应试的方式,达到了投机中第的现实收益。加之天启、崇祯以来相当一部分士子厌弃程朱理学,疏离现实,且游学无根,使他们的八股文尤显“竞尚浮华,疏浅无味”,以致落有“庸靡臭腐”之讥。另一方面,这一时期也有一些士子有感于明末社会学术空疏、士人思想涣散的教训,他们心思纯正,勤勉向学,以程朱理学和经世实学为道德、文章之本,其八股文从内容到格式皆恪守“成弘正统”。李光地即是这一类士子的体现。在理论批评上,李光地论八股首重经学和理学根底,注重对儒家义理的阐发,分别从“理”“法”“辞”“气”四个角度,将八股文批评与理学研究合二为一,提倡八股文以发明义理、阐释经义为第一要义,强调八股文有用于社会的文体功能意义。在创作上则以“清醇”、“本色”为标举,主张以程朱理学的思想作为八股文创作、批评的标准,显现出融冶经史、义理鸿博的文风特征,在对清初八股文的繁荣景象起到了积极作用的同时,也为之后以学问、考据见长的有清一代八股文特色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科举;理学;八股文;李光地
李光地(1642—1718)是清初著名的理学家,主要活动在康熙一朝,亲历了清初社会的由乱而治,如康熙帝平定三藩、收复台湾、治河理漕、复兴文教、肃革朋党、储君废立、朱子崇祀、经学复苏等国政时事,故而在清初政治、学术领域中,李光地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梁上治《四勿斋随笔》云:“李文贞公知兵又好讲学,酷似王阳明,先生之团结乡勇,抗耿逆,以此受知洊,跻卿相,亦与阳明相似。所不同者笃信朱子耳。”[1]151从其受学经历看,他精于权谋之术,早年兼有朱、王学说,并能揣摩上意,最终选择弃王从朱,成为清初程朱理学的一大代表。从其八股文批评来看,他强调阐发“义理”为八股文第一要义,并积极呼应康熙帝“雅正清真”的精神主旨,从理、法、辞、气四个角度,提出八股文写作应以“清醇”为宗。此外,李光地还针对晚明科举的弊端,在康熙帝的支持下推行科举改革,加强了士子与学人对传统经学的重视,也使五经之学在科举中的地位得到提高,既为之后“以考据为八股”的文风打下了深厚的基础,也为乾嘉学派的崛起做足了准备和条件。
一、八股文批评的理学基础
从《李文贞公年谱》的记述可知,李光地出生于文化世家,李氏一门中不乏因究心理学、研习八股得仕而显赫于世者。祖辈李懋桧,系明万历八年进士,先后任礼部郎中、光禄寺少卿、太常寺卿,有《李太常文集》行世。父李兆庆,系清顺治贡生,有《教忠堂遗稿》行世,一生笃信程朱,以教授为业。兄李光龙,系明崇祯十六年进士,官至翰林院检讨,以《易》学名世,有《阆山集》行世。对于家族往日的荣耀,李光地既引以为傲,又以之自省,称“诸公在隆、万间,皆一时之选也,虽奉常善扬祖德,然诸公靡然共声,可以观仁矣。盖吾祖之仁洽于乡,显于国,斯是以不可掩也。……是故今日之称祖德也,不以幸而以戒。”[2]38李光地的启蒙教育即是在这样深厚的家学背景和家族文化氛围中完成的。
具体来说,李光地的理学基础根植于其父李兆庆的庭训督导:“父生明季士习披猖之时,动以先儒诟病。乃独多蓄程、朱书,及同郡蔡、林诸公讲说,淳谆教授诸子。”[2]39李兆庆虽生活于明代中后期,但却不染晚明学者排诋宋儒、游谈不学的风习。又“明末,闽中学者饮酒读史,崇尚李卓吾书,举国若狂。而先君笃好《性理》。赤贫赴考时,十金买得一部内府板《性理》,喜若重宝。归而督予读之,遂开子孙读书一派。”[3]466由此可以看出,李兆庆对幼年李光地灌输的纯乎是濂、洛、关、闽的宋儒学说,对李光地也没有施以迎合时好、急功近利的功名要求,而是投以其成为“纯儒”的期望。据李光地之孙李清馥言:“先生(李兆庆)教子必备熟诸经,缚及天文、地理、六韬、九章之言,悉俾了然于心口,而后出帖括授之。诸子非十五而上,不知有八股业也。……时家计已大罄,益自刻苦穷日夜,专心一力。尝积月危坐,不就枕席。所讲诵无旁杂,卓然以前修自期。不徒追时好,务应举之业而已。”[4]118在父亲的亲自教育下,李光地早年为学不以应试为唯一动机,这使得他没有明末士子和王学末流那种不谙本经、专务迎合的“杂学”,取而代之的是心思纯正、学有根柢的“博学”,为他以后纯粹的理学思想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在康熙九年考中进士迁居北京之前,李光地大多在家乡福建一带从事学术活动,故而深受闽地学风传统的浸染。闽地学风在明末清初的一段时间里极为复杂。首先,“闽学”在宋代是“新儒学”四大学派之一,而朱熹又是福建尤溪人,一生中大半时间都在福建从事著述、教育活动。在朱熹及其弟子于闽地的讲学活动中,福建各地纷纷创建书院、学堂,确立了朱学在闽地学术传统和民俗民风意识中主流地位。因此闽地学人素有尊崇朱熹的传统,李光地亦然,认为朱熹即当日的孔子,肯定了朱熹学说的正统性:“孔子之生东迁,朱子之在南渡,天盖传以斯道,而时不逢。”[2]263其次,在明代中后期风行全国的心学思潮,也蔓延至闽地。对于如何在心学与理学之间取舍,早年李光地也确实有徘徊不定的犹豫,一方面,认为王学末流对传统经学、理学及文风士习造成了恶劣的影响:“当明季时,如李贽之《焚书》《藏书》,怪乱不经。即黄石斋的著作,亦是杂博欺人。其时长老,多好此种,却将周、程、张、朱之书饥笑,以为事事都是宋人坏却。”[5]383另一方面,并不将心学完全否定,而是对程朱、陆王学说加以兼容的态度,使其综合互补,甚至在某些地方更加倾向于陆王一派:“愚谓陆子之意,盖以物有本末,知所先后,连格物致知以成文,其于古人之旨既合,而警学之理,尤极深切,视之诸家,似乎最优,未可以平日议论异于朱子而忽之也。”[2]173晚晴学者徐世昌也据此称赞其为“以朱子为依归,而不拘门户之见。”[6]1531
由此不难看出,李光地早年的治学主要是对程朱理学的精研探索,这正吻合于清初统治者对于程朱理学的倡导和政治需要。康熙作为“武功”定鼎之后而继统的帝王,一度大力提倡程朱理学,认为:“(朱熹)文章言谈之中,全是天地之正气,宇宙之大道。朕读其书,察其理,非此不能知天人相与之奥,非此不能治万邦于衽席,非此不能仁心仁政施于天下,非此不能内外为一家。”[7]846以期用理学及传统儒学中“天人感应、君权神授”、“君臣父子”、“存天理、灭人欲”等伦理纲常去弘扬“文治”,进而维护与巩固清廷统治的长治久安。于是《四书》《五经》就成了清代科举考试的全部内容,朱熹注解也相应地成为衡量士子解经立言是否合乎“道统”与“政统”、能否达到“金榜题名”要求的唯一标准。作为康熙朝的重臣,李光地与康熙帝相配合,积极宣扬程朱理学,自言其治学是“近不背程朱,远不违孔孟,诵师说,守章名,服儒者,摒弃异端。”[2]255时时事事以儒家之道恪守自遵。这反映在文学批评,尤其是八股文批评上,表现出继统儒学,主张以《四书》《五经》为学问根柢的理论特色。
二、理学观念下的八股文批评
在理学观念的统驭下,李光地对于八股文从理、法、辞、气几个方面提出了具体要求。
(一)求理于经,弘扬义理
明清之际学术发展经历了巨大的变革,晚明王学末流日渐流入空言性理的狂禅之学,入清以后的学者更是纷纷对这种言心言性、束书不观的学风加以抨击,逐步由理论思想阐释转向从经史典籍的文本中寻求“真理学”的道路。梁启超说:“晚明王学极盛而敝,学者习于‘束书不观,游谈无根’,理学家不复能系社会之信仰。炎武等起而矫之,大倡‘舍经学无理学’之说,教学者脱宋儒羁勒,直接反求之于古经。”[8]李光地正是沿着此种“经学即理学”道路,于《六经》中开展关于理学和义理的探索。他说:“天下之道尽于六经,六经之道尽于四书,四书之道全在吾心。……夫子所留下的书,万理具足,任人苦思力索,得个好道理。若是他不说的,所见毕竟不确,久便自见其弊。”[5]7李光地将儒家传统中的“文以载道”观念和理学体系中的“万物之理”以及陆王“以心为本”的主张融合统一,使之相互促进、共同发展。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李光地又与顾炎武、朱熹、陆王不同,他既不走顾氏以音韵、训诂而通经的道路,也不走朱熹“格物穷理”的道路,更不走陆王向内心求理的“心即理”的道路,而是将《六经》视作“理”之载体,直接从经传文本中寻求答案,走了一条“求理于经”的道路。故而李光地尤为推重八股文创作要有经史学问的根柢本源和现实实用的指导意义,认为:“孔子之书,如日月经天,但看尊之,则天下太平。废而不用,天下便大乱。”[5]7简单来说,“求理于经”,是从圣人经传,即孔子之书中找得万物之理,即辅政安邦之道,并将其应用于实践,即落实到具体的八股文创作中去。
因此,李光地的八股文观念,首先是针对八股文的思想核心要素,即“理”的层面上主张体现出“发扬义理”的认识觉悟。李光地认为,八股文应当以发扬义理为第一要义。因此在审视八股文时就表现出重义理而轻词采、重书本学问而轻处世清谈的批评倾向。对于明末八股文的空谈之风,更是予以猛烈的抨击。他说:“明末时文,看其议论气势,直欲凌驾前人,掀天揭地。由今看来,卑鄙无味之甚。以其理不足,于题不相干。大约时文之坏,由不肯看书起。不肯看书,则于理题懵然。理不胜,则思以词采胜。以词采胜,则求新奇灵变,以悦人之耳目,遂离经叛道而不可止也。”[3]486于是,李光地主张通过刻苦读书的实际工夫将经学与理学相融合,在不断地经学研习中明晓理学义理:“读书以穷经为本,以明理为至,穷经所以明理也。然六经之规模宏阔而辞义简奥,故必以《学》《庸》《语》《孟》为之阶梯。四子之心传不继,而纯粹云亡,故必以濂、洛、关、闽为之门户。”[2]536《大学》《中庸》《论语》《孟子》与周敦颐、二程、张载、朱熹共为宋明理学的门户,李光地通过对《四书》和“四子”学说的提倡,呼吁学人、士子由此入门进而转向对《六经》研习的为学路径。由此可以看出,李光地的学术思想以程朱理学为进阶,其最终落脚点却是经学。这种思想反映在八股文批评上即主张以《六经》为根基,以效法先儒、阐释经义为八股文写作的努力方向。如其所云:“学者之学,期于有得,则制义之根本《六经》也,其门户先儒也。讲诵而思索之,固即汉、宋所谓专经之艺、穷理之功也。”[2]314既然制义的根本是《六经》,那么八股文理所应当的担负起羽翼经传的责任:“盖制义无论为一代取士之制,其精者羽翼经传,至者语皆如经。如顾亭林‘且比化者’一节文,直驾守溪而上。盖字字有来历,精于经学,而其辞又能补经之所未备,而不悖于经,亦可为经矣。”[3]478这就从文体功能上肯定了八股文与上古礼乐、圣贤经传、汉唐注疏一脉相承的地位。于是八股文写作,也理当以发扬儒家义理为主要内容。唯有如此,才能切实履行八股文的创作意义,并流传于后世。
(二)理法相融,文理合一
李光地对八股文法的要求,主要着眼于统筹八股文写作技法与理学义理关系的层面。在以发扬义理为第一要义的思想主旨下,李光地对士子理学学养极为重视,认为八股文创作与理学研讨是合二为一的,要求士子在八股文创作时于辨明经义、体会语气的基础上,还要对经书题义有所阐发。这是因为“圣贤说话,不过数言可了,正须以我意论断耳。如今之描画口角以求拟肖,圣贤肯为之哉”![3]490在李光地看来,既然八股文要担负起发扬义理的任务,士子就必须效仿先儒,即所谓“以先儒为门户”,对义理进行汉唐注疏和宋明传注般的发明创造。注疏与传注都是以质朴、严谨的语言和文法对经传内容做出精深的阐释,故而八股文也应该遵循“以其理透也,渠且会安顿题目语气”[3]490的写作模式。如其所云:“顾经义之文,主于明理,明理之文,主于深厚简切,平易疏畅,而恶乎以才乱之。”[2]312简言之,李光地对八股文法的要求,旨在融儒家义理、八股程式、文章写作和理学研讨于一体,以理学义理为八股文写作的基础,又以八股文写作为义理问题研讨的深入解释,主张向切于政事、利于国民的儒家传统回归。因此,李光地对明代中后期“徒事机法”“悦人耳目”的八股文风嗤之以鼻,肯定并提倡明代中前期义明理足、体大式正、自然工稳、言之有物的八股文。
在李光地看来,“理”是一切文学创作的根基,他说:“韩文公一肚皮好道理,恰宜于文发之。杜工部一肚皮好道理,恰宜于诗发之。所以各登峰造极。”[5]365韩愈之文和杜甫之诗的文学成就,并不是因创作技法的圆熟运用使然,而是通过对高层次儒家思想的扬弃,凸显文章的文用道德标准,从而获得了文学的不朽价值。以此说明,文人只需专注于“道”的体悟和“理”的遵守,将个人创作融入“理”的精神,文章即可成为佳作。如其所云:“小学生初作文,要得有词,有了词又要有气,有词气再要他有法,终之要他有理。成人不如是。第一须求理,理足而法、气、词具焉。此正法也。百余年不讲矣。”[3]486所谓“理足而法、气、词具焉”,即是达到了理法兼备,不工而自工的文法要求。
需要注意的是,李光地并非完全将八股文视为疏经述理的文体,而不注重其特殊的程式法度。恰恰相反,李光地对八股文的功令格式十分看重,这从他推重明代王守溪的八股文中即可看出:“问:‘王守溪时文,笔气似不能高于明初人。’曰:‘唐初诗亦有高于工部者,然不如工部之集大成,以体不备也。制义至王守溪而体大备。某少时,颇怪守溪文无甚拔出者,近乃知其体制朴实,书理纯密。以前人语句,多对而不对,参差洒落,虽颇近古,终不如守溪裁对整齐,是制义正法。如唐初律诗,平仄不尽叶,终不若工部字律密细,声响和谐,为得律诗之正。’”[5]389在这里,李光地以律诗创作的体式规范为例,强调八股文在弘扬义理基础上还要符合“体制朴实”、“裁对整体”的写作程式,才算得上规范合格的八股文。又“作文要词调不离样,屺瞻时文要字字有出处,读来却不似时文,作古文则可,时文断不可。”[3]486李光地认为,那些完全以古文笔法写作的八股文,纵然有深厚的经史根底,但由于忽略了八股文特有的程式规范,故而在整体上也丧失了八股文本来的语气和面貌。如果八股文缺失了本身独有的词调、语气、程式等法度规范,那么八股文也就无所谓“八股”之名了。
综而言之,主张八股文的“理法兼备”,是李光地对士子经史学问、发扬义理和经营构思三方面的总体要求。发扬义理是写作主旨,经史学问是写作基础,经营构思是写作体现,三者相互依存,缺一不可、偏一亦不可。此外,在义理、学问、构思的结合中,李光地还特别指出,三者于八股文写作中能够达到浑然一体,不求机巧、自然呈现的效果,才算得上是优秀的八股文,此种话语其在《榕村语录》和《榕村续语录》中有反复申说,如:“做时文要有口气,口气不差,道理亦不差。”[5]390又“守溪自然算时文第一手,本是一极体贴好讲章,又创出许多法则。其安顿亦极好,极费经营,而绝不见有巧处。此所以好。若一见巧,便不好。”[3]488等等,不一而足。以此为观照,再反观李光地本人的八股文写作,并无过多的浮烟浪墨,几乎全是简单明了的义理阐释和对宋人语录的稍加整饬,诚如清人蔡芳三所言:“海内论文家群推安溪为弘正嘉正宗,而不知安溪出于宋五子书,搜泽融浃,而又能自在流出,故卓然称大家。”[1]152
(三)辞尚清通,文字本色
李光地在对八股文“理”、“法”两个层面提出了明确的批评要求后,很自然地在八股文具体写作过程中对所采取的表述方式、言辞语气等“辞”的要求,也必然与其浓厚的理学思想相呼应。李光地将八股文写作中“理”“法”“辞”三者之间的逻辑关系解释为:“作文且未须说得体制法度,第一先要明白。若那事考究得十分明白,据事直书,自然不烦删减,而闲文自去,词必古矣。”[5]386从这里至少可以得出三点认识:第一,李光地认为八股文写作中的各项步骤环节是有序展开的。在“理”的统摄下,作文的形式遵循于经义、义理的文体需要,内容遵循于对“理”的发明、阐释的理解需要,语言又遵循于对“理”理解的表达需要。第二,八股文内容要有切实所指,不能流为空疏闲谈。八股文旨在“发扬大义”和“通经致用”,故而一切无关于发明经义、阐释义理的闲散文字都不应出现于八股文写作中。第三,八股文的言辞要以“古”为尚。八股文强调摹仿“圣贤口气”,其写作过程中的遣词造句也就不能以流行时好的语言为表述体现。以此三点认识为切入点,进而审视李光地对八股文“辞”的写作要求,就不难理出其完整且清晰的批评体系。
李光地认为,八股文是由“理”“法”“辞”三部分共同构建起来的一个逻辑有序的整体。作为官方学术正统思想的程朱义理,是万事万物的常存恒定之“理”,可以视作是长期以来人们思想、观念、认识取向标准的一个传统。在“理”的传统下,相应形成了一套约束人行为的规范法制,推及作文,就成了八股文特有的功令格式和思想范式。而士子在写作八股文时的具体表述,也就在“理”的传统和“法”的双重框架下展开进行,因此八股文对言辞的要求也必定是以合乎儒家传统和理学规范作为唯一衡量标准的。李光地即如是说:“文字不可怪,所以旧来立法,科场文谓之‘清通中式’。‘清通’二字最好,本色文字,句句有实理实事。这样文字不容易,必须多读书,又用过水磨工夫,方能到。非空疏浅易之谓也。”[5]388李光地对八股文字的批评要求具体落实到“清通”的标准上,实际上包含了两层用意与要求。其一是对经义、义理以雅致朴实的语言做出有根柢、有所指的阐释表述,“清”指八股文中所使用的本色文字,“通”指八股文作者具备通经有据的学问根底。由于晚明以后,在八股文写作中出现大量不遵朱注、不谙经史,反而竞尚辞采、好为机巧的空疏弊端,故而李光地提出以“理”为中枢,要求士人于创作之初首先要在贯通经义和熟识义理上做实际功夫。在李光地看来,“理”是古朴实在的,经传本文及汉宋诸儒的注疏文字也是古雅质实的,那么八股文的文辞也应该保持与经书文字一致的切实风格。他说:“时文要字字可以讲得方妙,一片雪白。虚字体贴传神,实字如铁板推搬不动,如经传一般。无一字无义理,方是正宗。”[5]486八股文既然是要“发扬大义”,其表述就必然是紧密围绕义理展开,于是八股文中的“辞”与“理”之间就产生了不夹杂其它任何中间因素的直接对应的关系,即所谓“一片雪白”。在这种观点下,李光地一针见血地指出那种尚词章、务机法的八股文纯属“以其理不足,于题不相干”的“卑鄙无味”之文。然而,先儒经传所用的质朴古雅的“本色文字”,并不等同于后人日常使用的浅显通俗的“平常文字”,其中差别即在于长期踏实的读书、训养功夫。李光地说:“明朝人真不肯读书。古人文字,看去简古,零零落落,若不可解。久而读之,脉络井然,一字不妄下。后人文字,如七八岁童子作,看去无不了然。然寻其字眼乱下,语无伦次,意不相接,多不能通。”[3]479只有通过大量读书之后,士子才能积聚起笃实的学问和丰厚的涵养,才能够对义理进行深入地思考,从而获得其微言大义,即其所谓“读书须有跋涉意。”[3]492做好了切实的学养功夫,再转向八股文写作,也就能自觉、娴熟且自然地形成“清通”的本色文字。
“清通”的第二层含义指的是在八股文写作过程中要尽可能做到文字简洁。这是由于特定文题下八股文写作的篇幅和语句形式,受制于八股文体的功令格式的限定,因此在有限的空间里必须同时满足言有所指和言简意赅两项要求,这也是孔子所提出的“辞达”之意。李光地认为古文与时文在评选上有共通之处,即都要以“句句有实理,有实事,简净踏实为上”[3]478为标准,做到“如今无论选古文、时文,即将其文当作经来看,一字不放过好”[5]388的从简、从严地评选。由此可以看出,李光地认可的八股文佳作,不是那些充斥着花哨华丽的辞采和精巧细腻的机法,却无太多关于发明义理内容的文章,而是语句整齐、文辞平易中却又具有深意的文字。诚如其所言:“其文似淡实有味,似疏实周密,似少实足有等。……此天下之至文也。”[3]488
(四)词气贵清,神气贵盛
在对“理”、“法”、“辞”展开评述的同时,李光地还特别关注其所展现出来的精神面貌,反复强调八股“文气”的重要性。李光地首先指出,文中之“气”是国家命运兴废、士人精神盛衰和社会道义隐显的重要表征。根据明代成化、弘治时期国家的兴盛与这一时期八股文的纯正、万历以后国家的衰败颓废与这一时期八股文的离经叛道的实际情况,李光地对八股文之“气”与国家之“运”做出了相互印证的论断:“文章与气运相关,一毫不爽。……明代之治,只推成、弘,而时文之好,无过此时者。至万历壬辰后,便气调促急,又其后,则鬼怪百出矣。”[5]366并针对文章与气运相关联的内在原因进一步形象地解释说:“某尝有一譬,春夏秋冬,气候之小者也;治乱兴亡,气运之大者也。虫鸟草木,至微细矣,然春气一到,禽鸟便能怀我好音,声皆和悦。秋气一到,蛩吟虫响,凄凉哀厉。至草木之荣落,尤显而易见者,况人为万物之灵,岂反不与气运相关?所以一番太平,文章天然自变。”[5]366在这里,李光地将禽鸟发出的“和悦”之声与“哀厉”之响,分别视作是春天生机勃勃与秋冬万物凄凉情景的具体体现。“和悦”表达了春天禽鸟鸣叫的两个特点,一是声音“祥和”,二是令听到声音的人感到“悦耳”。这种“祥和”、“悦耳”的声音也很契合儒家提倡的“雅正”、“温柔敦厚”的文艺传统和审美标准,于是便可以很自然地由此推论之八股文所呈现出的类似于禽鸟“和悦”之声的“雅正”文气,也必然是太平盛世的反映,反之则是萧条乱世的表征。
接着,李光地又对八股文“雅正”之气做了详细的说明。在他看来,“雅正”是八股文风貌的总体要求,落实到具体实践的文本创作中,表现为“词清”和“理淳”两个方面。“词清”即是八股文言辞要清畅平易,要切实近理,要有太平气象。他说:“文字肯切实说事说理,不要求奇求高,都有根据,天下便太平。明末,如金、陈、黄陶庵、黄石斋,具高才绝学,而其文求其近情理者甚少。观其自命,几几分座尼山,后亦归结于忠孝。到底文字好不好,真是关系气运之物。”[3]483又云:“向尝语韩慕庐以:‘时文奇,不如平。明末文毕竟是有词,气不如成、弘。公试看东汉之末文字,何如西汉;中晚唐诗,何如初、盛;南宋文字稀烂,何如北宋。自然太平时文字正气。’”[3]485这都是从文辞的角度讨论八股文所呈现的“气”。李光地认为凸显“气”的强盛的方式不是高才绝学的华丽词章,也不是精巧高奇的聪颖构思,而是清通近理、彰显盛世的平易文字。“理淳”即是八股文要运用正统的理学思想作为写作的主要内容。他说:“(杨宾实)其时文、散文,生成笔气,便似曾子固,气甚厚,下语甚重。其读五经,妙在不是好其文词为文章,却有甘其滋味的意思,故能措之乎用。”[3]191李光地认为杨宾实之所以能够做出文气厚重的经义八股,是因为他读经书不是“好其文词”,在词章上下功夫,而是“甘其滋味”,完全在发明义理上用功,再以对义理的个人理解为实质内容,下笔成文,自然就获得了“气甚厚,下语甚重”的文气。如所云:“临文在题之皮毛上铺排,似是而非,心思不入,了无神气。至于浮浅无味,最怕人,病却中在根本上。”[5]390他主张士子将心思和精力用在对义理的研究上,也唯有如此,其创作出的八股文才能有神气,不浮浅。
最后,李光地又统筹了“词清”和“理淳”两种观点,提出了以“清醇”为标准的八股文批评观。他说:“己丑会试,予与同事者极力欲返之清淳,且以观人学殖,非兼之后场弗尽也。……竣事后,士友议论,则或以清淳许之者有矣。夫极清淳之至,必也通经学古,理明而气盛。”[2]290由前文的论述可知,要想达到李光地所谓文辞“清通”、义理“醇正”的要求并不容易,它需要耗费大量的实践和精力去做切实经史、义理学问的“水磨工夫”。但以此八股文批评标准,却也恰恰可以反过来印证士子学人的是否具备丰厚、扎实的学养,从而为政府拣选出具有真才实学的合格优秀人才,这也是八股文实际功用的一项直接体现。另一方面,八股文“清醇”与否也是对于文学传统、世道学术和社会风气而言的一项重要维系,李光地说:“为文贵清而贱浊,何则?神气盛则清,衰则浊也。……人之盛也,耳目言貌,清明盎溢,或衰病则反是。繁词缛饰,无益于昏也。虽然,神气者物之主,而有所以主乎神气者,则其道大而说长矣。以文章一事论之,词气之清由于神气之盛,神气之盛根于义理之明,义理之明本于学术之端,与人心证,是亦道大而说长者也。”[2]315词清、气盛、理明、学端,这四者之间环环相扣、紧密关联又彼此相互顺应,因此,八股文的“清淳”指向也是连带着文学、学术与风气共同稳健发展的条件,对之后乾嘉时期“考据”八股文的形成以及整个清代学术的走向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综上所述,李光地以理学思想为旨归,主张“求理于经”,对清初经学和理学的复兴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他从“理”“法”“辞”“气”四个角度,将八股文创作与批评与理学研究合二为一,提倡八股文以发明义理、阐释经义为第一要义,强调八股文有用于社会的文体功能意义。所标举的“清醇”八股文观念,是对明末清初学术空疏、经史涣散、理学凋敝局面的一次整饬,并以此引导了康熙三十九年的科举改革,得到了康熙皇帝和众多学人的积极响应。据《清文献通考》载:“寻议,嗣后乡、会试作五经文字者,应于额外取中三名。若佳卷果多,另行题明酌夺。五经文字草稿不全,免其贴出。二场于论、表、判外添诏、诰各一道。头场备多页长卷,有愿作五经者,许本生禀明给发从之。(康熙)五十年,增五经中额。顺天二名,外省一名。会试增中三名。”[9]显然,通过此次改革,《五经》在之后的科举考试中的地位有了明显提高。与之相应地,这一时期的八股文创作也逐渐消弭了之前“空疏”“机法”“游戏”“奇巧”等弊病,展现出“宗经崇理”的文风面貌,这即是康熙帝“雅正清真”和李光地“清醇”八股文观得以落实的现实体现。
[1]梁章钜.制义丛话:卷九[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
[2]李光地.榕村全集[G]∥榕村全书:第8册[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13.
[3]李光地.榕村续语录[G]∥榕村全书:第7册[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13.
[4]李光地.榕村谱录合考[G]∥榕村全书:第10册[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13.
[5]李光地.榕村语录[G]∥榕村全书:第5册[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13.
[6]徐世昌.清儒学案:卷四〇[M].北京:中华书局,2008.
[7]朱熹.朱子全书:附录[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8]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3.
[9]清文献通考:卷四八[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88:5310.
[责任编辑 海 林]
10.16366/j.cnki.1000-2359.2017.02.020
陈水云(1964—),湖北武穴人,武汉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明清文学及文论方向研究;孙达时(1988—)河南开封人,武汉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明清文学及文论方向研究。
I206.49
A
1000-2359(2017)02-0129-06
2016-05-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