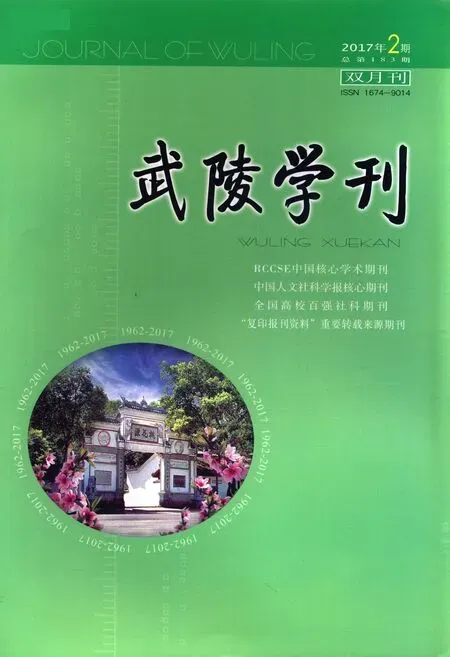被遮蔽的“第三空间”:跨文化写作者的文学表意实践
闫炜炜
(1.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校文化学教研部,新疆乌鲁木齐 830000;2.华东师范大学人文学院,上海 200241)
被遮蔽的“第三空间”:跨文化写作者的文学表意实践
闫炜炜1,2
(1.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校文化学教研部,新疆乌鲁木齐 830000;2.华东师范大学人文学院,上海 200241)
“第三空间”是隐匿于多民族文学关系中的一种跨文化写作的文学表意实践空间。跨文化写作者的汉族身份在少数民族文学领域往往受到重重遮蔽,但他们又因为所具有的双重视界与“有方向的写作”而成为民族文化阐释的有力发声者,他们观看事物的另类角度和始终持有的审美距离,使其作品抵达民族交往、文学交融、文化认同的“第二现实”境界。跨文化写作者的文学表意实践,凸显了文学人类学的素质与情怀,扩大了文学文本环境,有助于写作主体文化身份固有和建构的不断弥合。
“第三空间”;跨文化写作;“第二现实”;文学表意实践
一、“第三空间”:跨文化交流间的盲视与隐匿
如同地缘政治、区域经济的强烈显现一样,多民族聚居地及多民族文学呈现出的区位特征,一直是一个被不断关注和表达的话题。纵观中国当代多民族文学发展研究,成绩斐然,突出表现在多民族史观研究、多民族文学专题研究和多民族关系研究三个领域。暂且抛开前两方面不言,单就多民族关系研究方面,就有费孝通先生提出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乐黛云先生的“跨文化对话”、梁庭望先生的“中华文化板块”、杨义先生的“重绘中国文学地图”等一些有影响力的讨论和成果,但这些研究在展示中华多民族文学内部的互动、对话与交流意义方面,仍然有其疏漏之处,这就是对隐匿在跨文化交流间的“第三空间”的盲视。
“第三空间”是迈克·克朗曾在《文化地理学》中提及巴哈的言论时所指出的。迈克·克朗认为,各文化间的关联常被看成某个文化精髓的分离的容器,但这些关联根深蒂固。研究这些联系会压制内部和外部文化的想法,会开启称之为“第三空间”的想法,也即吉尔罗伊称之的既不是外部文化也不是内部文化,而是“两个伟大的文化集合”间占有一席之地的“双重意识”[1]。这个观点借用在这里,就是指在同一个多民族地域范围之内所衍生出的文学“民化”“汉化”现象以及相互之间循环互证问题。换言之,在当今的少数民族文坛上活跃着一大批汉族作家,他们具有双重乃至多重相互平行的民族特性基因,像周涛、沈苇、红柯、马丽华、迟子建、范稳等人,他们通过跨地域、跨族群、跨文化的异域体验,在“流亡”的路上,用超越家园意识的眼光叙述着一个个被“劫持”和“征用”的地方。跨地域文学表达的这一群体来自祖国的四面八方,他们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从中国内陆城市走向了地理版图的边缘地带,携带自我的籍属文化开启远方的追寻,突破了囿于“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本地人写本地风貌”的常规,打开并形成了中国地域文学的新视界。跨族群是指这些作家的“异族意识”,他们认为族群意识存在于与其他族群的互动关系中,并非单独存在。在进入到少数民族聚居地时,他们受到本族意识与异族意识的双重作用,在与异族密切互动时,也完成了族际间的身份转换。跨文化在于作家们在不同的文化穿梭游走间打破所谓纯粹本质的静态连续以及所谓的疆界、民族、类型的文化界限,秉持强烈的人类学实践性和宽容精神,在联系与接触的文化中,理解阐释他者文化,更新印证反思自我文化,呈现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文化混血状态。而这些被“劫持”和“征用”的地方,在他们的笔下重放异彩,留给读者新鲜的文化感受。他们从不同的文学样式、不同的文化价值立场构建当代多民族文学的面貌和格调。他们中,有的深刻参与了当代中国文学的演进,有的则需要更久一点的时间去证明其对当代多民族文学的意义。但从代表少数民族文学最高规格的“骏马奖”评审中,我们可以看到,“少数民族作者用汉文或少数民族文字出版的文字作品”作为明确规定的评奖范围,在一定层面上反映出作家族别决定论比作品题材决定论操作性更强,而族属、题材、语言缺一不可的“民族文学”范围的界定,无疑对他们来说是在场的尴尬。这一种忽略,其实更多的是割裂了多民族文学关系上优势互补、活力互注、素质互融、形式互启的反馈互惠的内在联系。
因此,“第三空间”写作表现在多民族文学的交流互动层面实质上就是一种体验式写作,是由跨地域、跨族群、跨文化的主体杂糅搭界着地域、民族和文化的文学表意实践行为,是创造力和生命力的有效磁场,不仅促进了文化间的交往交流交融,更是文化间互补互证互助的表现,对于文化的认同、文明的共享以及民族团结、社会和谐更起到了积极作用,具有现实价值。但在以往跨文化文本研究中,备受关注的是一些由自然地理、文化地理版图中衍生出的身份认同、宗教文化、生态意识以及作家作品细读等话题,从“第三空间”角度探讨未曾深入,对这一文化研究对象,缺乏“当下性”和一些文化焦点问题的观照,未见系统研究,更少有历史脉络的梳理。有鉴于这样一种文学语境、时代使命和拾遗补缺的研究需要,本文将聚光灯直射少数民族文学领域“第三空间”中具有双重视界的跨文化写作者们,根据已有资料、阅读经验和研究范式及策略,力图为丰富并深化对当代中国多民族文学创作的认识、形成与这个文学群体写作的对话、启发这个群体对多民族文学关系的话语表达略尽绵力。当然在这个研究主题的语域之内,笔者更热忱地期望,广大专家学者和文学爱好者对此进行思考评议与观点交锋,激活更富有参与感的分析目标与研究方法,拓展、掘进和改善多民族文学关系的文化话语环境。
二、跨文化写作者的双重视界与方向
20世纪末,乌热尔图先生和姚先勇先生围绕“声音的盗用”和“未必纯粹的自我阐释权”展开的文学争鸣而衍生出的关于“少数民族文学主体”的讨论研究①,留给我们广阔而深邃的理论思索空间。有人就对少数民族文学领域“第三空间”中的跨文化写作者们(包括一直居住在少数民族当地的“本土作家”、由内地迁徙至本地居住的“移民作家”、长期留住本地后来移居内地/国外的“流寓作家”、过客式的在本地做过短期或者多次访问的“客居作家”等)产生质疑,他们是否能够充当民族文化阐释权的有力发声者?是否具有双重视界?如美国的后殖民理论批评家斯皮瓦克所言:“文化身份的模糊是全球化时代的产物,而且实际上,所有的身份认同都不可还原地呈混杂状态,这是作为陈述的表演性再现所不可避免地建构而成的。”[2]霍尔在《文化身份与族裔散居》中也提到,应该把身份视为一种“生产”,它永不完结,永远处于过程之中,而且总是在内部而非在外部构成再现;文化身份是有源头、有历史的,但是,与一切历史的事物一样,它们也经历了不断的变化,它们绝不是永恒地固定在某一本质化的过去,而是屈从于历史、文化和权力的不断“嬉戏”[3]。这些都一针见血地指出了文化身份有存在(固有)和变化(建构)的双重性,它的意义就在不断的缝补、分割中产生。跨地域、跨族群、跨文化的写作者们在与异质文化相遇时,必然会对文化身份进行重新审视。当他们走进异乡的那一刻,就意味着他们原先那种稳定的文化身份会吸收“他者”的文化因子,他们穿行于两种文化甚至是多种文化之间,去观察、探索、交流、思考、认同异族异质文化时便拥有了双重的文化视野。笔者关注到,在民族文化“自我阐释权”的主体问题上作为萨摩亚人眼中异族的弗里曼有关《萨摩亚人的青春》的阐释②给了我们一个完美的回应。作为一个异乡人,他在对萨摩亚文化的深入调查研究中,以谦虚学习、平等交流、情感沟通的方式获得了萨摩亚人的认可与赞许,完美诠释了萨摩亚人的“地方性知识”。虽然透过吉尔兹的悖论可看出,认识和把握异民族的文化,其实是一种理想或者目标,也可以理解为是一个人类学乌托邦,但弗里曼的成功也说明了异文化间存在着沟通理解认同的可能性。民族文化“自我阐释权”的主体不仅仅由本族人构造,也应该取决于是否是这种文化的“此在者”,那么,也就不存在所谓的绝对、纯粹、天然的民族文化之声了。如果惧怕“异乡人”的介入会潜移默化改写本民族文化的纯粹,那么“异乡人”永远只不过是对异质文化理解认同失败的代名词。
由此可见,只要中国跨文化写作者们能够用虔诚平等、虚心学习的态度去体验理解文化间差异,并不断反思和突破自身的创造空间,基本反映和做到“从生命体验和文明变迁的角度追问困扰人类生命心性的共同问题,在人类文化现状和未来发展的坐标轴上反思中国文化的地位和人类文化走向”[4],那么,他们自然会真正开启由双重身份带来的双重视界,从而充当民族文化阐释权的有力代言人。只不过需要注意的是,这些群体,大多处于边缘中的边缘,一方面,聚居地为少数民族地区,时常陷落在主流中心文化的缝隙之中;另一方面,作为民族聚居地的汉族作家,是深处的人群,是被遮蔽在少数民族文学族属“金词”下的“哑存在”。当不可避免的全球化和现代性焦虑给中国当代文学世界抹上一层异样色彩时,跨文化写作者们恰恰在这种边缘化、边疆化古老的个性、缓慢流淌的时光中找到了镇静和喘息的机会。可以说,全球化给中国文学的多元化提供了一种崭新的视角,跨文化写作既不皈依于主流文化,又打开了少数民族文学的视界,这种介于二者之间的文学形态打破了二元对立的阐释模式;同时也使在时代喧嚣、暧昧语境与消费漩涡中生态环境恶化、生命意识弱化等现象,在少数民族聚居的边疆地区重拾原始本真的文化因子,使“单向度的人”在边疆地区找到失落的文明。如同杨义先生“边缘的活力”理论所说,存在于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边缘文化,往往以一种原始活力和新鲜思维,对在缜密思维建构中趋于模式化甚至僵化的中原正统文化发起新的挑战,注入一种为教条模式难以约束的强大力量,使整个文明在新的历史台阶上实现新的重组和融合[5]。因此,像王蒙的新疆故事,马原的西藏故事,郑万隆、迟子建的东北故事……这些所谓的边缘性写作,不能简单地以中心/边缘二元对立的空间位置来标识,它们是一种游走穿梭于中心和中心相交夹缝地带的批评者的独有话语资源。这种文学写作形态也不是以一种讨巧的、迎合“主流文化”审美和心理趣味的方式出现,它们所展现出的特点是文化的诗性色彩更浓郁,传统观念的沉积相对稀薄,人文精神有更多的感性与经验的特点,文化结构的整一性更弱,民间文化的内容更为丰厚,浪漫主义、自然主义倾向更强旺[6],是一种稳定的、“有方向的写作”。
“有方向的写作”的方向,就在于无论是本土型的还是外来型的跨文化写作者,都通过艺术表达和文本构筑来呈现本土文化资源的优势,同时,在强烈的本土意识中,追寻远方,探索对自我的超越。例如20世纪80年代出现的居住在少数民族聚居地的为西部山水立言,并使“西部文学”的建构成为一种现实的可能的“新边塞”诗人(汉族诗人),他们的“新”,在于他们的边塞不同于古代诗人笔下的边塞。古代诗人笔下的边塞,是一种自然严峻险恶与命运严峻险恶相重叠的边塞,人与边塞的关系是一种被动的接受,是一种失去选择权利的命运的驱使;新边塞诗人的边塞,是一种掌握了主动权的边塞,隐约看到的伸展于历史时空的触角,不过是要追取一种情感上的遥远血缘,并不妨碍他们对当下蓝图的新的把握和挑战。他们的写作,不仅反映了时代和改革春风下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在这片土地上的传播、推进、渗透,还通过捕捉和发掘反映了在这个过程中现代文明与民族传统文化的矛盾、碰撞和转化,更特别观照在变革时代西部人的情绪、思考以及精神,是西部与时代的契合,是文学的雄健阳刚之气和振兴的民族心理的契合。因此,无论是以支边文化青年身份来到新疆的章德益,迫于生计开始西部流浪生活的杨牧,还是随“老八路”的父母来新疆的周涛,“他们写山、写鹰、写马,是为了寄托一种时代的精神;他们写大漠、写草原、写绿洲,是为了传达一种开拓者的气魄;他们写夕阳、写暮色、写黎明,是为了表现一种除旧布新的社会心绪;他们写维吾尔人、哈萨克人、蒙古人、锡伯人,是为了揭示一种天风般的历史意志与人生向往”[7],在不断前行的过程中,他们的性别、容貌、种族、特征变得模糊不清,甚至消失不见了,这种交融慢慢地变成了一条没有边际的长河,体温和血液在交融中不断被融合和改变,唯一不变的是前进的方向,那就是:对生命的礼赞,对远方和诗的追寻!
三、跨文化写作者的目标:超越的“第二现实”书写
由双重视界的文化视野衍生出的有方向的写作无法模仿和重复,跨文化写作者只有通过体验习得,获得别样的惊喜与愉悦,产生新鲜的思想理念和文化感受,才能使母体文化摆脱遮蔽获得彰显,从而进行理想的拯救和新质的补充。无论是红柯笔下的“乌尔禾”、张承志的“乌珠穆沁草原”,还是迟子建的“额尔古纳河右岸”、马丽华的“如意高地”、聂华苓的“桑青与桃红”,均是这种跨文化写作的启示。萨义德在《东方学》等一系列著作中主张文化非“纯洁”,认为内部千差万别的混成的、杂交性文化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这要求我们对文化秉持强烈的实践性和宽容精神,打破所谓纯粹本质的静态连续以及所谓的疆界、民族、类型的局限。迈克·克朗在《文化地理学》中对于家的描写、领土的建立及空间的描写确定了“自我”的定义是与“他者”文化的特征相关联的,是通过他者的参照、对他者文化的解释和理解而获得的。从萨义德和迈克·克朗文化观的异曲同工之处不难看到,只有在“他者自我化”和“自我他者化”之中,写作者才能直抵“第二现实”。“第二现实”是作家物理的身的容器与精神的心的皈依的完美融合,是一种梦想,也是一种情怀,精准地说只有具备包容和欣赏人与文化的差异性的情怀,才能在这种复合的文化结构中提炼出“美美与共”的多民族文学交融境界,才能发现一种文化变迁的路径,同时建构认同和民族认同,使民族文学理论建设成为可能。“第二现实”是跨文化写作者文学表意实践的最终目标。
但需要指出的是,“第二现实”与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所谓的“想象的共同体”是背道而驰的,它不是长期积淀的“传统遗产”和“地方性意识”的封闭狭隘的民族文化自治,而是用比经济、行政、法律更柔性、更灵动、更包容的文学与文化的手段,去消除隔阂与偏见,去克服“地域”屏障,探求不同民族文化间的同一性。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在多民族聚居地,这种柔性的手段,对于反映历史、构建文明、丰富作者更能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以至今以来表现维吾尔族地域文化最成功的汉语作家王蒙为例。王蒙从1953年开始写作,他的文学生涯可谓是一部沧桑的交响曲。王蒙在新疆生活16年,其中在伊犁巴彦岱公社生活近7年,是一个特殊政治时期被主流边缘化的个体,但他通过对他者、他性的模仿,在异域远方获得了新的教诲与医治,将失去前途、希望与脱离人生轨道的主体命运嵌入另一个全新陌生的自我建构之中。论王蒙在艺术上的贡献,无法回避他在新疆16年的生活体验中结出的一系列精神硕果,新疆经验成为王蒙自我放逐之后新的创作素材和新的人生智慧、情感观念、价值取向的坚实的艺术支撑点。而对于新疆当代文学来说,在表现边地民族地区真切的生活,特别是维吾尔族地域文化方面缺少了王蒙的新疆书写,也是不完整的。王蒙的一系列小说,是一幅幅色彩浓郁的风景、风情、风俗画卷,既宏观描写了边疆村镇、雪山、草原的地理、物候等自然景观,也细致刻画了城乡街景和居民庭院布局甚至室内摆设等人文景观,而使新疆—伊犁—巴彦岱这几个概念大放异彩的,是他对于深层、动态的新疆少数民族生活习俗的文化记忆,像默罕默德·阿麦得招待“我”做喀什噶尔拉面的饮食方法、房东大娘的“彻日饮”茶、姆敏老爹室外酿原汁葡萄酒的工序以及去往和静探亲举行的盛大上路“乃孜尔”、维吾尔人的种种观念等等民族文化心理的开掘和民族灵魂的悉心体察与触摸。因此,对异域民族文化的理解和跨文化的书写,不仅体现了治愈的力量,使王蒙的生命与精神追求在异域异族文化滋养下更加充盈,更为重要的是,这种文化赋予王蒙在地域文化的巨大变迁之后,拥有了一种多维、立体、复合式的视角与思维方式,在多种文化的碰撞与融突之后,能够找到最佳的自我审美观照立场,并游刃有余于现实生活空间,真实贴切地展现新疆兄弟民族特有的民族个性和现实生活,这种接地气的书写成功地为边疆少数民族和汉族文化交往交融搭建起一座桥梁。
当然,“第二现实”是有待超越的现实主义书写,无论是王蒙的系列伊犁小说、董力勃的屯垦小说、赵光鸣的底层人民和流浪汉生活作品、党益民的藏族聚居区生活、迟子建的鄂伦春族群的历史变迁和文化意义、姜戎的草原牧人的文化和“图腾”;无论是藏地高原、遥远的河与岸、新疆大野,这种现实主义书写只有超越以往的道德关切、性别关切、族别关切以及地域关切,才能有更大的突破和创新。要想做到这一点,文学就应该更加谦卑和包容,正如艾略特所言“谦卑是无穷无尽的”,一个成功写作者的“个人传统”必然是一种可以融合、可以互补的传统,要完成“本己”向“他者”目光的转换,还要向人类学习,向除文学之外的广大世界学习。
四、跨文化写作者文学表意实践的意义生成
从跨文化写作者的生存空间和书写的现实语境不难发现,这些作家或者借由记游与想象、还原与重新给予的书写策略呈现边地之空间地理的冲击,或者借由恋乡与怀旧的书写策略对抗时间的变迁,或者借由对主流时间的脱序完成对一种相对静止、相对不变的家园价值的坚守,或者借由异族身份通过主体自觉的文学表意实践来重新观照民族文化的新格局。总体来说,跨文化写作主要有以下三点意义。
(一)凸显了文学人类学的素质与情怀
文学不管生活性质和外部条件发生多么大的变化,都以揭示人类的生存境况为己任,最终使命是“为人类写作”。在汉族作家的跨文化写作中,我们看到了诸多的人类学品质:十分注重对民间维度(少数民族传统和自然人文风情的描摹)和历史维度(将历史记忆、文学想象和族群文化相连接)的追求,注重实证性的田野调查,采用文学民族志的书写方式。此外,在马原的《冈底斯的诱惑》、王族的《图瓦之书》、红柯的《库兰》、范稳的《悲悯大地》等文学作品中,我们还看到了藏地探险、图瓦人的历史记忆和日常生活故事、蒙古族民间叙事诗等许多民间叙事资源和民族志材料,这种相互缠绕的、混杂的神话、传说、习俗和歌谣亦实亦虚,人类的生命智慧和生存经验弥漫于故事之中,不但表现出汉族作家对少数民族的文化观念、民族特质、现实历史等的构想和认知,更呈现出了历史与现实、诗性与理性、人类性与地方性交相辉映的民族文化景观。地方性知识是民间立场和地域文化的载体,阐释人类学家吉尔兹认为,世界是由多样性的地方组成的,每个地方都有其独特的生活方式、文化风习和价值观念,每种文化都有其存在的价值和意义,都是相对于普遍性而言的特殊性的地方性知识[8]。汉族作家的跨文化写作扩大了我们的观察视野,不同地域、不同族群、不同文化的世界在其作品中的纵横捭阖,让我们认识、了解和接受了人类生存方式的差异性、多样性,生命与智慧的美,以及普适性的文明。
(二)扩大了文学文本环境
跨文化写作展现了语言、历史、风俗、礼仪、民歌、谣谚、宗教等民间文化因素,扩大了文学文本环境,避免了仅仅以兜售地域特色来充当文学价值、用文学的鸵鸟政策来获得小国寡民式的自高自大和沾沾自喜的危机。跨文化写作者正是在异域民间文化的沐浴之下,开始对所处环境有了深刻认识,民间文化也在他们的生活与思想以及他们的作品中留下清晰投影,并作为敞亮的窗口见证了原生文化断裂与新质文化冲击下的一种新的和谐——一体化的文化身份认同的建构。汉族作家北野的诗歌,多以谣曲的外在形式承载可歌唱的功能,天然地融合了维吾尔十二木卡姆、藏地民歌、蒙古长调、哈萨克民歌、回族花儿等的节奏韵律和词语方式;汉族作家刘亮程,把巴扎之行、千佛洞和古城遗址,暮色中沉静的老街巷,祖传十三代还最后坚守着的铁匠,库车老城维吾尔族妇女至今仍保持的用植物汁液涂抹眉毛的民族传统等民风民俗尽收于散文集《驴车上的龟兹》和《库车行》之中;陕西籍作家红柯的《西去的骑手》,让我们读到了大量苍凉、悠扬、大胆的西部情歌。这些闪烁着民间智慧的民风民俗的描写,是作家感悟西部土地的博大和坚韧、生命力的崇高和顽强之后,带给读者的一个温暖世界。这种表达,是跨文化写作主体与民间传统文化资源二者相得益彰的情况下,浓缩出的一种哲学思想、一种韵律氛围、一种风格与结构方式、一种独特的语言表述意义系统,它们作为一种“召唤结构”隐藏在文本深处,使当代人的美好生命梦想在对抗无尽的精神焦虑时有了现实的着陆点。
(三)有助于写作主体文化身份固有和建构的不断弥合
从著名的文化批评理论家、阐释者、实践者萨义德(美籍巴勒斯坦人)的亲身经历熔铸在《知识分子论》《东方学》《文化与帝国主义》等一系列著作中的观点看出:“流散”最重要的效应之一就在于带着所形成的批判距离去获得一种重新审视事物的角度。“因为流散者具备过去与现在、此地与他方的觉悟与双重视角去超越固守教条主义家园意识的拘囿……就知识上而言,这意味着一种观念或经验总是对照着另一种观念或经验,因而使得二者有时以新颖、不可预测的方式出现:从这种并置中,得到更好甚至更普遍的有关如何思考的看法。”[9]12-13一个人空间地域的转换也是其自身生命之旅的主体迁徙。起初,跨文化写作者热衷于异域自然风景、少数民族风俗和风情的描摹,沉醉于浪漫的传奇和寓言的叙唱之中,依赖于这种文学的风土来进行文学的讲述和完成作为异乡人的身份确认。后来,他们逐渐认识到异乡人的身份确认是需要“破”(破除用汉族思维认识、理解少数民族文化或异地文化)与“立”(汉族文化与少数民族文化深层次的文化认同)的,只有从表象直抵文化内核,才能完成自我与他者的真正对话,拥有历史和心灵的同时在场。如出生于浙江湖州一个盛产丝绸和水稻的村庄的沈苇,在大学毕业后只身来到新疆,江南水乡和西部新疆带给他灵动的诗魂与雄浑的境界、细腻的情愫与粗砺的意象、富有弹性的语言与深邃的思考,这些构成了沈苇诗歌的独特景观,使他成为一个“金色的综合”。“我看见自己的一半在雨水中行走,另一半在沙漠里跋涉。”[10]205“从一个地方迁到另一个地方,时常感到一个不是自己的自己,走在一条不是路的路上。”[10]240诗人身上无数个“我”,正以遥远的方式亲近隐秘的“我”,这种隐秘的渴望,是跨文化写作者惶惑不安与情感需要的集积,惶惑不安于本土文化经验的缺失,情感需要于迫切自觉的身份认同感。但也正是由于跨文化写作者的身份割裂、重叠、流动飘零的特质,使得这个写作群体始终与地域保持疏离,从而具备了过去与现在、他乡与此地的观看事物的另类角度和始终的审美距离,再现了文学创作中“在路上”的美学主题。
注释:
①乌热尔图在《声音的替代》和《不可剥夺的自我阐释权》中,举例叙述了殖民者和他族文化主体误读和改写某一族群文学的文化现状,引起民族文化纷争,从而引发出强权文化和外族人是否有权阐释弱势文化和少数族群文化问题的思考,继而提出“某一民族或种族的故事应由本族人去说去写”的主张;姚先勇针对乌热尔图的论点,在《未必纯粹自我的自我阐释权》一文中,从民族文化生成历史、民族意识生成、强势文化的非自足性等角度,质疑了“不可剥夺的自我阐释权”,提出了不存在“绝对、纯粹、天然的民族文化之声”之论点。
②来自澳大利亚的人类学者德里克·弗里曼对美国文化人类学者玛格丽特·米德的萨摩亚研究方法论、具体研究条件和方法提出了质疑,他以谦虚虔诚的态度深入到萨摩亚人的生活当中去,在平等交流、沟通情感的过程中认同了萨摩亚人的文化,他的《萨摩亚人的青春》文化书写也得到了萨摩亚人的认可。
[1]迈克·克朗.文化地理学[M].杨淑华,等,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5:167.
[2]转引自王宁.文化身份与中国文学批评话语的建构[J].甘肃社会科学,2002(2):28-32.
[3]斯图亚特·霍尔.文化身份与族裔散居[M]//罗钢,刘象愚.文化研究读本.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212.
[4]陈晓华.生命之抒写与学者之公心——读王岳川《发现东方》[J].中国图书评论,2004(3):14-16.
[5]杨义.重绘中国文学地图[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99.
[6]韩子勇.西部:偏远省份的文学写作[M].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98:86.
[7]周政保.新边塞诗的审美特色与当代性——杨牧、周涛、章德益诗歌创作评断[J].文学评论,1985(5):52-58.
[8]张雪艳,李春燕.从“发现”到认同——当代汉族作家跨族文学的人类学考察[J].兰州交通大学学报,2014(10):32-34.
[9]爱德华·W·萨义德.格格不入——萨义德回忆录[M].彭坏栋,译.北京:三联书店,2007.
[10]沈苇.沈苇诗选[M].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14.
(责任编辑:田皓)
The Hidden"Third Space":Literary Expression Practice of Cross-cultural Writers
YAN Weiwei1,2
(1.Teaching and Research Department of Culture,Party School of Xinjiang Uyghur Autonomous Region,CPC,Urumuqi 830000,China; 2.College of Humanities,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Shanghai 200241,China)
"The third space"is a cross-cultural literary expression practice space hidden in the multi-ethnic literary relations.The Han nationality status of cross-cultural writers of was heavily hidden in the field of ethnic minority literature.But these writers are also powerful speakers for ethnic minority culture interpretation because of their double visions and"directional writing".Cross-cultural writers'works enter the"second reality"of communication among different ethnic nationalities,literature integration,and cultural identity since the writers are observing in different angles and always keep the aesthetic distance.The literary expression practice of cross-cultural writers can highlight the qualities and feelings of literary anthropology,expand the literature text environment,and contribute to consolidate and construct the cultural identities of writers.
"The third space";cross-cultural writing;"second reality";literary expression practice
I206.7
A
1674-9014(2017)02-0092-06
2016-10-15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社会科学规划项目“新疆当代多民族汉语文学实践研究”(14CZW083)。
闫炜炜,女,新疆乌鲁木齐人,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校文化学教研部讲师,华东师范大学人文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文学人类学、文化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