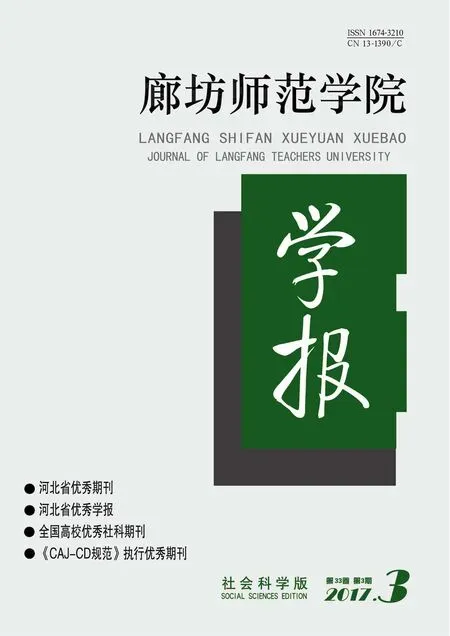I·A·瑞恰兹与后理论时代中国文论的反思性重建
孔帅
I·A·瑞恰兹与后理论时代中国文论的反思性重建
孔帅
(曲阜师范大学传媒学院,山东日照 276826)
作为英美新批评派的重要奠基人,瑞恰兹的“文本细读”“语境理论”“科学化建构”等理论观念仍对今天“后理论”时代中国文学理论反思与重建有启发或警示意义。其“文本细读”理论启示我们,面对新一轮“内部研究”转向,要树立一种整体性、综合性文本观;《孟子论心》的语境分析实践表明,中西文论交流离不开具体的语境解读,须深入挖掘与理解西方文论的文化背景和具体内涵;其科学化文论建构则警示我们,应恢复科学的本真概念和广义内涵,文学理论可以科学化,但绝不能是文学理论的自然科学化。
艾·阿·瑞恰兹;后理论;文本细读;语境;科学化
艾·阿·瑞恰兹(I.A.Richards)是 20世纪英国著名的语言学家、文艺理论家和批评家,和艾略特同为新批评派的重要奠基人,他将语言学植入文学研究,开创了语义学批评,“文本细读”“语境理论”“复义现象”“张力诗学”等理论对英美新批评派影响极为深远。同时他试图建构科学化文学批评理论,为此引入心理学方法,提出了独特的文学价值和交流理论。此外,他也是一位中西文化交流使者,一生多次来中国访问,曾在清华大学讲学,叶公超、朱自清、钱钟书、朱光潜、袁可嘉等当时中国一大批现代学者都受过他批评理论的影响,对中国现代文论的建构有重要的推动作用。然而,这位对中西文论都有着重要影响的理论家并没有引起我们的足够重视,正如有国内学者所评价的:“20世纪的英美文学批评家中,I·A·理查兹(即瑞恰兹,引者注,下同)或许是最受到忽视的了,尽管他被认为是现代英美文学批评的奠基者之一”①。国内除了《意义之意义》《文学批评理论》《科学与诗》,他的其他几部重要批评理论专著至今没有中译本。即使在西方,直到2001年英国才出版了一套10卷本的《I·A·瑞恰兹选集》。故而,本文旨在当前“后理论”学科最新发展范式背景下,对瑞恰兹的语义学和心理学批评理论进行再回顾与评价,以就教于学界,希冀能给今天中国当代文学理论的反思和重建带来某些启示。
一、后理论转向下的“文本细读”
新千禧年以来,随着学界对“文学终结”“理论死亡”“文论危机”等问题的持续关注,“后理论”进入了人们的视野并引发国内外学者的广泛关注。后理论首先面对的是文学研究对象的泛化问题,在20世纪60年代至80年代的“理论时期”,由于以跨学科甚至反学科为症候的“大理论”对文学的僭越,此时的文学理论变成了没有“文学”的理论研究,文学作为文学理论研究对象的合法性受到广泛质疑。昔日解构批评主将哈罗德·布鲁姆就不无痛心地说:“今日所谓的‘英语系’将会更名为‘文化研究系’,在这里,《蝙蝠侠》漫画、摩门教主题公园、电视、电影以及摇滚乐将会取代乔叟、莎士比亚、弥尔顿、华兹华斯以及华莱士·斯蒂文斯。”②因此,后理论主要针对后现代主义,特别是文化研究的“非文学化”现象进行反拨,回归文学文本和文学性成为后理论时代最鲜明的时代特征。英国学者拉曼·塞尔登描述了新世纪瓦伦丁·卡宁汉、乔纳森·贝特、乔纳森·卡勒等西方学者纷纷重返文学的各种主张①。国内学者近年来也开始重视文学文本和细读方法,呼吁建构“文学文本解读学”和文学文本的“本体阐释”等理论观念。中外学界纷纷主张重返文本细读和文学性的传统,无疑让文学理论大致呈现出“内部研究—外部研究—内部研究”的回摆式演进发展路径。对此我们不禁要问:新世纪出现的这种新的“内部研究”究竟是一种怎样的研究范式?是回到以作品为中心的形式主义文论传统,还是呈现出新的时代特征?要解答以上问题我们有必要对“文本细读”这一概念做重点考察。
众所周知,文本细读是瑞恰兹首次提出的理论概念和文本解读方法。针对20世纪初英国传统印象批评和唯美主义批评的主观主义和相对主义倾向,他一直想重建英国文学批评的价值标准。因此,他在《文学批评原理》一书中提出了心理学评价标准,认为文学的价值就是能对读者的心理施加影响,使读者混乱的心理经验得到平衡和协调。他受浪漫主义诗人柯勒律治的启发,认为作家的心理世界充满艺术想象,而想象是一种“综合的”“魔术般”的力量,作家的心理经验能使对立的、不协调的读者经验得以平衡。瑞恰兹进一步指出,如果想要把文学的潜在价值转化为现实,读者必须对文本做准确而客观的分析和阐释,否则无法还原作家的心理经验。然而,承载作家精神世界的文学文本远比散文或科学文本复杂,其蕴含着作家丰富而微妙的情感(包括意思、情感、语调、用意等四种意义),读者要准确把握文本的意义就必须对这四种意义进行全面考察。基于此,他创造性地提出了“文本细读”这一具体的文本解读方法,认为“唯有细读才能告诉我们足够有价值的判断标准”②。所谓“细读”就是排除与文本无关的一切干扰因素,对文本进行封闭式的细致阅读和反复阅读。他在《实用批评》中列举了无关联系、先存反应、滥用感情、压抑感情、技术性先入之见、理论性先入之见、教义附着等十处读者常犯的阅读错误,旨在防止读者对文本的意义进行过度阐释,从而帮助读者客观分析和解读文学语言的四种意义,以挖掘文本的所有意蕴并准确捕捉作家的心理经验。后来新批评派继承了他文本细读的批评方法,如燕卜荪的“朦胧”说、退特的“张力”说、布鲁克斯的“反讽”和“悖论”说等都是建立在文本细读基础上的。然而,新批评派对瑞恰兹的文本细读方法进行了大刀阔斧的形式主义极端改造,认为文本特指文学作品一端,“文本之外无他物”,一致主张“意图谬见”“感受谬见”,这时的文本概念就彻底地排除了与作家、读者等有关的一切外在因素。
通过对瑞恰兹文本细读理论渊源和内涵的回顾,从中可以发现,由于新批评对瑞恰兹“文本细读”的主观改造及其巨大的理论影响,我们往往会对瑞恰兹的文本细读概念产生误读,认为新批评和瑞恰兹的文本细读理论内涵并无二致。其实瑞恰兹并不像新批评派一样彻底割断了文本与作家、读者之间的联系,他本人始终以文学价值重建为旨趣,“文本细读”则是构建其文学价值标准的中介或关键环节,他在强调文本阐释的同时也充分肯定了作家、读者在文学活动中的重要作用和功能。在瑞恰兹批评理论体系中,“文本”绝不等同于作品的狭义内涵,而是集作品、作者、读者等文学维度在内的综合性、整体性概念。文本既包含好的有价值的作家心理经验,也期待读者对蕴含其中的作家经验进行解读和接受,这显然与俄国形式主义、新批评、结构主义等形式主义文论以作品为绝对中心的文本观有本质区别。虽然以新批评派为代表的形式主义文论始终围绕作品展开一系列深入分析和探究,从而保证了对象的明晰性,但这种以作品为中心的语言学研究路径已被历史证明是片面的文本观。既然文学艺术是一种人类精神文化活动,那么作者、作品、读者和世界四个维度就都是文学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对文学文本做任何一维的考察都应属于文学文本阐释和解读的范畴,这正是瑞恰兹“文本细读”理论对后理论时代新一轮“内部研究”转向的启示。在后理论时代,我们不是重回前理论形式主义文本细读传统,而是在经过后现代“大理论”的洗礼后重新树立一种整体性、综合性的文本观。当前我国学者所倡导的文学文本解读和阐释理论也正体现了这种整体性文本观倾向:孙绍振先生所倡导的“文学文本解读学”中的文本概念是由表层的意象、中层的意脉和深层的规范形式构成的立体结构;张江先生的“本体阐释”也包含核心阐释、本源阐释、效应阐释三个层次或三重话语①参见孙绍振:《文论危机与文学文本的有效解读》,《中国社会科学》2012年第5期;毛莉:《当代文论重建路径:由“强制阐释”到“本体阐释”——访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张江教授》,《中国社会科学报》2014年6月16日。。
此外,与“文本细读”密切相关的是作者意图和客观阐释问题,文本中到底有没有作者意图,读者能否对文本进行客观准确地阐释,这些问题其实在20世纪40年代以后特别是阐释学和接受理论就给出了否定的答案。然而,在整体性文本观语境下,我们需要对“意图谬见”和读者的碎片化解读做进一步审视和考察,因为根据瑞恰兹的文本细读理论,作家“意图在场与否”会直接关系到文学价值功能的实现和读者对文学文本的阐释。其中,文学的价值和功能是文学得以存在和发展的根本理由,文学阐释则是文学价值现实转化的基础。因此,在后理论重返文学文本的时代背景下,文本意图和阐释限度问题将是我们必须要面临和回答的重大理论问题,我们期冀学界对此有深入的讨论。
二、后理论时代西方文论的“语境解读”
除了回归文学,后理论的另一显著特征是多元性和差异性。与后现代主义的反本质、反宏大叙事的大理论不同,后理论已经不再以本质主义、基础主义、普遍主义建构为圭臬,曾经大写的理论变成了一个个小写的“理论化实践”。“单数的、大写的‘理论’迅速地发展成了小写的、众多的‘理论’——这些理论常常相互搭接,相互生发,但也大量地相互竞争。”②拉曼·塞尔登等:《当代文学理论导读》,第9页。这说明“大理论”经过“学科帝国主义”的极端发展后,在20世纪末逐渐丧失了理论的反思特性,而注定被“后理论”这一新的理论形态所取代。正如有学者所说:“‘后理论’表达了新的理论范式的生成,即在批判‘大理论’之专断、盲目、虚妄、牺牲经验、脱离实践等负面因素的同时,转而以反本质主义、分离主义、实用主义、非中心化、多元化、差异性、碎片化与部落化的知识立场来重构理论的合法性效度。”③李艳丰:《“后理论”时代的“文学性”话语反思——兼论元叙事的弥散与本质主义诗学的理论困境》,《文艺理论研究》2016年第1期。今天人们开始以一种更加开放的态度对待文学,众多小写的理论往往可以从不同的立场出发,对文学世界进行更有启发性的解读。按照塞尔登的描述,新世纪以来,西方版本目录学、发生学、新审美主义、政治批评等纷纷登场就是后理论时代多元化的表现。
乔纳森·卡勒则告诫我们,在后理论时代,多元化、差异化不仅表现在理论内部的多重解读上,在当今全球化语境下,也应体现在对不同民族传统和文化的尊重与互渗上。他说:“我们现在正处在一个相互依存的世界里,我们需要去思考西方理论和其他地方的文学理论和文化理论之间的关系。文学理论被西方看作是西方的东西,尽管其他文化也都在西方文化之前就有了关于文学的发展充分的叙述;未来的一大挑战就是搞清楚西方理论和其他关于文学的叙事之间的关系。”④乔纳森·卡勒:《当今的文学理论》,《外国文学评论》2012年第4期。这表明后理论时代文学理论的发展不仅要靠自身的理论自省,也要借鉴其他民族的优秀理论成果。“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只有在与他者的对话交流中才能发现自身的问题,进而更好地提高发展自己。在某种意义上,我国现当代文论的建构史就是西方文论的接受史,特别是新时期以来,西方文论如潮水般涌入我国。不可否认的是,西方文论拓展了我们的理论视野和多样性的研究路径,但它带给我们的更多是应接不暇的理论流派和时髦概念,并没有实质地推进中国文论的现代性进程,最后导致“影响的焦虑”。今后我们如何与西方文论进行沟通与交流,怎样将西方文论话语切实转化为我们自己的理论建构?对此,我们应认真思考并做出回答。瑞恰兹在20世纪同样面临着中西文化的碰撞和交流,他的探索可能会对我们处理中西文论的关系提供某些借鉴。
20世纪二三十年代,瑞恰兹曾到中国清华大学做过短暂的客座教授。其间,他发现中国学生的语言和思维习惯与西方存在巨大差异,因此想通过考察中国人特殊的语言和心理活动,让西方更好地了解中国文化。为此,他以中国传统文化典籍《孟子》为研究对象,写了《孟子论心》一书,重点研究《孟子》中语言的复义现象。他发现《孟子》中的多义现象极为普遍,譬如“彼长而我长之,非有长于我也”中的“长”字,就很难被西方准确翻译和理解。因为该字在《孟子》中有“年长”“尊敬”“智慧”“服从”等多种含义,“仅用‘尊敬’一词根本无法准确表达其含义,其复杂的意义范围使这一词语具有了某种准神秘的强迫力量,一种劝说性的约束力和权威力量”①I.A.Richards,Mencius on the Mind(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2001,p.37.。《孟子》中语言的多义性让瑞恰兹发现了汉字与西方表音文字的区别,《孟子》更像是“诗的语言”,西方话语则是典型的散文或科学语言,西方如果按照散文或科学的逻辑去读《孟子》肯定不得要领。那么西方人该如何正确地去读《孟子》呢?瑞恰兹认为,与习惯于把词语当作一个固定和独立单元的西方语言系统不同,汉语的意义取决于文中其他短语与文章的整体环境,因此西方人须弃用“非此即彼”式思维,释义时要结合汉语的具体语境才能确定某个汉字的意义。例如“为”字,同一个汉字在不同的语境下可能会产生不同的意义:在“故者以利为本”一句中,表“当作、作为”义;在“性可以为善,可以为不善”一句中,表示动词“是”;在“所恶于智者,为其凿也”一句中,则为“因为”义。瑞恰兹就运用这种语境解读方法分析了《孟子》中几乎所有的核心词汇,认为正确理解它们的文化内涵和意义是西方人理解《孟子》的关键。
我们发现,瑞恰兹为了破除中西文化交流的障碍,运用了自己一贯坚持的文本细读和语境释义的方法,通过具体的语境分析实践为西方了解中国文化提供了方法论指导。反观我们新时期以来在介绍和引入西方文论的同时,就缺少这种严谨而具体的语境分析。要么直接照搬西方文论的具体概念和理论观点来阐释中国文化中的文学经验和创作实践,要么对西方文艺理论只做一鳞半爪的理解,并没有对其进行全面而深入的语境解读和文化释义,结果自然会导致“以西释中”甚至“以西代中”的危险,造成理论的“水土不服”。这无疑是当代中国文论建构中“强制阐释”的典型表征,“中国学派”文论体系的建构也就无从谈起。瑞恰兹在《孟子论心》中的语境释义实践带给我们的启示是,我们对待西方文论不能一味地“跟着说”“照着说”,简单套用西方的时髦概念来阐释中国语境下的文学实践活动,这样除了可以一时“博人眼球”,造成理论的“虚假繁荣”,文学研究并不会有实质进展。在文化多元发展的今天,我们应时刻保持清醒的自我意识和问题意识,本着与西方平等对话的姿态,深入挖掘和理解西方文论的文化背景和具体内涵,积极寻找中西文论相互交流和借鉴的契合点,避免盲目跟风或全盘否定,真正做到“去其糟粕、取其精华、为我所用”。
三、后理论时代文论的“科学建构”
如上所述,回归文学和多元化建构是后理论时代文学研究的最新发展动态,二者都是理论反思的必然结果,因此强烈的反思和忧患意识也是后理论的时代特征。后理论时代的文论建构绝非反对理论探索本身,而是基于对传统文学理论与文化理论整体反思基础上的理论再出发。后理论的兴起再次印证了反思是推动文学理论学科发展的根源所在,文学理论的演进发展就是理论不断反思和自我否定的结果。其实中国文论的学科整体反思始于20世纪90年代,当时学界对西方文论影响下的中国文论发展现状进行了全面总结和反思,明确提出中国文论话语存在“失语”现象。有学者就喊出要扭转这一流弊,须实现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化”和西方文论的“中国化”。然而,中国文论的发展史也是学科“科学化”的建构史,我们不妨从科学化建构维度来诊断中国文论的过去,为其未来发展探寻方向和路径。
据有关学者考证,“科学”一词源于古希腊哲学,在古希腊哲学传统里,哲学就是科学,二者都是人类的求真活动,科学与人文在早期密不可分①。一直到了文艺复兴时期,人类为了摆脱教会神学的控制和思想的蒙昧,现代意义上的科学概念才正式出现,这时科学与人文开始分裂,后经理性主义哲学的崛起和自然科学的快速发展,诞生了唯科学主义观念,科学和人文最终分道扬镳②金永兵:《文学理论本体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29-131页。。总之,科学理性的无限发展导致了近代以来科学对人文的压制,广义的科学概念从此变成了狭义的自然科学内涵,科学成为自然科学的专有名词。在唯科学主义浪潮的席卷下,声势浩大的科学主义文论纷至沓来:泰纳利用自然科学的方法论,提出文学发展的“三要素”说;自然主义文论的代表左拉则把生理学、医学的实验方法“移植”到文学领域,十分看重遗传因素对人类智力和情感的影响;进入20世纪,俄国形式主义、新批评、结构主义等科学主义文论也聚焦语言形式、语义、结构规律等本文内部研究,这些都带有自然科学的客观实证特征。难怪有学者对此概括为:“套用数学、物理的方法生硬地阐释文学,这是一些西方文论学派的基本特征。”③张江:《强制阐释的独断论特征》,《文艺研究》2016年第8期。
受20世纪科学主义文论思潮的影响,建构“科学化批评”也是瑞恰兹批评理论的终极目标。为此,他特意引入了当时心理科学的最新成果,建立了独特的心理学价值理论。瑞恰兹直接将心理学的自然科学方法照搬到文学研究领域,把科学界定为狭义的自然科学概念,这显然是一种唯科学主义思维方式。韦勒克就曾明确对瑞恰兹的这种科学主义做法提出批评:“大部分提倡以科学方法研究文学的,不是承认失败、宣布存疑待定来了结,就是以科学方法将来会有成功之日的幻想来慰藉自己。例如,理查兹就惯以精神病学的未来成就,向人保证所有文学问题的解决。”④勒内·韦勒克、奥斯汀·沃伦:《文学理论》,刘象愚等译,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4-5页。其实韦勒克本人并不反对文学研究的科学化,但他认为文学研究的科学化建构绝不等同于自然科学的范畴,作为人文社会科学知识,有其特殊性:“真正的文学研究关注的不是死板的事实,而是价值和质量”⑤雷内·韦勒克:《批评的概念》,张金言译,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1999年版,第276页。。因此在韦氏看来,文学理论与自然科学的最大区别就是文学的人文价值,文学理论研究的对象不是纯粹的客观知识,而是文学丰富的情感世界和意义世界。
韦勒克和瑞恰兹二人都看到了文学价值在文学研究中的重要地位,可惜后者的文学价值标准建立在自然科学的观念之上,以自然科学的科学化为鹄的来构建人文精神领域的科学知识,这样的科学化文论无疑将以失败而告终。然而,瑞恰兹的尝试与失败可以帮助我们反思我国文论的“科学化”建构问题。一方面,我们过去争相引进的西方话语和理论并没有使我们建立起自己的科学化文论,即没有建构起自己的现代文论话语,反而造成集体“失语”,这从另一个侧面恰恰揭橥了我们犯得正是和瑞恰兹一样的错误。我们的文学研究也时常受唯科学主义思维的影响,并没有真正把作为人文科学的文学理论与自然科学加以区分,西方文论话语和观念像引进西方先进技术一样被直接照搬和移植就是最好的证明。因此,当下我们应该对文学理论的科学化建构问题进行审慎考量和深入反思。我们认为,科学化文论建构不能以狭义科学(自然科学)的观念来框定文学研究,而应恢复科学的本真概念和广义内涵,在尊重怀疑性、逻辑性、规范性、系统性等一般科学属性的前提下,重点关注中国当下的文学创作实践和现实,全面考察和分析我们自己文学中的人文价值和时代精神,这才是文论科学建构应坚持的原则和发展方向。
另一方面,既然在广义科学概念下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并不存在根本分歧,二者都是人类为改造世界和自身发展所进行的认知性活动,那么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也理应具有融合统一的可能性。现实也的确如此,20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科学界最新发展成果,如哈肯的协同学、艾根的超循环理论、托姆的突变理论、曼德勃罗特的分形理论和洛伦兹等创立的混沌学都致力于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两种文化的对话和融合⑥冯毓云、刘文波:《科学视野中的文艺学》,商务印书馆,2013年版,第8-15页。。我国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也曾掀起了一场方法论研究热潮,以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为代表的自然科学方法就应用于文艺学研究,并取得了一定成绩。可见,既然自然科学可以学习人文科学的思维和研究方法,以文学理论为代表的人文科学当然也可以借用自然科学方法对文学进行多元化探究。特别是在当下新媒体环境中,以科学技术为核心的媒介与文学的关系日益密切,广告文学、网络文学、短信文学、博客文学、微信文学等新的文学形态和样式不断翻新,更需要我们从技术媒介视域分析和解读这些文学现象。但研究方法的融合和借鉴并不代表学科之间可以置换,人文科学毕竟具有自己的学科特色和特性。人文价值的倾向性很难被数字量化或实证说明,鲜明的历史性不能下本质主义和普遍主义的唯一结论,所蕴含的审美性也绝非能用纯客观、无我式的概念来描述。总之,文学理论可以科学化,但绝不能是文学理论的自然科学化,这就是瑞恰兹心理学批评理论带给我们的警示。
结 语
中国文论的现代性建构已历经百年发展,但“强制阐释”“没有文学的文学理论”“文论重建”等当下热议话题说明我们今天深陷学科焦虑。如何推动中国文论的未来发展,真正构建具有“中国学派”的中国当代文论是摆在我们面前的艰巨使命。历史早已告诉我们,文学理论作为历史性建构,其理论反思理应“以史为鉴”,在文论史的发展演变中审视自己向前推进。为此之故,就中国当代文论的建构而言,积极借鉴和批判学习中外优秀文论资源仍是我们今后的必然选择。作为20世纪英美新批评派的重要奠基人,瑞恰兹的主要文学理论著作虽然都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所写,距今已八九十年历史,然而其“文本细读”“语境解读”“科学化建构”等核心批评理论仍对我们今天“后理论”时代的文学理论学科建设有启发或警示意义。概言之,在今天“后理论”学科大反思的时代背景下,我们要想建构能反映“中国经验”、体现“中国立场”、展示“中国价值”的当代中国文论,必须要坚持“立足本土、批判借鉴、科学建构”的原则。首先,由于文学作品是理论生长的内在源泉,因此一定要关注中国当下的文学创作实践和文学现象,并对之进行整体性或综合性的“文本细读”式阐释和解读,唯有如此才能生发出具有“中国化”的理论概括和文论话语。其次,西方文论作为当代文论建构的重要外部参考资源,我们既不能全盘否定、固步自封,也不能简单照搬,落入削足适履式强制阐释的窠臼。只有通过跨文化的“语境解读”才能真正实现中西方的平等交流对话,从而做到博采众长,兼容并蓄。最后,文论建构一定要保持自己的学科特性,处理好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的矛盾统一关系,始终坚持“以我为主”和“合理借鉴”,以建构符合人文科学特质的科学化文论。
Abstract:As an important founder of England-American NewCriticism,Richards's criticism theories of“close reading”,“the context”,and“scientific construction”have inspiring and alarming meaning to the reflection and reconstruction of Chinese literary theory in the era of“After Theory”.The“close reading”reminds us toestablish a holistic and comprehensive text view,facinga new“internal research”turn;Mencius on the Mind about contextual analysis practice tells us that the communication between Chinese and western of literary theories cannot leave the specific contextual interpretation and specific connotation.We should discover the special cultural background and specific connotation.His scientific theory also extorts us to restore the original concept and generalized connotation of science,the literarytheorycan be scientific,but it cannot be the natural science ofliterarytheory
Key words:I.A.Richards;After Theory;close reading;context;scientific
I.A.Richards and Reflectional Reconstruction of Chinese Literary Theory in the Era of After Theory
KONGShuai
(School of Communication,Qufu Normal University,Rizhao Shandong 276826,China)
I0
A
1674-3210(2017)03-0013-06
2017-05-16
曲阜师范大学校青年基金资助项目(XSK 201516)。
孔帅(1981—),男,山东曲阜人,文学博士,曲阜师范大学传媒学院讲师,主要研究西方文艺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