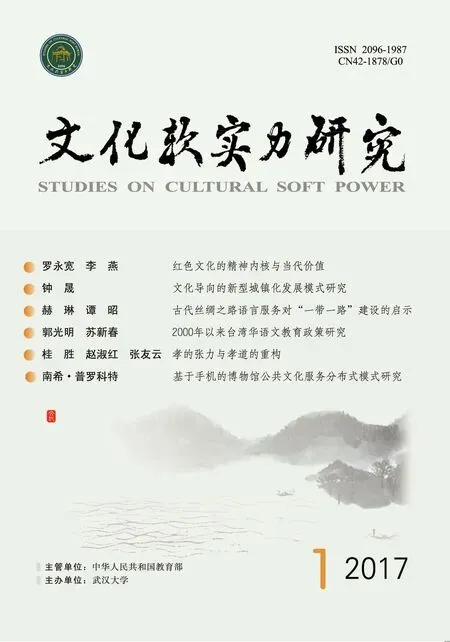古代丝绸之路语言服务对“一带一路”建设的启示
赫 琳 谭 昭
古代丝绸之路语言服务对“一带一路”建设的启示
赫 琳 谭 昭
古代陆上丝绸之路连接古代中国和亚欧地区,语言纷繁复杂。丝绸之路的开拓和发展,离不开语言服务。那时有关方面所开展的语言教育、佛经翻译、工具书编纂和通信交流等语言服务活动,不仅推动了不同语言文化的交流,而且促进了沿线地区的经贸和政治往来,为丝绸之路的形成和繁荣发挥了重要作用。当下随着“一带一路”愿景的提出,相关语言服务建设和中国文化软实力提升成为时代课题。本文以古鉴今,考察了古代陆上丝绸之路语言服务的主要做法,结合现实面临的问题和困难,就面向“一带一路”建设的语言服务问题,如外语培训、汉语传播、文化产品翻译、话语体系对接、工具书开发、智库建设和媒体宣传等提出了一些参考建议。
丝绸之路 语言服务 一带一路 文化软实力
西汉时期,张骞出使西域初探道路,数次“河西之战”打通了河西走廊,逐步形成了辉煌千年的“陆上丝绸之路”。这条横贯欧亚的交通线既是古代亚欧各国之间互通有无的商贸大通道,也承载着中外语言文化交流的使命,是相关国家语言文化碰撞交融的桥梁与要道。那时,在这条通道上,有关方面是怎样为商贸往来和各种交流提供语言服务的?探讨其做法和经验,对于当今“一带一路”的推进和中国文化软实力建设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本文拟透过一些蛛丝马迹,考察古代陆上丝绸之路的语言服务情况,结合当今面临的困难和问题,就“一带一路”建设中的汉语传播、人才建设、典籍翻译、话语构建和媒体宣传等提供一些参考和建议。
一、古丝路语言服务的主要做法
语言服务就是利用语言(包括文字)、语言知识、语言艺术、语言技术、语言标准、语言数据、语言产品等等语言的所有衍生品,来满足政府、社会及家庭、个人的需求*李宇明:《语言服务与语言消费》,《教育导刊(上半月)》2014年第7期,第93~94页。。据考察,古代陆上丝绸之路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语言服务活动较为突出,极大地促进了商贸往来和文化交流。
(一)语言教育
在张骞出使西域的“凿空”之行后,汉王朝与西域交往日渐频繁,但复杂的语言状况给交往沟通造成了极大困难。为了解决此问题,自汉代以来,有关方面就十分重视外族语教育和汉语传播。《汉书·西域传》记载:“元康二年……昆弥及太子、左右大将、都尉皆遣使,凡三百余人,入汉迎取少主。上乃以乌孙主解忧弟子相夫为公主,置官属侍御百余人,舍上林中,学乌孙言。”*《汉书·西域传》(下),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3905页。由此可知,早在汉宣帝时期政府就曾派人学习乌孙语。
《元史·选举志》记载,在各部门任职的译史、通事都须“识蒙古、回回文字,通译语”。另据《元史·兵志》记载,元政府每年勘查官马数目,也须造“蒙古、回回、汉字文册”*刘迎胜:《波斯语在东亚的黄金时代的开启及终结》,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1期,第70~79页。。为了培养波斯语翻译人才,元世祖忽必烈于至元二十六年(公元1289年)八月,始“置回回国子学”,即官办波斯语学校。回回国子学,按元代制度,属翰林院*参见《元史》卷八一《选举志》“学校”条;《元史》卷八七《百官志》“翰林兼国史院”条。。延佑元年(公元1314年)四月,元仁宗下旨依旧制重设回回国子监官,以“笃意领教”。在这所学校中不仅教授波斯语,还教授一种叫“亦思替非”的文字。
明永乐五年(公元1407年),一所学习、研究亚洲诸民族语言文化的学校和研究所“四夷馆”设立,它包括八馆:鞑靼馆、女直馆、回回馆、西番馆、西天馆、百夷馆、高昌馆、缅甸馆。它是我国最早结构完备的、带有语言教学功能的“亚洲研究院”*刘迎胜:《宋元至清初我国外语教学史研究》,《江海学刊》1998年第3期,第112~118页。。可见,自汉代以来,中国历朝统治者都非常重视外语人才的培养,并设置专门机构进行教学和研究。其中丝绸之路沿线所使用的语言显然是重点。
同时,西域各国和地区也在积极学习汉语言文字,为商贸往来提供服务,同时也促进自身文化的发展。例如,在部分回族、东乡族与撒拉族人民中一直流行着一种以阿拉伯文和波斯文字母为基础的拼写文字。这种文字通常被称为“小经”,而多数“小经”读物的语言实际上就是汉语。这种与汉语紧密关联的文字在穆斯林民间主要是私下传授,并不是一种死文字,而是一种使用至今的活文字,主要用于中国伊斯兰经学,不仅用于经学教育,而且历来在世俗生活中亦有使用*刘迎胜:《关于我国部分穆斯林民族中通行的“小经”文字的几个问题》,《回族研究》2001年第4期,第20~26页。。
此外,从很早的时候开始,阿拉伯及周边地区就已经出现民间零散式汉语教育。唐宋时期,由于中国的强盛以及在当时国际社会上的重要地位,阿拉伯王朝曾70余次派遣使者来华。在华的阿拉伯人开始接触并学习汉语,同时,也有中国人远赴阿拉伯及周边地区学习阿拉伯语,开始了较有规模的中国语言和文化的国际传播交流活动。而明清时期,中国留学生及学者赴阿拉伯及周边地区留学或旅游期间,以讲座的形式向阿拉伯人讲授汉语,则意味着汉语教学由民间零散式教育向大学学科式教育转型*张浩:《阿拉伯及周边地区汉语教育研究》,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6页。。
还有一些兄弟民族借鉴汉字构造原理创立了自己的文字体系,并通过语言文字教育的手段,来推动语言文化交流,服务各项事业。例如,西夏景宗李元昊在称帝前就命人仿照汉字创制了西夏文。《西夏书事》中写道:“元昊思以胡礼、蕃书抗衡中国,特建蕃学,以野利仁荣主之;译《孝经》《尔雅》《四言杂字》为蕃语,写以蕃书。于蕃、汉官僚子弟内,选俊秀者入学教之,俟习学成效,出题试问,观其所对精通,所书端正,量授官职。并令诸州各置蕃学,设教授训之。”*吴广成撰,龚世俊等校证:《西夏书事校证》,甘肃文化出版社1995年版,第152页。可见西夏王朝利用创制的番书翻译汉语典籍,让国人学习汉文化,以达到教化民众的目的。再比如,契丹人原无文字,操一种古蒙古语方言,以刻木记事。但在辽朝建立后,神册五年(公元920年),契丹人耶律突吕不和耶律鲁不古将所学汉字“隶书之半增损之,作文字数千,以代刻木之约”*参见《新五代史·四夷附录》;《辽史》卷七五《耶律突吕不传》及卷七六《耶律鲁不古传》。,创制了契丹文。这些措施的实施,无疑大大地推动了语言文化交流和民族融合,从而促进了丝绸之路的繁荣和发展。
(二)佛经翻译
随着陆上丝绸之路的开通,中国不仅重视对外传播中国语言文化,也重视引进外国文化,以此促进友好往来、相互了解和文明互鉴。其中,佛经翻译就是一个典型。据史书记载,汉“哀帝元寿元年,博士弟子景卢,受大月氏王使伊存口授浮屠经”*参见《三国志》卷三十引鱼豢《魏略》。季羡林总编、张岱年等主编:《传世藏书通典史库(4:三国志、晋书)》,海南国际新闻出版中心1996年版,第329页。。可见汉代已开始传入佛经,这是汉武帝开通西域、与西域各国交往的结果。自印度佛教传入中国,当时的儒士、民众不乏喜谈佛法之人,所以佛经翻译也就自然而然地成为现实需求。
据史载,佛经翻译始于东汉初年明帝时期。永平十年(公元67年)蔡愔等人奉命往西域取经,于大月氏国遇沙门迦叶摩腾、竺法兰两人,并得佛像经卷,用白马驮着共还洛阳。汉明帝特令为二僧建造精舍,供他们居住,称作白马寺。于是迦叶摩腾、法兰二人在寺里传授佛法,并翻译了《四十二章经》等*耿引曾:《中国亚非关系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第72页。。其后又有由外国僧人口译(所谓“传言”),汉人助译并写成汉语(所谓“笔受”)的译经。佛经的翻译不仅促进了佛教在中国的迅速传播,而且密切了中土与西域的关系,为丝绸之路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人文环境。
魏晋之际,河西名僧竺法护在西晋初年从西域带回大量的佛经,自敦煌至长安沿路传译。公元401年,天竺名僧鸠摩罗什被后秦姚兴请到长安担任国师,讲学布道。他学会了汉语以及一些方言,开始着手译经。他主张意译,“手执胡经,口译秦语(汉语),两释异言,交辩文旨”*(梁释)僧佑撰,苏晋仁、萧炼子点校:《出三藏记集》,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292页。。在短暂的后秦,西域高僧和中土的义学沙门汇聚逍遥园中,译出《法华经》《思益经》《菩提经》等30多卷佛典。另一天竺高僧昙无忏于沮渠蒙逊玄始年间来到姑藏学习汉语,后来与河西沙门慧嵩、道朗等合作译出《大般涅槃经》63卷,《方等大集经》92卷,共41部*刘建丽:《西夏时期河西走廊佛教的兴盛》,《宁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2年第3期,第41~46页。。
到隋唐,出现了密宗。唐开元四年(公元716年),中天竺僧人善无畏入唐。他翻译密教经典,沙门一行亲承讲传,笔受口诀,撰《大日经疏》20卷。这是密教在中国正式传授之始。天宝五年(公元746年),密教的不空到长安开始了佛经翻译工作,历玄宗、肃宗、代宗三朝,先后在长安、洛阳、武威等地译出《金刚顶瑜伽真实大教王经》等11部143卷,从此中国密教经典较为完整*周一良主编:《中外文化交流史》,河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482页。。
唐中叶是西域文明的巅峰时期。斯坦因、勒柯克和伯希和发现的一大批翻译文献,就是5—7世纪所完成的佛经翻译的巨大工程的缩影,它们分别用汉文、藏文和回鹘文翻译,集中体现了当时西域的宗教生活,也反映了当地的经济和社会生活*[法]鲁保罗著:《西域文明史》,中国藏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192页。。此外,叙利亚的景教(基督教之一派)僧人景净也曾协助印度僧人翻译中亚语文的佛经*周一良著:《中国与亚洲各国和平友好的历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67页。。
大规模佛经翻译和佛教传播的成功说明,古代丝绸之路不仅是商贸之路,而且是语言文化交流、融汇之路。而语言文化的交流融汇,无疑促进了古丝路人员交往和商贸往来的繁盛。
(三)工具书编纂
为了方便佛经翻译和语言学习及语言使用,辞典等工具书的编纂得到了重视,历代都有佳作问世。例如有人认为成书于唐代的《翻译名义大集》,采取梵藏对照的方式,收录了大量的佛教词语和普通词语,后来又增添了汉文。唐代玄应与慧琳的两部《一切经音义》收录解释了大量的佛经疑难词语,包括许多音译梵文词。在敦煌文献中也有一些唐代汉藏人民为互相学习彼此的语言而编写的工具书,如汉藏对音《千字文》残卷*法国国家图书馆:《法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西域文献》(第24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155~158页。、《汉藏对照辞语》*黄永武:《敦煌宝藏》(第22册,第3辑),新文丰出版公司1993年版,第702~703页。《汉藏对照词汇》*法国国家图书馆:《法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西域文献》(第18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第121~122页。等。类似的还有明代四夷馆编《西番译语》、清乾隆时期《西域同文志》等,都是留存至今的珍贵古工具书。
《突厥语词典》系宋熙宁七年(公元1074年)我国新疆喀什噶尔的突厥语语言学家马合木德·喀什噶里编写的一部工具书,是中国第一部用阿拉伯语诠释的突厥语辞书。他搜集了大量的新疆和中亚各地的语言和社会材料,在巴格达(今伊拉克境内)旅居时完成,记述了突厥语语法规则、方言特点,注释中引用了突厥语民族的诗歌、格言、谚语以及历史、地理、战争、生产、人民和风俗习惯等珍贵资料,被誉为11世纪中亚社会的百科全书。
元代,为方便汉人与蒙古族人交往,曾有《至元译语》,以汉字录写蒙古语词汇,再给出汉语释义。这种字书继承了北朝时代以汉字“录写本言”,再加汉字释义的古老传统,是一种特殊形式的双语对译字典*刘迎胜:《宋元至清初我国外语教学史研究》,《江海学刊》1998年第3期,第112~118页。。
《回回馆杂字》和《回回馆译语》则是明回回馆为教学和翻译而编写的波斯文—汉文词汇表,相当于今天的分类字典。所录词汇包括波斯文原文、汉字注音与汉译。此外,明会同馆也编写了一种《回回馆杂字》,即只包括汉字音译与意译,无回回字原形*刘迎胜:《回族与其他一些西北穆斯林民族文字形成史初探——从回回字到“小经”文字》,《回族研究》2002年第1期,第5~13页。。
这一系列语言文字工具书的编纂和流传为各民族地区之间的交流提供了诸多便利。一方面,这些工具书能够方便人们进行各类语言的学习,是古代中国和西域进行商贸政治文化往来的必要参考书;另一方面,它们传承了人类宝贵的文化财富,这既包括语言文字本身,也包括各地的民俗风情、文化传统。
(四)通信交流
公元前60年,汉王朝在西域设都护府,从此驻汉军,移汉民,屯田戍边,汉语在西域就已经扎下了根。至今出土的西域三十六国的语言文字中都有不同程度的汉字记载*赵杰著:《丝绸之路语言研究》,新疆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22页。。汉代已设置很多驿馆,唐朝发展了驿传制度,规定“三十里置一驿,其非通途大路则曰馆”*参见《通典》卷三十三。。1907年,斯坦因在敦煌西之古瞭望堡遗址垃圾堆中找出许多汉字木简,据考年代在公元1世纪。这些木简显示出精绝等地王公贵族和中原的信函往来。写信者都应是当地具有很高文化素养的上层人物,他们用汉文作为日常的联络语言。在罗布泊海头遗址发现的“李柏文书”是晋西域长史李柏和焉耆王龙会的来往函件,说明焉耆的上层人物熟谙汉字并在日常生活中使用*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编:《汉代西域考古与汉文化》,科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29~30页。。木简上有许多刮削的痕迹,可见木简来源的昂贵,于是用了又用*[英]奥里尔·斯坦因著:《斯坦因西域考古记》,新疆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149~150页。。此外,近来在河西走廊出土的悬泉汉简、居延汉简,以及驿站出土的文书等可以证明,汉朝与西域各国之间有着非常频繁的通信交流。沿着陆上丝绸之路,汉文化传播甚远。
《礼记·王制》记载,“五方之民,言语不通,嗜欲不同。达其志,通其欲,东方曰寄,南方曰象,西方曰狄狄鞮,北方曰译。”由此可以看出,古代中国各民族和地区间互相沟通时,常要借助翻译。公元5世纪,北魏政府接待周邻诸国来宾和四方使臣及降者的机构是“四夷馆”。《洛阳伽蓝记》说,当时御道之东有四馆:“一名金陵、二名燕然、三名扶桑、四名崦嵫。”*杨衒之、范雍祥校注:《洛阳伽蓝记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160~161页。“崦嵫”在北朝时指代西域以远诸族。西域使用的语言种类很多,但当时最为重要的商业语言应当是九姓胡人所使用的粟特语,崦嵫馆内应配有懂得这种语言的译员*刘迎胜:《华言与蕃音 中古时代后期东西交流的语言桥梁》,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版,第66页。。崦嵫馆的设立大大方便了内陆亚洲各国的商人使节,因此“葱岭以西,至于大秦,百国千城,莫不欢附,商胡贩客,日奔塞下”*刘迎胜:《华言与蕃音 中古时代后期东西交流的语言桥梁》,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版,第161页。,极大地推动了经济的繁荣发展。
2014年至2017年,西达里亚油田共实施提液、加大机泵拉升功率、控井筒流量、调驱扰动水窜等低成本措施16井次,累计实现效益增油0.74万吨。
有学者考证,《明史·哈列传》*哈烈为明代对沙哈鲁的都城Herat(今阿富汗西部赫托特)的汉文音泽。中保留了一段明成祖派指挥白阿儿忻台出使帖木儿汗国时携带的一封致沙哈鲁国王的国书的节录。而在布洛晒刊录的撒麻儿罕地有关帖木儿帝国国王沙哈鲁与明朝往来历史的记载中,亦有一份明朝皇帝致沙哈鲁国王国书的波斯文本,就是《明史·哈烈传》中明朝使臣白阿儿忻台所携国书的波斯文译本*邵循正:《有明初叶与帖木儿帝国之关系》,《社会科学杂志》1936年第1期,第135~427页。。可见在古代陆上丝绸之路上,各国的通信交往文件已有“原件”和“翻译件”之分,语言翻译成为常态。
在西域各民族中,粟特人接受汉文化影响最深。粟特文缘于西亚阿拉美文,本为横书,因受汉文化影响才改为直书,“粗有书记,竖读其文”*参见《大唐西域记》卷1。。8世纪初的唐朝慕格山粟特文书中有相当部分写在汉语文书的背面。可见,7—8世纪的粟特文化和蒙古、朝鲜、越南和日本文化一样,属于汉文化系统*林梅村著:《汉唐西域与中国文明》,文物出版社1998年版,第378页。。另外,在甘肃西部、楼兰、吐鲁番、高昌、焉耆、库车、叶尔羌、和阗等地,都发掘出了古代的纸张。从发掘确定的年代来看,蔡伦发明造纸法以后不久,纸就开始向这些地区传去。从这些地方又进一步传出中国,传到南亚、西亚许多国家,比如波斯、阿拉伯等等,当然也包括印度。后来又传到欧洲*周一良主编:《中外文化交流史》,河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41~142页。。由此可见,在陆上丝绸之路,西域诸国与中原书信文书往来频繁,汉字的书写方式影响了其他民族,而纸张作为便利的书写工具也流传甚广。
二、历史启示与现实问题
古代陆上丝绸之路语言服务的一些做法,对现今“一带一路”建设中的语言服务工作有诸多的借鉴意义。要顺利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离不开相应的语言服务,以解决交往沟通、文化隔阂等问题,促进民心相通,为开展经济等合作奠定基础。回顾历史,面对现实,我们应该看到“一带一路”建设所面临的困难和问题。
(一)语言格局的复杂性
“一带一路”沿线自古以来语言格局复杂,这为相互交往带来了很大的障碍。在汉朝,西域诸国并未形成统一的语言,即使匈奴各部落之间的语言也互有歧异*张力仁:《文化交流与空间整合——河西走廊文化地理研究》,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64页。。到唐朝,该地区的语言仍然复杂,不过,由于中央政府在西域设郡并派遣官员,加上做买卖的商贾、云游布道的僧人以及被充边发配的各类人员等大量西进,更加密切了西域各地与中土的联系,相互来往更加频繁,另加上大规模的译经活动的开展,促进了语言文化的交流与交融。西夏时期,虽然党项人不愿完全被汉文化渗透,但仍将《孝经》《尔雅》等儒家典籍翻译为“番蕃语”“番书”,将其应用于学校教育。这些做法显然促进了语言文化的交流,尤其对汉语言文化在西域的传播发挥了积极作用,也培养了精通“番语”、汉语和儒学理论的人才。
由此可见,自古代起,不同语言交流和汉语的对外传播,都得力于频繁的交往,也得力于中央政府的重视和推动;反之,不论是商人往来,还是贤士云游等各种人员往来和交流,都需要相应的语言服务做保障。这给我们的一个重要启示是,在推进“一带一路”建设时,必须高度重视语言服务建设,为相关交流合作铺路搭桥。2015年8月发布的《“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产业合作报告》中提出,要构建全方位的“一带一路”产业互利合作关系,加强与中亚地区经贸合作,共建西部开放窗口。要想加强经济合作,实现共赢,各国企业的沟通和联系会更加频繁,而语言沟通则是最基本的保障。但我们相应的语言服务能力非常有限。有研究显示,“一带一路”沿线64个国家使用的国语和官方语言就有78种,除了同语异名的之外,也有56种。如果把这些国家所使用的民族语言都计算在内,有2400多种。对这些语言我们了解很少,就连56种国语和官方语言,国内高校还有11种语言没有开设课程。*以上关于语种的数据,引自杨亦鸣和赵晓群主编:《“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语言国情手册》,商务印书馆2016年版,前言。相关语言人才十分缺乏,有的甚至没有。可见,“一带一路”建设面临的“外源性语言问题”会十分突出,语言障碍会影响中国企业的海外发展和海外利益,是企业国际化发展的“短板”*沈骑:《“一带一路”建设中的语言安全战略》,《语言战略研究》2016年第2期,第20~25页。。与此相关,中亚和西亚作为“一带一路”的关键地区和维护我国政治安全和能源安全的战略重地,汉语传播也很薄弱,孔子学院数量寥寥。总之,无论是相关语种的掌握,还是汉语的传播,都与“一带一路”建设的语言需求不相匹配,这是推进 “一带一路”建设的一大困难,迫切需要各方面重视并努力解决。
(二)宗教文化的差异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宗教较为发达也很丰富,这构成了复杂性,也是我们在推进“一带一路”建设时必定面临的客观环境和需要妥善处理的重要问题。不过,在这方面,有些历史案例也具有启发意义和积极作用。东汉至魏晋南北朝,来华僧人是汉语的主要学习者,而僧人学习汉语的目的是传播宗教而非传播汉语,因此,可称作“宗教伴随式”汉语传播。同时,那个时期佛经翻译也十分繁盛,不仅为需要者提供了语言服务,而且推动了不同语言的传播和交流。这样就形成了具有积极意义的互动局面,一方面,汉语依附于宗教传播而且促进了宗教传播;另一方面,宗教传播客观上也促进了汉语本身的传播*王建勤:《“一带一路”与汉语传播:历史思考、现实机遇与战略规划》,《语言战略研究》2016年第2期,第33~38页。。与此同时,外来僧人也把梵语等西域语言带到了中土,又促进了不同语言文化之间的交流。这种局面一直延续到唐代,由于统治者对佛教非常尊崇,而大量僧侣又往来于西域和中原之间,从事弘扬佛教的各种活动,翻译了大量的佛教典籍,既促进了中原与西域的语言文化交流和商贸往来,也为后人留存下许多反映历史景象和风俗信仰的宝贵材料。
以上情况表明,丝绸之路绵延千年,在历史的长河中,不同宗教文化的交汇和碰撞极其频繁,它带动了语言翻译等语言服务活动的发展,同时,语言服务的发展也促进了宗教文化的发展。而这些语言文化活动的开展,不仅丰富了人类的精神文明,也对国家和地区之间的商贸往来起到了促进作用。
今天,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仍然存在着复杂的局面。儒家文化、道教文化、佛教文化、穆斯林文化、基督教文化和其他各种本土宗教文化的差异性,以及上千种语言藩篱的存在,造成了沟通和理解上的诸多困难,致使产品走出去也面临困难*引自李宇明在第二届“一带一路”百人论坛上的致辞——《在“一带一路”建设中充分发挥高校作用》。。因此,了解彼此宗教和文化的差异,利用其积极因素,促进相互理解和交流,成为“一带一路”建设一个必不可少的关键环节。经由古丝路流传下来的大量宗教典籍与古时语言文化交流和语言服务的经验,都可以为我们今天实施“一带一路”建设提供丰富的资料和有益的借鉴。可以借助语言文化的交流交融,增进与相关国家之间的相互理解,以推动经贸等各方面的合作。
(三)话语体系对接的困难
语言服务从本质上说是一种帮助性行为或活动,旨在满足一定对象对语言文字及相关方面的需求*赵世举:《从服务内容看语言服务的界定和类型》,《北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3期,第4~6页。。这就需要充分认识服务的对象,避免因缺乏对服务对象的了解而出现失误。其中,做好话语对接就是一个十分重要的方面。因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国情各有不同,政治的、宗教的、文化的、领土的等各种因素错综复杂,需要对此有充分的了解,要选择符合对方国家国情和文化的正确得体的话语与不同的国家和地区交流。但现实的情况是,在“一带一路”实施过程中,话语表述失当与翻译错误的现象时有发生。例如,“西南战略大通道”的说法让印度不满,而东盟国家对“桥头堡”也非常警觉,俄罗斯则对中国的“西进”非常担忧。“汉语推广”“过剩产能输出”“辐射中心”“核心区域”等提法很容易被国际受众解读为中国谋求主导地区和世界的理念和姿态*黄行:《语言保障先行》,《中国社会科学报》2016年1月5日(第003版:语言学)。。这表明,我们与其他国家的话语对接还存在问题,需要调整和完善。话语表达及其翻译的准确性和得体性,依赖于对相关国家国情及文化风俗的深入了解,以及对其语言和表达习惯的精准把握。这就需要我们充分研究相关国家的国情,尤其是语言、文化。这方面也有很多古丝路的文化遗产可以利用。例如,被誉为“11世纪中亚社会的百科全书”的《突厥语词典》和西夏的《文海》《番汉合时掌中珠》等典籍,主要以字词条目的形式详细记录了丝绸之路沿线地区的语言、历史、风俗、政治、法律、战争、生产等知识,对于我们深入了解“一带一路”沿线的历史文化、风土人情等都有重要的参考价值。《番汉合时掌中珠》所表达的鼓励不同民族相互学习语言的理念:“不学番言,则岂和番人之众;不会汉语,则岂入汉人之数”,也很具有启发意义。有一种说法叫“翻译即背叛”(Traduttore-Traditore),来自意大利语,巧用了仅有细微差别的两个词,深刻地揭示了翻译的困境,即译文与原文不可能百分之百匹配,甚至可能因语言文化差异而变成“假朋友”*赵启正:《语言服务是跨越文化障碍之桥》,《中国翻译》2014年第1期,第6~8页。。这无疑表明不同语言话语对接的重要性。反观古人编纂的一系列具有双语字词典性质的工具书及其对相关文化知识的记录和阐释,可知古人十分重视跨文化表述的准确对接问题。上面提到的《突厥语词典》《文海》《番汉合时掌中珠》等,都是这类工具书,涉及突厥语、阿拉伯语、梵语、西夏语、汉语等多种语言的对译和解释问题,很有借鉴价值。
三、思考与对策
古代陆上丝绸之路的语言服务活动为当今“一带一路”的语言服务建设提供了诸多启示。回顾历史,面对现实,要为“一带一路”建设提供充分的语言服务保障,还需要深入研究,本文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一)企业语言培训与汉语传播
曾经活跃在古代陆上丝绸之路的很多商人、僧人群体为了实现商贸和传教目标,都非常注重学习目的地语言,通过语言互通,拉近与他人的距离,为经商传教创造条件,取得了成功。这对于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的国内外企业来说不无启发意义。就我们中国企业来说,整体上外语能力比较薄弱,尤其是面对“一带一路”沿线众多的非通用语言,可能短板更为突出。因而要参与“一带一路”建设,语言障碍是很大的挑战。这就需要企业根据自己的发展规划,做好相应的语言规划,加强对员工的语言培训。现实中有很多以语言文化融通来促进经贸合作的成功范例,也说明了企业语言能力在企业海外发展中的重要作用。例如在土库曼斯坦,我国某石油企业尊重当地文化,努力学习当地语言,融入当地生活,并且积极为所在地培训企业管理人才和工人队伍,赢得了当地信任和支持,从而实现了很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郝时远、殷泓、沈晨叶:《文化多样性与“一带一路”》,《光明日报》2015年5月28日(第011版:名家·光明讲坛)。。可见,对于跨国经营的企业来说,过硬的语言能力,有利于开拓海外市场,将产品和服务很好地本地化,能给企业带来经济上的巨大收益。因此,建议国家和企业都应该把企业的语言能力建设列入企业建设的重要内容,为参与“一带一路”建设提升“软实力”。一方面要对企业员工开展“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语言的培训,便于他们融入当地生活;另一方面,也要开展提升汉语水平和汉语传播能力的培训,以便在当地传播汉语和中国文化,促进相互了解。国家也应该把孔子学院建设纳入“一带一路”建设的总体规划之中,加强顶层设计和合理布局,以汉语的传播和文化的交流服务于“一带一路”愿景的具体实施。
(二)各国语言文化产品的翻译
我们在前面已经提到,“一带一路”涉及至少64个国家的50多种主要语言和约2400种非通用语言。要顺利实现与这些国家的“五通”,首先就需要突破语言之间的障碍和文化方面的隔阂。这就需要有好的跨语言产品来协助。各国间的关系发展急需要经贸合作的“硬”支撑,也离不开文化交流的“软”助力。可以借助各种优质语言文化产品,包括翻译产品,讲好中国故事,同时主动倾听其他国家的故事,扩大民间交往*引自潘超在第二届“一带一路”百人论坛上的发言——《提升文化软实力,助力“一带一路”建设》。。这在古代丝绸之路有非常成功的实践,比如中国的儒道禅宗和其他国家的佛教、伊斯兰教、基督教等文化的相互交流交融及借鉴,成就了那个时代丝路沿线的文化繁荣和商贸发展。而汉语和其他民族语言的接触,也赢得了共同的发展。当今我们应当从历史中发掘经验,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合作,对各国的经典文化产品尤其是古代丝绸之路遗存下来的宝贵语言文化资源进行发掘、整理和翻译,互通有无,分享优秀文化,增进互相理解和友好相处。同时,还应注重搜集整理或研发当代文化资源,加强翻译和交流。例如文学、影视、戏剧等作品的互译、网络资源的共建共享。还例如,可以搜集整理发生在企业间的语言文化交流的成功做法或冲突案例,编辑成册,并翻译成各国语言,供有关人员学习和掌握,以避免在交流合作中触犯宗教、文化禁忌,造成不良后果。
(三)重视话语体系对接与工具书开发
不同国家之间的话语对接是保障交流有效进行的前提。这方面大有文章可做。千百年前,流传于陆上丝绸之路的各类工具书,不但便利了民众的沟通,更在无形中起到了不同国家、地区之间话语对接的作用,客观上构建了不同文化和地域之间交流的话语体系。当前,“一带一路”建设面对情况十分复杂的众多国家和地区,更需要合适的话语体系,尤其是对外话语体系。我们感到,这方面是存在一些问题的。比如有些话语基调居高临下,令人误解;关键词火药味浓,让人生畏。因此需要校准话语基调,系统整理关键性词语,并组织专家研究翻译问题,增强“一带一路”话语权意识,确保话语准确得体*赫琳:《“一带一路”需要合适的话语体系》,《中国教育报》2015年12月16日(第006版:理论周刊)。。自2015年起,中央编译局开始发布“中央文献重要术语译文”,其中涉及“双向开放”“互联互通”“命运共同体”和“一带一路”相关的术语,这是非常好的做法。我国语言文字、新闻媒体、出版、文化、教育等行业领域,都应在“一带一路”话语体系建设方面发挥积极作用。例如,国家语委、中央编译局、全国名词委等机构,应联手针对“一带一路”术语,制定选择、使用与翻译原则,提供具体翻译词表,拟定忌讳词表或不建议使用词表,及时提供语言咨询服务*李宇明:《“一带一路”需要语言铺路(大家手笔)》,《人民日报》2015年9月22日(第07版:理论)。。出版部门可以开发面向“一带一路”的有关语言、文化、法律、经贸等方面的工具书,并翻译成多语种,以方便各类相关人员使用。2015年11月,首部“一带一路”语言服务工具书《“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语言国情手册》(杨亦鸣等主编)发布,介绍了沿线64个国家的语言状况,以及语言与民族、宗教的关系等,就是一部很实用的工具书,很受欢迎。 在“一带一路”的话语构建方面,新闻媒体应担当起主要责任,致力于正确得体的话语体系的建构。除了传统的做法之外,应当积极创新宣传手段。比如,充分利用互联网等新媒体,开展多语种宣传,争取受众的广覆盖。又比如,加强与外媒的交流与合作,将服务尽可能地覆盖到沿线国家和地区。注重从具体案例入手,传播“一带一路”倡议的理念及意义,宣传中外地区间和企业间的合作发展模式与具体成效,讲好故事,见人见事,用事实说话,以成效服人。还可以推动成立媒体合作、联动组织,让“一带一路”的积极信息及时通达四方,营造良好的舆论氛围。
(四)智库建设及积极发声
面向“一带一路”的语言服务是一项复杂的大事业,需要集思广益。这既需要语言学者和相关领域的学者自发的深入研究,也需要有语言智库专攻。只有通过智库型跨学科领域的专家团队的全力攻坚,才便于更加全面深入地研究“一带一路”的语言需求和语言服务,并持续进行跟踪研究,以满足不断发展变化的各种语言需求。同时,还可以推动建立不同智库之间的交流合作机制,打造更大的语言智库综合服务平台,更好地为国家、组织和企业的相关决策提供咨询服务。此外,鼓励和推动语言智库利用各自的研究成果积极发声,在引导社会舆论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尤其是在“一带一路”话语体系建设方面贡献智慧和力量。
总之,以史为鉴,古代陆上丝绸之路的语言服务活动给当今带来诸多启示。我们应该立足现实,古为今用,与时俱进,不断增强语言服务“一带一路”建设的意识,提高语言服务能力。比如,扩大汉语传播,提升企业非通用语种能力,构建得体完善的话语体系,翻译和开发多语种文化产品,开展语言咨询服务等等,为“一带一路”建设铺路搭桥。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只有将语言服务于经济、社会发展,才能有助于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有助于实现“一带一路”美好愿景和民族复兴的中国梦。
The Enlightenment on the Belt and Road Vision by the Language Services of the Ancient Silk Road
HeLin
(College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Wuhan Uniersity,Wuhan,China)
TanZao
(College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Wuhan Uniersity,Wuhan,China)
The ancient Silk Road connected ancient China with other Asian and even European regions,so the language conditions were quite complicated. The Silk Road could not be explored and developed without the language services. At that time,some relative language services,including language education,Sutra translation,reference books’ compilation and correspondence,not only incresed the communication of different languages and cultures,but also promoted the trading and political contacts along the way,which played important roles in the formation and prosperity of the Silk Road. Nowadays,with the proposition of the Belt and Road vision the relative service construction of language and the boost of Chinese cultural soft power are contemporary topics. Identifying today with the past,the paper investigates the language service items of the ancient Silk Road and combines them with the problems and challenges that we are facing in reality,therefore provides a series of suggestions on some language service issues such as education of foreign languages,popularization of Chinese,translation of cultural products,interaction of discourse systems,compiling of reference books,construction of think tanks as well as publicity of media among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Belt and Road. Key words:The Ancient Silk Road;Language Services;The Belt and Road;Enlightenment;Cultural Soft Power
10.19468/j.cnki.2096-1987.2017.01.006
赫琳,武汉大学文学院教授,中国语情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主要研究汉语语法学和应用语言学。 谭昭,武汉大学文学院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专业研究生,主要研究社会语言学。
国家语委“十三五”科研规划2016年度重点项目“‘一带一路’话语构建研究”(ZDI135-24)、国家语委项目“新疆少数民族中小学生通用语言能力建设问题及对策研究”(YB125-1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