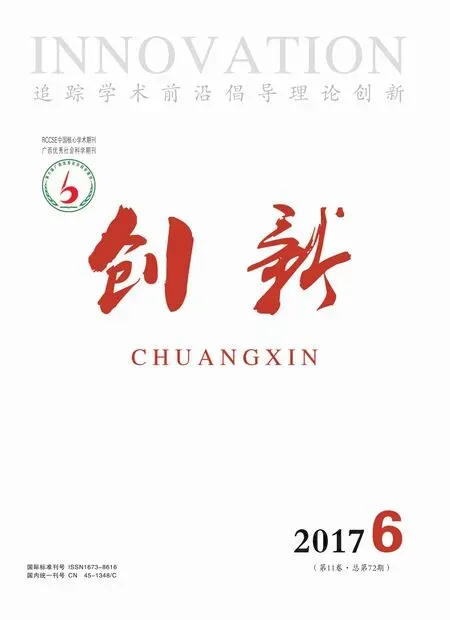虚拟社会化中的交往悖论
■ 肖 峰
虚拟社会化中的交往悖论
■ 肖 峰
网络时代人和人之间的社会交往可以在虚拟空间中进行,由此形成了虚拟社会化或虚拟交往的人际新关系。虚拟社会化对于现实交往既具有积极意义,也形成了消极影响,主要表现为在扩展交往的广度时影响了交往的深度,形成了浅交往、弱连接的泛化,甚至导致了“群体极化”“信息茧房”和“5A”等负面效应,构成为互联网对人和人之间既连接又隔离的交往悖论。认真看待和解决这一悖论,是信息文明建设的一项重要任务。
虚拟社会化;虚拟交往;现实交往;悖论
社会化是任何时代人的发展都要经历的过程,信息文明时代人的社会化过程则具有了新的特征,这就是日益广泛的“虚拟社会化”,即在网络的虚拟空间中所完成的社会化。这种新型的社会化由于兼具积极和消极的意义,因此对于通过它来实现人和人之间的交往就具有了“悖论”的性质,本文称其为“交往悖论”。探讨虚拟社会化中的交往悖论,可以扩展我们全面理解信息文明进程的复杂性。
一、虚拟交往的双重效应
如果说价值观是人成长和发展的一种趋向与追求,那么人的社会化无疑也是其重要的组成之一。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社会化是人的社会属性的本质体现,是人的内在需要;通过社会化而建立的社会关系对于人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社会关系实际上决定着一个人能够发展到什么程度”[1]295,“一个人的发展取决于和他直接或间接进行交往的其他一切人的发展”[1]515。从总体性和必要性上看,它使生物人或自然人变为社会人,使“个体人”摆脱孤立隔绝状态,处于与他人的交往关系之中。由于社会化是在普遍交往中实现的,因此交往就是走向社会化,或者说走向社会化就必须参与交往。又由于交往与社会化的实质性同一,故我们可以合称为社会化交往或交往社会化,社交就将两个不同的词合成为一个词,体现出两者的共同所指,而社交平台可以说就是行使这一功能的技术手段。
传统意义上的社交是人与人的直接交往,但在信息文明时代,由于网络和虚拟空间的出现,人们越来越多地以信息技术终端(包括计算机、手机等)和互联网为中介进行交往,结成社会关系,实现自己走向社会化的目的。信息文明时代社交网络与社会生活的交汇使网上交往变成一种重要的社会活动,促进了人类交往方式的变革和社会的发展。基于网络空间的虚拟特性,可将互联网化的社会交往称为“虚拟社会化”或“虚拟交往”。
作为虚拟社会化的网络交往具有自身的优越性,“当我们希望保持社会关系或扩展社会关系时,网络是一种上佳的交流方式”。[2]例如它所具有的一对一、一对多、多对一、多对多的交流功能,使得无论是单向的还是双向的或者是多向的交往,无论是小规模的还是大规模的社交都可以便捷地实现,从而以较低的沟通成本产生出较高的沟通效率。正因为如此,网上的虚拟社交在一部分人(如“数字化一代”,也被称为“技术社交的一代”)那里已经占据主导地位,较多地取代了现实世界中的社交。尤其是当今的微信、微博等将人们带入了“微时代”的线上交往,而更少从现实世界中进入到社会化的关系之中①据统计,微信作为中国微信用户强大的社交工具,接近一半活跃用户拥有超过100位微信好友;57.3%的用户通过微信认识了新的朋友,或联系上多年未联系的老朋友。参见《腾讯发布2015微信用户数据报告》,载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网站,2015年8月24日,http://www.cac.gov.cn/2015-08/24/c_1116346585.htm。,甚至还有这样一种夸张的说法:找到最佳恋人不再靠约会,而是靠计算或算法。那么这种具有“虚拟”或“赛博空间”性质的社会交往与现实的社会交往具有同等性吗?它对人的现实交往是一种增强还是削弱?它是扩展了人与人的联系还是因为网络而形成了新的隔绝?如果用“虚拟朋友”甚至“虚拟亲人”代替现实世界中的朋友和亲人,这是使人更具社会性还是更加孤独?从而我们是应该大力倡导它还是适度限制它?这就是今天我们面临的悖论性的困境。
其实,早在工业文明时代就因新的交通工具而将人类带入普遍交往的时代,信息文明则因新的通信工具(尤其是互联网)而使交往如虎添翼,将人类带入互联即更加普遍交往甚至全球化交往的时代。借助现代信息通信技术,我们消除了人和人之间物理距离的限制,犹如生活在同一个村庄那样紧邻和亲近,使得今天人们要想纳入社会与他人交往成为一件十分容易的事情,人们不用迈出家门只要打开网络就可以实现与地球上任何角落的人(无论认识还是不认识)进行实时互动。相隔千里的家人或挚友甚至可以经常在打开的视频窗口中享受彼此的陪伴,这无疑拉近了家庭和朋友的关系。当然更可以通过网络找到与自己秉性相投、志同道合的朋友,一定意义上实现了社交的开放、平等、自由和便捷。
但我们同时也看到,这种社会性的交往是一种“虚拟社会性”或“虚拟交往”,与现实社会性或现实交往还是有区别的,所以在虚拟社会性加强甚至成为主导性的交往方式中,它对现实社会性的交往起着双重性的作用,即对人的现实交往能力既可能提高,也可能削弱,由此带来人际关系的价值效应上的冲突。
作为文明基石的技术发展,不断促进了人类交往范围的扩大和交往能力的提高。交通工具的发展使人活动的物理空间扩展,从而能和更多的人实现面对面的交往;通信技术的发展则使人的信息活动空间扩展,由此能和更多的人实现以媒介技术为中介的交往,使得交往的精神需求得以充分实现。例如不少网民在网络社区寻求社会支持和友谊,表达对他人的人情关怀或处境关切,也为自己追求精神的归属感,其范围不限于已认识的熟人,也扩展到陌生人。当前,移动互联网带来了交往媒介的又一次革命,网络交往不再被束缚于室内或桌旁,而是在只要有网络信号覆盖的地方就可交往。通过网络手段作为个体的人还可以在多个终端同时在场,使得交往中“身体已不再有效地限制主体的位置”[3],由此可以克服“亲临现场”的种种局限:对于在场者来说,可以通过信息化的辐射使自己的在场效应极大扩展,可以被如此多的人所接触,也可以使人如此多地接触他人,极大地延伸了人际关系的边界,人的社会性、主体际性等特征得到更充分的展现。
互联网所结成的“网缘”关系中还可进一步发展为“网友”或网络友谊,“网友可能是离线朋友(或家人),离线朋友的朋友,也可能是和你认识的人毫无关系的人,还可能是历史人物的名字,甚至就是虚构的人物”。[4]这是一种更具自由度和能动性的人际关系,同时也是一种建立在一定的技术能力之上的技术性关系。这样,人际关系就包含了更多的由技术影响的成分,社交方式由此发生了重要的变化,人的社会化实现途径更加多样化。不仅如此,处于全面信息化中的人还达到了全球化交往的程度。今天的人作为电子媒介人、地球村的“村民”,同时也是互联网的“结点”,云计算和智能手机等已经使世界从“连接”走向了“超链接”,它使人更具有全球化普遍联系的社会人特征,从而极大地提升了人类的社会化水平。
但另一方面又不能不看到,这样的交往使面对面的交往成为被媒介隔开的交往,从而成为一种间接的交往,使人感到在获得交往的宽度时丧失了交往的深度,或具有了交往的新奇但却没有了交往的内涵,如此等等。
二、虚拟交往对现实交往的弱化
近些年,越来越多的研究和看法认为互联网上的虚拟社会化交往损害了人的现实交往能力,剥夺了人们面对面交往的时间,使人变得更趋向于逃避现实世界,从而变得更加孤独,增强了隔离感,还丧失了现实中的合作与团队精神等等,进而社会责任感弱化,人际关系淡化。盖瑞·斯莫尔和吉吉·沃根指出,随着新技术的影响,人们正日益丧失基本的社交能力,比如在交谈中参透对方的面部表情、把握对方一个微妙手势的情感内涵能力就减弱。斯坦福大学的一项研究发现,我们在电脑前每度过一小时,用传统方式与他人面对面交流的时间就将减少近30分钟,这会使得人脑中控制人类交流的神经回路发生退化,从而使人的社交技巧将变得笨拙不堪,于是我们会经常曲解甚至忽略微妙的非语言信息[5]102。网络中进行的交往也常常使人得不到实在的信息,使身体不再拥有个性象征或人格象征,人的面孔、行动、声音、思想和互动全部迁移到媒介之中,交流已经成为脱离人体的东西,其中传播的信息最终都是以符号的形式被接受,而符号化的大众传播并不向身体保证什么。这样,人的身体在符号网络中被截除,符号化传播最终找不到终端,形成了20世纪大众社会理论中的“5个A”:异 化(alienation)、失 范(anomie)、无 名(anonymity)、 冷 漠 (apathy)、 原 子 化(atomization)[6]。桑斯坦认为网络交往极易导向“群体极化”(group polarization),即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持有近似观点的人们更愿意进行沟通讨论,形成一种同质性的圈子文化,在其中不断强化其持续固守的偏向,最后有可能形成极端化的群体性观点,即“当想法相似的人聚在一起的时候,他们最后得出的结论会比交谈之前的想法更加极端”[7],于是排他性地与其他群体加深隔阂。久而久之,人就生活于桑斯坦所说的“信息茧房”(information cocoons)之中,只听自己所选择的东西和愉悦自己的东西[8],而与茧房之外的人和事形成隔绝。于是,形成了这样一种悖论效应:“互联网提高了人们开阔眼界的能力,且使上百万人正在从中获益;但是许多人因互联网眼界变得狭隘了,而不是开阔了。”[9]
还有一种交往悖论现象,就是互联网增强了交往的“马太效应”:那些会交往的更会交往,而那些弱于交往的更不会交往。一些在现实中乐于交往的人,有了互联网后则如虎添翼,成为网络交往的活跃者,在交往的范围和频率上得到极大扩展;而那些在现实生活中少于交往的人,在网上有可能仍是默默无言、离群索居。两相对比,使得社会性上的差距被拉得更大,从社会性交往差别走向社会化的交往鸿沟。
不仅有线上的虚拟社交平台改变着人们的交往方式,形成悖论性的效应,而且还有社交机器人,从线下改变着人的交往方式,如情感机器人甚至性爱机器人就正在被开发之中,但它们的悖论性后果显然一开始就引起了支持和反对的对峙,其中支持者认为,这些机器人将给孤独人士和无法建立恋爱关系的人带来很大帮助,反对者则指出这可能更加剧人与真人的交往障碍,甚至对性爱机器人的爱好极可能与强奸和恋童癖等紧密相关。
交往悖论中包含这样一种疑惑:随着交往手段(尤其是社交媒体兴起后)的便捷和交友范围的扩大,“你究竟需要多少朋友”的问题随之而来,许多交往成为“浅交往”“弱连接”,甚至是连浅交往都算不上的毫无意义的交往,使得一些人虽然沉溺在“交友瘾”中,但仍然感觉的是孤独。雪莉·托克尔在2014年发表的一篇文章中指出,美国人在几年前遇到紧急情况时一般都可以打电话给5到7个人,五年前从7个人下降到5个人,四年前是3个人,现在则只有伴侣(如果你运气足够好有伴侣的话)或者是父母。如果不是这样的话,有的人甚至连一个这样的朋友都没有。她认为这是一种深度的隔离状态,正是虚拟社交让我们前所未有地忽略直接对话,她将这一现象称为“社交死于社交媒体”[10]。这也是所谓深交往的削弱,浅交往的盛行,现实世界中的社会联系不断弱化。这种浅交往也是我们今天不时以“访客”的身份匆匆漫游于各种社交平台时常能体会到的情形,此时人们常常感到陷入了“碎片化交流”或“浅交流”的泡沫之中,缺乏对深交往的专注和投入,很难形成对某个交往对象的情感归属和稳固的信任,在各种临时性、表面化、形式化的信息交换中耗费时光。网上的匿名交往也多属于这样的“浅交往”,所以万维网(WWW)上的交往也被谐音化为“三无交往”,即无身份、无性别、无年龄的交往,所形成的无非是陌生人之间的陌生关系。如今兴盛的微信社交媒体,看似扩大了社交的范围,但通过个体的选择,朋友圈或好友群会被限制到一定的范围,而可以深交往的组群往往规模更小。对此托克尔还指出,这个新的通信革命正在降低人际关系的质量:其中包括了家人、朋友之间的关系,也包括了同事、恋人之间的关系。她描述了为人们所熟悉但又令人心碎的画面:在操场上、餐桌上,父母常常处于分心状态;孩子们因为不能得到父母全心地关注而感到沮丧;在聚会上,在场的朋友要和那些虚拟空间的朋友争夺注意力资源;在教室里,老师们所面对的是一群一心多用的学生。在现在这种约会文化中,人们有了无限多的选择,但是这么多的选择破坏了人们做出情感承诺的能力[11]。这就是在网络时代,本来敲敲键盘、点点鼠标就可以找到朋友,却发现能交到的朋友越来越少,或者说在互联网上不少人感到越社交越孤独。凡此种种,都是网络在扩展人们交往范围的同时又造成了现实人际交往关系的疏远,由此导致了另一种效应:“技术愈来愈忽略人类直接的相互依存。”[12]
一些实证性的研究也支持了互联网弱化社会交往的观点。克劳特(Kraut)于1998年发表的一项在匹兹堡进行的关于用户的研究表明:过度使用互联网会引起抑郁和孤立,它损害了社会凝聚和互动,因而它的前景越来越暗淡。将互联网技术视为导致人们孤独的社会技术还因此被称为“互联网悖论”[13]1-2。具体来说,网上冲浪的时间替代了“真实”的生活、友谊和社区参与,造成“孤独和社会道德沦丧”。而且,用户用来上网的时间侵占的是与朋友、家人一起进行户内和户外的社会活动时间;或者说,克劳特及其同事的研究实际上发展了鲍德里亚的观点,他们认为,网络是一种虚拟社会的技术,使用互联网过多会使人孤立。而在线联系过多会使人忘记真正重要的事情[13]20-22。
三、超越虚拟困境的社会交往
当然,对互联网在社交功能上的评价也存在与上述观点不同的看法。如凯茨和赖斯认为,互联网的使用在一般情况下不会导致强烈的绝望和孤独,也没有真正造就大批脱离现实而又厌恶政治的群体;它并没有破坏正常的社会交流,也没有将我们变成全球企业资本的傀儡[13]3。因此他们坚称,“噩梦般的反乌托邦观和白日梦般的乌托邦观都不免偏颇。尽管我们确实发现一些证据支持任何可能提出的有关互联网的武断之言,但在多数情况下,我们发现美国人使用互联网主要是为了拓展和改善他们的日常生活。我们也发现一些对互联网错误的认识和意料之外的使用。这些使用经常体现在自我表达和寻求社会互动上。不过这些活动也导致了新型的社会合作与整合。因此,如同互联网使我们的兴趣聚焦和浓缩,进而在某种意义上将我们与其他人或群体孤立开来,与此同时,它也把我们引荐给其他人和群体,从而产生统合性的情感联系和社会联系。因此,互联网在促进专业化和助长差异性的同时,也激励新型的互动和组织。”[13]25
就交往中的真实性来说,巴格等人认为由于在网络的虚拟世界中可以表现真实的自我,使其感到在真实世界中所表现的反而是虚假的自我,因为因特网看起来似乎和“火车上的陌生人”现象是同属一类的,在这里人们似乎更愿意向陌生人透露有关他们生活的细节。这种事情的发生既是由于匿名,也是由于透露细节的潜在代价降低了,因为陌生人并不是他亲密社交圈的一分子,所以不可能对他们产生任何的影响。巴格等人假设,由于匿名性的存在以及透露的社交代价的降低,因特网使人们能更加自由地表达他们的“真实”自我[14]123。这或许就是“用真名说假话,用假名说真话”的心理原因,由此还引发了身份悖论或认同悖论:现实的自我与网络的自我之间,哪一个更是真实的“本我”?同时还引出了一个关于交往对象的本体论问题:当我们在网上进行虚拟交往时,是在与真实的社会进行互动吗?这样的交往可以对建构真实的社会关系起到实在的影响吗?
对作为信息文明标志的互联网在人际交往效应上的不同看法,恰恰是社会化交往悖论的如实写照。互联网使人与人跨越空间的遥远距离,开拓了人类新的交往方式,使我们眼界大开、交往便捷、广识朋友,这都是信息文明时代人类交往范围和交往能力增强的事实。但现实中我们确实也看到,由于沉溺于互联网,一些“网友”终日足不出户,仅仅靠网络保持和这个现实社会的联系。互联网在技术上的发展还实现了“人黏在网上”(固定网络)到“网黏在人上”(移动网络)的转变,网络变得无处不在,几乎所有问题都可以诉诸互联网来解决,这就更多地减少了人与外界直接接触的机会,导致人与人之间的隔离感,与他人交往的困难,变得孤独、寂寞,人际关系可能变得越来越冷漠。出现“一旦关上电脑,你就觉得与世隔绝”[5]3;现在进一步发展为“一旦忘带手机,就觉得与世隔绝”,这就是所谓“网络幽闭症”或“虚拟交往依赖症”,表现为依赖微信进行社交时,也被称为“微信成瘾”,他们“早上不起床,起床就微信;微信到天黑,天黑又微信”。由此以虚拟社交代替现实交往,陷于网络社交而不能自拔。从哲学本体论来看,这种过度依赖虚拟社会化的根基,在于误将虚拟世界完全等同于现实世界,最后用虚拟世界完全代替现实世界。
虚拟交往无疑是现实交往的延伸和补充,没有它,人在今天的交往就会受限,就会如同井底之蛙,落后于时代。按哈贝马斯的说法,人的交往活动就是以符号为媒介的相互作用,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信息交流,它本来就存在多种方式,麦克卢汉将其区分为口耳相传、文字与印刷和电子媒介三种主要类型。虽然在口耳相传时代人和人之间只有面对面的直接交流,但自从有了文字后,由于文字可以离体存在,就使得通过传递文字(如书信)来进行的间接交流问世,这种交流一定意义上也就是虚拟交流,因为面对文字并非直接面对书写人,而是面对从文字中建构出来的书写人。这样的虚拟交流不仅有必要,而且还具有直接面对面交流所不具有的若干优越性,如消除面对面交流时的紧张或窘迫拘束,使不善言谈但擅长文字的人也能交往自如,当然也有其局限性,所以需要多种交往方式之间的互补。这种互补关系也存在于深交往和浅交往之间:浅交往在扩大交往面上具有深交往所不具有的长处,并且深交往通常是由浅交往发展而来的,因此没有浅交往就没有深交往。进一步看,现实世界中的人际交往并非都是深交往,网络电子空间中的交往也并非都是浅交往,不能将网上、网下的交往之间以及浅交往与深交往之间的关系一概视为非此即彼的零和博弈。交往的多样性和流动性,这本身就是交往所内含的特征,而一旦被固定和僵化,社会化交往就名存实亡。
马克思特别强调人和人的交往对于人的全面发展的重要意义,认为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必须以生产力的普遍发展和与此有关的世界交往的普遍发展为前提,而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社会交往形态有两方面的特征:其一是各民族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各国人民之间的民族隔绝和对立日益消失;其二是单个人与一切人发生联系和“各个个人全面的依存关系,使得狭隘的个人为世界历史性的真正普遍的个人所代替,任何人都没有特定的活动范围,每个人都可以在任何部门内发展”[15]。显然,就交往来说,信息文明时代的互联网无疑为实现马克思所描述的目标提供了物质基础或技术平台,以至于可以说今天的媒介技术为人的全面发展所需要的交往展现了更为充分的可能性。
当然,另一方面我们也必须看到,网络交往也不能完全代替现实的交往。从个体来说,自从有了网络交往后,人的交往类型变得更加多样化了,有的人乐于虚拟空间中的交往而不愿意现实世界中去交往,有的反之;有的人既乐于现实中的交往也乐于虚拟空间的交往,而有的人则两者都不去交往,如此等等。虚拟交往的出现至少使得一部分不擅长于现实交往的人也可以参加交往,从中可能培养和锻炼出交往的能力,并将其运用于现实的交往之中;或者说,一个人在网络交往中将自己塑造成什么形象——例如热爱交往,就会影响到他在现实中的行为,久而久之,人就会变成那样的实际人,此即“你就是你所扮演的角色”[14]122。这就是用虚拟来引导现实的积极作用。当然,即使是这种引导,也不仅仅有积极的方面,例如一些“人肉搜索”的案例中,就是从网络上的语词谴责变为现实中的人身攻击,攻击者自己也“实在地”变为了“网络暴民”。
从哲学属性上讲,通过虚拟交往而形成的社会关系是既实在又虚在的,这也导致了人的“多面性”,即既可能丰富人的社会性,但同时也可能形成新的单一性——在虚拟社会性中逃避现实社会性。而且,由于它的存在使得人的社会性也可能变为纯粹由技术支撑的关系,一种依赖于网络技术的社会性。一旦这一技术支架出了问题(如网络瘫痪),其中的人就会彻底失去其社会关系,某种意义上这也是虚拟交往所隐含的危险之一。如此,虚拟交往是优化了还是恶化了交往的环境和生态,也是一个双重效果兼具的现象。所以,认真对待网络背景下人的虚拟交往问题,看到互联网既连接又隔离的双重性,从而既要借助网络的社交平台,但又不沉溺于其中,不忘现实的交往所具有的独特价值和意义,从而不断走出因虚拟交往而带来的交往困境。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
[2]查德威克.互联网政治学[M].任孟山,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10:149.
[3]波斯特.信息方式[M].范静哗,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25.
[4]莱文森.新新媒介[M].何道宽,译.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4:19.
[5]斯默尔,沃根.大脑革命:数字时代如何改变了人们的大脑和行为[M].梁桂宽,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
[6]布努艾尔.我的最后一口气[M].刘森尧,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208.
[7]桑斯坦.谣言[M].张楠,迪扬,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0:8.
[8]桑斯坦.信息乌托邦 众人如何生产知识[M].毕竞悦,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08:8.
[9]霍文,维克特.信息技术与道德哲学[M].赵迎欢,宋吉鑫,张勤,译.北京:科学出版社,2014:80.
[10]TURKLE S.,FISCHETTI M.The Networked Primate[J].Scientific American,2014(3):83-85.
[11]WEISBERG J.数字时代的我们,如何夺回涣散的注意力?(2016-11-01)[2017-08-10][DB/OL].陶小路,译.东方历史评论,http://www.tisi.org/4804.
[12]海姆.从界面到网络空间:虚拟实在的形而上学[M].金吾伦,刘钢,译.上海: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0:102.
[13]凯茨,莱斯.互联网使用的社会影响[M].郝芳,刘长江,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
[14]乔伊森.网络行为心理学:虚拟世界与真实生活[M].任衍具,魏玲,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123.
[1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l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86.
The Paradox of Communication in Virtual Socialization
Xiao Feng
In the internet age,the social communication between people can be carried out in the virtual space,which has formed a new interpersonal relation:virtual socialization or virtual interaction.Virtual socialization has both positive significance and negative impact on reality communication.The negative impactmainly manifests thatwhile expanding the breadth of interaction,it also affects the depth of interaction,forms shallow contact,and the generalization of weak connection.It even leads to the"group polarization"and"information cocoons"and"5A"and other negative effects.Virtual socialization forms a paradox of both connection and isolation between people by internet.It is an important task for us to seriously look at and solve this paradox for the IT-based civilian progress.
Virtual Socialization;Virtual Communication;Realistic Communication;Paradox
B01
A
1673-8616(2017)06-0061-09
2017-10-09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基于信息技术的当代认识论研究”(15ZDB019)、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信息文明的哲学研究”(13AZD095)
肖峰,华南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哲学与科技高等研究所和中国青年政治学院科学与公共事务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广东广州,510641)。
[责任编辑:丁浩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