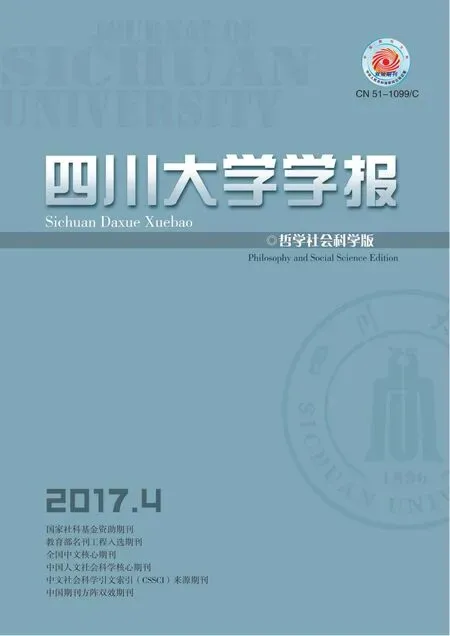电影节红毯仪式的生产和传播:以传播政治经济学为视角
喻宛婷
电影节红毯仪式的生产和传播:以传播政治经济学为视角
喻宛婷
电影节是文化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在电影节实践的诸环节中,红毯仪式及其传播形成了一道独特的大众文化景观。红毯仪式所展示的远远不止是明星,更是以缩影形式展示了涉及电影节及电影产业的各个群体。这些群体之间的社会关系及背后的权力运作,关涉文化、商业和政治的多个面向:红毯仪式的议程设置由专业话语支撑;内含的商品化链条体现了商业话语的运转;而空间的聚合与重置体现出政治话语的植入。红毯仪式便是电影节实践中多重权力角逐、多方话语交融的产物。
电影节;红毯仪式;传播政治经济学
2016年第69届戛纳国际电影节上,华语影片零入围,却有多位中国影星走上了开幕红毯,引发多方争论。中国电影工业对一个国际A级电影节红毯的征服远超其大荧幕,这种落差展现出明星和红毯之间独立于电影艺术本身的某种互利共生关系。随着电影节在文化产业中的重要性日益提升,电影节的相关研究日益受到关注。特别是21世纪以来,欧洲学界将电影节从传统的电影史研究中抽离,作为一个新的历史研究对象,放在系统化、网络化的社会脉络中进行考察。其中的代表学者如沃尔克(Marijke de Valck)、埃尔萨瑟(Thomas Elsaesser)就论述了电影节在全球电影体系中的角色,将国际电影节诠释为以网络节点形式存在的、多轨并行、自我定义的媒介事件,完善了电影节网络理论。①见Marijke de Valck, Film Festivals: From European Geopolitics to Global Cinephilia, Amsterdam: Amsterdam University Press, 2007;Thomas Elsaesser, “Film Festival Networks: The New Topographies of Cinema in Europe,”in European Cinema: Face to Face with Hollywood, Amsterdam: Amsterdam University Press, 2005, pp.82-107.红毯仪式作为电影节重要的组成部分,是电影节研究的一个分支,相应地也需放在围绕电影节的社会关系网络中考察。
红毯仪式是电影节的一种特定的符号行为,所展示的绝不仅仅是明星、奇观和八卦,而是以镜像/缩影形式在一小时左右时间展示了涉及电影节及电影产业发展的各个元素和群体,包括明星、制片方、专业组织、媒体、专家等,他们之间的社会关系及背后的权力运作关涉文化、商业和政治的多个面向。可以说,在电影节实践过程中,参与角逐的多重权力、相互交融的多方话语都体现在红毯仪式中。
作为一种在电影节的规则制度内被创造的仪式,红毯与大众媒体是相互建构的。因为重要的国际电影节红毯仪式的半公开性和地理局限性,红毯信息抵达大众视界的真正渠道是大众媒体。大众传媒,尤其是电视直播的规范与需要塑造了红毯仪式的内容。换句话说,红毯仪式是电影节在电影艺术范畴之外为媒体媚俗所准备的内容,在媒体传播过程中生产出娱乐价值、新闻价值、经济价值和专业价值。其生产过程内含了相关的社会关系和消费组织。
目前有关红毯的研究,大多聚焦在明星现象所构建的视觉文化、消费文化和传媒文化视域中的红毯奇观,*如Liz Czach, “Cinephilia, Stars and Film Festival,” Cinema Jounral, Vol.49, No.2, Winter 2010, pp.139-145; 郭盈伶:《视觉时代的“红毯文化”》,《文艺研究》2012年第12期;陈晓云、缪贝:《红地毯上的中国影星:身体表演、服装修辞与视觉政治》,《当代电影》2012年第8期;庞博:《“中国风”之风起风落——浅析女星的国际电影节红毯造型嬗变》,《当代电影》2015年第7期。总体上是在文化研究的范畴内进行,忽视了其中蕴含的政治经济权力的作用。西方电影节研究新的进展在方法论上强调系统和网络理论,与传播政治经济学的社会整体视角相契合,但是缺乏对红毯相关规制的政治经济学考量。因此,本文尝试以中央电视台电影频道(CCTV-6)和上海东方卫视对北京国际电影节、上海国际电影电视节红毯仪式的官方直播为分析文本,从传播政治经济学的视角考察电影节红毯仪式的生产和传播。对应传播政治经济学的三个关键词:结构化、商品化和空间化,从以下三个方面对红毯仪式进行分析:直播的议程设置、蔓延的商品化链条和空间的聚合。这三者分别是以专业、商业和政治的话语为支撑的,以此为线索,可以挖掘出红毯现象隐而不彰的内涵。
一、专业的话语:直播的议程设置
红毯仪式的符号行为发生在两个层面——现场层面和媒体层面。在现场层面,红毯仪式按工业流水线的方式进行其符号行为——各类明星从化妆间出发到“备场区”“集结区”和红毯现场,接受采访、拍照,进入礼堂,这一反复进行的行为过程,实际也包含此前化妆设计、媒体公关等各种工作流程。现场符号行为给传媒提供了大量专业及娱乐的新闻素材,并在大众媒体空间衍生出新一层的符号行为。相比多样化的纸媒和新媒体所提供的让各种身份的参与者作为叙述主体对电影节进行诠释或批评的空间,电视直播以其视觉性、完整性成为最接近红毯活动“原型”的再现方式,或者更准确地说,电视直播参与建构了红毯内容。这一点首先体现在红毯的议程设置上。
议程设置是电影节寻求政治参与,以提升电影和电影人在艺术、文化、民族以及社会政治领域中的意义的重要手段。*Valck, Film Festivals, p.211.电影节的议程设置包括多个层面,如对单元展映主题的设置,以及在高峰时段及中心影院播放的影片安排能影响电影节观众对电影题材、风格和类型的选择以及电影产业的生产方向;又如,回顾单元中对某位大师作品的集中讨论,能影响学界的知识生产。
红毯仪式的议程设置是以是否适合媒体直播为标准,在电影节的内涵和外延中选择某些主题和内容进行不同层次的展示和强调。例如,现场主持人会在出场明星中挑选重要人物进行采访。电视直播实际上对原生态的红毯行为进行了二度编撰——直播时导播镜头不断切换,以实现对现场的选择性呈现、省略和强调;同时,电视直播室里的主持人采访专家、导演,讨论相关的电影现象,对现场活动进行话题的再度挖掘和诠释。所有被展示的内容,包括作品、相关企业或机构,以及电影节环节本身,均是通过人物(明星)作为载体来呈现。
以2016年第六届北京国际电影节开幕红毯仪式为例。在议程设置上,首先安排吴天明导演的遗作《百鸟朝凤》的主创队伍出场,代表对老一辈电影人的尊敬和追忆;之后,安排各个类型片主创、流行歌手、网络新媒体、中外电影合作论坛等机构代表,以及国外名导演出场。主持人介绍出场明星、嘉宾所代表的影片及其制作背景,并对重要导演、制作人和电影研究学者进行专门采访,在其串场和采访中体现了支撑红毯议程设置的专业话语体系,包括新闻话语、艺术话语和学术话语。这些话语融合在直播的叙述中,表达了电影节的自我定位和主旨,也凸显了红毯议题的设置。如,在介绍小成本电影《我心雀跃》时,主持人解释北京电影节的定位是“关注小成本、独立制作、原创电影”;在介绍电影《进皇城》主创时,主持人又宣称电影节的目的之一是弘扬国粹、保护传统文化。这两个例子,均体现出电影节对肩负文化责任的定位和表达。而在对影片类型的介绍中,主持人话语中所使用的关键词“商业片、主旋律影片、军旅题材影片、小成本文艺片、青春剧、国家重点故事影片”,与国际上常见的电影类型分法,如歌舞片、战争片、喜剧片、恐怖片、犯罪片等,存在一定错位。后者的分类是基于资本主义电影生产的商业实践和经济策略,以消费为导向,提示了电影会满足何种类型的愉悦。*吉尔·内尔姆斯主编:《电影研究导论》,李小刚译,北京:世界图书出版社,2013年,第145-149页。前者的命名方式更侧重生产过程的规划性,如“主旋律”“国家重点”字样反映出选材对国家意识形态的考量;“军旅题材”与“战争片”的中性意涵不同,是对军旅生活的正面反映,同样体现了国家主流意识形态;“商业片”“小成本”突出的是投资方面的不同; “青春剧”的提法紧扣当下中国电影产业制作热点,但也暴露了该题材存在着投资过热、创作盲目跟风的问题。可以说,这种分类和定义既反映出当下中国电影产业对发展类型片的重视,又体现出中国电影产业在投资、认知和政策上的“中国特色”。此外,这次电影节红毯议程设置所凸显的议题还有:1. 新媒体在电影产业中的重要性。通过展示爱奇艺、微博、中外电影合作论坛的新媒体平台,暗示“互联网+”给电影产业带来的新机遇。2. 中外合作拍片的趋势。不过,除开中外合拍片和日本电影周参展片,本届红毯仪式中提到的其他将展映的外国影片只有三部。相对于“天坛奖”评委团的国际化程度(七位评委中只有一位来自中国),参展影片的国际化程度有待提高。3. 民营资本为中国电影产业带来的活力。一些原本处于产业下游播放渠道的民营资本,如万达,已参与到上游的影片制作上来,显示出中国电影产业发展的纵向一体化趋势。以上这些议题,都紧扣住当下中国电影产业的发展现状和趋势。
无论是北京电影节,还是上海电影节,都是由电视媒体和电影节组织共同设置红毯活动议程。红毯现场主持人由实行官方直播的电视台指派,现场的介绍、采访以及活动进度,皆由这些选派的主持人把控。相比之下,戛纳电影节和柏林电影节的红毯仪式上并没有设置此类统一把控现场的主持人,各媒体记者可以按照各自不同的议题进行采访(这也可能是外国媒体时常弄混中国明星的一个原因),其报道的多样性与北京、上海红毯报道中的整齐划一形成鲜明对比。中国红毯仪式的议程设置在表达电影节官方意图的功能上更加突出,这也是中国电影节作为国际电影节网络中的后起之秀,急需对外进行自我表达的一个体现。
红毯仪式除了通过具体的议题编排来诠释特定电影节在电影产业中的功能和定位外,在更宽泛的层面,它还可以通过为媒体准备可猎之“奇”来确立自己的风格。原生态红毯实践内含一对矛盾组合:仪式有周密安排和固定程序,即需要秩序;但成熟的红毯仪式又总是造出貌似的“自然”状态,以便在直播时抛出种种引人入胜的悬念,也提供更多可让媒体抓拍的细节、意外以制造话题。事实上,所有电影节的红毯仪式都处在“秩序”和“自然”这两端之间的某一点上,以此建立自己的风格。如果将中、西方电影节的红毯活动做一个总体比较,西方电影节红毯仪式的风格偏于自然,更具狂欢性质。如在戛纳电影节和柏林电影节的开幕红毯上,组织方的安排体现在灯光布置、现场大荧幕、安保、引导人员的工作上,而红毯走秀本身则体现出极大的随意性。明星们以充满个性的方式入场,如开着改装成旧式警车式样的私家车直抵现场,然后在红毯上任意位置接受各媒体采访,可长时逗留,也可快速路过,这就使红毯走秀更多地呈现为个体行为。明星个人化的走秀方式,为媒体提供了生动的素材库。如娱乐媒体就常常依靠捕捉明星间遭遇时的小表情,进行有关人际关系的八卦揣测。
相比之下,中国电影节对仪式流程控制严格,明星的入场方式、采访地点、前进速度、间隔距离基本被设定。这点尤其体现在2015年至2017年在室内举办的上海电影节红毯仪式上:红毯摆出常规舞台的空间结构,入场通道两面分别为墙和媒体,几乎成了为媒体准备的封闭型空间;组织者安排嘉宾前进、停止,前面的明星如果拍照时间长了,后面的就在两米开外的地方停下等待。机械的安排极大地避免了红毯上明星们可能有的“意外”情况,以及可以供媒体抓拍、制造话题的“野生”的场景。但对各类媒体来说,可猎之“奇”少,自由发挥的空间也就小了。同时,中国电影节的红毯亮相更多以团体、组织而非个人的形式出现,突出电影产业中生产组织的角色多过于强调明星个人魅力。
红毯仪式通过各自特殊的议程设置,能够排除在形式上的趋同性和内容上的扁平肤浅。基于不同的电影节生产环境——政治经济文化生态,不同的红毯仪式生产出差异化符号,表达和定义了电影节的个性,并与电影节其他层面的议程设置一起,决定了电影节观众所关注的话题。
二、商业的话语:蔓延的商品化链条
商品化是将使用价值转换为交换价值的过程。电影节红毯行为展示并生产出一系列的商品,包括华服珠宝、明星的身份和身体、红毯时空、媒体报道和受众注意力。在这个商品序列中,可以发现一个蔓延的商品化过程,以及支撑红毯运转的商业话语和经济秩序:华服珠宝衬托的明星形象即其身份和身体被卖给需要注意力的电影节,电影节红毯时空被售卖给媒体和赞助商,媒体报道出售给受众,而受众的注意力再被转卖给赞助商家。在此链条中,除了华服珠宝外,其他商品的使用价值都是社会建构的结果。可见,传播的过程和技术扩大了商品化的范围,*文森特·莫斯可:《传播政治经济学》,胡春阳等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3年,第169页。其中一个突出方面是劳动过程——从明星走秀、红毯组织、媒体报道到受众观看,均被商品化。
传播政治经济学进一步将这种商品化趋势细分为外在商品化和内在商品化,前者指将原本非商品化的领域商品化,后者指一种商品在另一种商品的创造过程中直接产生。*文森特·莫斯可:《传播政治经济学》,第181页。红毯仪式中同时存在这两种商品化趋势。
红毯仪式外在商品化的突出例证就是身体。红毯上呈现的明星身体是通过美容技术、仪态训练、设计包装而驯化的身体,是已超越私人范畴、供公共文化消费的身体。*参见郭盈伶:《视觉时代的“红毯文化”》,《文艺研究》2012年第12期;陈晓云、缪贝:《红地毯上的中国影星:身体表演、服装修辞与视觉政治》,《当代电影》2012年第8期。身体在成为产品展示平台的同时,其本身也成为电影工业及其周边产业的产品——和明星的身份标识一样,可以出售给代言的品牌,明星的身体及其身份因此被商品化。
红毯仪式内在商品化的例子是红毯时空。因为明星的身份和身体被商品化,其所存在的一定的红毯时空也被商品化,作为稀缺资源,被卖给媒体和赞助商。前者用一定的资质和成本换取报道权,后者的购买体现为红毯仪式上的各类实物的和象征性的广告。例如,北京电影节和上海电影节红毯仪式均用品牌汽车作为重要的舞台背景,明星签名板上也遍布广告标识。相比之下,奥斯卡电影节、戛纳电影节和柏林电影节的红毯空间上并没有如此明显的广告。其中,柏林电影节开幕式的赞助商广告通常是由开幕式主持以戏谑口吻播报,呈现出广告的非正式和个性化风格,也将赞助商和电影节组织进行了角色区分。但是,物的广告仍会在红毯上通过明星形象(包括其穿戴和代言)间接实现。一旦将明星、媒体和广告抽离,红毯时空这个商品也将不存在。
值得一提的是,在某些商品内部,也存在内在商品化过程。比如明星礼服常会采用民族元素设计,以在国际电影节红毯上标识身份、吸引注意。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在2010年第63届戛纳电影节开幕式上,中国演员范冰冰穿的“龙袍”。“龙袍”将皇族文化传统——非商品化价值,引入礼服——商品化的价值中,利用传统文化要素的非商业化的价值扩展其交换价值。“龙袍”成功地找到一个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之间的扩展点,吸引了大量关注。但当时媒体争论的焦点围绕在该现象背后的“权力关系”,即,是什么允许这样的珍稀文化价值被转换成交换价值?和电影节其他的展示空间不同,在红毯空间的运转中,商业权力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了公共权力。正是在红毯经济中所蕴含的商业权力使这种价值转换可能且有效。
媒体通过售卖报道给受众,实现一部分交换价值;同时又通过参加明星举办的媒体发布会、采访处于上升期的明星,将媒体的关注卖给明星,实现另一部分的交换价值,并间接创造剩余价值。相应地,受众注意力又是媒体卖给电影节和赞助商的商品。最终红毯上形成“华服珠宝-明星-红毯时空-媒体报道-受众注意力”这个蔓延的商品化链条,而链条中的后者皆因前者的存在而存在。
红毯仪式的内在和外在商品化链条展示了围绕电影节的经济秩序。通过蔓延的商品化过程,明星、电影生产商、各品牌赞助商、电影节平台以及媒体均能获益。因此,红毯仪式的完成过程也可以被理解为一个商品交换过程,在实现各种商品交换价值的同时也形成了围绕红毯的各种社会关系。
在这个商品生产、交换及社会关系的形成过程中,空间发挥了重要作用。基于福柯在微观政治层面对空间权力的分析来看,*参见米歇尔·福柯:《空间、知识、权力》,包亚明主编:《后现代性与地理学的政治》,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1-18页。红毯空间是通过将明星置于视觉中心——负责发出信息,让其他群体(媒体、观众)处于观看的位置——负责接受和传播信息,建构了参与群体之间的基本社会关系。这一关系中实际蕴含着一个审美评价体系,通过对审美评价的掌控,红毯空间实现了对明星和围观群体的规训和塑造,使明星的身体和身份拥有了商业广告的价值。最终围绕红毯这个电影节的次生事件,形成了一个处于交换关系中的社会群体——作为电影节群体下的次级群体,二者交叉但不重合。
而在政治经济的宏观层面,红毯空间所体现的空间聚合效应,则指涉了城市内部及城市之间的资源分配和文化经济秩序再生产。
三、政治的话语:空间的聚合
按照福柯的观点,伽里略式的无限延伸的空间已被基地(site)网络所取代。在现代空间的图式中,各个基地都是在相互的关系中定位自身,单个空间的意义被放置在这种相互关系中,组成某种结构和序列。*米歇尔·福柯:《不同空间的正文与上下文》,《后现代性与地理学的政治》,第19-21页。城市作为电影节的实在物理空间,便是电影节产业的基地,是确立电影节风格和文化的物质基础。电影节基地之间存在等级制的网状联结,而红毯空间是单个电影节基地的中心和焦点。
电影节基地是一个资源聚合的空间,其中既有集中的经济交易、文化交流,也有政策制度和物质条件保证,可通过信息的有效聚集,激发学习和创新的效应,形成以文化习俗和消费习俗为支撑的创新活力的生产体系。*艾伦·J·斯科特:《城市文化经济学》,董树宝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22、43页。同时,每个空间本身都是地域化和全球化趋势共同作用的结果。传播政治经济学的观点认为,商业集中的重要形式是空间和所有权的聚合,而权力在生产新空间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使城市内和城市间产生新的空间层级结构。*文森特·莫斯可:《传播政治经济学》,第224页。具体而言,以红毯空间为代表的电影节空间的生产可分为三个层次:1. 城市内部社区的建造和规划;2. 城市本身蕴含的区域化和全球化的矛盾集合;3. 城市之间的资源再分配。
首先,电影节作为重要的文化产业活动,可构筑城市的文化记忆,持续吸引有创造力的年轻人打造文化社区,聚集他们的消费力,繁荣地方经济。例如,二战后欧洲的电影节曾对举办城市的经济复苏起到过巨大作用,而自1970年代起电影节的举办更日益显露出对旅游的强大吸引力。*Janet Harbord, Film Cultures, London: Thousand Oaks, 2002, pp.59-75.进入信息时代,电影节通过与大众传媒的高频互动,在打造城市的文化品牌、繁荣城市文化产业中的作用不可小觑。因此在各个举办城市,电影节早已成为城市规划的重要考量因素。通过建造、设计和规划围绕电影节活动的文化社区,举办城市可以有效地聚集和保留电影节所激发的文化创造力,形成学习和创新的区域,使空间结构成为生产力一部分。*参见亨利·列斐伏尔:《空间:社会产物与使用价值》,包亚明主编:《现代性与空间的生产》,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49页;汪民安:《身体、空间与后现代性》,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101页。例如,从2015年起连续三届北京电影节的主要活动都被安排在怀柔国家影视产业示范区,就极大地提升了该地区在中国影视产业中的重要性。电影节使空间聚合效应周期性出现,*艾伦·J·斯科特:《城市文化经济学》,第31页。通过对文化创新活力和经济消费力的聚集,可以助推城市文化经济的发展,实现城市复兴或转型。因此,举办城市的政府部门往往会直接参与电影节的筹划。如北京电影节的主办方之一就是北京市政府。在历届北京国际电影节的开幕仪式上,北京市市长或市委书记均以电影节组委会主席的身份发表了致辞,显示出政府对电影节发挥城市文化建设力量的重视。因此,呈现在大众视野的红毯仪式以及整个电影节是电影界、传媒界和政府部门合作的结果。
其次,电影节的举办城市均展现出国际化和地域化两个纬度。红毯仪式通过明星,尤其是国际影星的出场,展示电影节网络的国际化联结,同时又通过城市地标显示出地域性,如历届北京电影节开幕式的举办地——国家大剧院、天坛公园、雁栖湖国际会展中心以及国家中影数字制作基地,都是可以代表北京及其文化软实力的具有标志性的地点。而历届上海电影节开幕式的主要举办地则是上海市城标中心——人民广场的上海大剧院。
北京电影节和上海电影节集合了地域性和国际性优势,发展势头迅猛,大有一抢长春电影节和金鸡百花电影节等老牌电影节风光的态势。作为电影节的举办城市,北京、上海与德国柏林相类,皆立足于国际大都市的地域优势,希望通过举办电影节从政治经济中心转型为国际文化交流中心,这与戛纳等旅游城市、鹿特丹等老牌工业城市的发展轨迹不同。而柏林电影节也曾经是西欧电影节中的后起之秀,与北京电影节和上海电影节如今在国际电影节网络中所处位置相似。电影节结合了国际化和地域化两个面向,其在文化产品的构成方面及在生产过程中更多地打上了地理环境的烙印,由此形成的文化产业地理垄断力量会提升城市的竞争优势,使城市影响力和其文化产品更好地扩散到全球。*艾伦·J·斯科特:《城市文化经济学》,第6页。城市通过电影节进行国际文化交流,同时也保留着自身独特的文化传统和习俗,既发挥对外的影响,又接受着外来影响,改造他者的同时也被改造。上海电影节作为国内第一个A级国际电影节,在红毯议程设置中既展示出国际化的一面,又多处突出其地方性,例如,现场主持鼓励外来嘉宾用上海方言打招呼,或在介绍出身上海的明星时,强调其又“回到上海”。可以说,上海电影节发挥了地域优势,利用了国际资源,并充分吸收了本国电影产业的营养,体现出民族性、世界性和多样性的融合。
2011年创办的北京国际电影节,同样是国际化和本土资源的双向优势促成其快速成长。北京作为国际大都市,拥有无可比拟的文化资本。早在第一届北京国际电影季(北京电影节雏形)活动中,包括威尼斯电影节、柏林电影节主席等22位全球重要电影节的负责人就被请到北京,共商北京国际电影节的发展方向。*《第一届北京国际电影季筹备就绪》,http:∥news.cntv.cn/20110420/104659.shtml,2017年5月5日。北京还拥有包括电影频道、电影学院、大小电影制作公司和文化创意企业等从媒体、人才、生产力到周边服务的系列专业资源,构成了成功发展电影节的基础。同时,北京更拥有充足的政治资本,包括政府实际的政策支持和象征性的政治资源。后者重点体现在举办地点的象征意义上,当城市地标隐含有一定政治意义时,由此形成的地域氛围可以影响观众对电影节的解读。*Harbord, Film Cultures, pp.59-75.如在2015年第五届和2016年第六届北京电影节上,红毯直播中多次插播雁栖湖国际会展中心的大全景,作为曾经的APEC会议举办地,这个“天坛”式样的建筑使北京电影节拥有了“传统与现代对接,中国与西方对接”的平台意义,使观众对北京电影节的解读与“大国崛起”联系在一起——从政治和经济领域的崛起,延伸到文化领域的崛起。当然,北京也明确提出过建造“东方影都”的构想。*《第七届北京国际电影节打造中国电影新高度新格局新地标》,北京电影节官网,http:∥www.bjiff.com/bannergdtp/201704/t20170423_36510.html,2017年5月5日。巧合的是,2016年北京电影节红毯上介绍的影片《纽约人在北京》,在片名上是1994年大热的电视剧《北京人在纽约》的翻转,似乎也应和着北京、中国电影乃至中国的上升和崛起。
特殊地域的政治支撑,往往也伴随着一定的话语限制。北京作为首都,和“中国”意象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致使其电影节话语中更多地表达出对文化崛起的责任感,相比之下上海电影节的话语则更为轻松自由,这点尤其体现在对嘉宾的采访和翻译上。在2015年北京电影节开幕式上,美国影星施瓦辛格的发言在字幕翻译中被多处修改,加入了发言中没有提到的内容,如“去年,中国的票房收入增加了36%”,将施瓦辛格从自身角度出发的演讲,改成了赞扬中国电影产业的角度。在2016年北京电影节的红毯仪式上,当奥地利导演瓦尔兹接受采访时,其话筒音量突然变小,主持人讲话时音量又恢复正常。反复如此,使观众只能听清主持的翻译,但翻译大大减少了瓦尔兹原发言的信息量。上海电影节红毯上对外籍嘉宾的采访,问题集中在方言模仿、与中国合作和对上海印象三大版块,并未出现类似的强势翻译情况。可见,城市的规划、经济策略、文化特殊性乃至地缘政治历史,均会参与塑造电影节的风格特征,使隐含的政治性成为解读电影节个性和议程设置的一个面向。
再次,电影节的空间聚合重塑了城市间的力量对比。随着电影产业爆发式增长,中国电影节体系在形成功能性网络的同时,也形成了一个可供错时游览的空间版图——4月北京电影节、6月上海电影节、8月长春电影节,以及9月在各大城市轮办的金鸡百花电影节。该版图显露出中国电影节产业在新近发展中向大都市聚合的趋势。
大城市作为产业和商业聚集区,是文化和经济交互作用的“融罐”,拥有“专业化的经济功能”和政治功能,聚集了不同性质的生产单位、精细化的生产体系、既提供管制又提供支持的政治环境及密集的社会关系。电影节相关产品的生产和消费需依靠大都会的时尚资源(明星)、信息资源(娱乐八卦)、受众资源(粉丝群体)以及其他社会服务系列。而当电影节产业在一个城市空间中发展起来时,其密集的劳动分工方式和“零散化且交易密集的运作模式不断重复组织和塑造独特的城市人文和文化资源。……这个资源在生产行动中不断地创造出新的自发的学习效应,这些效应积累在城市蜂窝状聚集区中”,*以上征引参见艾伦·J·斯科特:《城市文化经济学》,第5-7、6、127页。并由此导致了城市文化经济学中的“锁入效应”,即较早发展某产业的城市会逐渐形成地域垄断优势,使后起城市难以超越。*参见Paul A. David, “Clio and the Economics of QWERTY,”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75, No.2, 1985, pp.332-337;艾伦·J·斯科特:《城市文化经济学》,第28页。
当然,“锁入”与“锁出”*有关“锁出效应”,参见艾伦·J·斯科特:《城市文化经济学》,第28页。常是并置的,空间聚合和空间闲置往往并存。传播政治经济学理论认为,“集中和分散是构成当代经济地理学结构性转变的同一个过程”。*文森特·莫斯可:《传播政治经济学》,第224页。中国电影节的数量受中宣部调控,这就形成了对举办地的选择和淘汰。例如,曾经的珠海电影节虽然有地方政府的不断推动,却在1998年因为中宣部整顿电影节市场被停办,至今未能成功重办。有限的电影节资源与特定城市的组合,实现了电影产业的空间重置和地区文化实力的消长,并扩大了影视文化产业的地域差距。拥有电影节品牌的城市,能聚集更多文化产业的资源,从而强化了这些城市的相对优势,同时也形成了城市之间在电影产业发展上的层级结构。在被超越的城市中,包括一些有优秀的电影制作传统的城市,如西安,因为缺乏资源的聚合,在电影产业发展的新形势下逐渐势弱,成为在重组的产业空间中被闲置的那部分。因而,电影节实践是以一种城市间不均衡的态势助推了文化产业的发展。
四、结 语
作为电影节的衍生产品之一,红毯仪式直播宛如一个镜像,映照出电影产业发展的种种。红毯仪式是媒介权力展示的场所,是娱乐产业各种力量的角力舞台。红毯仪式通过展示一个政治经济文化的关系网,完成了红毯自身和电影节意义的社会建构,提供了专业、商业和政治的多重话语相互竞争的场所。红毯仪式的参与者拥有多重身份,既是活动的生产者,也是消费者、艺术鉴赏者和政治体验者,并在实践中不断调试自身定位。市场和政治力量在红毯仪式上,乃至整个电影节的成型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而由导演、艺术家、学者所代表的专业力量,依据电影节对社会、文化价值的追求,平衡市场和政治力量,保证此二者不因过度行使权力而损伤电影节的专业价值。专业、商业和政治力量在妥协中组成合力,共同塑造了红毯仪式及整个电影节。
电视直播以媒介视角构筑了大众视野中的红毯仪式,营造了一个让评论、八卦、猎奇聚集的公共空间。直播将参加电影节狂欢的有限的在场观众,扩大为理论上无限的不在场的电视观众,将电影节的受众从中高端知识阶层和消费阶层转向包括低收入者的广大人群,实现了媒介和阶层的双向跨越,在电视媒体建构的“想像的共同体”中,建立起大众对民族国家的文化身份和文化地位的认知。作为电影节文化商品的“图像浓缩”,红毯仪式直播展示了纠缠于其中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利益,成为文化商品政治经济学的生动实例。
(责任编辑:庞 礴)
The Production and Transmission of Film Festival's Red Carpet Ceremon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olitical Economy of Communication
Yu Wanting
Film festival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cultural industry. Among film festival's sections, the Red Carpet and its transmission have formed a special mass cultural spectacle. What the Red Carpet shows is far more than the stars. It demonstrates all the social groups related to film festival and the film industry, the relationship among the groups and the cultural, commercial, political power function behind. The agenda setting of Red Carpet ceremony is supported by professional discourse; the commodification chain shows the function of commercial discourse; and space aggregation and rearrangement are imbedded with political discourse. The Red Carpet ceremony is the result of the contending powers and blending of different discourses.
film festival, Red Carpet, political economy of communication
喻宛婷,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副研究员(成都 610064)
四川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研究专项项目“中德电影节产业比较研究”(skgb201604)
J943
A
1006-0766(2017)04-0169-08
§艺术理论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