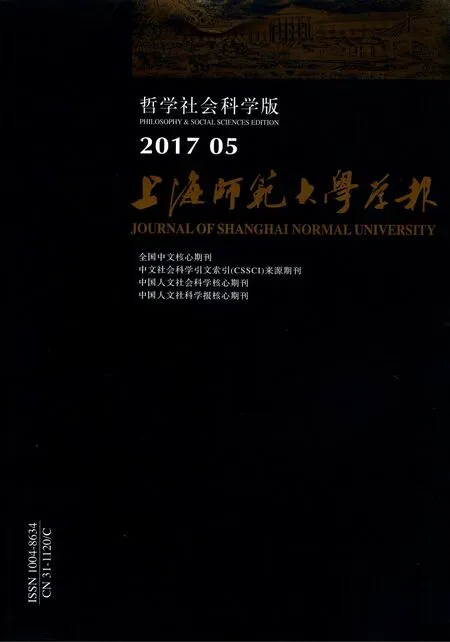契约论并不排斥残疾人的正义权利
——驳努斯鲍姆对罗尔斯的一个批评
任 俊
(江南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江苏 无锡 214122)
契约论并不排斥残疾人的正义权利
——驳努斯鲍姆对罗尔斯的一个批评
任 俊
(江南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江苏 无锡 214122)
当代著名政治哲学家努斯鲍姆对罗尔斯的契约论提出了系统的批评,指出契约论的某些核心要素和理论预设导致它无法容纳残疾人的正义权利。然而,通过对“大致相似”“相互性”“道德能力”等观念的澄清,可以发现,努斯鲍姆的批评对罗尔斯的理论并不构成致命的威胁。如果得到恰当理解的话,罗尔斯的契约论仍然可被视为一种具有包容性的正义理论进路。
契约论;残疾;正义;罗尔斯;努斯鲍姆
在政治哲学史上,契约论是一种富有影响力的理论。经典的契约论主要回答的是政治正当性问题,主张通过公民实际的同意,来论证国家或政府统治权力的正当性,解释公民政治义务的来源。20世纪中期,罗尔斯复兴了契约论的传统,以此作为分析正义问题的一个思想框架和理论进路。当代著名政治哲学家努斯鲍姆(Martha C.Nussbaum)对这一正义研究的进路提出了系统的批评,指出契约论的某些核心要素和理论假定导致它难以解决当前面临的一些重要而紧迫的正义问题,尤其是无法为残疾人的基本权利提供辩护。①通过义理分析,本文试图回应努斯鲍姆的挑战,表明契约论能够具有比批评者设想得更大的包容性,它并不削弱残疾人的正义主体地位。这番讨论不仅有助于我们继续深化对罗尔斯的理解,而且能够进一步提升契约论的理论潜力。
一、契约论和残疾人问题
当代契约论有不同的版本,高蒂尔(David Gauthier)沿着霍布斯主义的方向发展了一种道德契约论,而罗尔斯继承的是康德主义的传统。之所以以罗尔斯为矛头所向,是因为在努斯鲍姆看来,相比而言,罗尔斯的契约论更具有直觉上的吸引力,它是我们目前所拥有的最强有力的正义理论。即便如此,努斯鲍姆认为这个理论在某些方面、某些领域仍有严重缺陷。尤其是,它无法妥善地解决残疾人的正义问题。由于罗尔斯融合了道德哲学和政治哲学史上很多重要的思想观念,这些源自不同传统的观念也不可避免地造成其理论内部的紧张。
1.正义的环境
首先,罗尔斯吸收了休谟关于“正义的环境”(circumstance of justice)学说。所谓“正义的环境”,是指“使人类合作得以可能和必要的一般条件”。[1](P109)“除非这些环境因素存在,就不会有展现正义德性的机会;正如没有伤害生命和肢体的威胁,就没有展现勇敢的机会。”[1](P110)正义的环境包括客观环境和主观环境。为简化起见,罗尔斯强调得比较多的是客观环境中的中等匮乏条件和主观环境中的相互冷漠条件。然而,客观环境中有一点是罗尔斯没有详细阐述而被努斯鲍姆反复讨论的,那就是:人们在身体和精神能力上大致相似(roughly similar)。努斯鲍姆认为,如果这种能力上的大致相似是适用正义概念的必要条件,那么,对于那些能力明显弱于所谓“正常人”的残疾人来说,就被排除在正义的关系之外了。按照这种“正义的环境”观点,由于能力上和“正常人”存在巨大的差异,残疾人无法享有基于正义的权利;我们对残障人士负有道德责任,但这仅仅是出于仁慈,而不是正义的要求。这个结论和我们的道德直觉是相违背的。根据直觉信念,正义的权利和能力大小并无直接关联。残疾人力量弱小这个事实,并不能取消他们的正义诉求。此外,休谟主义的观点和罗尔斯理论中的康德主义之间存在张力。罗尔斯在《正义论》开篇明确指出:“每个人都拥有基于正义的不可侵犯性,这种不可侵犯性即使以社会整体福利之名也不可逾越。”[1](P3)也就是说,正义无条件地适用于社会上每一个人,每个人都应该得到正义对待。不管是普通人还是残疾人,都享有基于正义的权利。
2.互利
根据努斯鲍姆对社会契约传统的理解,互利的观念具有核心意义。传统契约论通常假定,人们是为了互利而进行合作、订立契约的。努斯鲍姆认为罗尔斯在这点上追随契约论传统,互利的观念在罗尔斯的契约论中同样占据核心位置。她这样来解释罗尔斯在《正义论》中表达的观点:“基于互利的理由,合作比不合作更可取。”[2](P60)合作的目的是互利,而这种相互利益是人们在非合作的情况下无法获得的。相比非合作的状态,合作能够改善每一个人的处境。如果没有这种对相互利益的期待,就没有契约的形成,人们宁可选择留在初始状态之中。尽管“无知之幕”的设计能够屏蔽掉很多与道德无关的信息(例如自然天赋、家庭出身、社会阶层、种族等),确保各方选择的结果公平对待每个社会成员的利益,进而发挥某种道德观念的作用,“但一谈到为什么应当有这样一个契约的问题,答案归根到底仍然是互利,而不是仁慈或对正义的热爱”。[2](P58)然而,如果合作的目的和意义仅仅是互利,那么这似乎就意味着,那些与之合作无利可图的人就不应被视为合作者,我们在设计社会基本结构的正义原则时不必把他们的利益纳入考虑。社会上存在很多患有严重生理和精神残疾的人,我们很难指望他们对我们的利益有所推进。按照契约论的逻辑,残疾人的正义权利难以得到保障。
3.人的观念
努斯鲍姆指出,基于契约各方自由、平等、独立的假定,传统契约论没有将残疾人纳入到立约者群体,而这点也将导致对残疾人不利的后果。“社会契约传统将两个原则上截然不同的问题——‘社会基本原则由谁来设计’以及‘社会基本原则是为谁而设计’——混为一谈。”[2](P16)根据传统契约论的这种结构性特征,参与制定基本正义原则的人,同时也是基本正义原则为之制定的人,两者之间的关系受到被选择的原则支配。换言之,被排除在立约群体之外的残疾人,也就不是基本正义原则保护的对象,正义原则并非为他们而设计。
努斯鲍姆注意到,罗尔斯的契约论比传统契约论更为精细,“由谁”和“为谁”的问题在他那里一定程度上得到了区分。在《政治自由主义》中,原初状态中的立约者被刻画成良序社会公民的“代表”。原初状态的各方是正义原则的选择者,良序社会的公民是正义原则的适用对象。然而,在努斯鲍姆看来,这并不表明残疾人的权益得到了充分的考虑。因为,罗尔斯假定契约各方代表的公民必须是充分合作的社会成员。罗尔斯写道:“既然我们从社会作为公平的合作体系的观念开始,那么,我们假定,作为公民的个人拥有使其成为社会合作成员的一切能力。对我们而言,这样做可以获得一种关于什么是政治正义基本问题的清晰而有条理的观点。这个基本问题就是,具体规定公民——自由平等且终其一生都是正常和充分合作的社会成员——之间社会合作条款的最恰当的正义观念是什么?”[3](P20)努斯鲍姆认为,“充分合作假定”(the fully cooperating assumption)意味着,在设计社会基本结构的原则时,契约各方只会考虑能够充分参与社会合作的人的利益,而那些不具有合作能力、患有严重残疾的人的利益无法得到公平对待。由于能力上的缺陷,残疾人不具有正义主体的地位。就此而言,罗尔斯的契约论似乎没有为残疾人的正义权利留下空间。
努斯鲍姆指出,尽管罗尔斯不赞同康德的形而上学观点,但他关于人的观念深深打上了康德的印记。罗尔斯把公民政治平等的基础建立在两种道德能力之上。第一种道德能力是正义感的能力(a capacity for a sense of justice) ,对应着罗尔斯所说的“讲理”(reasonableness),是指能够理解、运用某种公共的正义观,并愿意按照他人也能认可和遵守的正义观进行活动;第二种道德能力是善观念的能力(a capacity for a conception of good),对应着罗尔斯所说的“理性”(rationality),是指能够形成并修正自己的善观念,且采取最有效的手段实现这种善观念。[3](P19)显然,和“充分合作假定”一样,这种理性主义的人的观念也将残疾人(尤其是患有严重精神残疾的人)排除在外了。根据努斯鲍姆对罗尔斯的解读,“有严重精神残疾的人,缺少最低限度的道德能力,丧失了平等的资格”。[2](P133)
总之,努斯鲍姆对罗尔斯批评的要点就是:契约论中的三个理论预设——正义的环境、互利、人的观念——都从逻辑上导致残疾人在正义语境中的边缘化,削弱了他们作为正义主体的地位。下面,本文将分析指出,在努斯鲍姆提炼出来的这几个主要观念中,有些是对罗尔斯的误解,有些经过重新阐释后仍然可以得到辩护,契约论作为正义问题的研究进路可以容纳残疾人的正义诉求。
二、何谓“大致相似”?
努斯鲍姆对“正义的环境”学说的批评集中于人们身体和精神能力“大致相似”的假定。首先需要指出的是,这个假定不是罗尔斯强调的重点。罗尔斯只是在《正义论》中对此一笔带过,而在之后的著作中基本没有提及。例如,在《政治自由主义》中,他这样写道:“正义的环境有两种,一种是中等匮乏的客观环境,另一种是正义的主观环境。后者一般来说就是多元论的事实。”[3](P66)同样,在《作为公平的正义:重新阐述》中,罗尔斯在论述正义的环境时,也只提到了资源的中等匮乏,以及合理多元主义的事实。[4](P84)也就是说,只要一个社会中拥有不同的完备性学说和良好生活观念的人,对有限资源的划分提出相互冲突的要求,正义的问题就产生了。②
当然,尽管罗尔斯在后期的文本中没有强调“大致相似”的假定,但并不意味着他放弃了这个契约论的理论预设。而努斯鲍姆的批评仍然值得我们思考:“大致相似”的假定是否意味着取消了残疾人的正义主体地位?
努斯鲍姆的推论可以概括如下:(1)前提:人和人的生理及精神能力“大致相似”,是正义关系产生的必要条件(罗尔斯的“正义的环境”学说);(2)前提:残疾人和“正常人”在能力上有显著差异;(3)结论:残疾人不在正义的关系之中。争论的焦点在前提(2)。要想避免努斯鲍姆从“正义的环境”学说中引申出来的反直觉的结论,就必须论证:就能力而言,残疾人和“正常人”在某种意义上是“大致相似”的,我们和残障人士之间的差异没有通常想象得那么大。这里的关键是,如何理解罗尔斯所说的“大致相似”?
关于“大致相似”,罗尔斯在《正义论》中有一段值得重视的表述:“这些个人在身体和精神能力上大致相似;或无论如何,他们的能力旗鼓相当,任何一个人都无法支配所有其他的人。他们易受到攻击,每个人的计划都容易受到其他人合力的阻止。”[1](P109~110)从这段话可以看出,罗尔斯是在一个很弱的意义上解释“大致相似”的。只要社会中没有一个人强大到能够支配和奴役所有其他人的地步,这个社会的人们就可以算作能力相当。可以说,不管是过去、现在还是可预测的将来,任何一个人类社会都能满足这个条件。一个人的力量永远无法超越其他所有人的合力。残疾人固然不可能做到这一点,正常人也无法做到。一个人就算在体力和智力上都表现出无比的卓越性,他也只是凡夫俗子,不可能单凭一己之力为所欲为。在无法驾驭所有其他人的意义上,正常人和残疾人是“大致相似”的,这一点并不奇怪。
我们通常容易夸大正常人和残疾人之间的差异。麦金太尔批评西方道德哲学假定道德主体一直健康、独立、理性、毫无困扰,而对人的脆弱性和依赖性缺少应有的重视。他指出:“在考虑残疾问题时,我们倾向于把那些‘残疾人’视为‘他们’而不是‘我们’,视为一个分离的群体,而不是我们自己曾经是、现在有时是、将来可能是的样子。”[5](P2)事实上,正如已故作家史铁生所说,如果残疾意味着不完美、困难和阻碍的话,我们每个人都是残疾人。
如果我们把残疾理解成不同程度、不同类型的能力缺失,那么我们每个人在人生的某个阶段都是残疾的。这一点在幼年和老年格外明显。当人们处在幼年和老年时,都可能会存在一定程度的缺陷或障碍:不能随意地四处走动、不能从事基本的家务活动、不能和他人进行顺畅的交流……但即使在生命的中间阶段,我们的生活也会经常出现无能为力的情况。大多数人都可能会受到疾病的折磨,愈演愈烈的环境污染加剧了这一风险。严重的疾病会损害我们的身体和精神能力,使我们无法正常地生活和做自己想做的有价值的事情。生命在各种各样的苦难面前显得非常脆弱。“能力有限”是每一个人都不得不面对的事实,无论是残疾人还是正常人。也正是因为人的脆弱性、有限性这个事实,人们才迫切需要同心协力、相互合作。如果每个人都强大、自足,社会合作就无从谈起。人要生存下去,更不用说获得幸福,都不可能离开他人的支持。就脆弱性和依赖性而言,残疾人和正常人是“大致相似”的。和残疾人一样,正常人也需要依赖他人的帮助来应对生活中的麻烦和痛苦。如果我们从这个角度去理解罗尔斯所说的“大致相似”,那么,“正义的环境”就不像努斯鲍姆所认为的那样排斥残疾人。正义关系所要求的那种人们彼此之间的“大致相似”,并不意味着残疾人不拥有正义主体的资格。
三、互利和相互性(reciprocity)
众所周知,当代契约论的发展有两种进路,分别继承了霍布斯和康德的传统。高蒂尔是霍布斯主义契约论的坚定捍卫者,他在一篇回应批评的文章中总结了自己的核心观点:“虽然我们不应假定,实际的道德实践和社会制度来自于协议,但我们可以认为,如果个人是完全理性的,每个人都想促进自己的利益(或实现他的实质性目标),且能够事先通过自愿的全体一致的协议来集体确定互动的条款和条件,那么,对原则、实践和制度——它们以约束个人的方式支配和架构了人类互动——的恰当的证成性检验(justificatory test)就是,看它们是否将被这些个人所接受。契约论者认为这个检验既提供一个理性的证成,也提供一个道德的证成。”[6](P324)
在高蒂尔的契约论中,理性个人订立契约的目的是互利。正是为了实现各自的利益、改变自己在非合作状态下的不利境地,各方讨价还价并相互妥协。不难看出,高蒂尔是在日常意义上使用“契约”概念的。我们在日常语言中所说的“契约”主要发生在经济领域,它显示的就是这样一副图景:人们基于各自利益的考虑,经过谈判协商,最终达成协议,形成一种具有合作关系的联合体(association),实现经济上的互利互惠;如果不能从他人那里获利,就没有订约与合作的必要。
由于明确将互利视为合作的意义,高蒂尔版本的契约论就很难逃避努斯鲍姆的批评。事实上,高蒂尔承认,他的理论很难解决对残疾人的关怀问题。他甚至认为:“这样的人不在以契约论为基础的道德关系之中。”[7](P18)虽然努斯鲍姆的批评对高蒂尔的观点构成了有力的挑战,但这个批评不适用于罗尔斯。因为,罗尔斯不像高蒂尔那样在通常的意义上运用契约的观念。罗尔斯区分了以规范社会基本结构的正义原则为内容的初始协议(initial agreement)和在社会基本结构内部订立的特殊协议(particular agreements)。[3](P275~278)
在一个社会基本结构内部订立的特殊协议,尤其是经济领域中的协议,建立在各方的谈判能力基础之上。是否达成协议、参与合作,取决于各方的选择。如果经过审慎的计算和权衡之后,发现无利可图,人们就可以拒绝进入这种合作关系。而在对社会基本结构的原则本身进行集体选择的初始协议中,各方的社会成员身份是给定的。人从一开始就被设定为社会性的存在者,不合作不是一个可行的选项。诸如为什么要合作、合作的目的是什么之类的问题,根本就不会产生。真正相关的问题是:什么样的合作方式是正义的,合作产生的利益和负担应当如何分配。与传统契约论中的“自然状态”相区别,原初状态不是一个有显著缺陷、有待改善的非合作状态,不提供一个计算个人利益得失的基点;它是思想实验和分析装置,赋予我们一种思考正义问题所需要的道德的视野。这样,通过区分特殊协议和初始协议,我们就可以清楚地看到:互利并非罗尔斯契约论中的主导观念。
尽管罗尔斯在《正义论》中将社会描述成“为了互利的合作冒险”,[1](P4)但他后期放弃了这种提法,转向“社会作为公平的合作体系”的理念。③在罗尔斯看来,规范的社会合作有三个基本特征:首先,社会合作受到公共接受和认可的规则与程序的指导;其次,社会合作包含公平的合作条款;第三,合作者的理性利益(rational advantage)得以实现。[4](P6)这种规范的合作观表达了一种相互性理念,即“所有参与合作并按照规则和程序的要求履行职责的人,都应当以恰当的方式获益,而这种恰当性是由一种恰当的比较基准来衡量的”。[3](P16)罗尔斯认为,相互性对社会合作来说具有核心意义。如果一个人的理性利益没有得到公平地对待,那么就意味着他被剥削、利用了,而不是真正地参与社会合作。按照相互性要求,每一个合作者,不管其出身、性别、种族、信仰是什么,只要对社会合作做出了贡献,都有权利享有公平的分配份额。每个合作者都应从社会合作中获益,并不是说作为合作的条件每个人都应从其他每个人那里获益。这一点使相互性区别于互利。相互性在保护合作者正义权利的同时,并不意味着将不能提供利益的弱势群体从正义的关系中排除出去。
罗尔斯也明确指出:“相互性的观念和互利的观念不是一回事。”[3](P17)相互性要求合作者从社会合作中获益,但必须是以一种在道德上可以辩护的方式获益。相互性内在地体现一种道德要求,而互利和不公正、剥削是相容的。[8](P404)达到了相互性,并不意味着实现了互利。有时,相互性的实现恰恰是以牺牲互利为代价的。假设有一个贫富悬殊的社会,且其财富的不平等主要是由家庭出身而不是个人的努力造成的。现在,其决策者根据罗尔斯的两个正义原则对这个社会的基本制度进行改革。无疑,改革后的社会向相互性的方向进了一步,但很难保证每个社会成员的利益相对改革前都有所提升。事实上,那些出身权贵阶层、积累了大量财富的社会成员很可能会抵制改革,因为改革会损害他们的既得利益。
另一方面,实现了互利,并不意味着达到了相互性。一般说来,每个人在合作状态中的处境比在非合作状态要好。契约理论家通常设想出一种缺少社会合作的“自然状态”。在这种自然状态中,每个人自由而平等,只受自然法的支配。自然状态有这样、那样的缺陷,最主要的是缺少和平与秩序。霍布斯论证说,自然状态就是一种人人相互为敌的战争状态,“最糟糕的是人们不断处于暴力死亡的恐惧和危险中,人的生活孤独、贫困、卑污、残忍而短寿”。[9](P95)由于人们在自然状态中的生活极度悲惨,所以无论如何,只要进行社会合作,每个人的处境都会得到改善。在这个意义上,合作能够促进互利。然而,一种实现了互利的合作形式未必满足相互性理念,它仍然可能包含权贵集团对弱势群体的剥削。尽管弱势群体的处境比随时可能失去性命的战争状态要好些,但并不意味着他们从社会合作中公平地获益。
总之,互利既不是实现相互性的必要条件,也非其充分条件。在罗尔斯的契约论中扮演重要角色的是相互性而非霍布斯主义的互利观念。努斯鲍姆错误地把高蒂尔的互利观点强加给了罗尔斯,导致她的批评一开始就失去了正确的方向。我们没有理由认为,罗尔斯的具有道德色彩的相互性观念会排斥残疾人的正义权利。
四、道德能力和正义权利
罗尔斯的社会合作观点和两种道德能力息息相关。由于社会被视为公平的合作体系,那么,根据自由主义的正当性理论,社会公平合作的条款应当对所有相关社会成员来说都是可证成的。而对合作条款的证成性进行评价,要求社会成员拥有两种道德能力。善观念的能力使人们能够看到社会合作的意义,并愿意参与合作;正义感的能力使人们能够遵守社会合作的条款,即便这样做有时不符合自己的最大利益。可见,两种道德能力是从事罗尔斯意义上的社会合作的基本条件。所谓充分合作的社会成员,必须拥有两种道德能力。而不拥有最低限度的道德能力的人,则无法有效参与社会合作。基于相互性的理念,拥有道德能力的社会合作者有权利要求获得公平分配社会资源的份额。罗尔斯明确指出:“道德人格能力是获得平等正义权利的一个充分条件。除了这个基本条件之外,不需要其他条件。”[1](P442)现在的问题是,残疾人拥有罗尔斯所说的道德能力吗?
很明显,身体残疾而心智健全的残疾人是可以拥有这两种道德能力的。对于聋人、盲人来说,他们不但可以有对良好生活的设想并制定自己的生活计划,还能和外界进行某种形式的交流互动,拥有参与公共事务所需的正义感。真正困难的情形是那些有精神残疾的人(比如自闭症、唐氏症患者),他们似乎在运用道德能力方面存在严重的障碍,这是不是就意味着像努斯鲍姆设想的那样,他们被罗尔斯的理论排除出正义的范围了呢?
需要注意的是,罗尔斯将道德能力视为一种潜在的力量,而不是已经实现的状态,“应当看到,这里的道德人格被界定为一种通常在特定阶段实现的潜力。正是这种潜力使正义的主张发挥作用”。[1](P442)这样一来,几乎我们每一个人都具有道德人格,无论是正常人还是残疾人。即使没有充分地展示和运用道德能力,那些患有精神残疾的人仍然可能在一种潜在性的意义上拥有道德能力。事实表明,很多存在认知障碍的残疾人确实具有实现道德人格的潜力。医学界曾一度认为,唐氏症患者无法学会走路、交谈、自己穿衣服。然而,现在不少患有唐氏症的成年人已经成为富有活力的社会成员:有的成为电视剧演员,有的学会演奏乐器,有的从事公共服务,有的创办网站。从他们的行为举止和语言文字中可以发现,他们已经初步形成了一定的善观念和正义感。[10](P586~587)道德能力和大多数其他类型的能力一样,不完全是与生俱来的自然天赋。道德能力的形成和完善,有赖于特定的社会条件。缺乏有意识的培养和训练,道德能力是无法实现的。如果把一个出生时健康的儿童置于一个孤立的环境中,他将因为缺少关爱和交流而难以获得基本的道德感。而即便是先天不足的残疾人,也有希望发展道德能力,前提是获得有利条件的支撑,例如家庭成员的精心照顾、社会环境的支持、教育资源的投入等。实际上,那些智力障碍的残疾人得以实现某种程度的道德人格,离不开家庭和社会的强有力的支持。
既然罗尔斯将平等正义建立在潜在的道德人格之上,而患有精神残疾的人也具有实现道德人格的潜力,那么,他们就和心智健全的人一样拥有基于正义的不可侵犯的权利。在设计基本正义原则时,原初状态中的各方会将他们的利益纳入考量。由此可见,一旦我们从“潜在性”的观点去理解道德能力,契约论对残疾人的包容性就增强了。
然而,可能有人反驳说,“潜在性”的观点太乐观了,不是所有人都可以被视为具有道德潜力。不可否认,有些残疾人的认知障碍非常严重,以至于在现有的医疗和教育条件下不可能发展出任何形式的道德能力。他们不仅现在不是合作者,而且将来也不可能参与社会合作。这些明显缺乏道德潜力的非合作者,是否被罗尔斯排除出正义的范围呢?答案是否定的。必须强调指出,罗尔斯只是确认道德能力或道德人格是人们获得正义权利的充分条件,至于其是否构成必要条件,罗尔斯的观点表达得相当谨慎:“道德人格是不是一个必要条件的问题,我先放在一边。我假定正义感的能力是绝大多数人所具有的,因而这不会带来严重的实践问题。具有根本意义的是,道德人格足以使人成为权利的主体。我们在假定这个充分条件通常得到满足时不会有太大错误。即使道德能力是必要条件,根据这一点在实践中不给予(不具备这一条件的人)正义是不明智的。那样的话,正义的制度将会面临巨大的风险。”[1](P442~443)
一方面,罗尔斯坚持充分合作假定,强调原初状态的立约者代表的只是具有道德能力、充分合作的社会成员;另一方面,他又不愿否认那些不具有道德能力、患有严重残疾的人的正义主体地位。这里看似矛盾,其实不然。罗尔斯认为,严重残疾者也有权利得到公平的对待,只不过这不是原初状态要解决的问题。等到立法阶段,我们可以根据对社会事实(比如经济社会发展状况、可利用的资源、严重残疾者的数量)的了解,制定出补偿严重残疾者的法律制度。在罗尔斯那里,合作者之间的正义问题和非合作者(严重残疾者)的正义问题是分开处理的。对于这种分开处理的策略,有两点考量予以支持。
第一,从正义的主题看,首要主题是社会基本结构。所谓社会基本结构,就是指维系社会合作不可缺少的宪法,以及一系列社会和经济安排,如保护言论自由的法律、市场制度、财产制度等。缺少了这些制度,一个社会就无法正常运转。社会基本结构对每一个社会成员的生活前景影响深远。更重要的是,在维护社会背景正义方面,社会基本结构的作用不可替代。原初状态各方要选择的正义原则,正是规范社会基本结构的原则。然而,不是所有的社会制度都可以被纳入社会基本结构的范畴。补偿和救助严重残疾者的制度尽管具有道德重要性,但不属于社会基本结构。[11]关于如何补偿严重残疾者的正义原则,也不属于背景正义的原则,因而不是原初状态各方考虑的对象。
第二,从正义的类型看,包括相互性的正义和基于需要的正义。这两种类型的正义对应着我们关于正义的两个深刻的直觉:1.每一个合作者都有权利公平获得社会合作产生的好处;2.任何一个人,无论他是否具有社会合作需要的道德能力,社会都应当满足他的基本需要。[12](P90)我们难以“毕其功于一役”,一次性就制定出既满足相互性又满足特殊需要的正义原则。不同类型的正义问题只有在不同的阶段才能得到处理。原初状态主要处理的是相互性的正义问题,罗尔斯的两个正义原则表达了相互性的理念,回应了合作者的正义诉求。而非合作者或严重残疾者的正义问题,则要等到“无知之幕”进一步打开、社会信息逐步明朗之后再予以讨论。这种分开处理的策略,与其说是排斥严重残疾者的正义权利,不如说是关注他们不同类型的正义要求。
五、结语
应当承认,努斯鲍姆对契约论的批评是有价值的。努斯鲍姆的批评提示我们关注并反思契约论的理论预设及其理论限度,而且也确实切中了某些契约论版本(比如霍布斯主义的契约论)的要害。然而,这个批评对罗尔斯的契约论并不构成致命的威胁。一旦我们对“大致相似”“相互性”“道德能力”等观念做了澄清,就会发现罗尔斯的契约论并不排斥残疾人的正义权利,这个理论可以容纳每一个社会成员作为正义主体的地位。如果得到恰当的理解和诠释,罗尔斯的契约论仍然可被视为一个具有包容性的社会正义的研究进路。
注释:
①除了残疾人的正义权利外,努斯鲍姆认为契约论进路也不能很好地解决全球正义和动物权利的问题。参见Martha C. Nussbaum: Frontiers of Justice, p14-22。
②值得注意的是,关于正义的主观环境,后期罗尔斯强调的重点从相互冷漠转向了合理多元主义的事实。
③虽然罗尔斯在《正义论》中运用了“互利”的概念,但那里的“互利”实际上可以理解为“相互性”。在《正义论》的索引中,罗尔斯将这两个概念的条目合一。参见John Rawls: A Theory of Justice, p531。
[1] John Rawls. A Theory of Justice[M].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2] Martha C. Nussbaum. Frontiers of Justice: Disability, Nationality[M]. Species Membership,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3] John Rawls. Political Liberalism[M].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5.
[4] John Rawls. Justice as Fairness: a restatement[M].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5] Alasdair Macintyre. Dependent Rational Animals: Why Human Beings Need the Virtues[M]. Chicago: Open Court, 1999.
[6] David Gauthier. Rational constraint: some last words[A]. Peter Vallentyne. Contractarianism and Rational Choice[Z].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1.
[7] David Gauthier. Morals by Agreement,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86.
[8] Samuel Freeman. Frontiers of Justice: The Capabilities Approach vs. Contractarianism[J]. Texas Law Review, Vol. 85,2006.
[9] 霍布斯.利维坦[M].黎思复,黎廷弼,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
[10] Sophia Isako Wong. The Moral Personhood of Individuals Labeled “Mentally Retarded”: A Rawlsian Response to Nussbaum[J]. Social Theory and Practice, Vol. 33, No. 4 (October 2007).
[11] 徐丹丹.“国情—正义”理论刍议[J].江淮论坛,2016,(5).
[12] Cynthia A. Stark. Contractarianism and Cooperation[J]. Politics, Philosophyamp;Economics,2009, 8(1).
(责任编辑:何云峰)
ContractTheoryExcludetheRightofJusticefortheDisabled——RefutingNussbaum’sCriticismofRawls
REN Jun
(School of Marxism, Jiangnan University, Wuxi 214122, China)
In recent years, contemporary famous political philosopher Nussbaum has systematically criticized Rawls’s contract theory, and pointed out that some of the core elements and theoretical assumptions of contract theory made it difficult to accommodate the right of justice for the disabled. However, by clarifying conceptions of “rough similarity”, “reciprocity”, and “moral power”, the paper argues that Nussbaum’s criticism does not pose a fatal threat to Rawls’s theory. If properly understood, Rawls’s contract theory is still regarded as an inclusive theoretical approach to justice.
contract theory, disability, justice, Rawls, Nussbaum
B82-0
A
1004-8634(2017)05-0022-(07)
10.13852/J.CNKI.JSHNU.2017.05.003
2016-12-01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社会制度的道德证成理论研究”(15YJC720021);江苏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制度正义的证明问题研究”(15ZXC003)
任 俊,江苏盐城人,哲学博士,江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伦理学和政治哲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