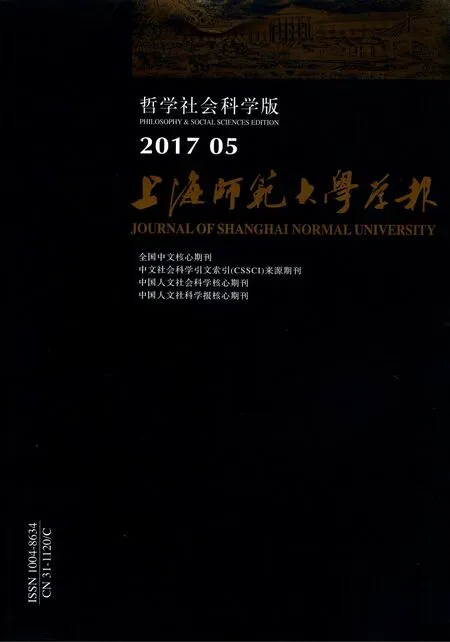编剧学的源流、现状与开创性探索
陆 军
(上海戏剧学院 编剧学研究中心,上海 200040)
编剧学的源流、现状与开创性探索
陆 军
(上海戏剧学院 编剧学研究中心,上海 200040)
编剧学是一门有着广泛发展前景的新兴学科,它从理论、实践、历史三个方面展开对编剧的研究。从源流上看,编剧学来自戏剧学,中国历史上与编剧学有关的研究可分为古典研究、近代研究、今人研究三个阶段,这些研究取得成果的同时仍然存在着大量的空白和问题。而西方的编剧从亚里士多德开始就打下了基础,无论是“三一律”还是先锋戏剧对传统“文本”的反叛,都代表了一种创作策略。当前编剧学应推进基础性的研究工作,包括:中外戏剧创作理论的资料整理与研究、优秀剧作的译介、编剧学理论研究成果的集中辑录。
编剧;编剧学;编剧学史;学科建设
一
编剧学,顾名思义,是一门将编剧理论、实践及历史作为研究对象的学科。虽然“编剧”作为一种创造性活动、一类行当、一份职业、一个专业,早已为我们所熟悉、关注和研究,但作为学科概念的“编剧学”被提出并进行建设则是近十年的事。
回看编剧的历史,从古希腊三大悲剧家中最早的埃斯库罗斯算起,已有2500多年。①编剧的相关研究,自亚里士多德的《诗学》算起,也超过2300年了。②中国戏剧晚出,现存最早的戏曲剧本是南宋的《张协状元》;③至于编剧的研究,直到清初李渔的《闲情偶寄》,④才以结构、词采、音律、宾白、科诨、格局六方面论,对戏曲编剧的理论与技巧做了全面的概括与精当的阐述。而大学的编剧专业教学,较早的有美国乔治·贝克教授在哈佛大学主持的“第47号工作坊”系列课程,培养出了尤金·奥尼尔等一批剧作家。⑤
在以往的学科分类中,编剧原是戏剧戏曲学下的一个子系统,一直依附或混杂于文学、戏剧和电影之中。如今自立门户,逐步自我完善,并形成体系化,实在是经过了漫长的求索之路。编剧学的建立,既是编剧专业自身发展的内在需求,也是戏剧影视与文化创意产业等社会事业发展的自觉选择,更是这一人类创造性活动获得人们进一步重视后的必然结果。
二
编剧有两层含义,既指从事编剧职业的人,也指根据一定艺术规律创作剧本的行为。据此,编剧学的学科构架应从理论研究、实践研究和历史研究三个层面展开,即在编剧学科体系中进行编剧理论、编剧史论、剧作评论和编剧技能的研究。
根据学科定位,编剧学至少要具有这样几个功能:第一,对编剧学的一些基本问题从理论高度做出科学的阐明;第二,对编剧史和当前编剧实践中有争议的问题做出科学的分析和判断;第三,对编剧实践中碰到的重大理论问题做出科学的探索;第四,对编剧的未来发展问题做出科学的预测。概括起来,编剧学的功能是科学地回答编剧实践中提出的根本问题,以及科学地提供回答编剧实践中提出的根本问题的观点和方法。
历史上对编剧的研究,最初主要来自经验、实践,着重于技巧层面。随后的理论研究则依附于文学理论的范畴,较多地注意剧作的社会背景、剧作者的世界观、戏剧作品的社会意义等因素。20世纪20年代,随着文学理论转向形式主义,戏剧文本创作的研究也较多地偏重于剧本分析。而近年对剧本创作过程即创作行为的学术研究,逐渐成为研究重点。
具体来说,剧作史论、理论、评论与技论的研究,又可分为对编剧行为、编剧成果、编剧主体的研究。
编剧行为的研究,乃指对选材、运思、创作、成文等过程的研究,以及对影响该过程的诸多因素的研究。对于编剧特别是影视编剧而言,当下的研究还要考虑大数据的应用、商业化的创作背景,这意味着创作不再是埋头书斋的单打独斗,而与营销策略、观众喜好、国家战略等有着密切联系。
编剧成果的研究,即对创作成品的研究,即传统研究中的作品论。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对编剧成果的研究不仅限于对新创作作品的研究,还包括对以往作品的重新诠释与解读。
编剧主体的研究,主要是对剧作家命运经历、学术思想、文化人格和戏剧创作成就进行系统的学术考察和分析,并将其人格发展和创作成就置于历史发展的长河中进行评析。
当然,我国编剧学的研究还承担着一个重要使命,即旨在建立中国编剧的知识体系,契合中国文化的审美框架,在此基础上建构中国编剧学。要完成这一任务,一是要做到中华戏曲剧论与传统艺术创作理论的融合;二是要做到编剧理论与当代国内外戏剧实践经验的融合;三是要做到编剧理论和实践问题研究与其他学科研究的融合。一句话,编剧学建设,不仅是历史的,更是现实的;不仅是理论的,更是实践的;不仅是戏剧的,更是多元的;不仅是中国的,更是世界的。由此可以断定,编剧学是一门有着广泛发展前景的新兴学科。
三
辨明编剧学的源流有助于我们更深入地认识这一学科。编剧学以戏剧学为起源和母体,“戏剧学是一门把戏剧作为研究对象的新兴学科,它的独立和体系化是从二十世纪初开始的”。⑥编剧学与戏曲史论作为戏剧学研究最古老的部分,其独立与体系化只有在戏剧学的独立与体系化完成之后开始。“对戏剧的研究,可以在不同的空间层次内进行。一是案头文学,二是舞台演出,三是剧场活动,四是社会现象。戏剧学研究的发展史正是研究领域不断拓宽的历史。”⑦同样,编剧学的研究领域和层次也是在不断地变化着、发展着。有戏曲以来,有关剧本创作的见解与论述便相伴相生。汉代的“角抵成戏”,⑧唐代的“美刺”原则,⑨元代的《制曲十六观》,⑩明代徐渭的“本色论”、李贽的“童心说”、汤显祖的“主情论”等,都曾风靡一时。特别是王骥德的《曲律》,视野开阔,承上启下,他对文本情感、事物描写、戏曲语言、故事结构等都有自己独到的见解;与之相关的风神论、虚实论、本色论、当行论,是对戏曲创作规律、创作方法的全面探索,对当时及后世的戏曲剧本创作都产生过重要影响。
历史地看,中国编剧学主要经历过以下阶段:
1.古典研究阶段。以燕南芝庵的《唱论》、王骥德的《曲律》、李渔的《闲情偶寄》为代表。这部分研究以编剧学研究中的戏曲剧作本体研究为主,在重视案头文学时兼重场上演出,如“词采”“宾白”“当行”“本色”等论述。其中,前两人与编剧学有关的研究重点是词采与文字,在对音乐的讨论中隐约包含了对文本创作的要求,但在当时“文本”“故事”服务于“曲”的体制下,对剧本的结构和创作技巧并没有过多阐述。李渔的研究则把“结构”放在第一位,提出“一人一事”等针砭时弊、对剧坛颇有影响的观点,体现了对“剧”的自觉意识。
2.近代研究阶段。以王国维和吴梅的研究为代表。王氏的研究主要体现在戏曲史论和戏曲本体论的建树上。王氏论著中与编剧直接有关的观点是其对戏曲概念的界定:“戏曲者,谓以歌舞演故事也。”在戏曲本体特色的论断以及作家作品论上,王氏有意识地注意到戏曲“歌舞演故事”的特色,而这一特色的提出对戏曲的编剧要求有着深远影响。可以说自此以降,戏曲的编剧技法及衡量标准都不脱此一定义。在作家作品论上,王氏对关汉卿的作品大力揄扬,认为《窦娥冤》 “列之于世界大悲剧中亦无愧色”,是中国古典悲剧的典范。其实关汉卿的喜剧轻松、风趣、幽默,无论在艺术构思、戏剧冲突、人物塑造、语言运用等方面都堪为后代喜剧创作的楷模。王国维擅长从作品的主题思想和人物形象出发进行评析,而且王氏深受叔本华“意志论”影响,故其对人物形象的看法,与对中国叙事散文、古典小说中人物的形象评价有着相似之处,或许这在某种程度上说明了王氏对“故事”的重视。而“故事”这一要素在戏曲中的地位,在相当程度上决定着戏曲艺术特色的走向——是“歌舞”服务于“故事”,或者“故事”服务于“歌舞”。如果是前者,那么歌舞是欣赏重点,“故事”不妨简略;如果是后者,那么“歌舞”必须是叙事性的歌舞,而与歌剧和舞剧中的“歌舞”表演有所不同。或者说,在戏曲中事实上存在两种歌舞:一种是纯为美观娱乐的歌与舞,如《长生殿》中的杨贵妃“玉盘”之舞;亦有另一种致力于表现人物精神状态、性格身份之舞,这便是人物的一举一动、一笑一颦,《马伶传》中马伶毕肖即有赖于此。相比王氏直接涉及编剧学的作家作品论,其“歌舞演故事”的论断对中国后世编剧技法及文本批评影响更大。
3.今人研究阶段。19世纪末西风东渐,西方戏剧演出开始影响中国,自1907年“春柳社”演剧之后,话剧正式登上中国戏剧舞台,话剧和戏曲遂并列于中国剧坛之上,两者互相影响。如果说前两个阶段的编剧学以戏曲编剧为本体进行讨论,那么此一时期便是戏曲编剧与话剧编剧并列研究的时期。在本阶段,无论是戏曲编剧,抑或是话剧编剧,均受到“冲突”“行动”“发现”“突转”等理论的影响。理论界以此为准绳衡量作品,并从前人剧作中发现相应的实例。创作界也以此为准绳结构剧本,如著名剧作家范钧宏的《猎虎记》就是一例。同时,研究者注意到戏曲“写意”“虚拟”的特色,并从表演扩展到剧本创作上,也发展出戏曲剧本创作要注重“内心冲突”“抒情”的提法,并强调了对“背躬”“独白”的重视,使得编剧学研究上升到一个新的层次。2015年由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的三卷本《中国现当代编剧学史料长编》(陆军主编),较全面地记录了这一阶段的研究成果。
四
必须看到,在前人的编剧学研究中,仍然存在着大量的空白和问题。以王骥德和李渔的研究为例。王骥德《曲律》对于创作实践的指引作用,极易随着创作体制的变化、音乐的更迭而失效。试想,若世人不再以元曲的四大套来创作,曲律还有何律可言呢?词采、宾白、当行、本色,也只是泛泛而谈。且不论戏曲创作,即便是小说、叙事诗歌,都会对人物的声形毕肖进行性格化的要求,其所论与戏曲编剧本体关联并不算大。李渔首创性地提出“结构”一说:“一人一事”的“立主脑”。鉴于明清传奇人物头绪众多、情节纷繁,李渔看出了当时剧作结构的要害。然而,究竟何为一人一事,李渔自己也语焉不详,是以后来深受其影响的金圣叹在评《西厢记》的“一人一事”时,时而说此人是“双文”,时而又说是“张生”,来回说颠倒话。这并非内有什么大玄机,而是李渔“一人一事”的提法太过笼统和粗疏。“一人一事”是指只写一个人、一件事,或者是以“一人一事”为主?这“一人一事”是结构上的要求,还是对“主题思想”的要求?结合丰富的创作实践来看,两者皆有可能,甚至还有第三、第四、第五种可能。如《桃花扇》中,虽以侯、李两人串起全剧,但两人也仅仅是串联的线索。《桃花扇》的主题是反映南明的兴亡,而并非单纯是两人故事。后世不解者只将“一人一事”解成“只写一个人、一件事”,又不对长篇传奇的篇幅进行克制,是以造成情节繁冗、人物单薄的弊端。其实在李渔自己的作品中,又何尝全是“一人一事”。再者,李渔在实践中给出的解决冲突和矛盾、如何将纷繁的头绪有序地组织到剧本当中的药方,仅仅是强调了一下互相对应的穿插安排,使得每一条线索、每一个人物都有可能按照顺序排列出现在剧作中;但故事矛盾冲突的解决又常常不依赖于主线人物和主要冲突,而是通过另加一条支线、利用支线人物的影响来解决。王国维的“歌舞演故事”对后世创作和理论研究影响巨大,然而成也王、败也王。后人多注意到“歌舞演故事”之“真正戏剧”,却忽略了王氏关于“滑稽戏”等的论述;而这几种算不上“真正戏剧”的戏剧,恰恰是不以“歌舞”为主,而以动作和念白为主的。事实上,这后几种戏剧并没有消亡,有些仍以经典折子戏的形式保留至今。这或许可以说明,王氏当时所论是“真正戏剧”也好,非“真正戏剧”也罢,放到今天,在今人眼中看来,都是戏剧(或曰戏曲)。再加推究,戏曲作为综合艺术,其衡量标准也是综合的、变动的、因剧而宜的,不能尽以是否以“歌舞”演了“故事”而“一刀切”。对“歌舞”“故事”及“念白”的重要性不分,导致后来的研究者在理论上将“歌舞”置于“故事”之前,却在实践评价中将“故事”置于“歌舞”之前,而尽以西方的“冲突”“行动”来衡量剧作,使得剧坛上仅有“故事”一种戏剧,其他戏曲罕有存身之处。此外,站在历史高度看,王氏的作家作品论确实提出了中国戏曲的艺术价值,引起了研究者的注意,但如前所论,王氏对戏曲人物形象、主题的评价,与他对小说的评价没有区别;换言之,王氏并未结合剧作本体中编剧技巧、情节设定、悬念设置等剧作法范畴的概念加以阐述。
今人的研究在王氏基础上无疑更进一步,“内心冲突”“以线串珠”的观点也给予戏曲剧作以具体支撑,“冲突”“行动”等西方剧作概念的引进,也使得戏曲和话剧在“故事”上更加严密和完整。然而,今人研究的误区在于,没有注意到中国戏曲创作历史上的丰富多变。宋元杂剧、明清传奇乃至花部的地方戏,在编剧体制和篇幅上均有所不同。明清传奇戏剧的剧本创作,既不同于元杂剧,其规律亦不同于单折杂剧;这种长篇连缀的体系受话本小说影响,在本质上更接近于长篇电视剧的叙事而不是话剧舞台剧的叙事。所以,以话剧舞台剧的标准来衡量,自然觉得其情节拖沓、叙事冗长,然而若用长篇电视剧的创作规则去衡量,其长度、节奏却在恰当范围之内。只是,明清以降的花部戏剧中,继承了明清传统情节连缀的体制,但因篇幅不及、演出时间又有限,未能因地制宜去恰当选材,反而为了适应时间和篇幅强去删减,是以造成情节简陋、主题单薄、人物苍白的弊病。以洪昇的《长生殿》为例,该剧虽然是以唐明皇与杨贵妃的故事为主,但按今日之观剧习惯,单单讲述李、杨两人的爱情故事都嫌来不及。今人写戏,大多以故事、情节、冲突来架构,已罕见类似于《梧桐雨》的真正的心理式结构剧本,更无接近于《长生殿》的长篇戏曲。所以,编剧学研究亟须分源别派,才可旁通四达。
五
东方与西方在戏剧创作上有着迥然不同的审美路径和发展历史。戏剧在西方从一开始就以一种庄严、肃穆的姿态登上文化舞台,戏剧家受到举国的重视;而东方,起码在中国,戏剧家是以优伶的娱乐姿态登上舞台的。由此,决定了东西方在剧作结构、舞台布景、主题意旨上的不同。在剧作结构上,从亚里士多德《诗学》对“悲剧”的重视、对“冲突”“摹仿”的重视,已经打造好了西方话剧写实的基础,而“三一律”则是对亚氏冲突、情节不可太长也不可太短的细化。不能否认,“三一律”至今仍对舞台发挥重要影响,是戏剧创作与小说、诗歌区分开来的最佳方式,也是最能体现戏剧剧本对题材选择、裁剪方式独具匠心的一种方式。然而,“三一律”毕竟只是创作策略之一种,对于旨在叙述“故事”的剧作行之有效,而对于重在抒发情感、表达意甚至是一种感觉的戏剧,就远远不够用了。仅以美国当代先锋戏剧对传统“文本”的反叛为例,其理论宣言和创作实践都主张减弱乃至取消有意义的语言,取代无意义、无差别的“音响”等元素,在未来主义、象征主义、达达主义等先驱的基础上,运用大量肢体语言、图像等手段,想方设法增强剧场性而取消文本;其指向重点并不是力求表达什么,而是给出一种情绪或者感觉。但笔者以为,这仍然需要编剧的努力。这里用的是另外一套叙事规则和语汇,其语汇更多以联想、象征的方式并列组合,而不是以情节的因果逻辑。编剧要把观众的反应和举动纳入到通盘考虑之中。虽然编写出来的剧本,主要内容不是对话而是舞台和动作提示,但笔者相信也并非没有规律。我们亟须的是对这样的剧本进行研究,发现其叙事或表达主题的规律。换句话说,主张取消文本或语言的先锋戏剧并非剧作理论的末日,而是将剧场活动纳入到编剧的范畴中来,并在文本中给予适当体现。也就是说,在固定的、预设的文本之中,不仅要留下即兴的余地,也要留给肢体、声音、图像等特殊语言形式以运用的空间。这也就是美国先锋戏剧中所要体现的内容。因此,如同“三一律”一样,先锋戏剧也只是创作策略之一种,是对积习日久、渐成泥垢的戏剧创作陈规陋习的反拨,是对戏剧故事性的摒斥,是对戏剧思想性旗帜的高扬——作为一种姿态,反叛本身就是意义,无需再寻求更多意义。当先锋戏剧成为主流或者与其他戏剧形式一起被人关注后,其先锋性与反叛性就不复存在,因为已经没有可供其反叛的主流了,这也是先锋戏剧在20世纪90年代消失的原因所在。
先锋戏剧有其自成一派的语言系统或叙事系统,其规律固然可以寻见,但这种规律是否具有可模仿性、可借鉴性,仍然值得商榷。毕竟先锋戏剧所秉持的理念是个体化的创作,是基于创作者的个体经验而进行的表达。理念可以借鉴,技法可以效仿,但创作者的个体经验却是难以复制或学习的。所以,这也是先锋戏剧始终难以建构起理论体系的根本原因。如何去归纳先锋戏剧创作的普遍性规律,是编剧学研究的重要命题。但有时对先锋戏剧的过分关注,反而会影响到我们对西方戏剧的整体判断。因为纵观西方当代戏剧的整体格局,依旧是传统剧作理念支撑下的作品占据主流。这从近年我们翻译、引进至国内的许多作品即可看出。但也需注意,西方编剧理念的传统之所以有庞大的普适性,一方面是因为它的稳定性,另一方面是它的包容性、开放性。例如,随着现代技术手段进入戏剧舞台并引发演剧形式的革命,对戏剧文本创作提出了新的要求,但西方编剧体系的开放性使之可以容纳这种新的技术手段并化为新的表达手段;即使是近年来所谓“后戏剧剧场”(“后文本剧场”)概念的出现,其实也没有弱化文本的功能,反而促进了人们对戏剧文本的多义性理解。从这个角度讲,西方编剧理论体系的开放性是它可以不断适应新的时代、新的内容、新的形式的原因。另外,全球戏剧市场一体化的趋势已成必然,欧美优秀剧目可以“无时差”地被引入中国,那些令人眼花缭乱的编剧方法、演剧形式随时都可以刷新我们对戏剧文本的认识,也随时可以影响到我们的文本创作。这些都在促使我们对西方当下最新鲜、最有影响力的创作予以理论上的回应。
总之,现如今,包括西方在内,人类的戏剧创作之路正沿着越来越广阔的道路前进。在这样丰富而多样的实践尝试下,总结创作实践和理论,是编剧学学科的不二任务。
六
编剧学的研究版图不应该只局限于中国编剧学,也不应该把眼光局限在遥远的西方戏剧世界,日本、印度等亚洲具有代表性的戏剧创作理论与实践同样应该被纳入我们的研究视野。印度浓郁的歌舞剧传统对其剧作结构有何影响?这与中国的“歌舞演故事”有何异同?与其自说自话地在自家理论和史料中打转,不如看看同属东亚文化的理论阐释,在比较当中提醒我们更好地维护自身的传统,避免被同化。
当然,编剧学学科的范畴并非地理环境的推演。从“剧”的内涵来看,它不仅应包括最早产生的舞台剧,还应包括随着科技进步、娱乐方式增加而应运而生的新型戏剧形式。如果编剧学学科仅仅将目光局限于舞台剧的创作理论与实践,那是不可能真正做到高屋建瓴并从具体规律上升到一般规律的。从编剧涉及的实践领域看,编剧早已突破原有的戏剧、电影的框架,有了广播剧、电视剧、纪录片以及应运而生的新媒体戏剧。随着演艺艺术、图像艺术、视听艺术的普及,包括竞选、广告、婚宴、庆典等也都需要编剧的策划和撰稿,将人类所有的仪式化的活动化为“剧”的因素。诗意的栖居,行动即表演,戏剧的人生,这些成了现代人某种生活方式的追求。在这样的态势下,传统的编剧理论与编剧方法受到严峻挑战,现实中需要更多的学术回应。
从学科的外延来看,编剧学与多个学科有着交叉与重叠。剧本创作本身就是容纳诗歌、小说乃至散文在内的综合创作。在创作手法上它与叙事学有着千丝万缕的密切关系。心理学学科也有助于它对创作者创作心理活动以及观众欣赏心理的把握。就演剧传播手段与方式来看,大众传播学、媒介学也不可不研究。就创作人才的培养、创作方法的习得来看,教育学也必须被纳入研究视野。从编剧涉及的理论研究看,编剧理论早已突破原有的戏剧学、电影学的研究框架。今日的编剧专业作为一个核心,连接了几乎所有的社会和人文前沿学科,甚至包括了一些自然学科的最新成果,如语言学、符号学、叙事学、美学、心理学、创意学、传播学、接受美学、人类学、教育学、策划学等,也包括医学、运动学、生命学、数字技术、材料学等多学科与交叉学科。编剧涉及的新理论与技巧如雨后春笋,早已拓展了研究领域、收获了鲜活成果,并呈现出前所未有的蓬勃姿态。这具体体现为:有关编剧的论著与论文、教材与译著数量上升,质量提升;越来越多的高校面向本科生、研究生开设编剧课程;相关前沿理论融合渗入,国内外频繁展开学术交流与切磋,提供了良好的研究路径与发展平台。
七
编剧学学科的设立无论在国内还是在国外都是首创。因而,目前编剧学理论与学科基础尚显薄弱稚嫩,整体水准还处于不稳定的初级状态。有的研究取向单一,路径狭窄,自我封闭,亟须“破茧成蝶”;有的存在着“分化不够”的问题,编剧专业的主要领域和一些次领域没有得到充分衔接,没有建立一个独立而完善的学术体系;有的存在“融合不足”的问题,编剧专业在内与文学、戏剧学、电影学、传播学等内部各领域的学术对话不够充分,在外又与心理学、社会学、哲学等其他学科的跨学科研究交流不够积极。从本土文化研究的角度看,我们仍在吸收和消化西方编剧理论,创建具有东方美学特征与戏曲剧作思维的中国编剧理论和方法论还没有形成成熟的体系与模式。
同时,我们也要看到,一个学科的建立与完善并非易事,它需要扎扎实实的研究、探索与实践。新学科起步时期最重要的是资料的收集与积累,没有资料佐证、支撑的研究是危险的。所以,当务之急依然是要继续推进基础性的研究工作。它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中外戏剧创作理论的资料整理与研究。这部分的研究,属于中国部分的已比较完善,除了原有的积累,由笔者主编的3卷本《中国现当代编剧学史料长编》(2015年由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10卷本也将在2017年出版)、10卷本《上海戏剧学院编剧学教材丛书》(第二辑10卷本正在筹划中)也是一个补充。对西方经典编剧理论著作,过去曾经有过许多重要的译介,不过近年则偏重于影视编剧技术书籍的引进,而这类图书大多浅显,缺乏学术见解,所以亟须把西方最新出版的有学术价值的编剧理论著作纳入视野。对同属东亚文化圈的日本、印度、韩国等国家的编剧理论的推介,一直是个软肋,必须集中人力甚至借助外援来挑选有代表性的著作进行翻译。
二是优秀剧作的译介。剧作文本是剧作理论的感性体现,是编剧理论的灵感之源。我国曾经有一段时期非常重视国外剧作的翻译,如施蛰存主编的《外国独幕剧选》(上海文艺出版社),以及《外国当代剧作选》(中国戏剧出版社)等;近年来又有胡开奇、童道明等学者的新译剧作。集中起来看,也是蔚为大观,令人振奋。笔者正在选编的《中外经典剧作300种》也已被列入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重点书目。比较起来,对东亚文化圈的剧作译介较少,需要补上这一课。
三是当代戏剧家正在进行的编剧学理论研究成果的集中辑录。笔者主编的《编剧学刊》也将在2017年出版,创办的初衷即在于此。
总之,基础性的研究与开创性的任务当然还有很多,即使是此处所列的三个方面,也需要有更多的学人鼎力相助,方可真正有所收获。
注释:
①埃斯库罗斯约生于公元前525年,卒于公元前456年。
②对《诗学》成书年代学界有两种意见,一种是公元前347年,另一种是公元前335年。参见亚里士多德:《诗学》,陈中梅译注,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8页。
③《张协状元》由温州九山书会才人创作,保存于明《永乐大典》第13991卷。
④《闲情偶寄》包括词曲、演习、声容、居室、器玩、饮馔等部,其中与戏曲有关的是词曲部、演习部、声容部。李渔吸取了前人的成果,建立了一套完整的戏曲理论体系。
⑤尤金·奥尼尔在《追悼乔治·皮尔斯·贝克教授》一文中说:“贝克教授课上向我们所教授的那些戏剧技巧和戏剧分析方法对我们研究本行当具有很大的价值。但更值得记取的是他在精神上和信念上给予我们的支持与鼓励。”见[美]尤金·奥尼尔:《戴面具的生活》,肖舒、高新颖译,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15年版,第144-145页。
⑥叶长海:《曲学与戏剧学》,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版,第9页。
⑦同上。
⑧角抵原为徒手相搏的伎艺表演,汉代亦用以泛称各种乐舞杂技。因“角抵”本身蕴含着戏剧冲突的因素,故而“角抵”一词也可视作戏剧冲突的原始表述。参见陈竹:《中国古代剧作学史》,武汉出版社1999年版,第82-86页。
⑨“美刺”原则乃中国古代诗论中的美学原则,亦是传统儒家教化模式,此处指剧本创作时要注意发挥戏剧劝善惩恶、移风易俗的教育作用。
⑩《制曲六十观》是元人顾瑛的曲论专著,从作曲过程、曲意、句法、语言、用典、音韵等方面总结了曲文创作的规律。
(责任编辑:陈 吉)
TheOrigin,Status,andPioneeringTaskoftheStudyofPlaywriting
LU Jun
(Department of Dramatic Literature, Shanghai Theatre Academy, Shanghai 200040, China)
The study of playwriting is new and with a broad development prospect, and it does researches on playwriting from three aspects including theory, practice and history. In terms of origin, the study of playwriting derives from theatre studies. Throughout Chinese history, researches related to playwriting can be divided into three stages, including classical researches, modern researches and contemporary researches. However, there is great space for further studies. Western playwriting began at the time of Aristotle. The “Three Unities” and the rebellion of avant-garde drama against traditional texts are approaches of creation. The basic fundamental research work should be promoted, such as arrangement and research of Chinese and overseas materials of drama writing theories, translation of outstanding dramas and plays, and compilation of research achievements of playwriting theories.
playwriting, the study of playwriting, history of playwriting, discipline construction of playwriting
I23
A
1004-8634(2017)05-0060-(07)
10.13852/J.CNKI.JSHNU.2017.05.008
2017-05-30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艺术学重大项目“戏曲剧本创作现状、问题及对策研究”(16ZD03)
陆 军,上海人,上海戏剧学院编剧学研究中心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编剧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