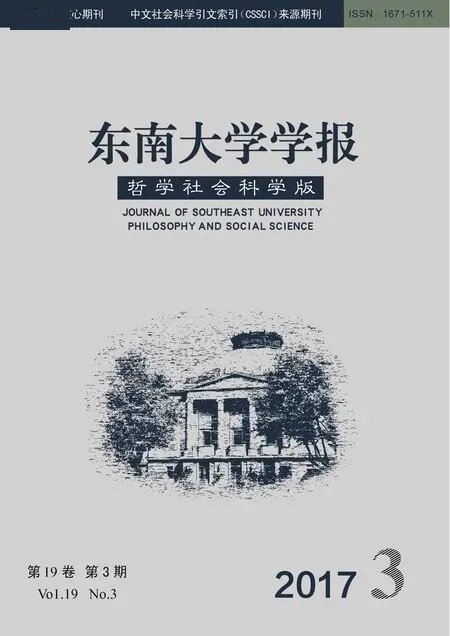救赎:社会历史中人的解放
——解放神学的“解放观”分析
刘春晓
(首都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北京 100089)
救赎:社会历史中人的解放
——解放神学的“解放观”分析
刘春晓
(首都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北京 100089)
解放神学基于拉美社会现实处境,部分吸纳马克思社会分析和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方法以及依附论相关思想,把基督教神学的主题“救赎”规定为“社会历史中的解放”,包括政治解放、社会历史中人的解放、灵性解放。认为拉美要真正获得发展,政治上的解放是前提,解放同时是社会历史中新人和新社会的诞生,是个体面向他人、面向上帝的完全敞开与联合。这是对传统基督教神学“救赎论”的革新,为基督教神学在当代的发展提出了新路径;同时为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人的解放理论提供了有意义的借鉴。
解放神学;社会历史;人的解放;救赎;政治解放;灵性的解放
解放神学是诞生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拉丁美洲的一种神学思潮,也是一次较大规模的群众运动,由于其对于依附论和马克思主义理论一定程度的吸纳和运用,也被称为基督教马克思主义。解放神学的理论主题仍然是基督教神学的“救恩”思想或称“救赎论”,但基于对拉美社会现状的认识和对资本主义的批判,解放神学家们提出了与传统神学完全不同的“救赎观”,概括而言就是:救赎即社会历史中的解放。
一
基督教神学自产生以来,所涌现的神学家和神学流派不计其数,但有一个主题贯穿着整个神学思想史,这就是,“所有基督教神学家对于救恩的共同关怀:神赦免与更新有罪人类的救赎行动。”[1]1
研究西方基督教神学史的学者一般认为,公元2世纪的第一位系统神学家爱任纽(Irenaeus)的“救赎观”对于基督教神学的整个发展与方向具有深远影响,有些神学家甚至认为,爱任纽之后的神学只不过是对其著作的一系列注脚。爱任纽的救赎理论反对诺斯替主义者主张的“基督的救赎完全属灵、与血肉之躯没有任何关系”的论调,强调救恩需要耶稣生平的每一部分,“道成肉身”是神永恒的道(逻各斯)经历人类的生存,是拯救与恢复堕落人性的要素。因此,“道成肉身”是整个救赎历史与个人得救的关键,如果耶稣基督没有经历道成肉身,救恩就不完整也不可能。耶稣基督完成的救赎,是借着他走过人类的整个生命历程,如果没有道成肉身,基督就无法使人的堕落逆转,救赎也就无法完成。爱任纽的救赎理论还包括“救赎与创造”的同一,认为,对于人类堕落的扭转即是救赎也是恢复创造的过程,借着这一扭转 “人类进入不再受制于受造存在的限制。”这就把创造看成与救赎一样是一个不间断的持续过程。
爱任纽之后,“救恩论”得到了不同程度、不同方面的丰富和发展,但“道成肉身”的救赎思想一直是基督教“救恩论”的基石。这其中,有一个问题一直困扰着神学家们,即人在救恩上扮演什么角色?如果救恩单单是神的恩典,那么,人是否具有主体选择能力,人的行为在信仰中又占有什么样的地位?早期教父和神学家大多主张救恩是神人合作的过程,这种观点遭到了后来大多数神学家的批评,及至奥古斯丁发展出了“神恩独作说”,强调人得救完全依靠上帝的恩典。他主张上帝在造人时曾经赋予人自由意志,但人类始祖的堕落使人的意志受到罪恶的污染,人被罪恶所奴役,从而丧失了自由选择的能力,因此,只有依靠上帝的恩典,人才能恢复意志自由,获得拯救。
中世纪经院哲学过度依赖亚里士多德的理智主义逻辑推理方法,这使许多神学家产生了一种错误认识,即人类的理智借着神恩典的帮助,有可能对所有实存(包括神在内)都能建立一个包罗万象且完全一致的命题系统。或者说,“中世纪的经院哲学,借用哲学的眼光,对于基督教神学的每一层面都详加检验,想要证明,基督教神学与其他的人类思想和见解都和谐一致。”[1]335并且试图建立关于神、世界与救恩等命题的宏伟体系,即“信仰寻求理性”,安瑟伦和托马斯·阿奎那更加关心“上帝存在的本体论证明”就是例证。美国学者奥尔森指出,经院哲学“把人类的理智微妙地置于神学思考的核心,以至于信仰、奥秘,甚至神圣的启示,最后都会被人弃之如敝屣,或者乖乖地臣服于逻辑和思辨之下。”[1]334可见,经院哲学在神学的覆蔽下把信仰置于理性之下,实际上是远离了信仰。
14世纪经院哲学开始分裂,欧洲进入动荡不安的时代,教会极度腐败,文艺复兴运动和基督教人文主义应运而生,这直接导致了遍及整个欧洲的宗教改革运动,“路德孵出伊拉斯谟所下的蛋”就是一个形象的说法。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打破了罗马教廷的至上权威,确立了新的神人关系。“因信称义”的救赎观强调基督徒不再受律法和“事功”(指实行教会规定的事务)的约束,而是战胜并超越了律法。路德强调“基督徒的自由,……并不在于让我们偷闲安逸,或者过一种邪恶的生活,而是在于让人们都无需律法和‘事功’而获得释罪和拯救”[2]447。这种救赎观强调个体无需僧侣阶层的中介就可以直接面对上帝;更强调无需好的行为,单单凭着信心,个体就能够获得真正的信仰。“因信称义”的救恩说强调信仰个体具有能够自由与上帝直接对话的权利,恢复了信仰之下人的个体自由。这种救赎观摧毁了教会的权威,但也暗含着某种自由主义的种子。
由上观之,“救恩”思想的演进,实际上是基督教神学对于人之自由在不同历史时期的不同理解。但自古以来,“救恩论”关注更多的是人精神上的自由,路德神学在推翻教会至上权威的同时,也开启了基督教世俗化的端口。19世纪自由主义神学进一步挑战了宗教改革以“信仰、恩典、基督、圣经”为中心的传统,并借着理性主义哲学和自然科学的发展力图做出合乎理性的神学解释。自由主义神学的救恩思想更加强调历史中的耶稣,强调耶稣的人性胜于神性;更加强调天国的内在性,否认超越的耶稣再临王国,希望依靠道德方法和教育方法来实现地上天国。这与当时整个西方文化界,包括哲学界的状况是一致的,是理性主义和科学主义在神学领域的表现。20世纪,世界历史风云变幻,两次世界大战颠覆了人们对于世界的认识。战后西方世界全面调整和繁荣发展,但社会问题仍然层出不穷,法国的“红色五月风暴”、美国的反文化运动等等,暴露了繁荣背后的种种危机,为思想理论界提出了新问题,也促发了基督教领域的改革。1962至1965年间,梵蒂冈第二次大公会议召开,会议的主题即“跟上时代”。会议向全世界宣布要和包括马克思主义者在内的“一切有良好愿望的人”对话,这是天主教历史上重大的改革。拉美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天主教地区,当地的神学家也参加了这次会议,解放神学的创始人古斯塔夫·古铁雷斯起草了会议部分重要文件。
二
20世纪60年代的拉美,在欧洲和北美普遍富裕的情况下,贫穷和压迫现象仍然十分严重,社会发展很大程度依赖于资本主义富裕国家,这样的处境使拉美神学家的理论建构转向社会实践。从基督教的普遍救赎论出发,解放神学家吸收了马克思主义社会分析和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方法,以及拉美本地的依附论思想,把神学的核心问题明确为“救赎与人的解放历史进程之间的关系”,认为,救赎与解放是一致的,救赎并不是一种外在于人、外在于历史的神的国度,而是存在于人和历史之中,是历史进程中人的解放。具体而言,包括三方面的内容:政治解放、在历史进程中人的解放以及灵性的解放。
1.政治解放
古铁雷斯认为,马克思通过对资本主义社会人对人、阶级对阶级剥削状况的分析,创立了真正的历史科学。拉美压迫状况的主要原因在于资本主义制度,资本的私人占有制“只能导致资本和劳动者的分离、资本家对于劳动者的高高在上、人对人的剥削等现象……生产资料私人占有的历史表明它必然减少或压制社会福利。”[3]31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商品拜物教的批判对解放神学非常具有吸引力,认为资本主义使商品的生产和销售成为生产的唯一目的,这实际上是金钱至上,金钱成为资本主义的上帝。在这样的制度下,工人无权决定生产什么和怎样生产,“市场的神化创造了金钱的上帝”。尽管资本主义高唱人道主义的调子,但是在资本主义条件下,人道主义是根本无法真正实现的。自由市场条件下不可能产生自由,它的同义语就是“屠杀自由”。资本主义追求利润最大化的生产目的只能导致社会贫富差距的悬殊和社会动荡。
基于这样的分析,解放神学从《圣经》旧约“出埃及记”入手论解放。认为“出埃及”对于以色列人来说就是从被压制的处境下脱离出来,从奴隶身份中获得解放,因此,整个出埃及的过程也就成为一个政治行动。拉丁美洲人的处境就如同身处埃及的以色列人,受到各种形式的奴役,而上帝的救赎就是要把人类从各种奴役中解放出来。古铁雷斯说:“如果把拯救仅仅理解为对我们而言只具有‘宗教’的或者‘精神’的价值,那么拯救对于人类的具体生活就没有什么贡献。但如果把拯救理解为从较少人道状态到更富有人道状态的过程,就意味着弥赛亚带给人更多的自由,并且把人类从奴役中解放出来。”[4]26-27这就把“救赎”从“宗教的”或者“精神的”层面扩展至整个人的生存层面。
针对拉丁美洲当时经济领域占主导地位的发展主义理论,古铁雷斯指出,不能把发展仅仅理解为单纯的经济增长,发展主义并没有给拉美带来生产力的真正发展,反而造成了对于富裕国家的高度依赖,社会贫富差距进一步加大以及社会阶层间的对立。古铁雷斯强调,拉丁美洲不发达的最深刻原因在于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各方面对于资本主义富裕国家的依附。解决的办法不是发展资本主义,而是要消灭资本主义,摆脱与资本主义大国的联系,打破对资本主义国家的依附,实现经济和政治上的独立,并对私有财产制度进行变革。也就是说,在拉丁美洲特定的环境下,只有实现社会制度的根本变革,“发展”才会具有真正意义。
2.在历史进程中人的解放
对于《圣经》出埃及记中以色列人的经历,解放神学认为,以色列人对上帝的第一个经验是,上帝是主动启示自我并介入人类历史的上帝,圣经中呈现的人类历史就是人类为解放而奋斗的历史。在此过程中,人的解放不单纯是从外在的各种宰制中获得解放,还包括心理层面的自我解放。因此,历史进程中人的解放是人成为自己命运主人的过程,而上帝之于人,就在于他引导并带来解放。古铁雷斯说:“在贫穷的处境下谈解放主要是经济、社会和政治的解放。但我们应该更加完整和深刻地理解人类的存在及其历史的未来。对于解放深切的渴望照亮着现今人类的历史,解放即从所有限制和妨碍人类自我实现中的解放,从所有阻碍人类自由的实践中解放出来。”[3]27
在《解放神学》一书中,古铁雷斯写道:“现代人类所要寻求的不但是从外在的各种压迫中解放出来,如从作为某一阶层、国家、社会的成员的各种宰制中解放出来;同时他们亦寻求一种内在的解放,一种作为个体或个人的心理层面的解放。”[3]30他认为在人类解放的历程中,从外在的各种压迫中获得解放与人的心理层面的解放往往不一致,但在今天的社会,解放必须是二者的结合,否则就没有意义。进一步讲,“异化、剥削和为消灭它们而进行的解放应该包括个人身心两方面的解放,在建立新社会和新人的历程中,忽视这一点是非常危险的。”[3]31基于此,古铁雷斯认为,“人类的历史就是解放的历史,而解放的历史即视自由为一种历史的超克;同时也意味着如果没有对于压迫人类恶势力的斗争,人类从抽象的自由到实际的自由便是不可能……而人类的解放不仅仅是更好的生活条件,或是社会结构的彻底改变和社会革命,更是一个永无止息的持续性创造过程,是人成为人的新方式,是一个永久的文化革命。换句话说,对于人作为一个动态性和历史性的概念注定是创造性地指向其未来……与本质主义和静态的观念不同,历史不是预先存在于人之本性中潜能的实现,而是一种新的超越,是一种成为人的质的不同的方式,为要实现个体与全体的联结达至完全彻底的实现。”[3]32-33古铁雷斯强调,在拉美谈解放不只是克服经济、社会和政治上的依附,在更深层的意义上讲,它是在历史中经历人的解放而成为人的过程。是对于不同质的社会的追寻,在这个社会中,人将从所有的奴役中解放出来,并将用自己的双手创造自己的命运。因此,这个过程同样是探索建构新人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人将摆脱来自各种外在和内在的束缚,成为自己命运的主人。
3.灵性的解放
自由是一个重要的哲学范畴,也是一个重要的神学范畴,传统基督教神学往往把人抽离于社会历史之外,仅仅从“灵魂获救”的角度抽象地谈论自由。解放神学则认为,对于自由和解放的渴望是深层历史运动的产物,古铁雷斯说:“《圣经》所呈现的是耶稣基督作为解放者的工作,而长久以来,神学似乎在规避着对于人类历史冲突特性的反思,如人与人、社会各阶级以及国家之间的冲突。而使徒保罗却一直提醒着我们,对于基督徒的存在和所有人的生命而言,逾越节的核心意义在于:从旧人到新人、从罪到恩典、从奴役到自由。”[3]35古铁雷斯认为,自由就是从“罪”中获得解放,而罪就是以自我为中心、是拒绝“爱”,即拒绝爱自己的邻舍和爱上帝。“按照《圣经》的观点,‘罪’指人与人、人与神关系的破裂,它是人类生活中所有贫穷、不义和压迫的终极原因。当然,这绝不意味着,我们可以否认导致这种状况的结构性原因和客观的决定性要素。而我们所强调的是,这种状况绝非偶然,在不义的社会结构背后,有着个人和集体的意志与上帝和邻人相背弃的意志之原因。同时,这也意味着,一个社会的变革,无论它多么激进,也不能自发地压制所有罪恶。”[3]35
因此,解放神学并不是完全抽象地谈论人的“罪性”,而是将人放在实际的社会现实中来考察,认为人性的扭曲就是异化,而人的异化又会导致社会的罪恶。古铁雷斯说:“只把罪理解为个体私人的内在事实是不全面的,罪也是一种社会历史事实,是人与人之间的伙伴关系和爱的缺乏,是人与上帝与他人之间友谊关系的破裂,而这一事实又会反过来进一步导致个体内在的自我分裂。”[4]194因此,异化是人性缺失和社会不义的综合。而自由也就不仅仅是脱离外在的辖制,而是对于“个体罪性”与“社会罪性”的整体克服。这个层面的解放也即“灵性的解放”。灵性的解放是以爱为核心,向他人和上帝的完全敞开从而达致与他人、与上帝的联合与合一(communion)。
三
解放神学从一产生就遭到了教会内部保守势力的反对,随着其影响的扩大,也引起了梵蒂冈教廷和美国政府的重视。1983年,教皇约翰·保罗二世访问尼加拉瓜,亲眼看到了解放神学在拉美的影响,认为解放神学所宣讲的政治方向和民众教会危害了正统教义和教会,从此开始了教廷对解放神学的批判。教廷先后发表多个文件批判和谴责解放神学,解放神学家的行动受到种种限制,一些解放神学家受到教廷的惩罚,有的解放神学家被迫放弃神职,解放神学被禁止在天主教大学和神学院讲授。尤其严重的是被解放神学视为拉美解放“新希望”的尼加拉瓜革命,由于桑地诺阵线在1990年大选中的失败而终结,给解放神学带来了沉重的打击。20世纪80年代以后,拉美的社会现实也发生了重大变化,军事独裁纷纷倒台,传统意义的左翼政党得以恢复和重建,各国先后开始了“民主化”进程。在这种环境下,有人说解放神学死了,对此,古铁雷斯并不认为如此。的确,面对内外环境的变化,解放神学并没有死亡,但其关心的问题的确发生了一定程度的转向,激进性有所减弱。比如,从原来主要强调基督教的政治方面、强调解放的政治意义转向了教会传统的灵性主题;对于《圣经》,也从重点强调出埃及、先知书转向《新约》的福音,文化问题和人类生存的环境问题也成为其关心的问题。当然,这并不能说明解放神学就退出了历史舞台,其“优先选择穷人”的思想,“入世”的历史观和基层宗教团体的组织形式,已经在拉美地区扎下了根,并对世界范围基督教的发展(包括神学和教会的发展与建设)产生了广泛影响,它所提出的问题在今天仍然具有重要的意义。
首先,解放神学基于拉美处境对资本主义进行批判,指出拉美要想真正发展就要实现民族独立和政治解放,突破了传统基督教神学对资本主义批判的单纯道德上的谴责。实际上,基督教世界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始自资本主义的产生,但其批判所依据的是基督教教义及其价值观。解放神学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则不仅仅依据基督教价值观,同时把批判的指向扩展到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各个领域,在此基础上吸收人文社会科学成果,从经济、政治和社会结构的角度寻找拉美问题的原因和出路,其政治向度的关注是解放神学对传统神学的一个突破,是神学在当代的发展。传统神学更多地强调个人生活、重视个人美德的修养,往往借口“上帝的归上帝,恺撒的归恺撒”,对政治很少或者根本不去涉及,因此对于社会现实往往只是泛泛而论,不能深入其中,导致在信仰上往往只是强调关于个人生活、强调和解的方面,而福音中关于政治与冲突方面的内容则未能给出应有的意义。恰如莫尔特曼指出的,“宗教的私人化使得政治神圣化,基督徒只是逃避到内心世界并拯救其个人的无罪。……教会只管宗教和良心,而社会便由不顾良心的权力政治所管辖。”[5]51这实际上是宗教的异化,是异化了的宗教。解放神学把救赎的范围扩展到社会领域,除了灵性解放,更强调人在社会生活中政治、经济和文化等领域的解放。把救赎与拉美特定的处境联系起来,强调被压迫民族、被压迫阶级的解放要求和实践,尤其着重强调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的冲突的性质,这是神学发展在当代的进步。这里需要指出的是,解放神学所强调的信仰对于政治维度的观照与基督教史上借助政治发展宗教、宗教又反过来成为统治阶级的工具的政教合一的做法完全不同。它与政治神学一样,是“以批判的态度看待政治意识形态和市民权力的宗教,并以肯定的态度看待基督徒为公义、和平及保护受造所做的具体努力。”[5]52其政治关切的维度是立基于基督教的普遍救赎观,在马克思主义影响下对于拉美处境的全面批判,这种批判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空想社会主义的局限性。[6]
同时应该看到解放神学所主张的解放理论的局限性。“打破对资本主义国家的依附,实现经济和政治上的独立”没有问题,但“消灭资本主义,摆脱与资本主义大国的联系”是有问题的。“解放”学说的提出与当时拉美对于资本主义富裕国家的全面依附直接相关,这种依附使拉丁美洲无法摆脱殖民主义的控制,走了西班牙又来了美国,新的殖民主义以经济援助为借口,不但没有解决拉美的贫穷问题,还掏空了拉美的自然财富,因此,古铁雷斯呼吁以“解放”代替“发展”。“解放”意味着反对殖民(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全面殖民)的斗争,意味着摆脱依赖关系,确立起拉美自己在经济、政治和文化方面的自主权,拉美的命运由拉美人民自己决定。这种摆脱依附争取全面独立的意愿具有合理性,然而,走“拉美人民自己的道路”并不意味着要与资本主义割断所有的联系。走什么样的道路与是否割断与资本主义的联系是两回事,割断所有与资本主义的联系并不意味着就能够很好地走上独立自主的社会主义道路。“摆脱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剥削、压迫和控制,并不等于割断与发达资本主义的联系,更不等于与资本主义市场决裂。”[7]190马克思在批判资本主义的同时也明确了资本主义在人类历史中的贡献,并且指出“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绝不会灭亡的。”[8]592当今时代,完全割断与资本主义的联系,封闭地发展社会主义是不可能的。马克思早就指出,近代以来,随着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形成,人类的历史就成了世界历史。今天更是全球化时代,整个世界成为普遍联系的世界,社会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国家的发展是彼此斗争又彼此依赖的,这也是历史发展的辩证法。作为社会形态的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发展也是如此,应该看到,资本主义在其发展过程中其内部也孕育和生长着社会主义因素。解放神学“消灭资本主义”的主张实际上是对马克思资本主义理论的误解,是把资本主义国家等同于社会形态上的资本主义,是对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关系的曲解。[9]
其次,对人类心理解放和灵性解放的强调对解决当今社会普遍物化状态下人的生存问题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和启发意义。
寻求心灵的解放是人类生存的需要。自近代以来科学技术的发展催生了物质财富的急剧增长,人们物质层面的需求基本得到满足,但人们却仍然感到匮乏与不自由。20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震醒了人们对于科学技术的盲目乐观,人们重新关注和思考人的生存问题。然而20世纪四五十年代科学技术的又一次大发展使人们再次被迷惑,以为人类的“生存危机”再也不会出现了。但事实恰恰相反,高速发展的科学技术不但带来了全球性的能源危机,也使人进一步异化为蛰居于世界却与他人隔离的孤独的存在,人为机器所辖制,人自身的机器属性也越来越凸显。对此,恩斯特·布洛赫形象地指出:“我们已经沦为最可怜的脊椎动物;我们中的所有人要么崇拜自己的肚子,要么崇拜国家;除此之外,其他的一切都降到了笑话或娱乐的水平。”[10]2同时,现代人面对的来自社会和自我的压迫与奴役形式更加多样、更加隐蔽甚至更加精致。人们常常难以觉察自己陷入强迫和奴役,同时又被强迫和被奴役的环境之中,这对人的摧残与伤害更加严重。
面对这种状况,许多思想家提出了真知灼见。从讨伐20世纪的科学主义出发,英国著名思想家迈克尔·波兰尼认为,科学中的客观实证方法和还原主义消灭了作为科学主体的人本身,使科学成为一个毫无激情的非主体的物的机械信息处理过程。实际上,科学从来都是由具有充分人性的个人知识构成的,科学研究是人的创造性活动,而不是物的外部静止投射。科学与人应该是合一的,科学本身就是充满人性的温暖的东西。丹尼尔·贝尔则提出了“限制的新宗教”的思想。这种新宗教包含对神圣力量的敬畏,对原罪的忏悔,对人性的冷峻认识和对欲望和自私的限制。牛津大学哲学家格劳维尔(Jonathan Glover)则明确指出,“需要切实而清晰地审视一下我们内心的一些妖魔,并且考虑‘降妖除魔’的方式方法”[11]1, 等等。
解放神学提出的心理解放和灵性解放的观点对于我们思考和解决这一问题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古铁雷斯把心理解放理解为人心理层面的自我解放,是自己成为自己的主人的过程;“灵性的解放”则是以爱为核心向他人和上帝的完全敞开从而达致与他人、与上帝的联合与合一。应该说,心理解放和灵性解放是人向自我、向他人、向上帝的彻底敞开与联合,只有实现这三个层面的联合,人才能获得真正的自由。诚然,任何人都不是抽离于世界之外的抽象存在,而是社会关系中的具体的人,作为社会关系中的人就不可能割断与他人的联系而生活在纯粹自我的空灵世界。因此,心灵的自由绝不是逃离现实社会生活的纯粹精神的逍遥游,但这并不能否定人的心灵或者精神有着自己独特的特性和发展规律。解放神学主张的“心理解放”与“灵性解放”强调人与自我、与他人、与上帝的彻底敞开与联合,一定程度揭示了人类心灵解放的特有属性和规律。撇开其神学层面的意义,我们可以把“上帝”理解为“终极意义”,尽管尼采早就宣告了上帝之死,但上帝(终极意义)的场域对人类来说在可预见的未来并不会缺席,科学主义、理性主义带来的种种问题使人们再次回到上帝(终极价值)面前寻求出路。在人类解放的历程中,人向自我、他人、社会以及终极价值的彻底联合和合一,意味着人能够从世俗秩序中摆脱出来,不再从自己“所拥有的或所匮乏的”角度去理解或看待自己和他人;也意味着人真正摆脱了一切内在和外在的限制,成为真正自由的存在者。当然,作为社会关系中的现实存在物,人不可能抽离于现实世界之外,但作为精神存在物,人又具有超越现实的特点。在此意义上,“自由”的个体能够从自己是具有独立自由意志的行为个体出发去面对他者,并尊重他者同样是自由的存在者,从而勇敢地承担起自己的行为责任。如此,自由所带来的就不仅仅是自我压迫的消解,也会是社会压迫的缩减。
当然,应当看到,解放神学的解放理论与马克思关于人的解放学说有着本质不同。马克思关于人的解放的学说是建立在哲学批判、政治经济学批判和社会主义批判基础上的科学理论。通过对资本主义经济运行规律的科学分析,马克思找到了工人阶级受压迫的原因,得出了无产阶级解放进而人类解放的途径、动力、主体以及人类解放的未来的科学理论。在马克思那里,人的解放是人摆脱来自自然、社会和自我的各种压迫的一个漫长的过程,其理想状态是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其中政治解放只是解放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环节。并且,“人”从来都是现实的人,是社会关系中的人,因此,人的解放过程与人类社会在不断解决社会基本矛盾和主要矛盾中前行是相一致的,是同一个问题的不同表述。而解放神学所谈的“政治解放”只是其解放的三个层面中的一个方面,解放神学不能对其所谈的解放的三个层面进行科学的分析,只是把马克思的政治解放简单地吸纳到自己的理论,因此,不具有科学性。
总之,解放神学基于拉美社会处境,部分吸收了马克思关于历史发展的思想,在神学框架内提出了“救赎即社会历史中的解放”的观点。它把解放首先理解为政治解放,同时强调人在解放历程中成为自己命运的主人,这是对于传统神学“救赎论”的革新,为基督教神学在当代的发展提出了新路径。同时,其“灵性解放”的观点为我们思考和解决现代社会人的普遍异化问题有启发意义,为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人的解放理论提供了有意义的借鉴。但作为一种神学思想,其对于政治解放及人在历史中解放的主张,是基于宗教的道义原则对马克思“政治解放”的结论和西方马克思主义心理解放理论的简单吸纳。因此,其所主张的“解放”本质上仍然是“蒙恩”的人的精神灵性向着无限终极实在的永恒过程,根本上仍然是一种神义论的自由观。
[1] [美]奥尔森.基督教神学思想史[M].吴瑞诚,徐承德 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
[2] 周辅成 编.西方伦理学名著选集:上卷[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7.
[3] Gustavo Gutierrez. A theology of Liberation[M]. Maryknoll, N. Y.:1973.
[4] James B. Nickoloff Editor. Gustavo Gutierrez Essential Writings[M]. ORBIS BOOKS, 1996.
[5] [德]莫尔特曼.俗世中的上帝[M]. 曾念粤 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
[6] 叶险明.马克思超越规范经济学与实证经济学对立的逻辑及其启示[J].哲学研究,2010(9).
[7] 叶险明.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与现时代[M]. 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6.
[8]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9] 叶险明.关于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关系认识的方法论批判[J].哲学研究,2013(9).
[10] Ernst Bloch. The spirit of Utopia [M]. trans. Anthony Nassar: Meridian. 2000.
[11] 哈佛燕京学社,三联书店 主编.理性主义及其限制[M]. 北京:生活 读书 新知三联书店,2003.
(责任编辑 许丽玉)
2017-01-16
北京市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解放神学历史观研究”(15ZXB011)、北京高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研究协同创新中心(首都师范大学)成果之一。
刘春晓,哲学博士,首都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哲学史。
B972
A
1671-511X(2017)03-003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