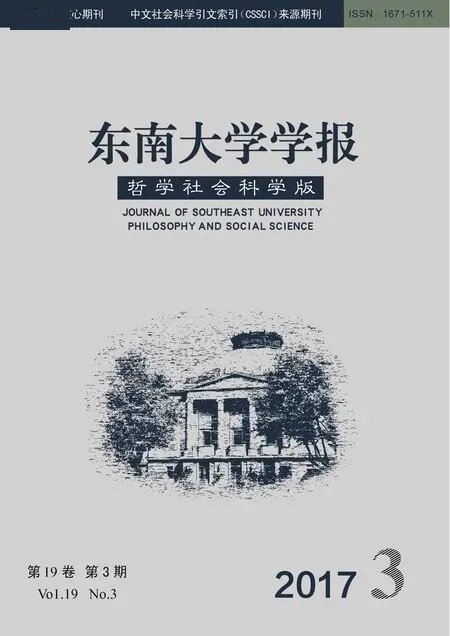论虞犯行为之早期干预
姚建龙,李 乾
(上海政法学院 刑事司法学院,上海 201701)
论虞犯行为之早期干预
姚建龙,李 乾
(上海政法学院 刑事司法学院,上海 201701)
虽然对未成年人虞犯行为的内涵和外延仍存在诸多争议,但未成年人虞犯行为应当进行干预则已成为学界与实务界的共识。从域外发展来看,虞犯行为的司法干预经历了全面干预、限制干预和废除干预的发展阶段。虽然域外少年司法界存在诸多纠结,但从我国情况来看,建立虞犯行为的早期干预机制仍有其必要性。以监护监督、亲职教育、宵禁、交友限制、传媒管理等非正式干预为重点,以警察部门、福利部门等行政干预为纽带,以司法干预为保障的“漏斗式”虞犯早期干预模式,应当成为我国虞犯行为早期干预制度建立的方向。
虞犯行为;早期干预;少年司法;未成年人;不良行为
笔者曾针对我国少年司法干预对象以及概念使用较为混乱这一现状,提出在借鉴国外经验的基础上将我国应当进行正式干预的未成年人行为统称为“未成年人罪错行为”,并将未成年人罪错行为分为虞犯行为、违警行为、触法行为、犯罪行为四大类的观点[1]。在四类行为中,虞犯行为在概念界定、应否进行干预、应采取何种方式进行干预等方面均存在较大分歧,为此,有必要对该问题进行专门研究,在廓清相关问题的基础上为我国少年司法改革提供理论支撑。
一、虞犯行为概念之界定
虞犯行为的特点是“成年人可为,而未成年人不可为”,这是一种基于未成年人特定身份而界定的特殊行为,在英美国家也被称为“身份罪错”(status offence)。虞犯行为不仅仅触犯了成人社会对未成年人行为规范的期待,也被认为是导致更严重越轨行为直至犯罪行为的危险征兆[1]。
(一)虞犯概念的比较
从各国少年立法来看,虽然具体称谓各异,但虞犯行为的外延大体相似,大多是指由未成年人实施的不服父母管教、离家出走等行为。美国作为少年司法的发源地,其将少年虞犯行为称之为少年身份罪错(statute offense)。少年身份罪错是能够让美国少年司法系统作反应的主要行为之一,其具体包括深夜在外游荡、酗酒、不服父母管教以及其他违反社会规范的行为。日本立法直接将此类行为称之为虞犯行为,其与少年犯罪行为、少年触法行为共同构成了日本少年法的干预对象即少年非行。根据日本《少年法》第3条之规定,所谓虞犯行为主要包括:具有不服从监护人正当监护的恶习;没有正当理由离家出走;同具有犯罪性质或不道德的人交往,或者出入可疑场所;习惯做有害自己或他人品德的行为[1]。此外,抽烟、旷课等行为虽不属于法定的虞犯行为,但大多也被纳入虞犯行为范畴予以规制[2]172。
我国台湾地区受日本影响,亦将该类行为称之为虞犯行为。其《少年事件处理法》第3条规定,少年法院的管辖案件除少年刑事案件之外,还包括少年具有如下情形之一,而依其性格及环境有触犯刑罚法律之虞者:经常与有犯罪习性之人交往者;经常出入少年不当进入之场所者;经常逃学或逃家者;参加不良组织者;无正当理由经常携带刀械者;吸食或施打烟毒或麻醉药品以外之迷幻物品者;有预备犯罪或犯罪未遂而为法所不罚之行为者[3]90。在此基础之上,其《少年不良行为及虞犯预防办法》又对虞犯行为的范围进行了扩充,除上述行为外,还包括深夜游荡、无照驾驶、持有色情猥亵物品等共十四项行为类型和一项兜底条款。
除上述少年司法较为发达的国家和地区外,其他国家也在其立法中对虞犯行为类型作出规定,如印度即将家庭贫困、无固定住所或者与不道德之人交往的放任少年以及为讨他人欢心而实施不道德行为的乞讨少年等纳入少年司法管辖范围,英国将不服父母管教或者父母放任不管的少年以及与不道德之人交往或者其家庭成员犯有特定罪行(如卖淫等)的少年视为犯罪少年,埃及将拾废烟头、夜不归宿、参与伤风败俗活动、不听家长管教的少年称之为不轨少年等[4]。
(二)虞犯概念的本土建构
我国并未采用“虞犯行为”或者“身份罪错”称谓,而是以一般不良行为与严重不良行为相指代,与域外相比,其立法体例与行为外延也有所不同。根据《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第14条之规定,未成年人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和学校应当教育未成年人不得有下列不良行为:旷课、夜不归宿;携带管制刀具;打架斗殴、辱骂他人;强行向他人索要财物;偷窃、故意毁坏财物;参与赌博或者变相赌博;观看、收听色情、淫秽的音像制品、读物等;进入法律、法规规定未成年人不适宜进入的营业性歌舞厅等场所;其他严重违背社会公德的不良行为。该法第34条对严重不良行为作出规定,其行为主要特征为严重危害社会但尚不够刑事处罚,大多是一般不良行为进一步恶化的结果。
受我国立法称谓影响,我国理论研究中多使用“不良行为”这一相近的概念来指代虞犯行为。但是,由于各研究者的研究视角、学科领域等各不相同,对“不良行为”概念的具体意蕴及其与虞犯行为、身份罪错、触法行为等概念的关系并未形成统一认识。就其具体意蕴而言,有的研究者在考察我国《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的相关规定后认为,“所谓不良行为,主要是指青少年违反社会公共生活准则与有关行为规范,或者不能良好适应社会生活,从而给社会、他人和本人造成不良影响或危害的行为”[5];另有学者认为未成年人因年幼这一特定身份而实施的越轨行为通常被称作“身份过错”,简单地说,身份过错通常仅指未成年人所触犯的违法行为,而非犯罪行为[6]。就其与虞犯行为、身份罪错、触法行为等概念的关系来看,有学者认为,我国《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第14条所采用的“不良行为”概念在实质上已经包含了日本《少年法》中的“虞犯少年”和“触法少年”的全部含义[7];另有学者认为,根据我国《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的规定,我国少年不良行为分为两类,即轻微不良行为和严重不良行为,这两类不良行为大体上相当于英美国家的“身份犯”,或者相当于日本的“触法少年”或“虞犯少年”[8];还有学者认为,少年虞犯行为与少年一般不良行为、少年身份犯、少年严重不良行为等概念均存在差别[9]。由此,目前我国理论研究中关于“虞犯行为”、“不良行为”的概念内涵及其与相关概念的关系等仍然呈现出众说纷纭的态势。
就虞犯行为与各概念的关系来看,其与英美国家所称之“身份罪错”无论是在行为类型还是在概念演变历程方面均存在着承继关系,因此,其概念实质大体相同,这也为学界所认可。虞犯概念源于日本,其自产生之初即与触法概念相区别,二者为不同概念自不必多言。但值得注意的是,考虑到我国采取的是违法和犯罪二元的立法模式,其触法行为自然包括刑事触法与治安管理触法两种类型,因此,不能一概将其以触法行为论。由于一般违法行为在社会危害性上尚不严重,而实施治安触法行为者又多为14周岁以下少年,其可矫正性较大,因此宜将此类触法行为归入虞犯行为行列,这也符合“儿童最大利益原则”的整体要求。
(三)虞犯的本质及类型
考察上述国内外有关少年虞犯行为的立法及其理论研究可以发现,自害性或者轻微的害他性是其主要特征之一,有些国家如日本《少年法》即以“习惯做有害自己或他人品德的行为”作为兜底规定。此外,犯罪倾向性是少年虞犯行为的又一重要特征,这也是国家对该类行为进行干预的重要理由。
据此考察我国《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第34条之规定,其严重不良行为在实质上已经具有了严重的社会危害性,在形式上也已经违反了我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等相关法律规定,再考虑到我国刑事立法中定性加定量的犯罪界定模式,其实质上已经构成域外所称的犯罪行为而非仅仅具有犯罪倾向性。因此,其当然应该被排除于少年虞犯行为之外。当然,如前所述,治安管理触法行为仍应归属于虞犯行为行列。最后,我国《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第14条所规定的一般不良行为,无论是从其兜底性规定“严重违背社会公德”还是从其具体的行为类型来看,其都与域外的“虞犯行为”或者“身份罪错”大致相当,因此其应与“虞犯行为”系属同类概念。综上来看,虞犯行为、身份罪错与我国的一般不良行为概念大致相同,而我国治安管理触法行为因其危害性较小,亦可归入虞犯行为行列,触法行为(本文仅指刑事触法)、严重不良行为概念则与虞犯行为存在明显区别。
就虞犯行为的具体意蕴来看,我国研究者多以“有犯罪之虞”来指代,或者直接引用域外的界定方式,如“虞犯是指少年的行为已经具有触犯刑法处罚的倾向,有犯罪的可能性,但尚未实施触犯刑法明文规定的禁止行为”[9]。此种界定方式既未指出虞犯行为的实质所在,也未在形式上给出恰当的判断标准,同时也并未与我国少年立法及其他立法的现实相结合。有鉴于此,笔者认为所谓虞犯行为应当是指由未成年人实施的、严重违背社会公德、但尚不符合给予行政处罚或采取特殊教育保护措施条件的行为[3],其主要是基于未成年人这一特定身份而在法律上正式禁止的有犯罪之虞的行为,具有“成年人可为,而未成年人不可为”的特点。
与我国刑事犯罪类似,少年虞犯行为在具备“成年人可为而未成年人不可为”“自害性或轻微害他性”“犯罪倾向性”等实质判断标准的同时还应当具有形式判断标准,此即法定性。所谓法定性即仅在法律有明确规定的情况下才可将某类行为认定为少年虞犯行为,这也是切实保障少年群体权益的要求。如上所述,我国现行法律中并无虞犯行为的概念,较为接近的是《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第14条所规定的一般不良行为,但该条所规定的一般不良行为有的已经超出了虞犯行为的范围,而属于违反《治安管理处罚法》的违警行为。此外,《中小学生守则》《小学生日常行为规范》《中学生日常行为规范》等规章条例中也规定了一些具有“成年人可为,而未成年人不可为”的行为,这也应作为界定虞犯行为的标准。在此基础上,借鉴国外通常的界定,可将常见的虞犯行为类型列举如下:
(1)抽烟、喝酒;(2)不服从父母、尊长或教师管教;(3)旷课、逃学,夜不归宿或深夜游荡;(4)与有犯罪习性或不道德行为的人交往;(5)进入未成年人不宜进入之场所;(6)参与不良组织或者参加封建迷信等不良活动;(7)持有、观看、收听色情淫秽、凶杀、暴力、封建迷信的音像制品、读物等;(8)侮辱、欺凌他人,打架斗殴但情节、后果轻微者;(9)携带管制刀具等危险物品但情节轻微不予治安处罚者;(10)偷窃、毁坏财物但数额较小或情节轻微者;(11)违反治安管理规定但因未达责任年龄而不予处罚者;(12)其他有害于自己或他人品德以及违背公共秩序和善良风俗的行为。
二、虞犯行为司法干预之变迁
将虞犯行为纳入少年法上的“罪错”并作为少年司法干预的主要类型之一,是现代少年司法制度的典型特征之一。但是,对虞犯行为如何进行司法干预却是百余年来少年司法理论与实践中纠结与争议的重大问题。虽然虞犯行为具有自害性与犯罪倾向性,但成人社会却并未对其采取一以贯之的态度,这在司法领域表现得尤为明显。从纵向角度来看,少年虞犯行为的司法干预主要经历了全面干预时期、严格限制干预时期与存废争议时期三个阶段。现详述如下:
(一)虞犯行为司法全面干预时期
作为少年司法制度诞生的标志,1899年美国伊利诺伊州议会通过的《少年法院法》虽然并未明确提出虞犯或者身份罪错概念,但其管辖范围中的部分行为类型或行为对象业已具备虞犯行为的雏形,甚至以如今的视角看来,部分行为已经属于少年虞犯行为。1899年伊利诺伊州《少年法院法》的管辖对象包括三类少年:16岁以下的无人抚养少年、被忽视少年以及罪错少年。其中,无人抚养少年以及被忽视少年并未触犯任何法令,其仅仅是因为有保护必要而被纳入少年法院的管辖范围。在这两类少年的行为类型中,街头流浪、同名声败坏的家庭或者腐化堕落的人共同生活、8岁以下沿街售卖物品或者演唱歌曲等多属于虞犯行为[10],此种提前干预的思想也为少年身份罪错的正式提出提供了指引。
随后,美国社会的儿童中心主义氛围日益浓厚,儿童保护福利化、儿童利益最大化、儿童优先等观念获得了日益广泛的社会认同。与此同时,美国总统罗斯福在其主政时期多次召开白宫儿童福利会议,并于1912年成立了儿童福利局,由此,儿童福利范围也由健康、教育等领域扩大到了青少年犯罪研究[11]。在此背景下,伊利诺伊州以福利为导向的少年法院模式为美国其他州纷纷效仿并迅速在世界其他国家传播。如德国在1908年于法兰克福成立了第一个专门审理少年犯罪案件的法庭,少年检察制度也随之确立;日本于1900年制定了《感化法》并于1923年开始实施其第一部《少年法》[12]。在这一被称为“少年法院运动”的少年司法发展过程中,少年司法制度本身也得到了完善和发展,少年身份罪错行为概念也被正式提出并受到少年司法的广泛干预。
受“儿童最大利益原则”等福利导向与“国家亲权”哲学等思想的影响,该时期的司法者认为,被忽视未成年人、身份罪错少年等均是因其自身所处的社会环境与家庭环境不能充分满足其健康成长需求而处于困境中的儿童[13]。为此,少年法院作为国家亲权的代表,有责任对其虞犯行为进行干预并为其提供良好的福利条件,以利于此类少年的健康成长。与此相呼应,美国的相关立法也对身份罪错少年进行了规定,如1935年《社会安全法》即规定,儿童福利服务是为了“保护照顾失依、失养、受忽视儿童及少年虞犯”[13]。据此,各种少年虞犯行为被纷纷纳入司法干预范畴,大批身份罪错少年被送入矫正机构。在这一少年虞犯行为司法干预浪潮中,少年法院的干预范围几乎涵盖了所有少年冒犯成人社会的行为,少年司法也开始替代传统的家庭、社区等成为新的少年控制手段。这一做法,也为其他国家和早期的国际少年司法准则所效仿,如日本即根据其1900年《感化法》设立了公立感化院,感化院的收容范围包括由地方长官认定的,缺少适当的亲权行使者或者缺少适当的监护人、有游荡或乞讨或不良交友等行为的年满8周岁不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14]14,移送感化院、矫正院和医院等措施也被其1923年实施的《少年法》所吸收,此外,1923年《少年法》还明确将少年裁判所的管辖范围扩张至虞犯少年。而其基于“国家亲权”哲学所设计的少年司法弹性规则又使得其干预范围不受控制的进一步扩大,这也导致少年司法在其后期发展中受到诸多批判。
(二)虞犯行为司法干预严格限制时期
20世纪前期的少年司法制度主要建构于两种基本考虑之上:一方面,少年司法是国家根据“国家亲权”哲学对罪错少年的帮助,其主要目的是为了维护少年自身利益而非追究少年责任,因此,其完全可以不受宪法之正当法律程序原则的约束而采用更加灵活的方式进行,被帮助少年也没有必要拥有刑事被告人的诸种权利;另一方面,机构化的少年矫正方式被认为是避免父母等成人世界对罪错少年造成侵蚀和污染的有效方式,而矫正机构也应采取父母对待子女的方式代表国家对罪错少年进行矫正,因此,交押(commitment)等矫正方式也不被认为是对少年的监禁与惩罚[13]130。然而,此种良好的制度设计初衷却被现实中罪错少年的悲惨遭遇所打破。20世纪五六十年代许多研究证实:矫正机构符合监狱的每一个特征,带栏杆的窗户、紧锁的大门,里面的护理人员并不懂得未成年人的心理,她们对无人照管者和罪错少年所知甚少,他们似乎这么认为,来此的少年就是要接受惩罚[15]328。甚至有学者直接指出,“上锁的门就是上锁的门,不管上锁的动机是什么”,处遇和复归社会之类的委婉说法,在监禁的现实面前是苍白无力的[16]31。自此,福利型少年司法模式开始受到挑战,罪错少年的法律权利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
美国对少年法院干预少年犯罪与少年罪错行为的限制首先是通过联邦最高法院的一系列判例来实现的。在诸多判例中,1967年高尔特案(In re Gault)最具有典型意义,被福克斯(Sanford J.Fox)视为继1825年创立纽约少年庇护所、1899年建立伊利诺伊州少年法院之后对美国少年司法发展产生重大影响的第三起事件[17]1187。该案发生于1964年6月,亚利桑那州15岁的高尔特(Gerald Francis Gault)与其朋友路易斯(Ronald Lewis)因向隔壁太太家打下流电话而被警察拘留。法官拒绝了高尔特母亲提出的让原告出庭辨认声音的请求,直接决定将高尔特送往州少年工艺学校直到其满21岁,这即意味着高尔特要承受长达6年的人身监禁。而同样行为如果是成人所为,其仅需承担5至10美元的罚金或者至多两个月的监禁。为此,高尔特的父母聘请律师提起上诉,上诉律师认为高尔特案并未经过正当法律程序审理,其侵犯了高尔特控诉告知权、律师辩护权、与证人对质权、不自认犯罪权、审阅法庭记录权以及上诉权等六项程序性权利。当上诉材料被递交到联邦最高法院时,联邦最高法院对其前四项权利做出肯定答复,后两项权利因属于州立法权限而不予回复[18]。由此,美国联邦最高法院以判例的形式打破了传统少年司法所追求的尽量减少正式程序对罪错少年进行干预的原意,少年法院对少年犯罪行为和虞犯行为的干预开始受到正当法律程序的限制。
与此同时,随着标签理论的提出,少年司法领域兴起了非犯罪化、分流与非机构化的改革浪潮。标签理论认为,一个人会对其他人(特别是那些有权力者)对自己的行为所下的定义(definitions)做出反应;如果我被称为坏孩子,而且被当作坏孩子对待,我会逐渐对此形成内心形象,而且按照他人对自己形象的模式定位去行为[19]。由此,标签理论直接对少年司法的提前干预思想形成挑战,坦南鲍姆(Frank Tannenbaum)、利默特(Edwin M. Lemert)等标签理论代表人物纷纷认为:少年司法对少年罪错行为尤其是身份罪错行为的提前干预实际上是在促使这些罪错少年向恶性罪错方向发展,其最终将会导致这些罪错少年实施更为严重的犯罪行为。在此背景下,许多学者和官员要求将身份罪错行为从少年罪错中剔除出去,但此观点也遭到了激烈的反驳。从实际效果来看,显然支持非犯罪化者获得了胜利,此后一系列的法令、法规都对祛除、限制身份罪错的司法干预作出规定,如1974年的《少年司法和少年罪错预防法》(Juvenile Justice and Delinquency Prevention Act of 1974)即以将身份罪错与少年犯罪区别对待作为获得联邦少年罪错防治资金的前提[13]147。虽然将身份罪错行为完全非犯罪化的呼声很高,但将其与少年犯罪区别对待并减轻处罚却成为普遍做法。另一受标签理论影响的措施即是分流,所谓分流就是由社会福利部门、教育部门等替代司法机关的审判活动,尽量减少罪错少年进入司法程序的概率,从而减轻标签理论的影响。除非犯罪化、分流之外,非机构化措施也深深地打上了标签理论的烙印。虽然早期的少年司法者鼓吹教养学校等机构能够使少年免受外界侵蚀,并可提供超越家庭的照顾。但是,大批罪错少年被监禁并被作为罪犯对待却是不争的事实,这也为联邦法院裁判的一系列案件所证实。标签论者认为此种举措不仅会造成交叉感染并影响少年的复归,同时也会对其日后的人格发展造成不良影响。为此,各州纷纷废除或者限制机构化监禁在少年司法中的适用,以社区为基础的矫正措施逐渐成为主流。在此后发展中,身份罪错少年逐渐成为社区矫正的主要适用对象,如1974年《少年司法与少年罪错预防法》即明确规定应对身份罪错少年予以非机构化,1976年少年司法和少年罪错预防局则针对身份罪错少年制定了专门的非机构化方案[13]153。
在美国之外,日本于1948年全面修订其《少年法》,其后又经历了多次修订。日本虽然在个别方面扩大了其少年司法的管辖范围,但整体而言,少年司法对少年非行尤其是虞犯少年的干预仍然受到了限制:就审前程序而言,日本少年法规定对未满14周岁的虞犯少年,警察等发现者有义务向儿童相谈所或者福利事务所通报,由后者决定是否送交家庭裁判所,对14周岁以上未满18周岁的虞犯少年,发现者也有权利选择是否送交家庭裁判所;就审理程序而言,虽然日本少年法对证据调查手续、证据法则等没有做出任何规定,但日本司法界普遍认为少年审判应受到来自宪法正当程序的保障[20];就处置措施而言,日本少年法增加了不予处分决定、实验观察等更具社会性的处置方式。我国台湾地区少年司法在其发展过程中,对虞犯少年司法干预最具影响的事件即是“司法院”大法官解释第664号。此“释宪”申请由台湾高雄少年及家事法院法官何明晃提出,他以多年从事少年事件审判的经验,认为台湾少年司法系统常常将无处安置的虞犯少年长期置于教养机构、感化院等监禁化、半监禁化的机构之中,且相关条文内涵模糊不清、司法程序与触法行为相同,这与“宪法”所规定的明确性原则、比例性原则、平等性原则等相违背,同时也侵害了公民的受教育权等基本权利。台湾大法官会议在经过了数个月的商讨之后,于2009年7月31日做出664号解释:国家对逃学、逃家等虞犯少年的干预是为维护少年利益,故不存在“违宪”情形,但其规定却存在内涵不清、范围过广等问题,应尽快修正;就少年逃学、逃家而被施以人身限制部分,与“宪法”之比例原则和保障少年人格尊严的立法意旨相违背,故其应在一个月内失效[21]。至此,逃学、逃家少年不再被送往教养院等监禁机构,大批被监禁少年也得以重回社区。
(三)虞犯行为司法干预存废争议时期
值得注意的是,随着各国少年犯罪形势的恶化,其少年司法的严罚性特征日益明显。美国由于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受到越战、水门事件、学生运动等因素的影响,其经济严重衰退、福利开支大幅减少。在此背景下,美国少年罪错无论是在整体数量、犯罪恶性还是少年罪错在整个刑事犯罪中所占比重都大幅升高。古典犯罪学派趁势兴起,对矫正理论进行批判,并重新提出报应主义、威慑刑理论等。受社会舆论严罚性期待的影响,美国少年司法开始转型:少年法院管辖的最高年龄被降低、最低年龄被升高,对罪错少年适用成人刑事司法系统的弃权程序被启用,罪错少年的监禁适用比率与适用时间提高,少年司法程序日益成人化[13]165。
日本在连续发生数起恶性少年非行事件之后,也对其少年立法进行了严罚化的修改:家庭法院的管辖范围被缩小,侵犯儿童福利的成人事件被剔除;警察等对触法少年的调查权得到扩张;观察保护时间被延长;少年审判中引入了检察官参与制度、公设辅助人制度,被害人被赋予阅览、抄录、旁听和知情权等[22]。在此背景下,少年法院的个别化处遇等措施受到质疑,甚至有激进者主张废除少年法院,将犯罪案件交由刑事法院管辖,身份罪错与无人抚养、被遗弃少年的保护案件交由社会福利机构管辖。20世纪美国著名少年司法研究专家福克斯(Sanford J. Fox)即预言:“美国少年法院将寿终正寝。”[23]赫希(Travis Hirschi)与戈特弗雷德森(Michael Gottfredson)在其自我控制理论(self-control theory)的基础上对少年犯罪与成人犯罪进行对比,并认为二者之间并无太大差别[24]。菲尔德(Barry C. Feld)也认为少年法院在其适用的原则、法律和遵循的程序方面与成人刑事司法相去不远,因此完全可以将少年法院并入刑事法院[13]。当然,此种观点也遭到了反对者的激烈反驳,他们从实证研究、少年权利保护与法治精神等方面展开批判,并提出了较为有力的证据。如佛罗里达州研究人员将3000名被移送成人刑事法庭的少年与3000名没有被移送者进行比较,发现前者比后者更早和更容易重新犯罪[25]。随着少年法院存废之争的持续,少年虞犯行为是应由司法进行干预还是完全归属于福利部门等行政机构的争论也一直延续至今。
三、虞犯行为之非正式干预
从上述域外少年司法发展历程来看,虽然少年虞犯行为司法干预经历了从全面干预到限制干预甚至废除干预的转变,但虞犯行为需要早期干预这一点仍然为学术界和理论界之共识。
美国等国家对虞犯行为司法干预的态度之所以发生如此巨大的转变,司法干预本身存在的种种问题当然是其直接原因,但此种态度转变也同相关国家日渐完善的非正式干预机制息息相关。根据发展理论早期代表人物威廉·麦独孤(William McDougall)的研究,人在出生后的早期内并无道德观念,其行为多受本能冲动支配,而本能作为一种先天的心理倾向,更多的具有情绪成分,此后随着年龄增长和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扩大,人们才会逐渐发展出道德品质与情操并以此指导自己的心理和行为[26]888。据此,人们在青少年时期存在适度的虞犯行为属于正常现象,多数情况下此种虞犯行为会随着少年年龄的增长而逐渐消失,此种情况也被称为虞犯行为的“自愈”现象[27]41。在此情况下,国家权威机构如果贸然以正式干预措施进行提前介入,不仅不能遏制虞犯行为的发展,反而可能使情况进一步恶化。为此,相关国家建立了监护监督制度、亲职教育制度、宵禁制度、传媒管制制度等相互配合的非正式干预体系,以填补正式干预机制之前的空白。据此反观我国,监护监督、亲职教育、宵禁制度、传媒管制等相关制度仍然存在缺漏甚至空白,这也成为我国虞犯行为早期干预机制中的一大硬伤。为此,我们建议将相关制度完善如下:
(一)监护监督
监护制度虽然以保护和发展未成年人权益为制度设计初衷,但监护环境的封闭性以及作为被监护主体的未成年人在监护关系中的相对弱势地位决定了监护权必须受到一定的监督,否则未成年人权益将有受到侵害之虞,近来频繁发生的监护人虐待、性侵、暴力伤害未成年人案件也证实也这一观点。不仅如此,家庭关系紧张也是导致未成年人实施虞犯行为甚至犯罪行为的重要原因。美国犯罪心理学家戴维·亚伯拉罕森(David Abrahamsen)即认为,家庭生活对儿童至关重要,紧张的家庭环境会使儿童充满敌意和恐惧,妨碍其成熟,并为其实施反社会行为或者犯罪行为埋下隐患[26]860。部分对犯罪青少年发展轨迹的研究也证实,经常被父母打骂的青少年中有95%以上的人会经常与同学打架、逃学等[28]。为此,法国、德国、日本、瑞士、巴西、我国的香港和澳门地区纷纷通过其民事立法设立了监护监督制度,以确保监护权的正确行使。反观我国立法,仅有《民法通则》《未成年人保护法》、最高人民法院等四部委《关于依法处理监护人侵害未成年人权益行为若干问题的意见》等少数法律法规中的个别条文对监护监督制度有所涉及,但也仅仅以监护权撤销为关注重点。当下我国监护监督制度存在主体不当、内容不清、标准不明、责任空白等问题,这一问题在新近通过的《民法总则》中也并未得到重视。有鉴于此,笔者建议从我国的实际国情出发,将有监护能力但未担任监护职责的其他近亲属设定为监护监督人。同时,考虑到机构监督的实际操作等问题,可以民政部门作为行政监督机构,由其对自然监督人进行监督和辅助。最后,赋予法院以最终决定和最终监督权。在监督人产生方式方面,首先可由具有监督资格者协商确定并报民政部门备案,发生争议时由人民法院进行指定与裁决。在监督职责方面,应当增加监护人定期述职制度、被监护人信息档案制度、被监护人财产清单与清算制度、监督人强制报告制度、代理被监护人对监护人的诉讼制度等。最后,还应在既有的撤销监护等处置措施基础上增加其他处置措施,以实现责任的衔接与协调。
(二)亲职教育
亲职教育在美国被称为Parental Education,俄罗斯学者将其称为家长教育,我国台湾地区将之译为亲职教育。根据《教育大辞典》的定义,亲职教育是对父母实施的教育,其目的在于改变或加强父母的教育观念,使父母获得抚养、教育子女的知识和技能[29]1216。家庭教育尤其是父母教育对少年儿童的健康成长至关重要,这也为许多研究所证实。但是,正如美国教育家陶森(F.Dodson)所说,生育和抚育是两码事,生了孩子并非意味着自然地具有了抚育子女的智慧和本领,要尽到为人父母的职责就必须彻底了解儿童的成长过程,但许多父母只是从经验中用大量错误换得了这份了解,而如果事先就对儿童发展下功夫,有许多错误都是可以避免的[30]。为此,许多国家和地区都建立了亲职教育制度,如我国台湾地区即在其《少年事件处理法》《儿童及少年福利法》中对实施虞犯行为、触法行为少年的父母规定了强制亲职教育制度,德国等国家甚至将违背亲职的行为规定为犯罪行为[31]90。
据此反观我国,仅在《未成年人保护法》《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中依稀可见亲职教育的踪影,其教育措施也仅是由公安机关对不当履行监护职责的父母进行训诫并责令严加管教。虽然我国在1980年代初即建立了以家长学校为载体的家庭教育指导模式,但受种种因素所限,我国家庭教育存在教育内容滞后、教育流于形式、教育刚性不强等问题。有调查显示,自孩子出生后,所有被调查家长参加亲职教育讲座的平均次数只有2.42次,平均到每人每年则不足0.5次,其中还有近半数家长从未参加过任何亲职教育培训[32];在此背景下,我国有超过2/3的家庭存在教育不当现象,过分保护型、过分干涉型和严厉惩罚型的家长分别占调查对象的30%、30%和7%-10%[30]。此种亲职教育缺失的状况导致家长在面对少年虞犯行为时往往表现得十分无力和无奈,如有研究证实,在未成年人初次实施离家出走行为之前或者之后,89.4%的父母对其进行过相关教育,但2次以上和经常离家出走者所占比重仍然高达73.2%[33]。
有鉴于此,我们建议我国尽快建立亲职教育制度:在教育强制性方面,采用自愿教育和强制教育相结合的方式,对准父母、有良好的子女教育意愿的父母主要采用自愿教育模式,对业已实施虞犯行为甚至触法、犯罪行为少年的父母则应实施强制教育制度,此强制适用的决定权应交由人民法院行使,并规定明确的适用标准和适用程序,对拒不参加参加亲职教育者可借鉴域外做法设立累进罚金制度,并由公安机关协助执行;在教育内容方面,建议借鉴美国PAT(Parent As Teacher)国家中心和澳大利亚家长充权项目模式[32],由国家成立权威研究机构,在科学调研的基础上,根据家长的虞犯行为矫正需求、虞犯行为预防需求、少年儿童发展需求等不同需求层次设计不同的教育内容;在教育机关方面,改变我国现有立法由公安机关进行教育的模式,改由专业的教育机构担任教育职责,如辽宁省试点的主管机关与高校联合教育模式[32],同时借鉴台湾做法,设立由中央到地方的专门管理机构,此机构以各地方政府直接担当为宜;在适用对象方面,以“普惠型”亲职教育为基础,重点针对留守家庭、单亲家庭、经济困难家庭、监护侵害家庭等高风险家庭家长进行教育;在具体适用方面,可建立综合发现机制,将公安、民政、法院等职能部门与监护监督制度相结合,实现亲职教育适用的最大范围覆盖。
(三)教师惩戒权
与父母不可能随着子女的出生而自然具备抚养和教育子女的知识和技能相类似,少年儿童也不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自然具备成人社会的知识储备要求和社会化技能。为此,教育就显得日益重要。在此过程中,由于少年儿童因年龄所限,并不具备完全的自律能力,因而他律就成为其学习和社会化过程中必不可少的因素。就学校教育而言,他律的具体表现即为学校的诸种规章制度以及教师和学校的惩戒制度。惩戒制度的存在有其必要性,这不仅可以保证正常的教学秩序,进而保障其他学生的受教育权利,而且如上所述,适当的惩戒措施有利于受惩戒者本身的健康发展。从域外教师惩戒制度的发展来看,其大体经历了任意惩戒或惩罚时期、惩戒限制时期以及惩戒法治化时期三个发展阶段。目前,美国、日本、英国、韩国、我国台湾地区均通过国家立法的形式确立了教师惩戒权,如日本《学校教育法》第11条即明确规定,校长或教师可根据教育上的必要,按主管部门的规定,对学生进行惩戒[34]274。不仅如此,其对惩戒主体、惩戒措施、惩戒对象、惩戒程序、权利救济和责任追究等均有明确细致的规定。反观我国,虽然有部分法律对教师惩戒制度有所涉及,但教师惩戒权并未在法律中正式确立。而且,上述法律整体较为零散且缺乏可操作性。此种状况导致我国教育制度尤其是虞犯行为少年学校干预制度向两个极端化方向发展:一方面,在教师惩戒制度定位不明的情况下,虽然我国法律对体罚与变相体罚未成年人多有禁止,但体罚与惩戒界限的模糊性使得部分教师和学校仍然在惩戒的名义下对未成年学生尤其是虞犯少年进行体罚与变相体罚;另一方面,部分教师因为法律对体罚与惩戒的界定不明且教师惩戒权并无明确的法律依据,为避免承担相关责任而对少年虞犯行为放任自流,导致相关虞犯少年得不到及时的干预与矫正。为此,我们在借鉴国外经验并结合我国实际的基础上建议将我国的教师惩戒制度做如下设计:首先,应当在《教师法》等相关立法中明确赋予教师以惩戒权,将其与授课自由权、授课内容编辑权等共同规定为教师的基本职业权利;其次,顺应《儿童权利公约》等相关国际条约的要求,严禁对学生采用体罚或者其他有辱人格的惩戒方式,在此我们可借鉴日本等国家的做法,明确提出体罚行为的类型或者标准,以避免体罚与惩戒行为界限模糊的弊端;再次,在现有基础上增加惩戒措施类型,如口头警告、取消某种优惠待遇、留校、没收违规物品、强制参加心理咨询等矫正活动、短期停学、长期停学、强制转入特殊矫正学校等,同时,将不同的惩戒措施分别赋予教师、校长、学校教育委员会等主体行使;最后,完善程序设置,包括惩戒措施适用程序、惩戒监督机制及监督程序、被惩戒者权利救济程序。此处值得注意的是权利救济程序,考虑到我国实践中此类纠纷的救济困境,可增设惩戒听证程序、完善既有的申诉程序、明确诉讼程序,此类纠纷因其性质及双方主体均具有特殊性,宜将其纳入少年司法的管辖范围之中。此外,惩戒程序中的责任配置与责任追究机制亦必不可少,其责任种类也应进行适当扩充。
(四)未成年人宵禁
所谓未成年人宵禁制度,主要是指在特定时间内限制或禁止未成年人外出或者在特定场所活动的制度。夜晚是酒吧、KTV等娱乐场所的高峰营业时期,此时也是青少年社会控制相对松懈的阶段,因此,少年虞犯行为、少年犯罪行为在夜间多呈高发态势。有研究者在对随机抽取的100例少年犯罪案件进行考察后发现,盗窃、抢劫、故意伤害、寻衅滋事等少年多发案件中有81.5%的案件发生在夜间[35]。为此,英国、美国、法国、俄罗斯等许多国家和地区设立了少年宵禁制度,如英国即在其1998年《犯罪与扰乱秩序法》中规定,各地方政府可根据本地情况向内务部提出实行儿童宵禁项目,项目一旦被批准,该地区即以发布宵禁通告的方式实施“本地儿童宵禁”,宵禁的最长期限为90天,宵禁期间,10岁以下儿童(或由当地政府规定年龄)在没有父母或者其他18岁以上的成年人带领的情况下,禁止在晚6点到早9点期间滞留于公共场所,否则警察即有权将其带回家或者通知社区的社会工作部门[36]。从我国立法来看,我国《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中也对宵禁制度有所规定,如第14条禁止未成年人夜不归宿,第16条要求父母、其他监护人、寄宿制学校等对擅自夜不归宿的未成年人及时进行查找,收留夜不归宿的未成年人应当征得其父母或其他监护人同意等。但是,与国外相比,我国的未成年人宵禁制度仍然显得过于粗糙,宵禁的适用时间、主管机关、适用程序等并未有具体规定。为此,我们建议对我国未成年人宵禁制度做如下改进:在适用对象上,考虑到我国《刑法》《治安管理处罚法》等相关法律对未成年人越轨行为做出反应的年龄规定,宜将我国宵禁制度的适用对象界定为14周岁以下少年;在适用时间上,宜将宵禁的适用时间规定为每天的晚10点到早6点,节假日时间可做适当调整,如此可在考虑未成年人社会需求的同时保证其睡眠需要;在适用程序上,虽然域外许多国家和地区采用的是“申请+批准”模式,但考虑到我国此前并未实施过宵禁制度,申请主体与批准机关也难以确定,为避免该制度流于形式,可由国务院直接做出统一规定;在执行监督上,可借鉴国外做法,由警察进行巡逻监督,发现违反宵禁规定少年时,及时通知家长或其他监护人,在无法及时通知的情况下,可对其采用保护管束性措施并及时通知少年福利机构、街道居委会等部门;我国现有立法中少年擅自夜不归宿、收留夜不归宿少年等规定也应进一步细化,如明确擅自收留者的法律责任等。
(五)交往限制
根据美国现代著名社会学家与犯罪学家埃德温·哈丁·萨瑟兰(Edwin Hardin Sutherland)的不同交往理论,人们的犯罪行为多是在与他人交流过程中通过与他人的互动而习得的,此种学习过程多发生在亲密的人群之中,他们多通过交往对象来获得犯罪动机与犯罪技巧,当周围人群中赞同违法的解释超过反对违法的解释时,行为人就很有可能变成违法者[26]。该理论的继承者,美国社会学家罗纳德·艾克斯(Ronald L. Akers)通过对3065名有吸毒和酗酒行为的男女青少年进行研究后发现,吸毒、酗酒与社会学习因素特别是不同交往之间有很大关系[26]。这一结论也为我国的相关实证研究所证实,如天津市在对两万余名在押青少年犯罪人进行调查后发现,有高达87.1%的青少年犯罪人认为他们实施犯罪行为主要是受到周围朋友的影响[37]。由此可见,朋辈交往对青少年的行为发展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这也成为构建我国未成年人交往限制制度的重要依据。从我国既有立法来看,我国已经初具未成年人交往限制制度的雏形,如《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第17条、25条、29条、33条等相关规定。但是,我国未成年人交往限制制度在整体上仍然缺乏系统设计。为此,建议对该制度做如下改进:首先,应当明确未成年人交往限制的目标对象即不良同伴和不良组织的范围,我们认为,具有虞犯行为、触法行为、违警行为、犯罪行为者均可认定为不良同伴,由具有上述行为者组成或者以实施上述行为为主要目的的团伙性组织均可认定为不良组织;其次,应当完善我国的未成年人正向发展机制,如加强对未成年人的同伴教育、建立完善未成年人矛盾化解机制、构建未成年人正向交友平台等,以此减少未成年人对不良同伴和不良组织的社交和心理归属需求;再次,建立完善我国未成年人不良交往预警机制,提高家长、学校、社区等对未成年人不良交往特征的识别能力,如衣着打扮、行为方式的改变等,同时对教唆、引诱、欺骗、胁迫未成年人参加不良组织者及时进行处理;最后,对于业已参加不良组织或者进行不良交往的未成年人,应当通过社工外展活动、警察街头商谈活动等及时发现并进行专业转介矫正,以使其脱离不良交往影响。
(六)不良场所禁入
与不良交往行为相类似,未成年人经常出入不良场所也会对其行为方式产生影响。有学者通过对比性实证研究发现,普通学生比未成年犯更经常去图书馆、青少年宫、文化馆活动,前者的比例分别比后者高出33.0%、10.6%、7.9%,前者比例分别约是后者比例的6倍、5倍、3倍;与此相反,未成年犯比普通学生更经常去歌舞厅、网吧、台球厅、游戏厅、洗浴中心、电影院等场所,前者比例分别约是后者的10.0倍、7.9倍、7.8倍、7.3倍[38]。另有学者在对重庆市某中院及其下辖基层法院2008年上半年受理的未成年人犯罪案件进行统计后发现,有133起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直接发生于网吧等不良场所,由网吧诱发的未成年人刑事案件涉案人数占总人数的六成以上[39]。由此,构建我国未成年人不良场所禁入制度之必要性可见一斑。从我国既有法律规定来看,我国相关法律法规对该制度已有所设计,如《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管理条例》全面禁止网吧接纳未成年人的规定、《未成年人保护法》严禁将营业性歌舞娱乐场所以及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等未成年人不适宜进入的场所开设在学校周边的规定等。但是,相关规定的实施效果却并不理想,如在被问及是否因未满18周岁而不能正常进入网吧时,有五分之一的被调查未成年人表示相当容易进入[40],甚至有研究者实地考察后发现几乎所有网吧均存在容纳未成年人的现象。为此,我们建议对我国未成年人不良场所禁入制度做如下改进:第一,明确不良场所的范围。考虑到我国社会正处于快速转型期,一方面可通过具体列举的方式对未成年人不良场所作出规定,将电子游戏厅、歌舞厅、台球厅、网吧、酒吧、洗浴中心、按摩保健场所等纳入其中,另一方面设计具体标准,以期将未来可能出现的不宜场所纳入其中。第二,明确各场所的管辖主体或者牵头部门。纵观各类不良场所管辖弊端可以发现,管辖混乱现象普遍存在,如我国酒吧即存在定位不明且工商、文化、药检、食品监督、卫生、劳保、公安等部门各管一段且分工不清的状况[41],我国网吧主管部门则经历了公安机关、信息产业部、文化管理部门等的轮转。为此,必须切实厘清部门职责,改变这一多头共管的混乱局面。第三,加强制度与技术建设。一方面,要改变既有的运动式执法模式,建立长效监督执法与定期专项整治相结合的工作模式;另一方面,加强技术投入,如将网吧实名制进入制度和公安机关摄像监控网络建设相结合等。第四,由政府或儿童福利部门加强儿童公益设施建设。公益设施缺位是导致未成年人进入不良场所的重要原因,如有学者在对比研究后发现,经济欠发达地区未成年人因接触网络机会较少而比经济发达地区未成年人更容易进入网吧并被当做网瘾少年对待[40]。甚至有报告指出,我国平均每7万名未成年人才拥有1个活动场所[42]。为此,必须增设未成年人公益活动场所,以降低其进入不良场所的风险并消除因资源不均而带来的“污名化”现象。第五,加强家庭、学校建设。家庭、学校等关爱和教育的缺失也是未成年人进入不良场所的推动力,因此也必须在此方面作出努力。
(七)传媒管理
根据美国心理学家、现代学习理论的奠基人艾伯特·班都拉(Albert Bandura)的研究,人们并不是生来即具有犯罪技能,这些技能必须通过学习来获得,其学习的方式又可以划分为观察学习和亲历学习两种,在人类知识更新日益频繁的今天,观察学习中的符号示范学习即通过广播、电视、电影等形式的学习变得日益普遍[26]960,这也为我们进行犯罪预防尤其是未成年人虞犯行为、犯罪行为预防提供了新的思路。我国学者进行的相关实证研究也为该结论提供了支持,如有研究者在对未成年犯和普通未成年人进行对比研究后发现,未成年人对含有暴力内容电影、电视、影碟或视频的兴趣每上升一个层级,则该未成年人实施犯罪的比率将提升1.834倍;如果未成年人上网最常做的事为看和暴力有关的内容,则其实施犯罪的比率将增加10.279倍[43]。有鉴于此,域外许多国家和地区如美国、法国、德国、韩国、新加坡、我国的香港和台湾地区等纷纷建立了影视分级、网络分级等传媒管理和传媒限制制度,以切实保护未成年人免受不良媒体信息的侵害。反观我国,不仅网络分级等新兴制度未在我国建立,影视分级等在域外较为成熟的做法也并未在我国出现。此种情况一方面造成未成年人因大量接触不良媒体信息而实施虞犯行为、触法行为等越轨行为,另一方面成人社会也因为国家在未成年人保护方面采用的此种折中措施而在信息与言论自由权方面受到限制。为此,我们建议在我国构建以影视分级、网络分级为主体的未成年人传媒限制制度,设计如下:第一,借鉴国外做法,将裸体、性及相关材料、语言、暴力等作为分类主题,并在各主题之下根据我国伦理道德要求以及青少年发育情况确定若干级别[44]。第二,在适用刚性方面,为避免强制分级对言论自由限制的诟病以及自愿分级易于流于形式的弊端,我国可采用自愿分级与强制分级相结合的做法,即在信息发布者或者网络服务商等发布相关信息之前,采用类似美国ICRA(Internet Content Rating Association)组织设计的“ICRA问卷”等形式将相关信息录入,然后由系统自动生成媒体内容级别并进行标识;随后,由政府机构对媒体内容是否分级以及分级的有效与否进行检查,对不符合规定者征收重税或者取消优惠等。第三,在管理机构方面,考虑到我国已经设有影视审查部门,可由其继续负责媒体分级管理及其检查等工作。第四,在具体适用方面,我国可通过立法要求电视、电脑等终端生产商在进行产品生产时安装传媒标识识别设备或相关软件,以识别、过滤或屏蔽相关标识下的媒体内容,当然,此种屏蔽与否的选择权是否应交由家长等主体来行使还存在争议。最后,应赋予影视制作者、网络服务商等主体以救济权利并对违反分级规定者规定相应的处置措施。
四、虞犯行为之正式干预
虽然如上所述,非正式干预对于预防和矫正少年虞犯行为十分重要,但是各种非正式干预措施因其适用范围所限,并不能实现对少年虞犯行为的完全覆盖。而且,诸种少年虞犯行为的社会干预措施重点在于预防少年虞犯行为的发生,在少年业已实施虞犯行为时,上述非正式干预措施仅能进行初期矫正,对多次实施虞犯行为或者实施危险性较高虞犯行为的少年,非正式干预措施经常会出现失灵现象。在此情况下,必须以国家的正式干预机制对其进行补位和保障,现做如下阐述:
(一)行政干预
就虞犯行为正式干预机制而言,行政干预因其干预的主动性、干预范围的广泛性等特征而为各国政府所关注。其中,警察部门受其社会治安管理、犯罪预防与犯罪侦查等职责影响,在虞犯行为预防和矫正工作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而虞犯行为的发生往往同一国社会福利制度建设息息相关,因此,社会福利部门对虞犯行为的干预也必不可少。现就我国少年虞犯行为警察干预、福利干预制度设计如下:
1.虞犯行为警察干预的制度设计
警察作为社会治理的重要力量,其往往最先接触治安案件、犯罪案件等事件,受其职责范围与工作性质等影响,少年犯罪案件、少年触法案件、少年虞犯案件等少年事件也多由警察部门最初发现与处置。为此,美国、日本、德国、英国、我国香港、台湾地区均设立了专门的少年警察队伍,以切实保障少年权益并对其越轨行为做出恰当处置。整体而言,在设有少年警察制度的国家,其职责范围虽然有所迥异,但均包括对少年虞犯行为的干预处置。但就我国而言,由于我国既有的少年司法体系是以少年刑事案件为中心的制度模式,所谓少年警察的职责更多倾向于少年刑事案件的侦查与提交审查起诉等活动。与此同时,少年违警行为与少年触法行为也为少年警务所包容,但少年虞犯行为在我国几乎完全被排除于少年警务之外,有关警察部门干预少年虞犯行为的法律规定也并不具有实际操作性。为保证少年虞犯行为得到及时有效的干预,我们在借鉴域外各个国家和地区经验的基础之上,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对我国少年虞犯行为警察干预机制做如下设计:第一,应当确立警察部门的虞犯行为发现机制。根据我国相关立法对未成年人保护范围的空间界定,未成年人保护分为家庭保护、学校保护、社会保护以及社区保护,在此空间范围内,家庭、学校、社区均有其具体的制度载体与执行部门,但社会保护制度与机构载体却一直缺位。为此,我们建议根据警察工作特点,结合日本少年警察之街头辅导制度,由警察部门在日常巡逻过程中承担虞犯少年社会发现任务,对工作过程中所发现的轻微虞犯行为少年进行登记和现场辅导等[45],同时相关警务人员亦应尽快通知该少年的家长、学校等监管主体。此举可同时与上海等地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工作核心指标体系建设中的青少年违法犯罪核心指标采集机制相结合,逐步建立虞犯行为少年信息系统,为其后期矫正及跟踪等提供依据,改变我国实践中因虞犯行为少年流动而造成的矫正断层现象。第二,建立非正式干预警察补位机制。在前述诸多非正式干预机制中,警察部门常常也扮演重要角色,如监护监督机制中警察对被监护人的紧急情况带离权、强制亲职教育情况下的警察协助执行、查处虞犯预防行为过程中对相关单位和个人的惩处及移送处理等。为此,必须根据我国非正式干预体系的发展需要,落实警察部门的保障与补位功能。第三,赋予警察对虞犯少年群体的干预权。对于实施轻微虞犯行为的少年,应结合英国、美国等国家的立法经验,赋予警察以训诫、警告、责令家庭管教、签订行为协议、联系少年辅导等处置权。对违反警告或行为协议以及多次实施虞犯行为等高危虞犯少年,警察部门可将其向少年司法部门转送。
2.虞犯行为福利部门干预的制度设计
虽然几经改变,但福利化一直是少年司法的重要特征,这也是李斯特“最好的社会政策即是最好的刑事政策”的重要体现。纵观各国少年司法体系,少年福利制度都在预防和矫正少年虞犯行为、少年触法行为、少年犯罪行为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如日本即根据其《儿童福利法》设立了儿童相谈所等机构,儿童相谈所可以就儿童各项问题与家庭进行商谈并对儿童家庭进行调查评估,提供必要的指导[46]:我国台湾地区《儿童及少年福利法》也规定,儿童福利措施应当包括对儿童及家庭提供咨询辅导服务、对无谋生能力且无父母或抚养人的少年提供生活和医疗扶助、提供儿童及少年适当休闲娱乐活动等。从理论视角而言,此种举措也符合赫希社会控制理论中有关依恋、奉献、投入、信念等方面的要求[47]。反观我国,随着社会转型,父母、学校等主体对青少年群体的教育控制能力越来越弱,大量青少年在逃学辍学后却因年龄等原因而并未立即进入社会职场,这导致其在家庭、学校控制与社会控制之间游荡,而其闲散状态又会为其实施虞犯行为留下契机。在此背景下,由于我国奉行“补缺型”儿童福利政策,其所针对的对象仅为孤残儿童等困境儿童,家庭辅导等事前预防性福利措施缺位,这也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养肥了再杀”的养猪困局。有鉴于此,我国必须加快儿童福利制度建设:首先,将现行试点的“适度普惠型”儿童福利制度在较发达地区进行普及,并进行全面普惠型儿童福利制度试点,增加儿童健康、卫生、娱乐等方面的建设支出,为少年虞犯行为的预防提供保障,避免相关调查中部分地区的少年儿童因资源缺乏而被迫流连于不良场所等现象的发生。其次,儿童福利机构应当对家庭、学校等非正式干预主体形成补位。为此,福利机构应当为家庭等主体提供发育迟缓儿童早期疗养服务、儿童托育服务、家庭咨询辅导服务、亲职教育服务、替代监护服务等多项服务措施,以使虞犯行为非正式干预制度切实落地。最后,儿童福利机构应当加强自身制度与人员建设,对司法机关判处福利性处置措施的虞犯少年进行适当安置、紧急戒治等有效干预。
(二)司法干预
1.虞犯行为司法干预的必要性分析
虽然许多西方学者力主将少年虞犯事件排除于少年司法管辖范围之外,认为将其完全交由社会福利机构等行政部门进行干预可能更为合理,但从我国实践来看,此种主张仍然有待研究。与西方国家司法干预为主的发展路径不同,我国将一般不良行为与严重不良行为完全交由社会及行政部门进行干预,但此种做法却问题重重:封闭性的行政执法程序极具随意性,在保护青少年的名义下,工读教育等矫正措施可由公安机关或者教育部门决定是否适用于严重不良行为少年,在此过程中,作为相对方的少年群体基本不享有类似刑事被告人或者犯罪嫌疑人的程序性权利;就工读教育措施而言,《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修订后,其适用方式的变化一方面导致该措施的适用刚性不强,大量应当送往工读学校进行矫正的不良行为青少年游离于矫正体系之外,另一方面,程序的自由选择性也为家庭、学校等主体进行责任转嫁提供了契机;在缺乏司法干预的情况下,收容教养、收容教育、工读教育、强制戒毒等监禁性措施被大量适用于严重不良行为甚至一般不良行为少年,此类监督性措施在背离“儿童最大利益原则”的同时也会造成标签效应、交叉感染等问题。为此,必须引入司法干预机制,通过“司法先议”等措施对家长、学校、公安机关等责任主体和执行部门形成制约和监督,以避免上述诸问题的发生。
2.虞犯行为司法干预的限度分析
虽然如上所述,少年虞犯行为司法干预有其必要性,但考虑到司法干预过早介入虞犯行为可能产生的标签效应等不良影响,其干预必须有相应的限度要求。而且,司法的滞后性、被动性特征也决定了其并不适宜积极全面的介入少年虞犯行为,这也是出于保障司法干预质量的考量。为此,我们主张对我国少年虞犯行为早期干预进行“漏斗式”的制度设计,将大量的轻微虞犯行为如旷课逃学、离家出走、不服父母管教、抽烟喝酒、出入不良场所等交由社会及行政部门进行干预。对于多次实施轻微不良行为且社会与行政干预效果甚微或者实施携带管制刀具、治安触法行为等高危虞犯行为者,应将其纳入司法干预范畴,由司法机关经过调查、裁决而对其适用恰当的干预处置措施。
3.虞犯行为司法干预的制度设计
虽然早期干预的初衷是对青少年虞犯行为进行早期矫正与保护,避免其陷入违法犯罪的深渊。但是,此种干预在实质上都会对少年群体的权利造成不同程度的限制或者损害。因此,其必须受到程序等方面的限制以避免国家公权以“爱的名义”对青少年进行侵害。否则,不仅会造成少年权利的减损,同时也会因为其侵害现实而引起社会公众对司法干预的反对,并最终不利于少年司法的健康发展,这也为美国少年司法的发展历程所证实。为此,我们建议引入“司法先议”制度,即对少年虞犯行为尤其是程度较重的虞犯行为事件如携带管制刀具、治安触法行为等在被发现后首先应当移送审判机关,并赋予虞犯少年群体以质证权、合适成年人在场权、程序救济权等权利,由审判机关在全面了解情况后做出适当的处置和裁决。如此,也可对学校、公安机关等责任主体形成监督和制约,改变我国当下少年严重不良行为干预过程中执法随意性过大与程序刚性缺失同时并存的局面,并最终实现虞犯行为司法干预的制度设计初衷。此外,鉴于我国既有的司法干预措施种类单一且监禁性措施居多的状况,我国可增设假日辅导、保护管束、保护观察、福利机构适当安置、义务负担、社会服务令等措施,以弥补我国在此方面的缺憾。
五、结 语
2016年10月,孟建柱在全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创新工作会议上明确提出要“完善未成年人不良行为早期干预机制”,这是针对目前我国未成年人犯罪预防制度设计中存在“养大了再杀,养肥了再打”的硬伤所提出的针对性要求。然而,不良行为早期干预机制是一个需要认真对待的议题,如果制度设计不慎则可能出现事与愿违的结果。
鉴于不良行为这一概念的含义模糊,本文使用了虞犯行为这一更加精确的概念,并在考察国外对虞犯行为干预的历史变迁、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对如何构建本土化的虞犯行为早期干预制度提出了初步的意见。希望本文的探索对于我国未成年人犯罪预防制度的进一步完善能够有所裨益。
[1] 姚建龙.论《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的修订[J].法学评论,2014(5):121.
[2] [日]田口守一.少年审判[M]//[日]西原春夫:日本刑事法的重要问题,金光旭,等 译.北京:法律出版社,成文堂,2000.
[3] 姚建龙.少年刑法与刑法变革[M].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5.
[4] 康树华.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若干理论问题研究[J].政法学刊,2000(1).
[5] 共青团北京市委员会课题组.北京市青少年不良行为相关问题调研报告[J].中国青年研究,2015(5).
[6] 张鸿巍.未成年人身份过错浅析[J].河北法学,2013(7).
[7] 吴海航,黄凤兰.中日未成年人事件诸概念及其分类标准比较[J].中国青年研究,2008(3).
[8] 高晓莹.少年司法制度论纲[J].中国刑事法杂志,2010(7).
[9] 高维俭,胡印富.少年虞犯制度比较研究[J].预防青少年犯罪研究,2013(4).
[10] 康树华.论世界上第一部青少年法规的产生及其主要内容[J].国外法学,1986(1).
[11] 刘继同.中国青少年研究典范的战略转变与儿童福利政策框架的战略思考[J].中国青年研究,2006(3).
[12] 刘灿华.德国、日本少年司法制度的变迁及其启示[J]时代法学,2011(6)
[13] 姚建龙.超越刑事司法:美国少年司法史纲[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9.
[14] 尹琳.日本少年法研究[M].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5.
[15] [美]罗森海姆.少年司法的一个世纪[M].高维俭 译.北京:北京商务印书馆,2008.
[16] [美]乔治·P·弗莱特.刑法的基本概念[M].王世洲,等 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
[17] Sanford J.Fox.Justice Reform: An Historical Perspective[J]. Stanford Law Review, Vol. 22, No.6, Jun., 1970.
[18] 姚建龙.美国少年司法变迁中的正当法律程序改革及其借鉴[J].求是学刊,2009(3).
[19] 姚建龙.标签理论及其对美国少年司法改革之影响[J].犯罪研究,2007(4).
[20] 刘建利.日本少年司法制度及其对我国的启示[J].青少年犯罪问题,2013(2).
[21] 郑瑞隆.“以教代罚”和“以辅代惩”——论台湾少年“司法”特性[J].广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3).
[22] 华瑀欣.日本少年法的发展与展望[J].青少年犯罪问题,2014(6).
[23] [美]桑德斯·J·福克斯.姜永琳 译.美国少年法院的过去、现在与未来[J].中外法刊,1988(1).
[24] Travis Hirschi, Michael Gottfredson. The juvenile justice system[J]. Crime and Delinquency, Vol.39,No.2,1993,pp.262-271.
[25] Cindy Lederman. Juvenile Court: Putting Research To Work for Prevention[J]. Juvenile Justice, Volume VL, Number 2, December 1999, p.24.
[26] 吴宗宪.西方犯罪学史(第三卷)[M].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10.
[27] 姚建龙.青少年犯罪与司法论要[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4.
[28] 屈智勇,邹泓.青少年违法犯罪的基本特点及发展轨迹研究[J].中国青年研究,2007(1).
[29] 顾明远.教育大辞典(增订合编本)[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8.
[30] 陈钟林.谈发展我国的亲职教育[J].青年研究,2000(8).
[31] 德国刑法典[M].徐久生,庄敬华 译.北京:中国方正出版社,2004.
[32] 盖笑松,王海英.我国亲职教育的发展状况与推进策略[J].东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6).
[33] 关颖.未成年人不良行为及其影响因素分析——基于全国未成年犯的调查[J].青少年犯罪问题,2013(2).
[34] [日]文部省大臣官房总务课法令研究会.学校管理运营实务必携(第七次改订)第一法规[M].昭和53年版.
[35] 龚一海,陈少琛,刘友水.对未成年人宵禁的立法思考[J].青少年犯罪问题,2006(4).
[36] 李玫瑾.犯罪预防的新思路与实践——英国〈犯罪与扰乱秩序法〉述评[J].公安大学学报,2001(4).
[37] 丛梅.不良信息对青少年犯罪的影响性因素分析[J].青少年犯罪问题,2013(4).
[38] 路琦,等.2013年我国未成年犯抽样调查分析报告(下)[J].青少年犯罪问题,2014(4).
[39] 陈伟.网吧管理与未成年人犯罪的实证分析[J].上海公安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9(4).
[40] 李玫瑾.未成年人进网吧屡禁不止原因调查——以贵州和北京两地未成年人为对象[J].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5).
[41] 未成年人涉酒吧犯罪研究课题组.未成年人涉酒吧犯罪的动向与对策[J].预防青少年犯罪研究,2013(2).
[42] “青少年犯罪问题”编辑部.数百万“网瘾少年”现象引发的思考[J].青少年犯罪问题,2008(5).
[43] 赵军,彭志刚,彭红彬.暴力资讯与未成年人犯罪实证研究——以社会学习理论为主要修正对象[J].江西财经大学学报,2010(3).
[44] 张志铭,李若兰.内容分级制度视角下的网络色情淫秽治理[J].浙江社会科学,2013(6).
[45] 吴海航.街头辅导与少年商谈——日本不良少年矫正教育的启示[J].中国青年研究,2010(4).
[46] 日本儿童福利法[J].沈重摘 译.国外法学,1980(4).
[47] 吴宗宪.赫希社会控制理论述评[J].预防青少年犯罪研究,2013(6).
(责任编辑 卢 虎)
2017-01-19
姚建龙,上海政法学院刑事司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 刑事法学,少年司法。
D922.7
A
1671-511X(2017)03-0051-0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