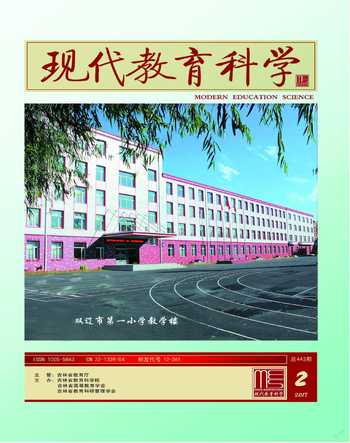影响师生冲突的结构因素分析
展学超
[摘要]师生冲突是发生在学校组织中的一种普遍现象,对师生关系的和谐发展造成了一定的影响。在影响师生冲突的众多因素中,最主要的结构性影响因素是学校的组织结构、文化结构、制度结构和课程结构。促进学校组织结构控制职能的弱化与服务职能的增强、文化结构“工具理性”的弱化与“价值理性”的增强、制度结构选拔功能的弱化与育人功能的增强、课程结构意识形态本位的弱化与学生本位的增强,是缓解师生冲突的四项重要策略。
[关键词]师生冲突;结构因素;服务职能;价值理性;学生本位
[中图分类号] G515[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1005-5843(2017)02-0076-06
[DOI]1013980/jcnkixdjykx201702014师生冲突是师生关系走向和谐的重要影响因素。近年来,随着师生之间在言语、行为等方面相互攻击事件的增多,师生关系问题成了引人瞩目的焦点。著名德国社会学家齐美尔和美国社会学家科塞分别在其各自的著作——《冲突论》和《社会冲突的功能》中提出了功能冲突论的观点,认为非暴力的冲突对组织具有正向功能。国内也有持类似观点的学者[1]。但在教学实践中,没有哪位教师或学生会故意挑起事端,从而让班级及学校显得更“富有生命力”[2]。
目前已有研究对引发师生冲突原因的分析集中于教师和学生两个方面,同时所提出的师生冲突消解策略又集中于教师身上,仿佛只要教师专业水平提升了,师生冲突就自然消失了。但实际上,冲突是伴随着组织的存在而普遍存在的[3],揭示那些隐藏在学校管理及教学中的影响师生冲突的结构因素是笔者关注的焦点。
一、师生冲突概念界说
(一)冲突
社会学中对冲突的关注,始于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对社会分工及人的异化的研究。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看来,社会生产在满足了人们的基本需求之后便产生了分工,从而导致了生产活动组织形式的精细化,剥夺了人们决定自己生产活动的能力,人们的劳动构成了社会生产的一个个齿轮,于是人便被异化了。马克思认为,资源分配不平等是导致社会冲突的根本原因,并且社会冲突最终会演变成为阶级斗争,从而导致社会形态的变革[4]。与马克思、恩格斯的阶级斗争论观点相类似,韦伯将冲突视为传统法权社会中人们与占有财富、权利及声望的精英阶层的紧张状态、仇恨甚至斗争[5]。辩证冲突论者达伦多夫认为冲突根植于社会结构之中,是“紧张、争夺、竞争以及社会力量之间明显的冲撞”,是辩证地存在着的,即冲突现象会导致一组新的对抗利益的产生,在某种条件下这组对抗利益又会引发新的冲突[6]。
与以上关于冲突的广义解释相比,特纳对冲突做了狭义的理解:“冲突即各派之间直接的和公开的旨在遏制各自对手并实现自己目的的互动。”[7]而郑杭生则认为:“冲突是人与人或群体与群体之间为了某种目标或价值观念而相互斗争、压制、破坏以致消灭对方的方式与过程。”[8]
综上可知,冲突是组织中普遍存在着的现象。一方面冲突会促进组织结构的整合和优化,另一方面冲突也造成了利益对抗双方直接和公开的争斗。学校作为基本的社会组织,其管理和教学工作必须符合统治阶层的意志,于是教师便充当了一定的社会代表者角色,然而其拥有的成人文化与青少年心智尚不健全的现状不能相统一,于是便导致了师生冲突的发生。
(二)师生冲突
与冲突相对应,师生冲突的概念也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的师生冲突概念相对含混,主要阐述了师生冲突产生的原因及表现;狭义的师生冲突则将视角聚焦于师生互动的过程之中,注重在教学实践中进行更加具体和更富有针对性的探讨。
最早使用師生冲突概念的是沃勒。他指出了师生之间是“制度化的支配与从属”关系,存在着不可避免的冲突因素,但未将冲突的概念明确化。伍兹在《社会学与学校》中阐述了“师生关系冲突模型”理论,把师生冲突指向学生的“逃避、不妥协及叛逆”等行为表现[9]。我国台湾学者王桂丛认为:“师生冲突是在学校中相互共存的师生之间,彼此觉得想要达到的目标不能协调一致,或者一方觉得另一方干扰了其达到目标或获得报酬时表现出的对立和不和状态。”[10]狭义的师生冲突观认为“冲突是师生由于在目标、价值观、资源多寡等方面的差异而产生的对立、分歧和相互干扰的教育教学互动”[11]。
综上,师生冲突是指在学校管理及教学实践中,学生因阶层背景、文化、价值观等差异与学校所体现的统治阶层意识形态及社会文化不统一,而产生的师生之间公开的、直接的相互遏制对方以实现自身目的的互动过程。由此可见,影响师生冲突的因素有主客观之分。主观因素有师生之间在文化、价值观等方面的差异,而客观因素则主要体现在规制学校管理和教育教学的各项结构之中。
二、影响师生冲突的结构因素
对于结构的理解,在西方社会学界也有较大的争论。其中,吉登斯的观念更为全面、深刻,他認为结构既不是左右人们行为而无法改变的制约因素,也不是仅存于人们“知识库”之中的意识,可以被随意地改造。他提出了“结构的二重性”理论,认为“结构是循环往复的卷入社会系统再生产的规则与资源,只作为记忆痕迹的人类认知能力的生物基础而存在,具体体现在行动之中”[12]。结构二重性中的“规则”主要包含了社会生活中的“一般化程序、构成性和管制性规则、规定及习惯”等[13]。而结构二重性中的“资源”则包含了“配置性资源”和“权威性资源”,前者指向物质性资源,后者指向非物质性资源——人的支配地位[14]。因此,结构既是规制人们行为的模式、规则、制度,同时也是人们在互动过程中产生的角色地位、价值观及习惯,二者统一于人们的社会行动之中。学校作为统治阶层意识形态宣传的窗口,必然包含了众多规制性的结构因素,左右了师生关系的发展且相对难以改变,从而引发师生冲突。在学校这一社会组织中,组织、文化、制度、课程等结构对师生冲突的影响较大。
(一)组织结构
学校作为基本的社会组织,其现行行政管理模式参照了韦伯提出的“科层制”(学校的组织结构如图1所示)。韦伯主张的科层制是以“合法性”为基础建立起的各级专门管理机构,依权力分工和分层制定与权责范围相适应的章程,并依据“规则化、非人格化及公私分明化”的原则运转的纯粹官僚体制管理模式[15]。科层制在今天看来,已有众多不足之处。在学校组织中师生之间并非应完全是命令与服从的关系,而学校的管理模式也并非完全照搬科层制。
1结构中自上而下的压力叠加是导致师生冲突的主要因素。学校并非一块与世隔绝的“飞地”,其管理及教学活动要受到各级教育行政部门的规制。教育行政部门提出的纲领性文件及要求会沿着学校的组织结构自上而下地得以执行,从而确保学校管理及教学工作符合国家意志。然而,在各项文件及要求的执行过程中,下级听命于上级而产生的压力最终会叠加到学生身上。随着各项规定及要求的增加,学生的厌烦情绪及心理压力会不断上升,当遇到某些特定事件时,这些压力便会以师生冲突的方式得以释放。
2结构中自下而上的权力位移是影响师生冲突的重要因素。正如韦伯对科层制的合法性基础所强调的那样,学校组织以 及其他科层制组织中下级对上级有稳固的“合法性信仰”,而这种信仰便保证了上级对下级拥有先天的权威性。在学校组织中,无论是“权威型”“放任型”,还是“民主型”的教师,“其对于学生的权威意识都不会完全消除,对于班级组织的控制也不会完全放弃,唯方式有所不同而已”[16]。正是由于学校组织结构中下级对上级都怀有稳定的合法性及权威性信仰,才导致了等級性的顽固存在,从而导致学校组织结构中下级部门的权力不断位移至上级部门手中,最终演变成上级对下级拥有控制和命令的权力。然而,随着上级命令的不断下达及控制力的叠加,学生的自主性会逐渐减少,基于追求自由的本能,学生便会通过与教师抗争的方式找回原有的自主和权力,从而引发师生冲突。
(二)文化结构
尽管各级行政部门和学校组织为学生营造了特定的文化氛围,但不可否认的是,学生同时身处社会、学校、班级及同伴多个文化场域之中。其中,对学生影响最大的是法定文化、教师文化和学生文化,这三者的关系呈现倒金字塔状(如图2所示),体现出三者的地位及影响力度。
1文化结构的等级性易造成师生间的冲突。处于文化结构顶层的法定文化是与统治阶层意识形态相一致的规范性文化,它以法律、法规、规章及准则等方式规定了学校组织所处的文化场域,是最高位的文化。教师作为社会代表者,其本身体现出的规范性主要来自法定文化。教师作为具有能动性的主体不可能完全符合统治阶层的期望,而又不能与法定文化相悖,否则便会受到批判[17]。而处于文化结构底层的学生文化则属于“受抑性文化”,受到法定文化及教师文化的规制和批判,从而使得学生的发展受到抑制,这便容易引发师生冲突[18]。
2文化结构的异质性易造成师生冲突。布迪厄在文化资本理论中阐述了文化资本对学生发展的重要影响。学生的文化资本一般体现在“语言能力、社会交往能力、专业技能、个人的风度举止及对成功机会的把握能力”等方面。在此基础上,布迪厄犀利地指出统治阶级所赋予子女的文化资本使得他们在教育上更易取得成功,因为学校所在的文化场域与统计阶级的意识形态是一致的。布莱克莱吉对布迪厄的文化资本理论做了进一步的研究,他认为政治统治阶级及经济统治阶级的子女并非都拥有较好的文化资本,而知识统治阶级的文化因与学校文化较为一致,因此其子女所具有的文化资本普遍较高。来自知识分子家庭的学生所拥有的文化与法定文化、教师文化较为一致,因此,他们能较好地适应学校文化的场域并与教师保持较为和谐的关系。然而来自非知识分子家庭的学生因所具有的文化与学校文化及教师文化不一致,便容易受到教师的批判和打压,这容易导致师生冲突[19]。
3文化结构的合理性规则易造成师生冲突。法定文化和教师文化是学校文化结构中的“规定性规则”,并采用“目的合理”的方式规制着学生文化的发展。“目的合理”是韦伯“合理性”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指“通过对外界事物的情况和其他人的举止的期待,并利用这种‘期待或者‘手段,以期实现自己取得成果的目的”[20]。因此,“目的合理”本质上是将实现自身目的的过程视作必要的手段。学校组织中的文化结构充斥着众多类似仪式、活动及准则等层面的法定文化,它们本质上都是依据“目的合理”而存在的,是统治阶层控制学校管理及教学活动的手段,但学生文化中的能动性和自主性却缺场了。因此,学生文化必然会与处于“目的合理”地位的法定文化、教师文化争夺场域,这容易造成师生冲突。
(三)制度结构
如同面临多重文化场域的挤压,学生还要面对多重制度的缠绕。与文化不同的是,制度的规制性较为刚性。学生面对的制度主要有选拔制度、考核制度和管理制度,三者分层围绕学生,呈地壳结构状。最外层的选拔制度是一切教育活动的指挥棒,是学校根据统治阶层的期望而制定出的纲领,决定了对学生的升学选拔及社会分流;以选拔制度为基础的考核制度,是学校根据教育行政部门对学生在习惯、礼儀、成绩和作业等方面的考核标准而制定的各项规范要求;而管理制度则是对二者的精确化与实践化,体现在对学生的各项具体管理工作之中。
1制度结构的密闭性与人的物化。制度结构为学生的发展制定了一整套的奖惩标准,在时空领域内从教育的分层机制到日常行为规范,形成了以学生为控制对象的密闭场域,致使学生从自主成长的个体演变成了制度结构所规制的“物”。卢卡奇针对人到“物”的转变提出了“物化”理论,他认为:“由于传统社会的变迁,人们对道德准则及实现社会整合的交往过程已大大丧失信心,而代之以更多地利用金钱、市场与理性的算计。其结果是社会关系等同于交换价值,等同于人们各自把对方看成‘物。”[21]因此,密闭性的制度结构促使教师将学生的成功视为自己仕途上升的台阶,而学生将教师的付出则视为自己进入较高社会阶层的资本,师生关系不再以感情为基础,而是以各自所需求的可量化的“物”和“价值”为基础。当师生之间未达到彼此所心仪的利益时,便会对对方这一“物”的价值产生怀疑,容易造成师生冲突。
2制度结构的多重性与管理的“非人格化”。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及学校管理部门会按照上级制定的规则和要求制定与自身权责范围相一致的制度和规章,从而构成了制度结构的多重性。然而,由于每层制度所制约和控制的对象人数众多,所以一般会采用科层制中的“非人格化”模式进行管理。“非人格化” 管理模式倡导在统治或管理的过程中,“没有憎恨和激情,没有爱和狂热,处于一般的义务概念;不因人而异,形式上对人人都一样”[22]。 “非人格化”管理模式看似合理,实则对师生关系的发展产生了十分不利的影响。师生互动的过程也是感情叠加的过程,当教师迫于制度结构中的相关规定而对学生的违规行为进行“非人格化”批判时,学生会因教师缺乏“人情味儿”而产生不满,从而引发师生冲突。
3制度结构的功利性与学生的标签化。制度结构的最根本特征是以选拔制度为导向的管理体制,其宗旨是选拔出社会所需要的,亦即统治阶层所期望的人,体现出对学生培养的功利性。功利性的培养模式促使教师为学生贴上了标签,如“好学生”“捣蛋鬼”“数学尖子”“大落儿”(读作Dala,指学习成绩差的学生)等。学生身上的标签表明教师已将制度结构中的功利性内化为评价学生的标准,并在主观上采用与标准相应的模式与学生互动。于是,教师与“好学生”互动时的言行往往更符合教育规律,而与“大落儿”互动时则会采用“非教育性”的言行。“对于学业成功者,教师更倾向于采取民主的、肯定的、充分考虑学生个性的言语表达方式;而对学业失败者,教师更倾向于采取专制的、否定的、控制性的言语表达”[23]。对于被教师贴上贬义标签的学生,会因互动时教师的区别对待及讽刺打压而心存不满,以致与教师产生冲突。
(四)课程結构
对于学生而言,其专业特长及兴趣爱好往往与任课教师的关系紧密相关。学生往往与自身兴趣浓厚学科的任课教师关系和谐,而与兴趣较弱及“功用”价值较低的学科任课教师关系冷淡,这便容易造成与该类学科任课教师间的冲突。由于学生感兴趣的学科及不感兴趣的学科都可能体现在国家课程中,因此,传统意义上的课程结构不能具体地展现哪些学科及知识容易引发师生冲突。相比之下,笔者认为依据师生关于课程的“功用”价值而划分的“高位学科”、“中位学科”及“低位学科”所组成的课程结构更能贴近学校课程实施的实际[24]。笔者以声誉较高的青岛市某附属中学九年级课程的实施为例(该校九年级每周安排课时36节,其中“高位课程”15节,“中位课程”12节,“低位课程”9节。其中“低位课程”包含了体育课3节、地方课程3节、校本课程3节),对其课程结构进行描述。
1学科阶层化与兴趣贬值。社会学视野中的课程因被赋予了“功用”价值属性而导致学科阶层化的产生[25]。部分国家课程因在各级评价及选拔过程中所占分值较重,因此便成为了学校教育及学校主体眼中的“高位学科”,这集中体现在语文、数学和英语学科上。基于同样的标准,像政治、历史、地理、生物、物理、化学等国家课程则属于“中位学科”。然而,像音乐、体育、美术、综合实践类国家课程以及地方课程和校本课程因几乎无“功用”价值,则只能被当成“低位学科”。但对学业失败者而言,其兴趣和特长多集中于“低位学科”,当其努力得不到应有的收益和认可时,便会产生厌学情绪。于是,当学生不感兴趣的“高位学科”和“中位学科”的任课教师对其进行规制时,学生往往会采用直接、公开的方式与教师相冲突,以对其拥有兴趣和特长的“低位学科”的学科价值进行抗争。
2知识垄断与地位争夺。所有课程本质上都是由知识构成的,因此课程结构中各学科地位的高低本质上也体现了该学科知识地位的高低。然而,由于“高位学科”和“中位学科”在课程结构中处于垄断地位,其学科知识在全部学科知识中也必然处于垄断的地位。而“低位学科”学科知识为提升自身地位必然会与“高位学科”及“中位学科”的学科知识展开争夺,学生的学习时间和精力便是争夺的内容之一。但对学生而言,如果其兴趣和特长集中于“低位学科”学科知识时,便会投入较多的时间和精力,而其他学科知识便会以自身较高的地位与其强硬地争夺时间和精力,这便造成了学生喜欢学习“低位学科”的学科知识但缺乏时间和精力的现状,从而造成学生为发展自身兴趣和特长而与“高位学科”及“中位学科”的任课教师发生冲突。
综上所述,尽管学校中存在着众多影响师生冲突的结构因素,但它们并非如同功能结构论者所说的那样不可改变,正如吉登斯所认为的——“结构既强制又使其能强制”[26],只要结构因素得到优化和调整,师生冲突就有可能得到缓解。
三、师生冲突的缓解策略
影响师生冲突的因素众多,并非所有冲突仅仅通过提升教师专业发展水平及改善学生学习能力就可以解决,优化组织、文化、制度及课程结构同样是缓解师生冲突的重要策略。
(一)弱化组织结构的控制职能,增强组织结构的服务职能
科层制的学校组织结构,一方面使压力自上而下叠加到学生身上,另一方面又将权力自下而上位移到上级部门手中,从而表现出结构中上级部门对下级部门的控制。但学校毕竟不同于工厂和车间,学校组织结构中各部门之间的关系也并非纯粹的命令与服从关系,这便要求学校组织结构增强服务职能,弱化控制职能。学校组织结构的服务职能与控制职能完全相反,是以下级部门的需要为导向的服务模式,以促使组织结构自下而上逐级完善管理职能。因此,组织结构服务职能的增强能拉平结构的等级性,从而缓解结构中压力的叠加及权力的位移,并赋予结构中包含学生在內的所有部门一定的自主权,以便于学校管理及教学工作能在相对自主的氛围中开展。学校组织结构控制职能的弱化以及服务职能的增强,可以促使师生在轻松、自主的氛围中开展互动,减少了冲突的发生。
(二)弱化文化结构的“工具理性”,增强文化结构的“价值理性”
文化结构的工具理性致使处于高位的法定文化和教师文化将处于低位的学生文化视作规范的目标,并将对与其不一致的学生文化的打压和批判作为其实现控制的手段,致使学校文化结构等级森严并与国家意志高度一致,结果造成了学生文化中的能动性和自主性的缺场,从而引发师生冲突。然而,价值理性却倡导对“无条件的固有价值的纯粹信仰,不管是否取得成就”[27]。学校文化结构的价值理性体现在追求真理和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等方面。因此,文化结构价值理性的增强,一方面可以弱化法定文化和教师文化对学生文化的打压,促使学生能更加自主的发展;另一方面,可以增强异质性学生文化的生存与发展,促使来自非知识阶层的子女有更多的机会与教师沟通。当学生拥有较高自主性及较多沟通机会时,与教师发生冲突的频率和强度便会降低。
(三)弱化制度结构的选拔功能,增强制度结构的育人功能
以选拔为导向的制度结构将选拔出社会所需求的人作为其运行的根本宗旨,像地壳结构一样以选拔制度、考核制度与管理制度将学生牢牢地限定在“地心”位置,对其不断地进行考核与评价。然而,制度结构的不断运行会使学生积累起越来越多的压抑与不满情绪,从而导致学生会像地心一样,因温度过高而产生火山喷发,与教师产生冲突。但以育人为导向的制度结构却将学生的发展作为其运行的根本宗旨,采用全面的、人性化的考核与评价模式将学生从密闭的、深层的环境中释放出来,还原其人格尊严与主体地位,为其“降温”与减压,从而减少师生冲突的发生。
(四)弱化课程结构的意识形态本位,增强课程结构的学生本位
以传播统治阶层意识形态为根本宗旨的课程结构,将“高位学科”及“中位学科”置于垄断地位,抢占了学生近乎全部的学习时间和精力,挤压了“低位学科”的生存空间,导致了“低位学科”不仅数量少而且“效益”低。因此,即便学生的兴趣和特长集中于“低位学科”,也会因缺乏时间和精力而放弃对它的学习,致使学生因喜欢的课程不能学而不喜欢的课程却必须学与“高位学科”及“中位学科”的任课教师发生冲突。学生本位的课程结构以培养学生兴趣、发展学生特长为根本宗旨,一方面弱化了统治阶层意识形态对课程的输出,另一方面增强了“高位学科”和“中位学科”的趣味性与实践性,并提高了“低位学科”的地位和价值。因此,学生本位的增强,促使课程结构不断优化和调整,以确保学生的学习时间和精力能用在培養其兴趣和发展特长等方面,从而缓解师生间的冲突。
参考文献:
[1]朱桂琴.社会学视野中的师生冲突[J].教育與职业,2003(11):42-43.
[2][3]刘易斯·科塞.社会冲突的功能[M].张立平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89:6.
[4][5][7][21][26]乔纳森·H·特纳.现代西方社会学理论[M].范伟达等译.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8:181-184,197-198,187,245,256-261.
[6]Ralf Dahrendorf. Class and Class Conflict in Industrial Society[M].Redwoo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59:135.
[8]郑杭生.社会学概论新修[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140.
[9]`[19]戴维·布莱克莱吉.当代教育社会学流派[M].王波等译.北京:春秋出版社,1989:284-288,182-190.
[10]王桂丛.师生间的冲突事件与处理[J].学生辅导通讯,1998:42-57.
[11]陈振中.重新审视师生冲突——一种社会学视角[J].教育评论,2002(2):40.
[12][13]田国秀.师生冲突的概念界定与分类探究[J].教师教育研究,2003(6):41.
[14]安东尼·吉登斯.社会的构成[M].李康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82-84.
[15][20][22][27]马克斯·韦伯.经济与社会(上卷)[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242-246,250-261,56.
[16][17][18][23][24][25]吴康宁.教育社会学[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8:281,330,259,293,70-71,327-3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