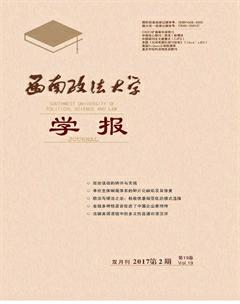论南海仲裁案的法律与政治
夏丁敏
摘要:
南海仲裁案深刻地蕴含着法律与政治之间的关系。国际法中的政治主要是指国家政治,即国家根据自身利益和意志而行动。国际法中还存在由超越国家政治的组织来调整国家行为的理想,这种理想属于国际主义。然而在现实中,国际主义往往被国家政治所利用,从而产生了虚假的国际主义。虚假的国际主义是貌似合法但实质上不正当的国家政治。菲律宾、临时仲裁庭和美国、日本都属于虚假的国际主义,分别对应工具的国际主义、错误的国际主义和虚伪的国际主义。国际批判法学揭示了这三者所涉法律背后的政治。
关键词:南海仲裁案;国际批判法学;国家政治;虚假的国际主义
中图分类号:
DF935
文献标志码:ADOI:10.3969/j.issn.1008-4355.2017.02.03
2016年7月12日,南海仲裁案拉下法律的帷幕,临时仲裁庭作出裁决,中国维持不接受、不参与、不承认和不执行的立场,坚持通过双边谈判解决争端,菲律宾低调要求中国尊重裁决,并且表达希望和中国展开谈判的意愿,美国和日本高调施压中国,要求中国遵守仲裁裁决和国际法。其实从2013年1月22日菲律宾阿基诺三世政府
2016年5月,菲律宾选出第16任总统杜特尔特,与前阿基诺三世政府的政策有比较大的差别,而本文的叙事只涉及南海仲裁的时间段,提起仲裁并与中国产生强烈冲突是阿基诺三世政府时期的菲律宾。因此,特别强调本文所指菲律宾既是作为国际法主体的菲律宾,又是阿基诺三世政府时期的菲律宾。提出仲裁案开始甚至之前,上述各方就围绕南海争端进行角力。裁决的作出意味着,虽然争端会继续存在,但是南海争端的法律过程告一段落,由此提供了一个机会,可以相对完整地来看待和研究南海争端仲裁案。本文旨在从国际批判法学的角度来分析和全面考察南海仲裁案中法律和政治本文的主题是南海仲裁案,所以在文章中所论的法律与政治,即是指国际法和国际政治。为了用语简单,直接使用“法律和政治”来表述。的关系。
一、国际批判法学和国际法中的政治
(一)批判法学和国际批判法学
法律和政治间的关系历史悠久,且两者之间存在极其复杂的关系。自法律成为一个独立的学科以来,众多学者都在论证法律的客观性和确定性,努力将法律和政治分离,但是有一个学派却相反而行,即批判法学派。该学派兴起于20世纪70年代美国的批判法学运动,目的在于打破法律的客观性和确定性的神话,揭示法律背后的政治,指出无论是立法还是司法判决都受到政治的影响甚至是由政治决定的。批判法学针对的对象是自由主义法学思想,主要批判:“第一,关于法律体现了社会成员普遍利益的观念。第二,关于法律具有独立性的观念。第三,法律具有确定性的观念。第四,关于自由主义法律具有内在一致性的观念。”[1]批判法学的代表学者是哈佛大学被誉为批判法学教父的邓肯·肯尼迪教授,其在代表作《判决的批判》中揭示了美国司法判决和权利背后的意识形态和政治本性,指出“批判是为了确立新的正确性(rightness)大厦而清除障碍的基础”[2]。在国际法中,哈佛大学的大卫·肯尼迪教授和芬兰赫尔辛基大学的马蒂·科斯肯涅米教授,将批判法学应用到了国际法中,形成了国际批判法学。例如,后者在代表作《从申辩到乌托邦》[3]中阐明了国际法律论证结构中的一个深层次矛盾和两难困境,表明国际法的客观性是难以维持的,最终必将导向政治和主观性
在国际事务中,有两种论证秩序和义务的方法。一种是将其回溯到正义、共同利益、进程、世界共同体的性质或者类似的观点,这些观点的共同点在于它们都先于或者高于国家行为、意志和利益。另外一种论证方法是将秩序和义务的基础归结于国家行为、意志和利益。这两者被分别称为“上升”的和“下降”的正当性证明模式。在下降模式中,法律具有有效的约束力。正当性证明不是来自于事实性权力,而是来自于规范性的被称之为法律的“观念”。在上升模式中,规则的正当性来自于与国家行为、意志和利益相关的事实。从上升的视角,下降的模式会因为不能以可靠的方式证明其先验的内容而落入主观主义,即容易导向乌托邦。从下降的角度,上升的模式是主观的,因为其使得国家意志或利益高于客观的有拘束力的规则,即容易导向申辩主义。
(二)国际法中的政治
国际法中的政治主要是国家政治,因为国家是最主要和根本的国际法主体,但是目前国际法中还存在着其他的实体,这些实体也会产生出自己的利益和意志從而形成政治,比如本文讨论的临时仲裁庭,但是其效果最终还是会落入国家政治。所以本文在揭示仲裁庭本身政治的同时,更主要的是将其效果归于国家政治。
透过国际批判法学,我们将深刻看到国际法中的政治是如何存在的。王铁崖先生在其主编的《国际法》中认为,国际法“主要是国家之间的法律,也就是说,它是主要调整国家之间的关系的有拘束力的原则、规则和规章、制度的总体”[4]。《奥本海国际法》第九版也表明“国际法是国家在其交往过程中有法律拘束力的规则的总体”[5]。事实上,国际法中的政治正是隐藏在这个概念之中——国际法主要是由主权国家创造和实施的,而同时调整的对象又主要是国家,甚至联合国的根基也是主权国家
《联合国宪章》第2条第1款规定:“本组织系基于各会员国主权平等之原则。”。可以说,国际法中的政治主要是指作为国际法创造者和实施者的国家的意志、利益和行动,即国家政治。同时,在逻辑上,国际法的诞生其实还预设了一种理想,即国际社会整体或国际共同体的价值观,这种价值观在20世纪以来逐渐开始进入现实
例如,在规则上出现了禁止使用武力原则、国际人权法体系和强行法,在机制上,出现了联合国大会、安理会和国际法院。,但是这种国际理想依然是微弱的,常常被国家政治所利用。
(三)国家政治和国际主义
上述理想可以称之为国际法中的国际主义。国际主义强调一个准超国家的第三方组织,这个第三方组织是根据国家的合意形成的,但又是超越国家意志和利益的。在国际争端解决的领域中,
第三方组织通常表现为国际法院或者仲裁机构等。根据与国际法的关系,现实的国家政治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是明显违反国际法的
本文不讨论明显违反国际法的政治,这种政治无须国际批判法学的批判和揭露,本文的主要对象是形式上符合国际法,但实质上违反正当性的政治。;第二类是得到国际法规定和许可的;第三类是指在违反和规定之间还存在着国际法既没有简单肯定又没有简单否定的国家政治。这种国家政治或其他实体的政治,通常符合形式意义
上的国际法,但是往往缺少实质的正当性,它通常以国际主义为外貌来呈现,使得国际主义必须要区分真假。
如上所述,国际主义区分为真实的国际主义和虚假的国际主义。首先,真实的国际主义,在逻辑上是一个理想的国际主义,要求国际法作为法应当有权威性和道德性
例如,在拉兹的《法律的权威性》和富勒的《法律的道德性》中,分别从实证法和形式的自然法两个不同的角度,提出了法治的八项原则和法律内在道德的八个要素,这两种是类似的,都涉及法的基本属性,要求公开、确定、稳定、可遵守、独立、普遍和不溯及既往等。,要求国际法像国内法那样具有中央立法机构、统一的执法机构和司法机构。但这是难以实现的,如果要实现,国际主义就应该改称为世界共同体主义,国际法也应转变为世界法。所以现实中真实的国际主义是合意的国际主义,这个版本是理想版本的弱化,或者说结合了现实的版本。在这个版本中,我们趋向理想的国际主义,但我们也尊重国家的利益和意志,要求通过国家的共同同意或协调同意来实现,而这种同意又是导向国际主义的。合意的国际主义是本文立论的根基,是本文的审查标准。当然合意的国际主义作为国际法也必须符合法的正当性要求,如果国际主义不是合意的,或者无法通过正当性的检验,那么这就是虚假的国际主义。其次,虚假的国际主义是指,把国际主义当作工具和借口来实现国家利益或其他组织的利益,这种利益不是国际法所规定和认可的,而是作为当前国际法本身所具有的缺陷和矛盾而存在的,同时也是批判法学主要的对象,批判法学的目的正在于揭示其背后的政治和政治性。虚假的国际主义,可以表现出多种形态,例如,工具的国际主义、错误的国际主义和虚伪的国际主义等。本文以举出的这三种为例进行阐述。第一种,国际主义被一方国家利用为工具,无视国家之间的合意,意图实现單方国家利益。第二种是错误地将理想的国际主义当成现实,违反了合意和正当性的要求,完全无视一方国家的利益,而事实上倒向另一方国家利益,其背后或者有其他的利益涉入或者被国家政治所利用。第三种是最为极端的,将国际主义仅仅作为一种话语和借口,实际上是“赤裸裸”的国家政治。
在南海仲裁案中,菲律宾阿基诺政府请求仲裁,仲裁庭作出仲裁,美日要求中国遵守仲裁,中国拒绝接受、参与、承认和执行仲裁,并且坚持谈判解决争端,看上去都是国际法的内容,但是通过国际批判法学的棱镜,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这其中法律和政治关系的真相。在该案中,从广义来看有三对关系:中国与菲律宾阿基诺政府、中国与仲裁庭以及中国与美日。经过合意和正当性的检验,本文得出结论,菲律宾、临时仲裁庭和美日三者都属于虚假的国际主义,菲律宾对应工具的国际主义,仲裁庭对应错误的国际主义,美国和日本对应虚伪的国际主义,而中国拒绝虚假的国际主义,坚持谈判解决争端符合国际法的规定和许可。接下去本文通过三部分内容,来呈现南海仲裁案中法律背后的政治和政治性,这便是国际批判法学应用分析的过程。
二、菲律宾与工具的国际主义
菲律宾是南海争端的当事国,同时又是南海仲裁的提起国。政治在菲律宾身上的体现集中表现为相互关联的两点:第一,争端的内容和性质;第二,争端解决的方式。我们从这两点来观察菲律宾是如何将仲裁作为一种工具的,并且将其国家利益和意志隐藏在这种虚假国际主义的背后。
(一)选择仲裁作为争端解决方式
本文首先从第二点“争端解决的方式”开始审查。要回答菲律宾为何选择国际仲裁这种争端解决方式,就必须将这点放到整个中菲南海争端中来看。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中菲南海争端的解决方式上,一直采用的是谈判和磋商[6],并且在众多中菲双边声明中重申了这一共识
1995年8月,中菲共同发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菲律宾共和国关于南海问题和其他领域合作的磋商联合声明》表示:“争议应由直接有关国家解决”;“双方承诺循序渐进地进行合作,最终谈判解决双方争议”。此后,中国和菲律宾通过一系列双边文件确认通过双边谈判协商解决南海问题的有关共识。其中,2002年《南海各方行为宣言》载明:“根据公认的国际法原则,包括1982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由直接有关的主权国家通过友好磋商和谈判,以和平方式解决它们的领土和管辖权争议,而不诉诸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菲律宾从双边谈判改为仲裁,有着现实的政治变化背景。菲律宾自20世纪70年代侵占我国南沙部分岛屿以来,一直在非法侵占和侵权,由于我国当时军事科技力量不足和南海距离大陆遥远,无法实施有效的实际控制和执法,多采用外交照会和抗议的方式。菲律宾则采取一边事实上扩大非法占领和非法执法,另一边与我国达成谈判协议的双重做法。这种事态在21世纪发生了重大变化,我国的先进军舰和飞机快速增长,在黄岩岛对峙事件发生后,我国实现了对黄岩岛的实际控制以及南海的常规化巡航和执法[7]。菲律宾才意识到其地理优势已经无法为其实现政治上的优势,所以积极谋求争端国际化,希望引入第三方势力来重新获得优势,而《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中的强制仲裁程序是菲律宾唯一可能将中国强制涉入的工具,即使菲律宾知道裁决不可能得到执行。
(二)仲裁争端的内容和性质
接下来回到第一点政治——争端的内容和性质,探求菲律宾提出的仲裁请求如何试图在法律技术上切开整体的复合争端,从而把争端包装成《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解释和适用问题[8]。但是这种切割只是形式上的,真正来讲,南海的争端是一个整体,内部相互联系,是无法单独切割开的,菲律宾的做法分割了真实的核心争端并且试图釜底抽薪地破坏中国的主权归属和海域划界诉求[8]。2006年8月15日,中国作出了排除性声明
2006年8月25日,中国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298条的规定向联合国秘书长提交声明。该声明称,关于《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298条第1款(a)、(b)和(c)项所述的任何争端(即涉及海域划界、历史性海湾或所有权、军事和执法活动以及安理会执行《联合国宪章》所赋予的职务等争端),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不接受《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十五部分第二节规定的任何程序。
,指出关于所有权、海域划界、军事和执法活动等争端,中国不接受强制程序[9]。2014年3月30日,菲律宾向仲裁庭提交的书面请求陈述了15条仲裁请求[10],这15条可以分为四大类:第一,请求1和2,要求争端只适用《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并且要求裁定中国所划的九断线及其权利诉求违反《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因此不具有法律效力;第二,请求3至7,主要要求裁定中国控制的南海诸岛都是礁,并且不享有《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规定的专属经济区和和大陆架;第三,请求8至13,要求裁定中国的岛屿建设和执法活动非法;第四,请求14和15,请求裁定中国扩大争端和违反相应义务。这些请求表面上不涉及中国所提出的保留声明,伪装成了《联合国海洋法公約》的适用和解释问题,但是刺破表面深查本质,就能发现这四类请求中的每一类都关联中国的排除性声明,或者本质上正属于中国所排除的争端。
第一类和第二类请求,要求南海争端只能适用《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并且裁定早于《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九段线无效,以及要求裁定中国控制的南海诸岛的性质为礁,都不享有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使得中国声明的与九段线相关的诉求成为无本之木,也就意味着中国无法提出岛屿主权归属和专属经济区以及大陆架的划界主张。这里就很明确,第一类和第二类请求本质上就关涉了所有权归属和海洋划界争端,事实上也起到了这种效果,并且效果更为突出,直接剥夺了中国所有主张的可能性。第三类和第四类请求,如果我们从确认中国拥有主权和主权权利的角度来看,岛屿建设和执法巡逻,都是合法且正当的行为,所以这两类请求的裁定必定会联系到岛屿归属和海洋划界。根据本文之前就中菲南海争端的叙述和某些证据,中菲争端的核心和本质是岛屿归属和专属经济区以及大陆架上的资源争端[11],其次才会涉及其他问题的争议。反过来讲,如果上述请求在本质上不是或无法联系到核心争端,菲律宾是没有必要也不大可能请求仲裁的。
三、临时仲裁庭与错误的国际主义
如果说通过仅仅合意的标准就可以揭开菲律宾工具国际主义的面纱,那么关于临时仲裁庭的分析是更为复杂的,还需要动用正当性的标准来检验,才能够深入揭示临时仲裁庭的仲裁是错误的国际主义。临时仲裁庭是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287条和附件七建立的,仲裁庭本身具有国际主义的性质,但是否实现了真实的国际主义依然要接受实质正当性的测试。从已有的事实来看,虽然仲裁庭的运行在形式上看有法律依据,然而很多方面实质上违反了公平的要求,政治便是以这种面貌呈现出来的。本文用错误的国际主义来描述临时仲裁庭,是指临时仲裁庭在现实中错误地将理想的国际主义代入,期望像国内最高法院那样独断行事,无视当今国际社会依然是由主权国家组成的事实,其违背了仲裁的合意性质,与尊重现实而又趋向理想的国际主义背道而驰,结果间接导致中国的利益和意见被全方位地忽视和反对,仲裁庭似乎成了菲律宾利益的代言人和美日意图的传声筒。以下从临时仲裁庭的组成、管辖权和实体裁决三个部分来分析仲裁庭是如何有违公平的。
(一)临时仲裁庭的组成
在南海仲裁案中,菲律宾首先提名德国籍仲裁员鲁迪格·沃尔夫鲁姆(Rudiger Wolfrum),其后,由于中国不参加仲裁程序,时任国际海洋法法庭庭长的柳井俊二指派了另外四名——加纳籍首席仲裁员托马斯·门萨(Thomas A. Mensah)、法国籍仲裁员让-皮埃尔·科特(Jean-Pierre Cot)、波兰籍仲裁员斯坦尼斯拉夫·帕夫拉克(Stanislaw Pawlak)和荷兰籍仲裁员阿尔弗雷德·松斯(Alfred H. A. Soons)。这里有几个使得公正性充满疑虑的问题:第一,当时的国际海洋法法庭庭长日本人柳井俊二从职业背景来看是“亲美遏华”的日本“右翼鹰派”,在担任庭长期间,同时担任日本“安保法制恳谈会”会长,成为日本首相安倍的智囊,推动修宪、解禁自卫权和敌视中国的政策[12]。由这样充满政治意识形态的人指派仲裁员,可以说仲裁庭形成的源头就是被政治污染的。第二,仲裁庭的构成中,没有一位亚洲人,这在代表性上存在着问题,欧洲和非洲籍的仲裁员对亚洲的争端无法深入了解,往往自然而然地持有无视争端现实和法律形式主义的立场,并且其中数人多次担任其他仲裁庭的仲裁人员[13],表现出了强烈的扩权倾向,这样的临时仲裁庭的组成便是错误国际主义的开始。
(二)临时仲裁庭的管辖权
退一步讲,即使源头受到政治因素的污染,仲裁庭依然有机会通过中国的立场文件察觉到中菲的争端本质就是或者必然关涉主权争端和海域划界
贾宇.南海问题的国际法理[J].中国法学,2012(6):28. 除了中国的立场文件,波恩大学教授Talman对菲律宾的请求逐条分析后认为,几乎每条请求都会实质上连接到岛屿领土主权或海域划界,而这些都已被中国的排除性声明排除出仲裁庭的管辖权。,从而拒绝管辖,但是相反,仲裁庭同意了菲律宾提出的观点,采取了分割的态度。仲裁庭认为,“涉及在海洋划界中所考虑问题的一个争端并不构成海洋划界争端本身”;“关于海域权源存在的争端不同于争端方权源重叠而涉及海域划界的争端。虽然确定争端方权源的内容和它们重叠的区域通常是海域划界中首要考虑的问题之一,但是这是另外一个问题。在国家海岸相反或相向或者权源重叠时可以进行海域划界。但是,一个关于主权权源的争端也可以存在于没有重叠的情况。”
参见:Award on Jurisdiction and Admissibility, paras. 155-156, pp. 60-61.这是典型的形式逻辑,理论上任何部分都可以从整体中分割出来,但是在探求本质的时候,必然要求将部分连接到整体中,整体的性质决定了部分的性质。正如上文所述,实体裁决之后的结果非常清楚,完全剥夺了中国海域划界的可能和资格,这就必然涉及海域划界问题。海域划界问题包含一个前提——有资格进行划界,那么这个前提就是整个海域划界问题中不可缺少的。虽然形式上可以区分,但是实质上这个部分具有整体性。
认识到这一点,就可以明白实质的逻辑相比形式的分割必然是更为正确和合理的,也可以让我们接着探索为什么仲裁庭要坚持不那么合理的逻辑背后的“目的”和“动机”。仲裁庭具有国际主义的性质,国际主义表现为一种价值观和倾向,通常被认为是一种理想和应然,但是如果完全不顾及现实,那么我们可以说它是错误的,必定有其他的利益和政治牵涉其中。一方面,虽然可以争辩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确实规定了强制仲裁程序,而且中国签署和批准了《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必须遵守《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关于管辖权的规定,即由临时仲裁庭作出裁决,且一方不到庭或不辩护不影响程序的进行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288条规定了“管辖权”:“对于法院或法庭是否具有管辖权如果发生争端,这一问题应由该法院或法庭以裁定解决。《联合国海洋法公约》附件七第九条‘不到案规定,如争端一方不出庭或对案件不进行辩护,他方可请示仲裁法庭继续进行程序并作出裁决。争端一方缺席或不对案件进行辩护,应不妨碍程序的进行。仲裁法庭在作出裁决前,必须不但查明对该争端确有管辖权,而且查明所提要求在事实上和法律上均确有根据。”。但是《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也同样载明了仲裁庭在一方不到案时的实质义务,即“必须不但查明对该争端确有管辖权,而且查明所提要求在事实上和法律上均确有根据”。强制仲裁的强制性使得仲裁庭有权利来裁定其是否具有管辖权和作出实质裁决,但是仲裁的属性依然要求仲裁庭考虑仲裁的性质属于合意解决争端。当一方强烈拒绝仲裁有更为合理的理由时,根据仲裁的性质和公平的要求,仲裁庭有理由拒绝管辖,不应该被错误的国际主义所控制。
(三)临时仲裁庭的实体裁决
再退一步来讲,即使仲裁庭的源头和管辖权的行使让大家充满正当性的怀疑,仲裁庭仍然可以在实体裁决部分实现公平和正当性的要求,但是2016年7月12日所作出的实体裁决完全背道而驰。
仲裁实体裁决的结果出现了整体性的偏斜,在菲律宾所提出的15项请求中,除了无关紧要部分,绝大部分诉求包括核心诉求都得到了支持[14],甚至超出菲律宾的请求进行了裁定;仲裁员整齐划一地表示了同意,没有任何独立意见和反对意见发表
在之前按照《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强制仲裁程序进行仲裁中,不少案件出现了独立意见和反对意见,而在中菲这样重大的争端中没有独立意见和反对意见是极其可疑的。另外更可疑的是,仲裁员和专家证人出现了与之前学术观点和立场完全相反的情况,却没有任何独立意见和反对意见。荷兰籍仲裁员阿尔弗雷德·松斯曾长期主张,确定岛礁的法律地位是海洋划界密不可分的组成部分。但成为菲律宾南海仲裁案仲裁员后,这位教授一改过去的立场,反而认为岛礁法律地位的判定可以与海洋划界问题脱钩。在2015年11月关于实体问题的庭审中,菲律宾所请专家证人斯科菲尔德教授,一改以往其学术文章中称太平岛为“岛”的说法,在本案中将其定性为“礁”。 。在如此重大的争端中,出现如此偏向的裁定,在国际司法中是极为罕见的。虽然中国没有参加仲裁程序,依然发表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关于菲律宾共和国所提南海仲裁案管辖权问题的立场文件》(以下简称《管辖权立场文件》),然而中国提出的所有观点,都无一例外地被仲裁庭反驳和拒绝接受。如果先把仲裁庭受到美国和日本政治力量直接操作的可能性放在一边,我们依然说仲裁庭是一种错误的国际主义。仲裁庭全面偏向的裁决似乎表明它本身即是“公平”的,事实上,这个裁决违背了公平的要求。正如上文所论述的,中国的理由更为合理,然而仲裁庭断然拒绝中国所有的意见和考虑中国的利益,这是不公平的。具体而言,至少有两点内容体现了这种不公平:第一,仲裁庭裁定,《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确立了南中国海海域权源的范围,以及取代了历史性权利或其他主权权利或管辖[15]。这里有一个重大的逻辑缺陷,也是对《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相关规定的违反。仲裁庭引用《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311条第3款和第4款的规定,即唯有协议才能修改《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运行,要件包括:一个国家主张不同于《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权利,而其他国家保持默认,并且经过了足够的时间
参见:Award by the Arbitral Tribunal between the Republic of the Philippinles and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para. 275, p. 116.。但这是针对《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之后的修改,并不能用来判断中国的历史性权利主张。中国历史性权利的主张表明我国的权利早于《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几百年前就存在并且一直保留了下来,同时主张其法律基础是一般国际法规则。《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在序言中规定了“确认本公约未予规定的事项,应继续以一般国际法的规则和原则为准据”,而仲裁庭的结论直接违反了《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这条原则性和前提性的规定。第二,仲裁庭超出了菲律宾请求仲裁的范围,裁定太平岛属于《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121条“岛屿制度”第3款所载的“不能維持人类居住或其本身的经济生活的岩礁”,所以“不应有专属经济区或大陆架”
参见:Award by the Arbitral Tribunal between the Republic of the Philippinles and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para. 622, p. 253.。这是越权的,不符合司法或仲裁不得裁判请求以外的事项这项一般法律原则。并且,具体而言,仲裁庭还修改了上述“维持人类居住”的标准为“维持一个稳定的人类社群的非暂时的居住”
参见:Award by the Arbitral Tribunal between the Republic of the Philippinles and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para. 618, p. 252. and para. 542, p. 227.。这两点都明确表明了仲裁庭的错误性和不正当性。
四、美国、日本与虚伪的国际主义
(一)仲裁背后关于美国和日本的政治参与
对美国和日本的分析相对简单很多,最大的原因在于美国和日本都不是南海争端和南海仲裁的当事方,属于“旁观者”,具有天然的政治性和无涉法律性。从政治操作和布局的角度来讲,整体分析南海仲裁案背后的政治,美国和日本是更为重要的部分。接下去我们可以看到,美日是如何“设计”南海仲裁案的。2012年美国实施“亚太再平衡”战略和敌视中国的右翼人员安倍晋三出任日本首相之后,美国和日本鼓动、支持菲律宾提起仲裁,由同时担任安倍首相重要智囊的日本著名右翼——国际海洋法法庭庭长柳井俊二搭建完成扩权倾向明显的临时仲裁庭,最后由临时仲裁庭作出“惩罚”中国的裁决。在实体裁决作出前,日本便动用各种外交力量寻求支持“已知”的仲裁结果[16],美国也发布《海洋界限—中国在南中国海的海洋主张》[17]报告,“抢先否定”中国南海九段线的合法性。仲裁作出后,美国和日本在各个场合施压中国遵守不正当的裁决,还拉拢了澳大利亚,甚至还发布了三国声明关切南海。美国和日本之所以如此热衷南海仲裁案,背后都包含着两国的间接利益,日本外相称南海是“生死通道”[18],美国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高官则称美国在南海拥有“至高国家利益”[19]。但美日都是南海的域外国家,并且中国从未破坏和威胁自由航行,却称“生死”和“至高”,这属于典型的霸权利益。上述描述清晰地展示了南海仲裁案背后美日的政治要素,政治在这里似乎清晰到了无须批判法学的揭示便一目了然的程度,但是依然有必要揭穿美国和日本在各个场合反复要求中国遵守仲裁裁决这种言词的政治性。
(二)美国和日本对待国际法的双重标准
这里有一个问题是,虽然美国和日本深入地涉及了南海仲裁案,但是这些国家要求中国遵守仲裁裁决的言论是否是真实的国际主义呢?答案是否定的。历史上美国和日本对待国际法的态度,就是“合则用、不合则弃”的“双重标准”。对待国际法双重标准的态度本身就是明确的政治,再加上上文所述的,作为域外国家的美国和日本,在仲裁提起国菲律宾低调表示要求与中国谈判时,依然高调施压中国,那么这种言词只是一种借口和话语,是虚伪的国际主义,只是为了实现美日单边的霸权利益。有几个例子可以明确地说明美国和日本对待国际法的双重标准[20]:第一,美国从来没有批准过《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原因在于美国担心主权和美国利益受到侵害,没有加入的好处在于美国一方面享有《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规定的权利(美国声称已经构成习惯法),另一方面可以避免承担《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规定的义务。同时,美国还经常要求他国遵守《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义务。第二,在1986年尼加拉瓜诉美国案中,国际法院最后判决美国违反国际法关于
禁止使用武力和以武力相威胁的原则,违反不干涉内政原则和违反主权原则
参见:Military and Paramilitary Activities in and against Nicaragua(Nicaragua v.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Merits, Judgment, I.C.J. Reports 1986, pp. 136-137.。美国拒绝执行,并且从此撤销其批准的关于国际法院的任择强制管辖权,以及数次动用安理会否决权否决要求执行国际法院尼加拉瓜诉美国案判决的决议[21]。第三,日本一直坚持在日本最南端的仅有9平方米大的冲之鸟礁为“岛”,希望借此去获得广阔的专属经济区。南海仲裁案中由于仲裁庭的越权,不正当地裁决了包括51万平方米大的太平岛在内的所有中国控制的南沙群岛岛礁都不是《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121条所指可以拥有专属经济区的岛。之后日本依然一方面要求中国遵守,另一方面日本官房长官菅义伟2016年7月14日在记者会仍然声称冲之鸟礁是符合《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规定的岛,可以獲得专属经济区[22]。
五、结语
南海仲裁案为我们呈现了两幅图景:一副是国际法图景,另外一幅是法律背后的政治图景。这两幅图景其实是一幅图画的两面,表面上是国际法,实际上从仲裁的提出、推进、管辖、作出裁定和要求遵守都充满了政治性,本文通过批判法学的方法揭示了国际法背后的国际政治。
国际批判法学的方法让我们
清晰地看到,国际法是如何被美国、日本和菲律宾等国家作为工具和借口利用的,虚假的国际主义是如何被实现的。第一,菲律宾将《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规定的强制仲裁程序作为工具,强制中国涉入不具有合意基础的仲裁。第二,日本从仲裁庭人员组成上施加政治影响,仲裁庭错误的国际主义和不正当的裁决正如美日所期待。第三,美国和日本在裁决后借口裁决的国际主义特性不正当地要求中国遵守,抹黑中国声誉和遏制中国的合法权益。另外,从政治对国际法本身的影响来看,国家政治,特别是大国和强国的国家政治,可以使国际法的实施和解释变得缺少确定性和融贯性,国际法是可以被割裂的,可以被倾向性地选取适用,这反映出国际法并非是独立的和客观的,而是充满了主观性。
参考文献:
[1]吴玉章.批判法学评析[J].中国社会科学, 1992(2): 145-148.
[2]Duncan Kennedy. A Critique of Adjudication[M].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7:341.
[3]Martti Koskenniemi. From Apology to Utopia[M].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6: 59-60.
[4]王铁崖.国际法[M].北京:法律出版社,1981:1.
[5]Robert Jennings, Arthur Watts. Oppenheims International Law:Vol. 1[M].9th ed. London: Longman Group UK Limited and Mrs Tomoko Hudso, 1992:4.
[6]《中国坚持通过谈判解决中国与菲律宾在南海的有关争议》白皮书[EB/OL].(2016-07-13) [2016-07-28].http://www.fmprc.gov.cn/nanhai/chn/snhwtlcwj/t1380600.htm.
[7]外媒称菲律宾告诉渔民避开黄岩岛:中国就在那里[EB/OL].(2016-08-05)[2016-08-06].http://www.cankaoxiaoxi.com/china/20160805/1257323.shtml.
[8]Award on Jurisdiction and Admissibility by the Arbitral Tribunal between the Republic of the Philippinles and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EB/OL].(2015-10-29)[2016-08-08].https://pcacases.com/web/sendAttach/1506.
[9]中国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298条提交排除性声明[EB/OL].[2016-08-06].http://www.fmprc.gov.cn/web/ziliao_674904/tytj_674911/tyfg_674913/t270754.shtml.
[10]“Submissions of the Republic of the Philippines”, The Philippines Memorial - Volume I[EB/OL].(2014-03-30)[2016-08-07].http://www.pcacases.com/pcadocs/Memorial%20of%20the%20Philippines%20Volume%20I.pdf.
[11]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关于应菲律宾共和国请求建立的南海仲裁案仲裁庭所作裁决的声明 [EB/OL].[2016-08-08].http://www.fmprc.gov.cn/nanhai/chn/snhwtlcwj/t1379490.htm.
[12]“起底臨时仲裁庭”之二[EB/OL].(2014-03-30)[2016-08-07].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16-07/16/c_1119229982.htm.
[13]刘衡.《海洋法公约》附件七仲裁:定位、表现与问题——兼谈对南海仲裁案的启示[J].国际法研究, 2015(5):3-22.
[14]要撕破仲裁庭的面纱——外交部副部长刘振民就南海仲裁案仲裁庭所谓裁决约束力问题答记者问[EB/OL].(2016-07-13)[2016-08-08].http://www.fmprc.gov.cn/nanhai/chn/wjbxw/t1380841.htm.
[15]Award by the Arbitral Tribunal between the Republic of the Philippinles and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EB/OL].(2016-07-12)[2016-08-09].http://www.pcacases.com/pcadocs/PH-CN%20-%2020160712%20-%20Award.pdf.
[16]柬埔寨首相:日本早就知道仲裁结果 这是政治事件[EB/OL].(2016-07-14)[2016-08-09]. http://news.youth.cn/gj/201607/t20160714_8279192.htm.
[17]海洋界限——中国在南中国海的海洋主张[EB/OL].(2014-11-05)[2016-08-08].http://www.state.gov/documents/organization/234936.pdf.
[18]日外相称南海是“生死通道”力推美日澳声明[EB/OL].(2016-07-27)[2016-08-09]. http://news.ifeng.com/a/20160727/49673804_0.shtml.
[19]2016年7月14日外交部发言人陆慷主持例行记者会[EB/OL].(2016-07-14)[2016-08-09].http://www.fmprc.gov.cn/web/fyrbt_673021/jzhsl_673025/t1381550.shtml.
[20]哈佛学者评南海仲裁案:美国习惯于使用双重标准和虚伪的做法[EB/OL].(2016-07-20)[2016-08-09].http://www.guancha.cn/america/2016_07_20_368278.shtml.
[21]1985年美国退出国际法院始末:至今尚未重回[EB/OL].(2016-03-08)[2016-08-10].http://history.huanqiu.com/world/2016-03/8669475.html.
[22]日本官房长官再次声称冲之鸟礁是“岛”[EB/OL].(2016-07-14)[2016-08-07].http://world.huanqiu.com/exclusive/2016-07/9174685.html.
Abstract:
The South China Sea arbitration case deeply contains the relation between law and politics. Politics in international law mainly refers to state politics which means a state behaves in accordance with its interests and will. In addition, there is an ideal that an institution beyond state politics governs states behaviours. It is referred to as internationalism. However, this ideal is vulnerable to be utilized by state politics and then it will become illusory internationalism. Illusory internationalism often is a kind of state politics which is legal in form, but illegitimate in essence. The Philippines, the temporary arbitration court, USA and Japan all belong to illusory internationalism, corresponding to treating internationalism as tools, wrong internationalism, and false internationalism respectively. Their political interests and intention are exposed to the international society under the international critical legal study.
Key Words: the South China Sea arbitration case; the international critical legal study; state politics; illusory internationalism
本文责任编辑:邵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