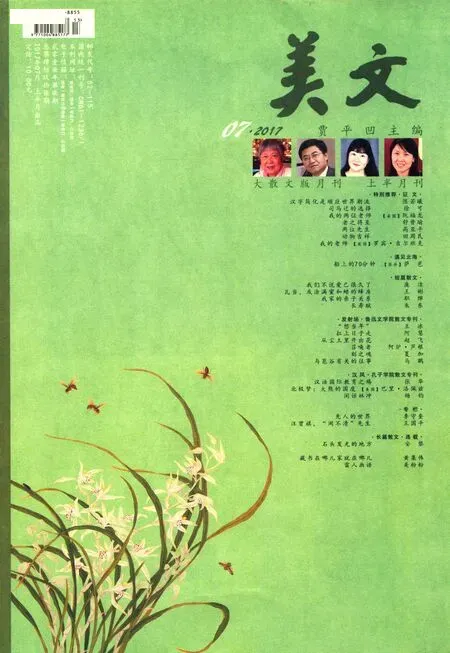司马迁的选择
◎徐可
司马迁的选择
◎徐可

徐 可 江苏如皋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高级编辑,启功研究会理事,《文艺报》副总编辑。长期从事新闻工作,业余以散文写作为主,兼及小说、诗歌、报告文学、评论等,发表作品上百万字,不少作品入选各种选本或作为高考范文。结集出版的有 《三更有梦书当枕》《三读启功》《为了我们的明天》《三更有梦书当枕 (之二)》等,译著有《汤姆·索亚历险记》《六个恐怖的故事》《热水河》等。曾获中国新闻奖、中国报人散文奖等奖项。
一
汉武帝天汉二年(前99)的秋天,一股肃杀之气弥漫在京都长安城内。秋风萧飒,草木枯槁,寒意袭人。
这一年,对太史令司马迁来说,是黑色的,他的人生从此堕入无尽的寒冬和黑夜;而这场灾难,又如凤凰涅槃一般,成就了人类文明史上一位百科全书式的文化巨人。
汉廷未央宫内,空气格外凝重。
汉武帝在大发雷霆,大臣们随声附和。
事情起因于李陵——西汉名将,“飞将军”李广的孙子。
这年夏天,汉武帝派宠姬李夫人之兄,贰师将军李广利率三万骑兵去攻打匈奴,想让他立功封侯,同时又命李陵担任他的后勤指挥官,但是为高傲的李陵所拒绝。李陵认为他的部下都是荆楚勇士,奇才剑客,力能扼虎,箭法高超,不愿接受这种后勤的差事。他请求汉武帝派他独率兵马到兰干山一带活动,这样就可分散单于兵力,减轻李广利的压力。汉武帝说:“我现在发的兵多,再无骑兵派给你。”于是拨给他五千步卒,命令他立即出击。李陵率兵从居延出塞,向北行军,行军三十余日,进展顺利,最后深入浚稽山一带扎营,并把沿途所见山川形势绘成地图,派部将陈步乐呈送汉武。汉武闻报,大为高兴,朝中大臣们也无不举杯欢庆李陵纵横千里的英雄壮举。
可是不久,李陵所部遭遇匈奴大军围攻。他身先士卒,智勇果敢,杀敌万人。可是由于叛徒告密、矢尽粮绝、后无援军,终于战败被俘。消息传来,武帝大怒,那些以前为李陵唱赞歌的大臣们也见风使舵,跟着皇帝大骂李陵。就在这一片讨伐声中,司马迁站了出来,仗义执言,勇敢地为李陵做了辩护。在十年后他写给好友任安的信中,我们看到了他是如何为李陵辩护的:
“夫人臣出万死不顾一生之计,赴公家之难,斯已奇矣。今举事一不当,而全躯保妻子之臣,随而媒孽其短,仆诚私心痛之!且李陵提步卒不满五千,深践戎马之地,足历王庭,垂饵虎口,横挑强胡,仰亿万之师,与单于连战十有余日,所杀过当。虏救死扶伤不给,旃裘之君长咸震怖,乃悉征其左右贤王,举引弓之民,一国共攻而围之。转斗千里,矢尽道穷,救兵不至,士卒死伤如积。然李陵一呼劳军,士无不起,躬流涕,沫血饮泣,更张空弮,冒白刃,北首争死敌者。”
“李陵素与士大夫绝甘分少,能得人死力,虽古之名将不能过也。身虽陷败,彼观其意,且欲得其当而报于汉。事已无可奈何,其所摧败,功亦足以暴于天下矣。”
在司马迁看来,李陵置生死于度外,赴国家之难,这已经是非常难得的英雄壮举了。他深入匈奴腹地,以五千步卒对抗八万骑兵,并杀敌万人。如今事情已经无可奈何,但如此卓越战功,也足以向天下显示他的本心了。虽然他最后投降了,但自己相信,只要一有机会,他还会重新报效汉朝的。
这一番话条分缕析,入情入理,有节有据。司马迁讲这些,没有丝毫私心,他看到皇上悲戚哀伤,真心想献上自己的恳切忠诚,为皇上解忧。“仆窃不自料其卑贱,见主上惨凄怛悼,诚欲效其款款之愚。”“欲以广主上之意,塞睚眦之辞。”他想用这番话宽慰皇上的心胸,并堵塞那些攻击、诬陷李陵的言论。没想到,他的几句话如同一勺凉水倒进沸腾的油锅里,不仅没有降温,反而点燃熊熊烈火。
当司马迁在皇上面前侃侃而谈的时候,这个不会察言观色的书生没有注意到,汉武帝的脸色渐渐阴沉下来;他没有想到,他的无心之言,恰恰触到了汉武帝的痛处。汉武帝认为,他为李陵辩护,称颂李陵的战功,实是讽刺李广利的庸懦无能,而讽刺皇帝宠幸的人,也就是讽刺皇帝本人。汉武帝大怒之下,当即把司马迁投入大牢。“明主不晓,以为仆沮贰师,而为李陵说游,遂下于理。”不久,又传来李陵为匈奴练兵的消息,于是汉武帝下令杀了李陵全家,判处司马迁死刑。
这一年,司马迁三十七岁,在朝廷里担任着一个不大不小的职务:太史令。官虽不大,吏禄只有六百石,却是他喜欢的职务。他继承父志,正在全力著述的《太史公书》(即《史记》)已经进入第七个年头。如果司马迁此时被杀,将是中华文明史上的巨大损失。
二
司马迁的先世源远流长,司马迁自称其先祖是颛顼时期的天官。《史记·太史公自序》记载,“昔在颛顼,命南正重司天,火正黎司地。唐虞之际,绍重黎之后,使复典之,至于夏商,故重黎氏世序天地。”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是西汉武帝时期太史令。司马谈是一位非常杰出的学者,著有《论六家要旨》一文,系统总结了春秋战国秦至汉初以来阴阳、儒、墨、法、名、道各家思想的利弊得失,并对道家思想进行了高度肯定。他在司马迁的教育上起到了关键的作用。
具有讽刺意味而又令人悲哀的是,身为历史学家,司马迁本人的生卒年份却是一个谜。《史记·太史公自序》和《汉书·司马迁传》都没有记载他的出生年代。后人根据唐人的两条《史记》注文,分为两派意见。一派推定司马迁诞生于汉武帝建元六年(前135),另一派则推定司马迁当生于汉景帝中元五年(前145),两种说法相差十岁。我认真比对了有关资料,倾向于取前说。
司马迁的童年是在故乡左冯翊夏阳县(今陕西韩城市)度过的。他自述这段经历说:“迁生龙门,耕牧河山之阳。”龙门山,横跨黄河两岸,对峙秦晋之间,两岸山崖高峻欲倾,湍急水流从中穿过,波涛激荡,声若雷鸣,是著名的险阻。清乾隆《韩城县志》卷一载:“两崖皆断山绝壁,相对如门,惟神龙可越,故曰龙门。”雄奇的河山,圣王的遗迹,优美的神话,在童年司马迁的心里刻下了深深的印记。在父亲的指导下,他刻苦学习,“年十岁则诵古文”。司马迁所学的“古文”,不是我们今天理解的文言文,而是用周代篆文书写的先秦残存的古籍。《史记》中提到的,便有《春秋古文》《国语》《系本》《论语第子籍》。他向孔子第十二世孙、武帝朝著名的古文大师孔安国请教《古文尚书》,跟随董仲舒学习《公羊春秋》。
汉武元鼎元年(前116),司马迁开始壮游天下。二十岁的他已研习了当时所能见读的今、古文典籍,学问具备了坚实的根底。司马谈为他安排的这次壮游,是一次有目的、有计划的行动。他从长安出发,足迹遍及江淮流域和中原地区,所到之处考察风俗,采集传说。《自序》记载了这次行程:“二十而南游江、淮,上会稽,探禹穴,窥九嶷,浮于沅、湘。北涉汶、泗,讲业齐、鲁之都,观孔子之遗风,乡射邹、峄;厄困蕃、薛、彭城,过梁、楚以归。”在汨罗江畔,他凭吊屈原投水自尽处,深为诗人的伟大人格与不幸遭遇所感动:“余读《离骚》《天问》《招魂》《哀郢》,悲其志。适长沙,观屈原所自沉渊,未尝不垂涕,想见其为人。”(《屈原贾生列传》)“想见其为人”这句话,在《史记》中至少出现了两次。还有一处是:“余读孔氏书,想见其为人。适鲁,观仲尼庙堂、车服、礼器,诸生以时习礼其家,余祗回留之,不能去云。”(《孔子世家》)当司马迁与屈原、孔子等古圣贤相遇时,他的脑海里浮现出传主的音容笑貌,不禁潸然泪下,低回不能去。他把自己的感情直接带入文中,丝毫不掩饰自己对先贤的追慕和怀想。他是带着感情来写传主的,不是冷冰冰的。
这次壮游大约花了一两年时间,足迹踏遍汉王朝的腹心地带,是为写《史记》做准备的一次实地考察。他亲自采访,获得了许多第一手材料,保证了《史记》的真实性和科学性。他这个漫游,也是《史记》实录精神的一种具体体现。回京后,他当了汉武帝的侍卫,护卫皇上祭祀天地、诸神、名山大川、封禅泰山,又奉使出征西南夷,行踪遍及全中国。正如他在《史记·五帝本纪》中所说:“余尝西至崆峒,北过涿鹿,东渐于海,南浮江、淮矣。”这在古今文人中是罕有其匹的。
元封元年(前110)司马谈卒,弥留之际,要求儿子在他死后一定要接任太史的职务,一定要完成他生前未能实现的宏愿:继续孔子的事业,作第二部《春秋》。“余死,汝必为太史;为太史,无忘吾所欲论著矣。”“今汉兴,海内一统,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余为太史而弗论载,废天下之史文,余甚惧焉!汝其念哉!”面对赍志将终的父亲,司马迁俯首流涕,对父亲立下了庄严的誓言:
“小子不敏,请悉论先人所次旧闻,弗敢阙!”
——儿子虽然驽钝,但我会全力编撰先人所记的历史材料,不敢稍有遗漏!
司马迁深深地理解父亲的心愿。父亲带着事业未竟的遗憾而死,他希望司马迁子承父业,克绍箕裘。面对父亲的重托,司马迁做出了庄重承诺,也做出了他人生中的第一次选择。这次选择,确定了司马迁的人生目标和价值标准。他立志要当一名历史学家,要写出一部伟大的史书。“迁闻君子所贵乎道者三: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父亲的临终遗命、自己的庄严承诺,成为司马迁前进的动力,精神的支柱,指引着他历经磨难而无怨无悔地把第二部《春秋》——《太史公书》写下去。
站在中华历史三千年文明之巅——大汉盛世,司马迁深刻地意识到自己所负的历史使命和责任担当,发出了“舍我其谁”的洪钟巨响。“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有能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让焉!”著史,成为司马迁人生中的第一次抉择。
元封三年(前108),司马迁继任太史令。他“紬(读)史记、石室、金匮之书”,开始了庞大而浩繁的资料整理编辑。太初元年(前104)正式开始著述。
正当司马迁全心全意撰著《史记》的时候,一场飞来横祸使他深陷于生命的绝境之中。
三
司马迁被投入监狱后,很快以“诬上罪”被判以死刑。
据汉朝的刑法,死刑有两种减免办法:一是拿五十万钱赎罪。二是受宫刑。如果这两条路都走不通的话,就只有死路一条了。
司马迁又一次面临人生的选择,而且是生死抉择:是选择生还是选择死?
求生避死,是人之本能。生命是世间最可宝贵的,不到万不得已,谁都愿意活下去。司马迁受到冤屈,当然也有活下去的权利。为了活下去,现在他有两条路可走:
第一是花钱赎罪。司马迁官小家贫,当然拿不出这么多钱赎罪。司马迁当时担任的是太史令,每年的官俸是六百石谷子。从公元前108年开始担任太史令职位,到他受冤下狱正好十年。五十万钱相当于他十年全部收入的一半。这样的收入维持正常生活应该没有问题,但是估计也所剩无几,一下子要拿出这么多钱肯定不行。所以他说,“家贫,货赂不足以自赎。”不唯如此,往日的亲朋好友就像对待瘟疫一样避之唯恐不及,没有谁敢去为他说上一句好话,没有谁肯出资为他赎罪。“交游莫救,左右亲近不为一言。”也不能怪亲朋好友们势利眼。在汉武帝的淫威之下,谁还敢为司马迁辩解,谁还敢施以援手?即使他们心怀同情也不敢流露半分,司马迁本人的遭遇就是前车之鉴。这条路显然是走不通了。
二是接受宫刑。宫刑,又称蚕室、腐刑、阴刑和椓刑,就是阉割男子生殖器、破坏女子生殖机能的一种肉刑,是古代极为残忍的一种刑罚。接受宫刑之后,一个正常的人就变成废人,与太监无异。孔夫子强调:“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一个人的身体发肤尚且不能受到损伤,何况是阉割生殖器这样的极刑?所以受过宫刑的人,被视为对祖先大不孝,生前被人鄙视,死后不能入祖坟。宫刑不但给当事人的身体造成巨大伤害和痛苦,而且残酷地摧残人的精神,极大地侮辱人格,这是士大夫万万不能接受的奇耻大辱。作为一个深受儒家思想影响的知识分子,司马迁比一般人保有更高的个人尊严,当然不愿意忍受这样的刑罚。他说:“行莫丑于辱先,而诟莫大于宫刑。”也就是说,最丑的行为就是侮辱先人,而一个人最大的污点,就是被处以宫刑。又说:“太上不辱先,其次不辱身,其次不辱理色,其次不辱辞令;其次诎体受辱,其次易服受辱,其次关木索、被箠楚受辱,其次剔毛发、婴金铁受辱,其次毁肌肤、断支体受辱,最下腐刑极矣!”显然,这也不是他应有的选择。
既然无钱赎罪,又不愿苟且偷生,那么,现在就剩下最后一条路了:接受死刑。中国古代文人特别重视个人名节,把它看得比个人的生命都重要。宁可丧失生命,不能丧失名节。在生命与仁义的关系上,先贤有过很多精辟的论述。“儒有可亲而不可劫也,可近而不可迫也,可杀而不可辱也。”“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司马迁不怕死,事实上他也考虑过接受这一选择。“人生实难,死如之何!”牺牲生命,以“全其名节”,这是司马迁最好的选择。
然而,如我们所知,司马迁最终选择的是第二条路:接受宫刑。他接受了阉割,接受了奇耻大辱,从此成了一个与太监一样的废人,成为一个苟且偷生的废人,终生生活在奇耻大辱中,生活在别人的白眼和鄙夷中。
难道他忘了先贤的教诲吗?难道他贪生怕死吗?
不。司马迁没有忘记先贤的教诲,他也不怕死。他之所以在这生死关头选择屈辱地活下来,是他想起了自己肩负的使命:他还有大业没有完成。他的心里有一个伟大的任务,有一个伟大的理想,他要写一部在他之前还没有过的、贯通千古的史书。这不仅是他的目标,也是他父亲的目标。他不能死,他的生命已经不属于他自己,他得为这个目标而活着。
接受宫刑,司马迁经受了痛苦的灵魂挣扎。他在《报任安书》中详细叙述了当时自己的心理纠结:“夫人情莫不贪生恶死,念亲戚,顾妻子;至激于义理者不然,乃有所不得已也。今仆不幸,蚤失二亲,无兄弟之亲,独身孤立。少卿视仆于妻子何如哉?且勇者不必死节,怯夫慕义,何处不勉焉!仆虽怯懦,欲苟活,亦颇识去就之分矣,何至自沉溺缧绁之辱哉?且夫臧获婢妾,犹能引决,况仆之不得已乎?”
接受宫刑,司马迁遭受了残忍的肉体虐待。“身非木石,独与法吏为伍,深幽囹圉之中,谁可告诉者!”“今交手足,受木索,暴肌肤,受榜箠,幽于圜墙之中,当此之时,见狱吏则头抢地,视徒隶则正惕息。”
接受宫刑,司马迁承受了沉重的精神压力。“仆以口语遇遭此祸,重为乡党戮笑,以污辱先人,亦何面目复上父母之丘墓乎?虽累百世,垢弥甚耳!是以肠一日而九回,居则忽忽若有所亡,出则不知其所往。每念斯耻,汗未尝不发背沾衣也。”
受宫刑对司马迁是一种难以忍受的侮辱,是对司马迁精神和肉体的无以复加的折磨和摧残。
当他的身体和精神备受摧残和凌辱的时候,为了维护人格的尊严,他曾多次萌生自杀的念头。但一想到《史记》尚未完成,他便涣然清醒了,他告诫自己:他无权选择自尽!“(《史记》)草创未就,会遭此祸,惜其不成,是以就极刑而无愠色。”众多倜傥不群的古圣先贤忍辱负重、发愤著书的壮举更坚定了他的生命意志:“古者富贵而名摩灭,不可胜记,唯倜傥非常之人称焉。盖西伯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他从古圣先贤发愤著书的榜样中获得力量,终于战胜了人生的大灾难、大痛苦、大屈辱,为自己寻求到了一条未来的战斗道路:隐忍苟活,发愤著书。“所以隐忍苟活,幽于粪土之中而不辞者,恨私心有所不尽,鄙陋没世而文采不表于后世也。”“发愤著书”,是司马迁选择“隐忍苟活”的唯一目的、唯一动力。为了实现父亲的遗嘱,为了实现自己的承诺,他以沉雄果毅的大勇主动申请接受奇耻大辱。
四
司马迁接受宫刑后,仍系狱服刑,直到太始元年(前96)“夏,六月,赦天下”,司马迁方有机会被赦出狱。他出狱之后不久,就以“中人”(太监)身份被汉武帝任命为中书令,以“闺阁之臣”的身份“领赞尚书,出入奏事”,类似于皇帝在后宫的秘书长。表面看来,是在皇帝近旁“尊宠任职”,实际上却是对司马迁人格的莫大污辱。但是,他以极大的毅力忍受着这种屈辱,全力以赴、争分夺秒地撰写《史记》。
李陵之祸,让司马迁重新审视他的撰述工作。他对汉武帝、对汉王朝有了新的认识,他对《史记》的撰述也有了新的考虑。在《史记》的叙事断限上,他将叙事上限由战国上升到陶唐,与孔子整理的《尚书》断于尧取齐,叙事下限由当初的“至太初而讫”下延到汉武帝铸黄金为麟止的太始二年。“七年而太史公遭李陵之祸,幽于缧绁。乃喟然而叹曰:‘是余之罪也夫!是余之罪也夫!身毁不用矣。’退而深惟曰:‘夫《诗》《书》,隐约者欲遂其志之思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来者。’于是卒述陶唐以来,至于麟止。自黄帝始。”而实际上,最后的下限是“下至于兹”。“下至于兹”当指《报任安书》写作和《史记》纪事截止的实际年代,也就是征和二年八月巫蛊之难中的卫太子刘据之死。这是《史记》最后的纪事。巫蛊之难对于司马迁来说,也是一大悲剧。他曾寄希望于刘据嗣位后能够拨乱反正,中兴汉室。而汉武帝一手导演的家族巫蛊之难逼迫太子自经,使司马迁在现实世界拨乱反正的最后一线希望彻底破灭。这是继李陵之祸后对司马迁的又一次沉重打击。于是他将《史记》纪事的下限“麟止”延伸到巫蛊之难,在卫太子刘据自杀之日画上一个句号,宣告《史记》至此绝笔!
《史记》的编纂主旨也发生了重大变化,由原来的为汉武帝歌功颂德改为“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他秉笔直书,在称赞汉武帝功德的同时,也斥责了汉武帝“内多欲而外施仁义”。《史记》由原先的颂汉尽忠之史,升华为拨乱反正之经,如包世臣所说的“百王大法”。司马迁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说:“维昔黄帝,法天则地。四圣遵序,各成法度;唐尧逊位,虞舜不台;厥美帝功,万世载之。作《五帝本纪第一》。”“法天则地”是《史记》的总主题。天道公明无私,地道厚德载物。这是百王治国的大本,也是生民为人的准则。这真正是应该“万世载之”的金言!经历李陵之祸后重新命笔,《史记》方才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第二部《春秋》。
征和二年(前91),司马迁终于完成了《史记》这部巨著。这年十一月他在《报任安书》中向知己任安通报了这个消息。“仆窃不逊,近自托于无能之辞,网罗天下放失旧闻,略考其行事,综其终始,稽其成败兴坏之纪。上计轩辕,下至于兹,为十表,本纪十二,书八章,世家三十,列传七十,凡百三十篇。……仆诚已著此书,藏之名山,传之其人。”
从太初元年开始起草,到征和二年杀青成书,司马迁用了14年时间完成《史记》的写作。如果算上写作的资料准备,则超过了20个年头。现在,他已没有遗憾,没有牵挂,可以坦然走向死亡了。
这是司马迁人生中的第三次重大选择,也是他最后一次选择:死亡!他的使命已经完成,现在他可以慷慨赴死了,以死抗争,以死明志,以死洗刷汉武帝带给他的耻辱!第一次选择,是遵父嘱而做,确立人生目标。第二次选择,是被汉武帝逼迫,在生死关头他选择了隐忍苟活,发愤著书。而第三次选择,则是他主动做出的,在没有任何外力的情况下,他主动选择了死亡。他不怕死,但是要死得其所,死得有价值,死得“重于泰山”。
《报任安书》是司马迁的一次总爆发,也是他勇敢地面对死亡的挑战!“要之死日,然后是非乃定。”司马迁决心用死来洗清那么多年来所受的屈辱,他要用壮烈的死来表明自己的心迹,让他和他的价值真正地被人们所认识。所以,死,对他来说是一个心甘情愿的选择。“仆诚已著此书,藏之名山,传之其人,通邑大都,则仆偿前辱之责(债),虽万被戮,岂有悔哉!”
任安(少卿),是司马迁的好朋友,汉武帝时曾为卫青舍人,后迁任为益州刺史,征和二年因太子事变被判处死刑。在司马迁受宫刑后出狱担任中书令时,他曾写信给司马迁,多有指责,“教以慎于接物,推贤进士为务”,“故人益州刺史任安予迁书,责以古贤臣之义”(班固《汉书·司马迁传》)。许是出于《史记》尚未写完的考虑,司马迁没有作答。现在,《史记》已经完成,故友面临死刑,司马迁终于无所顾忌,把一腔怒火倾泻而出。学界多数认为,正是这篇《报任安书》再一次触怒了汉武帝,致使他最终杀死了司马迁。
关于司马迁的卒年,古代典籍皆无记述。《汉书·司马迁传》叙述司马迁生平,只到全文转录《报任安书》便戛然而止,以后的事迹只字不提,更不记司马迁卒于何时,对于司马迁之死只以一语带过:“迁既死后,其书稍出。宣帝时,迁外孙平通侯杨恽祖述其书,遂宣布焉。王莽时,求封迁后,为史通子。”这一反常做法显然是有所隐讳。而前后汉之际的著名古文经学家卫宏在《汉旧仪注》中则明确写道:“司马迁作《景帝本纪》,极言其短及武帝过。武帝怒而削去之。后坐举李陵,陵降匈奴,故下迁蚕室。有怨言,下狱死。”司马迁在递送出《报任安书》后不久,再度下狱骤死,时间当在征和二年年尾(前90),终年四十五岁。
五
司马迁在李陵之祸后选择隐忍苟活,蒙受了巨大的耻辱,“重为乡党戮笑”。与司马迁差不多同时期的桑弘羊就曾说过:“一日下蚕室,疮未瘳而宿卫人主,出入宫殿,得由受俸禄,食太官享赐,身以尊荣,妻子获其饶。”(桓宽《盐铁论·周秦》)这段话似有所指。不仅桑弘羊,很可能任安在给司马迁的信中也触及了这个问题,对司马迁有所误解和指责,所以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才用了那么大的篇幅引今说古地反复解释自己的动机。
然而,时间的长河终于洗刷了汉武帝泼在司马迁身上的脏水,洗刷了他所蒙受的奇耻大辱。司马迁伟大的灵魂终于放射出璀璨光辉,《史记》也显示其巨大价值,成为中华文明史上一座巍然耸立、永不倾颓的丰碑。
最早对司马迁及《史记》做出高度评价的,是汉代史学家班固。他在《汉书·司马迁传》中写道:“自刘向、扬雄博极群书,皆称迁有良史之材,服其状况序事理,辩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扬雄也在《法言》一书中写道:“太史迁,曰实录。”他们不约而同地赞扬了司马迁“不虚美、不隐恶”的实录精神,可谓一语中的。
宋元之际的史学家郑樵对《史记》极为推崇,他说:“百代而下,史官不能易其法,学者不能舍其书,六经之后,惟有此作。”清代杰出史学家章学诚在他的史学理论名著《文史通义》中说:“史迁之学,《春秋》之后一人而已。”梁启超说:“史界太祖,端推司马迁。”更为当代中国人所熟知的是鲁迅先生的评价:“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司马迁为了实现自己的艺术理想,为了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不惜做出巨大的牺牲,他的英名永载史册。
多年来,我曾多次阅读《史记》,我是把它当成伟大的教科书来读的。书中那些英雄故事给我无尽的遐思和启迪。“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用之所趋异也。”在中国,这句话因为一位伟人的引用而深入人心。在生与死、义与利、荣与辱之间,司马迁做出了人生正确的选择,他用自己的抉择完美地诠释了生命的价值。
捧读《史记》,我时时触摸到那个伟大的、孤独的、不屈的灵魂。
余读太史公书,未尝不垂涕,想见其为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