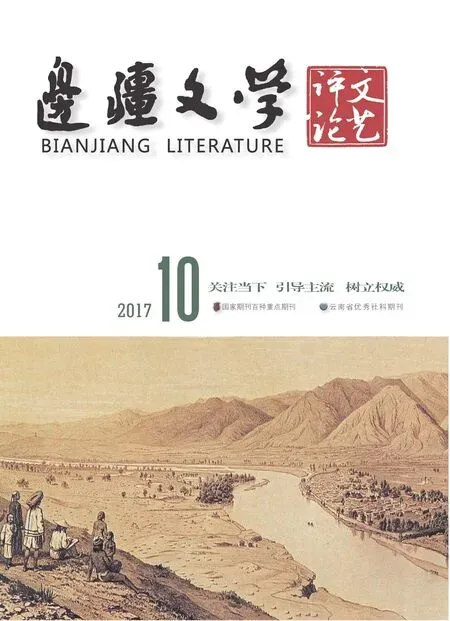《金缕曲》:穿越在空间、时间与创造之间
卢 辉
《金缕曲》:穿越在空间、时间与创造之间
卢 辉
“历史会不会说话?”这是我读完段爱松《金缕曲》最想抛出的一句话!
这一问让《金缕曲》变得生动起来。因为,历史每说一句话,都要付出沉重的代价,常常需要历经久远的年代变迁与更嬗,且其所透射出话语常常是静默而令人敬畏的,其话语又是一种历时性的话语。那么,如何让历史能够雄辩的“言说”着一切的古今之事,随着《金缕曲》的出场,一切的疑团与谜底都将迎刃而解。
众所周知,任何问题的思考一旦上升到空间或者与其相缠结的时间层面,率先显露的往往是历史,一个驾驭着时间行走的“历史”。很显然,行走的历史要想走得畅、端得出,就必须“自说自话”,而“自说自话”的这一功能的实现靠的就是玄想,这个玄想就《金缕曲》而言,那就是对历史的紧迫性与觉醒性的透视与雄辩,就是对流逝中的生命与空间予以时间上的觉悟,就是对褪色着的鲜亮世界的极力挽留。
一、空间与玄想:打开历史的视线
《金缕曲》空间最大的特性在于它的历史性,空间的深沉特性在于它的神话性,空间的最高特性在于它的寓意性,空间的首要特性在于它的现实性。《金缕曲》空间的历史性与现实性看似矛盾却又相互渗透和相互感染,即《金缕曲》空间是历史的现实,又是现实的历史。作者为我们展开的正是这样一个特定的空间:
我住在这个小镇,已记不清有多少年。在东南方,阳光穿过一片桉树林,稀稀落落照见青色的瓦盖,透过瓦盖间的缝隙,有几缕,时常落在老屋中央。
我看着这些鲜亮的轻飘飘的光线,随着我的思绪,一点一点移动,像那个一直在寻找我的骑马人,还有他的耕牛,他的豹子,他的金黄色。哦!就是这些一点一点移动的光亮,我知道其实是些脚印,发出从另一个世界抵达这个世间的声音。我凭借耳朵是无法听到的,只有我看着这些零碎肢解的光点,一步步逼近的时候,我才会不由自主地挪了挪位置。(第一部《驼鸟肉》)
的确,空间对《金缕曲》来说其重要性早已深深根植于作者的玄想之中。云南省昆明市晋宁区晋城镇,位于烟波浩渺的滇池南岸,是滇池流域历史最悠久的城镇之一,为云南省十大古镇之首,早在新石器时代就有先民在此繁衍生息,是古滇文化的发祥地,是古滇青铜文化的中心,历史悠久,文物古迹众多,在史前时期就有过灿烂的青铜文明,曾为“古滇国”都邑。由于作者生长于这片土地,长期受当地文化熏陶,耳濡目染,潜移默化,多年来,凭着内心对于这片土地的深沉热爱,他查阅了众多滇池沿岸、古滇国以及晋城相关的历史资料、诡异传说和现实事例,寻找熟悉古滇国、晋城民间故事和远古传说的老人进行记录整理,深入走访滇池沿岸古滇国遗址石寨山、晋城古镇、晋城新城区、清真寺、盘龙寺、基督教堂等地,正是处在这形形色色的空间——不管是物理意义上的,还是人文意义上的粘连、互摄、摩擦、碰撞或决裂,作者仰仗玄想的穿越性、涵括性和渗透性,以“古滇国”都邑晋城镇为创作大背景,以历史为线索,现实为依托,以资料为辅助,采取必要的虚构方式,按照人物命运的自然方式发展,将历史、地理、文化、传说、宗教、民族、民俗等众多地方元素整合为一体:
无数的交易穿梭其间;无数的商品飞流其间;无数的亡灵在混乱无章的意念下悄然退却。肉身继续在交易中被买或被卖。唯一有力量把这道门关上的,只有夜幕下,精致的咒语在特殊的纸张上,发出略带倦意的哑笑,以及手指捻数发出的窸窣满足声。(第一部《驼鸟肉》)
应该说,这无数的“物件”一直在作者的“玄想”中交集、筛选、过滤和淬火。可以这样说,《金缕曲》若离开了玄想,空间就会塌陷,而玄想越甚,空间也便越丰富越开阔。从这个意义上说,玄想,是《金缕曲》庞大空间赖以生成的始源,而空间反过来又为玄想提供更出人意料的超人遐思的可能性。而表现在叙述方面的玄想,作者则采用多角色多角度的表述方式,穿插真实的随笔记录和诗歌般的自由排列,并融合多种文体,探索出具有小说的紧密连贯、随笔的自由漫妙、更有长诗节律韵感的独创性长篇,从而让历史的“自说自话”显露出从容不迫之势。我以为,《金缕曲》空间与玄想相融渗的结果,就如阴阳相遇的结果一样:既有历史的现实,又有现实的历史。可以说,段爱松打开了小说家们的视线,使他(她)们注意到玄想的深度,及其无所不在的力量,而这种力量类似于柏拉图那种奔放的独创精神、飘逸的想象以及云诡雾谲的幻想。
二、时间与玄想:推动历史的迁演
《金缕曲》向我们展示的时间,既是历史迁演的产物,更是一种精神概念的产物。主人公的“我”既像是穿越空间、时间与创造之间的“超人”,更像是融通空间、时间与创造之间的“证人”。时间与玄想对《金缕曲》而言,更多的是来自于创作者的一种内在的对生命的敬畏感以及对精神的困守。在我看来,只有那些敏于反思的作家,只有那些对生存现状有深切领悟的作家,才会产生焦虑、困惑和迷茫,而内心的焦虑在文学创造中就不可避免地转化为时间玄想、怀疑精神和悲悯意识。因此,焦虑决不是游戏人生的人所能获得的精神体验,而是一种悲剧性的精神,是一种智慧的痛苦。不错,《金缕曲》让读者在时间玄想和历史迁演中一直处在惊惶和激动之中:
我得重新找回自己,重新找回属于我的王国。
我必须找到那把金色的钥匙,打开贮贝器上,通往未知领域的那个秘密通道,以解救被捆缚在祭祀台上,我被歪曲了的真身(那是对我的王国战败的无耻丑化)。我得按照头脑中的暗室提示,重新回到过去,以扭转现在不利的局面。(第一部《驼鸟肉》)
《金缕曲》正是以主人公“我”的心理变化为时间主线,以晋虚城现在、过去、以及石寨山发掘的古滇国遗迹为大背景,以古滇国贮贝器上金黄骑马人追杀现实主人公为复线,掺杂与之相关的晋虚城的古老传说,配以晋虚城十位性格鲜明、命运受控的少年遭遇,探究人物命运和人性脉冲,从中揭开古滇国建立之前和建立之后秘密消亡的谜底,拷问时代发展与社会良知的底线。小说结尾以世界上最伟大的五部交响曲作为伴奏基调,伴以诗歌推动和润泽,从而拓展了小说的时间切度、寓意指向和空间跨度。
在《金缕曲》的第一部《鸵鸟肉》、第二部《小镇》、第三部《活蹦乱跳》和第四部《葬歌》这四大篇章里:
其中,柔直系统的运行损耗可将系统各部分损耗求和。该损耗主要与柔直系统的有功、无功、换流变阀侧电压、换流变档位等相关。为便于在优化计算中应用,根据柔直工程实测损耗,可通过线性回归分析将柔直运行损耗表达为上述变量的二次函数形式。
一切由时间而生。
讲述主人公“我”生活古滇王国消亡后几千年的现代城镇晋虚城,被某些现代化变异发展笼罩下的现实所折磨,时常在梦幻中预感到有青铜贮贝器上的金黄骑士追杀,从而开始逃亡。一切为时间所容。
讲述“我”和十少年回归到古滇王国各自的身份与位置(王和将领),再现了古滇王国史前时期、战争时期、消亡时期的种种自然风貌、地域风俗、生产冶炼和巫术信仰。一切为时间所破。
讲述“我”在逃亡过程中,不断回顾和参与种种与晋虚城相关的人性抵抗、被巫术掌控的骇人场景,但始终挣脱不了金色骑马人的步步紧逼,必须找到开启青铜贮贝器上的金色钥匙才能打通与古滇国的通道。一切为时间而歌。
则以世界上最伟大的五部交响曲,交汇成与巫魔打赌、与巫魔交换、与巫魔周璇、与巫魔盟誓、与巫魔暧昧、与巫魔敌视、与巫魔合作、与巫魔隔绝、与巫魔赛跑、与巫魔同体的“大合唱”一切为时间而语。
讲述“我”回到晋虚城小镇与十位少年离奇经历,猛然发现十位少年和自己一样,正经受着某种不可规避宿命的牵引,这种宿命同样来自于古滇国隐秘的巫术之源的轮回之力。一切为时间而舞。
以《古兰经》、《圣经》、《坛经》为引子,追问现代化发展晋虚城带来的种种问题,蕴含顺应自然规律的和谐发展之道。一切为时间而书。
分别以大脑的思考、眼睛的观察、耳朵的谛听、鼻口的嗅闻、双手的把持、双足的行走、血液的流动、经脉的穿插、骨头的构架、影子的重叠分别叙述小说主人公在救赎道路上的迷茫与失落,并融入晋虚城若干民间传说,深化人性救赎的主题。晋虚城在我即将被时间消耗完的记忆中,一直存在着两个影子:一个是家族迁徙,携带贮贝器纹饰闪现的青幽旋律;另一个,则是我卸掉自身金色重量,脱离调性后,无以为继的音符。(第四部《葬歌》)
《金缕曲》以玄想召回时间,以时间唤醒历史。在推动历史的迁演过程中,为何我们一直觉得《金缕曲》的历史会有那么多“惊异”的产生,其“本在”的价值就在于历史的“自说自话”,而这“自说自话”的“原声”正是《金缕曲》的“我”的一种穿越式的“高峰体验”和“情感泄露”。在段爱松看来,历史有两个基本含义,一是作为史实的历史,二是作为对过去玄想和解释的历史,而作者看重的正是使之“复活”并对当下产生影响的后者。由此可见,相对于宏大叙事并趋向于全局视角的“历史”而言,爱松偏向的是历史的微观呈现和宏观视野的联袂。《金缕曲》不追求历史宏大的史实性,不求全面、完整的宏大叙述,而是从特定的视角出发,来推动并透视一段历史及其困惑,这种带有“视觉主义”的特性,它强调的不是从一个视觉来把握历史,而是关注从不同的视角对同一历史景观的多重审视和呈现。应该说,《金缕曲》的微观呈现和宏观视野的联袂,不但有助于把握历史的丰富性、复杂性和惊异性,而且为历史叙述的多元化和差异化提供更多的可能性。
三、创造与玄想:奏起历史的交响
什么是创造?创造即神圣的行动,创造即自由的呈现,创造在自由而神圣的行动中可以使自我破土而出并茁壮成长。一般来说,创造源于先天的按捺不住的激情催动,它驱使你一直不断地去尝试未知,去发现和开掘埋藏于自我深处的潜能,就《金缕曲》而言,创造就像是一部极富意志对抗性与力量较劲性的交响诗,它的每一个音阶都用心来拍打成鲜明的共振。
《金缕曲》的“我”,既是创造的“载体”,也是创造的“轨迹”:“我”沿着人性轨迹,先后回到变态杀人狂(第一部)、小镇十少年(第二部)、亡灵回忆录(第三部)、家族命运史(第四部)等各个时期的不同角色和场景,以期寻得金色钥匙开启谜团,找回自己真正的身份,从而得到救赎,却不料整个追寻过程无非只是重重幻象的影子与碎片,一切的艰辛努力与精心准备,宛如古老辉煌的古滇冶炼术一般,在强大的历史宿命与进展中,被不可知的那些隐秘力量渐渐埋葬和湮灭……
每一个被夕阳烙印下的脚步声,燃烧着金色的火焰。这是冶炼术,留给晋虚城现代性的假意镀刻,也是青铜被唤醒记忆之后,闪耀在身体内部的固体血液。它借助旋律流淌,在晋虚城开挖与填埋,破坏与建筑的现场,以准确的副旋律,一一封存。(第四部《葬歌》)
《金缕曲》的“创造”给我们带来异样酸甜感和跌宕起伏感,就此而论,创造才使时间成为真正的时间,创造赋予时间以生命和意义。反之,时间只有在创造的意义上才能涌现,也只有在创造的意义上,时间才能被历史言说。就《金缕曲》而言,只有推进到创造的意义上,在史前时期就有过灿烂的青铜文明的晋城镇“古滇国”的存在概念与时间概念之谜,才能迎刃而解。
在时间世界永恒的流动下,一个家族的命运和一个国王的命运,几乎是等同的。晋虚城,不过是两者之间,被大乐队演奏的一座墓碑之石。它久远的消亡,并未超过它短暂的存在。(第四部《葬歌》)
当我们走近《金缕曲》的“我”,若作者没有聚一切超常的心力肯定是无法创造出这样的主人公,特别是作者以交响经文和激昂雄辩的方式让“我”不时显露出不一样的“酒神式”的沉浮、迷醉与放旷,甚至于让读者也隐隐约约的感觉到是作者自身的酒神附体才使“我”的神韵如此逼真;另一方面,读者还会强烈地感受到历史的断层与生命的延续是如何通过“我”的神经、本能、意志、思想在相互冲撞、相互弥合中来“自说自话”。所以,段爱松打开了人们的视线,使大家注意到空间的厚度、时间的宽度和创造的深度,注意到人之所以能“参天地、赞化育”,就是因为人本身就是“为天地立心”的历史创造者。更为重要的是:段爱松是基于现在来打通历史的脉冲,在他的身上有一股不可遏制的敢于复活历史的强大气场,这股气场实际上就是把历史的意义“据为己有”的创生力。
面对着即将来到的真相与答案,我似乎有又转回到了原点。在晋虚城南玄村复活的老屋里,亡灵之舞层层围住的正中,响起了悲怆的种种音调。那是与老屋一脉相承对赎罪的死亡召唤。它们也跟着,复活过来了。
我对一个变异家族的破碎记忆,在毫无调性时光的伴奏下,正乘着这如水的月色,赶了过来......(第四部《葬歌》)
不错,段爱松的《金缕曲》向我们展示的何尝不是一部具备严谨的结构与经文的音律交织而成的盎然诗意与澎湃激情。这篇小说以音乐中的多声部复调手法进行创作,采用现实主义和超现实主义结合的方法进行描写,并在小说现代性的心理刻画、语言、结构、主题和风格上进行创新性的尝试与探索,创作出一部历史地域风俗下剖析人性、梳理历史与时代之变、具有云南地方浓郁色调的独创性小说。《金缕曲》让历史“自说自话”源于作者的“高峰体验”,这种体验有着诗一般的、神秘的和狂喜的“历史景观”,并常常产生出惊愕的、出乎意料的、惬意的认知震颤。不可否认,段爱松《金缕曲》创生力,归诸于神秘的外在力量,归诸于精英人士的文化特权。然而,当混乱需要秩序,朦胧需要澄明,含混需要意义的时候,创造的过程总是充满了玄机和偶然,一切都不是定数,基于这个层面的认知,就使《金缕曲》有了“历史的交响”,有了一种“永恒的现在”,有了一个无限绵延的“开放过程”,有了一处神秘可指的“精神秩序”,这正是《金缕曲》这部长篇小说的魅力所在。
(作者系高级编辑,福建三明学院兼职教授)
责任编辑:杨 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