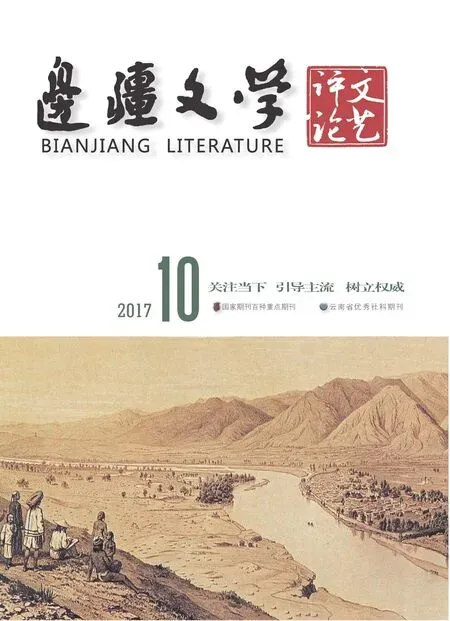《太阳照常升起》和《刀锋》对迷惘青年的不同阐释
曾子芙
经典重读
《太阳照常升起》和《刀锋》对迷惘青年的不同阐释
曾子芙
海明威1927年出版的小说《太阳照常升起》,毛姆1944年出版的小说《刀锋》,两部作品的主角都是美国退伍军人,他们经受了战争带来的肉体和精神创伤,试图在迷惘中寻找人生方向,用各种方式寻求精神慰藉,代表了一战后信仰崩塌、陷入迷惘且难以重建精神支柱的美国青年。
海明威在《太阳照常升起》中从在战争中性功能遭到损伤的退伍军人巴恩斯的视角,讲述了一战结束后,他和同伴在欧洲度过的几周,描绘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对现状失望、对未来悲观、对人生困惑的美国“迷惘的一代”青年。毛姆在《刀锋》中从作家自己的第一人称视角,讲述了他身边的退伍军人拉里的战后生活,拉里的战友在战场上为了救他而牺牲,战争结束后,拉里回到了正在积极建设“繁荣而伟大的时代”的故乡美国,却始终与周围环境、周围人格格不入,失去了人生方向,他以各种方式来重新追寻人生的意义,故事一直延续到了二战前。
两部小说都表现出了战后美国青年的迷惘心态,我们把小说里的男主人公单独拎出来,从作品中塑造的主角的迷惘心态的疏离感、漂泊感和失落感三个层面来看,他们展现了战后青年迷惘心态的不同侧面。我们会发现,两位作家在阐释战后青年迷惘心态上,不仅在时空跨度、叙述视角、写作技巧和语言风格等方面不一样,而且着眼点不同,海明威更专注时代情绪的深刻挖掘,毛姆更倾向于表现时代多方面的大变迁。海明威所阐释出的迷惘心态是沉痛而精准的,毛姆所阐释出的迷惘心态是有出口有希望的。
一、疏离感:封闭的心灵
迷惘心理的表现之一是疏离感,它的含义可以从不同维度进行解释。从社会学角度来看,美国社会学家卡普兰在其《疏离感与身份认同》中说:“当一个独立的个体察觉到他与他的社会地位、身份认同、人际、生活方式以及他的工作之间缺少了有意义的联系时,疏离感就会发生。”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疏离感作为一种内在的心理成分,主要指个体内心感受和身体体验到的一种远离、疏远和冷漠。从人与社会的关系来看,当一个人过于沉浸在浓烈的个人情绪时,自然就会对周围事物产生不同程度的疏远,成为一个冷漠的旁观者。
《太阳照常升起》和《刀锋》都重点表现了主人公疏离的心理状况,它们用不同的文本形式和叙述角度,表现了主角在社会环境、人际、自我认同三个方面所呈现出的疏离感。两部作品在解释导致美国青年这一状况的原因上也各有侧重。
1、社会环境疏离感
在两部小说中,两位主人公的物质需求都不高,都没有来自金钱的烦恼,《太阳照常升起》中巴恩斯有工作带来的固定收入,他对物质生活的质量要求不高,也懒得改变自己目前的生活状况,他基本上对自己的物质生活是满足的。他的焦虑、困惑都是精神世界的,为了缓和爱情生活的不如意带来的压抑,他赌博、喝酒、钓鱼、发呆、看斗牛……他依然在寻找生命激情,因为自己的生理缺陷,他的爱人做什么他都可以宽恕。“他始终感觉到他的战后生活如同做恶梦一般,梦境反复出现,虽然已经熬过,但现在又必须从头熬起。”他在繁忙的社交生活中感到异常为难,竭力排斥那些他不喜欢的人。
战争改变了巴恩斯,也改变了现实,他觉得战争“仿佛是一个天大的玩笑”。第一次世界大战导致社会政治腐败、社会犯罪增加、贫富分化、宗教矛盾、环境破坏等诸多问题,参加过战争的巴恩斯在战争中获得观察国际形势的能力,他喜爱冒险、旅行,同时也厌恶节约、谨小慎微等过去清教徒所倡导的“平民美德”。战争让他变得难以承担责任,并让他觉得现在的生活难以忍受。他远离自己的故乡,在“既肮脏又奢侈,厌烦、空虚、沉闷、丑陋”的巴黎过着沉沦的生活,他对现实感到失望,选择回避。他始终都和一个狭小的圈子里的人交往,没有一点扩大自己社交圈的欲望。在小说中我们看到的是在战争的蹂躏下,经历过战争的年轻人心灵上的疮痍,他们对现实不满,又看不到未来。
《刀锋》中的拉里始终同社会主流意识格格不入,他在美国时是迷惘的,他来到巴黎后,开始接触宗教、文学、艺术、东方文化……试图尽量广阔地寻找自己生存的可能性,去发掘新的精神依托。拉里与社会的疏离是他主动选择的,战争结束后他回到家乡,他的亲朋好友为他设计了所谓的“有前途”的人生道路,而他却对这些毫无兴趣,一心只想“晃膀子”。以当时社会的主流价值观看来,“有前途”的人生道路就是要像伊莎贝尔说的那样:“美国正在一日千里地前进,要有责任参加国家的发展事业,要有勇气去担当目前面临每一个美国人的重任”,要勇于建设社会,直面现实,而不是采取避世的态度。拉里选择了与主流社会相悖的“晃膀子”人生。对于“晃膀子”,毛姆在叙述时,一直没有让拉里明说出这到底是什么,毛姆一直在设置悬念,不断勾起读者的阅读兴趣。
巴恩斯被动地承受着战争带来的负面影响,不得不选择与爱人、社会进行疏远,他被海明威塑造成战后“迷惘一代”文学的代表人物。拉里的社会环境疏离感,是因为他内心的形而上追求,带有几丝积极和传奇的意味,拉里被毛姆塑造成一个理想主义式的人物。
2、人际关系疏离感
在《太阳照常升起》中,海明威用简洁的语言来描述巴恩斯琐碎的日常生活细节,走过哪里、怎样走过、看到了什么、吃了什么……海明威对这些日常行为和环境的叙述是直接而准确的,将日常生活琐事用朴实的语言表达出来,巴恩斯独自一人时,对美好生活是有追求的。但在巴恩斯与其他人的日常交流对话中,他却常常表现出一种拒绝交流的态度,巴恩斯的语言表达充斥着大量的消极和抗拒,无论任何人问起他的事情,他几乎都消极且敷衍地应对:“你想不想到南美洲去?杰克。”“不想去。”“为什么?”“不知道。”……这样的拒人于千里之外的对话,在小说中比比皆是。
在小说中,海明威对巴恩斯日常琐事及周围环境进行丰富的描写,同巴恩斯在人际交流上的空洞虚无形成一种强烈反差,表明巴恩斯虽有丰富的生活经历与内心世界,但他内心拒绝和别人分享,没有和其他人交流的兴趣,他的心理状态是封闭的。由于在战场上失去了性能力,又耻于向别人诉说,他陷入心理极度压抑的状态,即便每天都在聚会与社交,但在繁忙热闹中,却异常孤独。而在亲密关系中,由于性能力受损,巴恩斯只有不断抑制对布莱特的爱,一方面看着她和各色男性周旋,一方面与其维持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暧昧关系,于是在爱情中得不到宽慰,和爱人相互疏离。
《刀锋》里的拉里也常常参与各种社交活动,友善地同他人交流。但他始终和周围的人有隔阂,小说中多次强调他在战后和战前相比,就像换了一个人似的,战争对他有很大影响,但他从不与周围的人诉说他在战场上的经历,他的未婚妻伊莎贝尔多次让他告诉自己他在战场上经历了什么,“他却总是那样笑笑,说没什么可说的。”在小说前半段,他在战场上的经历,成为了他身边许多人疑惑的“悬念”。
毛姆在讲述拉里同别人交流的这部分,就不单单用对话来表达,他更多地是用小说中其他人对拉里的评价,来表达出拉里从战场回来后变得不太同人交流,变得行为古怪。比如他的未婚妻伊莎贝尔总是提到他和参加战争前就像变了一个人似的,拉里把自己的内心隐藏了起来,远离了过去的社交圈子,他可以一个人安静地在图书馆看一整天书,他的疏离感表现在他的与众不同,异类的脱离了正常人的生活轨道。对拉里来说,爱情和婚姻是可有可无的东西,他可以轻易放弃同伊莎贝尔的婚约,也可以随意就娶了落魄的索菲。
巴恩斯的人际关系疏离感是一种我行我素式的冷漠,带着重重的生硬感,由于战争剥夺了他的性能力,他被动地选择同人群远离,环绕在他周围的是无意义。拉里的人际疏离感来源于一种精神困惑,表现为拉里与社会主流背道而驰的追求,他对世界充满困惑,却依旧对人生有期待,只不过他是走在与社会主流大众背道而驰的追寻之路上。
3、自我认同疏离感
在《太阳照常升起》里,海明威笔下的巴恩斯对布莱特爱的本能和他们之间无法解决的现实问题,让他对自我产生厌恶。在日复一日的压抑下,巴恩斯不断地自我麻痹,在心里筑起一道道屏障,试图遗忘,用酒精麻痹自己,置身于喧嚣的环境里,茫然地走在大街上,尝试获得短暂的大脑空白。他的生活是得过且过,每一天都在痛苦、无聊与空虚中度过。战争给巴恩斯带来的决定性影响,在于剥夺了他作为一名男性的身份肯定,他不能接受这样的现实,于是选择自我疏离。
《刀锋》中多次提到拉里和战争前就像是换了一个人似的,他疏离的是没有经历过战争时的自我。他自动忽略了周围人的所作所为,也不关心当下的政治经济形势,后来索性远离了西方社会。他不在意对他“晃膀子”无关的人的看法,他不和周围的人进行过多争辩,即便他的未婚妻伊莎贝尔以退婚来威胁他,逼迫他停止“晃膀子”时,他也平静地接受分手。战争的创伤记忆对他来说,是跨越了一切的,是长久而深入的,拉里意识到死亡的色彩和滋味。经历了战争的拉里对生活对“自我”感到怀疑,他疏离了战争前的那个他自己,他在战后的美国环境里找不到自己的位置,于是开始急切地寻找新的信仰和新的“自我”。战争中突如其来的震动,让他对原本的自己和社会给他安排的社会角色产生疏离感,拉里的自我意识开始苏醒,开始关心“自我”和寻找新的“自我”。
巴恩斯和拉里都对自己的社会身份产生了怀疑,不同的是,巴恩斯是对他男性身份的一种逃离,他选择回避现实。拉里是对过去自我的一种否定,他选择抛弃亲人给他设计的社会身份,走上一条艰难的追寻新的“自我”的道路。
《太阳照常升起》里的巴恩斯的疏离感,来自于他在一战中留下的生理创伤,因不能和自己爱的人相爱,难以结婚成家,不能生儿育女,而否定自己,逃避现实,是被动的。《刀锋》里的拉里的疏离感,是他自我意识觉醒后的主动行为,他所有的行为,包括学语言、看书、去大学听课、去打工、去修真……都来源于他意识的主动性,他有自己的判断和打算。
海明威和毛姆都揭示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是造成年轻人对社会、他人和自己产生疏离感的重要原因,战争给他们带来了肉体和精神上的创伤,大战改变了世界政治经济形势,引发了各种社会问题,青年人无法在短时间内适应,没法融入社会,只有逃避,表现出对社会、他人和自己的疏离感。
二、漂泊感:逃离家园
漂泊感也是构成迷惘心理的重要部分。《太阳照常升起》和《刀锋》里的人物都有一种“逃离美国”的情绪,都远离了自己的家乡,在远离故土的地方寻找新的人生方向。小说中主要的故事都发生在欧洲,并辗转了欧洲的好几个城市,作品充满异国情调,并带有一种居无定所的漂泊感。
在《太阳照常升起》里,巴恩斯和一群年轻人来到欧洲,时而沉醉在狂欢和玩乐中,时而留恋于大自然的美丽风景里,时而陷入长久的困顿,巴恩斯对未来何去何从的迷惘心理表现为一种漂泊感,迷惘心理因心灵上的无家可归而更加深刻。巴恩斯的内心是矛盾的,他处于一种摇摆不定的漂泊状态。他和自己的土地失去了联系,却不能在新的土地上获得领悟,战后的欧洲环境光怪陆离,不论是在巴黎的纸醉金迷,还是深入比利牛斯山放松垂钓,还是在西班牙与巴斯克人一起狂欢舞蹈,他都始终置身其外,他用一种旁观者的态度看着他的同伴,他醉醺醺地看着其他人狂欢,看着布莱特换了一个又一个男伴。 巴恩斯来到欧洲,他在漂泊中找寻着自己的方向,却始终找不到出口,挣扎在漂泊者的泥淖中出不来。他的这种自我流放的行为一开始就是带有对原本传统的割裂之情的,可现实给他带来的影响依旧是负面的,他带着对故土、对欧洲的双重失望陷入迷惘。
《刀锋》中拉里的人生探索执着而漫长,他想要一生有所作为,但是又不知道做什么,只有慢慢地往未知方向去寻找,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不急躁,对人随和,慈悲为怀,丢掉一个我字,不近女色。”他不仅在欧洲各国漂泊游历求学,还走到了更远的印度,踏上一条心灵的自我修复之路,对生命价值进行了多方面的参悟,还在印度学会了神秘的催眠术,最终回到美国继续追求精神的完美。他逃离故乡来到印度,通过阅读、冥想、修真、练瑜伽等一系列他认为能够找到人生真谛的行为。
拉里从美国漂泊到伦敦,再从伦敦漂泊到巴黎,再从欧洲漂泊到遥远的东方,最后再从东方回到美国。从这样一条清晰的由西方到东方,再从东方绕回西方的精神探索之路可以看出:毛姆敏锐地观察到了欧洲大陆经历了战争后人们信仰的崩塌、精神的幻灭,新的信仰应该从何而来?毛姆试图解决这样的问题,最后根据他的经历,他把拉里追寻精神之路的落脚到了他自己也并不是非常了解的印度神秘的吠陀经哲学上。这是毛姆在创作上的一种叙事策略,把他自己也不太了解的印度神秘哲学当作拉里追寻人生真谛的终点,可以吸引读者的阅读兴趣,又体现出他对西方精神信仰缺失的忧虑,对东方文化的向往和期望。
从某种程度上看,两部小说在表达青年在漂泊中试图冲出迷惘心理的过程,都是带有一定自传性质的小说。海明威呈现的漂泊感是一种沉重的、难以掩盖的伤痛。而毛姆呈现的是旧价值观的破灭,在漂泊中对新事物进行探索,毛姆将自己的理想投射到了精神漂泊中执着探索的拉里身上。
三、失落感:生命价值失落
迷惘心理常常表现为难以消除的失落感,“迷惘的一代”也是“失落的一代”。简单来说,失落感是因为失去了自己原本拥有的,现实也没有达到自己的期望而造成的一种心理落差而导致的各种消极情绪,比如:沮丧、苦恼、心虚、彷徨。由多种消极情绪交织起来的情绪体验就是失落感。
对于巴恩斯和拉里来说,他们始终在思考着生存与死亡,因为他们感觉不到自由,他们行动的动因最主要的还是来自于心灵的“迷惘”。《太阳照常升起》中的每个人都面对着痛苦、疼痛、失望和死亡,他们过着放荡不羁的生活,靠酗酒、狩猎、看斗牛麻醉自己,逃避现实。 在小说的前半段巴恩斯说到自己的人生价值已经固定,不会再改变了。到后面又由布莱特一语道出,“你其实并没有什么价值观,你早已心如死灰,这就是事实。”
《太阳照常升起》里除了主人公巴恩斯之外,还写了很多和他一样经历了战争,在战后郁郁而不知所向的人,环绕在各色男性之间的布莱特,苦苦追求布莱特的科恩,乐于享受的比尔,他们面对不同的人生问题和不同的迷惘困惑,他们是战后一代人的象征。一战后,太多的年轻人意识到,他们可以获得基础的温饱,不用为一日三餐而奔波,但他们失落了人生价值追求,一战带走了生命,带走了爱情,这样郁郁无求的迷惘是一种无尽的、深入的失落感。
在《刀锋》后段,呈现出拉里已经形成了和当时美国主流社会人群完全不同的生活态度。是物质至上?还是追求精神的丰富?毛姆并没有在小说里直接回答,他一方面展现了一战后到二战前这段时间里欧美的社会现实——经济危机、上流社会的幻灭和巴黎艺术圈的变化等——一方面又兼顾着小说的可读性,除了讲述了男主人公拉里之外,也讲述其他形形色色的人物——追求生活富足的伊莎贝尔,纵情于酒精和毒品的索菲,享受着上流社会虚伪的尊重的艾略特,亦步亦趋地走着长辈安排的道路的格雷,一心要同艺术为伍的苏菲……他们追求的是不同的人生道路,形形色色人物的结局都和他们的初衷背道而驰。
从两部作品对人物失落感的叙述看,海明威剖析了心情愤慨的迷惘的一代方向失落、遭受失败和共同的创伤,《太阳照常升起》里的人物带有某种虚无主义色彩,海明威是绝望的,他表现的精神失落感带来的破坏力是毁灭性的,这样的绝望类似于艾略特在《荒原》里呈现的,是可以一直反复斟酌的无尽空虚。而毛姆试图在《刀锋》里探讨战后青年在失落感中重新寻找人生价值,在寻找过程中的各种可能性,他塑造的拉里带有理想主义色彩。
《太阳照常升起》是一部讲述精神世界被破灭了又要重构,却没有重构起来状态的小说。《刀锋》是一部讲述人物的一种理想化心灵修复的小说。两部作品给人带来的是不一样的阅读感受,这样的区别带有时代烙印,但最终都落到了对战争的深切控诉上。
《太阳照常升起》于1927年出版,此时正处于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小说集中展示了迷惘一代当时的窘境,精准地切中了一代人的要害,它具有显著的反传统性和革命性。而海明威简明扼要、朴实无华的“冰山体”创作是具有现代性的,小说一经问世,就获得了评论家的大量讨论,在文学和文化领域触发了革命性的轰动。这部小说成为展现“迷惘的一代”的代表作品,海明威也成为了“迷惘的一代文学”先驱,成为该文学潮流中最典型的代表作家,这部小说对美国文学乃至世界文学产生了深远影响。
《刀锋》于1944年出版,由于小说没有太多先锋性的涉及,在内容和叙事上都保留着的英国一贯的现实主义笔法,这部作品在当时的评论家眼中是一部平常小说,但这部小说又在读者中产生了广泛而持续的影响,《刀锋》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和价值,与它在读者中的极高的声誉间,存在巨大差异。毛姆用精巧的笔法,准确、简洁、悦耳的语言,引人入胜的情节,在不断地推动情节的过程中设置悬念,力求小说的可读性最大化,主角拉里的追寻是一种带有传奇性的积极探索,对读者有极大的阅读吸引力,给正在二战泥淖中挣扎的人们带来一丝新的希望,也给今天的青年许多启发。
[1] 莫顿 A.卡普兰.疏离感与身份认同.[M].纽约:自由出版社,1976.第118页.
[2] [3] [4] [6] 欧内斯特·海明威.太阳照常升起.方华文.译.[M].江苏: 译林出版社,2012.第207页,第7页,第42页.
[5] [7] 威廉·萨摩赛特·毛姆. 周煦良.译. 刀锋[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7.第71页,第28页,第49页.
(作者系首都师范大学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专业硕士研究生)
责任编辑:杨 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