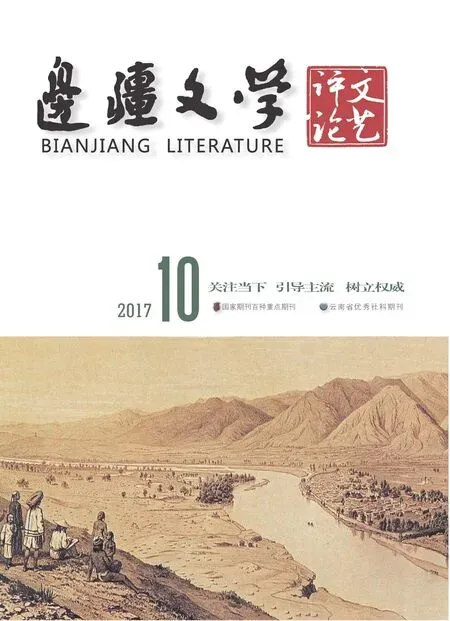对一条河流的诗意言说
——解读于坚“河流史诗”散文《众神之河》
农为平
对一条河流的诗意言说——解读于坚“河流史诗”散文《众神之河》
农为平
南方以南 高原是我故乡
古代的黄金 深夜的天堂
当诸神隐匿 河流闪着原始之光
逝者如斯 黎明滚滚不息
沧桑大道 日夜在我灵魂中激荡
于坚曾数次沿着澜沧江—湄公河进行考察,从海拔4875米的源头到远在数千公里之外的入海口,通过扎实繁复的田野调查,系统梳理了沿岸的自然风光、人文景观、风俗民情、生态变迁等诸多元素,最终形成了一部厚重的“河流散文”—《众神之河》。这是一部全面系统呈现澜沧江---湄公河流域人文历史的煌煌之作,作品不仅具有重要文学价值,更兼有独特的地理学、人类学、文化学、宗教学、民族学、生态学等多方面的参考价值,堪称当代文坛关于澜沧江—湄公河的一部独一无二的“河流史诗”。
一、对“神”的敬畏与膜拜
于坚可以说是第一个以一种开阔、完整的文化视野来打量澜沧江—湄公河的诗人、学者。因为地理位置的偏僻、国界的障碍,这条河流长期“犹抱琵琶半遮面”,正如于坚在其诗作《河流》中所写那样:“在我故乡的高山中有许多河流/它们在很深的峡谷中流过/它们很少看见天空……”。而《众神之河》弥补了这个缺憾,于坚通过经年奔波考察,又花了整整三年潜心书写,终于为世人奉上了这部厚重的“河流史诗”。“世界上没有哪条河流的两岸像澜沧江流域这样散居着众多的民族、部落、信仰、语言、服饰、风俗、生活方式……“群蛮种类,多不可记。”(《新唐书·两蛮传》)”《众神之河》犹如阿里巴巴打开了神秘的四十大盗之门,其内里所呈现的沿岸丰富多彩的自然、文化形态令人眼花缭乱、目不暇接。从人烟稀少、干燥寒冷、荒凉壮阔的青藏高原,到人口密集、温润炎热、物产丰茂的入海口;从上游的雪山、牦牛、嘛尼堆,到下游的稻米、鲜花、瓜果,从庄严肃穆、古朴凝重的查杰玛寺,巍山巍宝山的“阿央白”,到热带丛林里神秘的高棉的微笑、巴肯山的落日、泰国的四面佛……这原本形态各异的种种景致、风物、生活形态、思维观念,却通过一条河流的流淌,不可思议而又极其自然的联系在一起,既相异相悖,又和谐一致,不能不令人赞叹造物主的神奇伟大。作者以诗人的敏锐、诗性,文化学者的自觉、担当,出色地完成了对整条神奇大河的梳理、串联和书写,既原始本真又不乏主观激情地把这条原本被历史尘雾所笼罩的河流呈现了出来。
于坚对澜沧江—湄公河的书写,严格地说并非纯客观理性、科学思辨的,而是充满感情甚至是崇拜的。这与他一贯的山水情怀密不可分。作为第三代诗人,于坚的诗歌给人一种反崇高的冷漠映象,他总是尽量用抽离了情感的语言不动声色地摹写现代生活的种种情态。可是这种“冷漠”在大自然面前常常土崩瓦解,在抒写山水的过程中控制不住地一次次情感“出轨”。无疑,在当代作家中,于坚是具有鲜明的自然倾向的一位,对大江大流有特殊的情感,笔下屡屡出现江河湖海,如其被称为“河流系列”的《河流》、《横渡怒江》、《黄河》、《怒江》等。当他的目光投注到自然山水时,笔端顿时变得柔和缠绵,,深情款款。因而当他面对澜沧江—湄公河诸相,一种本能的情感紧紧攫住了笔下流淌的文字,使它们不自觉地溢出科学、理性、逻辑的轨道,自由地奔涌、碰撞于激情之中。全书一开篇就毫不掩饰地袒露出这种“激情书写”特色:
“我抵达的这个源头位于扎那日根山海拔4875米处的一块岩石旁。2006年的9月18日中午12点左右,我来到这里,看到未来的大河就从这石头下泪水般地冒出来。我踉跄几步跪下去,我一生从来没有这样心甘情愿地下跪过。泉水在我的两膝下汩汩而出,那不只是出水的地方,也是诸神所出的地方,是我的母亲、祖先和我的生命所出的地方,一个世界的源头啊!”
不仅如此,书中还多次出现对这种“跪拜”行为的描写,其中一次是在云南境内的梅里雪山,“群峰组成的大雄宝殿在大地和天空之间升起,诸神的头上戴着巍峨雪冠,比天空还高,好像刚刚获得谁的加冕”,面对整个澜沧江—湄公河流域最伟大的山峰,“我再次在大地上跪下,朝着卡瓦格博三扣。”不用去怀疑诗人内心的虔诚,或是去嘲笑其行为的矫情,对于一个敬畏大自然的人来说,面对神奇雄伟的大自然所产生的内心的震撼与臣服,往往不由自主地通过肢体动作来传达。那是一种本能的、神圣的情感体验,正如作者后来所言:“面对澜沧江湄公河那些伟大的现场,我无法不下跪。其实我是像原始人那样跪下,我像原始人那样在大地的神性力量面前战战兢兢,双膝发软。”
这里,很有必要探讨书名《众神之河》中“众神”是何指。对于这样一个带有明显宗教色彩的概念,于坚曾这样解释:“当我说神的时候,我指的既是那些、大地和庙宇中的那些偶像,也是不隐身在冥冥中的那一群。 一棵树是神的化身、一条河流是神的化身、一块石头是神的化身、一只鸟是神的化身……当我说到神的时候,我说的是风,我说的是云,我说的是琅勃拉邦的一位卖果汁的少女,我说的是黑暗,我说的是石头……”这个解释虽然给人以抽象神秘之感,但通览全书,其实不难发现,于坚所言“神”指向两个维度:外在层面是沿岸民众所信仰的宗教意义上的“神”,如上游民族普遍信仰的藏传佛教,大理白族地区的“本主”,东南亚诸国人民所信奉的各种神灵;而其内在的也是最重要的含义则是指向自然——人类赖以生存的大自然。书中处处彰显对自然的尊崇,比如前文所提到的三次情不自禁的跪拜,比如散见于全书里对各种自然物象的描写与歌咏。河流、雪山、草地、湖泊、森林、石头等等,既是描写对象,也是崇拜对象,鲜明地体现了作者“道法自然”的终极信仰。《众神之河》完全可以看做是一部自然之书,与梭罗的《瓦尔登湖》一样,体现了对自然的仰望情怀,具有鲜明的生态倾向。
“宗教其实是从大地得到的觉悟,道法自然,没有大地的启示,人无论怎么冥思苦想,也虚构不出宗教世界来。”在对天地自然的敬畏中,于坚悟出了宗教之道,即原始的自然崇拜。比如说在他的家乡云南,据清代的文献,被记录的各种民族多达140多种。“他们信奉万物有灵,大地不仅仅是人的大地,也是神的大地,而这个神不是一个单一的偶像,而是人之外的几乎一切,森林、河流、草木、野兽……都属于一个庞大的神灵体系。”到了东南亚,这种原始的自然崇拜依然在延续,人们对神的崇拜有增无减,只不过神的类型、面目、名称有所变化。书中所引印度教箴言如是说:“神虽唯一,名号繁多,唯智者识之。”这个形式千变万化,而本质始终如一的唯一的“神”,褪去神坛的种种虚幻装饰,其实质就是人类先民对大自然的膜拜的化身,虽然在后来的演进过程中,不可避免地被涂抹上诸多神秘诡谲、超验玄奥的色彩,又附加了对英雄、强权的崇拜等其他成分,但追本溯源,其基因是有迹可循的。于坚通过对流域内山水风光、世俗生活的品读,无形中还原了“神”之本相——“神”即自然,“众神之河”意即自然之河,信仰之河。其思想,与几个世纪前斯宾诺莎、布鲁诺的“泛神论”相互呼应,熠熠生辉。
二、充满劳绩而诗意地栖居
澜沧江—湄公河既是一条自然之河,同时也是一条生命之河,人文之河,沿岸自古栖居着众多的民族,“群蛮种类,多不可记”(《新唐书·两爨蛮传》)。从上游青海、云南境内的藏、彝、白、傣等少数民族,到下游越南、老挝、缅甸、泰国等国的不同民族,世世代代傍水而居,在河流的滋养下繁衍生存,他们的生活早已和河流融为一体,在生活方式、习惯思维等诸多方面都浸染上了独特的河流色彩,河流也因这些生命体的存在而彰显勃勃生机。这些沿岸的芸芸众生,他们独特的生命形态,很自然地进入作者的观察视阀,构成了作品中极富张力的一个书写重点。全书以河流为经,以游踪为纬,移步易景地为读者描摹、勾勒一幅幅多彩多姿的生活图卷。青藏高原极寒地区逐水草而居的牧民,寺院中潜心修行的喇嘛,集市中辛劳讨生活的商贩,湄公河上以船为家的渔民……透过作者的笔端,读者会惊诧于生命形态的多元共存,即使是同饮一江水的人们,生活方式也可以如此天差地别。比如在河流的两端,上游处于自然条件极为恶劣的高原地区,地广人稀,土地贫瘠,生活在那里的人们“天真、坚强,持有另一种世界观,相信神灵,轻视物质,吃喝不是为了品味,而是身强力壮之必需。脸膛黑里透红,是与太阳、风沙、冰雪和牦牛整日厮磨的结果”;而下游入海口则是肥沃富饶的鱼米之乡,物产丰富,人口稠密,“在湄公河三角洲漫游,我经常感觉到人世间洋溢着喜悦,这土地不需要思想,不需要思考‘我们从哪里来,到哪里去’的深刻问题,活着就好,在着就好,实用主义不是一种思想,而是大地决定的,在这样的大地上,实用、妥协、随遇而安,都是非常自然的,无关原则。时间不是金钱,时间就是生活。”作者一方面尽可能地还原流域内不同的生活形态,一方面又给予所有存在以理解、敬重,并不拘囿于某种观念形态、宗教认知,因而使得作品笼罩着一层人性的光辉。
可以明显感受得到,在面向自然时,作者的态度是庄重、尊崇的,而一返回到生活中,笔下的文字立刻变得温情、感性、悲悯。在沿河而下的考察中,他像一个行吟诗人一样,熟稔自然地走街串巷,脚步一次次踏进各种村庄、集市、寺庙、市井小巷、竹楼瓦肆,饶有趣味地记录下形形色色的生活图景。巍山流淌着古风韵味的悠闲时光,仰光熙熙攘攘的集市,琅勃拉邦寺院与民居共存的和谐景象,河内剑湖畔店铺林立的老街……无不在他笔下呈现出勃勃生机,作品因而浸染上浓郁的世俗滋味,弥漫着鲜活的生活况味,字里行间飘散着亲切的烟火气息。
对大理巍山的描写是全书中浓墨重彩的一笔。在这之前,叙述流程如水流一般徐徐推进,而进入大理之后,速度骤然慢下来,盘旋不前。对于巍山这座诞生了云南历史上最辉煌的南诏——大理文明的发祥地,于坚明显偏爱有加,除了简略回顾南诏文化,他用了很奢侈的笔墨细细描绘巍山的城市格局、民情风俗、传统美食、市井生活,以及熙熙攘攘的集市,毫不掩饰对这种凡俗生活的认可与向往。伟大的国度早已灰飞烟灭,而民间生活却蓬蓬勃勃地延续下来,历史隐匿在一些生活细节之中,火把节、阿央白、拱辰楼这些文明密码早已和生活融为一体,无所谓古代和现代,无所谓历史和现实,最打动人的是可以触摸得到温度的生活。这是于坚的体认,也是他所关注到的河流最动人的魅力所在。一条河流,最重要的不是它流径多长,力度多强,而在于它是否滋养生命,是否与日常生活交融一体,而澜沧江—湄公河,很显然是这样一个伟大的母体。
这种向下的生活化视角,决定了进入于坚视野的大多是同饮一江水的寻常民众:笑容灿烂的僧人,衣衫褴褛的朝圣者,街头晒太阳的老人,原始森林里的狩象猎人,湄公河畔沐浴的少女,看守废墟的老人,吴哥窟的乞讨者……他们姓甚名谁,何所来何所去,丝毫不重要,生命原本就是一种自然率性的存在。在于坚看来,身份固然受到国家、民族等外在因素的制约,而生命却是无国界的,是亲近相通的,因而虽然他的脚步不断穿越边境、国界,但在精神上可以毫无困难地与大地上朴实普通的人们打成一片。他走近他们,犹如在自家的院子里与邻人交谈那般自然亲切;他观察他们,用敏感的心品味世俗生活所蕴含的诗意和感动。 “放学的少年,接到孩子的父母推着摩托车慢慢穿越人群,卖纸烟的老爹守着一个摆着打火机和香烟的木盒坐在码头上,几个少年和一个少女蹲在栏杆边抽烟。另一些少年光着身子在河流中一个废桥墩上晒太阳,突然张臂飞起,跳入水中,炊烟在老屋顶上飘着,空气中有煎咸鱼的气味。” 这是于坚在越南西贡的一个普通码头看到的场景,原本是寻常不过的生活细节,却被他写得极具趣味,诗意盎然,原因何在?“父老乡亲、邻居、故乡、如复一日的日子,令我深深感动。”作者的情怀早已跨越地域,他乡即是故乡,生命原本就是相亲相通的。
荷尔德林诗云:人,充满劳绩而又诗意地栖居于大地。《众神之河》无比形象地诠释了这种生活图景,于坚用真诚而又富于诗意的文字,把澜沧江—湄公河绵延近五千公里沿岸各民族人们的生活串联起来,他们在这里繁衍生息、悲欢离合,像河流那样坚韧,又像河流那般逍遥自在,正如古代歌谣吟唱的那样:“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帝力于我有何哉!”正是这些依水而居的芸芸众生,使河流超越了单纯的地理概念,鲜活生动起来。自然之河实质上也是生命之河。这种朝向民间、关怀众生的世俗化视角,使得作品呈现一种平和温暖的质地,具有润物于无声处,动人于平凡中的内在力量。
三、文明之光辉映
文明始于河流。两河流域诞生了古巴比伦文明,尼罗河造就了古埃及文明,印度河、恒河滋养了古印度文明,黄河、长江孕育了华夏文明。河流是人类文化的基因。澜沧江—湄公河流经的虽然是中国偏远的西部、西南部地区,以及缅甸、老挝、泰国、越南这样的东南亚小国,在世界文化版图上明显处于边缘地带,但是其孕育的河流文明同样辉煌灿烂,而且流域内丰富多样的文化形态令人叹为观止。《剑桥东南亚史》提到,历史学家乔治·卡欣在研究了湄公河流域以及整个东南亚的历史后得出一个结论:“组成东南亚的各个国家无论在政治上还是在文化上的不同都要大于组成欧洲的各个国家。”这种特点,决定了这一流域内文化生态的多样性、别致性,它们不像四大古文明那般磅礴大气,总体而言具有小巧而精致的特性,别具风采和魅力。
对沿岸诸多文化现象的考察自然是于坚河流之旅的一个重点。从源头开始,他在书中为读者呈现了令人眼花缭乱的各种文化景观:青藏高原古朴凝重的藏传佛教,苍山、洱海间的南诏文化,隐匿在莽莽热带雨林中的吴哥文明,泰国帕南春寺里的未来佛,老挝琅勃拉邦密集的寺院,以及蔓延整个东南亚地区的稻作文化……组合起一幅绵延数千公里,色彩斑斓、震慑人心的恢宏文化图卷。这也堪称《众神之河》的一大创举,虽然古今已经有不少文献著作记录下这些文化风貌,但大多受制于地域国界、观念意识,它们多是以国别、区域为单位,以各自独立的形式出现。于坚摒弃种种人为禁锢,纯粹以河流为线索来收集、整理,串联起沿河的文化符号,赋予它们共同的精神坐标即河流。这种新颖的解读视角,无疑为东南亚各国文明的深度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和途径。
在书写各种文化景观时,于坚并非客观理性的去描述,每一次他都是试图深度进入其中,亲身感知,用心、用灵魂去进行解读。他并不在意既定的概念和模式,也不受制于普范的观点,只执着于自己的感受与认知,因而他笔下的文化景观,既显现古老拙朴的质感,同时也充溢着作者个体感性、激情的体认,呈现出一种新奇、活泼的面目来。比如他写藏地耸立的雄伟的查杰玛寺院:“对于当地人来说,查杰玛大殿就是大地上最神圣最美丽者,心灵的归宿,智慧的高峰,美学的经典,人生的依托,没有谁会想到要去与它试比高低。世上最美丽的女人、最勇敢的男子、最伟大的君主都要在大殿前面跪下来,这不是谦卑,也不仅仅是信仰,这是依托”,对于这样一座凝集了宗教信仰伟力的宏伟建筑,作者完全不吝溢美之辞,毫不掩饰内心的膜拜与赞叹;比如他写波罗芬高原上伟大的瓦普庙遗址:“石雕非常精美,花朵在石楣上盛开,众神在其间跳舞……那些发黑的石头窗子很阴郁,仿佛正在为昔日的过度明媚亮丽而忏悔,忽然看见一张脸,女王的脸,勾魂摄魄,我已经开始产生幻觉”,原本是冰冷凝固的石雕,被作者赋予了鲜活灵动的生命质感,在诗意张扬的文字中间传递出古代文明动人心魄的美。当然,全书最富激情的是写与吴哥窟的相遇:
“我在那个热得发昏的中午猛然看见丛林的帷幕拉开,充满光芒的天空下垒着一堆莲花般安静的灰色岩石,身上忽然不热了。我有一种恐惧感,仿佛面临审判,我的过去是一座地域,走向吴哥窟的时候我腿脚发软。我一直知道这世界存在着一个秘密,它藏在我们称为宗教的那个领域。在澜沧江—湄公河流域,我曾经进入过无数的寺院、教堂,但没有一个像吴哥窟这样,具有巨大的磁力,恐怖而令人兴奋。”
这种来自灵魂最深处的内在体验,是独特而难以复制的。相比几百年前周达观《真腊风土记》中对吴哥极为客观的描绘,现代西方作家雷·威廉姆斯“面对吴哥窟,最庄严的中世纪欧洲建筑也显得有些逊色”等诸如此类的赞叹、评价,于坚的文字中更渗透出强烈的个体化感情色彩,体验俨然成为主体,诱导着读者跟着他进一步去感知吴哥的神秘伟大。
吴哥窟无疑是整个流域内最辉煌壮观的文明遗迹,面对它,于坚难抑兴奋、膜拜之情,文字细腻、张扬,大吴哥、小吴哥,巴戎寺神秘的高棉的微笑,巴肯山的落日,雕刻精美的女神,无一不在他热情的观照下显示出感性的光彩。即使是在描写一些自然景象时,于坚也抑制不住激情的荡漾。比如在看到塔普伦寺被大树、藤蔓侵蚀的奇异景象时,他用极富诗意、极具想象力的语言生动写道:
“塔普伦寺遭遇了大自然对吴哥神庙群最严重的攻击,以周身散发着银子光芒的蛇树卡波克为首,丛林、藤蔓、苔藓、暴风雨、闪电、猛兽、炎热的阳光以及黑夜在几百年中疯狂地扑向神庙。蛇树的根茎攀上梁柱、探入石缝、绑起门窗、压住屋檐,甚至从神庙的心脏上长出来,像一个张牙舞爪的魔鬼的胃,日日夜夜地将神庙四分五裂,裹缠吞噬。但较量的结果是神庙与大地合二为一,大地、丛林和神庙像情人般彼此纠缠在一起,再也无法分开。”
在这样的文字里,大自然顿然显现出强悍的生命力量,原本是几百年间缓慢的侵蚀,被作者生动描绘为一幅仿佛是瞬间爆发的疯狂侵略图,就如他一直在现场目睹了整个过程的上演一般,想象力超凡,画面感十足,历史的沧桑与自然的力量被表现得淋漓尽致。
这种诠释方式贯穿全文,于是,那些原本隔着历史与读者遥遥相对的文明遗迹,在于坚用灵魂的感受和解读中,在其充满诗性的文字导引下,消除了隔膜,褪去了冷漠,瞬间变得真实、亲近,仿佛触目可见,触手可摸。与其说《众神之河》是完成了一次对河流文明的梳理,不如说是进行了一次精彩独特的深度再解读。于坚敏感真率的诗人气质,诗性灵动的文字,赋予了沿岸那些古老文明新的内蕴与生命活力。从这个意义上说,诗人自己也完成了一次精神涅槃。
《众神之河》既是一首雄浑激越的河流赞美诗,更是一曲深情的自然之歌、生命之歌、文明之歌。作者的目光穿越时间、空间的迷雾,把澜沧江—湄公河完整地托出历史的地表,全景式地展现它的地理概貌、人文形态。同时,通过这种独特的诗意书写,巧妙地完成了对河流意义的形而上解读:“河流是一个精神性的象征,一个神话,一种隐喻,人们望着有大美、大气象、大力量、大流动而不言的河流,内心充实,感受到永恒的存在。”

吕 印 国画 古城系列8
【注释】
[1] 本文中所用引文,除有注释之外,均引自于坚《众神之河》,陕西出版集团太白文艺出版社,2009.
[2] 于坚.诗集与图像,青海人民出版社.2003,23页。
[3] 朱宵华.对话于坚:我为什么要写《众神之河》.云南信息报.2009.10.20
[4] 朱宵华.对话于坚:我为什么要写《众神之河》.云南信息报.2009.10.20
[5] (新西兰)尼古拉斯·塔林.剑桥东南亚史.云南人民出版社.2003.105页
[1] 于坚.众神之河[M].西安:陕西出版集团太白文艺出版社,2009.
[2] 洪子诚,刘登翰.中国当代新诗史[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3] 马绍玺,胡彦.以个人的方式想象世界[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
[4] 何雪.于坚诗歌的语言策略[J].重庆师范大学学报.2006,(4).
(作者系南京大学新文学研究中心在读博士)
责任编辑:杨 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