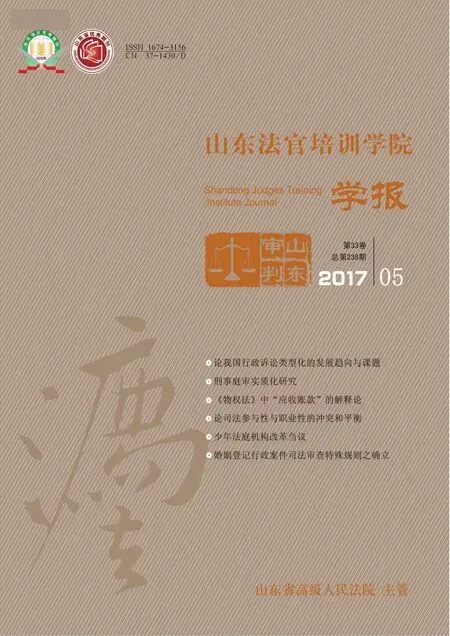论意思表示的解释规则
——《民法总则》第142条释评
●周玉辉
论意思表示的解释规则
——《民法总则》第142条释评
●周玉辉*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142条首次规定意思表示的解释规则,囿于条文表达所限,存有诸多争议且待阐释之处。意思表示的解释起点绝非“疑义导致解释”,概因何为“疑义”本就为解释结论。意思表示解释旨在为法律适用而服务,为法律适用问题,是对裁判依据的释明。意思表示的解释对象是“表示价值”,即为理性相对人所知悉的客观表示意思。基于需受领的意思表示与无需受领的意思表示的界分,意思表示的解释规则需综合配置以规范解释与自然解释为核心的简单解释规则,并辅之以漏洞填补为目的的补充解释规则。
意思表示 表示价值 简单解释 补充解释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以下简称《民法总则》)基于意思自治之理念,在总结《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以下简称《合同法》)第125条第1款①《合同法》第125条第1款规定:“当事人对合同条款的理解有争议的,应当按照合同所使用的词句、合同的有关条款、合同的目的、交易习惯以及诚实信用原则,确定该条款的真实意思。”立法经验并参酌国外立法例及相关学者建议稿的基础上,②有关我国意思表示解释规则的历史由来的著述,可参阅朱晓喆:《意思表示的解释标准——〈民法总则〉第142条评释》,载《法治研究》2017年第3期。于第142条规定了意思表示的解释规则,即:“需受领的意思表示的解释,应当按照所使用的词句,结合相关条款、行为的性质和目的、习惯以及诚信原则,确定意思表示的含义。”“无需受领的意思表示的解释,不能完全拘泥于所使用的词句,而应当结合相关条款、行为的性质和目的、习惯以及诚信原则,确定行为人的真实意思。”该条文基于需受领的意思表示(即无相对人的意思表示)与无需受领的意思表示(即无相对人的意思表示)的类型区分下,分别确立了规范解释与自然解释的意思表示的基本解释规则。
尽管《民法总则》第142条确立了意思表示的基本解释规则,然而在意思表示解释的适用范围、解释对象、解释目标以及解释方法等方面,仍失之宽泛。本文基于法教义学视角,对《民法总则》第142条展开释评,以期对意思表示解释规则的理解与适用有所助益。
一、意思表示解释的规范属性
(一)意思表示解释的适用范围
意思表示解释的适用范围上,亦即:意思表示在多大范围上需要解释,存有不同观点。《民法总则》起草者指出,“所谓意思表示就是指因意思表示不清楚或者不明确发生争议时,由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对意思表示进行的解释。”③参见李适时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释义》,法律出版社2017年版,第438页。王利明教授也持有此观点,他认为“所谓意思表示的解释,指的是在意思表示不清楚、不明确而发生争议的情况下,法院或仲裁机构对意思表示进行的解释。”参见王利明:《民法总则》,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308页。此即“疑义导致解释”,即:若意思表示的理解出现疑问时,该项意思表示即须作出解释④参见【德】拉伦茨:《德国民法通论》,法律出版社2013年版,第457页。。而另有学者主张所有的意思表示均须解释,即:“解释具有中心意义。因此,在进行一切法学思考时,解释都处在很前的位置。几乎没有哪一个方面明显处于解释之前,许多方面都处在解释之后。”⑤【德】梅迪库斯:《德国民法总论》,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234页。王泽鉴教授亦持此观点,参见王泽鉴:《民法总则》,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380-381页。
据学者考证,“疑义导致解释”作为意思表示解释适用前提的观点,成为学界通说。⑥参见朱庆育:《意思表示解释理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26-128页。但是,有学者从局部解释学与一般解释学的角度,剖析理解与解释的分离与统一问题,并基于意思表示解释的语言性,得出意思表示解释具有普遍性,⑦参见前引⑥,第128-135、154页。进而认为“所谓意思表示解释,乃是理解其规范意义的过程。”⑧朱庆育:《民法总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214页。
本文认为,意思表示解释具有普遍适用性,其旨在探寻意思表示规范意义,而非消除意思表示当事人之理解上的歧义。⑨尽管在司法实践中,意思表示的解释多体现为双方当事人就是意思表示的有无或确切含义发生争议之时,但是该争议的产生本身就是意思表示解释的结果。换言之,意思表示的初步解释,构成意思表示疑义的“前见”。支持此观点的理由如下:就条文表述而言,《民法总则》第142条未采用《合同法》第125条第1款“当事人对合同条款的理解有争议的”类似表述,据此我们无法从《民法总则》第142条的表述中得出意思表示的解释仅适用于“疑义导致解释”的结论;就语言性而言,意思表示与法律条文均以语言文字为表达工具,基于语言文字的多义性、模糊性以及应对复杂现实的局限性,此决定了意思表示解释的适用普遍性;就规范性而言,意思表示是表意人法律行为意思的实现过程的有效表示,⑩参见前引④,第452页。,具有个别规范意义上民法的法源地位,[11]前引⑧,第42页。因此意思表示解释应与法律解释一道遵循“法律非经解释不得适用”的基本规则。综上所述,意思表示解释具有适用上的普遍性,其规范价值不仅消除理解歧义,更追寻意思表示规范意义的理解。否则,意思表示解释将陷入“疑义导致解释”规则之理解与解释分离的窠臼。
(二)意思表示解释的性质
意思表示的解释究竟为事实问题还是法律问题,学界向有争论。[12]参见前引④,第477-479页;史尚宽:《民法总则》,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470页;王泽鉴:《民法总则》,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392-393页;前引⑧,第216-217页。譬如,有学者指出意思表示的解释是表示行为应有之意义,属于法律适用问题;[13]参见史尚宽:《民法总则》,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470页。而另有学者持有相反观点,即:意思表示的解释属于事实认定问题,隶属法院的事实认定之职责范围。[14]参见杨仁寿:《法学方法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237页。王泽鉴先生则认为解释客体和解释资料属于事实认定问题;而意思表示的解释本身属于法律的评价,理应归属法律适用问题。[15]参见王泽鉴:《民法总则》,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393页。
事实认定问题与法律适用问题的界分,[16]所谓事实问题,是关于事实上发生了什么的问题,由证据规则解决;而法律问题则指该发生之事件,依规范上的标准,具有何种法律意义的问题。事实问题的处理,应依证据由法院自由心证认定;而法律问题的处理,则由法院将该当之法律适用于其所认定的事实。参见黄茂荣:《法学方法与现代民法》,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第296页。在民事诉讼程序中具有重大意义。如前文所言,意思表示解释意在探究规范性的表示意义,肩负意思自治之基本理念,并根据行为人意志发生相应法律效果。
换言之,“意思表示是一种具有决定性的行为。意思表示的这一特征与法律或已具确定力的判决无异。”[17]参见前引④,第453页。因此,意思表示具有形同法律的规范性质,故意思表示的解释属于法律适用问题。
二、意思表示的解释对象
在《民法总则》的起草过程中,曾发生是规定意思表示的解释还是规定民事法律行为的解释的论争,而立法机关经研究认为:规定意思表示的意思问题涵盖更广,也更能准确地体现解释的真正对象[18]参见李适时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释义》,法律出版社2017年版,第439页。。因此,《民法总则》将意思表示的解释对象界定为意思表示,并分别配置有需受领的意思表示与无需受领的意思表示的解释规则。然而意思表示绝非铁板一块,其由 “意思”与“表示”两组词语构成,故意思表示的构成有外部要素与内部要素之分[19]前引⑧,第192页。。那么,意思表示的解释对象,究竟是外部要素、内部要素还是二者的组合呢?
(一)意思表示的解释对象:表示价值
诚如学者所言,意思表示的解释对象主要解决的问题,是以行为人的内心意思还是表示意思为对象。[20]张驰:《论意思表示解释》,载《东方法学》2012年第6期。当今学界,关于意思表示的解释对象,已形成相对集中的观点,诸如:拉伦茨教授指出,意思表示解释的对象只能是表示,即某种具有有效表示意义的行为[21]参见前引④,第452页。。王泽鉴教授则将意思表示的客体界定为表示行为,包括作为与不作为。[22]前引[15],第383页。而《民法总则》的起草者则认为意思表示解释的客体为表意人的表示意思,而非深藏于当事人内心的“内心真意”。[23]前引[18],第438页。值得注意的是,诸如当事人的先前谈判、特殊的语言用法、交易惯例、时间和地点等,则构成理解意思表示含义的背景和环境的解释资料,[24]参见前引②。并不属于意思表示的解释对象。
所谓表示价值,是可得而知之的“效果意思”,[25]关于表示价值的术语,笔者曾见之于王泽鉴教授的《民法总则》(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385页),但该术语的具体含义、要求及确定规则,则受益于金可可教授在2017年3月25日华东政法大学律师学院、沪法网法律实务高级研修班所作的《〈民法总则〉第六章“法律行为”规定之解读》,特此表示感谢。亦即具体确定的表示意思。依据《合同法》第14条第一项之规定,表示价值的内容要“具体确定”。所谓“具体”指的是表示价值具有法律行为的要素;[26]《合同法解释(二)》第1条明确了合同的基本要素为当事人名称或姓名、标的和数量,但该条文遗漏了表征该典型合同的基本权利与义务。而所谓“确定”则是表示价值的内容不存在歧义或矛盾,具有解释上的唯一性。表示价值的确定需要运用意思表示的解释规则,以客观相对人视角,确定表示行为所彰显的客观表示意思,但其存在当事人的特别约定、交易习惯、法律规定(推定或拟制)以及无相对人或相对人无合理信赖情形下的表意人的“真意”。
此外,意思表示之表示价值具有明示、默示和沉默等形式。所谓明示,亦称直接表示,指表意人直接通过语言文字将效果意思表示于外,包括口头、书面或数据电文等形式。所谓默示,又称间接表示,是指由语言、文字或特定行为间接推知行为人的表示价值。沉默则是不作为的默示,即当事人既未明示其意思,也无法籍于其他事实推知其意思。沉默原则上不由意思表示的价值,[27]前引[15],第320页。仅于例外情形具有表示价值。[28]《民法总则》第140条第2款规定:“沉默只有在有法律规定、当事人约定或者习惯时,方可以视为意思表示。”意思表示若以明示、积极的默示或构成意思表示的沉默作出,其表示价值的确定,需要借助意识表示的解释规则。
可能有人会基于无需受领的意思表示不存在合理信赖的保护,来质疑意思表示的解释对象为表示价值的结论。但是,笔者认为,尽管无相对人意思表示不存在意思表示的发出、受领乃至理解的问题,但无相对人意思表示的解释对象绝非表意人的纯粹“内心真意”,需要“结合相关条款、行为的性质和目的、习惯以及诚信原则”等解释因素来确定的“客观表示意思”,即表示价值。
(二)意思表示的类型界分
《民法总则》起草过程中,对意思表示的解释问题,存有如下争论:是区分需受领的意思表示和无需受领的意思表示分别规定不同的解释规则,还是不作区分而规定类似台湾地“民法”第98条的统一解释规则。《民法总则》第142条最终采取了前一种观点,将意思表示的解释区分为需受领的意思表示解释和无需受领的意思表示解释两种形式。[29]前引[18],第439页。因此,欲领悟《民法总则》第142条的规范内核,需要详加界分“需受领的意思表示”与“无需受领的意思表示”。
以意思表示是否需要受领为依据,意思表示可分为需受领的意思表示与无需受领的意思表示。
1.需受领的意思表示
所谓需受领的意思表示,是指对相对人发出、需要到达相对人或为受领人知悉方可生效的意思表示。需受领的意思表示存有意思表示的发出、到达、受领等问题。所谓意思表示的发出,指的是表意人对相对人作成意思表示,并完成使意思表示生效所必需的行为[30]前引⑤,第205页。。意思表示的发出,成为判断意思表示之有无、行为人之民事行为能力之有无、是否存在意思表示错误以及表意人死亡对意思表示效力之影响等法律问题的关键时点。研究需受领的意思表示到达的问题,目的是在于确认相对人随时了解意思表示内容的可能性,以及表意人有理由相信相对人已获悉意思表示的内容。
需受领的意思表示可基于受领人与表示人是否同时在场,可进一步分为对话的意思表示与非对话的意思表示。需要明确的是,在非对话意思表示中,意思表示的发出与受领人了解意思表示的内容具有异时性,且相对人支配意思表示的载体。例如,同班的甲同学向乙同学传递纸条,即为非对话的意思表示。《民法总则》第137条确立了对话意思表示的生效要件为相对人了解意思表示之内容;而非对话的意思表示则以到达主义为基本生效规则,且进一步规定:相对人未指定特定接收系统的数据电文采取自相对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该数据电文进入其系统时的生效规则。
2.无需受领的意思表示
所谓无需受领的意思表示,是指不存在相对人或无需相对人受领的意思表示。无需受领的意思表示,存在于单方民事法律行为中,例如单方允诺、抛弃、遗嘱、捐助等。无需受领的意思表示中,不存在意思表示的受领人,亦不存在意思表示的到达、受领等问题。因此,《民法总则》第138条规定无需受领的意思表示的生效时点为意思表示完成时。所谓意思表示的完成,就是意思表示具备了表示行为和效果意思两个要素,即表意人的效果意思通过自己的外部行为作出了表示。[31]杨立新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要义与案例解读》,中国法制出版社2017年版,第514页。
值得探讨的是,《民法总则》第139条的体系定位问题,[32]《民法总则》第139条规定:“以公告方式作出的意思表示,公告发布时生效。”该款所规定的意思表示究竟属于需受领的意思表示还是无需受领的意思表示特殊情形,存有疑问。《民法总则》起草者则认为该条为需受领的意思表示的特例,即:在意思表示有相对人的情况下,可能会发生意思表示的表意人不知道相对人的具体地址、相对人下落不明的情形[33]前引[18],第433页。。本文认为《民法总则》第139条规定的以公告方式作出的意思表示,为无需受领的意思表示的特例,理由是该种意思表示无需到达、受领和了解其内容的问题,且该种意思表示遵循意思表示完成即生效的判断规则。
三、意思表示解释的解释目标
意思表示的目标与前文所述的意思表示的对象不同,前者在于明确意思表示对象所显示的合理意义,而后者则意在明晰意思表示解释的客体。基于此理解,意思表示的解释目标,在于“解释终于何处”的探究,亦关系到意思表示误解风险的分担问题。[34]参见前引⑧,第220、223页。而就立法而言,《德国民法典》第133条以及台湾地区“民法”第98条均将意思表示的解释目标界定为“探求当事人之真意”,而《民法总则》第142条则认为:需受领的意思表示之解释目标是“确定意思表示的含义”;而无需受领的意思表示之解释目标则是“确定行为人的真实意思”。值得探讨的,《民法总则》第142条所确立的意思表示解释规则的解释目标救济是一元的还是多元的,应如何妥当界定
(一)意思表示解释之解释目标论争
意思表示解释目标的确定,历来存在意思主义与表示主义的论战。[35]参见前引⑥,第252页。具体而言:意思主义主张根据当事人意思 的原则,法律义务的产生是由当事人的自由意志决定和判定的,应优先考虑当事人的意思;表示主义则认为优先考虑外部标志,即意思表示的外部事实,因为社会和商业交往中要求保护信赖,而信赖体现在人们实际说出口的话上,不体现在他们所一直的含义上。参见【德】海因·克茨:《欧洲合同法》(上卷),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第155页。意思主义将意思表示的解释目标确定为探寻表意人的内心意图,但意思主义存在自相矛盾之处,即:法官基于理性人的假设,将对个体表意人的意思探究转化为对抽象理性人常识的判断,使得以当事人内心真意为解释目标的意思主义始于“当事人真意”,却终于抽象受领人所能理解的“表示上的意思”。[36]参见前引⑥,第254、257、258页。而表示主义则以意思表示之客观意义为“当事人真意”的载体,取代表意人的内心真意,重在维护受领人信赖利益和交易安全。此举虽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意思主义难以“客观化”之缺陷。但是,表意主义的致命缺陷就是该理论忽略了私法自治的行使。
为弥补意思主义和表示主义的上述缺陷,消除当事人内心意思与外在表示的区隔,意思表示就是对意思的表示,意思与其表示结合为一体,在意思表示之外不存在“超然独立”的意思,在意思之外也无“空白的”表示。[37]参见张俊浩主编:《民法学原理》,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29页。此情形下,意思表示解释的目标通常界定为“表示上的意思”,但是在意思表示之“内心意思”和“外部表示”二元区分的理论体系下,意思与表示难以拥有对方的特质。“表示上的意思”因存在体系违反,而致其无法得到界定。[38]参见前引⑥,第268页。为弥补意思主义、表示主义的缺陷,拉伦茨教授首创效力主义解释理论,即:意思表示并非单纯表达事实或想法的行为,而是一种效力表示,而表意人之所以要对外在表示负责,原因在于该表示可归因于表意人,故在解释需受领的意思表示时,应探求适用于表意人与受领人双方的客观规范意义。[39]参见前引⑧,第225页;郝丽艳:《意思表示的解释方法》,载《北方法学》2015年第5期。有学者在梳理意思主义、表示主义以及折中主义的种种缺陷后,提出意思表示解释目标为“论辩中的视域交融”,即:所谓意思表示解释,就是论辩各方视域交融的过程,而解释的目标的实现也以彼此辩论达成一致的视域融合为标志[40]参见前引⑥,第283页。。
本文赞同意思表示是产生规范意义的有效表示,且以意思表示为核心的法律行为具有民法法源性,故意思表示的解释宜秉持“效力主义”,并以探求表示真意为解释目标。
(二)《民法总则》所确立的意思表示解释目标
《民法总则》颁行后,学界基于第142条的解释论,对意思表示解释目标有所论述。有学者指出不同情形下的意思表示解释,其解释目标并不全然一致:无需受领的意思表示的解释目标为探求表意人的主观真实意思,而需受领的意思表示解释则以查知受领人理解的意思为解释目标,以公告表示的意思表示的解释目标旨在查知交易典型的表示意义。[41]参见前引②。而其他学者则认为意思表示的解释目标具有多重性:其一为探究隐藏在表示之下当事人的法律行为意思,此解释目标是纯粹的对当事人主观意思的查明;其二为对意思表示受领人之理解的探究,此以不特定第三人可理解的含义为解释目标,为客观规范解释。[42]参见龙卫球、刘保玉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释义与适用指导》,中国法制出版社2017年版,第500页。
意思表示的解释目标的确立,需要以意思表示解释的规范目的为出发点。意思表示解释,就是理解意思表示规范意义的过程[43]参见前引⑧,第214页。。《民法总则》创设意思表示解释规则的规范目的,在于定分止争,明确意思表示的真实含义。[44]参见前引[18],第438页。此外,意思表示为内在意思与外部表示的组合体,无外部表示,就无从表露表意人的内在意思;而无内在意思,其外部表示则沦为无源之水。因此,前文将意思表示的解释对象界定为可得推知的“效果意思”,即表示价值。故意思表示的解释目标就是对表示价值的探究。即使以遗嘱为典型的无需受领的意思表示,其解释目标也不是纯粹的当事人的真实的主观意思,而是结合遗嘱的条款、目的、习惯和诚信原则,综合探求遗嘱人的表示价值。否则,遗嘱解释将陷入无法求证的历史的心理事件。
四、意思表示的解释方法
《民法总则》第142条基于需受领的意思表示与无需受领的意思表示的类型划分,分别配置了意思表示解释规则。本文从意思表示解释方法类型化的角度,来探讨意思表示的具体解释规则。
(一)意思表示解释方法的类型划分
现代民法就意思表示的解释,主要采取自然解释、规范解释和补充解释的方法。[45]参见郝丽艳:《意思表示的解释方法》,载《北方法学》2015年第5期。王泽鉴教授则对意思表示的解释方法进行了图表式梳理,并类型化如下[46]前引[15],第390页。:

此外,亦有学者对意思表示的解释方法作了类似的类型化梳理,如下[47]参见金可可教授在2017年3月25日华东政法大学律师学院、沪法网法律实务高级研修班所作的《〈民法总则〉第六章“法律行为”规定之解读》的课件。:

(二)意思表示的简单解释
1.自然解释
所谓自然解释,是指以确定表意人的内心真意为目标的解释方法。自然解释主要运用于《民法总则》第143条第2款之无需受领的意思表示的解释规则中。因无相对人意思表示仅有意思表示的做成,而无意思表示的发出、到达和受领问题,故无相对人意思表示的解释,对客观情况考虑较少,主要探究表意人的内心真实意思,且不能完全拘泥于意思表示所使用的词句。但为防止解释的恣意,该款规定强调要综合运用所使用的词句、相关条款、行为的性质和目的、习惯以及诚实信用原则,探究表意人的内心真实意思。但值得注意的,此“表意人的内心真实意思”,需要法官运用民事证据规则和相关条款、行为的性质和目的、习惯以及诚实信用原则等解释要素进行探究。
2.规范解释
所谓规范解释,又称客观解释,就是以探求意思表示之表示价值为目标的解释方法。规范解释主要适用于需受领的意思表示解释。这是因为需受领的意思表示以意思表示必须到达受领人或为受领人所了解方可发生效力。[48]参见前引⑧,第240页。因此,需受领的意思表示解释存在相对人信赖利益保护的问题。即使表意人的表示意思与内心真意不符,在对该意思表示进行解释时,也应考虑相对人的信赖利益保护,而不能完全依据表意人的内心真意来解释,也就是说,应当考虑客观主义的运用。[49]王利明:《民法总则》,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309页。若表意人的表达有误,使相对人对意思表示做出了不同于表意人所欲表达的理解,那么表意人必须承认相对人实际所理解的意义是有效的。[50]参见前引④,第453-455页。为平衡表意人的自我决定与相对人信赖利益的冲突,规范解释要求法官须以“理性人”的立场,按照意思表示所使用的词句,结合相关条款、行为的性质和目的、习惯以及诚信原则,确定意思表示之表示价值。
(三)意思表示的补充解释
所谓补充解释,是以假设的当事人意思为准据,对意思表示的漏洞填补为目的的解释方法。[51]参见前引②。意思表示补充解释旨在创设客观规范,弥补意思表示的漏洞,最大限度维护既有意思表示的有效性,以完成意思表示实现相应法律效果所需要的细节。[52]参见前引⑧,第231页。
尽管《民法总则》未确立意思表示的补充解释规则,但应意思表示解释的基本法理,在意思表示解释适用中,引入意思表示的解释规则。孙宪忠教授主持的《中国社会科学院课题组关于“民法总则”建议稿》第196条可资借鉴。[53]《中国社会科学院课题组关于“民法总则”建议稿》第196条规定:“法律行为内容不完整不影响法律行为基本法律意义的,应当根据相关法律中的任意性规范进行补充;在无任意性规范可得适用时,根据诚实信用原则以及交易习惯来推断当事人的意思。”“在进行前款补充解释时,应当尊重当事人的意思自由,不得侵害当事人的利益。”此外,《合同法》第61条和第62条所确立的合同漏洞的补充规则,不仅适用需受领的意思表示的补充解释,亦可类推适用于无需受领的意思表示的补充解释。
意思表示补充解释的适用,应仅在于意思表示存在漏洞的场合。意思表示补充解释所应遵循以下规则:优先以法律的任意规定填补意思表示漏洞;补充解释仅对意思表示内容上常素的缺失进行补充,代之以假设的规范意思。[54]参见前引②;前引⑧,第231-232页;王泽鉴:《民法总则》,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389-392页。但是补充解释不得替代合同的缔结。
责任编校:姜燕
*周玉辉,山东政法学院民商法学院讲师,山东省高等学校人文社科研究基地(民商事法律与民生研究中心)研究员,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法学博士。本文系山东省社科规划项目《民法典编纂中的农地物权体系研究》(15CFXJ36);中国法学会2016年度部级法学研究课题《农村土地“三权分置”的立法表达研究》(CLS(2016)D74);山东政法学院校级课题《中国民法典内在体系研究》(2015F06B)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