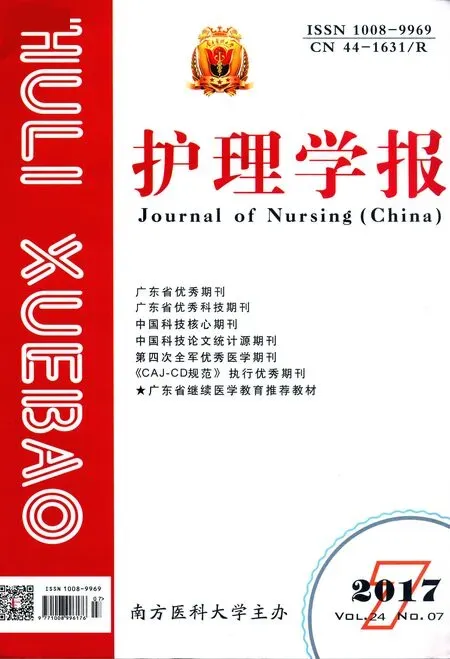Johns Hopkins循证护理实践模式的研究进展
卞 薇,Kim Bissett,田 旭,刘 洋,万君丽,谭明琼
(1.第三军医大学西南医院 眼科,重庆 400038;2.Dept.of Nursing Administration,the Johns Hopkins Hospital,Maryland Baltimore 21218,USA;3.重庆肿瘤研究所,重庆 400040)
Johns Hopkins循证护理实践模式的研究进展
卞 薇1,Kim Bissett2,田 旭3,刘 洋1,万君丽1,谭明琼1
(1.第三军医大学西南医院 眼科,重庆 400038;2.Dept.of Nursing Administration,the Johns Hopkins Hospital,Maryland Baltimore 21218,USA;3.重庆肿瘤研究所,重庆 400040)
系统介绍了Johns Hopkins循证护理实践模式,包括3大关键要素,即实践、教育和研究;其核心是证据,分为研究型证据和非研究型证据;以及众多内因和外因。阐述了循证实践的3阶段流程即实践问题、证据生成和证据转化以及国内外应用进展,旨在为我国护理人员开展循证护理实践、教育和研究提供思路和方法指导。另一方面,在实践过程中加强该模式与其他循证护理实践模式的相互比较,并根据我国国情对该模式进行不断地测试和修订,加强该模式理解、应用和实践项目成效报道,并根据不同研究目的和临床情景来发展其概念框架是未来发展方向。
循证护理实践模式;Johns Hopkins;循证护理
知识转化可以弥补研究与实践之间的巨大差距,而循证实践(evidence-based practice,EBP)致力于将现有最佳证据应用到临床中,是实现知识转化的重要途径[1]。循证护理(evidence-based nursing,EBN)作为循证实践的分支,是指护理人员在计划其护理活动过程中,审慎地、明确地、明智地将科研结论与其临床经验以及患者愿望相结合,获取证据,作为临床护理决策依据的过程[2]。随着2012年国际护士会“循证护理实践”主题的提出,一系列的循证护理实践项目在国内逐步开展,这不仅提高护理人员的循证意识,节约医疗卫生资源,还保障护理实践安全性和规范性,最终有效提升临床护理质量。如何有效开展循证护理实践,克服临床证据转化带来的困难和障碍,是护理人员面临的重要问题。目前,国外学者对循证实践模式进行了深入的探索和研究,如JBI循证卫生保健模式、健康服务领域研究成果应用的行动促进 (promoting action on research implementation in health service,PARIHS)循证实践模式、Stetler循证实践模式等,为循证护理实践提供了框架性的概念指导[3]。笔者通过对John Hopkins循证护理实践模式(Johns Hopkins nursing ebp model and guidelines,JHNEBP)[4]概念框架及应用进行系统描述,以期为我国临床护理人员循证实践活动的开展提供科学的思路和方法学指导。
1 Johns Hopkins循证护理实践模式的提出与发展
鉴于既往的循证实践模型较少专门用于护理人员的临床护理实践,且未能全部考虑循证实践整个过程的复杂性,因此,约翰·霍普金斯医院护理部和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护理学院共同研发了John Hopkins循证护理实践模式,旨在将护理临床、管理和教育领域的证据转化为实践策略[5-6]。与常规仅考虑单一因素的循证实践概念框架不同,John Hopkins循证护理实践模式既描述了3大基本要素在证据获取和应用过程中的相互作用关系,强调创建支持循证实践环境并构建组织文化的重要性,同时针对整个实践过程提出了3阶段步骤。随后,该团队不断从理论和实践上对其框架进行修订和完善,同时形成了该实践模式概念模型、实施和转化指南[7-10]。
2 John Hopkins循证护理实践模式的基本结构
该模式把循证护理实践看做一个开放性系统,由护理实践、教育和研究3个基本要素构成模型的基本点,以最佳证据作为理论框架的核心元素,并受到内因和外因的共同影响,见图1。

图1 Johns Hopkins循证实践模型
2.1 3大关键要素 John Hopkins循证护理实践模型描绘了奠定护理学专业的3大关键要素:实践、教育和研究,分别构成了模型的三角。(1)实践,是临床护理工作的基本组成部分[11],反映了护理人员从知识到实践的转化;(2)教育,是护理人员构建专业理论知识和操作技能、维持能力水平影响和改进其实践能力的重要途径;(3)研究,能产生新的知识并基于科学证据基础上推动临床实践[4,6]。John Hopkins循证护理实践模型采用结构化的方法提高护士在临床实践中提出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根据现有证据来评价并改进现行的临床护理实践,通过终身学习提高专业技能和持续的胜任力[5]。同时也要求护理研究以EBP作为理论指导,采用科学的方法来改善护理质量、护理体系和患者健康结局[12]。
2.2 核心 Johns Hopkins循证实践模型的核心为证据,分为研究型证据和非研究型证据[5]。在证据转化阶段,首要考虑研究型证据。研究型证据解决特定性环境下的特定问题,因此护理人员应充分考虑研究类型、质量、结果是否能根植于当前的临床情景以及实施改革的经济成本和风险等[4]。而当研究型证据难以利用或数量有限时,可考虑非研究型证据,如临床指南、文献综述、国家和地方专业组织的建议、规范、质量项目、专家意见等。近几年来,随着越来越多的患者主动参与到医疗卫生决策中,一些患者偏好相关证据包括患者访谈、患者满意度和焦点小组等也构成了非研究型证据的来源[13]。因此,临床护理人员应充分考虑具体的临床环境、患者的价值观、信仰和偏好,协助并支持患者做出正确的决策从而提高患者依从性[14]。
2.3 内因和外因 Johns Hopkins循证护理实践模型不仅受到证据的影响,还受内因和外因的影响。(1)外因,包括认证机构、合法性、质量评价、规范和标准,用于确保组织实施各项临床实践和标准都是基于可靠证据;(2)内因,包括组织文化、环境、设备供给、员工和标准[4,6]。Newhouse 等[8]进一步阐述组织机构创建支持循证实践环境的重要性,包括:领导层建立EBP文化;不断提高实施EBP的能力;持续变革;克服各种障碍和阻力。一方面,组织需为高水平的护理研究和循证实践提供基础设施,包括增加基本设备以及资源的有效分配。另一方面,护理领导全力支持并参与循证实践项目的开展,对整个循证项目进行监督和持续变革,从而确保实践的正常进行。同时,Newhouse等[15]指出除机构自身的组织文化以外,病区或团队层面还存在着亚文化,两种文化的能否有效协调将会影响临床决策。Johns Hopkins模型对内外因素的细化使其在应用过程中更具有动态性和可操作性。
3 John Hopkins循证护理实践3阶段流程
John Hopkins循证护理实践模式流程分为实践问题(practice question,P)、证据生成(evidence,E)和证据转化(translation,T)3 个阶段,共 18 个步骤,简称PET模型。体现了从问题提出到应用的完整过程,为研究证据向实践的转化提供了明确而清晰的概念框架。
3.1 实践问题 包括确定循证问题、界定问题范畴、分配职责、建立多学科团队并召开团队会议5个步骤。PET第一步,基于临床情境提出具体的临床问题,并采用PICO(patient intervention comparison outcome)程式将问题结构化[16]。同时界定问题范畴,明确具体的研究人群和利益相关者,建立多学科工作小组,并定期召开小组会议。
3.2 证据生成 PET流程第2阶段是检索、评价并综合可获得的最佳证据。包括5个步骤,检索内外证据、评估证据、总结证据、对证据强度进行分级并做出推荐意见。在John Hopkins循证护理实践模式质量评价体系中,采用I-V级来划分证据强度,I代表证据强度最强而V强度最弱。质量评估根据等级高、中、低分别划分为A、B、C共3个级别。同时,John Hopkins循证护理实践模式针对该阶段的各个步骤设计了专门的操作工具包括 《证据评估工具》、《单项证据总结工具》和《综合与建议工具》来帮助护理人员更规范、条理性地完成这一阶段工作[4]。
3.3 证据转化 该流程第3个阶段共8个步骤,EBP团队分析证据转化的适宜性和可行性,构建行动方案、实施变革并评估效果,明确后续方案并传播实践成果[17]。该阶段尤为重要的是,在组织的有力支持和资源有效分配下,通过团队培训、流程优化和使用评估工具等方式,以及对方案进行不断的评价、修订和验证,才能真正有效实施变革,改善患者结局以及护理的知识、行为和信念,实现系统的良性运转和不断循环发展[18]。
4 Johns Hopkins循证护理实践模式的应用进展
Johns Hopkins循证护理实践模式自2005年开发以来,广泛用于社区护理、精神病护理、五官科护理等多个领域的实践活动及相关研究。
4.1 以John Hopkins循证护理实践模式作为理论框架的应用研究 主要包括以John Hopkins循证护理实践模式作为理论框架指导临床护理实践活动以及采用John Hopkins循证护理实践模式中的证据评估工具对证据等级和质量进行评价两个方面。在证据评价方面,Santos等[19]采用Johns Hopkins证据评价工具对成人鼻饲管内部插入长度方法的相关文献进行整合性评估,从而确定鼻饲管插入长度的最佳测量方法,最后指出传统“鼻子—耳朵—胸骨剑突”导管长度的测量方法不能使导管正确到达胃内。马里兰大学Grant教授等[20]用该工具系统回顾并评价了目前促进有效沟通技巧的教育方法,框架和评估工具方面证据情况,并提出研究中使用概念框架以及基于信度和效度有效检验工具的重要性。同时,我国学者何雪姣[21]、张华芳[22]也采用John Hopkins循证护理实践模式工具对现有证据进行评估,并结合Delphi法制定了最佳压疮预防策略和综合医院护理质量敏感性指标体系。
在实践应用方面,Schwarzrock[23]为规范发生脑水肿的脑肿瘤患者高剂量采用地塞米松进行药物管理,从而促进开处方者和照顾团队更合理地对这类特殊患者的管理,采用Johns Hopkins循证实践模式用于指导实践的具体实施过程。同时指出,临床实践指南的制定应包括开处方和护理措施,且在用药监管中学科间的合作是极其重要的。Mori[24]以该模式为指导,探索减少全膝关节置换术和全髋关节置换术患者手术部位感染耐甲氧西林金黄色葡萄球菌的发生率的最佳实践。Buchko等[25]研究了预防女性泌尿系统手术后住院期间因膀胱膨胀而发生尿潴留的最佳循证实践,指出该模式在临床实践指导中的可操作性和系统性。
4.2 基于John Hopkins循证护理实践模式框架下组织文化的研究 美国学者Tabak以John Hopkins循证护理实践模式为理论框架,采用质性研究探索了健康部门推进项目和政策的促进因素包括领导支持、促进组织沟通、整合评估和实践以及灵活的资金利用度4个方面[26]。Farokhzadian等[27]调查了John Hopkins循证护理实践模式组织环境中护理领导者态度、自我效能以及培训需求对临床循证实践顺利开展的影响,指出领导者没有经过专门的循证培训或缺乏循证实践意识将会影响护理临床工作的质量和安全。与此同时,护士自身的能力建设包括循证实践知识、技能以及资源的合理分配对循证实践过程和结局产生重要影响[28]。
5 Johns Hopkins循证护理实践模式的评价及展望
5.1 Johns Hopkins循证护理实践模式的不足 虽然该模式提供了一系列工具引导实施者有计划地进行组织变革,特别适用于床旁护理循证实践,同时也为组织环境及促进因素提供了明确的概念框架。但有别于同样适用于评估组织环境循证实践模式如研究与实践合作促进(Advancing Research and Clinical Practice through Close Collaboration,ARCC), ARCC具有清晰可度量的组织环境和变化的评估工具,而John Hopkins循证护理实践模式缺乏,从而导致不同实践者对概念的解读存在一定的差异性[29]。其次,在证据质量分级中,该模型将指南定为第IV等级(即非研究证据类别),而在其他权威机构的证据分级中位于较高等级,如中国循证医学中心证据分级以及加拿大McMaster大学流行病学与生物统计学教授Brian Haynes提出的“9 S”证据金字塔中官方指南的等级均高于RCT等研究型证据等级[30]。
5.2 Johns Hopkins循证护理实践模式的展望 目前,我国引入循证实践的概念和方法时间较短,大部分护理人员对循证护理的理解仅停留在浅显的感知层面甚至误用循证实践的概念,而没有深入了解其内涵和方法学[31]。因此,清晰了解并选择合适的循证护理实践模式对临床护理循证实践项目的开展和学科发展是极其重要的。在实践中加强该模式与其他循证护理实践模式的相互比较,从而更加清晰明确地了解其内涵、步骤、核心要素和应用,如组织文化和支持环境的概念界定[32]。另一方面,在实践过程中需根据我国国情对该模式进行不断地测试和修订,加强该模式的应用和实践项目成效报道,并根据不同研究目的和临床情景来发展其概念框架也是未来发展方向。
综上所述,Johns Hopkins循证护理实践模式的三角框架结构从整体上清晰地阐述各要素之间相互作用和相互依存的关系,强调证据的多元化及核心作用,并重视内因和外因对整个循证实践过程的重要影响。同时,该模式对循证实践中的关键步骤还辅以工具表,具有很强的实用性和可操作性,有利于护理人员特别是初学者更规范、有条理地开展床旁护理循证实践,从而促进知识转化最终提高护理服务质量。
[1]Sudswad P.Knowledge Translation:Introduction to Models,Strategies,and Measures[J].Public Works,2007,2(2):97-104.DOI:10.1007/S12245-010-0168-x.
[2]胡 雁.循证护理学[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12:10.
[3]Kitson A G,Harvey and Mccormack B.Enabling the Implementation of Evidence Based Practice:A Conceptual Frame-work[J].Quality in Health Care,1998,7(3):149-158.DOI:10.1186/s12889-016-2882-7.
[4]Newhouse R,Dearholt S,Poe S,et al.Johns Hopkins Nursing Evidence-based Practice Model and Guidelines[M].Indianapolis:Sigma Theta Tau International,2007:5-15.
[5]Newhouse R,Dearholt S,Poe S,et al.Evidence-based Practice:A Practical Approach to Implementation[J].J Nurs Adm,2005,35(1):35-40.
[6]Newhouse R,Dearholt S,Poe S,et al.Organizational Change Strategies for Evidence-based Practice[J].J Nurs Adm,2007,37(12):552-557.DOI:10.1097/01.NNA.0000302384.91366.8f.
[7]Newhouse R P.Examining the Support for Evidence-based Nursing Practice[J].J Nurs Adm,2006,36(7/8):337-340.
[8]Newhouse R P.Creating Infrastructure Supportive of Evidence-based Nursing Practice:Leadership Strategies[J].Worldviews on Evidence-based Nursing,2007,4(1):21-29.DOI:10.1111/j.1741-6787.2007.00075.x
[9]Satterfield J M,Spring B,Brownson R C,et al.Toward a Transdisciplinary Model of Evidence-based Practice[J].The Milbank Quarterly,2009,87(2):368-390.DOI:10.1111/j.1468-0009.2009.00561.x
[10]Newhouse R P.Collaborative Synergy:Practice and Academic Partnerships in Evidence-based Practice[J].J Nurs Adm,2007,37(3):105-108.DOI:10.1097/01.NNA.0000262736.06499.94.
[11]Porter O,Grady T.Shared Governance for Nursing:A Creative Approach to Professional Accountability[J].Aorn Journal,1984,44(3):468-470.
[12]Crowther M,Maroulis A,Shafer-Winter N,et al.Evidence-based Development of a Hospital-based Heart Failure Center[J].Reflect Nurs Leadersh,2002,28(2):32-33.
[13]Zoe J,Anthea C,Fan X Y.证据指导临床决策[J].中华护理杂志,2009,44(4):377-378.
[14]van Dulmen S A,Lukersmith S,Muxlow J,et al.Supporting a Person-centred Approach in Clinical Guidelines.A Position Paper of the Allied Health Community-guidelines International Network(G-I-N)[J].Health Expectations,2015,18(5):1543-1558.DOI:10.1111/hex.12144.
[15]Newhouse R P,White K M.Guiding Implementation:Frameworks and Resources for Evidence Translation[J].J Nurs Adm,2011,41(12):513-516.DOI:10.1097/NNA.0b013e318 2378bb0.
[16]Richardson W S,Wilson M C,Nishikawa J,et al.The Well-built Clinical Question:A Key to Evidence-based Decisions[J].Acp Journal Club,1995,123(3):12-13.
[17]Anonymous.Johns Hopkins Nursing Evidence-based Practice:Implementation and Translation[J].Critical Care Nurse,2010,30(6):210-226.DOI:10.1093/geront/gnu123.
[18]Shirey M R.Evidence-based Practice:How Nurse Leaders Can Facilitate Innovation[J].Nurs Adm Q,2006,30(3):252-265.
[19]Santos S C,Woith W,Freitas M I,et al.Methods to Determine the Internal Length of Nasogastric Feeding Tubes:An Integrative Review[J].Int J Nurs Stud,2016,61(1):95-103.DOI:10.1016/j.ijnurstu.2016.06.004.
[20]Grant M S,Jenkins L S.Communication Education for Prelicensure Nursing Students:Literature Review 2002-2013[J].Nurse Educ Today,2014,34(11):1375-1381.DOI:10.1016/j.nedt.2014.07.009.
[21]何雪姣.基于循证构建压疮预防策略的研究[M].杭州:浙江大学,2014.
[22]张华芳.基于循证构建构建护理质量敏感性指标[M].杭州:浙江大学,2014.
[23]Schwarzrock C.Collaboration in the Presence of Cerebral Edema:The Complications of Steroids[J].Surg Neurol Int,2016,7(8):185-189.DOI:10.4103/2152-7806.179228.
[24]Mori C.Implementing Evidence-based Practice to Reduce Infections Following Arthroplasty[J].Orthop Nurs,2015,34(4):188-194.DOI:10.1097/NOR.0000000000000157.
[25]Buchko B L,Robinson L E.An Evidence-based Approach to Decrease Early Post-operative Urinary Retention Following Urogynecologic Surgery[J].Urol Nurs,2012,32(5):260-264.DOI:10.2147/IJWH.S55383.
[26]Tabak R G,Duggan K,Smith C,et al.Assessing Capacity for Sustainability of Effective Programs and Policies in Local Health Departments[J].J Public Health Manag Pract,2015,22(2):129-137.DOI:10.1097/PHH.0000000000000254.
[27]Farokhzadian J,Nayeri N D,Borhani F,et al.Nurse leaders’Attitudes,Self-efficacy and training Needs for Implementing Evidence-based Practice:Is It Time for a Change toward Safe Care?[J].Br J Med Med Res,2015,7(8):662-671.DOI:10.9734/BJMMR/2015/16487.
[28]Parkosewich J A.An Infrastructure to Advance the Scholarly Work of Staff Nurses[J].Yale J Biol Med,2013,86(1):63-77.DOI:10.1097/01.NNR.0000280629.63654.95.
[29]Levin R F,Feldman H R.Teaching Evidence-based Practice in Nursing[M].2th ed.New York:Springer Publishing Company,2013:223-366.
[30]Dearholt S L,Dang D.Johns Hopkins Nursing Evidencebased Practice:Model and Guidelines[M].2th ed.Indianapolis:Sigma Theta Tau International,2012.
[31]李幼平,陶铁军,孙 丁,等.我国专科医师分类研究初探[J].中国循证医学杂志,2004,4(3):173-180.DOI:1672-2531(2004)03-0173-08.
[32]Conklin J,Kothari A,Stolee P,et al.Knowledge-to-action Processes in SHRTN Collaborative Communities of Practice:A Study Protocol[J].Implement Sci,2011,6(1):1-11.DOI:10.1186/1748-5908-6-12.
[本文编辑:陈伶俐]
R47
A
10.16460/j.issn1008-9969.2017.07.026
2016-12-26
卞 薇(1984-),女,重庆人,硕士,主管护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