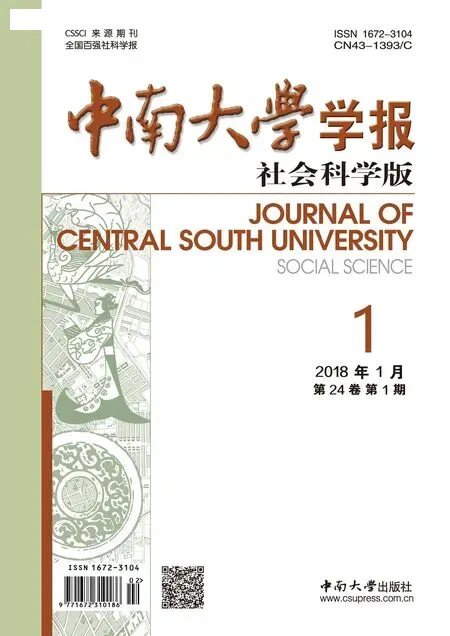超越“中西”
——劳思光的中西哲学沟通方法
冯骏豪
超越“中西”——劳思光的中西哲学沟通方法
冯骏豪
(北京大学哲学系,北京,100871)
从一开始的“逆格义”到新儒学“融通”中西哲学系统的尝试,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的沟通从晚清以来一直是中国哲学学科重要的课题。在新儒学之后,劳思光提出“开放哲学”的概念作为对哲学学科的理解方法,把中国哲学和西方哲学平等地安顿在世界哲学的框架之中,并以此为基础提出“成素分析”的中西哲学沟通和发展方法。分析劳思光的“成素分析”理论,不但可以看到中西哲学沟通的演变,同时对于思考中国哲学未来发展具有深远的意义。
劳思光;哲学沟通;后设哲学语言;开放哲学;成素分析
一、引言
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的互动始于“哲学”作为一门学科进入中国。当时西方国家以坚船利炮打开中国的大门,进入中国;而国人为了改革图强,开始学习西方文化从而思考其与中国文化的异同,以应对西方的挑战。哲学作为思考范畴之一,则由此开始了西方的“哲学”与中国思想学问之间的互动。由于中国的思想与西方的哲学方法并不一样,旨趣亦不尽相同,故此学人们开始思考中国哲学的定位问题。这个问题必然离不开以西方哲学作为重要的参照内容,而中西哲学的互动就从中国哲学的定位问题展开。从一开始的“逆格义”,到以西方哲学为参照来理解中国哲学,再到“大哲学”概念之建立以及融通中西哲学,不同时期的学者对于中西哲学的互动和沟通方式进行了很多尝试。本文则以劳思光作为中心,梳理和分析其中西哲学的沟通方法论。
二、20世纪中西哲学互动沟通的尝试
在清末民初时期,中国思想界流行一种“逆格义”的方式,使用比较生疏的西方哲学概念来理解中国传统思想,以求出现新的理解和诠释。这种“逆格义”的方式是中西哲学互动的开端,虽然可以为理解中国传统思想带来一些新的冲击,但毕竟“概念诠释”并不是哲学的全部工作,同时当时的学人对于西方哲学的理解处于初始阶段,故此概念上的名目转换并不能满足中国传统思想发展成中国哲学学科的需求。由此,学者开始进入以西方哲学为参照,定性和建立中国哲学学科的阶段。
以西方哲学为参照来定义中国哲学,以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以及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为代表。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被认为是开新纪元的作品,原因来自他突破格义的方式,以西方哲学的不同范畴,过滤中国学问,以找出中国哲学的内容。可惜的是胡适的作品并未完成,后来冯友兰的两卷本《中国哲学史》面世,把哲学分为宇宙论、知识论、人生论三部分,并以此为基准,过滤中国传统学说,以中国传统思想中“约略相当”于西方哲学的学问,作为“中国哲学”。此阶段中西哲学互动的特色是以西方哲学的内容为基点,由此过滤出“中国哲学”的内容,建构中国哲学的系统。不过,由于中西哲学的旨趣并不一致,故此以西方哲学内容为中心“过滤”出中国哲学的方法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失去了中国哲学的原有特色,出来的结果只是“在中国的西方哲学”。由此,对于探寻中国哲学特性以及建立统摄中西哲学的“大哲学”的想法萌生了。
张岱年在其《中国哲学大纲》中说:“我们也可以将哲学看作一个类称,而非专指西洋哲学。可以说,有一类学问,其一特例是西洋哲学,这一类学问之总名是哲学。”[1]由此,学者开始尝试在大哲学的框架下,探索中国哲学有别于西方哲学的特色。其中梁漱溟认为中国传统思想强调体证,与西方哲学以思辨为中心不一样,故此反对以哲学之名称呼中国传统思想;而熊十力则认为思辨不阻碍体证,反之思辨可以作为体证的通路,并认为儒学乃哲学的正宗。二人的取向虽然大相径庭,但是二人均在探寻中国哲学自身的特殊性,以思辨与体证分立中西哲学精神的特色。后来,熊十力融通体证和思辨的进路,被弟子唐君毅和牟宗三继承,唐君毅、牟宗三建立“大哲学”的方法则是由“思辨”转化出“实践”,以思辨为实践的资源工具。此中透显出“思辨”为“实践”服务的观点,呼应着熊十力认为儒学“为哲学之正宗”的价值意向。通观此时期中西哲学的沟通,学者依然以处理两大哲学传统的交锋融合问题为主要目的,着重于对中西哲学传统已有成果的梳理,故此均是以现有的哲学内容为研究焦点,而视角则是系统与系统之间的整合。
三、劳思光处理中西哲学沟通问题的基本态度
劳思光曾经与牟宗三及唐君毅在香港中文大学共事,三人在学术问题上有不少的交流与讨论。不过劳思光并没有继承唐君毅及牟宗三的学术路径,而是以不一样的问题意识进行哲学研究。劳思光与唐君毅、牟宗三一样,在传统学问受到西方学问冲击,以及中国学问反思自身价值的背景之下,思考中国文化和中国哲学未来发展前景的问题。但劳思光是以包含中国哲学在内的整体哲学学科的发展作为其研究的问题,而不是单纯考虑中国文化的未来发展与出路的问题。故此劳思光对于哲学以及中国哲学的定位,以至中国哲学与其他哲学传统如何沟通发展的观点均与唐君毅牟宗三不同。
劳思光认为“现代化”与“西化”的概念应该分开,中西哲学交流并不是单纯为了学习西方。劳思光认为黑格尔的文化哲学模型在解释异质文化交流的问题时有其限制,并提出“创生”和“模拟”的区分作为考虑中西哲学沟通方法的基础。同时,劳思光认为单纯从中西哲学的比较视角上找出融通方法的互动方式,并不是有效的方法,有必要设立一种后设语言(meta-language)重新解释哲学,突破哲学只有中西两支的视角限制,把中国哲学安顿在世界哲学之内。
从中西哲学互动的发展过程来看,学习西方或者以西方哲学作为发展资源是中国哲学自身发展的一个重要过程。可是劳思光认为“西化”和“现代化”的观念必须明确分开,前者是属于地区文化之间的互动问题,后者则是历史阶段的转移。晚清以来洋务运动等文化改革运动,人们只知道“西化”,认为必须“西化”,但是他们只是出于解决西方文化冲击的思考,是从异质文化冲突与调和的视角上处理问题。劳思光认为:“他们基本上承认‘西化’之不可避免,但他们并不觉察自己的国家社会必须面对一个文化巨变的新世界。”[2](190)言下之意即是“现代化”与“西化”不一样,“现代化”涉及“历史阶段”的意识和价值选择,“现代化”即是把传统的文化包括哲学推进另一个历史阶段。因为原来已有的文化成果已经失效,故此需要一些改变,令新的文化成果能够应对当前的文化问题。故此,“现代化”涉及价值选择的成分。劳思光说:“我们意识到世界进入一个新阶段,则原有的文化结构与文化成果,都可能进入‘失效’的状态,于是我们就觉得‘应该’要走向现代化。这就是一种价值选择了。”[2](191)由此可见,中西哲学的互动必须跳出“西化”概念的限制,互动发展并不是单纯为了处理异质文化冲突的问题,视域也不再限制在“中西”之间,而是同时要处理中国传统哲学在面对现代文化的问题时,现有文化成果的“失效”问题。
劳思光提出“西化”和“现代化”的区分,并不表示中西哲学沟通的目标是要中国哲学走向现代化,而是要共同面对现代文化所出现的问题。劳思光指出,现代文化并不是一个“选择”,现代文化已经存在,世界已经进入了现代文化的阶段,而且不能逆转,故此现代文化的内容是中西哲学发展与互动不能逃避的课题。不过,劳思光并没有拥抱现代文化,而是认为中西哲学沟通互动的目的是要借助双方的“有效”资源,处理现代文化的问题。劳思光引用威尔斯的观点,指出现代文化的出现令19世纪成为了“希望世纪”;但发展到20世纪,现代文化则出现了种种问题和不同的文化危机,要应对这些问题,应该走出“封闭系统”的视域界限,提倡“开放思维”。劳思光说:“针对各种封闭的系统、封闭的语言,应提倡开放的思维……开放的意思则是没有划定界限,没有说这是最终的(ultimate)。有形上学思考习惯的人,往往说了一大套道理之后,好像‘天下之理尽在是矣’,其余就没有了。这样就成了封闭思维。所以在态度上,我提倡开放的思维,作为理论上的基本态度。”[3]由此可以看出劳思光对于中西哲学沟通的两种态度:第一是中西哲学沟通并不是为了中国哲学“现代化”,而是借助对方的有效资源处理现代文化的问题,故此其沟通方法论需要具有反思现代文化及现代性的空间。第二,中西哲学的沟通并不是两个封闭系统的沟通,而是要步向“开放思维”,由此则导向了劳思光所提倡的“开放哲学”概念,作为中西哲学互动的基础。
劳思光针对中西哲学的沟通方法要走出黑格尔模型有限性的问题,提出了“创生”与“模拟”的区分。劳思光认为,黑格尔的文化哲学模型是外在化(externalization)的模型,是人的思维外在化成为存在的模式,故此文化活动就是人的主体性一步一步往外展开,在存在界实现价值,并建立制度系统。当现有的文化成果未能解决当前面对的困难时,制度系统就会崩溃衰亡,衰亡之后人类会创造新的文化成果逐步克服困难,这个衰亡与创新的循环构成了螺旋发展观。劳思光认为黑格尔的文化哲学模型在解释一个文化内部的发展过程时十分有效,可是对于异质文化的互动与学习问题则具有有限性。因为在黑格尔模型之下,中国文化要生出西方的文化成果就会变成中国文化需要内含西方文化的价值意识。故此劳思光提出“创生”与“模拟”的划分,他借用帕森斯的内在化(internalization)模型,认为要生出异质文化的文化成果并不是由内部生出,而是直接学习模拟,然后整合调适。由此,劳思光认为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的沟通,并不是从中国哲学内部找寻西方哲学的元素,“开出”西方哲学的思考成果,而是一个互相模仿与调适的过程,从而创造新的哲学成果。因此,劳思光为中西哲学的沟通建构了互相学习对方的理论元素从而整合出新哲学成果的理论框架,作为其“成素分析”的中西哲学沟通理论的基础。
中西哲学之间究竟选取对方的什么元素作为沟通学习的对象,这中间需要一套衡量标准,而成功的沟通亦需要共同的后设语言。前文曾提及梁漱溟与熊十力均认为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的着重点与旨趣不同,即使熊十力及后来的唐君毅、牟宗三等均作出了融通的尝试,中西哲学在学院研究中的阻隔依然很大。现在即使在文化层面上有沟通和互相学习的需要,但如果中西哲学的沟通学习只是一种拼盘的观念,缺乏统一的价值衡量标准,所出来的结果只会四不像,并不能有效解决文化危机,由此则涉及了后设语言(meta-language)的建立问题。劳思光说:“我的想法是,将‘理论效力’一观念扩大,而纳入‘后设哲学语言’(meta-philosophical language),重新解释哲学功能,以安顿中国哲学于世界哲学之中。”[2](20)劳思光认为需要建构一套后设哲学语言,以理论效力作为衡量中西哲学成果的标准,再由此建立中西哲学沟通及互相学习的桥梁,即是劳思光的“成素分析”理论。
四、后设哲学语言——“开放哲学”概念
劳思光认为,中西哲学之间的沟通不能局限于两个封闭哲学系统的比对,从而引入“开放哲学”的概念。所谓“封闭哲学系统”即是以现有的内容划定了某特殊哲学的范围,而不属于这个范畴的理论则会被排斥在外,造成整个系统的封闭性。劳思光认为,以哲学史的历史图像来看,哲学的内容一直不断流变,以现存已知的内容理解哲学会被封闭性所限制,阻碍了哲学产生新理论的空间,也无助于不同哲学传统之间的沟通。同时,以现有的哲学内容即综合中西哲学传统的理论来理解作为整体学科的“哲学”,为哲学定义,也会出现困难。劳思光从“哲学”定义与理解的问题开始,建构“开放哲学”概念,亦以此作为“成素分析”沟通理论的基础。
劳思光认为哲学难以定义,是因为找不到哲学与其他学问的“类差”,即哲学有别于其他学科的成分。由于哲学研究的题材一直在变化,因此类差一直都不能确定,亦导致哲学难以被定义。劳思光指出,哲学在前苏格拉底时代研究世界质料问题,到苏格拉底时认为哲学问题是研究人的范畴,即“认识你自己”,再到柏拉图以宇宙论、知识论和形上学组成的“系统哲学”,再发展至后来的“经院哲学”、康德的知识论、语言哲学、意义论等等的不同哲学学派,哲学研究内容一直在不同范围上变化,难以找到一个稳定的内容作为哲学区别于其他学问的类差,因而哲学难以被“定义”。
从哲学难以被定义的问题,劳思光提出对“哲学”概念的新理解方法,以哲学的共同特性——反省思考入手来理解哲学。劳思光说:“把‘哲学’当作一个‘开放概念’来讲,这个关键就在不要把‘哲学’当成一个首要的对象,而是把哲学思维(philosophical thinking)当作界定的对象,然后就‘哲学思维’的成果构成‘哲学’。”[4](12−13)劳思光不再透过内容理解哲学,而是透过各种特殊哲学的共同特性,即哲学思维理解哲学。只有哲学才有哲学思维,故此了解“哲学思维”即是理解哲学的特性。劳思光认为:“‘哲学思维’是一种自己对于自己的了解,因此就称作‘反省思维’(reflective thinking)——‘反省思维’,究竟是思考哪一些问题,这个地方是个变数。”[4](15−16)可见,劳思光认为哲学的思维就是一种自己对于自身活动的了解,而哲学的成果就是这种思维之下所得出的成绩。劳思光认为,理解哲学就是研究其思维方法,说明哲学如何思考和研究,而不是说明其思考研究的对象。劳思光指出,经验科学是说明世界的各种现象,同时说明现象之间的关系。“哲学思维”与“科学思维”最大的不同,就是“哲学思维”以自身的活动作为对象,而不是以外在的世界和知识为说明对象。由此可以显示,哲学是了解人自身的活动,而不是了解和报告人以外的世界。从哲学的共同特性——哲学思维的提出,劳思光的哲学理解跳出了以现有哲学成果理解哲学的封闭性的限制,走向“开放哲学”的概念。
从新的“哲学”理解方式,劳思光指出哲学思考的三个正面功能,包括批判功能、建设功能和整合功能。劳思光指出哲学是对自身活动的了解,而哲学发挥这三个功能则是为了达到了解自身活动的目的。劳思光指出,批判的功能并不是单纯指出理论的坏处,而是需要说明正反两面,即是“有效性”和“有限性”。当中所谓的“有效”和“有限”则是针对理论效力(validity)来说的,指出一个理论处理某个问题在什么地方“有效”、在什么地方“有限”,便是哲学思考所需要发挥的批判功能。哲学的建设功能则是建立某一种秩序,发现事物的普遍规则。劳思光举例说,要了解知识如何运行,了解人在什么原则下追求知识,都是假定了一些规则。这些规则是哲学思考追求的定律,但是这些定律并不是“不变的真理”。故此,哲学的建设功能就是要找寻自身活动的规律,发现某一种普遍的规则,而这些规则经常会是可以改动的。在整合功能方面,劳思光指出,古希腊的系统哲学建立了很长的形上学哲学传统,但这个传统在中古之后不断受到批判,先有康德哲学,再有语言哲学与解析哲学的批判。到了20世纪,各个哲学学派渐渐出现不能沟通的现象,甚至提出了“哲学的终结”这个概念。哈伯玛斯提出哲学需要重建,而劳思光指出这个“重建”就是要哲学发挥“整合的功能”。劳思光说:“在这个情况下……就是说一个重新整合的问题,一个在不同的哲学传统,如何能够相处而且有一个较高的发展,这就叫‘整合问题’,或者是‘系统化’(systematization)的问题。”[4](221)可见,哲学的整合功能就是不同哲学传统之间的系统化,从而能够往较高层级发展的功能。
劳思光认为哲学就是“反省思维”在不同领域的成果,这些成果则要在所思考的领域之中发挥着“批判”“建设”和“整合”三大功能。由此,劳思光指出哲学对人类文化活动的三个领域有所影响。而从这三个领域的划分,则可以找到中西哲学在劳思光的哲学框架下,各自所发挥功能的领域。劳思光指出哲学对人类文化活动的影响可以分为三个领域:第一个为“认知活动”的领域,即是人类建构知识,了解经验世界中事物的关系和性质的领域。第二个是“意志方向”问题的领域,“认知活动”领域是处理“存在”的问题,而“意志方向”的问题,则是处理“对不对”“应不应该”等价值判断与取向的领域。第三个领域则是美学的领域。劳思光认为美作为一种价值并不等同于道德价值,“艺术价值”的问题是“道德问题”这个规范价值之外的另一个领域。
这些领域的区分可以把中西哲学平等地安顿在世界哲学体系之中。劳思光提出西方哲学是“认知哲学”,而中国哲学则是“引导哲学”。前者的哲学思考是为了提供“确定的知识”,而后者则是为了达成“自我的转化”和“世界的转化”。故此,西方哲学的思考领域主要集中在认知活动之上,而中国哲学的思考对象主要集中在意志活动的领域之上。中西哲学各自通过反省思考在这两个领域发挥批判、建设和整合的功能,从而在文化世界上提供确定的知识或达成“自我的转化”和“世界的转化”。由此,劳思光重新把中西哲学平等地安顿在一个“开放哲学”的框架之中。哲学是反省思维的成果,而反省思维可以面对不同的问题,发挥哲学思维的正面功能,故此不同地区(不单是东方、西方)的文化面对不同的文化问题所作的反省思考成果,就成为了该地区的哲学,这就是劳思光的“开放哲学”概念。不同哲学的差异与特殊性是因为自身文化的旨趣选择而产生的不同的思考成果。如此,不同哲学的地位是对等的,没有一个哲学传统是先天地优越地可以代表整个哲学领域。在这个“开放哲学”的概念之下,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则可以平等地安顿在世界哲学的概念之中。而这个平等的哲学地位则是劳思光对中西哲学互动沟通的“成素分析”理论的重要基础。
五、哲学之间的沟通方法——“成素分析”
劳思光针对文化冲突的问题,以“开放哲学”为基础,提出了“成素分析”的理论,尝试指出不同文化和哲学传统之间的相处与沟通发展如何成为可能。劳思光认为,“文化传统”不能彻底地改变,人能做的就是弱化文化冲突的观点,是预设了“封闭系统”和“开放系统”的划分。各个文化以至形上学、宇宙论等哲学理论,如果某成素不能够收进该系统的类之中,则会被该系统认为是不成立的,而这个系统便是一个封闭系统。
劳思光认为,要思考不同文化和哲学传统之间的沟通与冲突问题,需要突破上述的划分,把“封闭性”和“开放性”落在系统的成素中说,即是“开放成素”和“封闭成素”的划分。而每个文化系统、哲学系统,应该都同时具有这两个元素。劳思光说:“一种文化成果若只是特定的历史及社会脉络的产物,则他即属于‘封闭成素’,由此便极难为异质文化所吸纳。倘若它具有超越特定脉络的普遍性及长久性意义,则它即是这个文化系统中的‘开放成素’;它虽在发生历程中是属于某地区的文化成果,其内含意义却是普遍性的。”[3](126−127)故此“开放成素”即是在该文化和哲学传统中能够超越历史脉络和社会脉络,具有普遍及长久意义的元素;而如果成果未能超越这两个脉络,则是“封闭成素”。不同的哲学传统都会有它的旨趣,可是人类总有一些发现普遍问题的能力,当哲学传统接触到一些普遍问题的时候,就会产生“开放成素”。这些“开放成素”就是不同哲学传统和文化传统之间相处和接合的地方。劳思光指出,当不同传统的“开放成素”互相接合,则可以出现效力较为普遍的“高层级”的文化组织和理论建构,从而吸收较“低层级”的文化系统。因此,世界不同的哲学传统,包括中西哲学传统可以在涉及普遍问题的“开放成素”上接合,从而发展出理论效力较为普遍的“高层级”理论建构。这就是劳思光在“成素分析”的基础上,提出的中西哲学在世界哲学之中互相沟通和发展的途径。
在判断选取“开放成素”方面,劳思光提出以理论效力的“普遍性”作为衡量不同哲学传统的“开放成素”的标准。不少学者认为,理论的“有效性”会自然被文化背景所限制,不同文化之间的元素是不可能互相借鉴的,故此西方的、外来的理论元素不可能适用于中国。劳思光指出,每一个哲学传统都发生在特定的时空,有其自身的历史背景和社会背景,可是这个特定的时空与背景并不一定限制哲学传统中各理论的“理论效力”。他认为理论的“发生历程”和“内含品质”需要区分,并不能以前者衡量后者的高低。例如一个画家以救灾慈善为目的创作一幅作品,还是以谋生和取悦权贵为目的创作一幅作品,并不会影响到该作品本身的艺术价值。引发某哲学理论的特定时空背景,并不必然会影响到该理论自身对于处理问题的有效性和普遍性。故此,理论的“发生历程”并不会必然影响到该理论对于处理问题的有效性,而同一问题发生在另一个文化体亦不必然会使该理论失效。正如西方的显微镜可以看到西方人血液中的细菌,并不会因为血液换成了中国人的血液就会使显微镜失效而看不见中国人血液里的细菌。因此不能以该理论来自自身文化体还是外来文化体作为衡量该理论的标准,认为外来的理论元素必然不适用于自身文化而否定其理论,必须另立衡量标准。劳思光认为不同哲学传统的哲学成素的理论效力判断标准,就在于理论处理哲学问题的“理论效力”之普遍性。该哲学传统中理论的普遍性越高,则“开放成素”越多,即这个哲学传统与其他哲学的可沟通资源以及未来“较高层级”的新哲学发展的有效资源就越多。由此,“理论效力”的普遍性,即其面对人类文化共同问题的理论效力的高低,成为中西哲学以至世界不同哲学之间选取沟通学习元素的评断标准。
六、劳思光“成素分析”理论的分析与反思
劳思光突破黑格尔螺旋发展观的“外在化”模型的限制,参考了帕森斯的“内在化”模型,以“开放哲学”为基础,将中西哲学平等地安顿在世界哲学的视野之中,通过把“开放性”和“封闭性”从系统间的分析转到成素之中,令不同的哲学体系之间出现了“开放成素”的沟通空间;通过“开放成素”之间的接合,交互发展出能够应对人类文化共同问题的“较高层级”的哲学。同时,劳思光以每个哲学传统中理论的“理论效力”的普遍性作为衡量该哲学的“开放成素”的多少以及其对人类共同问题的“理论效力”高低的评断标准。
劳思光以“开放哲学”的概念,突破以现有内容理解哲学以及沟通空间的限制,开拓了不同哲学体系沟通的空间。纵观前人探讨中西哲学的沟通问题,大多都是先为中西哲学现有的内容做史学式的梳理,从而理解“哲学”的概念和找出中西哲学的特色;然后通过中西哲学特色的“比对”和尝试“融通”,找寻中西哲学的未来发展空间。以现有内容理解哲学会造成哲学的“封闭性”,阻碍了不同哲学传统之间的沟通。同时,哲学传统的“特色”是根据其历史脉络和社会脉络产生的独特旨趣而形成的,往往是“封闭性”之所在,故以现有内容找出哲学学派的特色并尝试“比对”和“融通”的方法具有一定的有限性,并不能保证可以找到沟通空间。劳思光的“开放哲学”概念以哲学的共同特性——反省思维为基础来理解哲学,并认为人类会共同思考某一些问题,预设了各个哲学传统的共同性,再由此寻找不同哲学传统对于人类共同问题具有普遍理论效力的“开放成素”,作为哲学传统之间沟通互动的接合点,发展更高层级的哲学。劳思光的“开放哲学”概念预设了不同哲学传统的共同性和人类共同思考的问题,即普遍性问题的存在。以此作为指针则可以更明确地寻找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具有普遍理论效力的“开放成素”,从而打开中西哲学沟通的空间。
同时,劳思光的“开放哲学”概念和“成素分析”理论,使中西哲学能够在世界哲学的范围内平等沟通。回顾前人对中西哲学沟通的尝试,从借助西方哲学的资源建立“中国哲学”概念,到尝试“融通”西方哲学,都前设着一种中西哲学之间的地位较量。他们都认为某一个哲学传统是整体哲学学科的宗主,而其他哲学传统则是从属的地位。中国哲学要么就是要经过西方哲学化的改造,才能成为合法的哲学学科;要么就是需要透过建立一套新的评断标准,为中国哲学建立“正宗”的地位。比如前期的胡适、冯友兰以西方哲学为哲学的基础过滤出中国哲学,当中就有以西方哲学代表“哲学”的意向;而后来熊十力认为儒学为哲学之正宗的态度则被唐君毅和牟宗三所继承,认为“思辨”为“实践”服务,则是要为中国哲学夺回“哲学的正宗”的地位。在劳思光的“开放哲学”的概念中,认为不同哲学学派的差异只是反省思考的旨趣不同和发挥功能的领域不同,即使每个哲学学派面对共同问题是有“理论效力”的高低,可是并没有所谓“正宗”的概念。中西哲学与其他的哲学传统一样,都是反省思考的成果,并在平等的地位之中进行沟通与发展。
劳思光的“成素分析”理论,从“系统分析”的视野转换到“成素分析”的视野,让中西哲学的沟通开出双向的通路。前文提及新儒家熊十力到唐君毅和牟宗三的“融通”尝试,他们的方法就是从哲学系统的特色入手,尝试“融通”两种哲学的特色。故此三位新儒家学者的视角依然是中西两大哲学系统的整合问题,尝试把西方哲学的“思辨”作为中国哲学“实践”的资源。这个进路虽然回应了两个传统之间的冲突问题,可是并没有建立两个传统之间的双向互动进路。在三位新儒家学者的框架下,西方哲学的“思辨”为中国哲学的“实践”提供了资源,是一个从西方哲学成就中国哲学,即从“知”贯通“行”的单向通路。劳思光的“成素分析”理论则认为不同哲学传统之间的沟通是双向的,哲学的理论价值和“开放性”不再落在系统上,而是落在系统内部的各个成素上。只要该哲学传统的理论具有“开放成素”就可以成为对方的学习资源,从而建构“更高层级”的哲学成果,因此中西哲学的沟通在“成素分析”的理论下是双向的。
劳思光的“开放哲学”概念和“成素分析”方法,不但促进了中西哲学的沟通,对于中国哲学未来的发展也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开放哲学”概念以新的后设哲学语言回应“中国哲学”的合法性问题,给予中国哲学明确的定位,作为发展的基础。中国哲学不再是“蜕变”自西方的学问,或者是“西方哲学”在中国的“附庸”,而是具有自身理论特色以及合法性,能够与其他哲学传统分庭抗礼的学问。中国哲学得到明确的定位以及与其他的哲学传统平等沟通的地位,作为其发展的基础。同时,“成素分析”的沟通方法打开了中国哲学未来发展的新路径。中国哲学不只是从内部发展出新理论,也可以通过吸收和整合其他哲学传统的“开放成素”发展出新的理论,从而具有更多发展空间。由此,劳思光理论中的中国哲学,将会渐渐融入并非源自中国文化的新资源;中国哲学的未来不再是单独发展,也不是与其他哲学传统对抗而发展,而是同时与其他哲学传统一起通过成素分析方法,互相吸收对方的有效成素,共同发展。
劳思光的沟通方法以每个哲学传统都具有“开放成素”以及人类具有共同思考的问题(即哲学的“普遍问题”)作为前提,从而建构其“成素分析”的沟通理论。在中西文化沟通的立场上,劳思光所提出的理论开出双向沟通的进路,令中西两个哲学传统具有更大的沟通空间。但是这是基于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是“开放成素”较多,是“开放性”较强的文化。面对外来文化,中国文化和哲学均比较愿意接受改变。当封闭性较强的文化面对异质文化时,“成素分析”的理论则只会推导出该文化对于“较高层级”的文化的建立所提供的资源较少,但是并不保证该“封闭性”较强的文化会“欣然接受”新的高层级文化。部分文化的“封闭成素”对于“共同问题”的理论效力比较低,可是对于该地区的问题依然具有效力。如何让该文化放弃本身的成素而接受新的成素依然是未知之数。看见有效的成素而接受是“理”的问题,而部分文化领域并不单纯是“理”的层面,比如宗教及其衍生的价值观具有“信”的层面。同时部分宗教要求教义的完整性以及实践的严格程度。这些封闭性较强的文化与其他文化,尤其是现代文化的冲突问题,是不是能够以较为“温和”的“成素分析”方法解决则成为疑问。
七、结语
回顾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的沟通发展,可以看见劳思光的沟通方式开拓了中西哲学更大的沟通空间。同时这个沟通是双向的,不再是中国哲学从西方哲学获取资源,而是互相学习为新的哲学建构作贡献。此外,劳思光的“成素分析”沟通理论建构在“开放哲学”的概念之下,突破以哲学内容理解哲学概念的限制,令中西哲学能够平等地安顿在世界哲学的框架之中。西方哲学不再垄断地代表哲学学科,同时中国哲学不需要刻意“改造”以建立中国哲学的学科合法性。中西哲学之间的交流并不是地位与话语权的争夺与角力,而是平等的沟通发展。即使劳思光的理论在不同文化的沟通方面有其局限性,可是在“开放哲学”和“成素分析”的方法论下,中西哲学之间的交流进入了新的视域。中国哲学的发展不再是中国哲学应付西方哲学的冲击而产生的,也不是为了中国哲学在哲学领域中找寻生存空间和争取其地位,而是突破“中西”的地区文化交流视域,以“世界哲学”的角度,与中西之外其他哲学传统一起,对于世界哲学中具有普遍性的问题尤其是现代文化的文化危机,建构理论效力更具普遍性的“较高层级”的哲学。故此中国哲学不是在西方哲学冲击下的中国哲学,也不是与西方互相媲美较量的中国哲学,而是“在世界中的中国哲学”。
[1] 张岱年. 中国哲学大纲[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5: 22−23.
[2] 劳思光. 虚境与希望——论当代哲学与文化[M]. 香港: 中文大学出版社, 2003: 190.
[3] 劳思光. 危机世界与新希望世纪——再论当代哲学与文化[M]. 香港: 中文大学出版社, 2007: 80−81.
[4] 劳思光. 思光华梵讲词: 劳思光论哲学的基本问题[M]. 新北市: 华梵大学劳思光研究中心, 2016: 12−13.
Transcending the “Chinese and Western” horizon: The methodology of communication between Chinese and Western philosophies by Lao Sze Kwang
FUNG Chunho
(Department of Philosophy, 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1, China)
From comparison of concepts to integration of Chinese and Western philosophy by Neo-Confucianism, the communication between Chinese and Western philosophies is a crucial issue in Chinese philosophy. Lao Sze Kwang introduced the “open concept of philosophy” as a new understanding of philosophy and equally placed the Chinese and Western philosophies in it. He also raised the “element analysis” as the methodology of communication between Chinese and Western philosophies. By analyzing the theory of “element analysis,” we may realize the changes of the communication between Chinese and Western philosophies and also find valuable resources on the futur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Philosophy.
Lao Sze Kwang; communication between philosophies; meta-philosophical language; open concept of philosophy; element analysis
[编辑: 胡兴华]
2017−10−18;
2017−12−20
冯骏豪(1988—),男,香港人,北京大学哲学系2014级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中国哲学史,先秦儒学,现当代中国哲学,文化哲学
10.11817/j.issn. 1672-3104. 2018.01.004
B261
A
1672-3104(2018)01−00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