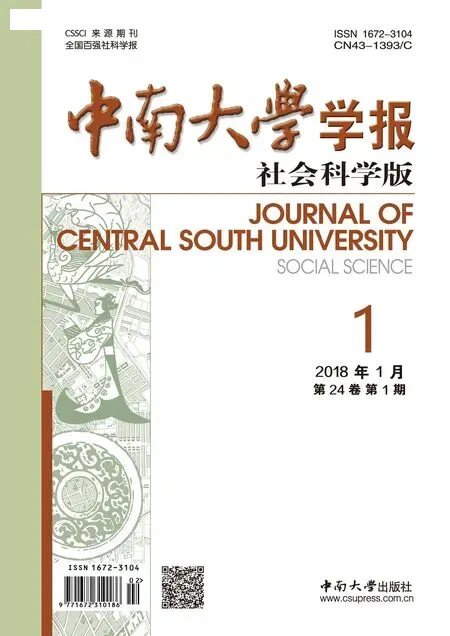行政保留的法治逻辑及其规范构成
刘春
行政保留的法治逻辑及其规范构成
刘春
(东南大学法学院,江苏南京,211189)
行政保留是学界涉猎较少的领域,急需理论上的填充。就法治逻辑而言,行政保留建立在行政权正当性证立的逻辑基础之上,并以与面临“合法性危机”的规范主义相对立的功能主义为其逻辑范式,以公众参与作为逻辑补充。就规范构成而言,社会科学领域的结构功能主义理论可以为其提供很好的诠释,而“功能最适”原则为行政保留范围提供了界定标准。
行政保留;正当性;规范主义;功能主义;结构功能主义
行政保留,对于我们来说,是一个既熟悉又陌生的词汇。说熟悉,是因为极其相似的“法律保留”,说陌生,是因为我们并不像对法律保留一样,了解它的具体内容。翻阅国内外研究著述,不难发现学者们对于行政保留的学术热情与法律保留有着巨大反差,与法律保留相比,行政保留的理论研究成熟度明显不足,研究成果凤毛麟角。而随着社会的发展,很多公权力现象溢出了传统的公法理论框架,建立在传统公法框架之上的法律保留理论,已经无法对此提供足够的解释力,相反,行政保留在这方面却展现出理论上的光芒[1]。总之,现实对行政保留的解释需求和行政保留理论研究的匮乏,已经产生了结构性的矛盾,对此,有学者已经意识到了这一点,并开始对行政保留给予关注①。然而,行政保留存立的基础是什么?在法治框架中,行政保留又处于什么样的位置?它的法治逻辑是什么?又包括哪些具体情况?这些行政保留的基础问题需要我们逐一展开讨论。
一、行政保留的逻辑基础:行政权正当性的证立
通说认为,行政保留是指宪法所保障的特定范围的国家和社会事务由行政机关自主决定,换言之,指行政不受其他国家机构过度干涉的自主空间[2]。它是对行政权在国家权力结构中所处位置的一种“辩护”。这样的关系决定了对它的讨论必须从国家权力的结构,也就是一国的政体结构入手,如此才能有的放矢。
(一) 政体结构与行政权正当性的传导机制
政体,即政权组织形式,尤其是中央(全国)政权的组织形式,主要涉及中央政权机关的设置、权力配置和相互关系等,其决定了国家机关设置和权力配置的基本原则,体现一个国家的横向权力结构和权力分配关系[3]。人们普遍会将政体与国体做联系讨论。一般来说,国体解决的是政权的归属问题,而政体则是指政权的运行模式。国体决定政体,政体是对国体的一种表达。
自近代以降,关于政权的归属问题,世界范围内已经形成人民主权的思想共识,我国也顺应这股“潮流”,在宪法中就政权的归属明确了我国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即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在人民主权这一共识之下,各国设计出了不尽相同的政体,以充分地表达和实现“民主”。然而,虽然说国体决定政体,但政体也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同样的国体可以有不同的政体形式,好的政体形式可以更充分地体现国体的性质,反之,则会妨碍国体性质的实现,出现以“政”伤“国”的情况[4]。为更好地实现政体对“人民主权”的表达,防止政体偏离国体,出现以“政”伤“国”的情形,“民主”作为一种控制机制被重视起来。这样的控制机制,在政体的具体权力结构中,表现为不同权力必须具有民主正当性②,以此将政体控制在“人民主权”的国体框架之内,否则权力便会面临政治合法性的质疑③。
就政体的“民主”控制而言,代议制是基本的制度起点,议会制度则是最典型的“民主”表达形式。然而,在具体的政体设计中,单纯的议会制是不存在的,世界各国是用政党制度、议会制度、选举制度、分权制衡结合在一起通过互补制衡的方式,来对民主进行复合表达,而不只是用议会制度一端来对“人民统治”进行单一表达[5]。就世界范围来看,这样的复合表达,主要存在三种典型的政体结构,即英国的代议制君主立宪制政体、美国的总统共和制政体以及法国的半总统半议会制政体。三种不同的政体,所体现出的行政权的民主正当性传导机制也存在极大差异。
英国的议会制君主立宪制政体强调议会至上,议会的立法权处于国家权力的中心,高于行政权,而司法审查中的越权无效原则,即通过宣布行政行为因超越了议会立法的授权而无效,进一步确保行政权被控制于立法权之下,“无法律即无行政”由此形成。而在选举方面,代表政府的英国首相及其内阁,并不由民众直接选举产生,而是由在议会选举中获胜的多数党领袖担任并组阁。因此,行政权的正当性,来源于议会的立法权,作为行政权最高代表的首相与内阁的正当性也来源于议会。
美国属于总统共和制政体,不论在理论还是实践上,美国的三权分立禁止立法和执法机构在人员上有任何重叠。国会和总统都由各自的选民直选产生;执法机构受单元首脑——总统——全权领导,且总统具有独立的全国性选民基础[6]。因此,行政权与行政权的最高代表总统的正当性直接来源于民众,而非议会。
与英国的内阁责任制和美国的单一总统制不同,法国在执法机构上实行的是双元执法首脑制,总统制和内阁责任制同时存在于法国,总统负责外交事宜,内阁则主管内政的日常运作。法国《第五共和国宪法》第6条规定,“共和国总统由直接的、普遍的选举产生,任期五年”,第7条规定,“共和国总统以有效投票的绝对多数票当选”。可见,与美国的联邦总统一样,法国总统亦和全国选民直接对话,因而具备独立的民主权力基础[6],其正当性直接来源于民众。总理则由议会下院(国民议会)中多数党领袖担任,并经总统任命,对议会负责。而内阁,由总理提名部长人选,由总统批准,并经议会同意组建。可见,在法国,行政权由于分属于总统和总理及其内阁,其正当性的来源也出现民众和议会的区分,属于双重民主正当性的传输机制。
(二) 正当性传导区分的引致:法律保留与行政保留的侧重
从以上的论述可知,行政权正当性的获取主要存在两种渠道:一种是从立法之处获取,行政权并不存在自身的正当性基础;另一种则是直接从民众处获取,从而保证行政权拥有自身的正当性基础。这两种不同的行政权正当性的证成模式,引致了作为公法基础原则的法律保留和本文讨论的行政保留的区分与侧重,并分别与二者存在直接的对应关系。
法律保留由德国行政法鼻祖奥拓·迈耶创立,它是指某些事项只能由法律规定,行政权非经法律授权不得行使[7]。国家机关之组织以及特定领域的行政行为,尤其是干预人民自由权利之行为,其行使所依据之法规范,应保留给立法者以法律规定,不得由行政机关以行政命令订之[8]。就本质而言,法律保留以民主为其理论根基,根本目的在于划定行政与立法关系中“行政不得侵入”的立法权的固有领域。而在运行机制上,其是以“行政合法性”作为实现的渠道,力求确保行政权的行使被严格控制在立法的范围之内,否则即为“行政违法”。从民主正当性的角度看,法律保留其实就是确保行政权的正当性通过立法机关以立法这一“传送带”将民意传送至行政机关,以补正行政权正当性的阙如。法律保留之所以强调对行政权正当性的补正,其原因在于行政权无法从自身获取正当性,必须由立法权传送,从而确保立法对行政的绝对控制。
相反,行政保留是指行政不受其他国家机构过度干涉的自主空间,包括立法机关的干涉。那么,在这种情况下,行政保留实际上是切断或者至少是压缩了行政权从立法机关获取正当性的渠道,它是为了防止行政权因受立法权的过度掣肘而变得僵化、被动。如此,行政权的正当性又从何获取呢?司法机关是走不通的,因为司法机关本身并不是民意机关,无法作为正当性的来源,相反,和行政机关一样,它是正当性的需求者。因此,行政权正当性来源的唯一选择也只能是从自身求取。
至此我们可以得出,法律保留所追求的立法对行政的控制以及行政保留所追求的行政对其他国家机关过度干涉的拒斥,在正当性的基础上,和行政权从立法机关获取正当性以及从自身获取正当性的两种渠道是分别对应的。从另一角度言之,就是在行政权只能从立法机关获取正当性的政体结构下,法律保留是调整立法权和行政权的核心原则,而在行政权自身具有正当性时,行政保留则成为调整立法权和行政权关系的关键。这也是为什么总统共和制政体的美国以及半总统半议会制政体的法国特别强调行政保留,而在只有立法机关由选举产生、行政不具有直接民主正当性的议会制国家,则往往侧重法律保留的主要原因。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议会制政体的国家就绝对不存在行政保留。随着行政国家的到来,建基于传统立法国家之上的行政权正当性的证立模式也在悄然地发生着变化。这种变化源于行政权的运作模式的改变,行政保留法治逻辑的范式随之也经历了变迁。
二、行政保留法治逻辑的范式转换:从规范主义走向功能主义
在西方公法研究领域,存在着两种主流的公法思想,即规范主义和功能主义。通过借鉴这两种公法思想,可以为我们分析行政保留提供很好的逻辑视角。
(一) 规范主义范式的“合法性危机”
规范主义属于西方传统的主流公法思想,它是以形式主义和自由主义为哲学基础,以法律为准绳,以个人权利为外部界限,以司法审查为实现手段的一种行政权的治理风格[9],其根源于对分权理想以及使政府服从法律的必要性的信念。这种风格强调法律的裁判和控制功能,并因此而关注法律的规则取向和概念化属性[10]。“禁止授予立法权”与“越权无效”是规范主义在法治中最主要的实现手段。
在规范主义背景之下,我们经常可以发现对干预最少国家的偏爱。行政法的主要功能也在于控制一切逾越国家权力的行为,使其受到法律尤其是司法的控制,行政法也当然地成为控制行政权的法,英国学者称这种行政法理念为“红灯理论”[11]。而从行政机关的角度而言,规范主义强调行政行为的正当性来源于作为民意机关的国会所制定的法律,行政行为的作出,必须有法律的授权,否则即为违法。此时,行政法就像一条以司法审查为齿轮的“传送带”,把民选立法机关的指令传送到各个当事人,行使管制权力的行政机关通过遵从行政法所传达的民意而获得合法性[12]。行政机关则属于纯粹的传送者,将作为民意的法律适用到具体的个案之中[13],此时的行政机关只是作为执行者这个“中间人”而已。行政权的正当性来源问题也转化为了形式法治的“依法律行政”的合法性(合规则性)问题。这是一种传统的行政权正当性的范式。
可见,从本质来看,规范主义侧重的是形式法治和消极行政,行政机关只是“守夜人”的角色而已。然而,事实并非如理论那般纯粹。规范主义所体现的那种立法对行政的绝对统摄,并不符合法治发展的一般规律,甚至面临着严峻的“合法性危机”:其一,严格的规范主义是不存在的,即使是古典自由主义的代表洛克,在明确立法至上原则并认为行政权是一项附属性权力的同时,仍然强调,在法律无规定、法律不宜规定、法律规定不当以及紧急状态下,行政主体享有自由裁量权[14]。在这样的行政权的自主空间里,立法无法给予行政以规范依据,其正当性的传导机制与行政的自我空间发生了龃龉,若按严格的规范主义进路,此时的行政权已然存在严重的“合法性危机”。其二,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国家事务不断攀升,自由法治国已向社会法治国转变,需要行政权更加主动地面对挑战,积极作为。此时,如若一味地强调立法权为行政权提供规范依据,传导正当性依据,行政权必然无法应对如此错综复杂的社会现实,此时的行政权也将面临着规范主义所圈划的“合法性危机”。因为,立法机关无法满足行政事务爆炸式增长所引致的“法规饥饿”状态的行政机关的立法需求,如果立法者努力想借着立法国之制度以取代行政国家之必要性,则会产生两种后果:导致“法律的肥大症”以及“遁入概括条款”[15]。而如果一味放任这样的境况持续下去,必然造成行政对立法机关产生信任危机,甚至会产生立法权对行政权的过度僭越,破坏独立的行政权,法治国家的理念基石也将随之崩塌。
综上,传统行政法模式面临着明显的合法化能力的匮乏, 并随之引发了行政过程的“民主赤字”和合法性危机[16]。在这样的规范主义的逻辑范式之下,行政保留的存在也是难以想象的。因为此时的行政权只是消极地、工具性地传达民选立法机关的立法指令而已,在没有立法机关的授权之下,行政权便不存在正当性基础,无所作为,更遑论行政权有着自己的形成空间。因此,行政保留所表达的行政权的自主性,规范主义无法满足,其面临的“合法性危机”也昭示着我们,行政保留的逻辑范式必须转向。
(二) 功能主义的范式转向及其正当性补足
公法中的功能主义范式,发端于文艺复兴时期,于20世纪初被系统阐释,并在二战后成为一股强劲的公法学思潮[17],与规范主义一并驱动着公法理论的发展。英国学者形象地称之为“绿灯理论”。
虽然功能主义与规范主义共生,但二者却有着截然不同的风格。相较于规范主义强调立法至上、追求形式法治不同,功能主义关注的是实质法治,更加注重对行政权本身的关怀。更为不同的是,功能主义侧重从行政权内部来观察行政权,而不是如规范主义那般,站在行政权之外“侦查”行政权。
从理念的本原和历史出发,规范主义的形成主要基于对行政权的极度不信任,重在以严密的立法为行政权划设边界,从而防范行政权对公民权利的侵害。因此,在本质上,规范主义对公民权利的保障属于一种消极的态度,旨在通过确保行政权保持“守夜人”的角色,实现公民权利的自由空间。相反,作为“绿灯理论”的功能主义,对政府职能的态度则是积极的。它寄希望于政府职能的有效发挥,政府能够提供越多越好的公共服务,行政合法性就得到越好的实现[12]。它不在于关注立法为行政权划设的不得侵犯公民权利的界限,而在于如何更好地实现公民的权利,追求的是实质正义。它不是把法律当作一种与政制完全不同的东西,而是将其视为一种作为政制机器的一部分的工具。这部政制机器乃是用来实现一套特定目的的。这些目的是与能动型国家的目标紧密相关的,它们凝聚在这样一种观念之中:政府是一种促进进步的进化式变迁的机构[10]。
正是功能主义所具有的从行政权内部出发,主张政府积极行政、注重行政权效能的品格,为行政保留的存立提供了思想和理念上的磐石。在功能主义的视角下,行政保留不再是立法权从外部控制行政权下的异数,而是行政权自身功能的一种展现。行政权的能动性、积极追求民意的完美实现,在功能主义下得到肯认与发挥,行政权的控制也不需要再单纯依赖民选立法机关通过法律的外部实现,而是由行政权发挥能动性,进行自我约束。
与此相伴的是,行政权的正当性证成模式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即由立法处获取正当性转变为从自身获取正当性,行政的民主化浪潮、公众参与制度的迅速崛起正是对此的积极响应。
在行政过程之中纳入公众参与,本质上是行政过程政治化的体现。作为一套制度系统的公众参与,不论是在国家宏观的政治生活中,还是在微观的行政过程中,都被理解为健全国家民主制度、提升公共生活民主性和公共性的重要途径[18]。行政保留法治逻辑的功能主义转向,在隔绝传统规范主义逻辑范式的同时,也与传统行政权单纯向立法权获取正当性渠道表示决裂,而公众参与则很好地弥补了功能主义范式下行政权的正当性来源问题,恰如其分。据此,戴雪所形容的“专制国家”的外衣,也由于公众参与对行政权的正当性补足,不至于“披”在行政保留的躯体之上了④。相应地,如何真正、有效地实现公众参与行政过程,则成为我们下一步需要关注的重点。
三、行政保留的规范构成:划分标准与内容因应
既然功能主义的逻辑范式能够很好地解释行政保留,那么,以功能主义的逻辑范式来观察行政保留的规范构成也理所应当。同时,行政保留毕竟是行政权一定程度的自主空间,而这种空间是立基于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这一政权结构之中的,对行政保留的规范构成分析自然也不能脱离这样的政体结构,妄自空谈。因此,对于行政保留的讨论,必须将二者加以综合考量。而这样的考量,与社会学上的结构功能主义理论极为贴切,我们不妨借此视角展开讨论。
(一) 划分标准的结构功能主义视角
结构功能主义(structure—functionalism)是社会科学研究的重要理论流派。它发端于孔德和斯宾塞,经由美国著名社会学家帕森斯细致建构,默顿进一步批判发展,而逐渐成为社会领域极具影响力的思潮,其实质是将结构主义视角和功能主义视角相结合来观察社会。
综上可知,对于《金瓶梅》中的影子人物,很多学者已经有了一定认识,但还未有人进行系统的研究整理,因此,本文主要以西门府内的影子人物为研究对象,以文本细读为研究方法,结合前人的成果,探究影子关系在文本中的呈现形式。
结构功能主义认为,社会是具有一定结构或组织化形式的系统;构成社会的各个组成部分,以其有序的方式相互关联,并对社会整体发挥相应的功能;社会整体以平衡的状态存在着,其组成部分虽然会发生变化,但经过自我调节整合,仍会趋于新的平衡[19]。当然,这样的结构化的运作模式并不总是具有助于系统调试的后果,很可能会出现削弱系统调试的后果,即负功能,或者无助于系统调试、系统参与方不期望也不认可的客观后果,即潜功能[20]。而且整个结构也会呈现出“结构制约性”特质,社会结构的既成状态,即各个要素之间的关系,产生了一种结构制约性力量,它规定着一个社会的结构变异即功能替代的可能范围[21]。
相同的路径,我们可以把国家权力作为一个系统,政体即为国家权力的结构或组织化的形式,而通过权力分立形成的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则属于这个系统的三个要素。在以往的意识里,对于立法权、行政权与司法权之间的关系,我们更关注于相互制衡,尤其是立法权对行政权的控制。这和权力分立理论所欲追求的权力制约权力以保护权利的目的是契合的,也是人类历经行政权肆无忌惮侵犯人权的历史教训后所采取的审慎态度。然而,权力制衡并不是权力分立的全部目的所在,现代国家实行分权的另一个目的是确保国家决定尽可能由其机构和程序合适的国家机关作出(效能保障原则)[22]。正如结构功能主义所揭示的一般,作为国家权力组成部分的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应当在政体这一结构之下,各自发挥其功能,以其有序的方式相互关联,并对社会整体发挥相应的促进作用,即国家决定的尽可能正确。毕竟国家权力本质上是一个整体,不能撕裂对待,破坏作为系统的国家权力的完满性。
而如果出现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三个要素之间功能的相互倾轧、替代,则整个政体结构的运作模式也将无助于作为系统的国家权力的调试,会出现削弱国家权力系统的负功能、潜功能。因此,政体结构的安排必须呈现出“结构制约性”特质,使得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之间产生一种结构制约性力量,规定着政体结构变异即立法权、行政权与司法权之间功能替代的可能范围,从而避免权力之间的相互侵犯、相互扯皮、相互替代。行政保留就是这样一种保证机制:一方面确保行政权与立法权、司法权之间以有序的方式相互关联,对社会整体发挥相应的功能;另一方面促成行政权对立法权和司法权形成“结构制约性”特质,确保权力之间的相互尊重,防止出现功能替代。
(二) 功能最适下行政保留的构成
如上文所言,结构功能主义是将结构主义和功能主义相结合的一种理论视角。结构决定的是系统中各要素的位置和角色定位,而功能主义则关注各要素在各自的位置上所发挥的功能。在结构功能主义的视角下,立法机关、行政机关以及司法机关在国家政体结构中有着不同的位置,担任着不同的角色,承载着不同的功能,它们相互尊重,相互制约,共同促成国家权力的整体运行。
在这样的政体结构之中,确定一项事务的管辖主体就必须将事务的特性与各权力要素的结构和功能相对接考虑,由身处特定位置、最利于功能发挥的角色来承担,这就是所谓的“功能最适”原则。
其实,近十余年来在德国宪法学界颇为流行并且在理论与实务层面也受到相当程度重视的所谓“功能法”论述取向,就是“功能最适”原则在宪法上的体现,是德国法为了理清当代权限分际难题之背景下的重要产物[23]。行政保留的功能主义范式,正是建立于这样的功能性权限划分的基础之上的。也就是说,从结构功能主义观之,行政保留所意指的宪法所保障的特定范围的国家和社会事务由行政机关自主决定的内涵,是从事务最适合行政机关来完成的角度加以考虑的,即尽可能由最合适的国家机构作出,这也是承认行政保留或者行政自负其责的理由所在[22]。从这个角度考量,行政保留的范围就可以“功能最适”原则作为界定标准,行政保留所指涉的便是那些最适合由行政机关来承担的事务。对于这些事务,如果由立法机关、司法机关承担,则会出现事务的特质与机构的功能承载互相杯葛的局面,从而不利于事务的完成。
然而,行政保留毕竟属于涉及一国政体结构、关系权力之间制度安排的宪政层面的问题,对此,我们必须回到具体的宪法规范上加以讨论。但这并不影响我们利用“功能最适”的标准去审视一国的宪法设计,因为,它们都透露着“功能最适”标准的色彩。
1. 职权立法
2.不确定法律概念
不确定法律概念是指意思不确定、具有多义性的法律概念,对此,行政机关具有一定的判断余地,司法机关不得干涉[27]。不确定法律概念本质上是从要件方面给予行政权以一定的自主活动空间。因为现实是复杂的,立法机关面对未来,在专业、技术等方面不及行政机关,赋予行政机关以不确定法律概念的判断余地是行政权功能性的体现。在这个空间里,行政权可以积极发挥自身的专业优势,最大限度地推动个案正义和实质正义的实现。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对于不确定法律概念的行政保留属性的界定,并不是由宪法及相关法律来完成的,而是由司法机关在司法实践中不断摸索而总结出来的,体现的是司法权对行政权的尊重。
3.行政组织权
行政组织权是事关行政机关、机构的设置,人员的配备以及职能分配、调整的权力。在这方面,行政机关相对来说应当有着一定独立的自主决定权,因为只有行政机关对自己内部的组织架构最为熟知,也最能把握事务的属性与机构设置的融合对接。比如,我国《国务院组织法》第11条规定:“国务院可以根据工作需要和精简的原则,设立若干直属机构主管各项专门业务,设立若干办事机构协助总理办理专门事项。每个机构设负责人二至五人。”《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第64条规定:“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人民政府的厅、局、委员会等工作部门的设立、增加、减少或者合并,由本级人民政府报请国务院批准,并报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备案。自治州、县、自治县、市、市辖区的人民政府的局、科等工作部门的设立、增加、减少或者合并,由本级人民政府报请上一级人民政府批准,并报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备案。”第68条规定,“省、自治区的人民政府在必要的时候,经国务院批准,可以设立若干派出机关。县、自治县的人民政府在必要的时候,经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人民政府批准,可以设立若干区公所,作为它的派出机关。市辖区、不设区的市的人民政府,经上一级人民政府批准,可以设立若干街道办事处,作为它的派出机关”。这些机构、工作部门的设立,虽然需要得到上级政府的批准,但却属于行政内部的控制与监督,立法机关只是备案机关,并无规范之实。这无疑属于行政保留的范畴。而在美国,虽然宪法并没有明确有关行政组织权的保留问题,但司法判例却向我们展现了“人事权”作为行政保留的影子,其与“法律执行权”作为美国宪法上行政权的核心,绝不容立法侵犯[28]。
4.特别权力关系
特别权力关系理论发端于19世纪的德国,后被日本、我国台湾地区所继受。它是指在公法上为实现特定目的所必要的限度内,一方总括地支配他方,他方必须服从的关系[29]。它是君主立宪制下所特有的政治、社会的产物,是为了说明19世纪后期德国君主立宪制的管理关系而提出的。在特别权力关系中,行政机关可以根据自己的权力发布为调整特别行政关系所必需的规则;可以在没有法律授权的情况下,实施侵害行为[7]。也就是说,特别权力关系完全排斥法律保留和司法审查,属于行政权实实在在的行政保留领域。随着人权和法治的发展,特别权力关系理论得到了极大修正,法治的触角伸入了特别权力关系的内部,特别权力关系中相对人的权利也逐渐得到保障。然而,这并不意味着特别权力关系就完全不合理。从功能主义的视角来看,在对公务员、服刑人员、军人以及教师等的特殊管理领域,有着特殊化的要求,他们与普通公民的身份也不一样,如果立法机关处处干预,必然影响这些领域的管理效率,不利于制度设计本身的功能追求。因此,必须给予行政权以一定的自主空间。这在《公务员法》《监狱法》《行政监察法》《教育法》对公务员、教师等特殊人员的管理规定上表现得特别明显。
当然,行政保留的情形远非以上4种,行政终局裁决、国防、宣战等对外的政治行为也可以纳入行政保留的范围之内,这些都体现了行政权的“独立性”。限于篇幅,本文不再讨论。
注释:
① 在中国知网上,以“行政保留”作为关键词进行搜索,可以发现国内学者中,只有门中敬教授对行政保留做了细致研究。
② “正当性”,是英文“legitimacy”的中文译义,也称“合法性”。目前国内学界对于这两个词在一定程度上是混用的,并没有明确的界分,本文也将二者混合使用,如有特别之处,文中会做说明。
③ 在政体结构中,一般存在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的区分。立法权是人民意志的表达渠道,本身就是民主正当性的形式,一般不存在民主正当性的质疑。相反,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由于并不属于民意机关,最容易存在民主正当性的疑虑,民主正当性最集中的讨论也在于行政权和司法权。比如,司法权的正当性论证就属于美国宪法学界热门的话题之一。
④ 虽然戴雪没有明确提及“行政保留”,但从其专著《英宪精义》对法治的定义中可知,他是明确主张法律至上主义,贬抑行政权的扩张,甚至反对行政裁量权的存在的,因此,“行政保留”所意指的行政权的自主空间自然也不会得到戴雪的承认。
[1] 门中敬. 论宪法与行政法意义上的法律保留之区分——以我国行政保留理论的构建为取向[J]. 法学杂志, 2015(12): 24−33.
[2] 门中敬. 规范行政保留的宪法依据[J]. 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 2017(1): 91−104.
[3] 王惠岩. 政治学原理[M].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5.
[4] 李铁映. 国体和政体问题[J]. 政治学研究, 2004(2): 1−6.
[5] 胡筱秀. 国体与政体之间的关系研究——兼论人民政协制度的定位[J]. 政治与法律, 2010(9): 75−86.
[6] 张千帆. 西方宪政体系(下册·欧洲宪法)[M]. 北京: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5.
[7] 哈特穆特·毛雷尔. 行政法学总论[M]. 高家伟, 译. 北京: 法律出版社, 2000.
[8] 李震山. 行政法导论[M]. 台北: 三民书局, 1999.
[9] 毛玮. 行政法红灯与绿灯模式之比较[J]. 法治论丛, 2009(4): 89−99.
[10] 马丁·洛克林. 公法与政治理论[M]. 郑戈,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2.
[11] 卡罗尔·哈洛, 理查德·罗林斯. 法律与行政[M]. 杨伟东, 等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4.
[12] 毛玮. 论行政合法性[M]. 北京: 法律出版社, 2009.
[13] 理查德·B·斯图尔特. 美国行政法的重构[M]. 沈岿,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2.
[14] 约翰·洛克. 政府论(下篇)[M]. 叶启芳, 瞿菊农,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64.
[15] 陈新民. 公法学札记[M]. 北京: 法律出版社, 2010.
[16] 王锡锌. 行政正当性需求的回归——中国新行政法概念的提出, 逻辑与制度框架[J]. 清华法学, 2009(2): 100−114.
[17] 程关松. 公法理论中的三种功能主义范式[J]. 江西社会科学, 2010(9): 193−198.
[18] 王锡锌. 公众参与: 参与式民主的理论想象及制度实践[J]. 政治与法律, 2008(6): 8−14.
[19] 刘润忠. 试析结构功能主义及其社会理论[J]. 天津社会科学, 2005(5): 52−56.
[20] 罗伯特·K·默顿. 社会理论和社会结构[M]. 唐少杰, 等译. 上海: 译林出版社, 2006.
[21] 文军. 西方社会学理论: 经典传统与当代转型[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6.
[22] 汉斯·J·沃尔夫, 奥托·巴霍夫, 罗尔夫·施托贝尔. 行政法(第一卷)[M]. 高家伟,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2.
[23] 黄舒芃. “功能最适”原则下司法违宪审查权与立法权的区分——德国功能法论述取向之问题与解套[J]. 政大法学评论, 2006(91): 99−144.
[24] 门中敬. 国务院在行政与立法关系中的职能定位——以行政保留为理论分析的视角[J]. 湖北社会科学, 2016(10): 154−161.
[25] 贾圣真. 总统立法——美国总统的“行政命令”初探[J]. 行政法学研究, 2016(6): 138.
[26] 王名扬. 法国行政法[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7.
[27] 周佑勇, 邓小兵. 行政裁量概念的比较观察[J]. 环球法律评论, 2006(4): 431−439.
[28] 廖元豪. 论我国宪法上之“行政保留”——以行政、立法两权关系为中心[J]. 东吴大学法律学报, 2000, 12(1): 1−45.
[29] 杨建顺. 日本行政法通论[M]. 北京: 中国法制出版社, 1998.
The legal logic of administrative reservation and its normative structure
LIU Chun
(School of Law, Southeast University, Nanjing 211189, China)
Administrative reservation is less studied in academia and is therefore in bad need of theoretical filling. In terms of legal logic, administrative reservation is based on the logical basis of the legitimacy of the executive power, and treats normativism as its logical paradigm with public participation as supplementation. In terms of normative structure, structural functionalism in the field of social science, can provide a good interpretation, and the “best function” principle provides a defined standard for the scope of administrative reservation.
administrative reservation; legitimacy; normativism; functionalism; structural functionalism
[编辑: 苏慧]
2017−05−08;
2017−06−26
2016年度江苏省法学会法学研究课题“政府补贴法律规制研究”(SFH2016C01)
刘春(1992—),男,安徽滁州人,东南大学法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行政法学
10.11817/j.issn. 1672-3104. 2018.01.009
D912.1
A
1672-3104(2018)01−0063−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