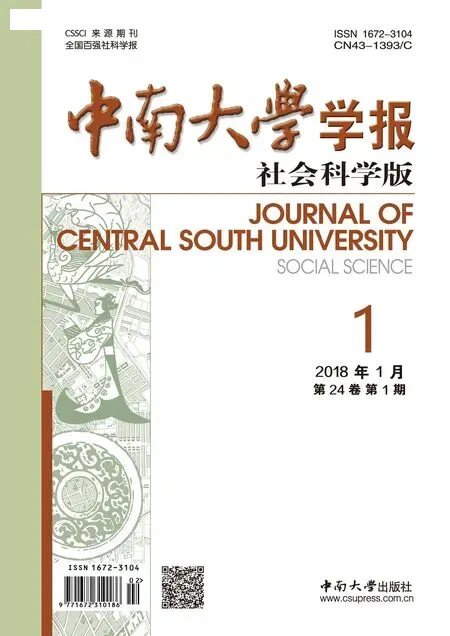新时代的中国伦理学使命
李建华
新时代的中国伦理学使命
李建华
(浙江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浙江金华,321004)
当我们进入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时候,需对新时代这一概念的内涵有科学的把握。新时代不仅仅是一个描述当代中国客观实际的概念,而且蕴含了深刻的伦理价值,体现为强国、利民、自信、担当、共享等。由于现代科技与社会变迁的特殊性,我们也应该看到新时代所面临的伦理挑战,如伦理主体日益被解构、伦理关系日益复杂化、伦理整合日益弱化、伦理预期日益模糊等。这就需要在新时代构建一种适应社会全面转型发展的伦理大思路,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伦理道德规范体系,提供中国伦理精神和中国伦理价值,构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气派、中国风格的伦理学。
新时代;伦理整合;伦理断裂;中国伦理精神;中国道德力量
伴随着中国共产党十九大的胜利召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事业进入了一个“新时代”。新时代不但预示着中国的社会发展面临新任务、新使命、新矛盾、新要求,同时也饱含了对未来中国的价值预期以及由此而产生的新姿态和新格局,这就是我们行将迈步的中国道路,而“道路问题,归根到底,就是伦理问题”[1](2)。中国伦理学不但要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时代提供可靠的伦理资源,而且要担当起面向新时代新要求的谋求自身新发展的历史使命。
一、新时代的伦理意蕴
“新时代”是中国共产党十九大召开后的一个高频词。如果要对2017年的流行语进行排名的话,“新时代”肯定排名第一。但是,生活的经验常常告诉我们,使用最多、习以为常的词,人们对其内涵与外延的把握反而不太讲究。要科学把握“新时代”的真实内涵,可以从四个维度去理解。
一是从时间性概念来理解。从时间性上讲,新时代是指时间的一维性上的某个点,或者说是在过去、现在和未来的延伸中的某个时段,具体就是承前启后、继往开来、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续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的时代。这就要求对新时代的把握不能做时间上的简单机械的切割,因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是一个过程,只是不同时期有不同任务罢了。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而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就是新时代的具体任务。从时间上来理解新时代,就应该注重其历史性、过程性和连续性,使其真正成为“历史方位”中的“方位历史”,从而避免新的历史虚无主义。
二是从描述性概念来理解。从描述性来讲,新时代就是中国共产党十九大报告本身所理解的“新矛盾、新思想、新使命、新征程、新要求”等,直接等同于“习近平时代”,具体就是“三个意味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意味着近代以来久经磨难的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迎来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意味着科学社会主义在21世纪的中国焕发出强大生机活力,在世界上高高举起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意味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文化不断发展,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了中国 智慧和中国方案。”[2](10)进而可以描述为“这个新时代,是承前启后、继往开来、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续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的时代,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而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时代,是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不断创造美好生活、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时代,是全体中华儿女勠力同心、奋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时代,是我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不断为人类作出更大贡献的时代”[2](10−11)。
三是从分析性概念来理解。从分析性来讲,新时代不是一种实体性概念。它不是指向某些具体,而是作为把握当代中国社会总特征的一个抽象概念,是一种对具体现象世界的理论抽象。在此意义讲,新时代并非是把过去、现在、未来分离成几个互不相干的独立存在,而是指中国社会发展整体性过程中的阶段性。作为理论抽象的新时代概念,是我们把握当代中国现实的基本范畴,也是分析中国社会发展和历史变迁新情况的工具。
四是从价值性概念来理解。新时代虽然描述的是当代中国社会的新变化,但真正体现的是一种理想追求、长远目标,是一种“应然”状态。新时代不是被建构的一个概念,而是对当代中国的发展姿态、历史方位、未来走向的提炼和概括,形成了一个“价值系统”,如民族复兴、美丽中国、以人民为中心、新发展理念、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合宪性审查、共享共赢、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等。正是因为新时代的价值指引,才具有如此大的吸引力和感召力。
如果继续遵循价值论的视角,我们就会发现新时代更多地饱含了伦理价值意蕴,构建了一种全新的社会伦理秩序,呈现了丰富多彩的伦理生活画卷,具体可以概括为:民族复兴时代的强国伦理、追求美好生活时代的民本伦理、全面自信时代的进取伦理、引领世界发展时代的责任伦理、共商共建共赢时代的共享伦理。
民族复兴是新时代的根本标志,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彰显强国伦理。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是我们的奋斗目标,“到那时,我国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将全面提升,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成为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领先的国家,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基本实现,我国人民将享有更加幸福安康的生活,中华民族将以更加昂扬的姿态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2](29)。可见,强国伦理是全面强大的伦理,而不仅仅是经济的强大,特别是要加强生态文明建设,避免重蹈西方以牺牲环境生态为代价的现代化之覆辙,同时在文化上也要强大起来,从而结束以西方价值观宰制世界的历史;强国伦理是现代化的伦理,坚持走民主法治之路,坚持走改革开放之路,坚持走自己的现代化道路,彰显中国道路的现代化之魅力;强国伦理是谋求人民利益的伦理,只有民富才能国强,只有人民幸福安康,国家才能长治久安;强国伦理还是世界正义伦理,我们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坚持共建共享原则,致力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强国伦理归根结底是一种“人类”伦理,终要打破国家、政党、社会、种族、地区等自我伦理局限,追求与创造人类生存与发展的“类伦理”。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2](11)这种社会主要矛盾的新变化是建立在“一切以人民为中心”这个永恒不变的中国共产党的执政伦理的基础上的,民本伦理是新时代伦理的核心。中国共产党代表了人民的根本利益,始终坚持以人民利益为中心,坚持人民利益高于一切。习近平同志反复强调“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从我们党诞生之日起,“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就成为党的宗旨,成为每位党员的行动指南。人民所向往的美好生活就是生活富足、身心健康、国安家宁,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全面概括了人民美好生活的基本内容。获得感意味着人民可以得到充足的社会资源,为自由全面发展创造良好的物质基础。同时,获得感还意味着获得社会认同,得到社会的尊重。幸福感意味着人民身心愉悦,不但能享有良好的生活状态,还对社会怀有积极的道德态度,情绪饱满。安全感则意味着人民应该生活在秩序井然的社会环境之中,面对社会风险时能够得到社会的有效支持。人民的利益是我们所有行动的出发点和评价的最高标准,也是最高的伦理标准。
如果从伦理道德的规范功能性质进行划分,可以分为协调性和进取性两类。新时代的到来意味着全面自信时代的到来,我们的伦理道德也真正由内敛式的协调性伦理道德转向发散式的进取性伦理道德,新时代蕴含进取性伦理。如果说,当代中国处于稳定与发展双重价值的选择与权衡之中,或者谋求二者的一致性,那么从价值照顾而言,协调性伦理道德有利于稳定,而进取性伦理道德有利于发展,我们是在发展中求稳定,所以进取性伦理道德的凸显理所当然。进取精神是人们在认识世界与改造世界的实践中表现出来的积极奋进的意识,是人的自觉能动性得以发挥的精神状态。无论对人类的整体,还是对单独的个人,这种精神都具有重要的意义。伴随着中国经济奇迹般地发展,中国进入了全面自信的时代,这种自信的伦理意义在于不仅仅是靠协调性道德来维系社会的平衡与稳定,而是要谋求更大程度上的发展与进步,成为世界伦理秩序的设计者和维护者。
“责任伦理作为一种新的道德思维,‘新’就新在它是一种他者思维,因而不同于传统伦理的以‘己’为本位的道德思维;它是一种复杂思维,因而不同于传统伦理的简单的道德思维;它是一种境遇思维,因而不同于传统伦理的律法主义思维。正是因为责任伦理学突破了传统道德思维的局限,才为解决当代人类社会所面临的道德难题提供了根本前提。”[3]在新时代,中国不仅对物质文化生活提出了更高要求,对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的要求也都在日益提高。中国人民不仅珍惜和平、稳定与安全,也将尽最大努力维护和保卫和平、稳定与安全。中国将是未来长期可依靠、可信赖、可预期的一支和平力量。中国将坚持改革开放的基本国策,以开放包容的态度与国际社会合作,谋求互利共赢。一个珍爱和平、开放包容、持续发展、精诚合作的中国将是世界的机遇,也是引领世界发展的主力,体现的是一种高度的责任伦理精神。
新时代是共商共建共赢时代,由此内生出共享伦理。2017年5月,习近平同志在“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圆桌峰会上的开幕辞中指出:“各方秉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携手应对世界经济面临的挑战,开创发展新机遇,谋求发展新动力,拓展发展新空间,实现优势互补、互利共赢,不断朝着人类命运共同体方向迈进。”[4]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当代中国为解决世界问题、引领世界发展所提出的中国方案,是中国智慧的体现,也是新时代的国际伦理之根本要求。共享的理想一直以来都流淌在人类文明的河流之中。在某种意义上,人类社会化的历史就是共享的历史。早在原始社会,人类就以共享的方式生活。由于个人力量的薄弱,单个的人难以应对自然环境的挑战,没有能力独自生活。为了和他人建立联系,共同为生存而组织在一起,开始诉诸分享生活资料的方式。广义的平均分配成为那一历史阶段最重要的共享模式。在新的社会历史条件下,社会生产和生活方式的新变化让共享成为必然选择。同时,在社会前进的脚步中也产生了与共享理念相违背的诸多现象,共享问题从而日益受到人们的普遍关注[5]。随着国际形势的深刻变化,建立国际机制、遵守国际规则、追求国际正义等正在成为多数国家的共识。顺应全球治理体制变革的新要求,中国倡导共商共建共赢的全球治理观。“共商”就是各国之间加强互信,共同协商解决国际政治纷争与经济矛盾;“共建”就是共同参与、协同合作,形成互利共赢的利益共同体;“共赢”就是在世界经济发展中实现互惠互赢而非互害互灭。在实践上我们树立“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新安全观,共同维护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支持建立开放、透明、包容、非歧视性的多边贸易体制和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以平等为基础、以开放为导向、以合作为动力、以共享为目标,完善全球经济治理等举措。“共商、共建、共赢”的全球共享治理理念,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注入了新动力,为构建国际伦理新秩序提供了新理念[6]。
二、新时代的伦理挑战
新时代是一种向往,也是一种追求,它不是空中楼阁,新时代与现时代之间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要实现新时代的目标,必须正视现时代的各种问题。从人们的伦理生活而言,真正的现代性伦理危机或者困境已然降临到我们头上。这绝不是危言耸听,我们必须保持清醒的头脑。新时代要有新目标,同时也伴随着新挑战和新机遇,我们只有正视挑战,才能有备无患,化不利为有利,构建好新时代新伦理秩序。新时代面临的主要伦理挑战有四个方面。
一是伦理主体日益被解构。当现实世界被虚拟世界完全摹写,海量的数据引爆了信息化的质变,人工智能成为信息革命的加速引擎,数据资源成为重构未来的基础与关键。2016年,以色列青年历史学家赫拉利出版了风靡全球的《未来简史:从智人到神人》,在对人类发展历程与科技创新进行一番考证与整理之后,认为“我是谁”这样的人文科学经典命题也会彻底瓦解。因为“所谓唯一真正的自我,其实和永恒的灵魂、圣诞老人和复活节兔子一样并不存在。如果我真的深深地去探究自我,就会发现自己一向认为理所当然的单一分解成各种互相冲突的声音,没有哪个是‘真正的自我’”[7]。并且,赫拉利提出了一个大胆的推测:基因工程、大数据与人工智能正在解构人类,人不再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拥有内心自由的个体,他与其他动物一样,只是生化算法的组合,这些算法是可以被认知的,外部算法有可能比个体更了解自己;文艺复兴以来盛行的个人主义即将崩溃,数据主义将主宰这个时代,服从数据比服从内心将让绝大多数人的决策更加完美有效;大数据会使人分解为一堆“他者”的数据,使自己无处躲藏,会从根本上肢解人的实体性存在,消解人的价值观,消解人的社会性。赫拉利认为,99%的人类特性及能力是多余的,但有些人仍然会不可或缺,形成一个人数极少的精英阶层,拥有前所未有的能力及创造力,为算法系统执行关键的服务;人类想要不被淘汰只有一条路,一辈子不断学习,不断打造全新的、无法被算法摹写的自己,否则,我们都会被沦为“无用阶级”,不再具有任何价值。
二是伦理关系日益复杂化。新时代科学技术的疯狂发展带来了复杂的伦理关系。有效调节伦理关系是伦理学的主要功能。但是,21世纪以来,以生物技术、人工智能、互联网为代表的现代“黑”科技,使人伦关系变得十分复杂并且难以把握,如基因技术不但可以改变人的容貌,还可改变人的心灵;人工智能带来的无人化趋势挑战人的存在价值等。伦理关系变得日益复杂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是从伦理主体性而言。由人与自然、个人与社会、个人与个人、个人与自我四种基本的伦理关系变化为自然人与机器人、机器人与机器人、单机人与组机人等多种伦理关系。这使现实的人伦世界及伦理实体发生了颠覆性的改变。赫拉利认为,“人”这个黑箱将被彻底破解,人类社会将面临全面重构,人与物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人与组织的关系以及建立在之上的人类文化规范将在新的技术条件下重新形成。一切似乎要推倒重来,这听起来让人感到不寒而栗:人工智能真的会取代人吗?未来社会的行为规则真的与现在完全不同吗?虽然赫拉利提到的很多改变还在进行之中,人工智能是否能演化出创造力尚且不知,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我们又面临着一个“数千年未曾有过的大变局”。信息化进入关键时期,它已经从局部走向整合,从旁支变成根基,从工具化变为核心。它不甘于只是帮我们改进服务、提升效率,它正在向人类、向组织、向行为规则发起挑战,它试图让一切都按照它的逻辑来行动,它代表着大多数人对美好与幸福的追求,也就拥有无穷的力量。其二是从人的存在状态而言。由于网络社会的来临,我们已经不是单一性存在,有现实世界的伦理关系、虚拟世界的伦理关系、现实世界与虚拟世界切换状态的伦理关系。现实世界是我们已经厌倦的世界,因为我们看到的都是趋名逐利,尔虞我诈,所以我们尽可能在现实世界中过虚假的生活。虚拟世界往往是我们理想的生活世界,这里没有真实身份,也便没有了规范压力,于是就可以自由交往和自由表现,就可以展现真实的自我。这很容易导致人自身的分裂、人格的扭曲,如在现实世界中讲假话,在虚拟世界中讲真话,在切换层面就真假共存或真假难辨。
三是伦理整合日益困难。中国社会进入了由单一的经济驱动发展型社会到全面发展型社会,社会的全面发展意味着速度慢、协同性强、整体性风险大。这对社会的伦理整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如果说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五大建设可以协调发展,是否也意味着,政治伦理、经济伦理、文化伦理、社会伦理、生态伦理也会自发地协调发展?事实上,在五位一体建设协调的同时,由于发展引擎不明确,全面使力而显无力,使五大伦理建设时常又是冲突的,甚至是相悖的。这就需要有种超越于五大伦理之上的伦理大思路。这种大伦理是什么?我们至今不得而知。伦理现代性的最大“成果”就是伦理在个体—社会—种属中的拆解和大断裂。法国大思想家埃德加·莫兰在他的《伦理》一书中认为,在专门化和区隔化的现时代,一切伦理之源的责任与互助精神被破碎和消解,我们这个时代的伦理危机也就是自我伦理、社会伦理、类伦理连接的危机。“它迫使我们必须再兴伦理:使责任——互助的源泉再生,这同时也意味着个体—种属—社会循环的再生,这种再生是在每个个体的各自再生中实现的。”[1](47)我们应该承认,对每一块(领域)的伦理要求和作用机制是清晰的,但是在各大伦理之间是常常不协调的,有时甚至是冲突的,所以当代伦理建设的主要任务是加强条块伦理之间的连接。其实,马基雅维利、霍布斯、尼布尔等思想家都提醒过我们,尤其是美国著名社会伦理学家尼布尔在他的《道德的人与不道德的社会》中就提出过个体道德与社会道德的冲突问题,对传统美德理论和基督教伦理学提出了批评,认为个体美德不能逻辑地导致道德社会的形成。相反,两者经常是矛盾的。因为“如果一种道德见识一开始就自鸣得意地假定自私冲动和社会冲动处于良好的平衡状态,并且认为两者同样是正当的,那么,实际上它们之间甚至连最低限度的平衡也不可能达到”[8]。黑格尔曾经用人的自由意志的辩证运动来解决抽象法、道德与伦理的连接问题。我国伦理学家樊和平教授曾提出当代伦理与道德的冲突问题,实际已经看到了条块型伦理建设的局限。伦理整合的困难已经是一个不容争辩的事实,就是我们倡导的职业道德、社会公德、家庭美德、个人品德之间是否是一致的关系,有无矛盾冲突之处,都需要我们认真研究。还比喻说,我们认为做事先学做人,所以伦理学有了某种优先性。其实学会了做人就能做好事吗?不一定,大多数落马的贪官,大都是能干之人,政绩显赫。这个社会到底是求成人,还是求成事,一定是成人优先于成事吗?是否存在一种与伦理学平行的事理学?这种事理学是否可以成为解决伦理整合问题的一种思路?所以通过伦理连接实现伦理整合成为新时代伦理建设的主题。因为,“一切伦理行为事实上都是一种连接行为,与他人连接,与自己亲朋连接,与共同体连接,与人类连接,最后是置身宇宙之中的连接”,“我们越是自主就越要担当不确定性和不安宁,也就越需要连接”[1](57)。
四是伦理预期日益模糊。传统伦理学的合法性前提都是有某种价值预期的,如为了至善、为了幸福、为了利他、为了社会和谐等。如果我们认定新时代社会的主要矛盾是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与发展不平衡不充分之间的矛盾,我们就会发现这对矛盾的两极都是源自于主体自身。过去的社会主要矛盾是落后的生产力与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之间的矛盾,是属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而现在的社会主要矛盾则是生产关系内部的矛盾,是人自身及其内在关系的矛盾。因为发展不平衡不充分还是人自身的问题,特别是发展不充分是人自身潜力、人的积极性的挖掘问题,就变成了人的需求与人的潜能之间的矛盾。在美好生活需要与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之间并不构成直接二元对立的矛盾,不同于落后的生产力水平与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之间的矛盾。因为发展本身只是手段,发展平衡了、充分了,能否带来美好生活,需要太多的中间环节,其中会呈现多种不确定性和复杂性,甚至会有社会伦理风险。从需要满足的过程来看,低层次需要容易满足,比较单一,对应满足的条件也单一,而高级需要的满足,大都属于精神与自我实现的领域,内容复杂,且对应满足的条件更复杂。同时从需要的内生规律看,低层次需要满足后可能催生高级需要,也可能催生低级需要,但高层次需要满足后,只会产生更高级的需要。“美好”是无止境的,美好生活也是无止境的,而任何形式的平衡充分的发展都是相对的、有限度的,所以,这对矛盾的存在也可能是无止境的[9]。由于人的欲望的无止境性、个体差异性和人的潜能的不可知性,决定了我们的伦理预期具有不可能性和不确定性。如什么样的生活才是美好生活,尽管有许多幸福指数的指标体系,但是对于伦理主体而言,只会是差异化的,目标是不清晰的。也许伦理的目标主要不再是调节个人利益与整体利益的关系,而是自我伦理关系,也就是欲望与能力的关系。这是伦理?还是道德?这些都需要我们作出精深的研究。正因为人性、人的欲望具有不确定性,所以未来的伦理预期都是难确定的。用莫兰的话讲,未来就是打赌。当然,他认为,善是我们最值得打赌的。如时下从江歌案的讨论到对电影《芳华》的不同评价,都表现出社会伦理标准的差异甚至模糊,甚至出现了“社会的堕落就是从善良教育开始”“拒绝善良泛滥”的论调,实在令人忧虑。
当然,有困惑,意味着有反思;有挑战,意味着有机遇;有危机,意味着有希望。中国伦理学,面对危机与变迁,要饱含责任伦理和“思想的伦理”,担当时代和社会的良知,去消解大众的焦虑,阐释好生命的意义和价值,以展示善的可能性。
三、新时代的伦理学使命
新时代的伦理要求与现时代所面临的种种伦理困境交织在一起,构成了当代中国伦理道德生活的多彩画面,同时也暗含了某种伦理的基础性危机。这就迫使中国伦理学要作出选择,展现姿态,承担使命。
第一,要有适应社会全面整体转型的复合型伦理大思路。当代中国正处在大改革、大发展、大提升的历史关键期,所谓“关键”的背后是社会的整体大转型。从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五位一体”建设,到“四个全面”的整体战略推进,再到“四个自信”的全面展开,标志着我们虽时有感触但未曾从理论层面高度关注的社会全面转型时代已经悄然来临。它迫使我们在经济社会发展和思想文化建设诸领域要全面创新理念和方法,形成适应社会全面整体转型的复合型伦理大思路,以此来适应由单一经济社会转型向社会全面转型所发生的深刻而往往鲜为人知的变化。这种复合型伦理大思路的特点就在于超越个体、超越单一性,进而在复杂中求明晰,在不确定中求选择,在选择中求再生,在再生中求蜕变,建立基于“人类”思维的共同体伦理,从而避免伦理道德的区隔化、碎片化。
一般而论,社会转型有两种:一种是单一性社会转型,即由单一性社会因素转型而带动的社会转型;另一种是社会各因素的整体全面转型。我国改革开放所推动的社会转型是一种以经济转型带动社会转型的单一性转型。在单一性经济社会转型模式中,伦理道德话语总是围绕着经济要素而构建,我们的伦理道德标准也总是向市场经济倾斜,不但肯定个人价值、肯定经济利益,而且把经济价值的实现作为道德评价的主要尺度。正因如此,一种被极大简化的功利主义道德开始出现并蔓延。从单一社会转型的现实来看,偏重某一价值的伦理道德体系是无法有效统领全面的社会建设的,只会导致社会伦理道德的狭隘与偏差[10],甚至带来道德内在价值的强烈冲突,如使好人得不到好报成为常态。中国共产党的十八大召开之后,中国社会进入全面转型期,即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诸要素的协调发展期。在社会全面转型的伦理秩序中,社会、经济、文化、生态、政治等诸领域的价值目标都应受到同等尊重和认同,没有任何价值目标处于绝对的优先地位而排斥其他价值。当然,我们承认社会各领域的价值诉求的同等重要并不是要否认价值共识,相反,对于社会生活而言,价值共识是不可或缺的。唯如此,我们才能期待超越个人差别而形成一致的伦理行动。问题在于,促成社会合作的价值目标要具有广泛的包容性,要能够兼容社会各个领域的价值标准,这就需要复杂性伦理思维和统合性伦理思维,只有这样才能建立复合型的价值目标体系并由此构建适应社会全面转型的伦理秩序。如果说单一经济社会转型以经济理性为基础,那么社会全面转型则须建立在公共理性之上。与经济理性关于人性的自利假设不同,公共理性从公民角度理解人的本质和人际关系。前者是对人性的简化,把人性中与市场机制相符的部分单独提取出来,作为市场运行的逻辑原点;后者则是对人性的丰富,帮助人们在复杂的社会情景中认识自我角色、认识自己所担负的道德责任。公共理性本身具有“共同意识”的意义,在它的牵引下,人们才能本着对于社会“善”的追求,通过重叠共识达成基本的、一致性的伦理认同,借以消除因个人差异所形成的道德张力,使公共伦理生活成为可能。正如罗尔斯所言,“公共理性总是允许人们对特殊问题提出多重合理的答案”[11]。这将为我们综合地、均衡地考虑社会诸领域的多元道德需求提供理性支持。
第二,要建立以核心价值观为主干的伦理道德规范体系。改革开放以来,社会主义道德规范体系的建立是基于社会主义市场体制的,当时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起到了非常好的辩护作用和规范作用。但是,随着社会由单一的经济转型向社会的全面转型,建立社会主义道德规范体系的基本参照发生了深刻变化,不但要适应市场经济的要求,还要适应社会主义法治化的要求;不但要继承中国共产党长期形成的革命道德的传统,还要承续中华民族几千年传承下来的优秀道德传统;不但要反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而且要充分吸纳西方现代伦理文化的优秀成果。因此,如何在新时代完善社会主义道德规范体系,是当前重大的理论问题和实践课题。我们所要做的工作主要有四个方面:一是选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德规范体系的基本参照,克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单一参照;二是理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社会主义道德规范体系的关系;三是建立适应新时代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德规范体系;四是连接社会主义道德规范体系的不同层次和不同部分,使之成为一个有机的、有效的整体,而非断裂的零散体。在此,笔者仅就第三个方面的工作谈点认识。社会主义道德规范体系应该是一个动态开放、不断完善的系统,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必须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指导下,对整个伦理道德规范体系作出相应的调整。以下提供一个不太成熟的思路,仅作参与。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伦理道德规范体系的初步构想是:以“人道主义”和“集体主义”为根本原则,以“发展、公正、共享、和谐”为核心伦理理念,以经济伦理建设、政治伦理建设、文化伦理建设、社会伦理建设、生态伦理建设为基本领域,以“爱国、敬业、诚信、友善”为个人基本道德规范,以“职业道德、社会公德、家庭美德、个人品德”为基本道德建设要求。这是一种伦理道德规范体系的宏大构 想[12],还需要另文仔细展开论证,这里只简要说明几点。一是为什么要增加人道主义作为道德原则?在以往的社会主义道德规范体系中,集体主义是唯一的原则。它强调人的社会性本质,强调社会利益本位,这有利于人们超越对私人利益的计较,关心他人和社会,并积极为社会利益的实现作出贡献。但它无法周全所有伦理关系,如人与自然的关系。而人道主义是以个人权利为基调的道德规范,可以成为集体主义的有益补充,满足核心价值观的人本需要。人道主义是人们对抗宗教权力和王权的产物,旨在恢复人的独立自主,肯定世俗世界的价值。人道主义不但要保护人们的合法权利,更要求从人性关怀的角度处理社会关系,考虑社会问题。将“人道主义”与“集体主义”并立为社会主义道德规范的原则,有利于我们在道德情景中兼顾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认识两者的界限,有效避免相互的矛盾和冲突,以增量方式促进两者的协调统一。二是为什么要增加“五大伦理建设”?新时代是“五位一体建设”全面推进的时代,可以说“五位一体”是新时代社会发展的核心,我们的伦理道德规范体系不能漠然置之,相反必须正面解决五大发展的伦理基础、伦理规范及其相互协同的问题。没有五大伦理建设,就不能体现新时代的伦理精神,或者说会在社会重大战略上出现“伦理缺位”,伦理学就没有用武之地。三是为什么要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个人层面要求取代原有的“五爱”要求?“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社会主义”的“五爱规范”是公民道德的基本要求,但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有重叠交叉之处。如果我们要强调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社会主义伦理道德规范体系建设的统领作用,要统分体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价值观要求,以“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取代“五爱规范”是稳妥的、可行的。
第三,要鼓足以构筑中国伦理精神为指引的道德力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已进入新时代,新时代需要有新的精神生活,新的精神生活需要有伦理精神价值的指引。中国共产党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牢固树立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断增强意识形态领域主导权和话语权,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继承革命文化,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更好构筑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为人民提供精神指引。”[2](23)精神生活深刻反映着社会的发展与时代的变迁,同时也会汇聚巨大的精神能量去影响社会历史发展的速度和质量。我们只有清晰认识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新变化,倡导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的新主张,开拓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的新思路,为广大人民提供精神生活指引,才能真正实现强国梦。那么,我们的伦理学就要构筑中国伦理精神和中国伦理价值,为人们的道德生活提供指引,从而彰显中国道德力量。这里实际上有两个重大问题需要思考:其一是当代中国伦理精神是什么?实际上就是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核心的思想精神、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自己时代精神的精华”,是在当代中国的历史性实践中生成的,具有典型的内生性特质和鲜明的时代色彩,继承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基因和血脉,以古鉴今、古为今用,反对简单复古,反对全盘否定,既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文化的有机结合,也实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换和创新性发展,关系到现实社会主义亲切感、感召力与凝聚力的实现。爱国主义作为民族精神的核心,是古往今来显现于中华民族历史的重要标识,中华民族精神的内涵也是以此为基础发展起来的。在中华民族源远流长的历史长河中,爱国主义始终是维护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的时代最强音。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是适应我国社会发展进程和实现“中国梦”的精神力量支持。历史无数次证明,一个因循守旧、固步自封的民族是不可能日新月异、蓬勃发展的。在当前中国社会,改革创新是我国人民精神风貌的真实写照,是协同社会价值观、实现个体价值塑造的重要载体。其二是如何彰显中国道德力量。中国道德力量就是人民的力量、团结的力量、战胜困难的力量、为世界担当的力量,这些都是源于中国的道路、制度、理论、文化全面自信的力量,是一种精神上的自信力。道路自信的力量来自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的正确性,体现了中国社会发展的规律性与中国共产党对道路选择的科学性;制度自信的力量来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以及被实践证明了的“中国崛起”“中国道路”的成功;理论自信的力量来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科学性、真理性、正确性;文化自信的力量来自中国传统优秀文化、革命文化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有机统一而形成的文化先进性。四者有机联系形成中国的整体自信。所以,我们要增加中国伦理学自信,主动关注道德生活,大力扬善抑恶,主动发声,主动介入,要有作为,且要有大作为,真正使伦理学成为新时代之显学。
第四,要构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伦理学。我国现有的伦理学基本上是用历史唯物主义原理解释道德现象的一种理论体系,为我国的伦理学建设和社会主义道德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但不可回避的是,这种理论体系已经明显地滞后于世界伦理理论的前沿和现实的中国道德生活。其主要原因是传统伦理未实现现代转型以及以苏联马克思主义伦理学为基础的伦理学体系与中国话语之间存在间隙,原有伦理学表现出时代的滞后性,没有体现中国特色,缺乏中国态度,因此,构建适应新时代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伦理学迫在眉睫[13]。“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伦理学”是具有中国特色、以问题为导向、基于中国经验和中国道路的当代伦理学新范式,它有别于传统的“马克思主义伦理学”,也不是中国传统伦理学的当代延续,更不是西方伦理学的中国化,而是中国伦理学发展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提出的全新的理论命题[13]。我国现有伦理学理论体系为中国社会的当代转型和社会主义道德建设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但国际形势和社会主义建设已经发生了日新月异的巨变,由于未能完成传统伦理的现代转型以及以苏联马克思主义伦理学为基础的伦理学体系与中国话语之间存在间隙,该理论体系已经明显地滞后于世界伦理理论的前沿和现实的中国道德生活。这种滞后性的主要表现是,现有伦理学理论建设依然未能完全实现传统伦理的转型、继承和创新,显示了伦理学理论建设的“先天不足”。同时,在马克思主义伦理学中国化的过程中,我们热衷于套用苏联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的基本理念、学术框架和学术方法,对马克思主义的深层思想重视不够,在马克思主义思想中提炼马克思主义伦理观念“火候不足”,显示了伦理学理论建设的“消化不良”。造成的不良后果就是:一方面,囿于苏联模式的伦理学框架而对它不加批判地搬用,导致中国伦理学呈现出知识内容和研究范式上的滞后性;另一方面,由于缺乏深层反思与检验,我们对伦理学的认知偏离了辩证唯物主义方法论原则,从而“误读”或窄化了伦理学的研究对象和方法。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伦理学建设的要义在于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引导,充分吸收人类道德文明成果,建设富有中国特质的学术体系、学科体系和话语体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是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区别于其他哲学社会科学的根本标志,必须旗帜鲜明地加以坚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为马克思主义的新形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伦理学的理论导向。与以往建立在全苏联模式的马克思主义伦理学不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伦理学不应简单地套用任何既有的马克思主义伦理学范式,而是要返回到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本质,在正确理解马克思道德思想的基础上系统构建马克思主义伦理系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伦理学以传统伦理和西方伦理为基本参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伦理学需要保持开放的学术话语,广泛吸收、借鉴传统伦理与西方伦理体系的营养,使自己站在世界伦理学发展潮流的前沿。传统伦理和西方伦理都构建了各自的理论图式,反映出在一定时期、一定社会环境下的道德镜像,积累了丰富的理论成果和研究经验,以之为参照可以更完整地把握人类道德生活脉络和规律,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伦理学的传承性、合理性和科学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伦理学的话语表达也一定要是“中国的”,从基本理论到原则规范都要讲“中国话”。中国传统伦理的言说方式和现代中国的道德生活语言,都应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伦理学的学术语言,都应该能回应中国道德实践,能提升中国道德建设经验,能讲好中国道德故事,唱响中国道德“好声音”[13]。
[1] 埃德加·莫兰. 伦理[M]. 于硕, 译. 上海: 学林出版社, 2017.
[2] 习近平. 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7.
[3] 曹刚. 责任伦理: 一种新的道德思维[J]. 中国人民大学学报, 2013(2): 69−72.
[4] 习近平. 开辟合作新起点谋求发展新动力——在“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圆桌峰会上的开幕辞[J]. 中国经济周刊, 2017(20): 57−58.
[5] 李建华. 从共生到共享: 人类的意义性攀越[J]. 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 2017(5): 88−92.
[6] 刘遗伦. 不断夯实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践基础[N]. 贵州日报, 2017-12-24(4).
[7] 尤瓦尔·赫拉利. 未来简史: 从智人到神人[M]. 林俊宏, 译. 北京: 中信出版集团, 2017.
[8] 莱茵霍尔德·尼布尔. 道德的人与不道德的社会[M]. 蒋庆, 等译. 贵阳: 贵州人民出版社, 1998: 263.
[9] 李建华. 如何理解美好生活需要[J]. 中国地质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17(6): 1−2.
[10] 李建华, 姚文佳. 社会全面转型与道德引领[J]. 湖北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6(3): 1−6.
[11] 约翰·罗尔斯. 公共理性的观念[C]//协商民主: 论理性与政治. 陈家刚, 等译. 北京: 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6.
[12] 李建华.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道德规范体系关系之探索[J].道德与文明, 2017(2): 2−7.
[13] 李建华. 中国伦理学: 意义、内涵与构建[J]. 中州学刊, 2016(3): 2−7.
The mission of China ethics at the New Times
LI Jianhua
(School of Maxism, Zhejiang Normal University, Jinhua 321004, China)
As we step into the New Times of constructing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we have to grasp very well the connotation of “the New Times”. We call our time the New Times because it makes far-reaching sense in ethical value, which means strengthening our nation, benefiting our people, upholding self-confidence, taking responsibilities and sharing interests. Because of the particularity in development of both modern technology and our society, we are confronting new challenges, including the ethical subject getting destructed, the ethical relations becoming complicated, the ethical integration being more difficult to be accomplished, and the ethical expectation being filled with uncertainty. Therefore, it is absolutely necessary to have ethics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Chinese style and Chinese spirit. Only by this kind of ethics, could we adjust our moral lives to the over-all social transformation, construct the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moral rules system, and build China ethic value.
the New Times; ethical integration; ethical fracture; China ethical spirit; China moral power
[编辑: 苏慧]
国家哲学社会科学重大招标项目“中国政治伦理思想通史”(16ZDA103)
李建华(1959—),男,湖南桃江人,哲学博士,长江学者,浙江师范大学特聘教授,中南大学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伦理学基础理论,政治伦理学,思想政治教育
10.11817/j.issn. 1672-3104. 2018.01.002
B82
A
1672-3104(2018)01−0007−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