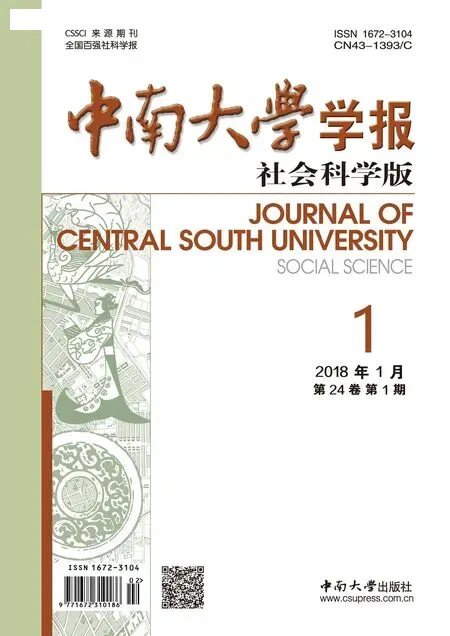警惕寻求权力与控制的“科技理性——解读C.S.路易斯的科幻小说《沉寂的星球》
潘一禾,郑旭颖
警惕寻求权力与控制的“科技理性——解读C.S.路易斯的科幻小说《沉寂的星球》
潘一禾,郑旭颖
(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浙江杭州,310028)
《沉寂的星球》作为C.S.路易斯科幻小说“太空三部曲”的第一部,一方面延续了路易斯一贯的诗性写作风格,具有很高的文学价值;另一方面也对20世纪初英国工业社会的弊病和科技思维崇拜进行了有力批判。作者以高度的哲思概括力,让小说的三位主人公分别展示了科学家、商人和人文学者在现代社会中的特殊地位与作用,深刻揭示了现代社会合情合理面貌下的荒谬与残忍。在这部充满才华与想象力的小说中,路易斯还特别澄清了寻求权力与控制的科技知识与智慧的区别,点明真正的智慧才能帮助人类及地球避免“失落”,走向未来宇宙。
C.S.路易斯;太空三部曲;《沉寂的星球》;科技思维崇拜
“太空三部曲”是C.S.路易斯的代表作之一,《沉寂的星球》是其中的第一部。但因为内容晦涩离奇,目前国内学界的相关研究几乎是空白的。在《沉寂的星球》中,作者预测了科技思维崇拜的种种表现和奇观,强调科技理性在提高社会生产力的同时,也因“进化论”发展观的盛行及经济与科技的联手共谋,严重威胁了人们的精神和生活世界。今天再读路易斯于1938年完成的《沉寂的星球》,能为我们关注的许多重大现实问题提供全新的认识视角。
C.S.路易斯(Clive Staple Lewis)是20世纪英国著名的作家、学者,先后任教于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虽然他以童话故事《纳尼亚传奇》为中国读者熟知,但他的作品包含诗歌、散文、小说等多种体裁,他的成就涉及英语文学史、文学创作和神学等多个领域。凭借富有诗意与深意的作品,路易斯在英美有持续、普遍、深刻的影响力,是英语世界里家喻户晓的人物。
C.S.路易斯的著作展现了在英国工业社会和现代性的浪潮中他对“科技理性”的思考,至今仍是我们的宝贵财富。尽管一个多世纪以来,对于启蒙运动以降的“工具理性”的批判声不绝于耳,但鲜有学者能像路易斯那样,凭借深厚的古典知识功底,将“理性”的来龙去脉阐述得如此清晰,并从全局和演变的视角,论证科技理性的危害和荒谬。
一、科技与科幻:共同繁荣与貌合神离
“每一个时代都有一种与之相应的艺术”[1](2),科幻小说属于工业时代。20世纪,科幻小说从各种文学题材中脱颖而出,取得了巨大的成就。现代自然科学、第一次工业革命和科幻小说都诞生于英国并非巧合,但是,科技与科幻却有着共同繁荣却又貌合神离的关系。
无论是付诸工业的科技,还是无意付诸工业的科学,都率先在英国蓬勃发展。17世纪末,牛顿的《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开启了现代科学的大门;18世纪下半叶,蒸汽机、织布机缔造了英国的工业社会;19世纪,达尔文惊世骇俗的《物种起源》宣告了“上帝之死”。“工业革命是认识现代人类历史的入口”[2](7),它带来了繁荣,也带来了光怪陆离的工业社会。与此同时,建立在乡村文化之上的英国,又是与工业文明格格不入的。看到科技带给英国的是人的异化、美的消失和社会风气的堕落,曾经给予牛顿无上敬意的英国思想界,决意不再为科学唱赞歌,而是选择了质疑和反思,守护受到损害的人性。人文精神和现代科学精神在19世纪中期分道扬镳,从此开启了英国批判工业主义的强大传统[3](124)。
19世纪初,科幻小说响应了这一反思传统,英国的科幻小说在对科技的批判中登场。1818年,玛丽·雪莱发表了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科幻小说《弗兰肯思坦》,讲述科学家在实验室里制造的怪物所引起的一场悲剧和各种社会新问题。从19世纪初到20世纪上半叶,英国科幻小说界群英荟萃,H.G.威尔斯、斯蒂文森、赫胥黎、奥威尔……这些熠熠生辉的名字及他们创作的科幻小说想象丰富、情节紧张、富有悬念,很快就成为人们喜闻乐见的读物。必须承认,科学给小说带来了巨大的想象空间。尽管在这些想象中乐观和悲观同在,但是在文学作品中,警惕和反思永远比附和和赞颂更发人深省。
虽然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科学和技术实现了真正的结合,但其实质是科学和资本的联姻。英国资本家为了扩大生产而求助于学院科学。借助科技的力量,“全球市场”才得以实现。从此,科幻小说也从对科技伦理的担忧,转向对整个工业文明爱恨交织的复杂叙述。而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一次经济“大萧条”的出现,一路高歌、如火如荼的现代工商新秩序受到了更多的质疑。正是在这种情境下,C.S.路易斯创作了科幻小说《沉寂的星球》,后来又陆续完成了《皮儿兰德拉星》和《黑暗之劫》,构成了科幻小说史上颇负盛名的“太空三部曲”。当时的英国,这类讲述星际旅行的“太空小说”非常流行。但是在小说《沉寂的星球》中,“硬科幻”元素并不显著,作者真正关心的不是火星和宇宙飞船,而是通过一个简单、隽永的故事,来揭示科技对人类精神世界的影响和破坏。
《沉寂的星球》讲述了20世纪初剑桥大学学者兰塞姆被绑架到外星球“马拉坎德拉星”之后的奇遇。科学狂人韦斯顿为了地球人的生存和发展,说服富翁狄凡投资制作了一架宇宙飞船飞往火星(当地人称之为“马拉坎德拉星”),贪婪的商人狄凡垂涎的是那个外星“殖民地”的无尽资源。当地统治者要求与一名人类代表见面,这两人误以为“外星野蛮人”要献祭人类,就将兰塞姆绑架到了火星当供奉品。得知阴谋的兰塞姆奋力逃脱,进入马拉坎德拉人的生活。这个星球上的原始风光怡人,高山、河流、植物美不胜收。星球上住着三种具有高级智慧的物种,分别生活在高原、低地和森林里,并由一位“神使”奥亚撒统治,彼此间少有往来却和平共处。他们的物质文明似乎还停留在地球的石器时代,主要依靠原始农业和捕鱼为生。但同时,他们心智成熟、具有理性,有自己的诗歌和艺术,且有着在地球人看来非常高深的天文地理知识,并能制作必要的、外形粗糙简单但“科技含量”很高的器件。他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生活宁静而简单。故事结尾,兰塞姆终于见到奥亚撒,并揭开了会面的真正目的。最后,两个坏蛋被遣返回地球,而兰塞姆也选择回到地球,准备投入新的抗争。
《沉寂的星球》行文优美、情节简单。尽管作者为我们描绘了一个生动有趣、如诗如画的世界,他的真实意图却是让我们去体会现代社会中的狰狞和扭曲。这个经过文学虚构后显得更简明的现代世界,是由科学家和商人塑造并统治的,曾经辉煌的人文事业已成昨日黄花。而路易斯的首要工作就是反思科学家、商人和人文学者在现代社会中的地位与作用。
韦斯顿号称是当时世界最伟大的科学家,狄凡戏谑他“早饭用爱因斯坦抹面包、喝一杯薛定谔的血 浆”[3](11)。他的大脑可以飞快地计算复杂的公式,处理各种高难度的知识。他发明了宇宙飞船,自称“肩负着全人类的命运”,高呼要“凭着生命的权利,……准备毫不退缩地把人类的旗帜插在马拉坎德拉的土壤上”[4] (194)。但令人费解的是,当面对具体的某个生命时,他又表现得冷酷无情。他的真实情感世界令人颤栗,因为他不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人,几乎失去了一切生理上的恐惧和喜怒哀乐,剩下的只有在科技无能为力情况下的焦虑。
再看书中所谓的成功商人狄凡,他靠着巨额财富跻身上流社会,对于资助韦斯顿这件事,他清楚自己“可不是闹着玩儿才冒这些风险的”[3](38),他看中的是马拉坎德拉的“太阳之血”——黄金,以及“殖民”火星比殖民亚洲、美洲、非洲有更为巨大的机会和利益。对于韦斯顿一本正经的科学精神,他抱着嘲笑的态度说:“他才不管人类的未来,以及两个星球的联系呢。”[3](37)
再看本文的主人公人文学者埃尔温·兰塞姆。C.S.路易斯以自己的好友、《魔戒》作者J.R.R.托尔金为原型刻画了这个人物。在小说的开头,这个英国剑桥大学的语文研究员正在英国乡间做徒步旅行,无意中闯入了韦斯顿和狄凡的科学实验室。他为人善良正直、彬彬有礼,在寻找住处的过程中,答应为素不相识的老妇人寻找儿子。尽管身处可疑的宅子,但是在听到哈利的挣扎声后,还是毫不犹豫地冲进去救他。虽然作为“一无用处”的人文学者,他在被绑架时陷入极度恐怖的危境,但当他在马拉坎德拉遇到第一个居民时,他忘记了原先对自身命运和外星人的可怕设想,立刻展现出了天然的温和、友好的一面,并顺利地融入了当地人的生活。
但他同时又有现代人的迟疑、软弱和胆怯。面对暴徒时,他竟然不知所措,甚至不知道说些什么,“就算他们在虐待那个男孩,兰塞姆也不可能硬把孩子从他们手里夺过来”[4](13)。尽管被下药绑架到宇宙飞船上,兰塞姆仍然出于善良和他那套礼仪,努力地和两个坏人维持友好的关系,并主动提出要分担劳动。在与马拉坎德拉居民的共同生活中,他“血液中沉睡多年的某种东西被唤醒了”,他对勇气和崇高有了更深刻的体会。
二、科技与商业联手:寻求权力与控制
综上所述,小说表面上展现的是好人与坏人的较量,其实是在探讨科技与人性的对立。全书通篇只写了几个场景,以大段的对话和景色描写为主,但轻描淡写间暗藏着对工业文明和科技思维的深刻剖析。路易斯认为,这种鄙视人文精神的科技思维,是一种“不彻底的理性”。现代人以“理性”的名义犯下的种种错误,根源在于将科技思维等同于理性。小说通过韦斯顿和狄凡的种种表现,向我们展示了现代科技思维的多幅面孔。
首先,科技思维的第一幅面孔是一种机械、冰冷的“约化主义”。它把逻辑推导等同于理性思考,用科学公式解释世上的一切秩序,将各种单一价值奉为完整的信仰,妄图将这个多姿多彩的世界和复杂的人性都约化成科学世界中简单机械的法则。小说中的韦斯顿就是个典型的约化人类基本价值观的人,他懂得高深的科技知识,却形同一个麻木不仁的“机械人”。当兰塞姆拒绝做人质时,韦斯顿说:“你的思想不能这么狭隘,只想着个人的权益和生命,即使是一百万个人,跟这个相比,也显得无足轻重了。”[1](32)路易斯将韦斯顿式的思维视为“人造良知”,认为是现代学校把孩子们教育成了人工制品。这类人工制品情感淡漠,虽然被灌输了一套冠冕堂皇的良知,但那不过是从传统价值观中择其一二奉为圭臬的“约化”教育,因为缺乏真情实感,他们常常将这套“人造良知”用错地方。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兰塞姆的表现。他不但为人善良,而且感觉敏锐、情感丰富。我们正是通过兰塞姆的眼睛、耳朵、舌头、鼻子和心灵,感受到了英国乡间的阴晴变化,观赏到了在宇宙飞船中才能看到的地球景观,看到了如诗如画的马拉坎德拉红色的高原、蓝色的河流、美丽的植物,体会到了在浩渺太空中对生命和永恒的真正敬畏。同时,他并非对科学知识一无所知,实际上,他有着丰富的科学知识,足够他日常使用;即使到了太空中,他仍然能根据“月亮”形状迅速判断身处何方;到了火星上,他也能立即适应环境,保护自己的安危。
科技思维的第二幅面孔是一种强权。它能与传统割裂也正在于它被赋予了这种“唯我独尊”、不容置疑的权力。在这部小说中,作为科技代言人的韦斯顿和狄凡盛气凌人、肆意妄为。而全书的起因正是他俩试图利用高科技殖民火星。在许多科幻小说中反复出现的各种技术其实就是一种强权,一种令人恐惧却又无力抗拒的强权。至于它的面貌究竟是哥斯拉还是迷人的“梭麻”,我们或许难以预测。但毫无疑问,它已经以某些面貌(时间、技术、市场、军事)悄然发生。
四百年前,培根指出“知识就是力量”。如果能重回培根的语境,我们会发现,培根在此是指“知识是一种权力”。只有科学知识,才有这样的力量消除蒙昧,消解中世纪的神权统治。虽然这一“权力”始于消除蒙昧,但作为强权,它却能给予我们舒适的当下,并许诺我们美好的未来。而后者曾经是宗教的职能。如同中世纪的神权,科技也是一种事实上的“一神制”,它许诺给我们一切,也就要求我们完全信任它。科技甚至免除了费钱费力的传教,宗教许诺给我们死后世界,而科技的彩票即开即兑。能治病的是医学,让我们飞翔的是飞机,不是上帝。这一切都是我们自愿选择的。我们理所当然地相信知识万能、科技万能。如果科技有什么问题,那么我们就用更先进的科技来解决。不仅韦斯顿面对科技的无能为力会焦虑,所有科技文明中的人都有同样的焦虑。技术带给我们的丰厚馈赠有目共睹,但是请注意,这种馈赠充满了危险。所有强权统治下都必有孱弱的人性。身体的舒适就是我们所要的一切,这是一种非常有欺骗性的假象,直通今天的“无痛伦理”,是对我们真实存在的人性的麻痹和扼杀。在此意义上,我们确实像浮士德一样把灵魂卖给了魔鬼。路易斯提醒我们:舒适不等于奢侈,不等于无节制的消费,舒适更不是“鸦片”,它只是幸福生活的一部分而已。如果我们想在与科技、商品的关系中重新反客为主,或许我们就要学习马拉坎德拉人对科技欲望的节制以及面对死亡和痛苦时的智慧。在此,“马拉坎德拉人”成为我们可资借鉴的“他者”。
科技的强权一方面体现在它与所有人的关系中,另一方面则表现为部分人对其他人的强权。科技不是任何时候对任何人都有求必应。路易斯认为,“人征服自然”同时也意味着一部分人征服了另一部分人。科技给予普罗大众恩惠的同时,也成为少数人和少数国家的“特权”,甚至通过军事、经济等手段成为“极权”。匈牙利学者卡尔·波兰尼在评价20世纪50年代的美国时就说:“发现一个高度发达的科技社会已经播下了它的极权主义种子。”[5](6)而这一担忧在今天的“后人类主义”批判中甚至变得更为严峻。
科技思维需要被反思的第三幅面孔,就是它和商业思维的联手共谋。现代科技以商品和消费的形式飞入了寻常百姓家。为什么路易斯要在韦斯顿背后设置狄凡这个角色?因为没有狄凡的资本和经济头脑,大科学家韦斯顿不可能实现他的火星之旅。事实上,狄凡才是这项事业的主导者。尽管韦斯顿在人质选择以及是否屠杀外星人的问题上有自己的看法,尽管韦斯顿在兰塞姆和外星人面前表现得义正辞严,但对狄凡却表现出全面的配合、妥协和屈从。
回顾历史,我们发现现代科技就是资本下的蛋。没有资本的邀请,自然科学不会走出实验室。在19世纪末期,就有工厂富有远见地成立了工业实验室。工业革命的诞生,离不开工业革命之前英国借助羊毛和国际贸易积累的巨大财富。科技与资本的联姻是现代社会最重要的事件之一。我们应该感谢资本推动了科技的发展。但是理性最重要的前提是独立性,被金钱绑架的科技不可能是独立、崇高、神圣的,也必然要跟随商人逐利的天性随波逐流。所以科技思维也常常是一种以利益最大化为目的的工具理性。在路易斯笔下,“老式”英国人根据风俗习惯行事,社会具有凝聚力和责任感。现在的英国人则在“看不见的手”的操纵下“自由行事”,其结果却是“无往而不在的枷锁”——限制我们行为的因素增加了,制约我们品行的力量却减弱了。在《沉寂的星球》中,韦斯顿遵奉约化价值,而狄凡根本没有道德底线;韦斯顿按人造良知行事,狄凡则根据有利可图行动,所以他的表现比韦斯顿更决绝。狄凡甚至能把屠杀外星人当作一个玩笑,说会给韦斯顿留下几个活口做玩具;韦斯顿不愿意拿同为白人的兰塞姆做人质,但和兰塞姆从小认识的狄凡,却六亲不认,把兰塞姆看作绝佳的绑架人选。
科技思维的第四张面孔,就是对科技文明的盲目自信和傲慢自大。例如在小说中,三位主角都有一个共同的“优点”——非凡的勇气。开展外星球冒险的韦斯顿非常勇敢,狄凡的勇气有过之而无不及。狄凡的勇气不但体现在冒着巨大的风险投资韦斯顿的科学事业,和韦斯顿一起进行外星拓荒,还在生死关头敏锐地发现新的商机。在返回地球途中,当韦斯顿发现生还无望时,终于“像孩子一样哇哇大哭”[4](213),狄凡却能镇定指挥、力挽狂澜,最终让宇宙飞船侥幸飞回地球。
细心的读者不难发现,他俩所谓的“勇敢”,不过是无尽的贪婪和盲目的自大而已。他们以为凭着一把手枪,就可以在火星上畅通无阻。他们把火星人看成“土著”的本能反应更是生动地表现了现代人对科技文明以外世界的无知和自大。在路易斯所处的时代,白人以外的世界多数还未进入工业社会,所以,狄凡和韦斯顿的土著思想又表现为一种“白人中心主义”。而韦斯顿所谓“生命的权利”“人类的未来”也仅指白人的权利、白人的未来。在他们眼中,白人以外的物种都是“土著”,即没有被科技之光照到的人种。这些“土著”可怜、可悲、愚蠢、无知,根本不能当人看待。对于拿“鞑靼”孩子做实验一事,韦斯顿说:“那个男孩挺理想的,……不能为人类服务,只会传播愚昧。像他这种男孩,文明社会应该主动把他交给国家实验室去用做实验。”[4](21)面对马拉坎德拉人,韦斯顿的“土著思想”更是暴露无遗。他先哄小孩似地吓唬他们:“是天上的大头头派我们来的。你如果不照我说的做,等他一来,就把你们全部炸飞——乒!乓!”[4](179)接着他又用廉价的彩色珠子诱惑土著,“只要照我们说的做,我们就给你许多漂亮的东西。看见吗?看见吗?”[4](180)对此,马拉坎德拉居民爆出了山洪般的笑声。此时此刻,在理智、高贵的马拉坎德拉居民面前,野蛮、邪恶、不可理喻的韦斯顿才是不折不扣的土著。
三、何谓智慧——重审科技思维下的发展和进步
在《沉寂的星球》的结尾部分,围绕着火星“神使”奥亚撒与兰塞姆的见面以及奥亚撒对韦斯顿和狄凡的“审判”,书写了大段的对话。不禁令人想起柏拉图用“哲学剧场”的手法,以苏格拉底式谈话引导人们去追求美德的一幕。为什么奥亚撒一直召唤着他的地球“人质”呢?随着兰塞姆与奥亚撒的会面终于真相大白,原来奥亚撒是想了解地球——这颗被魔王统治而失去了音讯的星球上正在发生的事情。其真正的意义也正是召唤人类走出迷思——向真理走去。奥亚撒沿用了苏格拉底式的诱导,让我们一步步接近真理,迫使对手承认失败。奥亚撒的戳穿让我们看到了现代社会存在的两大问题:急功近利的发展观和人性的扭曲。
在小说中,一种流行于20世纪初的“进化论”发展观清晰可见:贪婪的、建立在掠夺基础上的经济发展,急于求成、以牺牲个体利益、生存环境为基础的社会发展,其实是一种本末倒置、极其冷酷的发展。小说还由此强调,韦斯顿和狄凡利用现代科技将白人殖民地扩展到了遥远的外星球。殖民式掠夺思维从未在我们的历史中消失,而是以科技、贸易等更高明的手段出现。路易斯曾经如此描述当时的英国:“翻开一本杂志,你很少不会看见这等陈述,即我们的文明需要更多的动力或活力或自我牺牲或创造力。”“仿佛‘你须促进共同体利益’这一准则并非‘己所欲施于人’之多音节变体似的。”[6](34)效率曾经是对机器所使用的标准,是现代管理学说对工厂所使用的标准,却成了生命、生活和人生的标准。
但是,为什么经济的发展、科技的进步没有解决“粮食不够”的问题,而人类的工作却更繁重了呢?小说中,路易斯借兰塞姆之口与火星人卡纳卡贝拉卡讨论了这个问题。结果兰塞姆发现,地球人之所以“一辈子从事”挖掘黄金这样“很难的”行业,既不是因为他们“喜欢”,也不是因为“食物不够”,而是因为有一种机制让他们“不得不干,因为如果不干,就得不到食物”[4](163)。
显然,C.S.路易斯心中清楚:工业社会的现实就是商品过剩与贫穷同在!威廉·莫里斯在《乌有乡消息》里呼喊:“所有的节省劳动力的发明结果只是增加了劳动力的负担。”[7](121−125)牛顿的成就使17世纪晚期的欧洲人乐观地相信,只要找到了完美的定律,就能建立起完美的秩序和完美的世界。然而这个美丽新世界迟迟没有到来,而法国大革命似乎宣告了这个理性乌托邦的破灭。就在此时,达尔文的“进化论”给了欧洲人另一个选择。“进化论”传递了这样的观点:物竞天择、优胜劣汰,一切都是进化、发展、竞争的结果。这个观点和资产阶级精神不谋而合。从此人类牢固树立起了这样的观点:人类文明是不断进步、发展的,我们所要做的就是不断推动它的发展。这种发展主要指的是经济和科技的进步。
发展和进步作为今天最重要的命题毋庸置疑,但是它的目的、手段和实质值得我们反思。我们切勿忘记“人才是万物的尺度”,发展不等于科技上的发达,也不等于经济上的繁荣。不管是科技还是经济都只是手段,多数人都能有一段幸福的人生才是最终的目的。认识自己不是获得更多的生理知识,认识世界也不仅仅是了解经济秩序。匈牙利学者卡尔·波兰尼在经历了二次世界大战和经济大萧条后,富有远见地告诉我们,市场经济的全球化是必然选择,但是选择了市场经济,就必须面对它所带来的问题,而这些问题甚至会日益加剧。共同富裕是人类可以期待的未来,但共同富裕并不必然等于理想的社会。卡尔·波兰尼在半个多世纪以前就预见到:“西方的危机……更根本地是西方文化对未来人类更高形式生活需求上的思想道德的‘荒芜’。”[5](229)
路易斯一直致力于“灌溉思想道德的荒芜”。在这本小说里,路易斯首要的工作就是揭露科技思维如何导致人性的扭曲。前面我们提及科技思维是一种不彻底的理性,而这种不彻底正在于它破坏了传统人文价值。现代人与传统价值观一刀两断,以为这样就能让“真实”和“坚固”拨云见日。其结果却如马克思所说:“一切神圣的东西都被亵渎。”“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路易斯认为,“天道”恒常,我们的价值观不该随波逐流,不应在轮番登场的各种价值观中迷失自己,走向虚无。
由此而言,《沉寂的小说》也是韦斯顿所代表的科学与兰塞姆所代表的人文传统的直接较量。作为科学家的韦斯顿坚决地说:“我不把文学、历史之类的垃圾算做教育。”而且,他坚信:“所有受过教育(不包括文学、历史之类的垃圾教育)的人……完全跟我站在一边。”[4](33)在韦斯顿眼中,文学、历史纯粹是浪费钱,人文学者理应被划到那些对人类文明毫无贡献的人群之中。而当韦斯顿向外星人骄傲地细数地球文明时,他罗列的是医学、法律、军队、建筑、商业以及交通,并不包括文学艺术。
这种科技人士的傲慢自大完全没有事实依据。回顾人类文明史可以发现,科学和哲学几千年来都是相辅相成的。不但欧洲文明的源头古希腊以“自然哲学”著称,欧洲历史上最伟大的哲学家,从柏拉图、亚里斯多德到康德、莱布尼兹,他们的成就都同时涉及哲学和科学。
在“专业化”到极致的今天,我们不苛求全才,我们倡导的是健全的人格。当我们抛弃了哲学思辨时,科学也就沦为一门仅仅谈论知识的学问。当我们把人文和科学硬生生割裂开来,硬分高低的时候,其结局必然是“人性的废除”。奥亚撒告诉兰塞姆这样一条法则:“不要跟别人谈论规模或数量……你不明白,这会使你对虚无顶礼膜拜,而对真正伟大的东西却视而不见。”[4](208)
在此有必要重申,路易斯对科学并不持否定态度。相反,他认为“捍卫价值”,不但不是攻击科学,恰恰是“捍卫知识之价值”[6](88)。他只是想让我们知道缺乏引导的知识充满了危险。面对今天浩瀚的信息,我们需要有健康的心灵和真正的智慧来驾驭知识、灌溉科技世界中思想道德的荒芜。
要走出科技思维的迷思,我们需要重新唤起对生命的敬畏。马拉坎德拉是一颗行将枯萎的星球。尽管大限将至,大家却照旧安居乐业。相形之下,韦斯顿口口声声宣称“生命的权力”,但他既不爱人类的身体,也不爱人类的思想,他想留住的只是人类的种子。换句话说,其实他只是害怕死亡。韦斯顿虽然怕死,但他并不热爱生命;马拉坎德拉人虽然不惧怕死亡,但却热爱生命。狄凡的勇气是因为贪婪,韦斯顿的勇气只是一颗枯萎的心灵,只有兰塞姆的勇气才是对生命的真正热爱。兰塞姆在太空中看到深邃而未知的苍穹,想到地球浩瀚的历史,觉得自己的生命微不足道,这是一种敬畏,对大自然的敬畏。他觉得如果自己在这个天空中殒命,也是一种最完美的结局,“因为他相信那深渊里充满实实在在的、有血有肉的生灵”[4](208)。
[1] 布莱恩·奥尔迪斯, 戴维·温格罗夫. 亿万年大狂欢: 西方科幻小说史[M]. 舒伟, 孙法理, 孙丹丁, 译. 合肥: 安徽文艺出版社, 2011.
[2] 罗杰·奥斯本. 钢铁、蒸汽与资本: 工业革命的起源[M]. 曹磊, 译. 北京: 电子工业出版社, 2016.
[3] 雷蒙德·威廉斯. 文化与社会[M]. 吴松江, 张文定, 译. 北 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1.
[4] C.S.路易斯. 沉寂的星球[M]. 马爱农, 译.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11.
[5] 尼尔·波兹曼. 技术垄断: 文明向技术投降[M]. 蔡金栋, 梁薇, 译. 北京: 机械工业出版社, 2013.
[6] C.S.路易斯. 人之废[M]. 邓军海, 译.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5.
[7] 威廉·莫里斯. 乌有乡消息[M]. 黄嘉德,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5.
[8] C.S.路易斯. 天路回程: 对基督教、理性和浪漫主义的寓意辩护[M]. 赵刚, 译.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4.
[9] 卡尔·波兰尼. 新西方论[M]. 潘一禾, 刘岩, 译. 深圳: 海天出版社, 2017.
[10] C.S.路易斯. 返璞归真[M]. 汪咏梅, 译.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3.
[11] 约翰·德斯蒙德·贝尔纳. 历史上的科学: 科学革命与工业革命[M]. 伍况甫, 彭家礼, 译.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15.
On guard against the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rationality aiming at power and control Interpeting C.S.Lewis’ science fiction
PAN Yihe, ZHENG Xuying
(College of Media and International Culture, Zhejiang University, Hangzhou 310028, China)
is the first book of C.S.Lewis’ science fiction novels. It features Lewis’s poetic writing, which is of great literary value. This novel also has solid criticism on the ills of British industrial society and the scientism in the early twentieth century. With the excellent philosophical generalization, the author lets the three characters present the special position and role of scientists, capitalists and liberal art scholars in the modern society, and reveals the absurdity and cruelty under the seemingly reasonable society. In this very talented and imaginative novel, Lewis distinguished wisdom from science and technology knowledge which sought power and control, and pointed out that true wisdom can help mankind and Earth avoid being “lost” and go forward to the future universe.
C.S.Lewis; the space trilogy;; scientism
[编辑: 胡兴华]
2017−07−28;
2017−10−17
潘一禾(1959—),女,浙江杭州人,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世界文学;郑旭颖(1983—),女,浙江宁波人,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文艺美学
10.11817/j.issn. 1672-3104. 2018.01.025
I022
A
1672-3104(2018)01−0189−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