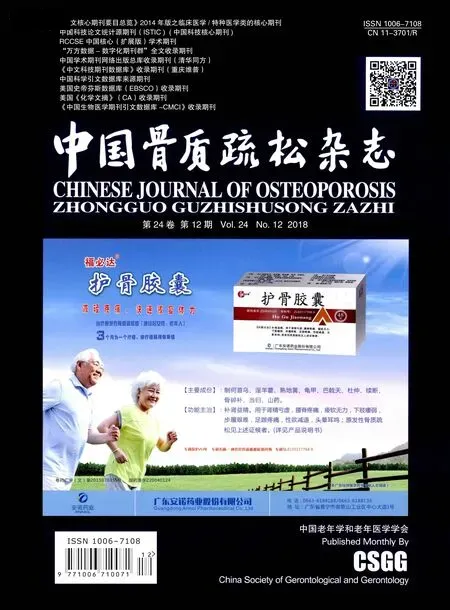肠道菌群对骨代谢影响的研究进展
陈晨 王邦茂 冯淑芝 王琳
1.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保健医疗部,天津 3000522.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消化科,天津 300052
人类体表及体内所寄居的微生物数量巨大,这些微生物在人体的生理活动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其中人体中最大的微生态系统当属肠道微生态系统,其微生物总数可达1014,而且其所携带的基因组是人基因组的150倍[1]。近年来,人们已经开始强烈地关注肠道菌群与人体健康之间的关系。肠道菌群除了在促进食物消化、产生维生素等营养物质、抵御外来致病菌侵入等方面有着重要作用之外,还影响着人体肠道以及免疫系统等的功能[2-3]。正常情况下,肠道微生态系统会保持相对的稳定状态,这种动态平衡对人体有益无害;但多种因素(如药物、酗酒、精神因素、胃肠道手术、放射治疗以及衰老等)可以将这种平衡打破,从而引起一系列疾病发生,包括多种肠炎、糖尿病、哮喘、肥胖、骨质疏松以及代谢综合征[4-6]。
骨质疏松症是与社会人口老龄化关系最为密切的疾病之一,是以骨量减少、骨组织结构退化为特征的一种常见骨骼疾病,其最大的危害就是骨质疏松性骨折。在骨质疏松的发病过程中,骨丢失起到了重要的作用[7-8]。目前,肠道微生态与骨代谢的关系已经成为世界范围内的研究热点,特别是近年来的研究发现,肠道菌群与人体的骨量降低及骨质疏松症的发病相关[9-11],这些微生物可能通过自身代谢产物、影响宿主代谢及免疫系统等途径来改变破骨细胞和成骨细胞的相对活性,从而影响骨代谢[12]。本文将对肠道菌群与骨代谢间潜在的关系进行综述。
1 肠道菌群与钙和维生素D
虽然遗传是骨峰值的主要决定因素,但后天的营养状况,特别是膳食中的钙摄入量,在整个生命过程中,对于骨的生长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13]。膳食中的钙是通过位于小肠上皮的钙通道,经过主动转运通过小肠而吸收入血液的,又通过被动运输分布到整个肠道。在以往的研究[14]当中发现,菊粉、低聚果糖和低聚半乳糖等作为益生元,可以通过增加双歧杆菌、乳杆菌及丁酸梭菌等益生菌的数量,促进分泌更多的短链脂肪酸,降低肠道pH值而提高了钙在肠腔内的溶解度,增加了机体对钙的吸收,从而增加了青年人群骨骼矿物质含量和骨骼矿物质密度[15-16]。
维生素D与骨代谢密切相关,对于钙的吸收也起到了至关重要的调节作用[17],虽然目前关于维生素D代谢与肠道菌群相互关系的研究还为数尚少,但是一些研究结果也显示了二者与骨代谢之间有一定联系。研究发现[18], Cyp27b1-/-小鼠不能生产1,25(OH)2维生素D3(维生素D的活化形式),并且经过葡聚糖硫酸钠的诱导之后,比野生型对照组出现了更严重的结肠炎。而在补充维生素D或者给予抗生素之后结肠炎得到了改善,说明维生素D的缺乏可以引起肠道炎症,从而引起了肠道菌群失调,使厚壁菌门(乳杆菌属、梭菌属等)比例减少,而变形菌门(大肠杆菌、沙门氏菌等)和拟杆菌门比例升高。
已经有文献[19]证实了维生素D可以通过作用于巨噬细胞、树突细胞、上皮细胞及T细胞发挥抗炎作用,它可以抑制炎症性肠病动物模型的Th1/Th17细胞,并诱导产生相应的Treg细胞。1,25(OH)2D3可以阻止树突细胞的成熟且不能诱导T细胞的活化,也可以减少巨噬细胞对TNFa和IL-12等炎性细胞因子的释放[18]。而在维生素D干预后,厚壁菌门的比例也得到了恢复。维生素D可能正是由于此作用稳定了肠道正常菌群,促进了小肠对钙的吸收从而影响骨代谢,这一机制值得深入研究。
2 肠道菌群代谢产物与骨代谢
肠道菌群中的某些益生菌(如乳酸杆菌、丁酸梭菌等)在自身代谢过程中会产生一些代谢产物,以短链脂肪酸为主。这些代谢产物除了具有抗炎作用外,也可能直接作用于骨细胞[20]。已经有研究[21]证实短链脂肪酸可以增加小鼠的骨密度及骨强度,而在一些病理状态(如炎症)下肠道益生菌的数量减少[18],导致了这些益生菌产生的短链脂肪酸减少,从而促进了骨质疏松的发病,不过该机制还需后续的研究加以证实。
一般来说,短链脂肪酸对宿主的调节主要通过抑制组蛋白去乙酰化酶、激活特定的G蛋白偶联受体及诱导自噬等几个方面来完成[22]。丁酸作为其中一种短链脂肪酸,可以直接抑制离体状态下破骨细胞的生长[23],但是对于这种抑制作用究竟是通过抑制组蛋白去乙酰化酶还是激活特定的G蛋白偶联受体途径来实现的目前尚不明确。
除此之外,短链脂肪酸还可以影响钙的吸收[24]。一方面,短链脂肪酸可以直接增加小肠的绒毛结构和小肠上皮的表面积,增加细胞旁途径的钙吸收及钙结合蛋白的表达,从而增加了小肠绒毛对钙的吸收。另一方面,短链脂肪酸也可以降低肠腔内的pH值[14],有助于提高矿物溶解度使钙更容易被吸收。
还有一些研究显示,血清素对成骨细胞有抑制作用[25],而肠道菌群中,一些微生物种类(如大肠杆菌及链球菌等)可以直接合成5 -羟色胺,而其他一些微生物种类(如芽孢杆菌及芽孢乳杆菌等)可以通过增加色氨酸羟化酶水平来调节5 -羟色胺前体—色氨酸的可用性[26]。因此可以推测,肠道菌群也可以通过血清素的代谢影响骨量[27]。
3 肠道菌群、免疫功能与骨代谢
骨骼的发育与重建是通过成骨细胞与破骨细胞实现的[28]。我们已知单核细胞是破骨细胞的前驱细胞[29]。
巨噬细胞集落刺激因子能够帮助单核细胞诱导分化为破骨细胞,并可以增加破骨细胞的活性。因此可以看出,局部微环境影响着单核细胞的分化方向。
骨代谢与免疫的关系比较明确,研究表明,一些与自身免疫相关发病过程中可以产生大量的由T细胞释放的炎性因子,而这些炎性因子可以导致骨量的丢失[30],甚至能够引起骨质疏松症。IL-17 A可以直接或间接的促进基质细胞中RANKL的表达,从而增加以及延长破骨细胞的存活。而干扰素-γ和IL-4可以抑制破骨细胞的形成,这种作用可能是通过细胞相关抗原通路实现的[31]。但关于T细胞对成骨细胞作用的研究尚少,而且其对成骨细胞的作用依赖于疾病的状态[32]。
已经有很多研究证实了肠道菌群与T细胞的调节与分化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肠内分节丝状菌作为一种小鼠的肠内定植菌,可以于回肠末端诱导血清淀粉样蛋白A,而后者具有促进Th17细胞分化的作用[33]。梭状芽胞杆菌也可以通过增加转化生长因子β(TGF-β)含量,促进小鼠Treg细胞的分化[34]。
有研究显示[35],无菌小鼠(肠道菌群缺乏)对于研究肠道菌群与骨量之间的关系起了重要的作用,其股骨远端骨量较正常小鼠有明显的上升,而且骨密度较正常小鼠有了明显的增加。但主要表现在骨小梁数量的增加与骨小梁间隙增宽,无菌小鼠骨小梁厚度较正常小鼠并没有改变。
通过对无菌小鼠的骨髓培养发现,无菌小鼠骨骼中破骨细胞减少,骨髓产生的CD4+T细胞与破骨前驱细胞也随之明显减少,而无菌小鼠骨形成速率较正常小鼠并没有改变,表明无菌小鼠骨量的增加主要是通过抑制破骨细胞的生成,从而减少骨吸收来实现的。而当为其种植正常肠道菌群之后,无菌小鼠的骨量便会降低到正常水平,CD4+T细胞和破骨细胞前体细胞的生成速率也会增加,这是由于没有肠道菌群作为抗原,从而血液及淋巴组织中CD4+T细胞数量少于正常小鼠,所以骨髓中CD4+T细胞形成率降低。这也进一步论证了肠道菌群对骨密度的影响与T细胞的调节与分化及破骨细胞生成减少密切相关[36]。
4 老年人肠道菌群变化对骨代谢的影响
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加剧,骨质疏松也越来越普遍,在不同性别的50岁以上人群当中,患有骨质疏松性骨折的患者比例分别是男性1/5,女性1/3[37]。虽然肠道菌群的种类个体差异很大,但老年人群肠道菌群的组成有了显著的变化,从专性厌氧菌为主变为兼性厌氧菌为主[38],而且致病性变形菌数量增多而抗炎的乳酸杆菌减少[7],从而导致炎症风险的增加。
成骨细胞和破骨细胞负责骨重建。而自身局部不同的微环境状态,可以对造血干细胞分化为破骨细胞或者是T细胞的过程产生影响。在炎症状态下,活化的T细胞可以介导破骨细胞的分化成熟[29],这说明老年人群肠道菌群的特征性改变,增加了骨质疏松的发病风险[39]。如此看来,对于肠道菌群成分的分析,似乎可以评估骨密度与特定细菌种属之间的关系,从而可以预测低骨量及发生骨质疏松性骨折的风险。
综上所述,肠道菌群对于骨代谢的影响是多方面共同调控的,无论是肠道菌群对宿主的钙吸收影响,还是菌群自身代谢产物、免疫反应及菌群组成变化等对骨代谢的影响,机制都是极其复杂的。因此对于肠道菌群的深入研究与分析,将有助于揭示其影响骨代谢的深层机制,甚至借此找到治疗代谢性骨病新的靶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