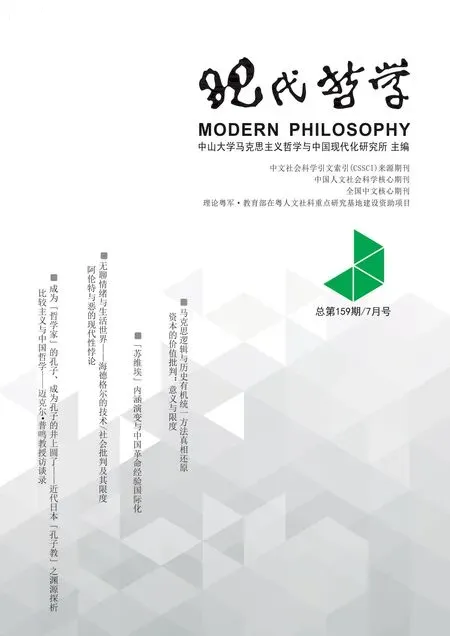论陈荣捷与余英时的朱熹“道统”诠释之异
郑秋月
从形上本体论到社会、政治、文化和思想史领域,朱子学研究者尝试以不同理路与方法诠释朱熹“道统”的微言大义。学者们在解释经典和研究立场上有诸多相似,如多以“道统”为朱熹之贡献,以师承关系来探讨“道统”之来源,以理解领悟、挖掘经典深层意蕴为理论旨趣。但在具体诠释视域及方法上,这些立场存在诸多不同,其中陈荣捷与余英时对朱熹“道统”的诠释之异尤为典型。陈荣捷以哲学形上学言说朱熹“道统”,将朱熹作为“道统”论集大成者及后世传续“道统”的内涵终结者;余英时从社会政治历史的角度宏观“道统”,将“道统”视为内圣外王兼收并蓄的助推器,视朱熹为“道统”确立的贡献者,但认为“道统”论并不止于朱子。
一、朱熹与黄幹*文中陈荣捷论述所涉及人物为黄榦,余英时论述的人物为黄幹,实为同一人。 :谁为“道统”确立者
朱熹是不是“道统”论集大成者,后世所传“道统”是否由朱熹最终完成,这是最受关注、也颇有争议的问题。依陈荣捷之见,道统观念由来已久,虽在历史演进中几经变易流转,但真正揭示古今道统之真谛、系统完整建立“道统”说乃有赖于朱熹的掊击之功。陈荣捷给出的具体解释是,朱熹对“道统”认知与诠释的主要路向是通过对文本内容考证分析以推究证成。如朱熹承认在他之前已有李元刚在《传道正统图》中使用过“道”“统”二字,并大致勾勒出由尧、舜、禹、汤、文武、周公至孔子,经颜子、曾子、子思、孟子以至二程的理路。然而,朱熹认为理解不能脱离文本、诠释亦不能过度,强调李元刚虽言及“道”“统”,但二字并未做连词使用。在一定程度上字与字的分离不单纯是文本内容的呈现,更是一种彰显不同义理与内涵的手段。这样的表述不足以证明李元刚所言为“道统”之源。朱熹以相同方式判别朱震所言:“臣窃谓孔子之道传曾子……子思……孟子。孟子以后无传焉。至于本朝……程颢、程颐传其道于千有余年之后……良佐之贤亲传道学,举世莫及。”*[美]陈荣捷:《朱子新探索》,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287—288页。通过逐字逐句分析言辞与意涵,可知朱震所言亦只是“道学”,而非“道统”。这样看来,以往圣贤大多只是在对历史流变的描述中意兴所至而有所感发,并非刻意追求“道统”之统摄,如随意疏解,难免会有比附穿凿之嫌。
盖自上古圣神继天立极,而道统之传有自来矣。其见于经,则“允执厥中”者,尧之所以授舜也……若成汤、文、武之为君,皋陶、伊、傅、周、召之为臣,既皆以此而接夫道统之传,若吾夫子,则虽不得其位,而所以继往圣、开来学,其功反有贤于尧、舜者……孟氏为能推明是书以承先圣之统,及其没而遂失其传焉……程夫子兄弟者出,得有所考,以续夫千载不传之绪……盖子思之功于是为大,而微程夫子则亦莫能因其语而得其心也。*[南宋]朱熹:《四书章句集注》,朱杰人、严佐之、刘永翔主编:《朱子全书》第6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29—30页。
在此,朱熹三次谈到“道统之传”,认为“道统”是儒家传道的统序,赞同由孟子首倡传授“道统”,尧、舜经成、汤、文王至孔子,韩愈重申孟子之绪,宋儒延续韩愈之说,伊川首倡其兄明道得不传之学于遗经的基本理路。如此,陈荣捷得出结论,“道统”观念得以全貌呈现并世代相传,毫无疑问归功于朱熹。他还列举宋元明清诸多有影响的言论,佐证朱熹所言“道统”在后世如日中天:
欧阳元(1238-1357) 以许衡(1209-1281)“上接周公孔子曾思孟轲以来数君子之道统”。数君子者,指周程朱。明儒薛瑄(1389-1464)所谓许氏“继程朱之正传”是也。薛瑄又云,“至宋二程朱子,既有以接孟氏之传”。胡居仁(1434-1484)则曰“程子遂扩而大之,朱子又集而全之”。康熙帝命李光地(1642-1718)编修《朱子全书》(1714)与《性理精义》(1715),御制序有谓“朱子集大成而绪千百年绝传之学”。李氏进表则曰,“朱子得四王之师承”。如是宋元明清一贯流传,已成公论。*[美]陈荣捷:《朱熹》,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年,第216—217页。
不仅如此,陈荣捷以记载朱熹及弟子的诸多史料为佐证,言明朱熹本人以继承道统自任的态度极为明显。《大学章句序》云:“河南程氏两夫子出,而有以接孟氏之传……虽以熹之不敏,亦幸私淑而有闻焉。”*同上,第216页。《告先圣文》曰:“熹以凡陋,少蒙义方,中靡常师,晚逢有道。”*同上,第216页。朱熹比较含蓄地表达了自己是道统传续之人。其弟子则对此确信不疑,站在拥护其师的立场上纷纷著述以巩固朱熹地位,使朱熹的态度更加明朗。黄榦在《圣贤道统传授总叙说》中云:“先师文公之学,见之《四书》,而其要则尤以《大学》为入道之序……此又先师得其统于程者也。”*[清]黄宗羲著,全祖望补修,陈金生、梁运华点校:《宋元学案》,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2023页。又在所撰《朱文公祠记》中强调:“周程张(张载)子之道,文公朱先生继之。此道统之传,历万世而可考也。”*[美]陈荣捷:《朱熹》,前揭书,第216页。同门陈淳亦言:“‘于是濂溪(周子)先生与河南二程先生,卓然以先知先觉之资,相继而出……朱文公即其微言遗旨,益精明而莹白之’。同门李方子(1214进士)亦云,‘先生身任道统’。”*同上,第216页。总之,依陈氏之见,朱熹在首创“道统”一词后,以儒家“道统”继承者自任,创新并完成了“道统”的建构,成为后世“道统”论的集大成者。
与陈荣捷相比,余英时在《朱熹的历史世界——宋代士大夫政治文化的研究》一书中明确交代自己将反其道而行,颠覆朱熹是“道统”论正式建立者和道学集大成者的“通常理解”,并做好被视为轻重倒置、喧宾夺主、受人质疑的准备。此番言论引起极大关注。余英时对朱熹“道统”的诠释到底有何不同,使其直言自己另辟蹊径?最明显的例证之一是:
遍检南宋文献,朱熹的大弟子黄幹才是后世“道统”观念的正式建立者。他的《圣贤道统传授总叙说》(《勉斋集》卷三)一方面发挥《中庸序》的主旨,另一方面则径以“道统”两字统合原《序》“道统”与“道学”两阶段之分,上起尧、舜,下迄朱熹,一贯而下。这样一来,“道统”的涵义改变了,它不再专指朱熹构想中的内圣外王合—之“统”或陈淳所谓“道学体统”(见《北溪大全集》卷一五《杂·道学体统》条);这正是后世通行之义。*余英时:《朱熹的历史世界——宋代士大夫政治文化的研究》,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1年,第15—16页。
余英时以为,朱熹正式界定“道统”一词见于《中庸章句序》,此与陈荣捷观点无异。但他强调,朱熹虽是“道统”论的正式提出者,但宋以后流行至今的“道统”论并非出自朱熹,而是由其弟子黄幹完成,黄幹在嘉定七年(1214)所撰《徽州朱文公祠堂记》中,已十分清楚地表达了“道统”的新义:
李离说:“昔年须菩提大师找孙悟空,弘忍大师找惠能,都是这么干的啊,米熟久矣,犹欠筛哉,提醒我们几个,三更天等您回来啊!要是我们没有认出您的花间游跟翡翠镯子,听吴耕的话,也骑驴子走了,您这半个月做掌柜的工夫岂不是白瞎了?”
道原于天,具于人心,著于事物,载于方策:明而行之,存乎其人。(中略)尧、舜、禹、汤、文、武、周公生而道始行;孔子、孟子生而道始明。孔、孟之道,周、程、张子继之;周、程、张子之道,文公朱先生又继之。此道统之传,历万世而可考也。*同上,第16页。
可见,黄幹继承了朱熹关于“道统”与“道学”的基本观点。“行”指朱熹所谓“道统”,“明”指所谓“道学”。黄幹发展其师观点,将“道统”“道学”归一,进一步彰显朱熹“道”尊于“势”的观念。依余英时的理解,朱熹与黄幹谁才是后世“道统”观念的正式建立者,是一个值得深入探究的问题。朱熹对“道统”一词的提出确有不可磨灭之功,但黄幹继承并发展其师理论,整合“道统”与“道学”,使其师首创但并未明晰意义的“道统”观念最终确定并得以普遍化、系统化。余英时未因朱熹名声显赫而将“道统”确立之功勉强归之,而是看到黄幹在后世“道统”传承中的点睛之笔,认为黄幹在不牵强附会的基础上将自己的思想赋予“道统”以新诠释,其目的是为提高其师朱熹的地位和影响。
为何陈荣捷与余英时在后世“道统”最终成于谁的问题上有此差异?通过各自诠释呈现出的理论特质,可作如下分析:
其一,陈荣捷晚年学术关注点集中在朱熹研究,曾作诗云“写作唱传宁少睡,梦也周程朱陆王”*[美]陈荣捷:《王阳明与禅》,台湾:学生书局,1984年,第238—239页。。他肯定朱熹在宋明理学及“道统”建构过程中的作用和影响,认为后世“道统”的确立与流传理应归功朱熹。与此相比,余英时认为“道统”在孔子以前的圣人那里业已存在,后来“内圣”“外王”分离后,需要有人通过“道学”将古往圣贤之“道统”传续下去,孔子正起到这个作用;朱熹所提“道统”并非古圣贤之“道统”,而是继承孔子“道学”之“新道统”;而后其弟子黄幹辨明事理,将“道学”“道统”分判离析,才将后世“道统”内涵最终定下;故朱熹有功于“道统”之提出,但不应把全部功劳归于朱熹。可见,陈余二人对待朱熹“道统”问题存在个人情感色彩差异。
其二,陈荣捷继承朱熹“六经注我”的方法,诠释重点不止于朱熹文本,试图确立和巩固朱熹在儒家道统传承中的地位。有学者评价陈荣捷既是一位创造者,也是一位传播者。此言有待商榷,但可见陈荣捷偏爱朱熹研究的学术旨趣。在陈看来,朱熹正式提出“道统”并创造性诠释,赋予“道统”以哲学意义,使其称得上“道统”集大成者。与之相较,余英时认为后世“道统”的核心思想最终由黄幹在朱熹“道统”论基础上完成,不能将主要贡献归功于朱熹一人。从某种意义上讲,余英时是从社会政治历史出发,注意到朱熹、黄幹等人是具有“使命感”和“政治、社会关怀”的儒者,剥离出他们寄希望于“道统”以全面重建新秩序的目的。余英时意识到黄幹的“道统”论既肯定朱熹“道统”论之实质,又在整合“道统”“道学”基础上更完备,所以二者各有其特定价值,不可从师徒角度做主次排序。
二、哲学特质与政治旨趣:“道统”释义的路径之殊
陈荣捷认为朱熹是“道统”论集大成者,在后世“道统”传承过程中占据重要位置。他通过对朱熹文本解读,知晓“朱子之维新,共有五端”*[美]陈荣捷:《朱子新探索》,前揭书,第287页。,即首次使用“道统”之名词、以哲学思想充实“道统”、上溯伏羲、添加周子、本人承继道统,其中尤以哲学思想充实“道统”、赋予道统以新面目为重。他认为朱熹以哲学思想充实“道统”,自此使“道统”成为哲学范畴,“此诚是破天荒之举。纵是武断,不害其为新观念也”*同上,第289页。。在他看来,朱熹对“道统”的维新,归根结底是整个新儒学系统建设需要,只有赋予“道统”以哲学思想才能夯实其理本论的哲学根基;而且朱熹以“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尚书·大禹谟》)十六字诠释“道统”,使“道统”具有确定的哲学意义。
朱熹在“道统”上的诸多维新,并围绕理本论哲学体系建构具体展开,其线索是从尧舜溯至伏羲。陈荣捷从朱熹著作中找到多处侧重讲伏羲的文字记载,如“此伏羲、神农、黄帝、尧、舜,所以继天立极”“道统远自羲轩,集厥大成”“先生(二程)之道,即伏羲、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孟之道”*同上,第289页。。这是朱熹扩充道统谱系以建构哲学体系的主动择取,他在尧舜禹汤之上增加伏羲,显然是想通过由相传伏羲所画之“八卦”牵引出《易》之所言“太极”,环环相扣将打通理气关系所需的“太极”观念提升为新的诠释中心。
陈荣捷指出,朱熹引入“太极”概念以完备其新儒学进而建构理本论,将朱熹把接续“道统”的桂冠赋予周敦颐、并将其纳入“道统”传授之列的必要性清晰勾勒出来。“先生(周子)道学渊懿,得传于天。上继孔颜,下启程氏”,“两程之绪,自我周翁”,“及先生出,始发明之,以传于程氏”*同上,第289页。等。在他看来,朱熹之所以在尊奉二程之外首推周敦颐,不惜摒弃其师李侗、排除汉唐诸儒、旁置邵子张子,看似只是“道统”传授系统改变,实则是朱熹毕生为建立以“理”为核心的哲学系统所作的努力。朱熹理本论哲学体系的建立,需要用“道统”来支撑;为厘清理气关系,需采用“太极”之说。朱熹因二程虽言“理”却不言“太极”而弃之,因周敦颐著《太极图说》而宏之。朱熹在二程之前加上周子,更注《太极图说解》以固其理,其以周子“太极”思想为重之动因乃明。至于李侗、邵雍、张载等对理本论哲学建构并无助力,且他们所言与理本论存在分野,这是朱熹不愿认可并予以摒弃的原因。
总之,朱熹以哲学思想充实“道统”、上溯伏羲、添入周子,皆为成全其理本论哲学体系。朱熹维新“道统”之贡献,亦由其理学建构而来,绝非偶然。因而,陈荣捷对朱熹“道统”的诠释,以朱熹哲学、理气学说为切入点,所言道统“非历史性或经籍上之系列”。
与之相比,余英时从社会政治历史角度独辟蹊径诠释“道统”。他在《朱熹的历史世界》自序中提醒读者,在实际的历史过程中,文化史和政治史的发展是交织在一起的,不可能清楚分开,二者统摄于士大夫的整体活动中。*余英时:《朱熹的历史世界》,前揭书,自序第1页。在陈荣捷呈现朱熹“道统”哲学特质后,余英时进一步追问,朱熹为什么要大费周章地去建构理学体系,难道仅仅是为纯粹儒学谱系传承抑或理学集大成者之虚名?余英时认为并非如此。他说通常做法是将朱熹“道统”论与“政治文化”关系做疏离处理,认为朱熹的历史世界只能以“道统”与“道学”为中心,“政治文化”不过居于边缘地位;但依据史料并辅以对“道统”“道学”“道体”问题的厘清,朱熹“道统”论内蕴的政治、学术和思想复杂交织的历史状况是能够呈现出来的。
余英时通过朱熹“道统”一词用法的前后比照,以察演变之迹。他认为最早在淳熙八年《书濂溪光风霁月亭》中,朱熹就谈论过“道统”,但涵义未定。正式界定“道统”一词是《中庸章句序》,并在晚年之作《沧州精舍告先圣文》中再次确认。朱熹所言“道统”“道学”有明显差别,即“外王”与“内圣”的分辨。朱熹言“道统”,是指伏羲、神农、黄帝、尧、舜、禹到周初上古圣贤相传的正道。传道者皆是兼具“内圣”之德与“外王”之才的圣人君主,因此有资格“继天立极”以传授“道统”,统治天下。自周公以后,君主背离正道,内圣与外王不复合一。孔子虽贤于尧、舜等人,但因未得到君主之位,惟有走上“继往圣、开来学”的新路。朱熹所言“道学”指孔子或子思而言,并非与上古圣贤所传“道统”同义。
余英时倾向于从“道统”“道学”皆具深刻政治意涵的视角进行诠释,通过社会历史性分析,将朱熹宋代士大夫身份呈现出来,认为其所言“道学”(或“理学”)不仅在中国儒学史上有突破性成就,其政治旨趣更显而易见。透过社会政治历史分析,他认为朱熹“道统”与“道学”虽有差异,但共同基调皆为抬高“道统”与“道学”的精神权威,用“道”来规范“势”,其积极方面是引“势”入“道”,消极方面是持“道”批“势”,这也是宋代理学家共同寻求的长远目标。
三、理学家与士大夫:朱熹身份理解之殊
陈荣捷对朱熹“道统”的诠释主要集中在哲学层面,究其根本是将朱熹的身份确定为理学集大成者,认为朱熹“道统”是理学发展、新儒学系统建构与维新的点睛之笔。换言之,他是以中国哲学家身份关注并研究朱熹的,“以朱言朱”,将朱熹的哲学义理融入自己生命之中,以“互为主体性”方式思考与诠释。一方面,这既可使朱熹“道统”论由理学体系建构的需要而彰显重要哲学价值;另一方面,亦可使人们通过自身对“道统”论解读来体悟其深入研究中国哲学的理论实践。
为突出朱熹“理学家”身份,陈荣捷对经典诠释理路进行精心设计。他首先引周敦颐入“道统”传续之列,突出《太极图说》的重要作用:“朱子以后,《图说》遂为理学之基石。《近思录》以之为首。以后《性理大全》与《性理精义》等书,无不皆然。”*[美]陈荣捷:《朱熹》,前揭书,第44页。他认为朱熹此番设计旨在证明周敦颐《太极图说》所言“太极”概念对理学体系建构的功用。“太极”的重要性何在?陈荣捷认为,理是朱子哲学的中心思想,理必搭于气而行,非太极则理气之关系无从厘清。《语类》云:“太极只是一个理字。”他明确指出朱熹重视“太极”概念的关键在于哲学系统建立之需。从朱熹的设计可见,其表扬周敦颐《太极图说》并予以重要地位的原因在于使“太极”成为新儒学哲学之基石,“实以一种具有逻辑性综合性有机性之新儒家哲学系统,不能无此观念也”*[美]陈荣捷:《朱子新探索》,前揭书,第149页。。
朱熹之所以大费周章地引入“太极”观念,主要是为了解决理气关系问题,更深层次缘由是解决作为本体的理的问题并塑造新儒学体系。陈荣捷指出:“有如朱子所释,极者至极也,因而太极为事事物物之极致。更明确言之,太极是理之极致。因之,朱子以太极即理。”*同上,第149—150页。太极即理,这是朱熹导引新儒学步入理之路向的探索与实践。“太极”观念的引入,太极同于理的思想,使形而上与形而下、理与气、一与多等诸多关系得以厘清,朱熹理本论建构问题得以解决。故周敦颐“太极”观念是理解朱熹哲学之关键,而朱熹太极即理的创见,是新儒学为理学发展的必需。朱熹道统论致力于哲学性努力之目的不言自喻,这也使陈荣捷所言朱熹理学集大成者身份得以确认。
与陈荣捷不同,“道统”在余英时那里不再与“政统”截然两分,他认为朱熹思想中的社会政治关怀是首要的,其“道统”有明显政治色彩。这一思路主要源于对朱熹士大夫身份的确认。在《朱熹的历史世界》中余英时开篇名义:“他之所以能从容发明义理、注释经典、兴建书院,或由于得奉祠禄,或由于出任郡守,无一不是凭借着士大夫的身份。以精神造诣与学术成就而言,他自然远远超过了一般的士大夫。然而超过并不等于跳过;若跳过士大夫这一身份不论,他的历史地位便反而不可理解了。”*余英时:《朱熹的历史世界》,前揭书,绪说第4—5页。余英时从社会政治历史审视朱熹“道统”,着力再现宋代士大夫的政治文化。他认为朱熹等儒者的主体精神在宋代已充分觉醒,开始关注世道人心,并以“文以载道”的方式关注现世,表达其理想性关怀与超越性追求。以朱熹为代表的一批士大夫认为自己的言论理应成为“得君行道”的精神支柱,试图借助王权的力量实现自己的人生理想。
余英时以士大夫之代表朱熹与陆九渊为例,认为超越朱陆之间“理”与“心”形而上之本体的差异,他们在作“致君行道”的努力时所采取的论证方式非常相似,都是将“道统”与“政统”直接挂钩,可谓“殊途同归”。在余英时看来,朱熹的角色只是当时政权巩固和发展的一个工具,如果没有他,统治者同样会选择其他人的类似理论来巩固政权、维护君权。至此,余英时所言朱熹的士大夫身份不言自明。
四、结 语
“道统”在儒家内部始终代表着一种明确的归属感,彰显了对儒家学说及价值理想的自觉认同与传承、对古圣先贤的自愿尊敬与推崇。在看待陈荣捷与余英时对朱熹“道统”问题“所同不胜其异”的主体诠释及最终结论时,必须清楚意识到,二人对“道统”在朱熹思想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的肯定皆不容置疑,但二人最终选择以不同的体悟与验证方式来引起思想上的碰撞,通过多维视域下的理论思考使诠释空间得到进一步拓展,对探究历史问题颇具启发性。陈荣捷从哲学视域理解并诠释朱熹“道统”,余英时从社会政治历史角度审视并考察朱熹“道统”,在各自去取标准之下,自然得出不同结论。
陈荣捷通过明确的哲学立场,肯定朱熹“道统”之哲学形上学的义理阐发之功,夯实朱熹在“道统”传承过程中的理论积淀,加固其在后世“道统”确立中的重要作用与不可替代的地位。余英时通过崎岖曲折、特立独行的史学立场,捕捉朱熹“道统”背后的政治关怀与史学预设,揭示朱熹连同整个士大夫群体所追求的“内圣外王连续体”及以秩序重建为归宿的题中之义。故“理念世界中的哲学家”与“权力世界中的理学家”皆可成为定义朱熹身份的“代名词”。从学术研究的视角来看,研究者或诠释者在实际操作中不时注入含蕴其学术背景、心路体验、表达方式等承载弦外之音的活水,对认识水平的提升和传统论题的新解大有裨益。
陈荣捷与余英时将朱熹“道统”问题纳入诠释学,加深了经典诠释不只是单纯彰显义理表象的手段、归根结底是一种诠释者自身对经典之内容“切己应用”的认识。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样的理解绝非是一种以文字解读为中心考据“一词一义”的活动,而是致力于在深层次上唤醒并调动主体的体悟,通过多维视域拓展意义世界与价值境域的活动。正如伽达默尔曾提出的观点所示:“真正的历史对象根本就不是对象,而是自己和他者的统一体,或一种关系,在这种关系中同时存在着历史的实在以及历史理解的实在。”*[德]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洪汉鼎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9年,第384页。显然,陈荣捷与余英时对朱熹“道统”的不同诠释,体现了朱子学研究的新视野与新方法。这种既“照原意”又“返本开新”,既追溯哲学内蕴与史学关怀,又突破习惯预设与固化思维的差异性诠释,不存在高低优劣之分,都是探究历史的实在与历史理解的实在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