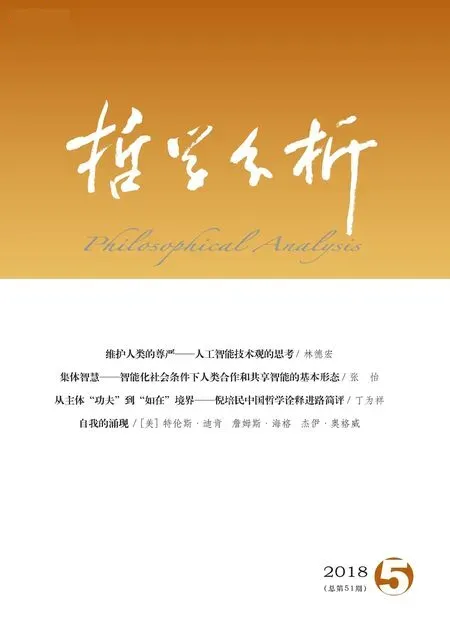从主体“功夫”到“如在”境界
——倪培民中国哲学诠释进路简评
丁为祥
一、“功夫”:主体性的回归
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倪培民先生即在西方传统哲学框架之外另开“功夫论”的领域。①倪培民先生自述说:“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我和其他一些大致在相同年代出国学哲学的人开始在西方大学里任教,也相继走上了精神的‘海归’之路,无论是研究的方向,还是我们讲授的课程,都开始转向中国古典哲学与中西方哲学的比较。” (倪培民:《孔子:人能弘道》,中译本补记,李子华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笔者这一看法即是在倪先生自述基础上一个可能性的推论。就是说,由于其在美国大学讲授东西方比较哲学的课程,因而他在不断地摸索如何引导西方人对中国哲学能有一种较为恰切的理解与把握。与此同时,他也在不断地摸索如何才能对中国哲学进行一种恰如其分的表达。所谓“功夫论”研究,在倪先生看来,大概也就可以说是一种比较接近中国哲学本来面目的进路吧。
为什么要从“功夫论”的进路把握中国哲学?由于倪先生主要讲授东西方比较哲学的课程,因而东西方理性之不同表现以及其不同的研究进路必然是其首先要面对的问题;而如何以接近其本来面目的方式对东西方哲学进行较为客观的介绍,也必然是其不得不面对的问题。这样,“功夫论”的视角及其领域,也就成为倪先生对于中国哲学之一种特殊的引入方式了。这说明,在倪培民看来,“功夫论”不仅有别于西方哲学,而且也有益于对中国哲学及其特殊进路的理解与把握。
显然,所谓“功夫论”进路,首先是对中国哲学之外的“他者”而言的,也是针对“他者”所设定的一种有别于其传统理解路径的进入方式。就是说,在倪先生看来,必须以“功夫论”的路径才能真正进入并理解中国哲学。但是,考虑到倪先生原本就是中国学者,而且也是以中文学者的身份在西方讲授中西方哲学比较课程的,因而这一原本根据“他者”之理解需要所设定的路径同时也就成为其在中西哲学比较基础上对于中国哲学及其特殊进路的一种揭示与阐发 了。
正因为“功夫论”研究的这一特点,倪先生又专门撰写了《什么是对儒家学说进行功夫的诠释?》一文,以说明其倡导“功夫论”的具体因由。其内容主要包括如下几个方面:“功夫解读意味着把儒家学说当作修齐治平的功法指导,而不是描述世界的理论系统”;“功夫解读意味着儒家学说的最终目的在于达到艺术人生的能力,而不是对人生作出道德规范”;“功夫解读意味着儒家经典中的许多言语需要从语用的角度去解读,而不是只看字面的意思”;“功夫解读意味着儒家经典的内容必须要通过修身实践才能充分理解”。通过以上四个方面的正面陈述与三个方面的明确否定,诸如“不是描述世界的理论系统”“不是对人生作出道德规范”等,说明所谓“功夫论”主要是针对中国文化之“他者”而言的。至于其对“功夫论”的正面规定,诸如“修齐治平的功法指导”“达到艺术人生的能力”“需要从语用的角度去解读”以及作为其正面总结的“功夫解读意味着……必须要通过修身实践才能充分理解”,又说明倪先生关于“功夫论”的正面规定及其总体上的“修身实践”特色。从这几个方面来看,倪先生对“功夫论”的正面规定无一不是从对中国传统经典及其基本精神的揭示出发的。①倪培民:《什么是对儒家学说进行功夫的诠释?》,载《哲学分析》2013年第2期。这说明,所谓“功夫论”并不仅仅是针对中国文化之“他者”而言的,同时也包含着倪先生的文化比较视野以及其对文化母体之基本特征的充分自觉。
在此之前,倪先生还有《将“功夫”引入哲学》一文,该文曾以英文缩减版的形式刊发于《纽约时报》,后又以较为详细的阐发分别刊发于《南京大学学报》2011年第6期与香港《中国哲学与文化》学刊第十辑。这说明倪先生对“功夫论”的研究并不仅仅是针对中国文化之“他者”而言的,而是对中西方哲学之共识而言的,当然也可以将其理解为代表中国学界对于世界哲学的一种建言。②倪培民:《将“功夫”引入哲学》,载倪培民:《孔子:人能弘道》 (附录二),第174—196页。从一定意义上说,这也是倪先生针对中国学界关于中国哲学“合法性”讨论的一种表态,认为中国哲学不仅应当肯定自己的“合法性”,而且应当从关于中国哲学的“合法性”讨论走向具有“立法者”意义自觉的表现。
在《将“功夫”引入哲学》一文中,倪先生对其“功夫论”展开了进一步的论说,比如该文一开篇就指出:“研究儒学的学者一般都承认,儒家学说的基本关怀不是追求对客观世界的认知,而是追求成人成己的生活方式。”③同上书,第174页。而在第一节的末尾,倪先生又申明说:“本文的宗旨,就是提倡将中国传统的‘功夫’概念引入哲学,以此为突破口,来摆脱那个两难困境——只有在那拓宽了的、也是更加合理的‘哲学’概念之下,中国哲学才既不用削足适履,也不会总是游离于哲学之外。”④同上书,第176页。很明显,这既是倪先生在对中国哲学尴尬处境认真分析基础上所提出的一种摆脱困境的思路与方法,同时也可以视其为以“功夫论”研究代表中国学界对于世界哲学的建言与发声。
在该文中,倪先生不仅以“功夫论”研究展开对儒学历史发展的系统梳理,同时也展开了与西方哲学的多方面比较。比如关于“功夫论”研究与传统儒学基本精神的关系,倪先生指出:“从‘功夫’概念出发,可以防止我们将实践或行为简单地看作是由主体的自由意志决断的结果,看到有效行为的根源不是抽象意义上的行为者,而是具备特定能力或功夫的行为者。它与主体的紧密联系直接导致了宋明理学中‘即本体即功夫’的命题及由此而来的对此命题的各种探讨和诠释。”⑤同上书,第180页。而在详细比较“功夫论”与儒学发展之各个历史阶段的特色后,倪先生总结说:
……功夫是一个三维合一的概念。从“功力”的角度看,功夫是本体的性质,是通常需要长时间修炼、有恰当方法指导而获得或者开发、彰显的才艺、能力。从“工夫”的角度看,功夫是有恰当方法指导,为了获得才艺、能力而进行的实践修炼。从“功法”的角度看,功夫是为了获得才艺、能力而进行长时间实践修炼的方法。如果硬要为这个三维合一的概念本身下一个简单的定义,也许只能说功夫是“生活的艺术”。①倪培民:《将“功夫”引入哲学》,载倪培民:《孔子:人能弘道》 (附录二),第181页。
从“功力”“工夫”与“功法”三维合一的角度讨论“功夫”,自然可以说是从中国哲学角度对“功夫”的一个总论;而“三维合一”的规定,又说明其所谓“功夫”必须是主体资质、修养基础以及才艺、能力表现的一个综合指标。至于倪先生在此基础上展开的与西方哲学的多重比较,自然是希望将源自中国传统的“功夫论”作为中西方哲学相互沟通的一种中介与桥梁来运 用。
但对倪先生关于“功夫”的这多重论说,笔者这里暂时只能用一个“主体性”来概括,并以实践追求作为其基本规定与总体指向。因为这里的“主体”,虽然是以儒家士君子为实际指谓的,但也必然包含着道家建立在人的“天性”基础上的自然主体。因为作为“功夫”主体的只能是人;而作为“功夫”追求指向与具体指标的实践以及其所含括的“才艺、能力”包括体现人之灵性的所谓“功法”“悟性”等,又是儒道两家所一致通用的。就是说,倪先生的“功夫论”实际上是在儒道通用、儒佛道三教融合基础上所提出的中国文化修养的一种 “共法”。
不仅如此,在倪先生关于“功夫论”的阐发中,英国的经验论、西方的分析哲学以及被国人称为“实用主义”的美国哲学,也都出现在倪先生的论说中。当然,倪先生的许多论述,首先是从对“功夫论”的特征及其与西方古希腊以来的认识论传统以及近代以来的伦理学传统相区别的基础上展开的。但这种区别,恰恰建立在对二者不同特点的认识、比较的基础上。就是说,虽然倪先生以与西方哲学相区别的方式展开“功夫论”的研究和阐发,但这种比较以及对双方不同特色的揭示又说明其“功夫论”是在与西方哲学相区别的基础上对于中国哲学总体特征的一种明确揭示,当然也可以说是对西方哲学这位“他者”提出了一种与自己传统相区别的理解方式与从入之途。②倪培民:《阳明心学的功夫伦理与价值重建》,载《孔学堂》2017年第1期。另外,在最近召开的“中国传统功夫论与功夫哲学”研讨会上,倪先生又撰写了《从功夫论到功夫哲学》一文,其从“哲学的功夫转向”一直谈到“功夫论的哲学转向”,这说明倪先生是试图将“功夫哲学”作为一种中西方可以相互沟通的中介或共通性哲学来定位的。这样一来,我们也就可以中国哲学的主体性及其实践追求精神来归类、概括倪先生关于“功夫论”的倡导 了。
二、“如在”:境界性的还原
正因为倪先生的“功夫论”是以主体性的实践追求为特征的,因而它也必然要面临整个中国哲学的一个共同指向,这就是“如在”或“如在主义”。
关于“如在”,倪先生首先是通过孔子的“祭如在,祭神如神在” (《论语·八佾》)来阐发的。而孔子关于“祭神如神在”的规定,也表明其“神在”首先是由主体“祭如在”的心态决定的,就是说,这里的“神在”,既不排除也不否定其客观的“在”与“不在”,因为所谓“在”首先是对祭祀主体而言的,是以其真诚的“祭”,从而才导致了这种“在” (就客观而言,它有可能在,也有可能不在);但对主体之“祭”而言,它却是一种真切而又真实的“在”。很明显,这里的“在”首先是对作为祭祀者的主体精神而言的。由于它既不排除也不否定客观的“在”,而仅仅是从主体之精神感受出发的,因而从客观的角度看,也就只能说是一种“如在”。
但对主体而言,它不仅是一种“如在”,而且就是一种非常真切的“在”。那么,对这个“如在”究竟应当如何把握呢?倪先生 说:
“祭神如神在”既非有神论,亦非无神论,更不是怀疑论或者不可知论。它关注的焦点不在于神是否真的存在,因而也不是对神的信仰,而是人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态度和方式去参加祭奠,去进行精神性的活动。①倪培民:《儒学的精神性人文主义之模式:如在主义》,载《南国学术》2016年第3期。
显然,所谓“如在主义”关键也就在于“如在”一点上,这无疑是对主体而言的,也是对主体之精神感受而言的“如在”。正因为这一点,所以“如在”“关注的焦点不在于神是否真的存在……也不是对神的信仰,而是人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态度和方式去参加祭奠,去进行精神性的活动”。就是说,无论“如在”是“在”还是“不在”,都不是一个客观性的认知问题,而是一个主体性的精神感受问题,是其主体精神之感受使“神”成为一种“在”。②倪培民对孔子的“祭如在”分析说:“鬼神本身的在场与否已经不是关注的重点,重要的是在祭鬼神的时候要当作鬼神就在场一样表示虔敬。换句话说,在他(孔子)那里,重要的是献祭者自己的在场:‘吾不与祭,如不祭’。” (同上)所以,在该文的“摘要”中,倪先生便强调说:“‘如在主义’所关注的焦点,不在于神是否真的存在……而是人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态度和方式去参加祭奠,去进行精神性的活动。经过孔子的这个转折(“祭如在”),一方面,人与鬼神的外在关系变成了人本身与他的精神状态的内在关系,于是人人可以成为鬼神之德的主体;另一方面,通过将原先主要指祭礼的礼拓展到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去,于是事事可以是礼的实践。从如在主义的态度出发,儒家形成一个从人世间开发出精神性的传统。”①倪培民:《儒学的精神性人文主义之模式:如在主义》。
从这些论述可以看出,“如在”所标志的并不是一个客观性的“在”,而是对于主体精神而言的“如在”。实际上,这一点也可以印证于其前边提到的“研究儒学的学者一般都承认,儒家学说的基本关怀不是追求对客观世界的认知,而是追求成人成己的生活方式”。“如在主义”之所以“不是追求对客观世界的认知”,首先就在于其所看重的并不是客观的“在”与“不在”,也不是客观性、对象性基础上的认知问题,而是在主体精神外向投射与观照下的“如在”。②关于“如在”,倪先生解释说:“‘如在’却又不是鬼神本身之自在,而是献祭者的主体状态,所以它与自在的鬼神拉开了距离……换句话说,‘祭如在’反映出的是儒家的精神人文主义……” (同上)就是说,所谓“如在主义”,既不是一个客观的“在”与“不在”的问题,也不能从客观的对象认知的角度来理解。
那么,这个“如在”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在”呢?倪先生通过对《中庸》“天命之谓性”以及儒家“诚之”之道的分析清楚地说明了这个“如在”的具体含义:
虽然作者(子思)没有直接去描述那个“性”是什么,但他告诉人们,通过其功用或功效,人们能够迂回地知道,那个性就是能够使人们最终“发而皆中节”的潜力。虽然这种内在的可能性似乎藏得很深,但它也是最最明显地摆在人们面前,是“夫妇之愚”也可以知、可以行的。通过它的日常功用,人们可以体验到它的存在。反过来,这又是与天相通的——“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妇,及其至也,察乎天地”。说到底,这个“中”是人可以“赞天地之化育”“与天地参”的内在能力。
如果我们想象孔子作《春秋》时的心态,不正是“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那种“天命在我”的感觉吗?其实,从《中庸》 《孟子》,乃至程朱理学和陆王心学,都是一脉相承的!无论是把四端说成性,把性说成是天命,还是把“天理”或者“心”的良知抬到天道的地位,都是在为天地立心,是神如在我、天如在我的担当。可以说,“如在主义”是儒家功夫中一个核心的功法,是理解从孔子到思孟乃至到宋明理学和心学关于性、心、天理、良知、天道的一把钥匙。③倪培民:《儒学的精神性人文主义之模式:如在主义》。
看到倪先生对“如在”作出这样的界定与说明,那么所谓“如在主义”的具体内涵也就比较清楚了,这就是作为“功夫”之具体呈现以及作为其所反映或回馈的境界。说“如在”是功夫的呈现,是因为无论是“功夫”还是“如在”,首先都是与主体紧密相关的,也是主体实践追求的产物:说是“功夫”,是就其主体自觉的实践追求而言;说是“如在”,则是指所谓人生世界也就在实践追求的基础上向着主体作不同程度、不同层次的响应和显现。日常用语中所谓“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其实也就指人生境界的不同层次以及其不同的沟通和理解方式而言。
那么,何以认为“如在”又是主体实践追求之反映或作为其回馈产物的境界呢?这是因为,既然主体的追求“功夫”具有不同层次与不同进境,那么在其不同层次的“功夫”进路上之所见也就必然具有不同的内涵;而这种不同内涵,也就是境界的内容及其层次性。所以说,“功夫”本身的层次性也就决定了“如在” (境界)的不同内涵,这就是境界的不同层级性。
但“如在”无论是作为主体追求的“功夫”还是作为其主体所显现的“境界”,都存在着一个更为深刻的关联,这就是“本体”。作为“功夫”,其与本体的直接关联则有黄宗羲的“心无本体,工夫所至,即其本体”①黄宗羲:《明儒学案·自序》,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版。一说;这就明确将“本体”规定为“功夫”的产物或直接对应者了。所以,倪先生也认为“它(“功夫”)与主体的紧密联系直接导致了宋明理学中‘即本体即功夫’的命题及由此而来的对此命题的各种探讨和诠释”。但这毕竟是对“功夫”之一种较狭的取义,而倪先生的“功夫”论说则始终定位在“工程”和“夫役”②倪培民:《阳明心学的功夫伦理与价值重建》。另见《从功夫论到功夫哲学》一文。的层面上,就是说,倪先生所倡导的“功夫”是一种涵义较为宽广的“功夫”论说,或者也可以说是一种由“功夫”论说拓展而来的“功夫哲学”。
让我们先看作为其狭义“功夫”中所体现的“本体”。由于“功夫”与“本体”的必然关联,而作为“功夫”追求指向的“境界”本身又对“本体”具有一种必然蕴含的关系,因而儒学或整个中国哲学都具有一种“境界形上学”的特征,即以形而下的境界来蕴含并表达其形而上的“本体”。这样,“本体”与“境界”就具有了一种不可分割的性质(从形而下之表现的角度可以说是境界,而其内在也就必然蕴含并表现着其形而上的本体),一段话,一种表达,其究竟是指谓“本体”还是“境界”?这只能由其具体语脉来决定,更多的甚至就直接具有内“本体”而外“境界”的性质,即从其内在根据上看,就是所谓“本体”;但如果从具体表现上看,则是所谓“境界”。这样一来,其“本体”与“境界”也就具有了同一表达的性质。请看倪先生对于这种“本体”与“境界”的同一性表达:
以如在主义为标志的圣贤哲人宗教从“敬”的自我状态中开发出神性,开始克服神人的对立。神不再是神,而是我的“神如在”状态;我不再是我,而是神的媒介或“尸”。而这同时也就是神即我,我即神的开端。神我合一的最基础的形式是对鬼神的祭礼,其扩展的形式是“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把所有的人间日常活动都当作礼,整个人生都成为祭礼活动,在世俗生活中“与鬼神合德”。其最高的形式,是以人自己的“性”或者“良知”为天命……把性看作天命,是最高的自我超越,自我神圣化,天人合一。①倪培民:《儒学的精神性人文主义之模式:如在主义》。
在倪先生的这一描述中,究竟哪些属于本体、哪些属于境界呢?一般说来,从“我”出发或由“我”引申而来的就属于本体,比如“性”“良知”包括“天命”;而所谓“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以及“与鬼神合德”包括“天人合一”则属于境界。在“我即神”“神即我”的状态下,不仅本体与境界合一,而且由于本体是通过“我”之“功夫”得以彰显的,因而“本体” (“性”“良知”包括“天命”)与作为境界的“与鬼神合德”与“天人合一” (包括“神即我,我即神”)也就在“我”之“功夫”追求中实现了三者的统一,而且具有一并朗现的性质。倪先生关于“功夫”之“三维合一”的论说,也就在其“如在主义”的境界追求中得到了一个圆满的展现。
三、回归与原有的困境:“功夫”的滑转与“境界”的光景化
既然倪先生对其“功夫论”研究与“如在主义”追求作了如上论说,那么,这也表明其对中国哲学之主体性精神的一种全面回归,也是以主体性精神对于中国哲学的一种重新诠释。在这里,作为“回归”,自然是指其对中国哲学进行忠于其基本精神与特征的理解与把握;而作为“诠释”,则是指其在“回归”的基础上,也就必然会带有中国哲学原本就存在着的各种缺弱或不足。②实际上,倪培民先生对其“功夫论”探讨与“如在主义”的境界追求所包含的负面效应是有其清醒自觉的,比如其在《儒学的精神性人文主义之模式:如在主义》一文的末尾明确指出:“如在主义虽然兼具合理性和精神性的优点,但它的实践不容易把握,很容易滑向两个极端。一个极端是从‘神如在’很容易变成‘神在’的迷信……而对此的纠正,又容易走向另一个极端,禅宗的‘呵佛骂祖’本来是为了把人们从偶像崇拜中拉出来,回到自己的内心,认识到本心即是佛,但不知本心是佛的人只学了那‘呵佛骂祖’,结果又完全失去了精神性的意味,变得毫无‘如在’感,更可怕的,是以此为借口,肆无忌惮,胡作非为。”倪先生的这一反思可以说是对其“功夫论”探讨与“如在”追求的一个自省式的“回头望”。
让我们从倪先生对“功夫”的论说和规定谈起。
如前所述,当倪先生从“功力”“工夫”与“功法”之“三维合一”角度讨论其“功夫论”时,自然是从中国文化的主体性立场对于“功夫”的一个总体性概括;而“三维合一”的规定,又说明其所谓“功夫”必须是集主体资质、修养基础以及才艺、能力表现的一个综合指标。但是,如果我们对这些“功夫”规定稍加叩问,就会发现它其实并不专属于宋明理学,甚至也不专属于儒学;而其“工程”和“夫役”的规定,也说明它是建立在囊括中国传统的儒佛道三教思想的基础上,从而专门从“人”这个主体性角度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一种概括性论说。正因为这一原因,所以主体资质、修养基础以及才艺、能力表现才会成为它的一个综合性指标;而作为“生活的艺术”这样一个总体指向,又说明它是根据现代人与现代性所提出的一种可以包括东西方不同传统的人生价值观。
正因为如此,所以中国以“三教”为代表的传统文化所原有的毛病也就仍然并存且可作乱于倪先生的“功夫论”中,其他方面暂且不论,仅就“主体性滑转”①所谓“主体性滑转”是笔者对中国文化及其负面作用的一个概括,主要指谓人生追求在主体之不同层面间的滑落现象。比如王阳明所批评的“近世所谓道德,功名而已;所谓功名,富贵而已。”[王守仁:《与黄诚甫》,载《王阳明全集》 (卷四),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161页]这种将“道德”滑转为“功名”,又将“功名”滑转为“富贵”的现象,就是一种典型的“主体性滑转”。参见拙作:《从“形神之辨”到“性气之归”——中国哲学的特征及其内在张力》,载《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017年第6期。一项就可使其成为一种由于泛化运用而滑转为有意“作秀”式的“功法”表演。比如仅从儒佛道三教之不同主体来看,儒家的出发点无疑就是人的“德性”,而道家的出发点则是人的“生性”或“天性”;至于佛教,则又是以般若智为特征的“佛性”。当这三种“人性”合成一个综合性的主体且作为“功夫”追求的基本出发点时,那么,作为其落实与表现的“功夫”也就可以因为其不同的出发坐标而表现出不同的实践指向。因为也只有在这个意义上,倪先生所谓的“功夫”才必须是包括主体资质、修养基础以及其才艺、能力表现的;而这三个方面的“统一”才能够成为其“功夫论”的一个综合指标。
但这一综合指标非但不能弥合其在儒佛道三教不同出发点上的分歧,反而可能会因为其统一从而使其原有的旧病沿着三个不同的方向蔓延。仅从儒学来看,所谓“功夫论”就不能排除同一主体在不同追求指向与不同功夫进境上的差别,这就为“主体性滑转”甚或有意式地“作秀”创造了条件。比如说,王阳明是儒家心性之学的集大成者,但在其笔下,那种通过“主体性滑转”所形成的“作秀”或内外在世界的“背反”就已经成为其所著力批评的现象了。请看阳明笔下的“主体性滑转”以及其所表现的“作秀”甚或内外在世界的“背反”现象:
志于道德者,功名不足以累其心;志于功名者,富贵不足以累其心。但近世所谓道德,功名而已;所谓功名,富贵而已。②王守仁:《与黄诚甫》,载《王阳明全集》 (卷四),第161页。
今之大患,在于为大臣者外讬慎重老成之名,而内为固禄希宠之计;为左右者内挟交蟠蔽壅之资,而外肆招权纳贿之恶。习以成俗,互相为奸。①王守仁:《陈言边务疏》,载《王阳明全集》 (卷九),第285页。
在阳明的语境中,所谓“富贵”“功名”与“道德”也就构成了人生追求的三个不同方向,但由于这三者可以同时共存于同一主体的人生追求之中,因而又可以说是同一主体之不同追求层次的表现。一旦表现出“主体性滑转”,那么其追求也就可以形成口头上的“志于道德”,其实际追求不过是“功名而已”;至于追求“功名”,则又完全可以沦落为“富贵而已”。这就由“主体性滑转”演变为一种全面的精神堕落现象了。进一步看,甚至也可以形成阳明所批评的“为大臣者”与“为左右者”之全面的内外“背反”现象。这说明,仅仅对传统“功夫”进行抽象化概括虽然可以表现出更大的含括性,但却并不足以克服传统功夫学所存在的毛病。
对于宋明理学来说,“功夫”之所以能够成为一个核心概念是从阳明心学开始的(虽然程朱乃至整个理学都比较注重修养功夫)。这是因为,对修养“功夫”的重视不仅受制于宋明理学的主体性精神,而且也存在着学理积淀与探索发展的因素;更重要的一点还在于,由于阳明心学本身就代表着理学主体精神的高峰,因而其不仅极为重视功夫,而且也最善于识别人们在功夫上的“作秀”与“表演”现象。请看阳明对其弟子在真实用功方面的敲打:
诸君功夫最不可助长。上智绝少,学者无超入圣人之理。一起一伏,一进一退,自是功夫节次。不可以我前日用得功夫了,今却不济,便要矫强,做出一个没破绽的模样。这便是助长,连前些子功夫都坏了。此非小过,譬如行路的人,遭一蹶跌,起来便走,不要欺人做那不曾跌倒的样子出来……②王守仁:《语录》 (三),载《王阳明全集》 (卷三),第101页。
问:“近来妄念也觉少,亦觉不曾着想定要如何用功,不知此是功夫否?”先生曰:“汝且去着实用功,便多这些着想也不妨,久久自然妥帖。若才下得些功,便说效验,何足为恃?”③同上书,第123页。
以阳明心学来评点倪先生的“功夫”论说显然是不公平的,因为这无疑是以最严格的功夫进路来评点最宽泛且最具含括性的功夫论说。但这里确实存在着所有的功夫论说都特别值得记取的一点教训,就是所谓“助长”与“效验”。“助长”本来是为了强化功夫的正面作用而故意“作秀”;至于“效验”,则是为了展现功夫的正面功效而故作夸饰之谈。所以,在阳明的语境中,所谓“助长”与“效验”都是作为对功夫之“作秀”或“表演”出现的,而且也是特别值得警戒、防范的负面现象。这说明,在如何防范“功夫”之“作秀”或“表演”方面,倪先生的“功夫论”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
正由于这一原因,所以当倪先生由“功夫”论说展现为对“如在”境界的追求时,也就出现了不少的问题。当然在这里,我们必须先从“如在”之作为功夫所表现的境界来分析。因为当倪先生的“功夫论”以“人”为出发点,以“三维合一”为基本规模,而以“生活的艺术”作为总体指向时,其主体及其实践追求与境界表现也就具有了“三维合一”的特征。就是说,儒家的主体活动(作为本体流行的表现)、功夫追求与人生境界本身就具有三者合一的特点,所以,其以实践活动所表现的功夫同时也就具有境界的属性。比如孔子在回答其弟子“师(子张)与商(子夏)孰贤”的问题时就曾提到“过犹不及” (《论语·先进》);而孟子在论及心上功夫时也曾提到“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长也” (《孟子·公孙丑》上)的勿忘勿助一说。这样一来,儒家的道德实践(“必有事焉”)也就必须达到勿忘勿助而又无过无不及的状态;这种状态,既是一种实践追求(勿忘勿助而又无过无不及)的功夫,同时也是主体道德实践追求之自然而然的境界。前面征引阳明弟子所谓的“近来妄念也觉少,亦觉不曾着想定要如何用功”实际上就指功夫与境界直接统一的勿忘勿助而言。但由于其功夫连同境界都脱离了“必有事焉”之主体实践的基础,所以被阳明批评为“才下得些功,便说效验,何足为恃?”
就境界而言,由于其具有一定的示范、榜样与激励作用,因而其在阳明心学中往往被称为“光景”——光的影子。因为光景本身就是“光”在照射中遇到“障碍”所投下的影子,因而其对人也就具有一定的示范与激励作用,这就形成了一种专门卖弄各种“光景”的“光景之学”。实际上,“光”只有在照射的过程中(穿过障碍)才会形成“光景”,一如水只有遇到坎坷才会激扬为浪花一样。但如果陶醉于“光景”的瑰丽、钦羡于浪花的可爱,从而专门收集各种“光景”和“浪花”来叫卖,这就成为一种“光景之学”了。严格说来,所谓“光景”其实就是境界的表现;而“光景”之所以会成为“光景之学”,就是因为真正的境界从来都不脱离“光”的照射本身,一如浪花从来都不脱离水的流动一样。但如果专门就光景说光景、就浪花说浪花,从而脱离了光的照射与水的流动本身,那么这就成为一种“光景之学”了。阳明心学从来不乏精彩的光景,但真正的心学却只有在破除光景的过程中才能真正凸显阳明的真精神。比照于阳明建立在“破光景”基础上的实践追求精神,倪先生的“如在”境界也只有在能够有效地防范各种“光景之学”与“心灵鸡汤”的基础上才能真正高扬起中国传统“三教”的境界追求精神。
四、对“功夫”之溯源及其科层、底限的探寻
之所以这样评说倪先生的“功夫”论说与“如在”境界,绝不是要否定倪先生之推陈出新的努力与融合中西文化的探索,而主要是来自一种“风险评估”意识,并且也是为了排除这些“风险”,才故意进行这种鸡蛋里面挑骨头式的批评。因而,我们这里也就不能不继续追问:为什么“功夫”会出现“滑转”,为什么“境界”又会沦落为“光景”?
“功夫”之所以会出现“滑转”,主要源于主体追求的多层次性,一如阳明所谓的“富贵”“功名”与“道德”都构成了人生的基本追求一样;而对现代人来说,我们也不能像阳明那样只将人的追求限定在道德的层面,或者以道德来统摄人对“富贵”与“功名”的追求。这样,面对日益现代化的社会格局,我们也就可以有两种彼此递进的选择:其一即必须深入探索“功夫”之源;其二则在肯定人之“富贵”“功名”与“道德”追求为合理的基础上探索其层级规定与边界、底限意识,从而防范其可能出现的“滑转”与“作秀”。
从“功夫”之原发动因的角度看,人之所以会形成各种不同的追求,首先源于人之生命本身就是一种感性而又立体的存在;作为感性的存在,它就必须通过与周遭世界的质能交换才能维系自身的存在,这可以说是维系生命存在的需要。在这一基础上,人生并不仅仅是像动物那样“活着”,而是必然存在着体现其生命价值的各种各样的追求,于是,这就有了阳明所谓的“富贵”“功名”与“道德”之不同层次的追求,以满足人生各种不同的所需,彰显人生的立体性与多样性。但在这里,当人生追求进展到对人之生命进行道德层面的肯定时,来自道家人之自然天性的层面与来自佛教关于人之超越的般若智层面的肯定也就一并展开了,这就构成了对人之精神生命之各种不同角度的肯定;由于在这种不同方向下必然会形成各种不同的人生,因而先发于西方文化之现代化追求与现代人伦文明建设也必然会成为中国传统关于人伦文明建设的一个参照坐标。在这种状况下,中西文化最大的公约数也就必然会成为其双方相向而行的一个大方向。在这一背景下,儒家从孔子所概括的智、仁、勇三达德到现代人所面临的内在德性、自然天性以及以慈悲为怀的佛性也就必然会成为其最高统领。这就是倪先生“三维合一”的关怀及其建构。因为这不仅是中国传统文化在历史上经过长期的“儒道互绌”“儒佛融合”所得出的结论,而且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也只有儒学才代表着积极建构并推动人伦文明发展的正面力量,因而也只有儒学,才能担当起与西方文化相互沟通与相互借鉴的责任。
但建立在这个基础上的儒学,就已经不仅仅是处理人伦关系的伦理学了,也不仅仅是体现其人文涵养的道德水平,而是体现着人生最高追求并作为人之为人之根本依据的德性之学,是实现人之生命之最高理想的信念、信仰之学。这种学问,虽然未必以上帝、真主为皈依,但其关于人之德性的信念同样具有信仰的蕴含;而其在人生中所起的作用,也必然与上帝、真主处于同一层面,因而也就必然要发挥出其大体相同的作用。①倪培民指出:“道德本身就是功夫之源。有诚信就是获得信任的功夫。所以中国传统功夫里有‘万法归宗,以德为本’的说法。” (倪培民:《阳明心学的功夫伦理与价值重建》)这样一来,整个人的生命也就立体地撑开了:而居于最高层的,就是关于人之德性的信念与信仰追求,这既是来自儒家人与“天地参” (《礼记·中庸》)的传统,同时也是人在天地间的一种自我肯定与自我写照。然后依次展开的则是道德实践的人生、自然天性的人生以及慈悲为怀与解脱追求的人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人生才展现出其多种关怀与多样的面相:诸如道德的人生、艺术的人生以及出离与观照的人生等等。依次下贯,人生又可以表现为感性欲望的、功名财富的包括英雄豪杰的等各种各样的面相,而这种种人生,既可以是不同层级的,也可以是不同面向的,当然还可以是不同情趣的。
在这一基础上,所谓主体性的“功夫学”就既可以展现其面相的丰富多样性,同时又可以表现其归根还原的一本性。作为人生的“一本”追求,这就是孔子所谓的“为己” (《论语·宪问》)之学。正因为“为己”,所以没有必要取悦于人,也没有必要以他人的人生作为自己的人生标准。如此一来,所谓“说效验”“卖光景”之类也就从根本上失去了存在的依据;每一个体都从对自己人生负责的精神出发来展开自己的人生追求,此正所谓如人饮水,冷暖自知。相反,如果一个人要将自己对人生的认知强加于人,必然会面临“夫我则不暇” (《论语·宪问》)之类的反省,也必然要面对“耘人之田” (《孟子·尽心》下)的自责。因为对自己人生负责的只有自己,孔子所谓的“为仁由己” (《论语·颜渊》)正是从这个角度提出的。实际上,也只有对自己负责的精神,才能展开真正的人生。除此之外,这种“为己”之学又不是一种整齐划一的模式,每一个人,既可以从自己生来的“天性”出发,也可以从自己对人之为人的认知出发,当然还可以从对人生意义之超越的反省与观照出发。总之,每一个人都尽可能地展现自己对人生的认知,也尽可能地展现对自己人生意义的追求。这样一来,人生将最大可能地展现其丰富性与多样性,而不必担心虚伪与骗术的流行。
然而一旦展现出人生的多层级性与同一层面之多样性,所谓“主体性滑转”就会成为一种在所难免的现象,这并不完全是出于虚伪和欺骗,而认知之不彻底性也同样可以导致这种现象。在这种情况下,来自西方文化的层级规定与底限意识便会显现出极大的作用;而对立体纵贯的中国传统文化来说,则所谓“主体性滑转”既有可能来自虚伪和欺骗(比如为了取悦于人),也同样有可能来自认知的不彻底性,在这种情况下,也就需要西方文化的层级规定及其边界与底限意识来防范,这就需要中西文化的融合来共同面对。
之所以需要中西文化来共同面对,是因为纵贯立体的中国文化天然就存在着“主体性滑转”的可能;而这种“滑转”也并不完全是缺点,甚至首先是从优点与优势的角度表现出来的。比如关于人生的信念与信仰追求为什么可以直接贯通于人生的各个方面,这就主要是通过纵贯立体的渗透与主宰意识实现的。严格说来,这种“贯注”与“渗透”能力本身就包含着“滑转”的可能,甚至,从一定意义上说,中国传统文化本身就是通过“滑转”来实现其“贯注”“渗透”与“主宰”功能的,只是由于这种“贯注”与“渗透”的“滑转”体现着人生的正面价值与正面追求,体现着人对自身德性的自觉、落实与担当,因而人们并不以“滑转”视之。至于需要否定的“滑转”,则往往是通过价值界限的“渗透”以至混乱表现出来的,一如阳明所批评的“近世所谓道德,功名而已;所谓功名,富贵而已”,包括所谓“外讬慎重老成之名,而内为固禄希宠之计”“内挟交蟠蔽壅之资,而外肆招权纳贿之恶”。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现象呢?这当然是因为人之精神的沦丧所致,从而以“富贵”代“功名”,又以“功名”充“道德”之任;而在精神沦丧的基础上,则所谓的“为己”就已经停留在“富贵”与“功名”的层面了。
在这种情况下,西方文化的层级规定与边界、底限意识就为我们提供了可以应急的药方;而这一“药方”说来又非常简单,这就是“在学言学,在商言商”,而决不允许其他层面的窜入或“滑转”,尤其是其牢不可破的底限意识也就成为我们言说的范围、用语的界限以及行事的准则;任何超出行规之外的言说都不能破坏层级本身的规则,也绝不能越出其边界与底限之外。
这样一来,对“功夫”之原发动因的追溯必然会使我们形成对人与天地关系的一种德性信仰,并以真正“为己”的精神展开人生之多样与多层面的追求。而在每一行业、每一层面,我们的“功夫”追求又必须遵循其内在规则及其底限意识,并以此来防范“主体性滑转”以及各种“卖光景”的虚伪与各种“心灵鸡汤”式的“作秀”现象。这样一种指向,既坚持着中国文化的主体性精神,同时又面向中国现代化追求的现实,从而将西方文化的科层智慧、钻研精神与底限意识熔铸其中。在笔者看来,这就是倪培民先生从主体“功夫”到“如在”境界的指向,也是其以中国文化的主体性精神吸取、消化西方现代意识的具体表现。
(笔者附言:该文完成后,曾提请倪培民先生批评、补充,故笔者愿借此对倪先生坦诚交流、真诚对待各种不同看法的心胸与精神表示最大的敬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