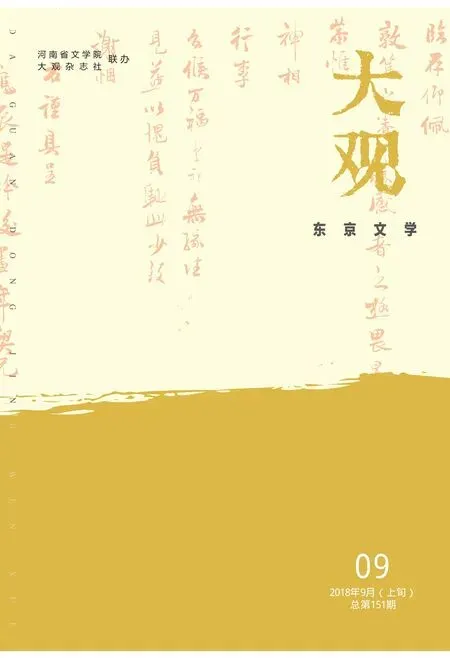钱眼里的人生(三题)
房 贷
在我认知范围内的汉字词组中,再没有比“房贷”这两字更有分量的组合了,我穷尽想象也找不到准确的词语、贴切的比喻来描述它的沉重。那沉重不压肩不压头,不压迫身体的局部,而是将你层层叠叠包裹起来,从四面八方挤压你的整个身体,精确到每个部位,每根神经,每粒细胞,连细胞核也在劫难逃。
我想不出由数字构成的房贷,以什么样的姿态挤压人,它沉重的分量来自哪里。轻如鸿毛的纸币,一旦取名为房贷,陡然间身怀隔山打牛的神奇功力,不动声色地伤人于无形。
2008年夏天,我和妻子痛下决心,一定要在闷热的季节里结束居无定所、提心吊胆的租房生涯,在拥挤的城市买一套属于自己的房子。租来的房子,住多久也没有家的感觉,寄人篱下的凄凉挥之不去,有一套自己的房子,就该有家的温暖了吧。
从租客到房主的道路是用钱铺垫出来的,我和妻无法在收入上大张旗鼓地开源,只能想方设法在有限的工资里节流。妻改掉了喜欢时髦打扮的习惯,舍不得吃两元钱以上的早餐。我们用日常生活的清苦,一点一滴地堆砌理想中的房子。一平方米,两平方米……房子的空间在积少成多的钞票里慢慢长宽长高。一万,两万……首付终于攒够了,我们欣喜得一夜未眠,第二天直奔售楼部,签合同办手续,贷款15年。尽管房子还矗立在售楼部的展台模型上,我和妻挽手站在展台前,看着我们的“房子”,仿佛从虚无缥缈的云端一下降落到坚实的大地上,从未有过的踏实瞬间遍布全身。
直到开始按月从微薄的工资里剔除一半往卡里还房贷,压力才如同黑夜般铺天盖地席卷而来。还房贷的卡,像贪婪的嘴,钱放进去连声响动都听不见。孩子出生、父亲生病、房子装修、人亲往来……花钱的项目接踵而至,工资的数额始终固若金汤,无法突破。
我和妻常在暗夜里相对无言,长吁短叹。买房给我们带来的幸福还没来得及盛开,早早夭折在房贷的寒冷霜冻里。无形的压力让人喘不过气来,每一笔或大或小的意外开支都让我们心惊肉跳,继而怀疑人生,感觉全世界都在跟我们过不去。房贷不理会我们的辛苦,兀自岿然如一艘大船,我和妻是羸弱的纤夫,艰难地拉动大船一点一点地前行。许多难以入眠的夜里,房贷具象为一张张的红钱,状若雪花,飘满我的世界,围着我翩翩起舞,我听见它们的哂笑,看见它们翻起的白眼,承受它们不断发出的巨大功力。十五年的时间长河,是一段看不见光明的黑暗旅程,我人生中最年富力强的十五年,注定要拖着房贷的沉重纤绳,在黑暗里摸索碰撞,艰难前行。
买房第三年的11月份,父亲患上严重的冠心病,我服侍父亲去贵阳手术,忙中出错,还房贷的时候忘了银行要扣除短信费,没算足余额。12月份,银行通知我有不良记录。我赶忙跑到银行查询,结果显示,我欠下银行一角钱的债。
一角钱。菜场里很多年买不到一角钱的菜,超市里找不到一角钱的商品,上公厕撒泡尿最低五角了,谁要是给街头乞讨的人一角钱,准会招来谩骂,这叫钱吗?买个屁人家都不愿脱裤子。我们生活的世界里,价值一角钱的买卖早已经绝迹。而我,一个身高一米六八的公务员,将自己辛辛苦苦一月一月积攒起来的诚信,一角钱卖给了银行。
自动存款机不识别面值一角的纸币,它只认百元大钞,我没脸取号排队到柜台上偿还我欠下的债,往自动存款机里存了一百元。冰冷静默的机器吞下钱,顿时欢笑起来,持续不断的嗤嗤欢笑里,我欠下的一角钱翩然从出钞口飘来,在我头顶打了个优雅的旋,飞过拥挤的人群,飞出纤尘不染的银行大门,在蓝天下抖抖身子,变得巨大无比,遮住了我目力所及的每一寸天空。
讨 债
人,无论潦倒到何种程度,总会有比你更潦倒的人。活在自己看不到头的困境里,老幻想有个什么贵人来帮自己一把,没承想,有一天自己也会成为别人眼巴巴看着的救星。特别像我这种从农村出来的人,背景是一片贫瘠的辽阔土地,后台是挥舞锄头统治牲畜和农作物的父母,周围环境遍布穷亲戚瘦庄稼,不管在城市混得多么底层,回到村里,立刻身价倍增,成为乡亲眼中高不可攀的权贵,锦衣玉食,挥金如土。在熠熠生辉的光环笼罩下,人的善良极易虚胖,乡亲们有了困难,伸手借点钱,就强撑着不让他们长满茧子的手空空缩回去。
张家三百,李家五百,赵家一千……参加工作到现在,十多年的时间,我借出去的钱几乎占到全部积蓄的一半以上。当钱变成债,即便是别人欠自己的,也是一种卸不掉的负担。天长日久,那些未如期归还的债,在年月里汲取了世俗的精华,修炼成精,化身体力旺盛的猎物,在我的视线里若隐若现。我这个疲于奔命的猎手,累到虚脱,始终无法将它们捕获。恍惚间,乾坤倒转,黑白颠倒,猎物成了猎手,我沦为猎物,它们身手敏捷,轻易捕获了我,猫玩老鼠似的,以胜利者的绝对优势和绝对实力在股掌之间倒腾我。我假装出一副享受的样子,有时微笑,有时欢叫,生怕一不小心惹它们不开心,它们一溜烟逃离我的视线,从此无影无踪。
很多年来,我和妻家庭生活的主要内容之一就是讨债,我们的感情在讨债的得失里升华或者坠落,悲喜爱恨大多维系于讨债上。关爱彼此的精力悉数转移到维护和欠债人的融洽关系上,把所有欠债人奉为上宾,小小心翼翼和他们相处。几乎每次讨债失败,和颜悦色避开欠债人之后,夫妻间都会爆发一次大刀阔斧地践踏对方尊严的战争,像两只饥肠辘辘的狗,守着刺猬一样的债无从下嘴,只能相互撕咬,相互指责,发泄不满,然后精疲力竭地相依相偎,期待奇迹发生。
有的人偶尔捎些土特产和几句什么时候还钱的话来,我们感激不尽:“有钱钱打发,无钱话打发,瞧人家这为人,钱借给他很放心,多急用也不能问他要,愧对了人家。”有的人跟村东头的宋八一样,先借二百,再借三百,承诺年底还五百,后来说干脆凑成一千,数字大好记,零借整还,再后来人就销声匿迹了,五六年不见踪影。有的人来了,天南海北什么都说,只字不提还钱的事。人走了,留下一屋子的惶恐和疑虑。我说:“不会忘了吧,怎么闭口不提还钱呢?一定是不好意思开口。知道害臊为什么不还?没钱也该解释一下啊。”我眼巴巴望着妻,希望求得她的安慰和认同。妻比我更加不安:“怕是来试探的,他希望我们忘了。万一他真忘了怎么办?几百块钱,借的时候人情美美的,一开口要,一辈子的交情就完了。不要吧,一人头上损失几百,他们倒没事,我们事大了。”这正是我所害怕的,我痛恨妻轻而易举说出真相来,不捅破窗户纸,心中尚存一丝念想,逮不到猎物,能看见也好啊,望梅还止渴呢。我为妻子的话一个下午没理她,即便她好几次以认错的姿态笑脸相迎。我要让她明白,同样的错误不能再犯第二次。
我私底下第105次拨打宋八们的电话,电话仍然坚持欠费停机。那是个月朗星稀的夜晚,月光透过阳台玻璃洒在我身上,我看不见的宋八,月亮一定看见了,他此刻会想起我来吗?我独自伫立阳台上,看着万家灯火的城市,突然顿悟:人活在世上,总有一些别人欠自己的债是要不回来的,就像有些债自己无法偿还一样,这是命定的劫数。
礼 金
家里几个书柜,满满的全是书,大部分没好好读过,很多书,包装的塑料封皮也未曾撕开,就放在时间里陈旧了。夹在书里记录礼金往来的一本硬壳笔记本,却被翻阅得油光闪闪,好似珍藏多年的古玩,有了不停把玩留下的包浆。
这些年,生活的负累使我静不下心来完完整整地看完一本书了,读得最认真感悟最多的就是这个账本,每月读每年读,遇到办酒席的高峰期,每周读甚至每天读。账本是我和妻结婚时的礼金记录,每个熟悉的名字后面,对应标注了我和名字之间的情谊价值,人和人的亲疏,静静躺在或大或小的数字里沉睡。一旦翻开账本,它们就伸胳膊抖腿地醒过来,瞪着一双明亮的眼睛,虎视眈眈望着我,说我在这里,我一直在这里。
我和妻,从未同仇敌忾地像读账本一样读过任何一本其他书籍,我们之间的分歧抱怨、厌恶愤懑,在共同翻阅账本的时刻自然消散或弥合。我们讨论账本的时间多于谈情说爱的时间,即便有时候我们无话可说了,目光会不约而同落在账本上——礼金,已经成了我们生活里逃不开躲不掉的最大支出,远远超过房贷的负担。
我们在每一个还过礼的名字后面做上记号,还一次画一个勾。礼金是画不上句号的,画上意义复杂的勾,记录我们对礼金这种无奈支出的复杂情绪——深受其苦,无法摆脱,只好随波逐流。一年年过来,已经没有一个名字后面是空白的了,账本里的几百号人,经年不息地轮番操办各种名目的酒席,有些人的名字后面,列队检阅似的,排了一长串勾的队伍,那些勾都有自己的响亮的名号:乔迁、升学、入伍、做寿、住院、结婚、生子、过世……一排一排,如同疯狂生长的野草,渐渐铺满洁白的纸页,却掩盖不掉名字和名字后面的数字。名字像统领,数字如旗帜,统领一挥旗帜,后面的队伍齐刷刷在眼前立正稍息,振臂呼喊那一串数字。
如此往复,年复一年。
有一年的某个酒席高峰月,我和妻把两人当月的工资全部画成账本上的勾。傍晚,我们终于赶完一天里的第七家酒席,筋疲力尽走在回家的路上。妻一手紧紧拉住我,一手攥着孩子,说,我只剩下你们俩了。她眼里的悲凉霞光一样淹没了我。她说,我们把账本烧了吧,我怕看见。我点点头,茫然走在人流之中,每个擦肩而过的人都像匆忙移动的勾,满街游走的勾汇成江汇成海 ,朝我们汹涌而来,在我们身边冲撞咆哮。我看见我以勾的形态,从别人的账本里走出来,绝望地汇入勾的汪洋,兴风作浪,彼此推搡,相互淹没。
账本终究没有烧掉,纸可以化为灰烬,礼金却是烧不掉的,只要人在,礼金不灭。账本依然盘踞书柜最醒目的位置,独自热门,漠视群书。生命力极度旺盛的勾,无论春夏秋冬,仍旧葳蕤地在账本里生长。
妻再也没打开账本画过勾,她把这个权力下放给我。每次打开账本,我为还能在某个名字后面找到一处勾的容身之地倍感庆幸。我不知道,当这个账本找不到空白画勾的时候,我和妻,已经变成了什么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