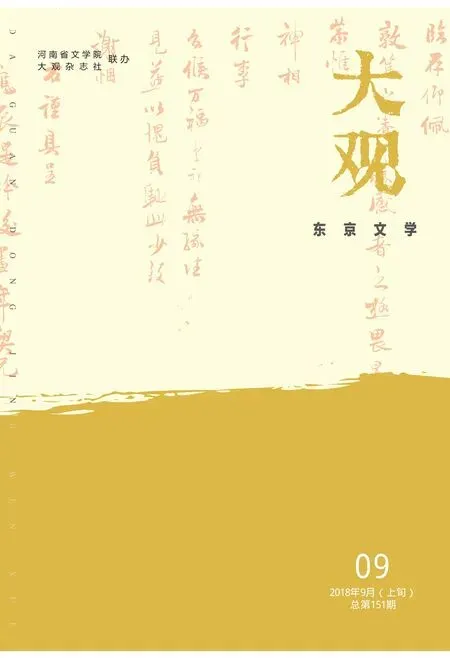海风这边吹
蓝色的录取通知书攥在我手里,我能感受到手心的汗渍。我把研究生录取通知书拿给父亲看的时候,父亲不言语,脸上透露出欣喜。
这些年,生活让父亲从年少轻狂到成熟稳重。父亲二十一二岁的时候,我来到这世间,那时候他比现在的我年龄小些。父亲个高不见佝偻,但是脊背上的老茧脱落和新生了无数次。
六月底,我从学校回家来,到九月份开学,和父亲喝酒几十斤,像兄弟一般。每次只要是父亲倒酒总先给我倒一碗,有时候爷俩坐着话不多,父亲起身拿起碗便去倒酒,你一口我一口,三两句话,像多年好友一样。须臾间,有些渣滓的碗底呈现出来。
七月,我和父亲搭着长途车去了潮安,父亲说,这是他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出省。过了黔西南州到了百色,过了梧州到了广州,过了汕尾汕头,终于到了目的地。一下车,咸湿的海风迎面吹来,十分燥热。父亲点燃一支烟,若有所思地长叹。我知道,这的确是他第一次出省。
从外砂车站打了摩的,到潮安县庵埠镇,摩托车司机玩起了文字游戏,毫无疑问多花了三十块钱。等到了目的地的时候,已是傍晚时分,晚霞被落日余晖渲染得绯红,好看极了。我和父亲已经几十个小时没吃东西了,在路边胡乱买些东西垫罢空腹,给六姨妈打了电话,然后一路询问。问到一个当地的老者,老者从门缝中探出头,说不知道。我和父亲有些失望,转过身后柳暗花明,原来六姨妈家就在老者家对面,父亲说这老头和村里的老头不一样,我心里也不免有些失落。
七月的潮安在燥热中骚动,每个人都如此。当晚,我和父亲去买了些生活用品,心里的石块可算落下。吃过晚饭,在人来人往的街道上游荡着,漫无目的,像迷失前路一样。
次日,和六姨父两口子去了工地,我们要做的就是给一栋七层小洋楼的外墙贴瓷砖。我负责将白水泥、黑水泥兑水和匀,然后递到架子上。父亲站在七楼外墙的竹架子上,摇摇晃晃,父亲个子高,在架子上有些施展不开只能弯腰。我拎着两桶水泥,一黑一白,我突然想起了黑白无常。人生就是如此无常,头一天六姨妈还说起,前几天我们还没到的时候,另外一个工地上,一个贵州老乡从九层架子上摔下,抢救无效死掉了,我想死者生前也不会想到自己会被死神从这里带走吧。
我有些笨拙地爬到架子上时,我感受不到任何居高临下的威风,只觉双腿发抖,心跳加速。额头上的汗水滑进眼窝,这一刻我是如此的胆怯。父亲说,你慢点,不要往下看,往前走。我不说话,点点头,这话似乎在我跌跌撞撞学走路的孩提时代,他已经说过。父亲站在架子上,竹架子摇摇晃晃,父亲正给墙上刷水泥打底,我负责给他们送水泥。我是第一次做这样的活计,看着父亲不算娴熟的动作和有些发抖的双腿,我敢肯定父亲也是。父亲的衣服湿透了,紧贴着宽阔的脊背,汗水成行地顺着流下,我身上也是,我舔了舔干燥的嘴唇,有些咸涩,更有些苦。吹海风了,凉快极了,海风中夹着海水咸湿的味道,和汗水一样。
傍晚时,站在这栋不属于我的楼顶上,看着天边的晚霞。那晚霞十分漂亮,像一个花枝招展的少女或盛装的新娘。晚霞另一头有什么,是否有人和我一样,我胡乱地猜想着。
走咯,下班咯!六姨父叫道。他是四川人,有着四川人身上的热辣劲儿,喜欢打牌,跟个老顽童一样。从工地到家的路上,我们骑着摩托车,在城市街道上穿梭,早晚都不用担心,因为错开了高峰期和交警。
吃过晚饭,没啥事情做,一身劳累。大家围着电视看,我并不觉得有什么好看的,拿着手机到门口的大榕树下坐着。以前在一篇文章上知道了榕树,我没见过,如今见到了,出乎意料。太大,太老,据说几百年了,我坐在大榕树下,像母鸡双翼下的鸡崽。
父亲在接电话,母亲打来的。父亲说一切都好,不累,架子上很安全。只有我知道,父亲站在竹架子上的表情——恐高。这些年,同样的话,父亲不知对我说了多少次。在学校里,父亲总是叮嘱我要吃饱穿暖,再穷不穷教育,说他一切都好。我的眼泪流了下来,偶有行人路过,榕树下、墙壁上受惊的壁虎四处逃窜。天际的晚霞早已消散,城市的霓虹灯四处亮着,有些张扬,朝街道眺望去,没个尽头。
天气十分燥热,下雨天也透露着这种焦躁不安的热。有时候刮海风,带着挑衅的味道,雨水噼噼啪啪滴落在瓦檐上。这里的瓦房很有特色,不像家乡的那样,瓦檐宽阔伸展出来,这里的瓦房像娇羞的女子,而村里的瓦房则是山野汉子。当然,这里的瓦房是为了避开大风吹才这样设计的。六姨妈说,这是要刮台风了。只有刮台风的时候才能感受到一丝凉,却不爽,因为太过潮湿。
我不喜欢下雨天,一下雨就休息不能干活,我闲不住,父亲也闲不住。六姨妈问我,为啥毕业了不去找一份工作做一段时间,总比干工地好。这样的问题,我听过好多次了。母亲生病,从小到大,家里的担子大多是父亲一肩挑下,他太累了却从不说,我知道。我对六姨妈说,我也知道去做其他事情清闲还能学到东西,但是当务之急是要准备不久后的各种开支费用。其实生活不只是为了挣钱,还有其他。谁不是苟且地过着呢,只是从未忘记心中的远方而已,至于远方在何处?就快能看到了!
父亲不会说普通话,或者是非常蹩脚。一次因为另外一个小工做错了事情,和楼主发生争执,父亲被楼主数落一顿,一单活计谈不成了。我看到既然做不成活计了,索性操着一口普通话和楼主争论起来,父亲拉扯着我说出门在外为的是求财,不算委屈。父亲给我上了一课,我知道父亲这么多年在外打工受了不少气。
我们要走的时候,六姨妈带着我到菜市场买了不少菜,和父亲吃过饭后就回家了。乘坐的车和从贵州到潮安的车是同一辆,走的路线也是原路,不同的是目的地。临走之际,我在大榕树下拔了几株小榕树,细心地包裹好,带回家。几株榕树被我种在水池两边,可惜这喜热之物受不了山坳里的湿寒,一场凝冻后全死掉了。
在返程途中,父亲身穿一件廉价白色衬衣,衣领有些汗渍,却十分合身,父亲个高,倘若是工薪阶层,一定是少女们口中的“大叔”。想起才来时候,爷儿俩饿了一路,我买了些食物,顺手买了一瓶酒。车子出发的时候,浓厚的云层压在城市建筑上方,更低层的云似在车顶一样,有种喘不过气来的感觉。
车过海边时,海浪声声击打着海岸。海浪并不像电视上那样白,海鸥低空飞行,似乎肚皮就要贴在海水上一样。我指着海对父亲说,爸,你看,海。父亲点点头,不说话。这是我第一次见海,我知道他也是。可是未来我会有很多机会去看海,然而他却要在山坳里慢慢老去。
返程的车和去的时候一样,到了站就停。凌晨两点到五点,客运车辆必须下高速,我们在广西一个不知名小站休息,等到五点再出发。站台里十分拥挤,吃饭喝水、撒尿睡觉,人声鼎沸,夜市一般。
小站里的工作人员,或者说是商人,扯着嗓子卖吃食,态度十分不友好。我从包里拿出食物和父亲吃,父亲说他不饿,让我多吃些,他永远都这样。我拿出酒,你一口我一口喝完一瓶,真是多年父子成兄弟。
车子出发了,父亲睡着了,靠着我。我像他曾经给我盖被子一样,将一件外衣盖在他身上,他有白发了,皱纹也爬上额头了。
未来的岁月里,我将踏上新的征程,每一次孤独的背后,我都会想起和父亲相处的日子,尽管在我的读书生涯里,和父亲相处的时间少,但是父亲的爱从未缺席。看着熟睡的父亲,他的脸上有些褶皱了,像一道道铁犁划出来的沟壑,在这每一条沟壑中都曾播撒无数希望的种子。
九月了,杉树上的斑鸠咕咕咕地叫着,父亲和母亲送我到村口坐车,我将再次远行,父母的背影渐行渐远,最后以一个黑点的形式消失,也许有一天我们的村庄也会远去。
云贵高原的山坳某处,和那个湿热的他乡,两个世界。
起风了,带着咸湿的海水味道,我知道海风正往这边吹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