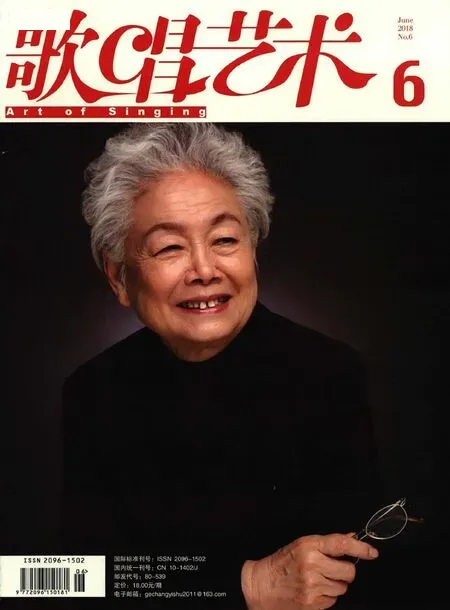阳光雨露滋润多成腕遇坎人挪活
——我看学生换老师
赵世民
大多数歌唱家,在学习阶段,没有不换老师的。
1985年我就认识了男高音歌唱家范竞马,那时,我为一家青年杂志专访了他。谈到学唱经历时,他说自己开始并没有老师,只是模仿广播电台里播放的歌曲。他是以男中音的歌曲《我爱这蓝色的海洋》考上的四川音乐学院声乐系。
入校以后,范竞马没有显露出很好的歌唱条件,没有老师愿意带他。是蓝幼青老师救了范竞马,“没人带,我就带呗”。范竞马被当成男中音跟蓝幼青学。后来中央乐团的韩德章在四川讲学,听了范竞马的演唱后,说:“你不是男中音,是男高音。”范竞马就投向了韩德章,他不但改了声部,学唱男高音,还对意大利美声唱法有了一个系统的概念。
1985年,范竞马又北上投在沈湘门下,系统地学习、实践意大利“美声”。1988年,他游学意大利,拜“世界十大男高音”之一的科莱里为师。1989年,又拜美国朱利亚音乐学院的费罗为师。以上这些都是有名的,还有没名的,那也不少。范竞马就是这样,在每个学习阶段都有不同的老师,或者某个阶段同时有不同的老师,帮助他成长为一位男高音歌唱家。
范竞马的老师,声乐教育的一代宗师沈湘先生在求学阶段也换过老师。最早的启蒙老师是他的父亲,一位留法归国的西医大夫,除了主业医生外,他酷爱西洋交响乐、歌剧等,自己还会吹小号,他从欧洲带回了大量交响乐、歌剧唱片,沈湘从小就被意大利“美声”浸淫着。中学时代,沈湘的老师是天津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合唱团的老师。后来他考到上海“国立音专”,又换过很多专业老师,有名的有苏石林、帕契等。
我采访过的歌唱家有上百位了,他们都换过老师。女高音歌唱家和慧,在安康上中学时,跟安康艺校的老师学声乐;考西安音乐学院之前,师从陕西师范大学的一位老师;考上西安音乐学院后,刚开始师从一位男低音声部的老师,后来换到男高音王真的班上;再后来,和慧又南下东进师从饶余鉴老师;出国游学后,她师从过多明戈、弗蕾妮等大师。
女高音歌唱家雷佳,在湖南省艺校学习时,有教学组几个老师教她;考上中国音乐学院后,师从邹文琴老师,后来又师从彭老师攻读博士。
冯健雪在“陕歌”时,跟过的老师就多了。后来到上海拜朱逢博为师,再后来又跟上海音乐学院的王品素老师学了两年。
男中音歌唱家廖昌永在四川时,师从四川省歌舞剧院的周维民学习,周老师也是沈湘的学生。考上上海音乐学院后,师从罗魏、周小燕老师。后来,廖昌永又拜饶余鉴为师。
既然每位歌唱家的成长都会换不同的老师,那为什么学生换老师还成了问题呢?我虽然没学过音乐,也没从事歌唱,但我和声乐圈接触了三十三年,知道不少事。比如,中央音乐学院有位声乐教授,就因为自己的学生换了老师,从此不再跟学生说话。中国音乐学院有位教授因为学生换老师,给气病了。有一位教授,因他的学生投奔另一位老师,就大骂后面这位老师是骗子,抢别人的教学成果。有位处于“地下”状态的老师,在自己和学生的音乐会节目单上公开了和学生的师生关系后,遭到这些学生公开老师的“围剿”。我发现,引出的问题、矛盾多出在老师身上。
我曾采访过一些在国外留学的歌唱名家,比如和慧、迪里拜尔、张立萍、梁宁、张建一、田浩江等,问他们国外的声乐教授对换老师怎么看?他们说这没什么,很正常,师生之间不会因此而产生矛盾,骂学生是“白眼狼”等。这是一个正常的教学生态、竞争机制。学生上课交学费,老师挣到了钱,把知识技能教给学生,就尽到了他的职责。我还发现,外国歌唱家在中国演出的节目单上很少提教过自己的老师。比如帕瓦罗蒂、多明戈、卡雷拉斯、卡巴耶等。我去意大利米兰斯卡拉歌剧院、纽约大都会歌剧院看歌剧,节目单上演员介绍也不提授业老师。我想,如果他们一直师从同一位老师或许就提了。正是因为他们换过的老师太多了,简介篇幅有限,提甲不提乙得罪人,干脆谁都不提了。
在国外的声乐教学中,把教学活动当买卖来看,依着市场经济的规律运行。范竞马跟我说,无论科莱里多么喜欢他的声音和味道,但要想上课,还是得凑足了学费。意大利“美声”大师费拉罗在清华大学办大师班时,我全程在场。我是大师班的策划者之一,知道他的学费在当时(2001年)可不低。有时,费拉罗大方地给谁多上一点儿时间的课,那也是在学员交够了学费的基础上进行的。
有些歌剧院的培训机构可能不收你的学费,甚至主动给你换各种老师,那他们也不是慈善或公益行为,而是想把你培养成才,在歌剧院演角儿,为剧院挣钱的,这都有事先签订的合同。说白了,歌唱教学就是商品交换,你跟我学,交了学费,就购买了教学服务。学生买甲的教学服务,买乙的教学服务,这是买方的自由;卖方——老师,是无权干涉的。
只要中外一比较,我们就知道目前在中国的声乐教学中出现这一问题和矛盾的根源何在。
第一,传统观念:师徒如父子。过去的戏班,从小拜师学艺,都是要立字据的。戏班里一般就一个师傅,其他的是师叔、师兄、师姐等。一个学徒成角儿,也是多人教育的结果,比如琴师、武师、身段老师等,但多归在一个师傅名下。如果换师傅,就意味着改换门庭,在本门派里意味着背叛,这是很严重的事,要逐出师门的。如果在武术行当里,还要面临原门派的门徒追杀。这种传统也显现地、潜伏地、或多或少地影响到我们的声乐教学。你拜我为师,就是我门派的人。我就曾见过有的老师举办自己学生的音乐会,宣传报道就以老师的姓,如“某家军”“某家班”等,就像当初马俊仁搞中长跑的团队,叫“马家军”。其实,“马家军”里的运动员也不一定就是马俊仁一个人带出来的。
过去的戏班为什么把自己的门徒把持得这么严?动不动就家法“伺候”?那也是那个时代市场竞争的需要。每个戏班能立足于演出市场,都有自己的绝活儿、看家本领,这些当然是绝密的。一个由学徒学成角儿的人,如果改换门庭,原戏班班主、也就是师傅,首先想到的不是你到别的戏班学到什么新东西,而是担心你把本戏班绝密的看家本领泄露给竞争对手,使对手在市场竞争中将战胜自己。要不然怎么会用“背叛”这么严重的词呢?其次,才是担心你学了竞争对手的绝活,再加上已经掌握的本戏班的绝活,将如虎添翼,可你是给竞争对手演戏挣钱,甚至挤垮自己的戏班。自己培养的人,反而成了自己的“掘墓人”。
第二,供养关系。既然师徒如父子,拜我为师、进我戏班,不但不教交学费,戏班还要供养徒弟,这也是事先立了字据的。结果,学成了或将要学成时,换老师了,改换门庭,那不等于我白养你了?
当代的声乐教学,这种“供养”关系还是很普遍的。比如,沈湘给他校外的学生上课,几乎很少收学费,而且赶上饭点儿,学生还在老师家蹭顿饭,这是常有的事。再比如孟玲,把学生当自己的孩子,给学生加课,几乎每个学生都享受过。诸如穿衣、吃饭、睡觉、生病等生活细节,孟玲都百般地呵护。
在这种“供养”的师生关系中,如果学生擅自换老师,原来的老师当然会有看法了。
第三,利益关系。我发现,由学生换老师而引发矛盾,多数是发生在已经成名或将要成名的学生身上。如果这个学生始终默默无闻,无论怎么换老师,原来的老师都不会有什么感觉。为什么对已成名的或将要成名的学生换老师就耿耿于怀呢?答案特别简单。你跟某个老师这儿学成名了,那老师也就有名了。在老师这儿,不是“名师出高徒”,而是“高徒造名师”。某某是跟哪位老师学成名的,相当于活广告,将会有一批学生投奔其门下,而这些学生大部分是要交学费的。学生换了老师,替后面的老师(没准是原来老师的竞争对手)扬名立万,大批学生都投到他门下,那原来的老师不就吃大亏了吗?所以老师不但要说你背叛师门,还要诋毁你后面的老师是骗子,专门抢别人的教学成果。
我发现有的声乐教师特别支持自己的学生换老师,那得从地方换到北京、上海,本科换到研究生,中国换到意大利、美国、英国、德国、法国等。我就知道贵州有一位老师,已经往中央音乐学院、中国音乐学院等专业音乐院校输送了数十位她的学生。这位老师为什么心甘情愿地让自己的学生换老师?首先,不换老师,学生就不会有更高的平台和更大的进步。其次,这也是利益关系。你教的学生考上中央音乐学院、中国音乐学院的越多,你的名气越大,投奔门下的学生就越多,收入自然也越丰厚。在皇宫里,母凭子贵;在声乐教育行当里,师凭生贵,但不是一般的学生,而是有名的、成了大腕儿的学生。
就换老师这个问题,我曾和西安音乐学院的二级教授、男高音歌唱家白萌讨论过。白萌说,美声唱法,一个学生要学的东西太多了,语言、发声方法、风格、表演等,往往一位老师是无法胜任的,所以换老师是再正常不过的。他在西安音乐学院、上海音乐学院,还有美国朱利亚音乐学院办的大师班学习时,就换过不少老师。所以他的学生要求换老师,他都支持。因为老师的职责就是培养人才,只要能成才,在不在你的名下都无所谓。再说了,学生成名成腕儿了,在你的门下学过是永远无法更改的。所以,老师不要像把着私有财产似的把着自己的学生,这不但把不住,甚至还影响师生关系。
三十多年前,沈湘经常跟我说,他们那会儿经常开教学研讨会,学生有什么困难、问题,大家一起“会诊”,有时就主动地给学生换了老师。有一次,我在沈湘的课堂上,听一个学生唱的某首艺术歌曲不到位,沈湘就说:“你去跟蒋英老师上上课,她在德国艺术歌曲方面是专家。”
1985年,我刚到中央音乐学院任教,教授本科生马克思主义哲学。有一天,在二道门看见一幅音乐会海报,是谭盾的硕士研究生毕业音乐会,那上面感谢的老师有他的作曲老师赵行道、复调老师段平泰、和声老师吴式楷、曲式老师吴祖强、配器老师刘霖、音乐史老师汪毓和、美学老师潘必新、音乐美学老师蔡仲德,还有“马列”老师赵文博,就连体育老师陈贵康也榜上有名。我当时看到这个名单挺感动的,谭盾认识到了,他成名、成腕儿是有这么多老师的功劳。这对我也是一个鼓舞,因为我是一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课教师,我教“马列”课也会帮助音乐学子成名成腕儿。
其实,不单声乐、作曲专业的学生成功需要更多的老师,几乎“一对一”授课的音乐学子都需要。
二十多年前,中央音乐学院的小提琴教授林耀基教学成果卓越,有很多小提琴学子纷纷“离开”原来的老师,换到林老师门下。有一位学生家长特别矛盾地跟我说:“为了让孩子出来,只能忍痛换到林老师班上。其实我们也知道,孩子的基础是原来老师打的,但没办法,这教学就像接力赛,不能把接力棒总攥在自己手里。”恰好,我也访过之前教这个学生的小提琴教授。谈到自己的学生换老师,他还哭了,说孩子家长没良心,抱怨林老师就不该接这位学生,说自己完全有能力带出这位学生……
郎朗的成长也是一个经典的例子。我访郎朗的父亲郎国任时,他说,孩子自小跟的是朱雅芬教授,到一定阶段,朱老师劝我,孩子不但要换老师,还要换环境,由沈阳换到北京。郎朗考上了中央音乐学院附小,换到赵屏国教授门下。郎朗顺利升到中央音乐学院附中,郎国任自作主张,又将儿子换到殷承宗门下。后来,甚至中央音乐学院附中文凭都不要,考到美国柯蒂斯音乐学院,换到当时的院长、钢琴家格拉夫曼门下。再后来,在格拉夫曼的支持下,又换到巴伦博伊姆门下。这期间,郎朗还跟小提琴大师斯特恩,指挥大师艾森巴赫、马泽尔、西蒙·拉特尔等世界顶级大师都学习过。郎国任告诉我,在换不换老师的问题上,家长自己一定要有主见,千万不能儿女情长、婆婆妈妈,要当机立断。换老师,当时带你的老师可能会有点儿难受,但如果孩子学成了,照样会传你的名。因为郎朗那个阶段,是你带的。
像郎朗,换不换老师,决定权不在自己和老师的手上,而在家长手中,因为孩子还未成年。可学习声乐的学生多已成年,所以换不换老师的权利,多掌握在学生自己手中。
学生多在什么情况下选择换老师呢?
第一种情况是学生碰到了声乐技术难题。或许这位老师能很顺利地解决其他学生类似的问题,就是到你这儿,老打圈圈,破不了圆心,有点儿类似“山重水复疑无路”;而换个老师,就有可能“柳暗花明又一村”。
中央歌剧院男高音歌唱家王丰,有一段时间就是高音上不去,“逢G必破”。后来换到男高音歌唱家程志门下,程志教他先用半声、弱声唱,他用半声、弱声很轻松地唱到小字二组的a、b,再到High C。就这样唱一年,然后再慢慢扩大到全声、强声,结果王丰高音难的问题解决了。后来他在中央歌剧院成功地演唱了《蝴蝶夫人》《图兰朵》《乡村骑士》《丑角》《茶花女》等歌剧的男一号。
我访女高音歌唱家和慧时,她谈到了自己遇到的坎儿。有一段时间,她的声音很通、也很洪大,但就是很难有质量地弱下来,这为她塑造角色带来了局限。后来换到饶余鉴门下,饶老师用一种方法让她知道了怎么唱弱声。自从有了弱声,她的演唱进步了一大块,能更丰满地塑造角色。
和慧说的,我和白萌都可以作证。2011年,我们在意大利维罗纳露天歌剧院看和慧唱《阿依达》里的女一号阿依达,在唱《祖国蔚蓝的天空》这首咏叹调时,和慧有一段弱声似蚊鸣,但这声音居然穿过百十人乐队的音墙,辐射到剧场每一个角落,让我形容,就像用一支长筒狙击步枪将和慧蚊鸣般的弱声,射到每一位听众的耳朵里。要知道,这个剧场坐满观众是三万人,且没有任何扩音设备,这是世界上最难唱的歌剧院!
第二种情况是师生气场不合,学生不信任老师。三十年前,沈湘跟我讲过,迪里拜尔之所以进步那么快,就是因为她完全信任老师,从不怀疑沈湘教她的任何方法,所以他们配合得特别好。但有的学生会怀疑老师,因为有时为改掉毛病用一种新的办法,不是几天就出效果的,甚至学生唱得还不如过去。学生就怀疑是不是老师教错了?如果经过几次这样的反复,我觉得学生也许换老师会好一些,没准他信任新老师,能和新老师配合好,为什么不换呢?
有一天,我在中央音乐学院旁西便门小公园见一个学生正在练咽音,我一听这种发声方法,就知道这位学生一定是私下投在某位咽音大师门下。而这位学生的主课老师我也认识,他最反对学生私下换老师学习,更排斥咽音训练法。我想这位学生一定是不信任自己的老师了,可又碍于各种非音乐的因素,不敢提出换老师,只能自己“双轨”制地学习声乐。这位学生见到我,脸一下红了,请求我千万别告诉他的主课老师。
我在想,我肯定不会“背叛”学生,找他的老师打小报告。但这样的“双轨”制,“互相打架”地学习声乐,会不会毁了这个苗子?正如我的担心,他后来没学出来。可他刚入校时,唱得多好呀!这样的学生,如果早点公开换老师,或许会是另一番景象。
第三种情况是学生想借势,利用老师在圈内的巨大影响力,更快地成名成腕儿。
我长期追踪采访研究的一位歌唱家,他换过至少两次老师,每次换老师前,他都征求我的意见。我说,你原来的老师教得那么好,没必要换老师。他说,要从实际出发,换的这位老师虽然在声乐技术上对自己帮助不大,但他势大,能把我推向一个更高的平台。正如他所说,自从换了这位老师后,他上电视晚会、大型音乐会的机会就多起来,确实没用多长时间就成了大腕儿。他换对了!
过去,我对这种换老师的情况有些偏见,觉得这新的老师抢了别人的教学成果。现在,我能正确地理解这种情况了。一个学生能成为歌唱家要经过很多环节,而其中一个重要环节就是要将学成的学生推向市场。有的老师因多年积累的人脉,能达到一呼百应,学生换到他门下,他也真的尽力给学生创造机会、提供平台。所以这样的老师在学生成名的过程中也是功不可没的。
像戴玉强、阎维文等大歌唱家,现在名下也有大量的学生。这些学生中的大部分是从其他老师那儿换过去的,他们确实经常带着学生参加电视节目、剧场音乐会、院校大师课,为这些学生成名提供了画龙点睛般的助力。这些学生的前任老师应该高兴才对,因为教师的目标,不就是为了培养有影响力的歌唱家吗?
在学生换老师方面,我发现一些可圈可点的榜样。比如作曲家谷建芬,20世纪80年代办了通俗歌手培训班,出了那么多的大腕歌手,毛阿敏、那英、孙楠、孙浩、崔京浩等。谷建芬会根据每个人的特点,给他们选适合的声乐老师、形体老师、文化老师等,一旦不合适了,谷建芬立马给他们换老师。因为谷建芬明白,她的歌手培训中心就是要培养社会需要的歌手,仅靠她一个人是不可能成功的。
现在一些成功的公司,其实也是把谷建芬的方法发扬光大了。歌手跟公司签约后,公司会全方位地给歌手选老师,演唱技术、形体、音乐创作、造型等方面都会给配备或换最合适的老师,所以每一个歌手的成名,都是幕后多位老师协同打造的结果。
我在想,我们音乐学院的声乐歌剧系为什么不能引进这种教学模式?声乐学子一入校,就相当于进了一个艺人公司,实行项目负责制。项目的负责人不一定是这个学生的声乐主课老师,但他懂声乐、懂市场,懂歌剧院、音乐舞台的需求,能预测歌唱行业发展趋势。在他的统筹安排下,给学生制订四年或五年甚至更长的学习计划,该换老师就立刻换老师,这样学生换老师也就不成为问题了。
培养歌唱家的艺术教育不是义务教育,这种教学活动具有一定的商品属性,放在市场经济环境中,声乐教育就是一种买卖。正如同消费者花钱去歌剧院、音乐厅购买歌唱家为我们提供的歌唱审美服务,歌唱家挣我们的门票钱,那么声乐教育也是学生购买教师的教学服务。在市场上消费商品,我们都会货比三家,买性价比最合适的商品,那么声乐学生也可以自由地买声乐教学服务。所以,声乐学生换老师是他们神圣不可侵犯的权利。既然是权利,当然也可以不换,我们同样看见了许多“从一而终”的歌唱大腕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