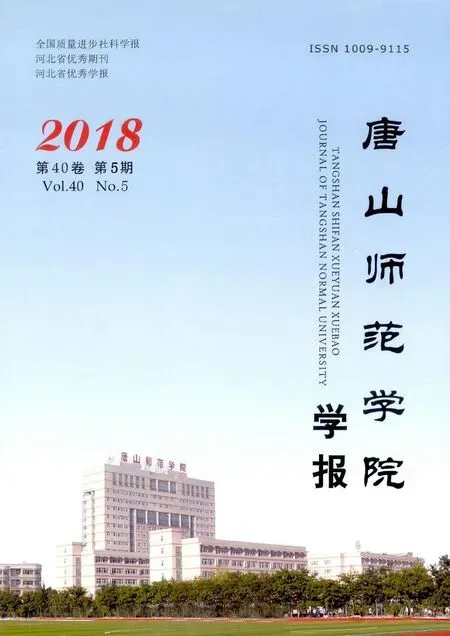汉语动趋式表达功能研究述评
周 红
(上海财经大学 国际文化交流学院,上海 200083)
动趋式是“动词+趋向动词”构成的结构,最早由吕叔湘提出[1]。动趋式语义类型丰富,句法类别多样,引起了学界较大关注。动趋式研究经历了一个由描写到解释、逐渐深化的过程。周红对动趋式的句法语义类别、特征和语义演变进行了梳理[2]。本文将从对称性、特殊构式、语言类型、偏误习得四个方面对其功能研究概述,从而对动趋式做一个比较系统全面的回顾。
一、动趋式对称性研究
对称性研究可以是语义相近结构的研究,如徐静茜描述了趋向补语“起”和“上”语义上的异同点,认为都可表示人或事物随动作由下方向上方、表示动作完成、表示事物随动作的形成而出现、表示动作开始并持续、表示够不够标准等。不同点主要有:前者指动作在同一个地点从下方升高,后者指从一处(低处)移到另一处(高处);前者地点总不外乎“地面”“桌面”或其它水平面,后者则不受限制;前者强调动作开始,后者则没有这样的强调;前者强调事物出现,后者强调动作完成;前者表动作完成只限于“收、做、藏”等少数动词,后者则相当普遍等[3]。
也可以是语义相反结构的研究。一是“上”与“下”的对称性,研究较多,如萧佩宜认为“上”和“下”在宾语语义角色上存在不对称:与“上”连用的宾语是目标含义,而与“下”连用的宾语则可以是带有目标或来源含义的词[4]。以上研究多是描述,未做进一步解释。缑瑞隆认为“V上/下”存在着“接触/不接触”“附着/不附着”“参照点”的语义对立,这是因为“上”有“施控是上”的隐喻,“下”有“受控是下”的隐喻[5]。任鹰、于康则从映射角度分析:第一,“上”终点常为得到凸现的前景化信息,到达终点引申出使某物附着于某物或某处;“下”原点常为得到凸现的前景化信息,离开原点引申出使某物脱离某物或某处。第二,“上”是“附着”“由低至高”,是一种正向移动;“下”是“脱离”“由高至低”,是一种负向移动;第三,“上”由低至高的移动易转化为心理上的目标的达成,“下”由高至低的移动易转化为对某一事物的占有[6]。李思旭、于辉荣认为“V上/下”还体现为单指向性(指向位移终点)与双指向性(可指向位移原点和终点)的对立,这受到“凹凸原则”的认知制约[7]。胡晓慧则认为存在[持续性]与[瞬间性]、[高尚]与[低下]的语义对立,这是因为[接触、附着]是持续的,[分离]是瞬间的;[愿望得到实现][占有某种事物]分别视为[等级或地位高][等级或地位低][8,p92]。周红认为二者在空间域上具有上向与下向、依附与脱离、前向与后向的语义对立,在状态域与时间域上对称性较弱;两者产生中立化的语用选择性在于“上”具有难达成性,“下”具有易控制性;这些均可通过驱动-路径图式进行解释[9]。这些研究对动趋式的对称与不对称进行了认知解释,使得研究进一步深化。
二是“来”与“去”的对称性,如卢福波认为“来/去”用于动词后,意义虚化,表趋向或背离说话人或叙述人的方向性标志,前者凸显起点,可带来源宾语,后者凸显终点,带终点宾语[10]。胡晓慧从空间、领属、时间、状态、数量、获得性状域引申义、目的等认知域分析了“V来/去”的对称与不对称:“V来”突显位移的终点,“V去”突显位移的起点;“V来”的位移终点是可预知信息,“V去”的位移终点是不可预知信息[8,p155-156]。
三是“起来”与“下来”的对称性,如刘月华比较了表状态义的“起来”与“下来”的句法语义差异:第一,“起来”可搭配正向和负向形容词,可表合乎常规的变化,也可表不合乎常规的变化;“下来”只能搭配负向形容词,只表合乎常规的变化;第二,“下来”可表新状态的开始,也可表新状态达到的终点;“起来”只能表示进入新的状态,不能表示状态达到终点[11]。
四是“上来”与“下来”的对称性,如童小娥从事件角度分析“V上来/下来”的对称与不对称:表达时间位移事件时,只有“述+下来”结构,没有“述+上来”结构;不对称性与物理空间的上下位移事件密切相关:由物理空间的上下位置关系投射到不同认知域中,可衍生出“动态为上,静态为下”“时间较早为上,时间较晚为下”“高量度的状态位置为上,低量度的状态位置为下”“动态为上,静态为下”“前为上,后为下”“靠近观察者为上,远离观察者为下”“不知道为上,知道为下”等抽象位置关系[12]。
二、动趋式特殊构式研究
(一)“V+起来/上去/来+AP/VP”研究
该类构式如“这辆车开起来很快”“这桃子摸上去软软的”“这事说来很奇怪”,其中NP处于主语位置上,但它是V的支配对象。这类构式的表达功能引起了学界的较大关注,存在较大的争议,主要有五种观点。
1. 中动句观
将该构式比对英语的中动句,但在中动句的理解与范围上明显存在差异。曹宏将其看作中动句,即NP在V-NP的时候通常呈现出AP状态,整个句子表达情状类型的状态性特点和命题的通指性特点[13,p11];句首NP具有通指性特征,充当话题,提供言谈的出发点,“VP+AP”针对话题做出评论[14,p205];中动短语VP具有传信功能,表示说话人做出评论的根据和信息来源[15,p67]。何文忠认为中动结构表述虚拟事件,具有恒时性,功能是聚焦事件的被动参与者对事件发生所发挥的积极作用,可表由于主语内在的特性而使得动作的发生呈现出某种性状;并认为难易句与中动句不同,不排斥动词补语,如“塑料轮胎磨平起来很不容易”[16,p12]。余光武、司惠文认为AP语义指向V的格式是典型的中动句,表示的是主语的内在属性,而且主语要对谓语感官感受的事件具有致使性,如“这本书读起来很容易”,排除了AP语义指向NP和AP语义指向隐含施事的情况,如“这本书看起来很不错”“这本书读起来很轻松”[17,p71-72]。
中动句的语义限制条件主要集中在:(1)施事论元的隐含问题。如宋国明运用约束理论分析了中动句的形成,认为施事论元隐含出现在动词旁,并吸收动词的格,造成受事论元名词组移位,变成表层结构的主语[18]。曹宏赞同宋国明关于中动句的理解,认为中动词隐含的施事在语义指称上的任指性特点,隐含的施事出现只能通过介词和轻动词“使/让/叫”的引导,或者包含在 AP中,一般不能以主语的身份独立出现[14,p25]。何文忠则认为隐含施事论元不能作为中动结构的界定标准,实际上动词的逻辑主语的论旨角色并不一定是施事[19]。(2)NP的语义功能问题。曹宏认为NP有时是定指的,但这并不影响句子整体上的通指性[14,p211]。何文忠认为中动句除了满足体式条件(动词为完成类事件动词)外,还要同时满足广义责任条件(被动参与者对事件的发生负责而具有认知显要性),主语可以由工具、处所等事件的外围参与者充当,还可以是方式、对象等其他角色[16,p10]。(3)V与AP的语义限制问题。曹宏分析认为 V都必须是及物的自主动词;形容词必须是在语义上指向中动词的受事的形容词,或者是在语义上指向中动词的施事的非自主形容词,而不能是自主形容词[13,p23]。何文忠提出进入中动构句的选择限制是选择满足体式条件的事件动词和选择语义上不是由施事自主控制的副词或形容词[20]。
汉语中动句的句法构造与类别研究,如曹宏认为中动句的层次构造为 NP|(VP+AP),中动短语VP是状语、其后面的成分AP是谓语核心[21,p42];后附成分“起来”具有评价义,“来”是起始义“起来”的紧缩形式,“上去”具有附着义[22];根据中动短语VP在中动句中可能的位置,分可前置型中动句和不可前置型中动句;根据中动短语删除后剩下的NP+AP能否成立,分可删除型中动句和不可删除型中动句[21,p44-45];还分析了从典型的受事做主语的中动句发展到工具和处所做主语的中动句的过程[15,p63]。余光武、司惠文将“NP+V-起来+AP”分化为三种:AP指向句子主语NP(A式),AP指向V的施事(B式),AP指向动词 V(C式),并可通过是否可删去“V起来”、“V起来”是否可移至句首NP前、是否可变为NP+AP+V、是否可补上施事等句法测试来比较三种句式,认为C式是典型的中动句,表示的是主语的内在属性,而且主语要对谓语描述的事件具有致使性[17,p72-75]。张德岁将“VP+AP”结构细分为三个小类:“VP+AP”式典型中动句,AP语义指向VP,即把VP所代表的动作行为作为谈话的主题,AP是对这一主题做出的评论,如“跑起来非常快”;“VP+AP”式非典型中动句,AP语义指向跟 VP相关的施事、受事等,V的意义具体、实在,是非典型的主谓结构,如“她生来苗条纤细,看上去弱不禁风”;“VP+AP”式非中动句,VP用作独立成分,V的语义高度虚化,AP指向语境中省略的施事或受事,如“这种方法看起来还不错”[23]。
2. 话题句观
以殷树林、宋红梅为代表。殷树林认为“NP+(状语)+V起来+AP/VP”是最常见的一般话题句:NP充当句子的话题,“V起来+AP/VP”是对话题的评述,“V起来”起附加说明的作用,看作全句的状语。与英语中动句主要不同之处在于:可不表实体的性质,而表示其他条件的变化对动作造成的影响,如“以后你们的车存起来就方便了”;隐含的施事也可以是特指的;可否定AP;排斥动词补语。并从底层结构上进行了区别:语义指向NP的“V起来”虽可去掉,但它具有概念和人际功能,是固有性质AP的凸显手段,可以给句子添加主体意识,根本不涉及内论元升格等操作;语义指向V的格式中NP为实现话题化而前移至句首,受韵律影响V后加上“起来”[24,25]。宋红梅认为“这个面包吃起来很香”之类的格式不是中动句,原因有二:“这个面包”是“吃”的客体,也是“很香”的主体,这与中动句主体名词背景化不同;“吃起来”不是谓语中心,这与中动句是相对于主动和被动而言的说法也不一致。她认为这类格式也不是一般的话题句,而是有形态标记的话题句:强制性的NP移位是由于“V起来”中的“起来”所具有的强话题性特征所致[26]。
3. 述补结构观
熊仲儒以“V-得”句为基础,从语义指向和结构上的平行性竭力证明“V-起来+AP”是个述补结构:都指向名词短语与动词;主语前可以有“是不是”正反重叠;主动词不能采用“A不A”式正反重叠;补语成分都可以有“A不A”/“是不是”式正反重叠;否定词出现在补语部分;否定词“不”不能出现于主动词之前;“V-得”与“V-起来”之间不能插入任何成分;NP与其后的成分之间有语音停顿,并可增添语气词。“V-得”句与“V-起来+AP”句不同的是:前者描述的是状态变化,是有界事件;后者描述的是主语的永恒属性或命题的通指性[27]。
4. 构式观
吴为善将“NP+V起来+AP/VP”看作构式,具有即说话人对某种活动或现象的状态所引发的主观感受加以评述的构式义,并认为不是中动句:该构式命题虽然具有通指性,是建立在说话人主观意念上的,而非社会规约化共识基础上的;NP更多的是定指或特指的,在具体语境中还会突显NP的特征(说明理由);“V起来”肯定不是谓语核心;AP多是以形容词为中心构成的词组,是真正的谓语[28]。周红赞同吴为善的观点,认为该构式表达在某认知条件(或情况)下认知对象(某实体或事件)状态特征被动引发认知者对其产生某认知结果,具有一定的致使性;“V 上去+AP/VP”“V 起来+AP/VP”“V 来+AP/VP”的主观化程度依次增加,其中受事型和评价型占优势,时间认知条件范围广,感官或言说类认知条件下易替换[29]。
5. 中立观
避开“S+V起来+AP/VP”格式是中动句的争议,着眼于格式本身的句法语义特征。吴峰文根据句首 NP与动词的施受关系将“NP+V-起来+AP”分化为两类,其中受事是广义受事,还包含工具、处所、结果等;V绝对排斥述补式的动词、V不能是心理感官类的动词、V的时态具有不确定性;还具有句首NP的通指性、动词V的无界性、施事的隐含性、格式的非事件性等句式特征[30]。黄冬丽、马贝加将其分为三类:S为施事型的、S为受事型的和S为当事型的,并认为“V起来”表达预测、估计和评价义,具有较强的主观性,含有预设背景[31]。
(二)“V来V去”构式研究
学界均认为“反复”是该构式的核心语义。吕叔湘、刘月华均认为“V来V去”表动作的多次反复[32-34]。陈前瑞更是认为该构式是反复体的一种[35]。然而,李晋霞[36,p63]、刘志生[37,p74]分出[+行为义,+向度义](A 类)、[+行为义,-向度义](B类)和[-行为义,-向度义](C类),认为“想来想去”类具有持续义,“说来说去”类具有归总义。对此,曾传禄认为不管V是否持续动词,该格式都表动作行为的反复[38,p23]。杨德峰批驳了李晋霞提出“动作的持续进行或重复发生”的说法,认为这抹杀了“来/去”的作用[39,p207]。张虹则认为反复是持续的,区分了空间位置和非空间位置持续、反复的变化[40,p66]。周红认为空间域和时间域分别对应循环反复和持续反复两类反复义[41,p26-28]。
对进入该构式的动词小类多是从持续与瞬间[36,p64]、单音节与多音节[39,p207]、动作与心理[40,p66]等角度进行说明,但未能很好地分析格式与动词之间的互动关系。对该格式后续成分的考察,李晋霞A类后接“目的型”和“评价型”,B类后接“结果型”[36,p65-66];曾传禄认为A类还有“结果型”和“伴随型”[38,p24];杨德峰则通过统计发现出现频率为结果型>伴随型>评价型>目的型[39,p204];周红则认为目的型多于评价型,除此之外,还有接续、原因和解释三种类型后续小句[41,p30-31]。
对该构式的语法化过程存在差异。李晋霞认为A、B类元代时出现,两者之间没有语法化关系,C类是由 B类语法化而来的[36,p67-68]。刘志生和曾传禄则认为 A、B、C类具有演变的渐次关系,即A类→B类→C类[37,38]。周红认为空间类出现于六朝时期,时间类出现于南宋[41,p32-33]。
对该构式语用功能的理解存在差异。张虹认为该构式具有主观评定的功能[40,p67]。王平认为该构式表反复纠缠,很难使动作者或相关的人感到满意,多带有“不如意”的主观色彩,还可用于具有[+小巧]特征的被移者的活动[42]。杨德峰则认为A、B类用于对动作进行描述或陈述,不带感情色彩;B类后续小句表示的结果可以是积极的,也可以是消极的,但没有倾向性[39,p204-205]。周红认为不管后接小句是未实现预期、实现预期还是实现非预期,该构式不具有主观评定性,也不具有“不如意”主观色彩[41,p31]。
(三)其他动趋式特殊构式研究
主要有“V+得/不+来”“V+得/不+起”“名词/拟声词+起来”“V得(不)过来/过去”等特殊构式。宋玉柱分析了“这样的文章我写得(不)来”之类的格式,其中“来”是动词后缀,表示V得/不了(liǎo)[43,44]。徐静茜则认为这类格式表示“有无能力完成某事”,在吴方言中普遍存在,由表“能/会/成”的动词“来”语义虚化而来,吸收进普通话中动词只限于“谈、合、处”等少数几个,表“融洽”义[45]。史有为认为“得/不来”是表能力的合成助词,“融洽”义只是“能力”的引申[46]。彭湃、彭爽分析了够得上或够不上义形成的“对得/不起、看得/不起、瞧得/不起”,该类格式是非自主的,多带人称宾语[47]。邱天分析了“程度副词+名词”和“名词+起来”的异同,认为只有具有显著描写性语义特征的名词如“草根”“流氓”等才能进入格式中,前者表示属性特征所达到的深度,后者表示属性特征状态上的变化、置换和持续[48]。封帆则认为除了动词、形容词加“起来”可表开始、持续义外,还提出“名词/拟声词+起来”也可表开始、持续义,如“你今天怎么突然‘绅士’起来了”“感冒发烧以后,耳朵也嗡嗡起来了”等[49]。曾传禄认为“V得(不)过来/过去”常常以“障碍图式”为其内在隐喻基础映射到抽象空间。“V得(不)过来”表示有无能力周遍完成,而“V得(不)过去”发生了分化,有的表示某人或某事可能或不可能通过某种“障碍”,有的表示某物或某种行为事件是否符合一般的标准、情理,是否能为人所接受[50]。曾文运用意象图式解释结构的多义性,说服力较强,具有一定的借鉴作用。吴为善、夏芳芳认为“A不到哪里去”构式表达说话者认为某个主体性状的程度不会超出某个有限量幅的评价[51]。
除此之外,还关注动趋式固定短语的词汇化过程及表达功用,主要有“看上去”“看起来”“看来”“话说回来”等。张谊生分析了“看起来”和“看上去”由动趋式短语虚化为评注性准副词的词汇化过程,二者在搭配关系、表达功用、观察视角和虚化程度等方面不同[52]。刘楚群认为“看上去”“看起来”和“看来”的虚化程度不断加强:“看上去”更倾向于现象观察的结果,体现出某种评价意义;“看来”更倾向于逻辑推理的结果,体现出某种推测意义;“看起来”则居于二者之间,既可表推测,也可表评价[53]。刘楚群将语义虚化的固化语“看起来”作为预转语,可联结转复句,其基本语义特征是主观判断,可体现现象和本质的对立,前后分句间的语义关系可分为相斥性对立和相容性对立两类[54]。李胜梅将“话说回来”作为回说自述短语,“话说回来”增加了话语的前后语义连贯性,一般出现在摆事实讲道理阐明自己观点时,使对某一特定话题的阐述更全面客观,更具有可接受性[55]。
三、动趋式语言类型研究
(一)汉外对比研究
主要为与英语、日语与法语的对比。居红比较了“上/下”类、“进/出”类和“回”类动趋式与英语中相对应的形式,英语中使用“VP+up/down”“V+into/out of”“VP+in/out”“VP+back”方式,或者使用“V+up+to+N、V+down+from+N”“V+in+to+N、V+out+from+N”“V+back+to+N”方式表示,其中 up/down、into/out of、in/out、back指明方向,to/from指明起点和终点[56]。于善志等认为汉语趋向义有三种表达方式:趋向义自含性动词、VP-内趋向动词或介词性附加趋向成分、VP-外趋向动词,并有内驱力与外驱力之分。英语趋向义则只通过趋向义自含性动词或介词短语来体现,如:“He is climbing the mountain.”“She put it in the bag.”[57]朱巨器比较了汉语的“来”“去”和日语的“来る”“行く”在基本词义和引申词义上的差别,动趋式体现在vcv型、vpc型、vg型、vpg型、gpv型等[58]。耿京茹分析了汉语趋向补语与法语中不同类型完成体动词之间存在的对应关系,如法语中有些动词的意义较宽泛,可对应于“V+来”和“V+去”;汉语动词只能表示动作行为本身,而法语中的有些完成体动词可表动作行为,还可表结果等。二者句法表现也不尽相同:汉语用动词(形容词)+趋向补语,法语通常用“一个动词”或“动词+副词”的形式来表示;汉语趋向补语句中宾语的位置复杂多样,法语句中由名词充任的宾语位置比较简单,或者位于动词后,或者位于介词后[59]。这些文章多限于例举,缺少一定的解释。
(二)方言中的趋向补语研究
趋向补语“起去”一般认为在普通话中少见,可在不少方言中却出现频率较高,使用范围较广。主要研究有:马晓琴认为陕西方言“起去”在动词、形容词后面作补语时只表趋向意义,没有引申意义[60]。张光明认为晋语忻州方言“V起去”可与名词、代词和形容词组合表示动作或动作的趋向,还可用“不/没+V起来”或“V+不+起去”表否定义[61]。张清源认为成都话有“V起去”,表人或物在水平方向由近而远的移动,也可表制造出某种成果或结果,“V起”表示“去”的伴随状态,“去了”表示说话人对事态的一种强调;还有“V起 xy”复杂形式,xy即除“起来、起去、开来、开去”之外的复合趋向动词,如“把箱子搬起上去”[62]。彭兰玉认为江西安福方言“V起去”可表示人或物向上离开原来所处的着落处,也表用于受人操控的物件的动向,也有类似忻州方言的否定形式,还有“Q去去”和“Q来去”形式,中间的“来/去”表示位移与说话人所处位置的关系,末尾“去”表示离开[63]。崔振华认为湘方言中的“起去”由动作动词表示位移,到作趋向动词表示位移,再到作趋向动词表示动作行为、性质状态的继续,其词汇意义逐步虚化,语法意义逐步凸显,已经完成了语法化[64]。
其他趋向补语的研究,主要有:何天祥描述了兰州方言里的“上”和“下”,认为用“V上/下”可表示说话者的不同立场,如“东西不错,价钱不贵,买上吧。——好,买下”;在两个动词之间也使用“上/下”表示两个动作的同时或连续,如“他唱上走了”;“V下”可表状态或结果,且含有否定的、不幸的意味,如“他把祸闯下着”[65]。丁力将安康方言中的“V开(NP)了”结构分为两种:表示事件已完成和表示事件业已开始且持续进行,并分析了二者的句法语义差异[66,67]。谷向伟描写了林州方言的动趋短语“V来”与“V上来”,认为趋向动词可以和动词“来”组合,但非趋向动词却不能说“V来”,要说成“V上来”[68]。罗昕如、龚娜分析了湘方言中的“V+X+趋向补语”结构的句法语义特征,其中V多为单音节动词或性质形容词,X是动态助词,表动态或动向;该结构常用于祈使句与陈述句中,前者不能使用表完成的“X”“咖”或“哩”,后者“X”的各种形式都可使用,表义有所不同[69]。
方言中趋向动词的语法化研究。吴福祥概括出与趋向动词相关的四个语法化模式:从趋向动词到比较标记、从趋向动词到傀儡补语或能性助词、从趋向动词到补语标记、从趋向动词到空间/时间/与格介词,认为尽管不同方言里“上/下/来/去/起/过/落”等语法成分具体语法功能和演化路径不同,但最终均可追溯到趋向动词[70]。
方言中趋向表达的句法语义类型研究。唐正大将关中方言位移事件分为两类:一类是路径动词表达位移事件,包括“直指性路径动词(来)+背景名词”和“非直指性路径动词(上/下…)+背景名词”;另一类是趋向补语表达位移事件,包括终点位移事件、起点或途径的位移事件、表达和使役性位移事件,分别如“张三爬着/到那一座山上去咧”“长虫打窝窝里岸钻出来咧”“张三打井上面往井里面扔下去一个个绳”。关中方言在位移表达上属更彻底的“卫星框架式”类型[71]。
四、动趋式偏误习得研究
(一)动趋式偏误研究
杨德峰发现英语、朝鲜语和日语母语学习者习得趋向补语时的主要问题是宾语类推泛化、搭配错误、立足点错误和错把表示引申意义的趋向动词当作动词来使用等,并指出这些错误既有语内迁移的影响,也有语际负迁移的影响[72-74]。李淑红认为趋向补语与英语动介结构的差异性越小,留学生对趋向补语的掌握就越容易,趋向补语体现的时空知觉越具有独特性,留学生对趋向补语的掌握就越难;并提出在对外汉语教学与教材编写上应强调汉语趋向补语的空间知觉和时间知觉[75]。吴丽君认为日本学生学习趋向补语的偏误主要集中在该用简单趋向补语的地方用了复杂趋向补语和回避使用引申义的趋向补语两个方面[76]。黄玉花分析得出韩国留学生中高级汉语学习者偏误在于趋向补语的残缺、动趋式带宾语时宾语的错位、趋向补语的混用等,影响习得的主要因素有趋向动词的语法化增加了习得难度、动趋式使用频率与趋向补语习得成正比、趋向动词组合能力与趋向补语使用频率成正比、母语干扰作用、教材编写与课堂教学等[77]。
(二)动趋式习得研究
外国学生习得动趋式研究,主要研究有:钱旭菁统计了日本留学生的作文和问卷调查中初、中、高三个阶段趋向补语的准确度顺序,找出日本留学生趋向补语的习得顺序:动词不带宾语的简单趋向补语、动词不带宾语的复合趋向补语、“起来”表示开始(不带宾语)、动词带一般宾语的趋向补语、动词带处所宾语的趋向补语、“出来”表示暴露、“起来”表示评价、“过来”表示恢复和“过去”表示失去、“下来”表示开始、“起来”表示集中和“起来”引申带宾语[78]。杨德峰分析得出了不同母语习得者的共性与个性:与趋向补语的引申意义的抽象程度成正比,趋向补语的引申意义越抽象,习得起来就越难,反之,就越容易[72,p64];“动词+复合趋向补语(引申义)”和“动词+复合趋向补语+宾语”较难习得,“动词+简单趋向补语”和“动词+趋1+宾语+趋2(引申义)”较易习得;“动词+复合趋向补语”对朝鲜语母语学习者来说比较难习得,而对日语母语学习者和英语母语学习者来说就不是那么难;同样,对英语母语学习者来说,“动词+复合趋向补语(引申义)+宾语”不太难,但对日语母语学习者和朝鲜语母语学习者来说却很难[74,p34]。肖奚强、周文华探讨了外国学生习得趋向补语句的情况,首先将趋向补语句划分为 7类句式、14个下位句式(分本义和引申义),其次对比了汉语母语者使用情况,分析了外国学生在不同阶段各句式的使用情况和偏误情况,得出的结论主要有:外国学生汉语趋向补语总的使用频率只占到了汉语母语者使用频率的一半多一点;趋向补语句的总体使用频率是随着学习阶段的上升而递增的,正确率总体上是随着学习阶段的提高而递增的[79]。
儿童习得动趋式研究,主要有:邹立志等探讨了普通话儿童“上、下”两组共六个趋向动词习得的时间序列、产出频率、语义发展规律等,认为谓语用法习得先于补语用语,单音节习得先于双音节;单音节产出频率高于双音节;“上”的产出频率高于“下”,“来”组高于“去”组,“上”作补语的频率远高于“下”;语义习得基本遵循“趋向义→结果义→状态义”的发展趋势,但只有“上”例外,“上”的结果义先于趋向义出现,这是由“上”的基本语义和语用频率决定的,“上”侧重于运动的终点,易脱离原始意义而产生隐喻意义,导致使用频率和充当体标记能力远强于语义上与之相对的反义词“下”[80]。
五、结语
动趋式是具有汉语特色的重要结构,学界对其功能进行了较多研究,取得了不少研究成果。但目前仍存在不少问题:一是缺乏跨语言或跨方言的比较;二是仍多限于结构主义研究范围,分析解释较少;三是动趋式的语法化与词汇化研究不够;四是不同动趋式的功能分工及原因还有待进一步探讨。动趋式功能研究的重点是立足于语言类型学的研究视野,加强不同语言、不同方言等之前的异同分析,探究共时类型和历时类型的演变,构拟语义地图,加强认知功能解释,并以此观照语言习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