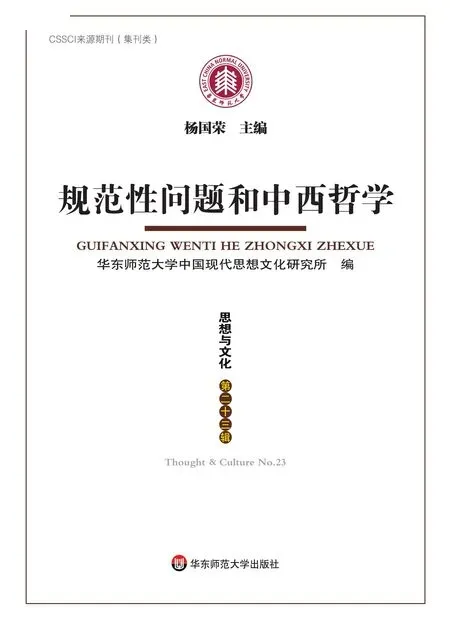美德是否可教,如何教?*
●
[内容提要] 孔子的教学内容既不是理论知识也不是技能,而是成德之方。尽管孔子充分认识到,一个人最终只能靠自己变成有德之士,但他确实认为,美德之人可以做很多事情去帮助别人成为有德之人,而其中最重要的是成为美德典范。任何一个有德之士当然都可以做到这一点,不过,孔子更加注重政治领袖,因为他们的影响更广更深。因此之故,在孔子的政治哲学中,政府的首要职能是对民众的道德教育,这与当代政治自由主义形成鲜明对照;此外,政府履行道德教育的职能主要不是通过法律和其他政治手段,而是通过统治者自身的道德典范作用,这又与亚里士多德的观点形成鲜明对照。在孔子看来,法律和惩罚还不能完全废除,但应该仅仅作为临时性的补救措施。即使这样的措施势在难免,一位有德的政治领袖在不得不使用这些措施时也会自然而然感到悲伤,一方面因为恶人令人遗憾的状态,另一方面因为他自己未能通过其他措施改变恶人。
一、 引言
人们普遍认为孔子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私人教师。这一看法未必正确。[注]孔子之前,晋国的叔向也是一位私人教师;大约在孔子所处的时代,郑国邓析、鲁国少正卯、周王室老子、卫国蘧伯玉、齐国晏婴、楚国老莱子、郑国子产,以及鲁国的孟公绰皆以非官方的身份授徒。此处参见蔡尚思: 《孔子思想体系》,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177—178页。尽管如此,但可以肯定的是,他作为私人教师的影响在中国历史上无人企及;弟子三千的说法可能有些夸张,但他的学生应该人数不少。是否每个人都能通过教育成为完美的人?孔子对这个问题的回答似乎并不一致,因此我们首先考察这个表面上不一致的回答(第二节)。为了理解这种表面的不一致,笔者将论证,孔子主要讲道德教育,旨在帮助学生成为有德之士。这让我们联想到美德是否可教的苏格拉底问题(第三节)。笔者认为,虽然孔子对这一问题的回答是肯定的,但他并不认为教美德就如同教理论知识或技术技能。孔子认为,教人成为有德之士,最有效的方法莫过于让自己成为道德典范(第四节)。个人和政治分离,这是当代政治自由主义的教条,而在孔子那里并没有这样的区分。在他看来,政府的主要职能是对民众进行道德教化,尤其是通过政治统治者的典范行为而非诉诸法律或者公共政策(第五节)。最后,笔者将以简短的结语绾结全文(第六节)。
二、 孔子教育哲学中一个表面上的悖论
孔子有一名言,“有教无类”(《论语·卫灵公》;以下凡引《论语》只注篇名)。这一主张的意义,首先不在于人皆有平等的教育机会,而在于人皆有走向完美的可能性: 一个人无论贫富、智愚、贵贱,教育都将对其产生影响。这一主张具有革命性,因为在孔子之前的时代及其所处的时代,官学和私学都只对贵族开放。尽管我们没有绝对可靠的资料[注]胡适: 《中国哲学史大纲》,《胡适学术文集: 中国哲学史》,北京: 中华书局,1998年,第87—88页。,但的确可以从《史记》、《吕氏春秋》及《论语》本身的其他章节中了解到,孔子的学生子路原本为“野人”,子贡经商(一种被人轻视的职业),仲弓的父亲是“贱人”,子张来自鲁国一个地位低微的家庭,而颜涿聚曾是强盗。[注]蔡尚思: 《孔子思想体系》,第192页。事实上,孔子的学生鲜有出自富贵者。而且,这里提及的子路、子贡、仲弓名列孔子十位最卓越的学生(见《先进》),而孔子认为,仲弓甚至可以成为一国之君(见《雍也》)。因此,在当代著名儒家徐复观(1904—1982)看来,孔子对中国文化最重要的一个贡献,在于他打破人与人之间不合理的区分,倡导人皆平等,属于同一个类。
孔子认为每个人都能通过教育成为完美之人,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基于他对人性的形上学看法:“性相近也,习相远也。”(《阳货》)孔子在《论语》中唯此一章论及人性。后世儒者激辩人性善恶,常常试图由此章弄清楚孔子究竟主张性善抑或性恶。显然,仅此章并不能提供明确的答案。它明白告诉我们的是,教育至关重要。不过,让我们感到困惑的是,孔子在下一章(有些版本将它与本章合为一章)的论述似乎与此相左:“唯上知与下愚不移。”(《阳货》)对此常见的解释是:“性相近也,习相远也”讲的是一般原则,“唯上知与下愚不移”则意在指出一种例外情形。例如,陈大齐认为,孔子主张人性分三等: 上知(极少数)、下愚(也是极少数)和居中者(大多数)。因此,“性相近也,习相远也”讲的是居中的大多数人,对他们来说教育很重要;“唯上知与下愚不移”讲的是居于两端的“上知”和“下愚”,对他们而言,教育要么无效,要么没有必要。[注]最愚蠢的人不可能通过教育成为聪明的人,而最聪明的人既然生而知之,自然无需教育。此处参见陈大奇: 《孔子学说》,台北: 正中书局,1964年,第277页。
为了有更好的理解,我们有必要看一看《论语》中相似的一章。看到自己的学生宰予昼寝,孔子言曰:“朽木不可雕也,粪土之墙不可杇也。于予与何诛?”(《公冶长》)显然,宰予必定属于顽愚不化之辈。倘若这样,孔子不会浪费时间继续教育他。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宰予不仅继续留在孔门,而且最后还成为十位成就最高的学生之一。宰予因为在白天睡觉,被孔子比作不能雕刻的烂木头和不堪涂抹的由腐土垒成的墙。换言之,他不努力学习,因此属于那种虽困而不知学的人。[注]孔子认为这类人层次最低:“生而知之者,上也;学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学之,又其次也;困而不学,民斯为下矣。”(《季氏》)这样,当孔子说下愚不移的时候,他的意思是说那些不学习的人是不会变聪明的。只要愿意学习,任何人都可以变聪明。因此,孔子说,他从来没有见过一个人缺乏为学习所必要的理智能力。(《里仁》:“吾未见力不足者。”)他的学生冉求说:“非不说子之道,力不足也。”孔子回曰:“力不足者,中道而废。今女画。”(《雍也》)因此,孔子要求他的学生不要自以为能力不足而中途放弃。就此而言,学习“譬如为山,未成一篑,止,吾止也。譬如平地,虽覆一篑,进,吾往也”(《子罕》)。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笔者认为,宋儒程颐对这段文字的解读貌似激进,实则深达孔子之意: 孔子讲上智下愚不移,“非谓不可移也,而有不可移之理。所以不移者,只有两般: 为自暴自弃,不肯学也。使其肯学,不自暴自弃,安不可移哉?”[注]程颢、程颐: 《二程集》,北京: 中华书局,1989年,第252页。程颐所讲的不可移之理乃是: 任何放弃自己的人都不会变聪明,任何努力的人都会变得聪明。
不过,如果以上理解不误,下面这段文字就变得令人费解了:“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泰伯》)“可”字可能的意谓,包括“能够”与“被允许”,与之相应,其否定词“不可”则可能意谓“不能够”或“不被允许”。因此,传统对孔子上面这句话的解释主要有两种。按照其中的一种解释,“可”意谓“被允许”,因此孔子允许百姓做某些事情,但不允许他们知道这些事情。批判孔子和儒家的人(尤其是在20世纪70年代的反孔运动中)接受这种解释,以证明孔子有愚民的想法。不惟如此,一些对儒家抱有更多同情理解的注家也接受这种解释。例如,清儒颜习斋(1635—1704)在捍卫这种解释的同时,还论证“可”不应解为“能”。在他看来,人们要是知道了这些事情,“则离析其耳目,惑荡其心思,此不可使知也。后儒圣学失传,乃谓不能使之知,非不使之知,于是争寻使知之术,而学术治道俱坏矣”[注]程树德: 《论语集释》,北京: 中华书局,1990年,第533页。。
大多数当代学者接受了另一种传统的解释,即以“能”释“可”,这样孔子之意在于,有办法让百姓做事,但没有办法让百姓知道事情。倘若如此,则关键的问题在于,为何无法让百姓知道某些事情。典型的回答是百姓缺乏知道这些事情的理智能力。例如,汉儒郑玄(127—200)认为,“民”实际上意谓着“冥”,即距人道甚远的顽愚之民。[注]程树德: 《论语集释》,第532、533页。清儒赵佑虽然没有说百姓距人道甚远,但他也以百姓为愚:“民性本愚,故不可使知之。王者为治便在议道自己,制法宜民,则自无不顺。”[注]程树德: 《论语集释》,第532—533页。
因此,一种解释认为孔子提倡愚民政策,另一种解释则认为孔子感慨民愚。然而,这两种解释看起来都是成问题的。第一种解释不可能是对的。诚如陈大齐所言: 此与孔子思想相左;《论语》中有两处都提到,孔子认为有知的人不会被欺骗;依此,除非孔子希望让人永远处于被欺的状态,否则他不可能不想让人们从无知变成有知。[注]陈大奇: 《论语臆解》,台北: 商务印书馆,1996年,第153页。一些学者认为郭店简《尊德义》作于孔子同时代,其31简有一相关论述:“民不可惑也。”此处见荆门市博物馆编: 《郭店楚墓竹简》,北京: 文物出版社,1998年,第174页。第二种解释也不可能是对的,因为这与本节曾论及的孔子观点直接对立: 每个人都是通过教育达到完美的。为了更好地理解这一点,我们有必要了解,在孔子看来无法让百姓知道的是什么,以及为何如此。
三、 作为道德教育家的孔子
孔子的教育目标是什么?孔子希望他的学生成为什么样的人?要回答这些问题,我们必须了解孔子的教学内容。我们可以从诸如“四科”、“四教”、“六经”得到解答这一问题的一些线索。
首先,《论语》中提到“四科”的文字如下:“德行: 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言语: 宰我,子贡;政事: 冉有,季路;文学: 子游,子夏。”(《先进》)此即著名的“四科十哲”。司马迁《史记·仲尼弟子列传》言,孔子弟子超过三千,其中七十余人掌握了本节稍后即将论及的“六艺”。显然,《论语》所提及的十哲在七十名学生中最为出色,尤其是在孔子所教的四科中各自取得突出成就。虽然关于《论语》这一章的作者仍存在争论[注]“德行”前并无他处习见的“子曰”二字,故有注家认为,此乃孔子门人之说。另一些注家则认为,此段文字紧接上章,也属于上章开头“子曰”的内容,故此乃孔子之说。见程树德: 《论语集释》,第742—744页。因此,第一类注家将此段文字独立成章,而第二类则将之缀于上章之后。由于古代汉语没有标点符号,故不易判断孰是孰非。,而孔子对四科的教法,与我们今天在大学里对英语、数学、物理学、社会学等科目的教法不太可能相同(尽管在汉代,官员的选拔以此四科为准),但是,此四科无疑是孔子教学最为重要的方面。
就四科而言,我们看到“德行”和“政事”显然系孔子的道德教育。人们通常认为,“文学”指的是“六经”,系孔子在道德教育中使用的教科书,这点我们将在下文详加讨论。唯一有些麻烦的是第二科“言语”,因为《论语》中多处记载孔子瞧不起善于言语的人。例如,有人告诉孔子,他的学生冉雍颇有仁德,可惜没有口才。孔子回答说,尽管他并不知道冉雍是否有仁德,但可以确定的是,“焉用佞?御人以口给,屡憎于人”(《公冶长》)。因此,他“恶夫佞者”(《先进》)。在他看来,“巧言令色鲜矣仁”(《学而》;亦可参见《公冶长》第二十五章,《子路》第二十七章,《阳货》第七章);相形之下,“仁者,其言也讱”(《颜渊》)。因此,那些在言语科取得很高成就的学生显然不同于今天在演讲课上取得好成绩的学生。
《论语》中的一些相关段落清楚地表明,孔子那些在言语科上出类拔萃的学生必有两种品质。其一,信。因此,孔子说“言而有信”可以视为已经学习过的标志(《学而》);“信近于义”(《学而》);“夫人不言,言必有中”(《先进》);“古者言之不出,耻躬之不逮也”(《里仁》)。其二,行之于言的优先性。例如,孔子说,君子“敏于事而慎于言”(《学而》),“先行其言而后从之”(《为政》),“讷于言而敏于行”(《里仁》),“言之必可行也”(《子路》),“耻其言而过其行”(《宪问》),“言忠信,行笃敬”(《卫灵公》)。上述两种品质都是道德品质,故而“言语”与其他三科同属于道德教育。[注]此四科皆为道德教育的科目,对此钱穆论曰:“四科首德行,非谓不长言语,不通政事,不博文学,而别有德行一目……自德行言之,余三科皆其分支,皆当隶于德行之下……文学亦当包前三科,因前三科必由文学入门。”此处参见钱穆: 《论语新解》,北京: 三联书店,2005年,第278页。
其次,关于“四教”,《论语》记弟子之言曰:“子以四教: 文,行,忠,信。”(《述而》)文指“六经”,将另加讨论。这里的问题是行、忠、信三者之间的关系。如元代学者陈天祥认为,“行为所行诸善之总称,忠与信特行中之两事”:“存忠信便是修行,修行则存忠信在其中矣。既言修行,又言而存忠信,义不可解。”[注]见程树德: 《论语集释》,第486—487页。因此一些学者怀疑,《论语》中的这段话一定是弟子记错了。[注]陈大奇: 《孔子学说》,第293—294页;李泽厚: 《论语今读》,香港: 天地图书出版社,1999年,第184—185页;匡亚明: 《孔子评传》,南京: 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第300页。尽管无关本篇主旨,我们还是可以注意到,长期以来已有诸多注家试图给出合理的解释。理学的集大成者朱熹提出的解释至为繁杂,它试图表明,文、行、忠、信四者实际上代表着由至易到至难、循序渐进的道德教育过程。[注]见匡亚明: 《孔子评传》,第341页。不过,笔者认为晋代学者李充的解释最为合理。根据李充的说法,为人臣则忠,与朋友则信,因此,行必须理解为一种狭义的家庭之内的孝悌恭睦。[注]见匡亚明: 《孔子评传》,第341页。不管此三教的确切含义如何,孔子教学的重点显然在于美德。
其三,如上所述,“六经”被列为“四科”之一的“文学”,而作为“四教”之一的“文”则指孔子用来教学生的教科书。它们在孔子之前的官学中就被使用了。然而,在孔子的时代,“六经”出现了残缺、混杂、重复(多个版本)的情况。我们尚不清楚孔子对于我们所熟知的“六经”即《诗》、《书》、《礼》、《乐》、《易》、《春秋》所发挥的确切作用。有些人认为它们都是在孔子之后形成的,而另一些人则声称孔子著六经。[注]匡亚明: 《孔子评传》,第341页。更有可能的情形是,孔子删订“六经”,尽管流传至今的“五经”(《乐》不幸亡佚)在汉代被编辑过,但已非孔子时代之旧貌。
按照一种流传甚广的看法,“四教”中的“行,忠,信”及“四科”中的“德行,政事,言语”显然是道德教育,但“文”或“文学”既教以六经,则旨在为学生提供知性知识。[注]匡亚明: 《孔子评传》,第303—307页;蔡尚思: 《孔子思想体系》,第197页。笔者认为这是一种误解。孔子教授六经,他的做法显然不同于今天的古典学教授: 为好奇的学生提供古代文本知识。相反,孔子以六经为道德教育之具。例如,孔子论六经之用:
入其国,其教可知也。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诗》教也;疏通知远,《书》教也;广博易良,《乐》教也;洁净精微,《易》教也;恭俭庄敬,《礼》教也;属辞比事,《春秋》教也。(《礼记·经解》)
很显然,对孔子来说,我们学习经典,不是为了满足我们对于古人想法的好奇心,而是为了让我们自己成为更好的人。
据《论语》记载,六经中孔子谈得最多的是《诗》、《礼》、《乐》。《泰伯》很好地概括了三者在道德教育中的重要性:“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如古汉语中的很多用例,这三句话没有主词。但人们通常认为其主词是美德,或有德之士,因此这段话说的是,一个人经由诗歌开始美德修养,进而通过礼仪把美德行为稳定下来,最后通过音乐成为自然不费力而有美德的人。很明显,对孔子来说,道德教育不是发出道德命令,而是激发一个人的道德情感。为此,孔子认为《诗》三百最有效。因此,他要求弟子学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阳货》),在孔子看来,“《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为政》)。孔子不赞成以其他方式读诗,这也清楚地表明孔子对诗歌的道德功能感兴趣:“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子路》)
然而,诗歌所激发的道德情感稍纵即逝。例如,在当代社会,看电影、读报纸,或者看到电视上的自然灾害都可能会引发我们的道德情感。然而,离开电影院,放下报纸,或者关掉电视,这些道德情感可能很快就烟消云散了。为了使诗歌所引发的道德情感稳固,孔子强调礼的重要性:“恭而无礼则劳,慎而无礼则葸,勇而无礼则乱,直而无礼则绞。”(《泰伯》)因此,他要求学生“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颜渊》)。礼不同于刑法。倘若违礼,一个人不会受到惩罚,而是会感到羞愧,因为他会被人瞧不起。然而,在遵礼而行的道德行为中,人们依然会感到某种不自在,常常需要努力克服自己去违礼视、听、言、动的欲望。因此,孔子认为,道德教育必须通过音乐来完成。
上文提到,《乐》已亡佚,但现存的《礼记》中有一卷论乐,从中可以了解道德是如何成于乐的。“乐”字两读,也可以读作“快乐”之“乐”。故《礼记·乐记》云:“乐者,乐也。”听一段美妙的音乐,不禁“手之舞之,足之蹈之”。故乐常与礼对,礼指向外在行为,而乐针对内在情感:
致乐以治心,则易直子谅之心油然生矣。易直子谅之心生则乐,乐则安,安则久,久则天,天则神。天则不言而信,神则不怒而威,致乐以治心者也。(《礼记·乐记》)
简而言之,乐在道德教育中的作用在于,一个人做出道德行为时,不会被外在的礼所束缚;相反,这种行为是自发的、毫不费力的、快乐的。确实,这正是孔子所描述的自己在七十岁达到的境界:“从心所欲不逾矩。”(《为政》)
除“四科”、“四教”、“六经”之外,《论语》中尚有一段名言:“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述而》)人们通常认为这里的“艺”指的是孔子之前及当时的官学所授的“六艺”,即礼、乐、射、御、书、数。然而,在笔者看来,除了通过“六经”之《礼》、《乐》所传授的礼乐之外,孔子是否还传授其他四艺不得而知,尽管他的确精通此六艺。[注]朱熹认为,前两种属于“文”,后四种属于“术”。参见程树德: 《论语集释》,第444页。这一怀疑有几个理由。首先,“六经”有时也称“六艺”,因此所谓“游于艺”也有可能说的其实是精熟“六经”。这是可能的,因为只有“六经”和道、德、仁处于同一层次。其次,即便在官学,“六艺”也被认为是教育初学者(儿童)的“小学”,而“六经”则是随后教育高年级学生的“大学”。第三,《论语》没有提及“书”、“数”,另一方面虽提及“射”、“御”,评价却不甚高。比如《子罕》所记:“达巷党人曰:‘大哉孔子!博学而无所成名。’子闻之,谓门弟子曰:‘吾何执?执御乎?执射乎?吾执御矣。’”[注]《论语》中,孔子仅在此处言及“御”。言“射”尚有几处,如:“君子无所争。必也射乎!揖让而升,下而饮。其争也君子。”(《八佾》)“子钓而不纲,弋不射宿。”(《述而》)这表明,在孔子看来,人之“大”既不是因为他在任何特定领域所拥有的特殊技能,也不是因为博学,而是因为他是仁者。根据蔡尚思的说法,军事领导人必须掌握射、御这两种技艺。[注]蔡尚思认为,六艺可分为三类,书、数是关于读写的基本知识,礼、乐是贵族政治、宗教行为所需要的基本知识,而射、御是军事行动中的主要技能(参见蔡尚思: 《孔子思想体系》,第175页)。然而,有人问孔子军事,他却说:“军旅之事,未之学也。”(《卫灵公》)[注]匡亚明走得更远。他比照当代中国的社会主义教育,认为孔子的教育也包括德育、智育和体育三个方面,而射御乃体育之事。
由此可见,孔子作为教育者的首要目标不是传授学生知识或技艺,而是教他们如何成为有德之士、成为真正的人。[注]陈大齐认为,孔子的教育哲学基于道德哲学,故而教育目标是理想人格,其焦点则是人格修养;孔子的理想人格是君子,故而孔子的教育旨在教育君子(参见陈大齐: 《孔子学说》,第273页)。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孔子反对理智或反对技术。事实上,孔子能文能武;他捷足以逮兔;他会钓鱼、打猎、养牛饲马,可以计账,可以主丧事。然而,孔子认为它们都不是成为君子的必要条件。这一点《论语》中讲得很清楚:
太宰问于子贡曰:“夫子圣者与?何其多能也?”子贡曰:“固天纵之将圣,又多能也。”子闻之,曰:“太宰知我乎!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君子多乎哉?不多也。”(《子罕》)
历代对于如何理解最后两句话(“君子多乎哉?不多也”)素有争议。[注]参见程树德: 《论语集释》,第583页。以下两种看法各居一端: 其一,孔子认为君子不应该有那么多的技能;其二,孔子认为君子从不担心技多压身。[注]陈大齐: 《论语臆解》,第172页。前者认为多能和君子不可得兼,后者认为君子得多能。不过,笔者以为,从上下文来看,更好的理解是,多能之于成圣既非不相容亦非不可少。
倘与另一段文字对读,这一点就可以看得更清楚:“樊迟请学稼。子曰:‘吾不如老农。’请学为圃。曰:‘吾不如老圃。’樊迟出,子曰:‘小人哉,樊须也!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子路》)考虑到上引《子罕》中孔子之所言,或许我们不能说孔子欠缺农业和园艺方面的技能。跟我们的讨论特别相关的是,它不仅告诉我们孔子没有教学生各种技能(即便他有这些技能),而且告诉我们他教学生的乃是礼、义、信。
《论语》中有一章极简,仅四字,却很难解:“君子不器。”(《颜渊》)最具影响力的解释莫过于汉儒包咸(6—68)之说:“器者各周其用,至于君子,无所不施。”[注]程树德: 《论语集释》,第96页。包括当代学者在内的诸多注家均接受此说。例如,钱穆说道:“器,各适其用而不能相通,今之所谓专家之学者近之。不器非谓无用,乃谓不专限于一材一艺之长,犹今之谓通才。”[注]钱穆: 《论语新解》,第38页。笔者原先在美国就职的大学除了现有的传统专业学科之外,新设一本科生专业,名曰“通识教育”。如按包氏之说,“通识教育”专业的学生都是君子,或者至少是后备君子,而那些学习传统专业分科的学生只能至于“器”。此显非孔子之意。在笔者看来,朱熹的说法已触及孔子之真意:“器者,各适其用而不能通。成德之士,体无不具,故用无不周。”[注]程树德: 《论语集释》,第96页。这里重要的是,朱熹不是在一能和多能之间作出区分,而是在技能和美德之间作出区分。有德之士当然可以有一能或多能,但修德并非学习技能。有德之士不是“器”,因为无论他是老师还是学生,是君还是臣,是父母还是孩子,是艺术家还是技师,是天文学家还是医生,有德之士所拥有的美德都可以展示出来。[注]因此,显然,尽管成为君子不是学会特定技能,但君子常常希望多能。如《卫灵公》篇所说:“君子病无能焉,不病人之不己知也。”(《宪问》篇亦曰:“不患人之不己知,患其不能也。”)陈大齐引此章,说明多能乃是成为君子的必要品质(参见陈大齐: 《孔子学说》,第172页)。然而,重要的是要注意到,孔子在上述一章中所讨论的是,君子究竟应该忧心自己无能,还是应该忧心别人不知道自己有能。此章没有涉及到,让人成为君子的,究竟是有能还是有德。君子固然可以多能、希望多能,常常实际上也做到了多能,但他之为君子并不是因为多能而是因为美德。例如,君子爱父母,此为德性之知;但要想找到爱父母的最佳方式,他必须学会一些技能(如冬温夏凊)。然而,如果一个人倘因天生智力缺陷而没有这些技能,相较于具有这些技能的人来说,他的孝心无损一分。
四、 美德能教吗,如何教?
我们已经看到孔子的教育是道德教育。换言之,其教育目标主要不是为了让学生知识渊博或技艺纯熟,而是使他们成为有德之士。我们再来看一下另一令人困惑的陈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泰伯》)这里的所“知”者显然既非理论知识,亦非技艺,而是作为美德的知识(knowledge as virtue)或作为知识的美德,后者有别于关于美德的知识(knowledge about virtue)。如果我们告诉某人,一个人应该有美德(如爱父母),他自然明白这是什么意思。这是关于美德的知识,一种知性理解。然而,孔子说“知德者鲜矣”(《卫灵公》),他所抱怨的,显然不是关于美德的知识,而是作为知识的美德或作为美德的知识。在孔子看来,作为美德的知识有两个特点。第一个特点和它的来源有关。关于美德的知识或一般的理智知识只依赖智力(mind),而作为美德的知识还依赖心(heart);它需要一个人“默而识之”(《述而》),即在知的过程中获得属己的内在体验。第二个特点与其功效有关。它不仅仅是对美德的一种冷静的理解。它还促使一个人行美德,成为有德之士。孔子说“民不可使知之”,他的意思实际上是说,不能强迫人们成为善人。你可以强迫一个人去做事情(包括德行),但你不能强迫一个人成为有德之士。
这是否意味着,孔子对苏格拉底问题“美德是否可教?”的回答只能是否定的?初看起来似乎如此,因为孔子强调道德自我修养的重要性。例如,他说:“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颜渊》)他对比了他所钦佩的古人和他所鄙视的今人:“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宪问》)他还要求“躬自厚而薄责于人”(《卫灵公》),“攻其恶,无攻人之恶”(《颜渊》)。所以,他对比君子和小人:“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卫灵公》)[注]正是在此意义上,陈来认为:“虽然不能断言‘美德可教’,我们可以肯定美德可学……因此,对于苏格拉底和柏拉图美德是否可教的问题,传统儒家倾向于把问题转化为‘美德是否可学’的问题,后者才表达了儒家的问题意识。”(见Chen Lai, “The Ideal of ‘Educating’ and ‘Learning’ in Confucian Thought,” in Roger T. Ames and Peter Hersh (eds.),Educations and Their Purposes,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2008, p.319。)对孔子来说,美德当然可学,但我们这里的问题更为困难: 对孔子来说,美德是否也是可教的?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孔子认为,有德之士只能对他人行善,却无能教他人行善。倘若如此,他的伦理学也就具有了所谓的自我中心问题。一些当代哲学家认为,这是任何美德伦理学都无法回避的问题。然而,孔子的伦理学虽然也是一种美德伦理学,但它显然没有这种意义上的自我中心问题。儒家教育的目的,就是要使人有德。在孔子看来,最重要的美德是仁,它包括或者至少引导所有其他美德。仁者爱子忠亲,爱弟忠兄,爱下忠上。然而,对于孔子来说,爱某人或忠某人并不仅仅是关心他们的外在幸福:“爱之,能勿劳乎?忠焉,能勿诲乎?”(《宪问》)劳者,劝勉行善也;诲者,进谏规诲也。
因此,孔子之意,并非不能使人成为有德之士,而是不能像使人做事那样使人成为有德之士;并非美德不可教,而是不能像教理论知识或技能那样教美德。陈来所言甚是:“关于美德教育,教师的基本责任是启发学生……并激发他们养成卓绝的品质。教师应该唤醒学生敬重君子并心向往之,希望自己也能成为如此完美之人。”[注]Chen Lai, “The Ideal of ‘Educating’ and ‘Learning’ in Confucian Thought,” p.322.显然,这不能简单地通过发布道德命令甚或刑法来实现,它们至多驱使人们行仁义或避免做恶,但无论如何不能使人由仁义行而成为有德之士。
接下来的问题是美德如何教。我们已经触及孔子教人有德的两种方式。首先,由于无德之人的问题在于,他们没有成为善人的动力,而他们之所以无此动力,部分原因在于他们觉得成为善人是件苦事,因此,诚如库珀曼(Joel Kupperman)所言:“良好的教育也需要激发学生的动力,这样才能积极吸引学生,否则教育过程就会令人感到乏味沮丧。许诺一种至乐可以赋予学生十足的动力。如孔子所指出,这种满足比较可靠,而认识到这一点可以增加人们获得德性的动机。”[注]Joe L. Kupperman, “Fact and Value in the Analects: Education and Logic,” In Roger T. Ames and Peter Hersh (eds.), Educations and Their Purposes,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2008, p.408.因此,孔子反复强调成为有德之士的快乐,并把它跟道德教育中音乐的作用联系起来讨论。[注]亦参见Huang Yong, “Confucius and Mencius on the Motivation to be Moral,” Philosophy East and West vol.60 no.1(2010): 65-87。其次,既然无德之人并不缺乏对美德的知性理解,而是缺乏成为有德之士的情感或愿望,那么激发他们产生相应的情感或愿望就至关重要。我们已经看到,对于孔子来说,诗在道德教育中之所以重要,正是因为它有此之用。此用类似于罗蒂眼中记者或小说家讲述生动、悲伤、感人的故事所起的作用。罗蒂讲道:“波斯尼亚妇女的命运要看电视记者能否像斯托(Harriet Beecher Stowe)报道黑奴那样加以报道——要看这些记者能否让我们这些远远呆在安全国家的观众改变以往的感观,感受到这些妇女也跟我们一样是人。”[注]Richard Rorty, Truth and Progress: Philosophical Paper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8, p.180.除此之外,还有另一种道德教育的办法,即劝谏,笔者将在别处详加讨论。下文将指出,道德教育主要由亲教子,或由君教民,不过孔子也意识到,有时亲与君也会有道德上的缺陷。在这些情况下,子与臣以劝谏的方式成为他们的道德老师,劝谏他们不做错事,或者纠正已经做过的错事。
不过,本节接下来及下一节将详细讨论对孔子来说最为重要的一种教人成德的方式,那就是让自己成为堪称典型的君子。这种方式有助于我们理解他说的一些话,那些话初听起来像是主张有德之士应当只关心自己是否有德。孔子说道:“君子笃于亲,则民兴于仁;故旧不遗,则民不偷。”(《泰伯》)“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则四方之民襁负其子而至矣。”(《子路》)[注]库珀曼也认为,对孔子来说,通过典范而教非常重要。他说道:“正因为此,孔子强调无友不如己(《学而》)。就一个核心家庭而言,这意味着父母的举止至为重要,它在孩子早年生活中起到了关键的榜样作用。父母为孩子的人生定调。只要承认榜样在人们道德发展过程中的重要性,那么家庭内部的早期个人关系的品质就会极为要紧。”(Joe L. Kupperman, “Confucian Civility,” Dao: A Journal of Comparative Philosophy, vol.9 no.1(2010): 19.)
孔子相信以个体典范设教的有效性。他说:“德不孤,必有邻。”(《里仁》)在他看来,有德之士的品性和行为可以感染人,所以他必然会有信从者。事实上,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理解《论语》开头的三句话:“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说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学而》)通常的理解不仅忽略了孔子的要义,而且也模糊了这三句话之间的重要联系。孔子之所教与门人之所学乃是成人,而“习”乃是“实践”。所以,首句真正的意思为,把自己所学的关于如何成为有德之士的知识付诸实践真乐事也。[注]参见钱穆: 《孔子和论语》,台北: 兰台出版社,2001年,第143—144页。这与孔子对相较于言语的行动的强调相契。我们已经看到,孔子批评那些诵《诗》三百却不会用诗的人(《子路》)。同时,这也反映了孔子德行带来快乐的观点。孔子说:“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雍也》)虽然“之”的所指并不明确,但它显然指善事。这可以在如下一章中得到证实:“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述而》)次句中的“朋”可以解作信从者。“朋”“友”在现代汉语中是同义词,但它们在《论语》中却有不同的用法。“友”是相友善之人,而“朋”则是同志或信从者。因此,笔者同意朱熹的解释,他认为次句与首句紧密相联。首句说的是,把自己所学的关于如何成为有德之士的知识付诸实践是件乐事;次句说的是,以善及人而信从者众,故可乐。朱子进而说道,这里的乐并不是因为信从者众足以验己之有德:“己既有得,何待人之信从,始可为乐?须知己之有得,亦欲他人之皆得……至于信之从之者众,则岂不可乐!”[注]朱熹: 《朱子语类》,北京: 中华书局,1986年,第451页。这一解释与孔子的说法相契: 有一位好的国君,则“近者说,远者来”(《子路》)。
在此我们可以看到孔子与亚里士多德(至少按照人们对他的一种解读)之间有一显著差异。亚氏的《尼各马可伦理学》中有一段语义模糊的文字: 真正的自爱者,除了其他方面,还会“让朋友们去完成某项事业。因为,让朋友去做有时可能比自己去做更高尚。所以在所有值得称赞的事物中,好人都把高尚的东西给予了自己”。[注]Aristotle, Nicomachean Ethics, (trans.) W.D. Ross, In The Works of Aristotle, vol.9,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3,1169a33-36.(中译参照亚里士多德: 《尼各马可伦理学》,廖申白译,北京: 商务印书馆,2003年,第277页。——译者)有人说,亚里士多德在此回应了那种以美德伦理为自我中心的反对意见。在他看来,有德之士,真正的自爱者关心他人的美德,所以把行美德的机会让给别人。托纳(Christopher Toner)设想以下情境来解释亚里士多德: 我们俩是朋友,一起去执行危险的侦察任务。必须有一个人自愿首先穿过一片开阔地带。我想上前去,但马上想到这样会让你背上懦夫的恶名,而这对你来说是不公平的。为了避免给你带来恶名,于是我保持沉默,让你成为第一个冲上前去的人。[注]参见Christopher Toner, “The Self-Centeredness Objection to Virtue Ethics,” Philosophy, vol.81(2006): 595-617,611。克劳特(Richard Kraut)的解释与此相仿: 我认为我的朋友有能力监督大型的市政项目,但他没有太多机会展示自己的价值;于是,我说服监督这些项目的政府官员为他争取机会。[注]参见Richard Kraut, Aristotle on the Human Good,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9, p.126。
笔者曾在别处论及,且不管这是否就是亚里士多德的意思,有德之士不可能通过把行善的机会让给无德之人这样的方式而使他变得有德。[注]参见Huang Yong, “Confucius and Mencius on the Motivation to Be Moral”。这里想强调的是,从我们上面的讨论来看,这显然不是孔子建议有德之士让其他人变得有德的方式。孔子认为,虽然一个人在面对外部利益的时候应当把机会让给别人,但是,“当仁,不让于师”(《卫灵公》)。依照清儒黄式三的解读,这是说,倘有践习美德的机会,则不应当逊让于众人。[注]参见程树德: 《论语集释》,第1124页。钱穆先生亦采此说,言曰:“师之与我,虽并世而有先后,当我学成德立之时,而师或不在”,故“师”字当训“众”。(参见钱穆: 《论语新解》,第422页。)孔子心中所想,并不是克劳特在讨论亚氏关于美德友谊的概念时所讲的“道德竞争”(在道德竞争中,所有竞争者都可能是赢家)。相反,正如朱熹注解“当仁,不让于师”云:“盖仁者人所自有而自为之,非有争也,何逊之有?”[注]程树德: 《论语集释》,第1124页。此外,亚里士多德的兴趣在于有德的朋友之间的关系,而孔子的主要关注点则在于有德之士与无德之人之间的关系。如果有德之士在这种情况下退让,那就没有人行善了,因为无德之人既为无德之人自然不会去行善的。相反,如果有德之士带头行善,那么无德之人就有可能在道德上被感动,从而变成有德之士。[注]王庆节对道德感动有精彩的论述(参见Wang Qingjie, “Virtue Ethics and Being Morally Moved, ” Dao: A Journal of Comparative Philosophy vol.9 no.3 (2010): 309-321)。
当然,有德之士之所以可以成为榜样,从而可以吸引信从者,即能让他人变得有德,是因为他及其德行为他人所知。如果他不为人所知,因而没有信从者,那又会怎样呢?这正是第三句话想要说的意思: 一个卓越的人不会怨恨别人。这句话通常被理解为,对孔子来说,学习以自我修养为旨趣。因此,一个人只要有德,别人是否知道实在是无所谓的事。[注]参见陈大奇: 《孔子学说》,第5页。朱熹甚至以吃饭为喻。一个人吃饭是因为他想要吃饱,完全没有必要去问别人是否知道自己已经吃饱了。[注]参见朱熹: 《朱子语类》,第453页。这是有道理的。然而,对孔子来说,一个人不仅要自己有德,而且还要帮助别人有德。事实上,除非一个人也想让别人有德,否则我们就不能认为他是有德的。因此,如果别人没有认识到我们的美德,那我们不能抱怨别人;相反,我们倒应该抱怨自己尚无完德足以感化无德之人。换而言之,有德之士应该提升自己,而不是责怪别人不知道、不信从自己。《论语》对此再三致意焉。孔子说:“躬自厚而薄责于人,则远怨矣。”(《卫灵公》;亦可参见《宪问》)又说:“不患无位,患所以立;不患莫己知,求为可知也。”(《里仁》)所有这些都与笔者在别处所强调的一个要点一致: 在有德之士眼里,只要存在一个无德之人,就表明他还没有充分履行自己的职责。
五、 政府在道德教育中的作用
孔子对政府职能的论述,最有名的莫过于下面这段话:“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里仁》)必须指出的是,对孔子来说,问题不在于以刑(惩罚)、政(强制措施)治国没有效果。它们在阻止人们做不道德的事情方面颇有成效。孔子的关注点在于,如果以刑、政治国,普通民众尽管遵纪守法,却会变得无耻。以德、礼治国同样可以防止人们做坏事,但孔子提倡德、礼,因为用这种办法治国可以让人们有羞耻感。换言之,在孔子看来,政府的首要职能是对民众的道德教育。正是在这里,我们看到孔子和当代政治自由主义者对政府职能的理解形成了鲜明对比。
自由主义在当代政治哲学中的独特之处,至少部分归因于它严格区分政治之域和个人之域。这一区分有两个面向。其一,“个人之域不是政治的”: 政府的职能仅限于人们在公共领域的生活,而他们在私人领域的生活,尤其是在家庭内部的生活,是受到“保护”的,政府不能加以干预。许多女权主义思想家已经充分指出这一主张的问题之所在。女权主义者正确地主张,个人是政治的。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政府可以无孔不入地介入个人生活。然而,自由主义关于政治之域和个人之域的划分尚有第二层涵义,女权主义的口号“个人是政治的”并没有抓住它,它所带来的问题不但没有被女权主义所界定,而且还(将)进一步渗透到女权主义所提出的旨在减少个人之域的不公正的程序之中。在自由主义的传统中,不仅个人不是政治的,而且政治也不是个人的: 政府的职能仅限于建立由法律和公共政策所规范的社会制度,而无关乎究竟什么样的人生活在这些制度之中。换句话说,政府的工作是改善社会制度,使它们公平对待生活在制度中的每一个人,但不是培养个人的德性,当然,也不是要让他们变成恶人。自由主义的这一看法是成问题的。
初看起来,既然自由主义传统坚持认为政治不是个人的,如果它没有援手培养个人的美德,我们可能会认为至少它不会引发恶习。它使人如其所是。它只是制定对每个游戏者来说都公平的游戏规则。实则不然。科恩(G.A. Cohen)批评自由主义尤其是罗尔斯的正义论,他指出,“社会结构广泛塑造了动机结构”,因为人性在动机方面的“可塑性”相当强。[注]G. A. Cohen, If You’re an Egalitarian, How Come You’re So Rich?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p.119.在他看来,自由社会不仅没有改善人性,实际上还鼓励人们成为自私的人。他对罗尔斯的差异原则(第二个正义原则的一部分)尤为介怀,因为它试图证明社会与经济不平等是正当的: 最有才的人,如果不多给他们一点东西,就不会充分发挥他们的才能,这样一来其他人也就处于更糟的境地。罗尔斯认为,让最有才的人适当多得一点,以激发他们充分发挥自己的才能,从而让社会上其他每一个人从中受益。在科恩看来,这一原则鼓励了最有才的人的自私心: 如果不允许我们(最有才的人)获得比其他人更大的份额,我们就不作出最大的贡献;不仅如此,它也鼓励了最弱势者的自私心: 如果我们不能从最有才的人的施展才华中获得更多的好处,我们就不允许他们拿到更大的份额。[注]参见G. A. Cohen, If You’re an Egalitarian, How Come You’re So Rich?第八章。
这已经表明,自由主义者认为政治不是个人的,这完全是错的。政治是个人的: 一种特定的政府不仅决定了将有何种社会,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将是何种人生活于社会之中。只有在这样的脉络之中,我们才能认识到孔子政治哲学的意义,因为它明确指出,政府的职能是对民众的道德教育。不惟如此,在孔子看来,政府实现这一职能主要通过君主的典范行为而不是通过君主所制定的规则。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孔子的观点也明显不同于亚里士多德的观点,有时人们认为我们可以拿后者替代今天的自由主义政治理论,因为亚氏认为,政府确实承担对公民进行道德教育的功能。然而,亚里士多德的理论有两个独特之处。其一,主张道德教育是专属于立法者的工作,个体公民(如父母和朋友)不得预于其间,即便立法者通常并不可能像父母了解子女或朋友了解朋友那么熟知公民,也并不必然贤于父母或朋友。这一点关联到亚氏理论的第二个特征: 立法者实施道德教育,不是通过他们足以让民众模仿的典范行为,而是通过他们所制定的法律。在亚氏看来:“如果一个人不是在健全的法律下成长的,就很难使他接受正确的德性。因为多数人,尤其是青年人,都觉得过节制的、忍耐的生活不快乐。所以,对青年人的哺育与教育要在法律指导下进行。”[注]Aristotle, Nicomachean Ethics 1179b30-1180a2.(中译参照亚里士多德: 《尼各马可伦理学》,廖申白译,第313页。——译者)他进而指出:“大多数人都只知恐惧而不顾及荣誉,他们不去做坏事不是出于羞耻,而是因为惧怕惩罚。”[注]Aristotle, Nicomachean Ethics 1179b11-13.(中译参照亚里士多德: 《尼各马可伦理学》,廖申白译,第312页。——译者)因此,亚里士多德和当代自由主义者都认为,政府的首要职能是制定刑法。差别在于,自由主义者认为,法律相对于人们的品性来说是中立的,它们不会让人变得高尚或邪恶,而亚里士多德则主张,刑法能够并且应该使人有德。
亚氏理论的以上两点,孔子均不会同意。孔子的确区分了有德的个体和政治领袖在道德教育中的作用。政治统治者可以在道德教育中发挥作用,恰恰因为普通的有德之士可以发挥这样的作用。因此,就像普通的有德之士只能通过自己典范性的道德行为来让别人成为有德的人,政治统治者也只能通过他们自己的典范性的道德行为来让民众成为有道德的人。孔子之所以强调政治统治者在道德教育中的重要性,主要并不是因为他们可以通过任何政治或法律措施(这是普通的有德之士所做不到的)实现道德教育,而只是因为他们的行为将被他们治下的所有民众所效仿,而普通有德之士的典范性善行只能影响到身边的小圈子。
正因为此,他在劝谏政治统治者的时候不断强调有德的重要性。例如,他说:“苟正其身矣,于从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子路》)“政”与“正”是同源字。因此,季康子问政,孔子回答说:“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颜渊》)季康子患盗,孔子告诫他:“苟子之不欲,虽赏之不窃。”(《颜渊》)季康子进一步问:“如杀无道,以就有道,何如?”孔子回答道:“子为政,焉用杀?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颜渊》)在孔子看来,如果统治者“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子路》);“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为政》)。[注]《孔子家语·王言解》述之更详:“上敬老,则下益孝;上尊齿,则下益悌;上乐施,则下益宽;上亲贤,则下择友;上好德,则下不隐;上恶贪,则下耻争;上廉让,则下耻节。此之谓七教。七教者,治民之本也。……凡上者,民之表也。表正,则何物不正?”
当然,尽管孔子是位理想主义者,但并不是乌托邦主义者。他知道,完全放弃刑法还为时过早。他高度赞扬“善人为邦百年,亦可以胜残去杀矣”的说法(《子路》)。这表明,在很长一段时期内,即使一个国家由善人来统治,仍然需要有刑法。不过,孔子的理想是,这样的法律设而不用(《孔子家语·相鲁》)。因此,他说:“圣人之设防,贵其不犯也,制五刑而不用……是以上有制度,则民知所止,民知所止,则不犯。故虽有奸邪贼盗,靡法妄行之狱,而无陷刑之民。”(《孔子家语·五刑解》,《孔子家语·相鲁》)在孔子看来,刑法显然主要用以阻止坏人去做坏事,而非作为一种对付人的计谋。重要的一点在于,坏人被这些刑法阻止做坏事的同时,他们也应该被教导要有美德。孔子也许在反思自己作为大司寇的经历时说道:“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颜渊》)
当诉讼案件确实出现时,孔子也认为,尽可能寻求法律决定之外的解决方案很重要。孔子在鲁国担任大司寇时,曾发生过一起父讼子不孝的案件。孔子把他们关在同一间牢房里,关了三个月都没有做出判决。父亲最终请求撤诉,孔子便将他们俩都放走了。有人问,孔子本人一直强调孝对于治国的重要性,但为什么把儿子放了而不是惩罚他。孔子回答说:“上失其道而杀其下,非理也。不教以孝,而听其狱,是杀不辜。三军大败,不可斩也。狱犴不治,不可刑也。何者?上教之不行,罪不在民故也。”(《孔子家语·始诛》,《孔子家语·五仪解》,亦参见《荀子·宥坐》)
孔子进而认为,在理想的古代社会,“威厉而不试,刑错而不用”,而在他所生活的社会则相反,“乱其教,繁其刑,使民迷惑而陷焉,又从而制之,故刑弥繁,而盗不胜也”(《孔子家语·始诛》,《孔子家语·六本》)。当然,孔子并不想完全放弃刑罚,而是主张惩罚必须在道德教育之后。在他看来,“既陈道德以先服之,而犹不可,尚贤以劝之,又不可,即废之,又不可,而后以威惮之,若是三年,而百姓正矣,其有邪民不从化者,然后待之以刑,则民咸知罪矣”(《孔子家语·始诛》)。
然而,即使作为最后手段的刑罚是必要的,政治领导人仍必须牢记两件重要之事。首先,惩罚主要不应该是报复性的,即将罪犯对他人造成的伤害返还给罪犯,而是应该作为一种改造罪犯的措施。由此,孔子更加认同古代社会而不是自己身处其中的社会:“古之知法者,能省刑,本也;今之知法者,不失有罪,末矣”;而“今之听民者,求所以杀之;古之听民者,求所以生之”(《孔子集语·论政》)。其次,更重要的是,法官当然应该尽其所能做出正确的司法裁决。不过,即使他们判定一个人确实犯了所指控的罪行,孔子也劝他们“哀矜勿喜”(《子张》)。[注]“哀矜勿喜”已经用作成语,描述我们发现别人做错事之时当持的恰当态度。孔子在别处也有类似的说法:“听讼虽得其指,必哀矜之。死者不可复生,断者不可复续也。《书》曰:‘哀矜折狱。’”(《孔子集语·论政》)一个人之所以应该有这样一种哀矜之情,原因在于他应该认识到,如果他教育这个人很成功,就没有必要动用惩罚了,但他现在不得不求助于刑罚作为最后的手段。这是赫斯特豪斯(Rosalind Hursthouse)所讲的“道德残余”(moral remainder or residue): 一位有道德的人做了一件不得不做且是最好的事,但在理想状态下他不必做这样的事,这时他就会感到某种内疚、自责或后悔。[注]参见Rosalind Hursthouse, On Virtue Ethic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pp.75-76。这与老子关于战争的说法相似。总体而言,老子是反战的。如果一位明君发现战争不可避免并打了胜仗,他不会认为这值得称赞,而是以丧礼处之,不仅为那些为他而战死的人,也为死去的敌人(《老子》第三十一章)。
这种悲伤、内疚、悔恨或自责之情本身也是值得称赞的,因为一个人的美德不仅表现在行为上,也体现在情感上。同时,这种“道德残余”也可能具有道德转化的力量。在《孔子家语》中,有个故事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卫国宫廷政变引发混乱。担任卫国刑官的季羔正逃离都城寻找安全之所,这时他意识到守门人曾受过他的惩罚。守门人让季羔从残破的矮墙逃走;季羔拒绝了,说君子不会翻墙。守门人又说走墙下的地道;季羔再次拒绝,说君子不钻地道。最后,他又被告知有一密室。季羔获得藏身之处,从而在混乱中得以保全。当政变结束,季羔出来时,他问守门人:“亲刖子之足矣,今吾在难,此正子之报怨之时,而逃我者三,何故哉?”答曰:“断足,固我之罪;……临当论刑,君愀然不乐,见于颜色,臣又知之。”孔子闻之,曰:“善哉!为吏,其用法一也,思仁恕则树德,加严暴则树怨。”(《孔子家语·致思》,《孔子家语·本姓解》)
六、 结语
孔子经常被认为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私人教师。然而,如上文所分析,他并不是通常意义上的教师,因为他的教学内容既不是理论知识也不是技能,而是成德之方。尽管孔子充分认识到,一个人最终只能靠自己变成有德之士,但他确实认为,美德之人可以做很多事情去帮助别人成为有德之人,而其中最重要的是成为美德典范。任何一个有德之士当然都可以做到这一点,不过,孔子更加注重政治领袖,因为他们的影响更广更深。因此之故,在孔子的政治哲学中,政府的首要职能是对民众的道德教育,这与当代政治自由主义形成鲜明对照。此外,政府履行道德教育的职能主要不是通过法律和其他政治手段,而是通过统治者自身的道德典范作用,这又与亚里士多德的观点形成鲜明对照。在孔子看来,法律和惩罚还不能完全废除,但应该仅仅作为临时性的补救措施。即使这样的措施势在难免,一位有德的政治领袖也会自然而然感到悲伤,一方面因为恶人令人遗憾的状态,另一方面因为他自己未能通过其他措施改变恶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