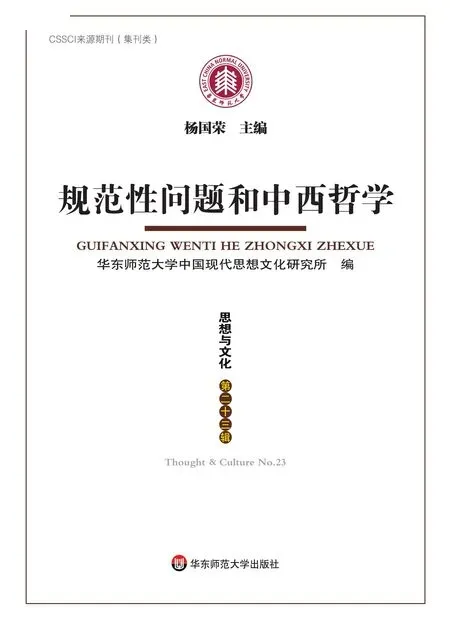阐释的悖论、隐含的规范性和人性: 从比较哲学的视角重审意志薄弱问题*
●
1. 关于意志薄弱(weakness of will)的实践问题和理论问题
在西方世界中,自苏格拉底以来,意志薄弱问题一直就为人们所津津乐道。苏格拉底对其可能性(《普罗泰戈拉》)的否定取决于这样一种观点: 自愿地追求次一级的善并不是“出于人性”。而为完成这一否定,被称之为“柏拉图原则”(Plato Principle)的这样一条基本原则[注]Donald Davidson, “Paradoxes of Irrationality,” In Philosophical Essays on Freud, Richard Wollheim and James Hopkins (ed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2, p.294.也表明,“无人愿意与其所知是最好者背道而驰”。在面对我们日常生活中诸多明显不能自制的行为(incontinent acts)时,这一原则仍能真正成立吗?人们可能会认为,该原则太强了或者太脱离实际了,以致难以在实践领域相信或坚守该原则,这里典型地涉及各种各样的驱动性因素,很可能涉及不受控制的本性(unruly nature)产生的因果力。
举例来说,约翰·塞尔(John Searle)想要拒斥(实践)理性的经典模式,戴维森的行动因果论(causal theory of action)是这一经典模式的当代代表,塞尔则通过断言一个行动的心理前件和行动的实现之间存在一个本质上的因果间隙(causal gap)来进行拒斥。弗雷泽和王启义(Fraser and Wong)在理解“性格懦弱”(character weakness)这个问题的本质及其独特的解决方案的语境下,运用了塞尔的这一批判和他关于“背景”(Background)的观点。[注]Chris Fraser and Wong Kai-yee, “Weakness of Will, the Background, and Chinese Thought,” In Searle’s Philosophy and Chinese Philosophy, Mou Bo (ed.), Leiden: Brill, 2008.然而,在向弗雷泽和王启义作出大量正面回应的同时,塞尔也表达了一些异议,即不认同他们在处理意志薄弱问题时对中西之分做出的刻画: 他们认为这种差异是解释非理性行动(irrational action)的理论问题与克服它的实践问题之间的差异。“我之所以认为这是有误导性的,是因为克服意志薄弱的问题在西方文化的传统道德教育中也十分重要,这与其他文化是非常接近的。”[注]John R. Searle, “Reply to Chris Fraser and Kai-yee Wong,” In Searle’s Philosophy and Chinese Philosophy, Mou Bo (ed.), Leiden: Brill, 2008, p.335.
对这一主张本身是否为真在此不做讨论,我想指出的是,尽管从一个更大的比较视角来看,西方世界(尤其是当代的分析传统)普遍的哲学取向更多地偏于(现代科学范式背景中的)理论解释,但这不仅会激发技术层面的发展,而且也会在科学自然主义框架内典型地或不可避免地导致对传统观点或议题的挑战。例如,用塞尔自己关于“间隙”的观点来看一个普通人的问题:“为什么在我的深思熟虑与我后续的决定或意图之间存在这样一个难以避免的间隙?”除非人们对分析哲学的当代面貌比较熟悉,否则人们此时此刻会感到一头雾水。可以说分析哲学涉及到的一项主要研究纲领是,将我们熟悉的规范性观点(比如理由、规则,或者内容)关联到(又甚至是还原到)物理主义或自然主义的观点。就此而言,上述塞尔对所谓的经典理性模式的拒斥,只是在一个共享的解释框架的整体中,围绕一个特定论点而展开的某种内部争论(这里指戴维森的因果充分性论点,即一个人根据自身的最佳判断做出随后的行动[注]Cf. Donald Davidson, “How is Weakness of the Will Possible?” In Essays on Actions and Events,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80.)。
因此,不必诧异,人们可以很容易地辨识出意志薄弱问题的传统路径(东方的或西方的)和科学驱动下的自然主义路径(比如,那些依赖于理由与行动的因果性理论观点的路径)之间的显著差异。辨明这些差异并不是本文之意。[注]我并非在暗示,以某种有说服力的方式辨识这些凸显的(或许是深层次的)差异对于比较哲学而言是不重要的。与之相反,除非这些差异被恰当理解了,否则就谈不上富有成效的深入比较。我不打算评价每一条进路的功与过。我想在此做一番追索的是,在意志薄弱问题的理论进路和实践进路之下潜存着一个隐含的规范性维度——“隐含”(implicit)在这里的意思并不是指,道德教育或实践指导层面上的任何一种命令或指示的形式是否明晰。我将表明,儒家作为中国智识传统的一个主要代表,不仅对这样一种特殊的规范性之维不缺乏敏感性,而且长期以来一直在独特地运用它,尽管在事实上对描述性与规范性的清晰、明确的区分在现代西方哲学中也只是较为晚近的事。随后,我将仔细讨论戴维森提出的一个非理性悖论(paradox of irrationality)。
2. 意志薄弱的某些代表性观点所揭示的隐含的规范性形式
每个人都会觉得,一个人自愿的行动若违反他自身的最佳判断是十分奇怪的事,不过还是有可能出现无自制力的行动(akratic actions)。绝大多数人会视这种活动为非理性的,至少在一个较窄的、主观的意义上会这样看(即不论一个人的最佳判断是否在客观上是最佳的)。视某事物为非理性的,本身就包含着一种明晰的、可评估的规范性形式,可能同时也有某种更进一步的规范性意图去更正它。所以,关于理性/非理性的判断已经超出了纯粹的描述领域,或者至少部分地进入到了规范性之域。然而,关于所谓的无自制力行动案例的引人关注之处在于,作出判断的资料,或者有待解释之物绝非理论上中立的。即是说,对于任何所谓的无自制力现象的特定案例,似乎总是存在着一定的空间去根据某些背景性的理论或理性原则来进行重新描述或阐释。
按照黄勇教授所做的分类[注]Huang Yong, “How is Weakness of the Will not Possible?— CHENG Yi’s Neo-Confucian Conception of Moral Knowledge,” In Education and Their Purposes, Roger T. Ames and Peter D. Hershock (eds.),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2008, pp.439-440.,起码存在着下述六种类型的行为,它们不同于严格的无自制力现象,但与它在某一或某些方面又很相似或易生混淆: (1)鲁莽(recklessness)或者无节制(intemperance);(2)冲动(compulsion);(3)虚伪(hypocrisy),指一个人做了他口头上说他不应该做的事;(4)无知(ignorance),例如,一位烟民不知道或者不是真正地相信吸烟是有害的;(5)疏忽(negligence)或者遗忘(forgetfulness),尽管在事实上,这个人应当知道,或者通常情况下知道,他正在做什么或者他是否应该去做那件事;(6)实质上的理性选择(rational choice),例如,一个人十分了解吸烟带来的长期的不良影响或危险,也知道吸烟带来的当下快适或刺激,他头脑清楚地选择了后者。这份清单尚未穷尽所有可能类型。[注]例如,我讨论了一种特殊类型的准理性(或者准非理性)行为,该行为与意志薄弱行为共享同一种潜在的因果性机制模式。
枚举它们(可能还包括其他行为)是为了表明,只要我们在区分所谓值得怀疑的无自制力现象的案例与这些部分地相似的不同现象/案例时感到困难,那我们就没那么容易辨识,进而也没那么容易证明存在着一个严格意义上的无自制力行动的标准案例。因此,不足为怪,“一些古代哲学家主张,不仅不存在这种意义上的意志薄弱之人,而且意志薄弱本身也是完全不可能的。任何被认为是意志薄弱的案例只不过是上述六种现象之一的某种伪装罢了。因而,任何主张意志薄弱是可能的(甚至是现实的)人就有义务去证明它是如何可能的”[注]Huang Yong, “How is Weakness of the Will not Possible? — CHENG Yi’s Neo-Confucian Conception of Moral Knowledge,” p.440.。
不论这种证明的义务是否应该由在现象层面上断定而非否认意志薄弱的人(完全地)承担,有件事似乎是比较确定的: 援引我们的常识直接断定或否认其可能性(好像每一个人在这样一种精微的或技术的概念区分中都应该共享一个信念)并不能令人满意。就此而言,塞尔几乎无权断言戴维森及那些追随戴维森的人明显有违常识,更不消说那些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服膺亚里士多德或苏格拉底的人。此外,为了公正地对待戴维森在意志薄弱方面所做的工作,人们应该承认,这些工作彰显了,在一个有关行动和理性的更为统一的理论中,去协调材料的描述和解释的融贯所可能涉及的丰富细节和义理。
就我正在某种深入、隐含的层次上揭示规范性类型这一当下目的而言,关注和强调下面这个极其重要的事实似乎是有决定性意义的: 支持或排除意志薄弱(在熟悉的行为和不熟悉的行为之间存在一个几乎连续的光谱作为背景,这些行为所拥有的特征交织重叠或相似并立)本身就是一种规范的操作或要求(可能有,也可能没有明晰的理论动机或实践动机)。我将通过对戴维森非理性悖论的深入讨论,以及它与孟子思维方式所隐含的维度之间可能的联结来论证这一点。在此之前,我想对江欣燕和黄勇的相关工作稍作评论,我试图表明,他们各以其独特的方式揭示出(尽管不那么明显)同样的规范性层面。[注]Jiang Xinyan, “What Kind of Knowledge does a Weak-willed Person Have?— A Comparative Study of Aristotle and the Cheng-Chu School,”Philosophy East and West, Vol.50 No.2 (2000): 242-253; Huang Yong, “How is Weakness of the Will not Possible?— CHENG Yi’s Neo-Confucian Conception of Moral Knowledge.”
首先,江欣燕的文章十分明确地将意志薄弱之可能性的问题归入一个假设,这个假设是指,在任何意向行动中都会涉及一个认知—欲求—行动(knowing—desiring—doing)的必然联结。正因为一些人认为这种联结是理所当然的,所以一个人违反当下最佳判断的意向行动(实际发生或可能出现)对该联结的违背就会变得令人疑惑,因而需要做出某种特别的解释。接着,江欣燕似乎合理地论证了,亚里士多德和程朱学派对这一挑战有着类似的答案,他们都认为这一挑战是站得住脚的,因为他们都认同这一假设。他们回应该挑战的策略是,“去表明意志薄弱的能动者在不能自制的行动中真的不知道什么是最佳的”[注]Jiang Xinyan, “What Kind of Knowledge does a Weak-willed Person Have? — A Comparative Study of Aristotle and the Cheng-zhu School,” p.242.。
当然,沿着这条线索,现代哲学家可能会做进一步的区分,将上述必然联结的本质看作是广义逻辑性的,或将它看作是因果性的,后者是塞尔通过因果“间隙”观点所断然否认的。要求亚里士多德或程朱学派做出这一区分是不切实际的,或者说是不合时宜的,尽管某种程度上说,它事实上引发了人们在意志薄弱问题上的当代争论,重燃了人们对这一问题的兴趣。然而,即使古代学者尚未做出这一区分,我们仍然有很好的理由认为,他们对认知—欲求—行动的必然联结的承认或默认是规范性的[注]在此,我所使用的“规范性联结”不能与较狭义的逻辑联结等而视之。两者的不同在于,前者而非后者是与所谓的因果间隙观点相容的。——很可能它是一种隐含的规范性形式,只不过其理论地位尚不明晰,以致对之未能进行有意识的反思。
第二,黄勇对新儒家程颐(1033—1107)和苏格拉底、亚里士多德就知行关系进行了精微而富有洞见的比较。前者对知行关系的关注引发了对知识的一个重要区分,即德性之知与见闻之知的区分(knowledge of/as virtue versus knowledge from seeing and hearing)。前一类型的知识在双重意义上是“内在的”: 不像后一类型的知识产生自外部联系,它源自内部体验,仿佛顿悟(sudden enlightenment),因而可称其为“自得”(self—getting)[注]Huang Yong, “How is Weakness of the Will not Possible? — CHENG Yi’s Neo-Confucian of Moral Knowledge,” p.446.;它也与出自它的行动有逻辑上的内在(即,蕴含性)关系[注]Ibid. p.444.。容我在此稍作评论。如果这种知识划分客观上成立,换言之,如果这种知识划分可独立于一个规定知识与行动之间须有内在关系的规范性原则——这一原则便可在无经验证据的情况下从概念上排除无自制力现象的可能性,那么这一区分就一定能够在从表面上无自制力的行为中筛选出那些严格的无自制力的行为方面作出有效解释,也一定能够在借德性之知的独立存在而对严格的无自制力行为之不可能性进行辩护方面起到关键作用。但问题正在于,这是一个很大的“如果”,我本人暂时不想在这一点上草草定论。
尽管德性之知作为一种理想的知识类型(例如,知道如何做)是广受认可的,或者说这种知识的规范性原则及其对行动的指导力是广被接受的,但这仍不等于说,在现实生活的任何时刻缺乏这种品质本位的(character-based)德性之知就绝不是实践判断(根据这种判断,我们来评测无自制力行动);也不能等于已证明,德性之知是那些在不同程度上朝向有德性的知识状态迈进的人通常所具备或期待的。再者,对于许多无关道德的日常行为,其所含主观的、明确的最佳判断(及其何时被违反)似乎只牵涉最低限度的知性能力或理智德性,这与任何特定类型的实践行动关联都不大。换言之,程颐的新儒家标准可能是不太切合实际的或者要求过高的,以致它对于我们世俗生活中的一系列待选的无自制力行为的判定来说似乎是不必要的。
总的来说,虽然关于(实践)知识与行动之间的真正关系绝不是通过一个粗糙的定义方式或者一个武断的规定来完成的,这一点可以令人信服地得到证明,但是通过谈论知识类型去排除无自制力现象的一般性进路也正揭示出一个复杂的(sophisticated)规范性立场中的某种(隐含的或潜在的)承担。当我使用“复杂的”时候,我意在表明,在某种意义上,与这种复杂的立场相关联的任何描述性部分或基础都几乎不可能被简单证伪——无论何时某人对一个待定的无自制力行为给出声称的证据,持这种规范性立场的理论家总是可以诉诸这样一种策略,即将它(重新)描述或阐释为属于上述清单的某一种现象。对于这种可坚持的既定规范性立场,其实践功能和理论地位则需要做更为细致的检验和探索。
3. 戴维森的非理性悖论
实际上,在考虑有吸引力的、复杂的规范性立场时(这种规范性立场嵌入到关于意志薄弱之类的非理性行为的整个解释任务中),戴维森做了下述评论:
没有理论可以完全逃避的非理性的底层悖论是这样的: 如果我们把它解释得太好(too well),就会将其转变成理性的一种隐蔽的形式;但是,如果我们太轻易地把某种不一致归于行为主体,那么我们就等于放弃了为有效诊断任何非理性所必需的(行为主体的)理性背景,从而使我们理性批判的能力大打折扣。[注]Donald Davidson, “Paradoxes of Irrationality,” p.303.
一些理论家试图为意志薄弱问题和它具有的理性问题提供一个充分的解释,但是他们大都未能充分领会这一评论的内蕴之意。我相信其中有些东西对于理解严格的无自制力现象或主观非理性行为而产生的诸多明显困惑尤为重要。这一欠缺在一定程度上似乎应归咎于这样一个事实: 戴维森本人并没有详细阐明这一评论在何种意义上揭示了一个真正的悖论,以及这一评论如何关联到他的行动理论和阐释理论中的其他重要观点。
为了让我们对这个悖论有一个基本了解,我在这里先做个初步的评论。显然,在解释融贯性/不融贯性,可理解性/不可理解性,以及非理性的辨识之间有着某种一般性的关系。第一,在现象描述的同一层面上不融贯性引起不可理解性(例如,社会或心理层面的,这与物理层面相对)。即是说,当我们将一个确定的行动甄别为非理性的时候,并不一定意味着该行动在其物理性质方面是不可理解的。比如,我们可以理解为什么有人吸烟,尽管早些时候他曾下定决心要戒烟,我们会认为他是非理性的,因为他一如既往地吸烟。为了进行甄别或批判,我们不必知道潜在的因果机制的精确细节。我们关于非理性的判断可以简单地是我们对某些行为所采取的先定规范性立场的一种表达。在每一个可能的描述或解释层面上,非理性与悖论性之间在不可理解这一点上似乎并无必然联系。
第二,非理性乃理性之殿内部的一个失败。[注]Ibid. p.289.即是说,如果一个人从不进行任何相关的推理,他就不可能被判定为非理性;我们至多只能称他为无理性(nonrational)。尽管非理性不能完全落在理性的疆界之外,但也不能完全落于其内。“完全在内”意味着,被推定的非理性行为中涉及的一切元素皆有一个或显或隐的合理解释,这种合理的解释看起来是如此之好,以至于会“将其转变成理性的一种隐蔽的形式”;或者换句话说,能动者他自己可能会运用这种合理解释去辩护其按外在标准显得不理性的行为。
第三,“不能自制的特殊之处在于,行为者不能理解他自身: 他在自己的意向行为中发现某种荒唐难解的东西”。[注]Donald Davidson, “How is Weakness of the Will Possible?” p.113.这一刻画所呈现出的挑战是,我们如何在对某类非理性行为给出一种圆满解释的同时不因此而把它们变成“主观上合理的”——也就是说,从能动者自身的角度来看,即便有此解释,他的行动也仍然是非理性的。所以,该行为中必须有某种至少部分地落于理性范围之外的东西使之成为非理性。换言之,在非理性行动的内核之中,一定会包含一个理性(即运用理由)的成分和一个无理性(亦即理由之外的支配)的成分,二者任缺其一我们都将难以拥有非理性。
当戴维森开始采用一种有关心智区域的分隔模型并声称理性不具备跨域性司法权力时,他似乎就在遵循上述思路。[注]Donald Davidson, “Deception and Division,” In The Multiple Self, Jon Elster (e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6.然而,一些理论家试图指出,戴维森将不能自制的行为与他关于推理和行动之间关系的原理进行调和的做法是不成功的[注]例如,参见Joseph Margolis, “Rationality and Weakness of Will,” Journal of Chinese Philosophy, 8 (1981): 9-27。,并且太唯智主义了[注]例如,参见Kirk Robinson, “Reason, Desire, and Weakness of Will,” American Philosophical Quarterly, 28(1991): 295-296; Robert Audi, “Weakness of Will and Rational Action,” Australasian Journal of Philosophy, 68(1990): 276-281。相反,罗伯特·奥迪(Robert Audi)提出了一个更宽泛的、整体性的和非理智主义的理性行动概念。。然而,这些批评者并未触及非理性悖论这一内核。[注]我在一定程度上触及这个悖论,采用的方法是,使用一个动态的超微观经济模型(a dynamic pico-economic model)去解释产生不能自制现象的因果机制,以及解释一个人对其自身进行非理性批判而形成/保持的判断。(参见Yujian Zheng, “Akrasia, Picoeconomics, and a Rational Reconstruction of Judgment Formation in Dynamic Choice,” Philosophical Studies, 104(2001):227-251。)我尚未察觉到其他学者对戴维森悖论所产生的兴趣和足够重视。这里的问题是: 当一个人试图去辨识非理性时,悖论处于何处?
构成戴维森式非理性悖论的双角可重述如下: 其一,如果我们对于意志薄弱如何产生解释得太好——即是说,如果我们在因果上和心智上找到了一个对它而言十分融贯的图像,那么我们就会将其转变成理性的一种隐蔽的形式;其二,如果我们太轻易地把某种不一致归于行为主体,即是说,如果我们轻易地将意志薄弱从可理解的现象类别中排除出去,那么我们等于是将本来在理性上可诊断的某些人类行为神秘化了,从而给人类交往中成功地阐释他者的可能之径设置了人为障碍。
这第二个方面似乎是比较容易理解的。如果某人由于他自身懒惰或能力不足而导致未能理解某个复杂的现象,并且他通过将问题转移到对象本身的不融贯上来为自己开脱,那么这显然不是什么困境,只不过是我们须加杜绝的委过做法。但是,就第一个方面来说,我们可以问: 在恰当的解释和解释得“太好”之间的界限在哪里?倘若融贯一致性是我们解释的目标,“太一致”之讥评从何谈起?
于我而言,若要反对上述人造的“隐蔽形式的合理性”,首先需要对如下关系提供一种可取的说明: 一个因果解释如何能够在正常或标准的情况下与理性的归属(rational ascription)产生关联?这种说明有希望在个人的(而非亚个人的)层面上给出一个必要的背景原理,即一个意向行为的恰当因果解释能够合法地将被解释的行为转化为某种形式的合理性。只有当这一背景图像确立之后,人们才能谈论在一些可能的情境中,因果解释可能会出现偏差,包括“太好”,以致不合法地将该行为转变成一种确定的理性形式。
背景原理的一个版本,可称之为P1:“对一个行动而言,任何因果的解释理由(作为一个因果前件)都能够使该行动(作为这个原因的后果)合理化。”[注]我在这里提到的“理由”一词指的正是为大家所普遍接受的用法,即是说,在能动者行动前的心理层面,“理由”主要是由欲求或信念构成的。这种理由并不总是意味着任一相关类的合理化(rationalization);否则P1或者它的缩写“理由合理化”将只是一个同义反复。比如,人们会说,在任一情境中,一个特定的行动会具备一个次要的理由和一个主要的理由,主要的理由在因果上直接表现为对该行动负责,而次要的理由作为因果上无效的理由不会使之合理化。本文所涉及的范围有限,不会去讨论这一原则的其他呈现形式,也不会去讨论不同形式间可能存在的联结,甚至对戴维森行动理论中更好的建构原则(称之为P2)也不会展开讨论。P2作为P1的反面,它主张一个行动的(基本的)辩护理由就是它的原因。详见戴维森在“How Is Weakness of the Will Possible?”中对P2的创发和辩护。现在我们可以重建无自制力的行动,以不同于事先辩护理由的解释理由来重建。原则上可以保证的一点是,在任何已经发生的行动中都可以找到一个确定的解释理由,尽管在能动者的最佳判断中所表明的解释理由与事先的辩护理由之间的分歧已经被隐含在无自制力行动的定义中了。在典型的无自制力的情境中,这样一种有分歧的、解释性的理由不难找到: 它通常就是一种欲求、感受等诸如此类的东西,或者与这些东西相对应,它们朝向次要选择而非最佳判断的某些吸引人的特征。甚至在辨识一个人实际意识当中这样一个因果上有效的个项变得异常困难时,也仍然很容易想象有一个因果项(尽管对于能动者自己来说,他不可能对之产生任何一种清晰的理由形式)潜藏于其脑(或身体)中。
有了P1,人们就能相对容易地设想这样一种可能性: 为使一种古怪的行为(即有待解释项)更加地融贯一致,解释者会冒不合理的合理化的危险;解释者可能将某些凭空想象的因果个项(即解释项)放入有目的的解释当中。如果这个想象的个项被当作是一个理由——不一定是一个足够好的理由——持此理由的能动者就会在有关这个行动的因果充分解释中弥合间隙,那么根据P1,这个想象的解释理由将会在某种相关的意义上合理化该行动。因此,真正的危险在于,错误地或武断地将某种样式上的合理性归于原本非理性的行动(即,将其转变成“理性的一种隐蔽的形式”)。
沿着这条线索,令人疑惑的是,一个人如何能够确信一个特定的解释项是想象的而非真正运作着的(比如,以某种尚未认识到的方式运作)。虽然在解释一些自然现象时这种疑惑也会产生,但是当人们面对的是一个典型的包含诸多心理属性的人类现象时,它会变得更为紧要。一个心理事件可以同时是因果事件和心智事件,亦即它可以用神经生理学(根本上是物理学)的术语来描述,同时也可以按照它的命题内容进行描述。心灵(心智)的特殊性在于,它不仅可以创造和理解意义,即是说,它拥有某些带有命题内容的心智状态或事件,而且也在于,能够描述这种心智状态的日常心理学(folk psychology)意义上的术语本身并没有清晰的概念边界。典型的日常心理学术语包括信念、欲求、理由、判断、愿望、意图、意志、决心、情感等等;通常情况下,它们相互重叠、相互交织、相互转化,并且它们在诸多语境下可能是变化不定的。人们并不能轻易地看到这一点,我将引用下述段落(类似的文章不在少数)来稍作阐释:
我们的日常心智术语展现了盘根错节的交叠状态,引人侧目的模糊性,范畴的模棱两可,以及丰富多样的细微差别……例如,我们通常会将一个信念归向一段记忆、一种选择、一种假设、一个偏见,以此代替将一个信念归之于一个能动者;或者说我们理应知晓或记起某事……我拥有两只手是一个信念吗,或者它应该被视为理所当然吗?当一只狗正在树下狂吠时,我们能够说它相信有只猫在树上吗?……我们的精神生活似乎是赫拉克利特流变说(Heraclitean flux)的一个极佳范例(参阅威廉·詹姆斯:“意识不是粘连的,而是流动的。”),我们可以随心所欲地去划分它,但这不等于建议或规定唯一的范畴划分方式。[注]K.V. Wilkes, “Functionalism, Psychology, and the Philosophy of Mind,” Philosophical Topics, 12 (1981): 152.
这一事实意味着,就辨识非理性的问题来说,当我们发现在特定的实践情境中情况紧要时,我们通常还是会有足够大的概念操作空间去解释(因而也是某种意义上的合理化,当P1是给定的时候)或者拒斥(排除)令人疑惑的现象。
准确来说,由于这种难以避免的概念松弛性,在将融贯性的这一层面或那一层面归于心灵的这一部分或那一部分(带有相应的命题内容或逻辑关系)时,我们几乎总是有,且总是要做出一个选择。这意味着,在理论中有多种方式可以获得想要的整体解释上的融贯性。因而完全可以设想,可能存在一个确定的获得整体融贯性的方式,它比其他方式更能保持规范性原则的完整性,而我们可将这种规范性原则的完整性接受为我们推理和行动的基本原则。[注]有理性的人除了会遵从纯粹的逻辑规则之外,很可能也会接受一些其他类型的规则。例如,卡尔纳普和亨普尔曾提到,所有人都接受的一条原则竟然不属于归纳逻辑。归纳推理要求完整的证据: 你所相信的假设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一切可获得的相关证据来支持的。参见Davidson, “How Is Weakness of the Will Possible?” p.112。另一个例子是,我们一开始就表明的柏拉图原则,我稍后再转回这一原则。例如,当我们说一个能动者被假定的某心智个项是不存在的时候,当我们拒绝将我们的批判性辨识奠定在有关行动者的“杜撰”部分之上时,我们通常不应武断行事,而应尽可能地遵守相关规则。
甚至当我们在正常情况下谈论简单的和自然的行为时,我们也会遵守许多种类的规则;并且我们遵守的规则,或运用规则的方式有可能在语境上是错误的,而对此我们并不自知。这里永远有一个问题,即以某种特定方式来定位有待解释的心灵: 也就是说,我们是否已经获得下述两方面的最佳平衡状态,一方面是,使个人的某心智个项与全部的可观察行为模式相适应[注]从理论上来说,在我们的阐释中所获得的最佳平衡可能不一定是能动者在行为时深思熟虑所达到的平衡点或平衡状态。;另一方面是,在遵守规则的情况下保持我们的批判能力,这些规则包括那些基本的理性规则,它们构成了我们理解事物的基本背景。
但话说回来,除了在上述达致最佳平衡的问题中涉及到的可能的张力之外,悖论到底栖身何处?在几乎每个人类实践领域里,似乎都存在着这样一些张力,它们与获得某种最佳平衡状态有关。我们通常不会称这些张力为“悖论”。与其说悖论的元素来自于行动解释中套用某些规则去排除虚构个项时存在的困难,毋宁说悖论的元素植根于解释非理性行动所无法回避的一种规范必然性(对某种推定的不可辨识的不融贯性进行理性批判的规范必然性)。
一个人在行为表现中所具备的理性程度似乎是他自身的某种内在特性——不可能取决于第三者怎么看他。至少在他生命中的一些特定时刻,他的心智能力或倾向应当是既定的事实,他可以展现出某些一般性的思维和意欲驱动模式。若对此没有争议,我们又该如何理解如下主张呢,即阐释者有权将一定程度上的融贯性/合理性归于被阐释者?[注]在这种表达中,有一种可能性会凸显出来: 阐释者和阐释对象正是同一个人,即一个人想要理解自身。难道可以说关于某个心灵的独立而既定的客观事实反倒依赖于另一个心灵是否决定及如何决定去理解它,这种说法本身难道不正是一个悖论吗?
对这个问题的一个简明回答是,只要我们在概念上区分存在论(本体论)的独立性和认识论的独立性,上述所谓的悖论就会迎刃而解。质言之,一个心灵在存在论上独立于阐释者并不与关于它的“事实”(这个“事实”的构建是通过阐释者的概念工具和阐释策略来完成的)在认识论上依赖于阐释者相矛盾。我们可以毫无矛盾地说,关于一个对象的任何“事实”陈述无非是来自某个解释者的特定理解的一种描述形式;这个解释者无需否认该对象在存在论上的独立性和(因果)一致性。此处所关涉的存在论假设是,任何自然事物或自然事件因果上都是融贯一致的,由于心灵也是一个自然事物(或者心智事件本身也是物理事件),因而心灵也一定是因果机制上融贯一致的。[注]本文的目标并不在于去论证这不是一个纯粹的假定,或者去论证我们具有好的理由去相信它。这一假设独立于或者说优先于任何人对心灵的理解(包括诠释学意义上的理解)。
当我们判断某种行为是内在地或主观上非理性的时候,也就是说,该能动者在意向上违背了他自愿采纳的标准时,我们是在将某种自然的不一致性归于他吗(好像那是他自然构成上的一种根本缺陷)?如果答案是肯定的,则会产生一个误解: 我们用仅有认识论相关性的理由僭越入存在论的领地。在另一方面,如果我们说我们“归之于”对象的并非存在论上的不一致性而是解释上的不一致性,即一个解释性框架内部的这种不一致是建立在一个被假设的能动者的心智个项、其他或多或少已经确立下来的心智部分,以及某些被广为接受的行动/思维原则之间,那么接下来的问题就是,为什么我们应该把这解释上的困难之源头归于对象而不是归于我们自己(比如我们在认识上的不完善或不胜任等等)?进一步的问题是,把某些行为判断为内在非理性而不是暂不可解的,这有助于达到何种目的呢?
在此,有一条进路似乎提供了比较合理的答案。不管在阐释者一方有多少可能的解释上的不一致来源,在能动者一方至少永远存在如下可能性: 即在他自己关于行动的有意识的理由与别的有关底层(或许尚未了解的)行动机制的其他心智个项之间具有某种真实的不一致性。因此,对阐释者来说,可以考虑把任何解释的“剩余物”归于能动者一方,而这永远是(或者原则上是)一个默认的、后备的策略。至于何时、何地这种策略的使用可以得到充分的证明,这本身也是一个规范性问题,它取决于许多经验的、语境的因素,以及某些一般的规范性方法,比如在彻底翻译中涉及到的“施惠原则”(the principle of charity)[注]奎因在考虑彻底翻译时首次提到“施惠原则”;但戴维森确是这一原则的最重要的支持者,他用该原则来阐释语言和行动。这一原则的基本信念是,不认可非理性的判断。参见W.V. Quine, Word and Object, Cambridge, MA: MIT Press, 1960, pp.26-79。又可参见Donald Davidson, Inquiries into Truth and Interpretation,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84。关于不同程度的施惠原则的比较性讨论,参见Paul Thagard and Richard E. Nisbett, “Rationality and Charity,” Philosophy of Science, 50(1983):250-267。。
阐释者必须非常仔细,以避免对于非理性的不成熟指控,即是说,须将这样的两方面区别开来: 一方面是,将不融贯性的浅层次根源归入本文第2节所列举的6种现象;另一方面是,能动者一侧不融贯性的深层次根源,而且仅仅只有后者才能为批判非理性提供可能的理由。当我说“浅层次”的时候,我所指的是,这些根源一经辨识,消除或规避它们就变得相对容易了;相对照地,所谓的“深层次根源”指的是,无论是辨识那些根源还是消除它们都更为困难。
尽管我们对这些不一致性的可能的深层次根源(这可能会产生所谓的“内在非理性的”行动)尚未进入任何细节性讨论,但是我更感兴趣的是,探索规范性阐释的一个更加细微的层面。让我们回到柏拉图原则,本文伊始我们便提到它,它是我们进行施惠型阐释(charitable interpretation)的一个重要原则。柏拉图原则讲的是,无人愿意与其所知(且所能)的最好选项背道而驰。十分有趣的是,这一原则的表述方式看起来像是对自然事实的一个纯粹描述,换言之,每个人出于本性都会根据他自己认为是最好的(或正确的)选项来行动(或推理)。然而,这一原则不太可能为真,除非你在这里把“自己认为是最好的”定义为,无论即时的心灵状态是什么,它都可以由他随附的、外显的行为揭示出来。而一旦这样定义,柏拉图原则所陈述的内容就是琐碎的真。
关于柏拉图原则一个可取的观点似乎是: 尽管它看上去像是描述性命题,但实际上是一个规范性原则,其正当功能不是描述或预言,而是命令、指导或教化。由此,我们不难领悟将一不自制行为判定为非理性的真正用意: 这是因为它未能达到它本应达到的规范标准,这一标准是能动者本人自然(自发)地采纳且无法合理地拒斥的;同时,也因为我们相信这个行为是能够按照这一规范标准来改正的。但另一方面,我们不必假设这个非理性行为在存在论上是不融贯的。从而我们总是保有这样一种可能性,即有一天我们能够在所有的因果细节上充分地解释这个行为的自然发生过程;但即使到了那一天,我们也并未“将其转变成理性的一种隐蔽的形式”,因为我们仍然在规范层面上将它视为是不融贯的,即不合规范。当然,若我们到时已根据新发现的心理学事实而部分地修改或放弃了我们现在使用的规范原则,则另当别论。
一言以蔽之,只要我们充分意识到这些基本原则或要求在我们有效的人类实践中的规范本性,那么戴维森的非理性悖论的暗影似已就此烟消云散。[注]然而,我关于戴维森悖论的解决方案不同于大卫·亨德森(David Henderson)提供的比较类似的方案。我的进路是,接受所有对可解释的非理性进行的归因,甚至对之没有一个充分的因果解释;而亨德森的方案并未强调非理性归因的规范性本质,也没有在不同层面的非理性之间做出区分。(David Henderson, “A Solution to Davidson’s Paradox of Irrationality,” Erkenntnis, 27(1987): 359-369.)
4. 当成真(holding true)和做成真(making true)之间的关系: 揭示一个儒家—孟子式范例
甚至在人们已经认可柏拉图原则的规范性基础之后,他们仍想知道为什么我们应当采用这个而不是那个特定的原则来作为一个阐释的(与之相对的,例如,教育的)规范性原则。我们创制及贯彻这样一个规范性原则的自由度有没有任何自然而终极的约束?如果有约束的话,那么这种约束是否应当来自人们现有的平均心智状态或其一般水平?换句话说,就一个规范性原则而言,是否存在一个描述上的准确性或似真性问题?
我们很容易想到一些规范性的规则,其唯一的目的只是要求服从和遵守。比如,一种有关工作制服的规则。规则制定者不必在意那些被要求服从规则者是否,或者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具有规则所要求的行为;在此唯一需要关心的是此后这些行为的出现,不论他们为了遵守规则要付出多大努力。很明显,在这些规则中不存在描述的精确性问题,即这些规则的应用对象的现状(status quo)或常规状况对规则本身的成立与否并不构成约束。但值得注意的是,任何规则制定者必须假定,规则的应用对象能够达到规则的要求[注]与这一假定相对应的一条被普遍接受的原则是,“应当蕴含着能够”。,或者是他们能够朝着那个尚未达到的方向去改变自身;否则的话,制定这样一个规则就没有意义。简言之,除了潜能性或(一种狭义上的)“可完善性”乃其必要条件之外,人们的现状并不是这类规则的考虑因素。
然而,当谈及阐释领域时,事情就变得大为不同了。由于阐释的目标在于搞清某个现存和既定的现象,它的内核自然是以真相为依归的描述性。那么,在一个关乎客体实质的阐释当中,对于一个以遵守服从为导向的规范性内容而言,哪里还为客观描述留下空间呢?因而,“阐释的规范性原则”的提法不免会产生某种悖论感: 一方面阐释要求关于被阐释之人现状的真实陈述,另一方面该原则的规范性则要求阐释对象对某一标准的适应或服从。这后一方面所对应的特殊的(即批判的)规范性要求预设着阐释对象作出改变的潜能性。人们如何能够无矛盾地将这两个对立的要求并置一处呢?
理论上说,对某一对象进行客观阐释的尝试应与对同一(所谓非理性)对象进行理性批判的尝试分开来。倘若这两种尝试在人类实践的现实中是互相分离的,则无必要去讨论批判性阐释及由此产生的任何悖论。然而不幸的是,现实的诠释学境况与此理论图景相去甚远。在戴维森关于非理性悖论的表述中,以及他在别处的一些饶富辩证意味的评论中,他对辨识非理性的理性背景之必然性的强调似乎产生于一个直觉: 即不大可能将阐释从整体理性背景下对非理性的规范性批判中分离出来。这种观点是,如果没有将大量的理性属性归之于阐释对象,就不会有任何有意义的批判性阐释凸显出来。
在某些层面上,也许仅仅只有一种可能的理解模式——这种批判式理解是由基本的理性规则建构和规定的,对于这些基本的理性规则,我们别无选择,只能将其作为具有思想的必要前提条件。正如戴维森自己提及的那样,“把至少某些非理性确认为内在不融贯……并不是去解释,甚至很难说在多大程度上是去描述这些心理状态;相反,它使描述和解释的难题变得几乎没有可能解决”[注]Donald Davidson, “Incoherence and Irrationality,” Dialectica, 39 (1985): 346.。在这里,“描述和解释”指的是那些欲摆脱像柏拉图原则这类理性规则而在理解上做出的努力。
对于人类行为的一些有意义的理解来说,如果某些理性规则和原则是必要的根据或不可或缺的成分,那么一个明显的暗示是,它们接近正常人或其潜能得以实现的正常条件,或者说至少不会偏离得太远。[注]倘若尚未清晰,那么就有必要强调一下,“人类行为”,以及理解人类行为的“规则和原则”并不是特定领域的行为,比如道德或法律的行为;应当说,我们正在谈论的是最一般的、共同的,或者最低层次上的可理解行为。那就是说,存在着这样一种与这一主张并不矛盾的可能性,即一个道德上不正常的人在绝大部分时间里都缺乏正常的伦理条件。然而另一方面,若要问这些规则和原则于现实描述的精确性要达到何种程度才会对整体的人类规范性实践最完美或长远最有利,则似乎没什么实际意义。因为更可信的事实是,大多数这类原则不是任何个人刻意设计或自觉选择的产物,而是长期进化过程中人类适应种种环境(包括自然变化,以及文化与自然的相互影响)的某种“社会积淀物”。
这里还有另外一层意思,谈论基本理性规则的个人选择或重新制定是令人难以置信的。因为这些规则长期以来就是我们交流、阐释和相互批判的社会实践生活之不可或缺的一个构成性部分,长期以来也在我们的行为和思想中占据很大比例(如果不是全部的话),包括行为和思想的模式、习惯、倾向等等,而所有这些社会实践生活、行为和思想在某种程度上都必须总是由这些规则来塑造,在这里任何整体性变化或彻底背离都是不可想象的。总之,理性批判通常会拥有效力,因为建立在规则之上的理性批判被认为具有某种程度上的自然真实性(natural veracity),对它们的完全背离被认为是违反常情的、荒唐的或不自然的。这些规则的外衣看起来越是“先天的”或描述上完善的,那么它们所拥有或产生的规范性—构成性力量就越强。我认为,这是对戴维森非理性悖论进行反思所引出的一个洞见——即关于当成真(与之相对应的是上述所谓“描述性的外衣”)和做成真(与之相对应的是上述所谓“规范性—构成性力量”)之间的某种有趣的关联。
基于此洞见,现在让我们对儒家经典的一些耳熟能详的篇章重新进行一番考察,希望我们由此可对上述关系及相关问题获得某种更加深入的理解。孟子最为独到和著名的性善论(idea about the goodness of human nature)不仅是儒家天人关系(the Confucian picture of Heaven and Man)的一个基础性部分,也是对后世儒家的道德实践或方向的深刻启发。在孟子著名的“乍见孺子入井”的篇章中,他评论道:“无恻隐之心,非人也;无羞恶之心,非人也;无辞让之心,非人也;无是非之心,非人也……人之有四端也,犹其有四体也。”[注]D.C. Lau (trans.), Mencius, Hong Kong: The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2003, 2A6.此处的和之后的《孟子》英译文皆出自Lau, 2003,以下凡引该文献仅标注简要信息。
正是通过这些表述所具有的清晰的语言形式,可以明显看出它们是描述性的而非规范性的(即未含“应”或“当”这类词)。即使这些表述潜在的或根本的意义(至少部分地)是规范性的,它们的描述性外观也在获得或引出道德目的方面起到了某种独特的、难以替代的作用。孟子这种范例性评论与上面所阐明的柏拉图原则在形式上具有明显的相似性,这一点绝非偶然。为此,申论如下。
孟子似乎将羞恶之心视为重中之重:“耻之于人大矣……不耻不若人,何若人有?”[注]D.C. Lau, 2003, 7A7.如果羞恶之心是人性深处的一种原初倾向,孟子的如下主张会是相当融贯的: 人之本性会由于他缺乏其他人所具有的尽责或克制的行为而感到羞愧,这些尽责或克制的行为展现出(规范性的)人性本身的典型特征,同时(在描述上)“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注]D.C. Lau, 2003, 4B19.。一方面,人禽之别实际上很微小,没有人(也许除了圣人)能被自动地保证总是或在通常情况下展现出道德的/理性的行为;然而在另一方面,每个人都有潜能和抱负去成为一个道德上更好的人,或者努力按此标准去行事。道德上更好的人作为一种理想类型(由圣人所例示)对于成为一个真正的人来说是定义性的。这后一方面意味着,把一个君子成熟的、全面发展的状态描述为,而非单纯地希望,宇宙中人的自然的(有别于人为的或古怪的)状态,这对于孟子而言,绝不是武断的、不切实际的,或模糊不清的文学修辞。[注]人们可能会说,孟子在此处对人的自然状态的理解可以与亚里士多德意义上的“第二自然”相比较。
无论相关表述的描述性形式是否,抑或在何种程度上,与一个规范性—构成性的意义或成分等同,一个难以否认的道德心理学事实似乎是,没有人能够真正接受或忍受这样一种意识,即自己内在地劣于他人,自己具有较少的“人类”品性,或者自己与禽兽同列。一个人也许会出于多种理由对这种“低劣”的可能证据不了解或产生自欺。正如孟子观察,“指不若人,则知恶之;心不若人,则不知恶,此之谓不知类也”[注]D.C. Lau, 2003, 6A12.。但准确地说,如果一个人已经有了清晰的证据证明他自己在道德上的低劣,并面临一个难以避免的指责时,他自然会萌发修正该行为以对令人生厌的情境作出改变的动机。因而这也是道德进步的可能性来源。[注]在实验心理学当中可能已经有了充分的经验证据来证明我的假设,换言之,人类行动运用的原则的描述性形式或者隐含的规范性形式往往比直接的规定或清晰的诫命在动机上更为有效。
同样的说法可用于戴维森意义上的理性低下或主观非理性,这些东西也都可纳入孟子“心不若人”这个一般性范畴之下。更为贴切地来说,我们最好还是使用孟子关于心的原初倾向当中的一种特定类型,即“是非之心”,以凸显理性评价中的一个独异特征(即内置于理性评价的批判意向)。接下来让我们跟随刘殿爵先生一道去关注认知判断和意动认可(conative sanction)之间的一个重要联系,关于这一点,我们似乎在孟子的人性论中可以看到:
“是非之心”有双重重要性。首先,它指辨明是非的心之能力。其次,它指的是心里对是非对错的认可和不认可。现在这种心的能力与理由的理解有关,因为孟子主张性善论。甚至当我们未行正确之事时,我们也忍不住想弄明白我们为何未行正确之事,并且我们会对我们已经选择的行动路线表示不认可,同时也有羞恶感。如此来说,人性本善的陈述在一个特定的意义上是完全独立于人类的实际行为的。[注]D.C. Lau, 2003, xix-xx.
这里的要旨是,强调孟子关于人性的隐含的规范性观点在逻辑上独立于人们行为表现或道德/理性发展的事实层面,尽管这样一种规范性所意味着的东西原则上不会超越人性的范围,即是说,人类潜在的能力自然地是由上天赋予的[注]刘殿爵先生在此处的解释并不是唯一的,例如,张岱年先生似乎也分享了关于孟子的这样一种解释。,或者进化而来的(如果按照现代自然科学的说法)。
孟子关于人性的特殊规范性地位在与荀子所努力建构的理论图景的对照中似乎变得更加清晰。荀子在性(人性,人生而有之的)与伪(审慎的努力,或者只有通过学习、培养或深思熟虑的实践才能实现出来者)之间做出了明确区分。[注]在这里,我在很大程度上沿袭了张岱年先生关于荀子和孟子之争的简明扼要的评注。尽管性伪之区分所具备的分析性和描述性功用明显加强了荀子对孟子关于人性评价问题的批判力度,但是它绝没能关闭孟子所展示的这另一种可能性,即以不受该区分限制的方式来定义人性。
孟子阐发人性的进路是,挑选出少量而独特的得到全面发展的人类代表(例如,圣人)作为事实证据去使人确信,其所体现的这些特征在原则上是每一个人都可以达到的;对于人类的每一位成员来说,他们为了实现圣人所做之事就必须拥有同样的端,否则即使圣人也不可能将之实现。潜能性,而不是现实性或实现的概率大小,必须内在于或者代表着一个特定的物种。与之相对,荀子进路背后的逻辑是,一个人生命伊始便完成了的和准备充分的(所以说是天生的)东西(因而任何后天审慎的努力都无法改变)仅仅只属于性。从这个角度来看,潜能性无法作为性,因为在定义上潜能性对于任何不涉及“积伪”就实现不了的特定道德结果来说既不是完成的,也不是指标性的。“今将以礼义积伪为人之性邪?”“故圣人之所以同于众,其不异于众者,性也;所以异而过众者,伪也。”[注]John Knoblock, Xunzi: A Translation and Study of the Complete Work, 3 vols,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8-1994, [Ⅲ] p. 153.所以,顺着这个逻辑,荀子必会否认,某个圣人的任何特定成就会蕴含着道德之端作为既定人性之一部分是普遍存在的。
这里无法对荀子和孟子之争进行全面衡量和裁定。我们现在的目的之特别引人关注和相关之处在于,将这一争论与有关“隐含的规范性”的论点进行联结。此论点似只能与孟子的进路发生关联。让我在此稍作阐发。
自不待言,孟子和荀子共享了儒家的根本理想,实现每一个人的仁、义、礼、智。即是说,他们都承认这一理想的可实现性。人们可以认为,他们的主要差异是实现理想的道路或方法不同。给定荀子关于性的观念,在这个理想的指引之下,道德行为或理性行为的实现必须对我们被赋予的性进行重塑,我们是根据某些清晰的规范程序进行重塑的。与之相反,孟子从关于性的一种隐含的规范性观念出发,把某些符合该理想的现实的目的-结果当作证据来证明性对于该理想来说的适切性或同质性,从而将理想的元素或其端与性绑缚在一起。那么,每一个人的道德任务仅仅是去丰富和扩大性的潜能性,包括克服一切外在逆境或厄运,以此来实现性之终极归宿(即命,或该理想的实现)。这是绑缚一个过程之两端的历时整体性运作,也就是说,某种目的论结果作为一端,而某种初始条件的一个特定状态作为另一端。这种操作揭示出一种动态(或者进化)规范性的独特形式,不管孟子或其他人在何种程度上或何种形式下对它获得清晰的自我意识。[注]顺带提一下,有必要注意一下这样一种可能性,即中文中表示品质的“端”(duan)作为上述所引文章(也就是Mencius 2A6)之中的一个关键词通常可以被译为“terminal”和“germ”。为了在不同风格之下理解这同样的绑缚两端的思想运作,让我们进一步考察孟子另一篇引人关注的文章:
口之于味也,目之于色也,耳之于声也,鼻之于臭也,四肢之于安佚也,性也,有命焉,君子不谓性也。仁之于父子也,义之于君臣也,礼之于宾主也,智之于贤者也,圣人之于天道也,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谓命也。[注]D.C. Lau, 2003, 7A24.
当孟子清楚地表明我们感官的倾向或功能属于人性时,为什么君子不将它归为人性,而是将其归向某种规范性的命(Decree)?相应地,当孟子清晰地表明道德性质属于命时,为什么君子不将之归于命,而是指向某种描述性的人性?很显然,孟子并非故意混淆性与命之间的概念区分,或者说他并不赞成君子在这样一种混淆之上进行任意归因。
我以为,更为合理的答案与上述绑缚观念相关,它关乎先天禀赋与命所规定的道德命运之间某种更深刻的联系。说得更具体点,先天禀赋的适当运用指向着某种特定的规范性命运,而规范性理想的可能实现则需要某些根源于本性的潜能性。倘若我们被赋予的天性没有受到规范性的限制,则君子和小人(道德上未得到发展的人)之间的差异就不会出现;倘若仅仅高唱着某些规范性高调(而从未留意我们先天的局限),则所有人之间的自然相似性,又甚至说人和进化上相近起源的动物之间的相似性就会被一概忽略掉——换言之,奠基于自然主义之上成为道德之人的普遍可能性路径就会很难获得深刻的揭示。这一绑缚观念是对当成真和做成真之间隐蔽的辩证关系的一种反思和揭示。
我之所以称孟子深刻的规范性进路是“隐含的”,有一个特殊的理由,即该进路不会认为终极的道德理想是某种外部嵌入的东西,好比从某种独断的外在权威那里获得一个明确的规则,而该种权威对接受该规则的臣民之自然禀赋的发展而言则是漠不关心或毫不相干的。相反,这种终极的道德理想对于这些臣民应该成为的那种类型的存在者来说是一个核心的、构成性的方面。说得再具体点,这种规范性的假设在双重意义上是“隐含的”: 第一,这种关于“端”的隐喻表明,主体已经禀具能被恰当地发展的本质成分;第二,对于主体而言,实现理想的规范性力量最好是来自内部,即来自其动态性动机结构的激励,而不是来自某种荀子好像十分热衷的与某些心灵工程相关的强制性重塑。
这种孟子式的规范性所具有的两个隐含的方面显然也会适应和支持上面提到的那种洞见,即当成真和做成真之间在实践上具有十分重要的关系。第一个隐含的方面与孟子关于“端”的隐喻的描述性外衣有关,它具有的一个作用是,树立人们对未来可预想的结果之可能实现的基本信心。而第二个隐含的方面具有改变或更正的内生性来源,它具有的一个作用是,调动与“羞恶之心”这一类东西相关的隐藏的能量。
因为本文的主要目的不是围绕道德教育/培养,故我不会对当成真和做成真的实践性面向进行探寻。相反,我要对这层关系的理论性面向进行一番新的考察。也就是说,考察这样一个问题,从我们对这层关系的反思中清晰地浮现出的优越视角出发,在解释意志薄弱时,孟子式的规范性进路具有什么可能的优势。
由上所述,我们可以更好地看出塞尔的断言中缺少了什么。塞尔断言,尘世间几乎无处不在的意志薄弱问题足以证伪戴维森对意志薄弱的可能性所陷入的迷思。对于塞尔的指责,持孟子进路的学者将如是回复: 对意志薄弱之可能性的问题产生困惑再正常不过了,我们关于人性的善/理性所固有的基本信念乃是某种描述性真理(这意味着意志薄弱在存在论上是成问题的)。但与此同时,作为理论家的我们则不应该忘记信念的深层次的隐含规范性,以及这种信念在整个宇宙进程中具有某种自然的必然性,以及它在充满着各种各样偶然性的现实生活中时时面临的脆弱性。换言之,当我们为了实现人必须是道德的这一天命而认识到这种理性的需要和实际的机会或前景时,我们不应该对人禽之别是细微的这个恒久的背景性事实视而不见。这两个方面的张力,或者说瞬变着的事实性与永恒而隐蔽的规范性之间所存在的无法根除的差距,是对意志薄弱如何可能的这一问题的根本性说明。
简言之,孟子基本的洞见如下: 人类不仅仅与动物有着类似的或同质的自然根源,而且十分重要的是,人类有一个自然使命,就是成为完全有理性和有道德的存在者;换句话说,明确的或隐含的规范性在一个独特的儒家-孟子意义上也是自然的。[注]可以说,它也是对亚里士多德意义上人被视作“有理性的动物”的重新解释。无论它是否,或在何种程度上,会将某种悖论的弦外之音传入彻底的还原主义者或物理主义者的耳朵里,这都是我们不得不在自然世界里发现的一种宿命。
5. 结论
本文的主要抱负体现为下述两点: 第一,它从一个比较哲学的新视角出发,结合对戴维森广受忽视的非理性悖论的关注,批判性地介入那些围绕古老而备受争议的意志薄弱问题的大量现存工作。第二,它致力于从根本上建立一个关乎动态规范性的统一的论点,这是一种特定的隐含类型的规范性,据我所知,这种规范性类型还从未被明确而充分地阐述过。[注]我称这种论点为“历时整体论”,并且最近也重新分析了戴维森著名的“沼泽人”思想实验,以此对“历时整体论”进行一些尝试性的表达。
有此抱负,本文几乎难以避免地是不完整的(部分地是由篇幅所限),这并不奇怪。一方面,这种不完整是由于它对儒家(特别是新儒家)资源的处理显然是不充分的,这些儒家资源很明显对于此处所涉及的主要问题有直接或间接的关系。[注]例如,戴震(著名清代学者)对宋代新儒家代表者的一些富有洞见的批判,戴震批判他们对孟子—荀子在人性方面的争论存在误解,戴震的工作似乎就能够与我正在处理的问题相匹配。(参见Zhen Dai戴震, Annotation and Interpretation of the Mencius孟子字义疏证, 2nd ed., Beijing: Zhonghua Shuju中华书局,1982, pp.25-38。)另一方面,这种不完整是由于它未能展开一个极其重要的思路,关于这一思路的讨论在这里只是个开头而已,换言之,上面所呈现的历时整体论的孟子式洞见仅仅是该思路的一个(卓越)代表。
尽管在余下的短小篇幅之中难以弥补这种不完整,但我还是想大致概括一下本文的主要观点,以使这些观点之间的某些结构关系或逻辑上的递进关系能变得更为明晰。第一个观点是,隐含的规范性这种观点很显然可以以不同方式进行揭示。最引人关注的是,它能将自身揭示或显露为一种动态的过程,这是通过先见之明与后见之明可能的混合,一种特定的可被描述的潜能以规范性方式获得实现。尽管描述性元素和规范性元素在概念上是不同的,但是它们通常相互混合、相互渗透。第二个观点是,在对戴维森非理性悖论的理解中,关键是要把握其批判性阐释观。此观念的核心是,描述性方面和规范性方面的相互作用及交融。第三个观点是,从(深层次的规范性解决方法出发)这种非理性悖论到当成真和做成真之间的关系的转移是独特的。这似乎可以含括柏拉图原则和孟子的某些范例性原则的描述性外衣的非偶然性。第四个观点涉及的是,在某种宽容的解读之下,孟子进路的历时整体论倾向(或其底层范式)如何能够为塞尔、戴维森关于意志薄弱的争论提供一个恰当的解决方案,该方案实际上也正是对戴维森非理性悖论的一个合理的、在实践上重要的解决方案。最后一个观点是,比较哲学中存在着相互依赖的两个方向(无论本文中关于它们的例示是如何地不完整): 以本文为例,一个方向上,我沿着戴维森的思路阐释孟子,同时在另一个方向上,我按照历时整体论的中国式思路去阐释(与戴维森式悖论相关的)柏拉图原则。总而言之,这里的重点并不在于有多详尽或准确地忠实于“原初的”思想材料,而是融贯的、富有启发性的新的综合。
意志薄弱对于人类自身在自然中的独特地位或者我们关于它的概念意识来说既是一种实践的挑战,亦是一种理论的挑战。我们对这一挑战的成功回应尽管不甚完美,但是在最深的意义上揭示了我们自己作为规范性存在无可逃避的、基础性的本质。我愿以孔子的一句名言来结束本文,希望它可藉由上述讨论之助而彰显出某种新的意蕴。“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
——基于巴尔金理论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