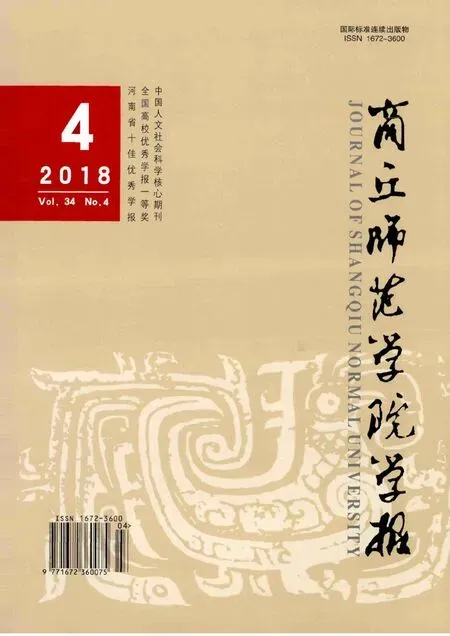豫东崇火习俗的历史解读
王 小 块
(商丘师范学院 人文学院,河南 商丘 476000)
本文所指豫东,包括今河南东部、鲁西南、安徽北部、江苏北部一带,其范围大致相当于古代宋国。中国古代的星宿分野说把天上星宿与地上州城相联系,根据某星宿的分野可以追踪、确定地上某一区域的归属,并称分星所在之域为虚(墟)。关于宋的分野,《晋书·天文志》曰:“自氐五度至尾九度为大火,于辰在卯,宋之分野,属豫州。”[1]308-309“大火,心也”,“心,宋之分野”,“宋,大辰之虚也”[2]2084。其中的心、大火,即东方苍龙七宿中位列第五的心宿,由于它红光如血似火,故称之为“大火”,又称商星、大辰、辰、天王,与豫东商丘关系密切。《汉书·地理志》云:“周封微子于宋,今之睢阳是也,本陶唐氏火正阏伯之虚也。”“宋地,房、心之分野也。今之沛、梁、楚、山阳、济阴、东平及东郡之须昌、寿张,皆宋分也。”而“自微子二十余世,至景公灭曹,灭曹后五世亦为齐、楚、魏所灭,三分其地。魏得其梁、陈留,齐得其济阴、东平,楚得其沛。故今之楚彭城,本宋也,《春秋经》曰‘围宋彭城’。宋虽灭,本大国,故自为分野。”[3]1663上述记载表明,在汉代,西迄开封(梁)、东到彭城(徐州),南至蚌埠,北到定陶、菏泽,皆归古宋国,其都商丘,为心宿分野。
由汉至清,史籍中对豫东地望多有提及,除《汉书·地理志》外,《后汉书·郡国志》梁国睢阳下云:“本宋国阏伯之墟。”[4]3426《春秋左氏经传集解》于襄公九年“阏伯居商丘”下云:“商丘在宋地。”[5]850而《春秋释例》中曰:“宋、商、商丘三名,梁国睢阳县也。”[6]153《括地志》宋州下云:“宋城县,古阏伯之墟,即商丘也。”[7]153《元和郡县制》宋城下说与上同。《太平寰宇记》宋州下云:“《禹贡》豫州之域,即高辛氏之子阏伯所居商丘,今州理是也。”[8]59王国维先生进一步引申“古之宋国,实名商丘,丘者墟也,宋之称商丘,犹洹水南之称殷墟,是商在宋地。”[9]21995年至1997年,中美联合考古队在商丘古城西南发现宋国故城遗址,进一步证明《左传》中所记“商丘”即今豫东商丘。
豫东有着较多的崇火习俗,被称为“中国火文化之乡”。
一、对火祖燧人氏的尊崇
豫东民众对“仰察辰心,取以出火,作钻燧,别五木以改火”[10]卷5的燧人氏非常尊崇,把其陵墓——燧皇陵称为“老爷坟”,并于每年除夕、清明等节日从家中用衣襟、手帕兜一包黄土,撒到“老爷坟”上,给火祖添坟扫墓、烧香磕头、答谢敬拜,以盼火祖保佑全家在新的一年平平安安。此外还有“取新(薪)火”、拜火和“赛火把”“玩铁花”等习俗。
1.豫东“取新(薪)火”、拜火和“赛火把”“玩铁花”习俗
旧时豫东,每当春节来临之际,有到陵前“取薪火”、拜火和“添新土”的习俗。“取薪火”仪式由族长或族里德高望重的老人带专人到各家各户将旧火全部熄灭,以示过去一年的结束,并向每户收取一些旧灰、食盐、粮食及其他食品送到燧人氏陵。在陵前,举行拜火仪式,由祭司杀鸡酹酒,祭拜火祖,再把鸡血和旧火灰带到陵后深埋,以示送走灾难、不祥。然后,用钻木方法取出新火,作为新一年生产、生活的起点。各家各户拿火种到陵前接燃新火,引回家中,以示引来吉祥。为庆祝取回新火,各家各户要献上祭礼祭拜火祖。
旧时每年正月十五晚上,豫东还有在野外“赛火把”“玩铁花”的习俗。“赛火把”的道具是家里用过的旧箅子,里边卷上麦秸,到野外一齐点燃玩耍,相邻的村庄还要进行比赛,看哪个村的火把多,玩的时间长。而“玩铁花”则是在套牲口的铁笼嘴里放上木炭,裹挟碎铁屑,用木棍或钢叉挑起,由几名身强力壮的年轻男子轮番摇动,甩出去的烧红的铁屑碰触到地上或事先放好的树枝上,幻化出一簇簇、一团团、一朵朵漂亮的火花,围观的男女老幼兴致勃勃,其乐无穷。据当地民众称,这是在娱火祖燧皇爷。
2.对豫东尊崇燧人氏的历史解读

人工取火,结束了先民“茹毛饮血”的野蛮生活,并引发了以后一系列文化、技术上的革命,开启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作为有信史记录的最早用火为人类造福的人或者氏族代表,也是人类利用自然资源改善自身的英雄,燧人氏被称作圣人、奉为“三皇”之首,亦属名副其实。鉴于火的巨大功用,以及燧人氏的首创之功,豫东民众对火、对发明人工取火的英雄先祖加以顶礼膜拜和崇祀也在情理之中了。豫东的“取新(薪)火”仪式即采用原始钻木取火的方法取出新火。火所具有的无可比拟的威力,以及带给人间的温暖、光明和社会的进步,以及造成的巨大灾害,使民众对它充满无上感恩与畏惧,进而有了拜火仪式,而“赛火把”“玩铁花”应是祭祀时的活动内容,是远古居民自然崇拜、图腾崇拜、英雄崇拜的一种展示和历史延续。
由于“火”有着几乎无坚不摧、所向披靡的神异力量,拥有极大的能量,甚至可逐邪驱鬼,所以豫东一带还有新娘跳火盆、设“挡门灰”的习俗。在新媳妇下轿进婆家大门时,需从烧得很旺的火盆上跨过,以此扫去身上所沾染的污垢(邪气),把不洁之物挡在门外,以保新娘健康平安,来夫家后子孙兴旺,日子过得红红火火。豫东民众认为,在干草(谷杆)燃烧时发出的噼啪声,尤其里面再加了油和盐,火会烧得更旺,邪祟妖魔看见火光、听见响声便不敢近前,不会加害于新人。而撒“挡门灰”的原因和目的也是如此。经过火的淬炼、燃烧后的灰烬既保留了原物的精魄,具有一定法力,同时还凝结了火的威力,其祛邪驱鬼的功能更强大。遇到周边有丧事,在家门前撒一道灶灰,以避免邪物进入门庭,带来灾祸。这些都是远古民众自然崇拜的一种演变。正由于火具有如此大的威力,在用火时还要遵循一定的规矩。旧时豫东用火非常讲究,对火绝不容许玷污、亵渎。炉灶、香炉都看得非常尊贵,任何人不能随意跨越;烧火做饭的干柴,都要顺着放整齐,烧时先从一头开始,不允许乱烧乱燃;熄灭余火时,不能打散火堆,不能用唾液灭火,更不能用脏水泼灭,否则就是对火的不敬、对火祖的亵渎。
二、对火神阏伯的信仰
豫东有中国目前所知最早的天文观测台——阏伯台,又名商丘,即为大辰(大火)之虚,上应大火、商星、辰星或宋星。据《左传·襄公九年》载:“陶唐氏之火正阏伯居商丘。祀大火,而火纪时焉。相土因之,故商主大火。”[2]466《商丘县志》载“阏伯,高辛氏之后,封商丘为火正,主辰星之祀”[14]78。当地流传,火正阏伯在商丘观察天上的“大火”,并管理火种,为民众作出巨大贡献,死后被埋于台上,尊称火神,阏伯台也被称为火神台,人们定时在此纪念火神阏伯。
1.豫东“朝台”、元宵节小孩打灯笼习俗
正月初七,相传是火神阏伯生日,又恰逢中国农历春节期间,几乎每年此时,豫东都会举行盛大的火神祭祀活动,周边省份数百里民众到火神台添土圆坟、进香、祭拜,谓之“朝台”“台会”。活动时间过去为7天,现为1个月。除正月朝台外,豫东集中朝拜火神还有两次,即四月四的祭商星和六月二十三纪念阏伯去世的活动,这两次会期各10天。像这样一年3次隆重、系统祭祀火神的活动还是比较罕见的。每年台会期间,舞火龙、耍火狮、跳火圈、吞火吐火、取火种、续火香、烧鸡蛋、烤食品、祭火神、祀火星、放烟花、赛花灯、玩铁花、赛火把等活动都会有所展示。来自各地的朝台团体也会带舞狮、扭秧歌、耍钢叉、跑旱船、踩高跷等节目来娱火神。
正月十五元宵节是中国重大传统年庆之一,而夜间活动是其一大特点。届时,万民张灯、出游。因此,元宵节又称灯节。这一天,豫东每家大人都会给孩子买或做个灯笼,点亮了,让孩子晚上在外面提着玩。其含义有二:一是明亮的灯笼所象征的光明、正义可以使任何鬼怪都不敢靠近,能为孩子起到驱邪的作用。二是孩子提着点亮的灯笼外出,即便迷路了,也能被火神爷引回家。豫东元宵节小孩打灯笼的独特内涵,凸显了豫东民众对火和火神阏伯的崇信。在“大火”沉没不见的冬季,豫东民众以燃亮的灯笼来取寓天上明亮的“大火”,是对火神阏伯信仰的一种曲折表达。
2.对豫东火神信仰的历史解读
豫东的火神信仰与火正阏伯“祀大火”有关。关于中国古代观星授时,《尚书·尧典》有重要论述:“(尧)乃命羲和,钦若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时。”[15]31-32“日中星鸟,以殷仲春”;“日永星火,以正仲夏”;“宵中星虚,以殷仲秋”;“日短星昂,以正仲冬”[15]56。其中的“日中”“宵中”“日永”“日短”分别指春秋二分、夏冬二至;而“星鸟”“星火”“星虚”“星昂”则是鸟、火、虚、昂四星黄昏时于二分、二至时在天空中的位置(南中天);“仲”指四季中每季的第二月。推算这种星象出现的时间,约为公元前2400年。这说明,远古居民已能通过观察天象与昼夜时间的变化来确定四个主要节气的时间。对于羲、和敬天授人时,尧大加赞赏:“咨嗟!汝羲仲、羲叔与和仲、和叔。一期之间有三百有六旬有六日,分为十二个月,则余日不尽,令气朔参差,若以闰月不缺,令正朔得正定四时之气节,成一岁之历象,是汝之美可叹也。又以此岁历告时授事,信能和治百官,使之众功皆广业。”[15]31-32叹美羲、和敬天授时,使风俗大和。由此可知,观测星象,在当时是一个十分重要的职责。上古时期的“火正”即担此职,负责对“大火”进行观测、祭祀。传说,颛顼时有火正黎,帝喾时有祝融,尧时为阏伯,舜时是益。
《左传正义》云:“火正之官居职有功,祀火星之时以此火正之神配食也。……而火正又配食于火星者,以其于火有功,祭火星又之后稷,得配天,又配稷。”[2]1941由于阏伯行火历,以火纪时,所以最迟在先商时人们便开始将阏伯与“大火”一同祭祀了,商周秦汉时期便作为国家祭祀而存在。《作洛》篇中提到周人于开国之初不仅接受了殷人的国土,连殷人的族神帝喾与族星“大火”也延续了下来。而《史记·封禅书》中秦朝把奉祀“大火”(辰)排在国家祭祀的第四位,由此“大火”的重要性也就可想而知了。汉代的后稷祠、灵星祠都是祀“大火”之祠。至北宋,其尚火气象更是远超唐汉,直攀商周,不仅以火德王①,且在商丘以阏伯配食,对“大火”于“建辰、建戌出内之月,内降祝版,留司长吏奉祭行事”[16]2513。《宋史·天文志》曰:“心宿三星,天王正位也。中星曰明堂,天子位,为大辰,主天下之赏罚。前星为太子;后星为庶子。星直,则王失势。明大,天下同心;天下变动,则心星见祥。”[16]1006作为龙星诸宿之心的“大火”,象征着帝王,居于中央的位置,以支配四方。所以,先秦龙旗上所绣之龙即龙星之形。庞朴由此甚至认为,中国文化中较浓厚的崇龙现象也与“大火”有关,反映在民俗中即为尚龙、龙戏珠、星回节、火把节,等等[17]。
古人认为,观天象,知人事。古代帝王自诩“受命于天”,认为天象变化关乎自身统治,希望上天能够随时传递“信息”给自己,并且只传递给自己,是以牢牢掌控着天文观测机构,只许在皇城建立天文观测台,并由官方来控制天文历法。在观测天象的同时,政府还定期不定期举行多种祭祀活动。后来,随着天文观测项目的增加和祭祀活动的频繁,活动场地需要分开,祭祀改到明堂举行,天文台专司观测天文和气象。

火正阏伯在商丘‘祀大火’,保存火种,造福当地。而豫东民众对阏伯的崇信亦随着历史的演进发展为要用一种专门的方式来表达,这就是“朝台”。据史料载,阏伯台在商周以及春秋战国的宋国时期一直是国家的社庙,为重要的祭祀场所,每年官方都要举办多次隆重的祭祀活动,至唐代已发展成相当隆重的庙会。在官方倡导下,民间响应更为积极,至宋代,对火神阏伯的崇祀达到顶峰。关于豫东“火神台会”在地方志中备有记载,如宁波天一阁藏明嘉靖本《夏邑县志》第8卷岁时民俗中有“正月:初七,有‘火星庙会’”[18]71。清康熙四十四年《商丘县志》风·节序载:“正月七日,俗传阏伯火正生辰,男女群集于阏伯台及火星庙进香,车马阗咽,暄豗累日。”[14]38第20卷岁时民俗曰:“正月:……初七,俗传‘阏伯火正生辰’,男女群集于阏伯台及火星庙进香,车马阗咽,暄豗累日。”[14]130清乾隆十九年刻本《归德府志》卷10风俗载:“正月:七日,俗传阏伯火正生辰,男女群集于阏伯台及火星庙进香,喧豗竟日”[19]386。在新中国成立后编撰的《商丘县志》风俗中,也写道:“正月初七为阏伯生日,旧时男女老少,朝台(阏伯台)进香,今人在初七前后到阏伯台赶物交会、看戏和民间舞蹈。”[20]485
三、结语
作为“大火”分野的豫东,其特殊的地理位置使得燧人氏能够在此“察辰心而出火”、发明人工取火,而尧之火正阏伯亦在此“祀大火”以纪时。与地上残留的古迹相映衬的当地围绕燧人氏、燧人氏陵、阏伯、阏伯台和阏伯庙,广泛流传着“后羿射日”“燧明国”“燧人氏与太阳鸟”“金蚰子和火龙珠”“阏伯保存火种”“阏伯盗天火”“火烧亳州”等神话传说。这一切都与天、地之“火”这一原始先民们视为神圣、无可抗御、能够带来温暖、光明、希望、畏惧和永恒的事物有关,围绕“火”而形成的种种神圣空间、禁忌、仪式、观念等,浸淫着豫东民众的物质和精神,造就了豫东独特的崇火习俗,它不仅参与了中华文明的建构,也是对中国丰富历史文化内涵的一种解读。
注释:
①时人自称“火宋”,并派定南朝刘宋为“水宋”,河南旧志整理丛书。参见俞樾《茶香室丛钞》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90页。
②作者访查时据当地村民所说。据说新中国成立前曾有商丘寺(现在开元寺的前身,之前在阏伯台下)寺谱,新中国成立后被毁。
[1]房玄龄.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4.
[2]阮元,刻.十三经注疏[M].北京:中华书局,1982.
[3]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2.
[4]司马彪.后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59.
[5]杜预.春秋左氏经传集解[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
[6]杜预.春秋释例(清乾隆敕刊本)[M].武英殿聚珍版.
[7]李泰,著.贺次君,辑校.括地志辑校[M].北京:中华书局,1980.
[8]乐史.太平寰宇记[M].北京:中华书局,2000.
[9]王国维.观堂集林·王国维遗书[M].上海:上海古籍书店,1983.
[10]罗泌.路史[M].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1]韩非子[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
[12]李昉,等.太平御览[M].北京:中华书局,1960.
[13]真北宋板古三坟书·太古河图代姓纪第二[M].河南旧志整理丛书绍兴十七年婺州州学刻本.
[14]河南省商丘县志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商丘县志(清康熙四十四年)[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89.
[15]尚书正义[M]//十三经注疏(标点本).李学勤,主编.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16]脱脱,等.宋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7.
[17]庞朴.火历钩沉——一个遗佚已久的古历之发现[J].中国文化,1989(12).
[18]夏邑县志编撰委员会.夏邑县志[M].上海:上海古籍书店,1982.
[19]河南省商丘县地区地方编纂委员会.归德府志(清·乾隆十九年)[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4.
[20]商丘县志编纂委员会.商丘县志[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