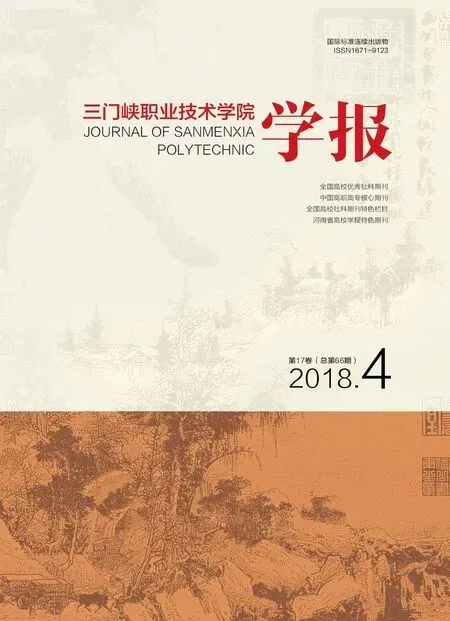论苏童小说女性形象的美学特征
◎李瑞萍
(三门峡职业技术学院 电大部,河南 三门峡 472000)
苏童,当代最优秀的小说家之一,是公认的“天生说故事的高手”。他的创作题材大致有三类:写故乡的“枫杨树系列”小说、描写少年成长的“香椿树”系列和旧时代女性系列小说。而他的以“红粉”为意象的旧时代女性系列无疑是最成功的,改编成影视剧的也大都属于这类题材,如《妻妾成群》《红粉》《妇女生活》等。小说中成功塑造了一群独特的女性形象,即那些旧时代南方边缘化的女性。与20世纪主流文学的积极乐观、阳光向上的基调不同,苏童笔下的女性形象呈现出一种独特另类的唯美主义美学特征。
一、南方地域文化色彩
苏童的女性形象,与北方女性泼辣、爽朗、直率相区别。无论是女性主题、感伤灵动的风格,还是精致唯美的语言,都体现了明显南方地域特色。
南方的地理环境长期形成了南方人细腻、阴柔的性格。南方地势高低不平,峰峦叠嶂,气候多雨潮湿,雾气迷茫,易于形成梦幻迷蒙的思维品行;相比之下,北方平原居多,地势空旷,因而性情直率粗犷。另一方面,自古以来,江南文化就有唯美主义的传统特色。东晋的永嘉年间,名人雅士闲情逸致,赏玩文学,追求雕琢辞藻,附庸风雅,开启了中国文艺审美的一个新风貌,是江南唯美文化的萌芽。到南朝,唯美风尚趋于成熟,文士们更加推崇细腻的审美追求。贵族文士蓄妓成风,狎妓赏妓成了贵族文人的一种高雅活动,歌妓舞女自然成了他们创作的主要来源。隋唐时代,晚唐五代的词,尤其是“花间派”,表明江南文人走进更为细腻的官能感受和纤细柔媚的情感捕捉中。南宋建都临安后,市民文化异常发达,文人与市井青楼的联系更为密切,产生了不少有关各级女性的作品。明清是江南唯美主义文化又一鼎盛时期。应该说,江南的唯美文化是中国典型的一种区域文化。进入20世纪以来,由于启蒙主义文学的功利需求和宏大叙事,江南这种唯美主义文化被强行赶出文学界。到80年代中期,由于改革开放,思想解放,多种文学思潮涌现,回归传统,苏童、叶兆言、范小青等一批南方作家续写历史,续写文化,重新叙述江南绮丽秀美的文化。[1]
苏童小说的女性主题,就明显体现了南方地域色彩。在潮湿、阴暗、发霉的生存环境中写了一群柔媚的女性形象。他写的女性多是妓女、姨太太、情妇、戏子等,小说中,颂莲、梅珊、秋仪、娴、芝、箫、姚碧珍、红菱等女子,她们或是妓女,或者身上体现了旧时代妓女的影子。可以说苏童在他的作品中塑造了一大批栩栩如生的卑微、低贱的“妓女”形象。她们大都有着漂亮的外貌,对生存充满了欲望。但都无一例外地依附男人,对男人一味地屈从、接受,而把心计都用在了姐妹的身上。都用身体勾引男人,或者用“性”占有男人。“妓女”本指被迫卖淫的女人,但这些女性都将自身价值与爱欲的实现寄托于男子,她们的实质无异于妓女。这些“妓女”在苏童的笔下又灵动异彩,《妻妾成群》中的四个女人,虽在同样的环境,但风情各异,大太太毓如呆板固执冷酷圆滑,二太太卓云满面堆笑阴险歹毒,三太太梅珊冷艳刚烈大胆多情,四太太颂莲单纯感伤。同时小说中的曲折窄巷、青石小路、拱桥河流、阴暗房间、阴雨绵绵,雾气迷蒙,人物的生存环境也体现了明显的南方地方色彩。
二、阴郁独特的审美趣味
20世纪主流文学的现实主义创作是一种宏大的叙事模式:选择重大题材,表现重大主题,塑造典型形象。与之相适应的文学基调是奔放、刚健、雄伟、热烈,人物也是积极乐观、豪迈欢快的个性色调。《青春之歌》《创业史》《红日》都体现了这一模式的经典之作。
苏童则创造了女性形象的阴郁另类审美特征。他的小说完全放弃“宏大叙事”的追求,以意象化的人物消解典型人物的权威模式,回避重大主题和重大题材,而将目光投向边缘化的女性如妓女、小妾,“讲述”她们的生存状态和个体生命的体验,以日常生活的叙述取代宏大叙事。《妻妾成群》《红粉》《妇女生活》中的女人们,他们的世界就是自己生存的小空间和依靠的男人,从他们身上听不到时代前进的脚步,看不到社会发展的新面貌。她们体现出的精神特征是与正统文学相对立的精神面貌:阴暗、低沉、卑琐、阴柔、绝望,这使苏童的女性小说充满了阴霾的气息。这些女性似乎天生如此,跟不上时代的潮流,或者压抑、恐惧(《妻妾成群》),或者顽固不化、贪婪享受(《红粉》),或者母女间仇恨、冷漠(《另一种妇女生活》),或者通奸情杀(《南方的堕落》)。拟旧的气息、灰暗的色调、潮湿而迷蒙的氛围,使读者感到压抑和窒息。正因为这些与众不同的、独特的女性形象,使苏童在当代文学占有重要一席之地。
三、人物的意象美
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前,五四新文学所开创的中国现代文学的现实主义传统始终处于主流地位,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成为20世纪中国作家普遍的追求。作为先锋作家的苏童,却沿袭了中国古代诗画的创作方法,人物更多呈现为意象性。这些人物一般来说不是经典现代小说人物所要求的“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的立体感、真实性,而是意象的混沌感、象征性。
“意象”是中国古代诗学的一个基本概念。“意”是指客体化了的主题情思,“象”是指主体化了的客体物象。意象具有象征性、暗示性、多义性特征。而“典型”是西方文论的独创。西方文学侧重于叙事,中国文学则侧重于抒情。意象偏重于主观方面,典型是一种写实的文学形态,客观多于主观。[2]中国自古以来的文艺理论中,意象一直是个重要的概念,但中国古典文论对意象的研究大多是着眼于诗歌,对于小说创作及其欣赏中意象问题的研究则几近于零。[3]在诗歌创作中运用意象是不足为奇的,尤其是古典诗歌。而把意象引入当代小说创作中,在当代文坛实属不多。能把意象用得出神入化,我们不能不敬佩苏童的文学功底。显然,苏童继承了中国古代写作文法。另外,苏童在年轻时也写过诗歌,虽然没有成为诗人,但在语言上为以后的小说意象写作奠定了基础。
与现实主义写作不同,苏童小说中的人物不是追求人物的典型性,人物塑造被推到了次要地位,而故事的讲述(方式)才是作家重视的。这些人物本身并不承载什么“社会真实”,而只是体现个体生命的存在状态,尤其是女性身上包含着的丰富的文化内涵。颂莲违背时代和所受的教育,做了大户人家的姨太太;秋仪、小萼从内心拒绝社会主义改造;娴到死都认为自己的人生悲剧是因为那次怕疼没有做堕胎手术;姚碧珍在宛如与世隔绝的梅家茶楼过着阴暗堕落的生活一直到老。在描写女性中,作家运用了大量的意象,如《红粉》中的胭脂盒、《另一种妇女生活》中的简家酱园、《武则天》中的紫檀木球,《妻妾成群》中的意象更是俯拾皆是,简直就是一个意象集:夏天的海棠、秋天的菊花、冬天的白雪;颂莲醉酒、梅珊唱戏、飞浦吹箫、陈佐千阳痿;还有枯井、紫藤架,戏曲片段《杜十娘》《女吊》。这些意象很难说清它的具体含义,但与人物的心绪、感觉和命运是同构的,给阅读者带来一种艺术上的想象与回味。小说中人物的情绪与环境相融合,达到情景相融的艺术效果。
苏童的小说运用意象化白描,呈现出诗化的特征。《妻妾成群》是苏童转折性的作品,遗弃早先繁华丰盈的叙事方式,竭力简化小说的程序,采用顺叙这种传统而古老的叙事方式,省略小说多余的词语,留下充足的意象空间。“天已寒秋,女人们都纷纷换上了秋衣,树叶也纷纷在清晨和深夜飘落在地,枯黄的一片覆盖了花园。几个女佣蹲在一起烧树叶,一股焦烟味弥漫开来,颂莲的窗口砰地打开,女佣们看见颂莲的脸因愤怒而涨得绯红。她抓起一把木梳在窗台上敲着,谁让你们烧树叶的?好好的树叶烧得那么难闻。女佣们便收起笤帚箩筐,一个胆大的女佣说,这么多的树叶,不烧怎么弄?颂莲就把木梳丛窗里砸倒她的身上,颂莲喊,不准烧就是不准烧!然后她砰地关上了窗子”。[4]很显然,这是在叙事,表现颂莲在秋日烦乱的心绪和越来越乖戾暴躁的性格。但作者没有一句叙述性语言写人物的心情,而纯粹用描写性语言——写实白描,具有一种强烈的画面感,并有一种意象性感觉。作者将“寒秋落叶”的诗歌意象与人物的情绪相结合,延伸了意象的内涵,也扩大了描写的张力。
苏童运用多种艺术手法,突出了人物形象的意象性。苏童在写人物对话去掉了冒号和引号,充分发挥了汉语特有的意象性功能。他善用色彩,用色彩作为意象烘托气氛和基调。苏童还运用一些声音和气味,强化意象效果。苏童描写女性,语言凄迷、唯美,懂得“用最少最简洁的语言挑出人物性格中深藏的东西。”[5]简洁而准确地描写女性心理和细节。
四、精致的细节描写和心理刻画
关于苏童的心理刻画、细节描写,张清华曾说:“在我的印象中还没有哪一个当代作家能够像苏童这样多和这样精细地写到女性,这样得心应手和在最深层的潜意识处对女性进行描写。我甚至震惊,他是否比女人自身还要了解女人?他究竟依据什么,为什么如此熟知她们的内心?”[6]可以说这段话说出了许多评论家及读者的共同感受和疑惑。王干也说:“颂莲、梅珊、秋仪、小萼等青年女性的性格心理深度几乎填补了当代文学的空白,可以说是一种‘典型'”。[7]在去年江苏召开的苏童创作研讨会上,女评论家张燕玲说,苏童的女性描写,常使女作家感到惭愧。这主要是指苏童对众多女性的心理刻画和细节描写。可以说,就凭这方面的成就,就可奠定苏童在当代文学上的地位。
《妻妾成群》中这样写颂莲第一次见大太太毓如时的情景:“颂莲刚要上去行礼,毓如手里的佛珠突然断了线,滚了一地,毓如推开红木靠椅下地捡佛珠,口中念念有词,罪过,罪过。颂莲相帮去捡,被毓如轻轻地推开,她说,罪过,罪过,始终没抬眼看颂莲一眼。”[8]。简单的“滚珠”“捡珠”“相帮”“推开”,还有口中的“念念有词”,把大太太对颂莲进门的嫉妒、虚伪、吃醋的心理,刻画得入木三分。接着见二太太卓云,在卓云这里受到了热情的礼遇。当颂莲要离开就“偷偷瞟陈佐千”,但陈佐千对颂莲的眼神视若无睹,似乎有意在这里多待,颂莲就判断陈佐千是宠爱卓云的,眼睛就不由地停留在卓云的脸上身上。心想卓云讨男人喜欢女人也不会讨厌,很快就喊卓云姐姐。这段描写,透露出颂莲刚入陈家的单纯和幼稚,也体现了卓云善于伪装的虚伪和老到,为后边的剧情和结局埋下伏笔。当颂莲无心说出让梅珊找那个医生陪着看戏时,对梅珊的描写更是精细:“梅珊愣了一下,她的脸立刻挂下来了。梅珊抓起裘皮大衣和围脖起身,她逼近颂莲朝她盯了一眼,一扬手把颂莲嘴里衔着的香烟打在地上,又用脚碾了一下”。表现出梅珊的惊愕、恐惧和仇视。这里“愣”“挂”“抓”“起”“逼近”“盯”“扬手”“打”“碾”,对一个女人一系列动作描写得如此准确,心理反应把握得如此精细,对于一个男性作家来说确实令人惊异。
五、结语
苏童是个善于写女性的作家。他说过,“我喜欢以女性形象结构小说,比如《妻妾成群》中的颂莲,比如《红粉》中的小萼,也许这是因为女性更令人关注,也许我觉得女性身上凝聚着更多的小说因素。”[9]苏童塑造女性,努力摆脱性别视角,客观地展示女性真实的内心世界,从人性的角度写女性的欲望、命运、弱点与生存困境。他的笔墨一触及女性便能生辉,苏童写得最好的最有典型意义的总是女性形象。他与众不同的女性写作在文学史上也有着独特的意义,一方面是对20世纪主流文学中女性形象的颠覆,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一是对传统意识形态的疏离,二是对社会进步历史观的颠覆,三是对传统历史叙事话语的消解,四是对主流文学叙事模式的解构。另一方面是对欧洲19世纪后半叶出现的风靡全世界的唯美—颓废主义文学思潮叙事传统的继承,打通了唯美—颓废主义曲折而漫长的道路,在西方—东方、现代—古典之间发现了小说的可能,给当代小说带来了拓展表现力的叙述空间和话语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