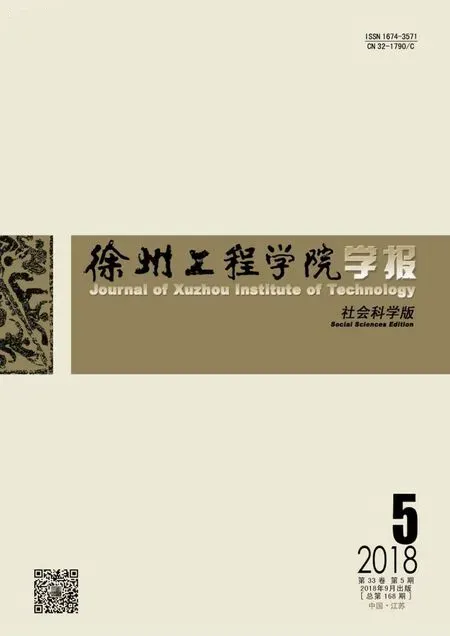传家宝: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体系”例要
彭兆荣
(1.四川美术学院 艺术遗产研究中心,重庆 401331;2.厦门大学 人类学研究所,福建 厦门 361005)
“体系”词与物
我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必然有自己的体系,否则,中华文化便无体系可言。因为,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文化最具表现力和说服力的遗存和遗续。我国传统的遗产存续和继承有自己的一套方式,其中本文论及的礼制与宗法是两个重要的基石。
那么,何为体系?中国式的解答可以这样:以体为本,以人维系。二者正好在汉字“体”(以人为本)中圆满地“系”之。《说文解字》:“体,总十二属也。从骨,豊声。”指总括人身十二(所有)部分,强调主干,即“骨”支撑的身体的全部。
其实,我们今日时常将“以人为本”挂在嘴边,所云者并非中华民族传统所属者,却是西方舶来之物,特别是自文化复兴之后,对现代西方思想界产生重要影响的“人本”概念。这是需要我们进行认真反思的。换言之,我们现在所说的“以人为本”并不是自己文化土壤中生产出来的果实。
以西方的角度,“体系”首先存在于所谓的“本体论”,指对存在的认识理论。每一种学科的哲学既包含某种认识论又包含某种本体论——一个限定着“我们能认识什么”和“我们怎样才能最终认识它”的框架。它们一起被用于限定某种方法论,一套将如何在学科内进行规则和程序,即如何才能信息收集并组织的方法[1]。从哲学角度说,“体系”既是一个时间和空间的概念,又是一个关涉认识论、本体论和方法论的结构性组织。任何一个文化体系也都包含着独特的价值存在、认知方式和表述方式,因而需确立独特的方法论。
福科在《知识考古学》(L' Archéologie du Savoir)中以“知识考古学”的方法论对既往的文明体系和文化结构进行表述:
过去一向作为研究对象的线性连续已被一种在深层上脱离连续的手法所取代……我们可以看到另外一种几乎静止的历史——缓坡历史,诸如航道史、麦子或金矿史、旱灾和灌溉史、轮作史、人类的饥荒与繁育的平衡史……应该建立何种类型的体系?[2]1-2
福科采用了“知识考古学”予以回答。如果说,知识考古学在宽泛的意义上属于方法论的话,那么,“词与物”则更加具体地从构造要素逐一进行驳离,接近于分析的方法。福科对《词与物》的写作动机及缘起作如是说:
博尔赫斯(Borges)作品的一段落,是本书的诞生地……这个段落引用了“中国某部百科全书”,在这个令人惊奇的分类中我们突然间理解的东西,通过寓言向我们表明为另一种思想具有异乎寻常的魅力的东西,就是我们自己的思想限度……而且还有促使词(les mots)与物(les choses)“结成一体”,……一个“要素体系”。[3]
福科在两部重要的著述中的开篇都使用了“体系”的概念,意思却并不一样:前者指历史上的一系列自然史事件在表面上似乎并无明确的关联,是分割和断裂的,实际上却具有整体的意义,需要通过知识考古学以建立其类型的体系。后者则对“中国某部百科全书”的分类与西方人惯习性之间的巨大差异,这种差异导致了不同文化上的差异。而无论在什么历史语境下,“体系”所赋予的意义都具有相应的一致性,仿佛语词与语法之间的关系。便捷的方式就是采用“词与物”的知识考古方式,确立“语法”的结构意义。
无论对“体系”做何解释,都与认知、经验和表述相关联,即所谓的“知识体系”。对知识体系的探索以求得对不同文化体系的认识无疑是一个重要途径。这也是历史上欧洲传教士在通过他们的眼光观察中国,通过他们的知识理解中国,通过他们的文化观照中国,通过他们的经验分析中国。17世纪耶稣会传教士柏应理(Philippe Couplet)所编的《中国哲学家孔子》(Confucius Sinarum Philosophus)于1687年在巴黎出版。以柏氏为代表的欧洲传教士认识到,他们所面对的中国思想自身存在着一个与西方完全不同的知识体系,即所谓的“中国知识”(Sinensis Scientia)*后来,殷铎泽也把《中庸》译成拉丁文,书的标题为《中国政治伦理知识》。见[法]梅谦立《欧洲传教士文献里的中国》,载复旦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章培恒先生学术基金编《域外文献里的中国》,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4年版,第188页。。他想暗示:中国思想体系完全能够回应“欧洲知识”(Europea Scientia),进而希望搭建两个体系之间的思想桥梁[4]。以知识体系为理解不同文明的路径显然是一个重要而有效的角度。
即使以“体系”论,将system译为“体系”和“系统”也需辨析,其中除了不同的学科各自有“体系”外,表述上也各自言表,有时甚至人言言殊。人类学对“体系”的表述因分支、对象不同而有异同。兹列举几例:
人类学有关系统的概念(包括技术)有不少,如水利系统(hydraulic system),分类学(systematics主要研究生物体种类型及相互关系),三期系统(Three Age System,即把史前史分为三个连续的时代:石器时代,青铜时代,铁器时代等,此外还有一些世界民族志中的特殊性系统和模式。[5]
文化结构中各部分之间是相对稳固的关系。美国人类学家克鲁伯和克拉克洪认为,文化的结构不是由文化中各部分或各种文化元素简单相加而成,而是在结构中各部分之间相对稳定的一种关系的作用下构成的[6]。
人类学的结构主义被认为是一种具有美学分析风格的、哲学特性的、表现力最为充分的一种方法。奠基者当属法国的结构主义人类学家列维-斯特劳斯,其结构主义被认为是一种法国式的实践理论。但结构主义作为后来更大发展的一个重要部分表现在二十世纪晚期的现代主义运动之中,它与形式主义中的音乐、戏剧、哲学、文学等有着密切的关联。也与罗兰·巴特尔、阿尔都塞、福科、拉康、德里达、皮亚杰等存在着代际关系。这些人或多或少被称为“结构主义”,也有的被称为“后结构主义”。在人类学界,利奇、尼德汉姆、萨林斯、哈里斯、奴宾等都深受结构主义的影响[7]。此外,以体系分析(systems analysis)见长的体系理论(systems theory),将政治和社会体系作为理想的分析单位,被帕森斯等人引入社会学、政治学。诚如帕森斯所说,社会系统包括四种系统亚系统(subsystems)因素组成,它们是适应性(adaptivity)、目标寻求(goal-seeking)、整合(integration )和潜在因素(latency)。这一体系理论深受生态系统的模式影响[8]。此不赘述。
语境与话语:遗产体系
任何文化的表述都是语境化的,仿佛当下社会风气中的“流行色”。“非物质文化遗产”何妨不是流行色?其中所有入选“名录”者,无论是联合国,还是国家、省、市各级者,皆非当世之创造;所谓“遗产”,即先辈遗留下来的,今天之所以能够入选,实乃符合当下语境,用我们日常的说法就是:符合当今的形势。因为今天流行非遗。就“流行体系”而言,时尚符号化体系并非单一的指标,而是具有不同层面的构造。罗兰·巴特(Roland Barthes)在他的著作《流行体系》(Système de la mode)中对服装做了符号学的分析,他认为,服装作为流行体系中一种特殊的表述方式,包含了三种划分体系,即所谓的“意象服装”“书写服装”和“真实服装”。第一种是以摄影或绘画的形式呈现;第二种是将衣服描述出来,转化为语言;第三种是“存在着一种向其他实体、其他关系转化的过程。因而,真实服装形成了有别于前两种的第三种结构,即使它们视它为原型,或者更确切地说,即使是引导前两种服装信息传送到原型属于这第三种结构。我们已经知道,意象服装单元停留在形式层面上,书写服装单元停留于语词层面上……有了意象服装的形体结构和书写服装的文字结构,真实服装的结构只能是技术性的。”[9]3-4巴特对服装的三种体系划分旨在通过从整体的语言(langue)和具体的言说(parole)之间的关系,以及将语言符号中能指(signifant)与所指(signifiè)的功能差异应用于服装。在他看来,这一切语言学上的结构要素以及所表现出的各种形式都是实现“转换”:“对任何一个特定的物体来说都有三种不同的结构:技术的、肖像的和文字的……它们之间依靠转形(transformé)的作用。”[9]5
“体系”倘若如上所述,属于语境中的“话语”,便不言而喻地羼入了权力的色彩。字面上看,“话语”(discourse)其实就是说话。只是,说话是需要建立在语境范畴的,人们不会无对象,无情境地乱说。于是,话语便被描述为在人与人的互动过程中呈现的具有社会性的叙述。如果将“话语”说成白话,就是在社会交流过程中的讲述。由于社会化的表述具有权力特征,所以,话语常常被用于指示“言说的权力”。根据福柯的研究,话语可以被视为上述语言与言语结合而成的更丰富和复杂的具体社会形态——指与社会权力关系相互缠绕的具体言语方式。既然话语是特定社会语境中人与人之间从事沟通的具体言语行为,也就会有言说者、受话人、文本、沟通、语境等要素组成的结构体系。根据话语的特征,我们当今的“遗产事业”则带有明显的社会运动的特点,都因此染上了话语色彩。
文化遗产之所以在今天受到重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在20世纪70年代以公约的形式开始了世界遗产事业,与其说这是一种文化事业,不如说首先符合政治体系。换言之,遗产学在当今的显露,首先是一门政治学[10]。“体系”的使用在当今哲学政治学中最具影响者之一是沃伦斯坦的“世界体系理论”(The World-System)。他一反已经流行于世的“三个世界”的概念体系,宣称只有一个“世界体系”。它是由经济交换关系建立起来的复杂的网络,即“世界经济体系”(world-economy)——由资本和劳动形成了两分制(dichotomy of capital and labor)。它与无休止的资本积累和竞争联系在一起,并历史性地包括但不限制民族国家的历史作用[8]。这样的世界体系具有范围、结构、成员集团、合理规则和凝聚力。其生命力由冲突和各种力量构成。冲突的力量由于压力的作用把世界体系结合在一起。而当每一个集团不断地试图把它改造成有利于自己的时候,又使这个世界体系产生分裂[11]。事实上,沃伦斯坦世界体系有三种不同形态的历史分析系统,即微系统(mini-system),只有有限的劳动力分工,互惠地组织交换,年龄和性别是社会内主要的区别特征。世界帝国(world-empires)系统中,交换在一个层次上是互惠的(在工匠和食物/原材料生产者之间),在另一个层次上则是再分配,剩余物被军事—官僚统治阶级所享用。最后,在世界经济(world-economies)系统中,生产和交换是通过市场来组织的[1]189。沃伦斯坦试图通过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的建构对当下世界情状进行分析和评述。总体上说,这样的描述是客观的,具有现实性,但带有工具论的明显痕迹。
我国的文化遗产在体系方面有何特色需要我们进行挖掘和总结呢?比如西方学者对我国文化遗产体系的工具性给予特别的观照。在讨论我国的遗产形制方面,似乎更关注我国文化遗产制作和表现方面的体系性。比如在艺术制造与生产方面,德国学者雷德侯的“模件化体系”是一个有创意的概念*德国学者雷德侯将中国艺术的制作和生产,包括汉字体系、商代的青铜器生产制作,古代的墓葬形制,瓷器的生产,活字印刷技术等皆纳入所谓的“模件体系”。参见[德]雷德侯《万物:中国艺术中的模件化和规模化生产》,张总译,北京:三联书店,2005年版。。模件化体系的基本意思就是以使用同样的部件可以创造出各种各样的产品来,以汉字为例,笔画横、竖、点、撇等可以组合成为无数个汉字。如此,中国的文字,即是以五个由简而繁的层面构成的形式系统:
元素(element) 单独的笔画
模件(module) 构件或成分
单元(unit) 单独的汉字
序列(series) 连贯的文本
总集(mass) 所有的汉字[12]14
按照这样的总结,模件体系不仅仅是艺术品的制作、生产和组装,甚至涉及了中国文化的认知性思维。以汉字体系论,“模件即是可以互换的构件,用以在不同的组合中形成书写文字”[12]22。这与字母文字的无象性组合迥异,也反映出中国艺术创造的思维特征和差异。
英国学者杰西卡则从我国古代的艺术表现体系,特别是青铜器的纹饰,提出了“装饰纹样体系”(ornamental system),即“包含着众多组件的整体,而所谓的组件,指可供工匠按照既有的规则去学习、使用和组合的基本元素”。在西方,图案被锻造在青铜器甚至金器上,而在中国古代黄河流域,青铜礼器则是模铸而成的。中国的“装饰纹样体系”中一个重要特性是能够让世代的工匠去学习和遵循。这个特性是决定图案如何被复制的有效途径[13]。
无论在哲学上,认识论上或是不同学科对“体系”的性质规定有什么差异;无论“体系”在定义上、对象上、表述上、译名上有什么差异;无论不同学者发现“体系”在文化遗产中的功能、功效等“工具性”方面有什么差异,都不妨碍“以体为本”“以人系之”这一根本。
传家宝之承:传统的遗产传承系统
上述表明,今日世界之遗产体系有一个背景:即在世界范围内以国家为单位的共同体范畴。这就是说,“民族-国家”作为基本的单位成为遗产的所属和继承者。换言之,世界遗产体系首先建立在当代世界体系之上,只有进入到既定的体系之中,依照其游戏规则,方可以被接受、被表述。比如,如果一个国家想要申报世界遗产,前提是要成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的缔约国,成为世界遗产事业体系中的一员。
而中国传统的遗产存续和继承有自己的一套方式,其中礼制与宗法是两个重要的基石。人们通常称说中国的社会为宗法社会,它与礼制社会结构中的等级制度及其观念,是贯穿整个中国历史的两个大制度及观念,而体现宗法(宗法性)制度与观念的宗族,无疑成为中国历史的极其重要的成分[14]。在乡土社会中,宗族也很自然成为最具影响力的因素,并成为联结具有社会关系结构的、始终的贯穿性特质。
至今学界对于宗族的表述和定义虽未达成共识,主体却基本一致,只是在强调主体的范围和外延方面不同。比如有强调“家”的;有强调宗法的、共识的、首领的血缘共同体;有把宗族分为不同的层次的;有强调姓氏关系和作用的。有的学者认为,宗族的基本要素包括:1.父系血缘系统的人员关系;2.家庭为单位;3.聚族而居或相对稳定的居住区;4.有组织原则、组织机构和领导人进行管理[14]14-17。钱杭在《宗族建构过程中的血缘与世系》一文中,给出一个相对全面的定义:
宗族是一个父系世系集团。它以某一男性先祖作为始祖,以出自这位始祖的父系世系为成员身份的认定原则,所有的男性成员均包含其配偶。虽然在理论上,宗族的基本价值是对世系的延续和维系,但在实践上,其成员的范围则受到明确的限定。[15]

在我国,传家宝作为遗产,首先被认定为财产。“财”在中国传统的认知中主要指实物,《说文解字》释“财,人所宝也。”《康熙字典》择录“财”之多义:“可入用者”,包括食谷、货、赂、资物、贿、地财、土地之物、裁(《尔雅·释言疏》裁、财音义同)、祠(《史记·封禅书》民里社各自财以祠)。“产”即“生”,包括人的生产和万物的生产。这样,一个完整的连接性传承系统便呈现出来:首先,我国的传家宝制度总体上是“家传”方式,如果要上升为“国家”,则至多也是中国古代的“家国”范畴。其次,作为一种传承体系,传家宝的基本背景是宗法社会,宗族是主导力量。再次,传家宝不仅只是传承,还是社会再生产的示范。
国有国体,法有法规,家有家法,文化系之。中国的非物质文化最能反映中国文化面貌,存在着中华民族最为鲜活、最具广泛性、最备地方特色、最有民间风范的文化内容,因此,探索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体系也成为重中之重的事务。我们或许可做的工作,除了配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操作规则外,更要总结中华文化自己的体系。作为中华民族最具代表性、活态性的文化遗续,我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有着自己独特的体系;它不仅具有作为传统文化遗产的结构方式,而且自身也具有独特的价值。笔者的观点是:以体为本,以人系之。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当代性,有着特定时代语境的特性,表现出强烈的话语特征,如何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中,以词与物的“知识考古”,寻找自己的传统与传承方式,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体系,是一件具有历史意义的事情。“传家宝”不啻为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