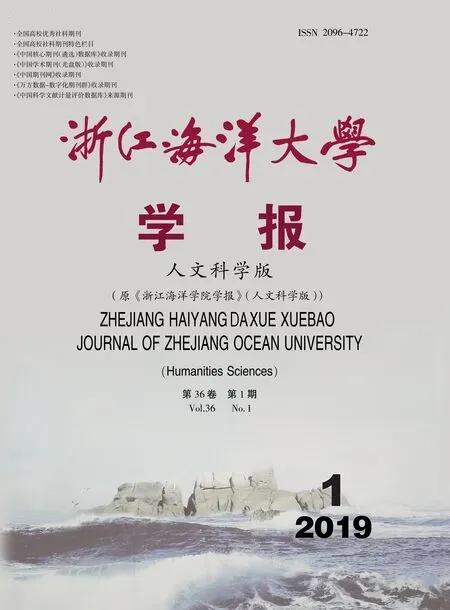船舶污染的司法实践及其立法思考
——以“金玫瑰”轮系列案件为例
李 军
(青岛海事法院,山东 青岛 266061)
2018年1月6日20时许,巴拿马籍油船“桑吉”轮与香港籍散货船“长峰水晶”轮于长江口以东约160海里处发生碰撞事故,导致“桑吉”轮全船失火,并于1月14日被确认已经沉没。“桑吉”轮碰撞沉没溢油污染事件是进入21世纪10年代以来,继“康菲”钻井平台溢油事故后又一起引起公众持续关注的重大海洋溢油污染案件。作为海事审判机关的从业人员,也在积极地思索:当此类案件突发时,海事法官是否能够及时准确应对,做好审判实践工作。若想在大案突至时从容面对,需要平时认真积累相关法律知识,并且积极从已有的司法实践中总结吸取经验。笔者特意梳理了20余宗涉及船舶碰撞后引发污染损害赔偿的系列案件,从中发现“金玫瑰”轮与“金盛”轮碰撞沉没海洋污染系列案件最有代表性,对其处理的审判实践至今仍有较大借鉴意义。通过对该系列案件的详细研究,对照其他同类案件的审理工作,笔者也产生一些相关思考,在此进行总结阐释,以期对审判实践工作以借鉴与启示。
一、“金玫瑰”轮案件的案情
2007年5月12日,圣文森特籍“金盛”轮与韩国籍“金玫瑰”轮遭遇碰撞,碰撞位置属于山东烟台海域,“金玫瑰”轮在附近海域沉没。两船雾中航行时,没有按照《避碰规则》的要求,保持正规瞭望和使用安全航速;发现来船后没有运用适合当时环境和情况的一切有效手段判断会遇局面和碰撞危险;在排除碰撞危险之前没有依据《避碰规则》第8条和第19条的规定运用良好船艺及早地、大幅度地采取转向和减速等避碰行动,任凭两船进入紧迫局面。在进入紧迫局面之后,两船违反《避碰规则》第19条的规定,未及时减速、停车和停船且在未查核避让效果的情况下盲目转向,最终导致碰撞。
对于两船碰撞的发生,“金盛”轮和“金玫瑰”轮均负有责任。其中,“金盛”轮承担55%的碰撞责任,后者对此负45%的责任。本案中“金玫瑰”轮不仅起诉了“金盛”轮的船东,也对该油轮的船舶管理人提起诉讼,但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船舶碰撞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四条规定,法院驳回了对船舶管理人的诉讼请求。
关于人身伤亡损失,两船已自行和解。关于非人身伤亡损失,“金盛”轮请求了修理费与船期损失;“金玫瑰”轮请求了打捞费用与船期损失等。法院分别作出了具体认定。
二、“金玫瑰”轮案件中烟台海事局的诉讼请求
(一)法律依据
本案主要涉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海洋环境保护法》第五条第三款、《防治船舶污染海洋环境管理条例》第四条、第四十一条。海事局作为国家海事行政主管部门,对船舶污染事故不仅应依职权进行调查处理,还应采取必要措施减轻污染损害。自事故发生之日起至2007年6月21日,长达四十余日的清污工作在烟台海事局、烟台碧海公司、北海救助局协作中展开,“金玫瑰”轮油污问题基本得到解决,最大限度地减少了污染损害。对于应急反应作业的相关费用,三家单位共推烟台海事局向法院进行主张。烟台海事局主张:对“金玫瑰”轮船东及保险人请求本次事故发生应急反应费用合计人民币18 491 665元:
(二)索赔项目
关于海洋污染应急反应作业的费用,一直欠缺权威统一的具体标准,烟台碧海公司对于该系列费用制定有《收费标准》,并已在烟台市物价局进行了备案,因此使得相关诉讼请求在法院较为顺利地获得大部分支持。今天看起来,相关的收费项目与标准仍有较强的参考意义。烟台海事局请求的具体项目包括如下9项:(1)船舶费:682 410元;(2)清污设备和器材费:5 512 862元;(3)清污人员费:1 797 435元;(4)车辆费:181 000元;(5)预测分析费:108 460元;(6)废弃物处理费:30 000元;(7)杂费:164 000元;(8)管理费;(9)海事管理费。
(三)法院对9项请求项目的认定
青岛海事法院认定,“金玫瑰”轮承担45%的碰撞责任,“金盛”轮负责55%的碰撞责任,均可以享受责任限制。
烟台海事局要求“金玫瑰”轮的互保协会对所诉损失承担连带责任,于法无据,法院不予支持。
实际发生的费用14 617 917元(烟台海事局请求项目第1至7项),相关证据充分,标准明确,数额准确,法院予以认定。
由于清污行动的民事法律属性,烟台海事局、烟台碧海公司、北海救助局,可依据或参照烟台碧海公司的《收费标准》收取合理费用,烟台海事局主张占15%的实际费用的即2192688元的管理费的请求(烟台海事局请求项目第8项)合理,法院予以支持。
因烟台海事局在清污行动中并非作为行政管理主体参与其中,而其也主张所采取的清污行为为民事行为,故原告主张就本次行动收取实际发生总费用的10%的海事管理费(烟台海事局请求项目第9项),于法无据,法院不予支持。
“金玫瑰”轮的船舶所有人应当承担本次溢油污染事故所造成的溢油应急反应费用中 16 810 605元的45%即人民币7 564 772.25元的赔偿责任。
“金盛”轮的船舶所有人应当承担本次溢油污染事故所造成的溢油应急反应费用中55%即人民币9 245 832.75元的赔偿责任。
(四)法院对烟台海事局的债权是否应当在基金中优先受偿的认定
烟台海事局清污债权应当在海事赔偿责任限制基金中优先受偿,其提出的法律依据是《防治船舶污染海洋环境管理条例》第五十五条。法院认定:依据《海事诉讼特别程序法》第一百一十八条第三款,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以及其他有关法律以确定海事赔偿责任限制基金分配方案中烟台海事局如何受偿。《海商法》第二百一十条第一款第(四)项的规定,并未规定海事局面临应急处置、清除污染所支付的必要费用能否优先受偿;而《海事诉讼特别程序法》规定的“其他有关法律”并不包括行政法规,无法适用《防治船舶污染海洋环境管理条例》的规定;且海事局没有提供其他可以优先受偿的法律依据,据此,烟台海事局所持的其债权在基金中优先受偿的诉讼请求没有充分的法律依据,法院不予支持。
(五)烟台海事局案件最终判项
确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烟台海事局对“金玫瑰”轮船舶所有人延成海运公司的债权为人民币7 564 772.25元;对金盛船务有限公司的债权为人民币9 245 832.75元,自2008年2月29日起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的利息;分别依法自延成海运公司和日本船主责任相互保险协会设立的“金玫瑰”轮责任限制基金、“金盛”轮海事赔偿责任限制基金中分配。
三、“金玫瑰”轮案件中山东省海洋与渔业厅的诉讼请求
(一)法律依据
2002年“塔斯曼海”案件中,国家海洋局授权天津市海洋局提起海洋生态损失索赔,天津市渔政渔港监督管理处代表国家提起渔业资源损失索赔,这树立了中国海洋生态环境污染损害司法索赔的先例。此后,国家海洋行政主管部门越来越多地走向前台,进行海洋生态司法维权。在“金玫瑰”轮系列案件中,山东省海洋渔业厅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海洋环境保护法》第五条第二款,同时肩负了海洋生态损害与渔业资源损失两项索赔。
(二)索赔项目
2007年5月20日,国家海洋局北海环境监测中心、农业部黄渤海区渔业生态环境监测中心经山东省海洋与渔业厅所托,对此次碰撞溢油事故引发的海洋生态损害与渔业资源损失进行评估。
同年6月15日,山东省海洋与渔业厅经国渔资环便[2007]41号《关于对金玫瑰轮燃油泄漏污染事故进行调查处理的函》确认,对具体事故缘由等事项进行调查处理。
同年12月,两部门共同出具了《韩国“金玫瑰”轮溢油海洋生态损害和天然渔业资源损失评估报告书》。
该报告书认为: “此次溢油事故对海洋生态和渔业资源造成的损失费用合计1 620.4844万元。其中对海洋生态造成的损害898.1644万元,对天然渔业资源造成的损害722.32万元。”
(三)法院认定
《韩国“金玫瑰”轮溢油海洋生态损害和天然渔业资源损失评估报告书》主要依据是2007年国家海洋局北海环境监测中心编制的《海洋溢油生态损害评估技术导则》(HY/T095-2007),该导则的法律地位为海洋行业标准,因此是否可以采用成为争议的焦点。青岛海事法院最终完全采纳了根据该标准作出的报告书的结论。即该起事故造成的损失共计人民币1 620.4844万元。
“金玫瑰”轮的船舶所有人应当承担海洋生态与渔业资源损失总额45%的责任,即人民币7 292 179.8元。“金盛”轮的船舶所有人承担损失总额55%的责任,即赔偿原告人民币 8 912 664.2元弥补海洋生态和渔业资源损失。
(四)山东省海洋与渔业厅案件最终判项
确认原告山东省海洋与渔业厅对被告延成海运公司债权为人民币7 292 179.8元,自2010年5月28日起以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利息;该限制性债权依法自被告延成海运公司和被告日本船主责任相互保险协会设立的海事赔偿责任限制基金中分配。
金盛船务有限公司以其责任限制基金支付于省海洋与渔业厅赔偿款人民币8 912 664.2元,赔偿款以该公司所享有的责任限制而确定的省海洋与渔业厅应获数额为限
四、“金玫瑰”轮案件中韩国现代海上火灾保险有限公司的请求事项
(一)案件事实认定
“金玫瑰”轮船舶所有人延成海运公司的代理签发了延成海运公司为承运人的、编号为270269的清洁提单,提单载明货物品名数量为23卷热轧钢卷,净重为630.200公吨,运费预付。涉案货物经检验应作全损处理,四票损失总额为CFR韩国唐津港3 128 494.41美元;因该损失为CFR价格损失,运费已包含在内;涉案货物的保险费为5102.61美元。涉案货物损失计算为3 133 597.02美元。“金盛”轮的船东应承担55%的涉案货物损害赔偿责任,即依法应当赔偿货物损失1 723 478.36美元,“金玫瑰”轮以45%的碰撞责任担责。
(二)韩国现代海上火灾保险有限公司案件最终判项
确认原告现代海上火灾保险有限公司对金盛船务有限公司的债权为1 723 478.36美元,加自2007年6月20日起以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的利息。该限制性债权应自“金盛”轮海事赔偿责任限制基金中分配。
五、“金玫瑰”轮案件中基金的最终分配
(一)“金玫瑰”轮债权人会议分配方案
“金玫瑰”轮可分配基金总额9 274 496.46元,登记债权人包括金盛船务有限公司、山东省海洋与渔业厅、烟台海事局。山东省海洋与渔业厅债权比例46.36%,受偿约430万;烟台海事局53.64%,受偿约497万。
(二)“金盛”轮债权人会议分配方案
“金盛”轮可分配基金总额13 118 112.32元,登记债权人包括延成海运公司、山东省海洋与渔业厅、烟台海事局、现代海上火灾保险有限公司。延成海运公司债权比例20.57%,受偿约270万;山东省海洋与渔业厅18.68%,受偿约245万;烟台海事局24.475%,受偿约320万;现代海上火灾保险有限公司36.275%,受偿约476万。
六、“金玫瑰”的司法难题及其立法完善
(一)本案不同索赔主体参加诉讼的依据
1.《海商法》中的法律规定。(1)有关船舶碰撞的第一百六十九条中碰撞造成第三人财产损失的相应索赔权;(2)有关海难救助的第一百八十二条中救助方关于救助报酬、特别补偿的请求权;(3)有关海上运输合同的第五十一条和五十四条中承运人对货损的赔偿责任;(4)有关海上保险合同的第二百五十二条中保险人的代位求偿权。由上述法律规定可见,对于船舶海上油污索赔,《海商法》并未单独专章专条专项进行规定。对此类损害赔偿,可以通过不同的法律关系,经由“第三人”相关的财产损失这一宽泛的途径介入并进行主张;也可以经由具有环境保护性质的海难救助特别补偿途径获得另行增加的补偿。根据《海商法》的现有体系已有的条文,尚不影响当事人纷纷加入索赔,但并没有体现针对船舶油污损害的特殊责任,也没有对减少环境污染的清污行动进行足够的特别保护。甚至在第一百八十二条中还是以“取得防止或者减少环境污染损害效果”作为取得特别补偿的前提,这还是没有脱离海上救助“无效果无报酬”的基本原则,并不利于防污作业的开展。随着海洋环境保护重要性的凸显,以及与国际立法接轨的现实需要,对船舶海上油污索赔进行专章立法越来越重要对海上防污进行更多倾斜性保护和支持也势在必行。
2.《海洋环境保护法》中的法律规定。《海洋环境保护法》第五条规定了国务院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国家海洋行政主管部门、国家海事行政主管部门、国家渔业行政主管部门、军队环境保护部门五类国家机关的海洋环保职责,并且进行了细致的分工。但从第八十九条来看,仅仅授予了“行使海洋环境监督管理权的部门”代表国家的索赔权,该部门应为上述国家海洋环境主管部门。《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对于国家海洋局的该项职能进行了调整。具体为:“(二十五)组建生态环境部。将环境保护部的职责,……国家海洋局的海洋环境保护职责,……整合,组建生态环境部,作为国务院组成部门。主要职责是,拟订并组织实施生态环境政策、规划和标准,统一负责生态环境监测和执法工作,监督管理污染防治、核与辐射安全,组织开展中央环境保护督察等。不再保留环境保护部。”目前看来,《海洋环境保护法》的修改已势在必行。原先地方海洋与渔业厅(局)同时向法院主张海洋生态损害与渔业资源损失索赔可能将成为历史,生态环境部与农业部下属的国家渔业行政机关如何协调进行海洋生态环境索赔,需要法律予以规范。
(二)新的诉讼主体加入海洋污染索赔的依据
在“金玫瑰”轮系列案件之后,青岛海事法院审理的“畅通”轮、“华顺88”轮等海洋污染损害案件中,又有新的诉讼主体成功地加入诉讼程序,作为索赔主体进行诉讼。其中最典型的是养殖户和船舶污染清除单位。
1.《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域使用管理法》中的法律规定
《物权法》第四十六条规定:“矿藏、水流、海域属于国家所有。”《海域使用管理法》规定:“国务院代表国家行使海域所有权;单位和个人使用海域,必须依法取得海域使用权。”《海域使用管理法》一方面强调了海域所有权属于国家,另一方面规定了海域使用权的取得和丧失途径。随着越来越多的集体和个人积极参与海洋的开发和利用,在发生船舶油污损害时,养殖户等用海主体也积极主动地参与到索赔中来,例如青岛海事法院审理的“畅通”轮海上污染系列案件中,多家养殖集体与个人提出索赔请求并成功获偿。
对于养殖户参与海上污染索赔,需要注意的重点为:1.养殖的合法性问题。2.是否与海洋行政主管机关的索赔存在重合与冲突。《海域使用管理法》第二十五条规定海域使用权最高期限,其中养殖用海十五年。《海域使用管理法》颁布于2001年,据该法取得的证书已经会产生超出15年的超期证书,这正逐步成为现实存在的问题。对于超期证书,是否可以接受颁证机关的相关说明认定其继续有效,还是严格按照法律根据证书表面显示的有效期来进行认定?笔者认为,应该考察超期原因是由于持证人造成还是颁证机关造成,如系后者原因,可适当放宽;如系前者问题,即使有颁证机关认可,也不应认可其有效性,否则会动摇相应的行政管理制度,也会影响中国法院和行政机关在国际上的公信力。另外,假如计算海洋环境修复期超出了海域使用权证期限,索赔主体如何确定?笔者认为,法院在审查养殖户证书和《评估报告》后,如发现上述问题,不宜直接驳回养殖户相应的超期诉讼请求,而应通知发证机关代表国家参加诉讼。
2.交通行政法规
(1)《中华人民共和国船舶污染海洋环境应急防备和应急处置管理规定》应缓行。该管理规定新设了“船舶污染清除单位”这一概念,第十三条规定:“船舶污染清除单位是指具备相应污染清除能力,为船舶提供污染事故应急防备和应急处置服务的单位。”第十四条、第十五条规定了从事船舶污染清除的单位应当具备法定条件的应急清污能力,能制定污染清除作业方案、污染物处理方案,受海事管理机构的监督检查,并应将有关报告、方案报海事管理机构。第二十条规定该单位应按国家海事管理机构公布的协议样本签订船舶污染清除协议。由上述应急管理规定的具体条文可见,船舶污染清除单位是船舶污染清除协议的签订主体,并且此类单位并非国家海事行政机关本身。这标志着国家在船舶污染清除领域由国家行政机关为主转为社会民事主体为主,这与“金玫瑰”轮系列案件完全由海事局包办完全不同。
此类模式也面临新的问题。从法律层面来说,第一,海事管理行政机关退居后台,但是船舶污染清除协议的权威样本尚未问世;即使推出合同样本,推广和应用过程中也会有后续问题争端不断涌现;第二,船舶污染清除的收费标准尚无依据,遇到船舶污染应急情况,怎么有时间再讨价还价?第三,海事管理行政机关目前仍必须在船舶污染清除协议中担任至少类似于联络、中介的角色,但这些工作并不采用任何书面行政文书进行规范,如船方和清污单位在清污合同履行中出现问题,行政机关如何能置身事外?第四,在出现多家船舶清污单位同时进行作业时,如何协调分工?如果指定某家清污单位担任总指挥,与船方签订总的清污合同,在进行款项交接后出现费用分配问题,海事局能否轻易摆脱?从经济层面来说,将船舶清污作业市场化,发展趋势是正确的,但要看到船舶清污工作投入成本较大,偶然发生的清污作业收费能否支持船舶日常维护的支出?在多数船舶污染案件都可以申请海事赔偿责任限制基金的情况下,包括清污单位在内的债权人只能按比例受偿,这就存在入不敷出的风险。长此以往,如何能保证在出现突发油污事件时,海事管理行政机关能够迅速召集社会海上清污企业积极参与?
有鉴于此,笔者建议,首先,应加快制定海上清污合同标准格式,并积极进行试点推广;其次,应推出与国际接轨的清污收费标准,收费标准过低难以吸引社会力量投入清污行业;最后,应设定一定的过渡期,在过渡期内仍由海事局主导清污作业,再逐步向社会企业移交清污重任。
(2)《防治海洋工程建设项目污染损害海洋环境管理条例》亟待修正。《防治海洋工程建设项目污染损害海洋环境管理条例》第二十六条将其调整的“固定式平台和移动式平台”定义为“海洋油气矿产资源勘探开发作业中所使用的钻井船、钻井平台、采油平台和其他平台”。在第三十九条中,对海洋工程造成海洋环境污染事故,规定了两层报告制度,并将消除污染的责任归为规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和有关主管部门。
第一,作为规范海洋工程的条例,在第二十六条中出现了“钻井船”,钻井船既然被称作船,应该具有船的属性,其在海上航行,对应的管理机关应为海事行政管理机关,而海洋工程建设项目的管理机关应为海洋行政管理机关。第二,随着科技的发展,越来越多的钻井平台具备了自身动力,例如我国建造的全球最先进的超深水钻井平台——“蓝鲸1号”,自投入使用以来,总航程近2263公里,航行7.1天,航速之快达8.27节。[1]钻井平台已经逐步脱离了被拖带航行的笨重面貌,越来越具有船舶属性。第三,钻井平台的属性在法律定义上也存在冲突。我国于1983年7月1日加入了《国际防止船舶造成污染公约及其议定书》,该公约规范的“船舶”系指在海洋环境中固定的或浮动运行的各种类型的船舶,包括水翼船、气垫船、潜水船、浮动船艇和固定的或浮动的工作平台。根据该定义,“船舶”完全包含了上述条例第二十六条第三款当中的“固定式平台和移动式平台”。第四,越来越多的钻井平台开始进行船舶登记。例如:2018年4月4日,中海油田服务股份有限公司的“海洋石油982”钻井平台获湛江海事局签发的船舶所有权证书和国籍证书。[2]第五,如果钻井平台发生污染事故,根据《防治海洋工程建设项目污染损害海洋环境管理条例》应由沿海地方政府为主进行分工防制,而根据《船舶污染海洋环境应急防备和应急处置管理规定》行政机关是居于幕后的,而船舶污染清除单位本身应为清污的主要力量,出现事故后如何进行协调?清污是否还需要现场签约?第六,在有可能出现的钻井平台溢油污染诉讼中,如何选择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环境侵权责任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船舶油污损害赔偿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这两个司法解释在举证责任、赔偿范围等方面规定仍存在差异,而后者对船舶的定义为“非用于军事或者政府公务的海船和其他海上移动式装置,包括航行于国际航线和国内航线的油轮和非油轮”,钻井平台是否包括在海上移动式装置中,还需要更加明确的解释。
《中华人民共和国船舶污染海洋环境应急防备和应急处置管理规定》的制定单位为交通运输部,《防治海洋工程建设项目污染损害海洋环境管理条例》的制定单位是国务院,前者制定时间较晚,新法优于后法还是国务院法规效力大于部门规章?《国际防止船舶造成污染公约及其议定书》系我国已加入的国际公约,我国在将有关国际公约转化为国内法时的做法是采用国际公约的法律效力高于本国立法的法律适用办法。上述存在矛盾的条文,在行政执法和司法实践中,确实存在引发混乱的风险,希望能够进行统一。
(三)两船碰撞后造成污染是承担连带责任还是漏油方单方责任问题
“金玫瑰”轮系列案件以及青岛海事法院审理的船舶碰撞导致溢油污染案件,均为权利人同时分别起诉碰撞双方。碰撞双方中,往往产生溢油的一方是承担次要责任的、吨位较小的、碰撞受损较重甚至沉没的船舶。而设立基金的多数是碰撞双方均分别设立。单方设立基金的情况也是由碰撞受损较轻、未发生溢油船舶的所有人设立。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船舶油污损害赔偿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施行后,该规定的出台对上述纠纷处理原则产生了冲击和争论。笔者认为,对该规定特别是第三、第四条需要较为谨慎地理解和执行。
1.该规定第三条规定:“两艘或者两艘以上船舶泄漏油类造成油污损害,受损害人请求各泄漏油船舶所有人承担赔偿责任,按照泄漏油数量及泄漏油类对环境的危害性等因素能够合理分开各自造成的损害,由各泄漏油船舶所有人分别承担责任;不能合理分开各自造成的损害,各泄漏油船舶所有人承担连带责任。但泄漏油船舶所有人依法免予承担责任的除外。”该条的前半部分仍沿用了各自造成损害分别承担责任的原则,但设置了“能够合理分开”这一前提;而后半句出现了各泄漏油船舶所有人承担连带责任的规定。但笔者认为,连带责任并不应被视为是经常普遍适用的原则。该条款应认为是更强调对于溢油来源的追溯与追责的重视。在嫌疑肇事船范围明确的情况下,可以通过提取嫌疑船所载燃油,对照污染海域提取的油样,通过油指纹比对技术进行对比分析,并根据卫星定位、追踪等技术确定污染的范围,大多数情况下,各自造成的损害“能够合理分开的”,即应该分别承担责任;对于“不能合理分开”承担连带责任的情况,限于笔者知识范围及想象能力所及,应该是两船泄漏油类在海上发生混合,且污染范围重合。
《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第一百零四条规定:“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作出的属于审判、检察工作中具体应用法律的解释,应当主要针对具体的法律条文,并符合立法的目的、原则和原意。” 该司法解释制定的规则原则应有可以针对的具体法律条文,而不能自创归责原则。笔者认为,该条款应根据对应的法律条文进行限制性解释。首先,该条文应符合《侵权责任法》第八章环境污染责任中第六十七条的规定,即“两个以上污染者污染环境,污染者承担责任的大小,根据污染物的种类、排放量等因素确定。”其次,该条文第一句前后两部分的不同归责原则还可以在《侵权责任法》更基本的归责原则中找到依据,即第二章“责任构成和责任方式”第十条确定的原则,“二人以上实施危及他人人身、财产安全的行为,其中一人或者数人的行为造成他人损害,能够确定具体侵权人的,由侵权人承担责任;不能确定具体侵权人的,行为人承担连带责任”。
2.该规定第四条规定:“船舶互有过失碰撞引起油类泄漏造成油污损害的,受损害人可以请求泄漏油船舶所有人承担全部赔偿责任。”但对该条文的理解不能脱离既有法律。根据《立法法》第一百零四条的原则,第四条规定针对的具体法律条文是《海商法》第一百六十九条。因此,对第四条的正确理解,必须在不违反《海商法》的基础上进行。按照《海商法》第一百六十九条,船舶互有过失碰撞,各船按照过失程度的比例负赔偿责任或者平均负赔偿责任。既然是互有过失,就不可能存在一方全责的情况,也就是说不可能出现单方承担全部责任的情况。《海商法》第一百六十九条已明确“碰撞造成第三人财产损失的,各船的赔偿责任均不超过其应当承担的比例”。因此即使司法解释第四条规定“受损害人可以请求泄漏油船舶所有人承担全部赔偿责任”,也只能是受损害人单方的一面之词。如果泄漏油船舶所有人自愿履行就皆大欢喜;但如果向法院作为诉讼请求提出,则该请求的权利只能停留在“请求权”阶段,不能获得法院的支持。与该司法解释第四条异曲同工的条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海上交通安全法》第四十条,该条也仅将主管机关强制打捞清除沉船等的费用承担者限于沉船一方的所有人、经营人。
倘若根据第四条和《海上交通安全法》第四十条这两个条款的这两个条文的精神修改《海商法》,在执行时面对的现实问题就是:漏油船、沉没船往往是碰撞事故的弱势一方、受损严重一方、清偿能力较弱一方,甚至支付清污费、打捞费都捉襟见肘,而碰撞另外一方却没有条款可以追究责任。
(四)被忽视的“非限制性债权”
依据《海商法》第二百零七条,船舶碰撞导致燃油泄漏基本都符合限制性债权的条件,但是在“金玫瑰”轮系列案件及青岛海事法院此后审理的类案中,还涉及到沉船打捞、防污救助等非限制性债权的问题。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海事赔偿责任限制相关纠纷案件的若干规定》第十七条,打捞为非限制性债权;根据《海商法》第二百零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船舶油污损害赔偿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一条,救助也为非限制性债权。在船舶碰撞油污损害中,救助与防污的双重目的常常难以区分主次,打捞沉船同时也要防止扩大污染或产生新的污染,因此在此类案件中,非限制性债权是客观存在不应忽视的。然而,我国现有的法律在设计的时候,过于注重突出船舶责任的限制性,忽略了非限制性债权的存在。
1.“任何人”团灭一切
《海商法》第二百一十四条规定:“责任人设立责任限制基金后,向责任人提出请求的任何人,不得对责任人的任何财产行使任何权利;已设立责任限制基金的责任人的船舶或者其他财产已经被扣押,或者基金设立人已经提交抵押物的,法院应当及时下令释放或者责令退还。”该条的问题在于过分突出责任限制基金的设立效果,在立法概念的外延上未加适当限制,因而不当地采用“任何人”这样的表述排除了非限制性债权人的权利,甚至还排除了与责任人有关的其他并非因为事故产生的普通债权人的权利,例如船员工资、船舶抵押贷款等等。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海事赔偿责任限制相关纠纷案件的若干规定》对规定在一定程度上修复了该条文的不良影响。根据该规定第八条,海事赔偿责任限制基金设立后,海事请求人基于责任人依法不能援引海事赔偿责任限制抗辩的海事赔偿请求,仍可以对责任人的财产申请保全。
2.不登记不应以为放弃债权
《海事诉讼特别程序法》第一百一十二条将债权限制为“与特定场合发生的海事事故有关的债权”,这样排除了与船舶相关的普通债权,这在立法技术上已经比《海商法》中的“任何人”有了进步,但仍然存在未充分考虑到非限制性债权的问题。该条规定:“公告期间届满不登记的,视为放弃债权。”实际上迫使非限制性债权人也必须进行基金的债权登记。
实践中,不论是否是非限制性债权,各种与事故相关的债权人均会积极参加登记并分配。即使是非限制性债权人,也很少在设立基金后采取扣押船舶和其他财产等手段。笔者认为,首先,就是《海商法》和《海事诉讼特别程序法》这些未加充分考虑的条文客观上对司法实践起到了影响作用,当事人及其委托代理人(即便是海事专业律师)都积极遵守现行法律制定的规则;其次就是此类案件多为涉外案件,在不能扣押船舶的情况下,除基金外境外当事人可执行的财产难以取得。笔者强烈建议,对《海商法》进行修改时,应考虑到文义上存在的问题,使用更严谨的立法语言进行规范。
(五)船舶溢油损害公益诉讼问题
1.公益诉讼的法律依据。目前被广泛引用作为介入海洋环境方面对于公益诉讼的规定主要源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第五十八条。需要注意的是,“金玫瑰”轮等系列案件中海事局、海洋与渔业局作为原告请求防污费用、海洋油污损害赔偿是依法履职后代表国家进行的民事诉讼,而目前提起公益诉讼并具有原告资格的只有检察院。
2.《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检察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规定,提起检察公益诉讼的途径有两个,分别是民事公益诉讼和行政公益诉讼,相应的程序规定简述就是民事的需要办理公告,行政的需要进行检察建议,主要涉及第十三条和第二十一条。
3.检察机关在非海事法院实现的海洋环境公益诉讼突破
根据笔者所了解的情况,青岛海事法院尚未审理过检察机关作为原告提起的海洋环境公益诉讼,已经公开宣传推广的全国及全省海洋生态环境公益维权的第一案,在程序上都存在瑕疵。
(1)全国海洋生态环境公益维权的第一案
中国海警局2017年1号督办案件。2018年3月22日,灌南县人民检察院经批复向该县人民法院提起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以被告在禁渔期及禁渔区以禁止方式非法捕捞水产品提起诉讼,根据有关水产资源法规请求以非法捕捞水产品罪追究被告(荣成伟伯渔业有限公司和被告人何延青、王文波等18人)的刑事责任。并请求判令被告以可行性方式,修复海洋环境或赔偿环境修复费用1.3亿余元及损害调查、评估费用,并公开道歉。[3]
(2)山东海洋环境公益诉讼第一案
2018年4月12日,山东招远检察院在巡查工作中认为在招远市伟龙渔业有限公司擅自建造小码头一案招远市海洋与渔业局存在不完全履职行为。2018年6月21日,烟台市人民检察院在组织专业人员进行涉案海域勘查中,发现伟龙渔业有限公司违法以石料填海搭建构筑物即非透水式构筑物,在辛庄镇海埠村以北海域违建钳形临时停船码头。其后,招远市检察院成立了专项活动工作领导小组,抽调出庭经验丰富的检察官,购置相关技术设备,通过无人机航拍优势以高空视角及动态且广阔的拍摄面加之细节捕捉涉案海域受侵害之现状。
山东招远检察院委托烟台市检察院对烟台市海洋与渔业局发出调查函,查明了该局的未依法履职情形即未向上级提报相关说明材料或申请移交查处。经上级检察院批准,山东招远检察院以招远市海洋与渔业局为被告,为督促被告依法全面履行职责保护公共利益,提起行政公益诉讼,请求判令被告履行法定监管职责,对上述伟龙渔业有限公司的违法行为依法进行行政处罚。8月6日,该案作为山东省首例海洋环境资源领域行政公益诉讼案件公开宣判,判决被告履行职责即在该判决生效后三十日内对招远市伟龙渔业有限公司在招远市辛庄镇海埠村以北未经批准实施填海施工建设码头的行为,依法作出行政处罚。[4]
从上述两个案例来看,均存在不同程度的程序问题。1.两个案件中检察机关均应起诉至海事法院,属地管辖分别归属上海海事法院和青岛海事法院;2.全国首例公益案件系民事公益诉讼,但检察机关没有进行公告即提起公诉,而且检察机关应该了解相应的职权应属于当地海洋与渔业局,当地海洋与渔业局是《海洋环境保护法》确定的民事索赔主体;3.全省首例公益诉讼案件系行政公益诉讼,但检察机关未提出检察建议,并且检察机关已经明知对应的行政机关应为当地县级海洋与渔业局;4.上述两个案件均是在两高司法解释开始施行后提起的公诉,作为程序性法律,应该自施行后立即产生效力。遗憾的是,两地的法院和检察院都选择忽视了两高司法解释的明文程序规定。希望随着两高司法解释的全面深入推行,可以看到更多更加规范的案例出现。
4.社会组织进行海洋环境保护公益诉讼没有法律依据,第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海洋环境保护法》第八十九条有明文规定:“对破坏海洋生态、海洋水产资源、海洋保护区,给国家造成重大损失的,由依照本法规定行使海洋环境监督管理权的部门代表国家对责任者提出损害赔偿要求”。据此,海洋环境污染的民事索赔权仅限于特定国家机关。第二,《环境保护法》最新修订时间为2014年4月24日,《海洋环境保护法》在此后三年多才完成修订(2017年11月4日),但没有引入《环境保护法》第五十八条类似的公益诉讼条款。第三,从实践上看,社会组织提出的诉讼请求缺少法律依据。例如,某社会组织的诉讼请求为因某海上溢油事件,要求污染方在三个月内制定并实施科学的生态修复方案,否则应设立基金生态修复专项基金,基金使用由专业的公益公募基金会监管。这既没有法律规定支持,也很难以进行司法执行。第四,相对海洋环境监管部门,社会组织缺少举证能力,欠缺科学手段、物质条件,对海上污染损失污染来源、损失确定方面证明能力较弱。第五,个别社会组织不顾海洋环境监管部门已经进行了行政监管并已代表国家进行索赔的事实,仍坚持提起平行的诉讼请求,对污染方构成重复索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