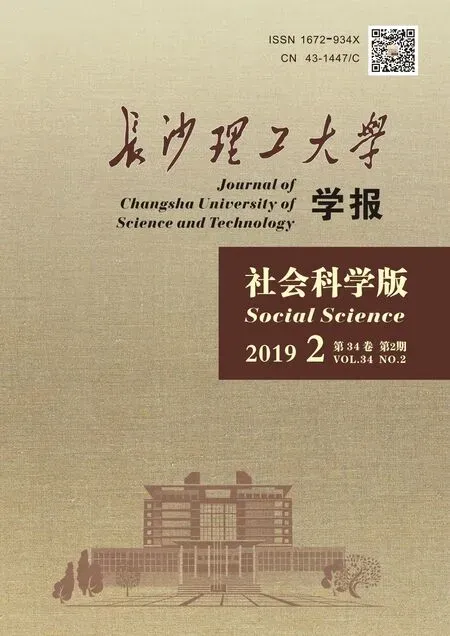老年辅助技术的风险及社会伦理挑战
陈四海,韦宇婷
(河南师范大学 科技与社会研究所,河南 新乡 453007)
辅助技术就是“任何设计用来增强残障人士或老年人独立性的产品或设施”[1]。辅助技术首要的适用对象是残障人士,用以提升残障人士的独立性和自主性,缩小残障者个体的能力和其生活环境之间的间隔,使得残障人士可以更好地融入和参与社会生活。由于老年人在某种意义上和残障人士具有相似的形而上学地位,都属于能力受限者,因此也是辅助技术适用的重要目标群体。辅助技术在消除老年人的社会阻隔、提升老年人的生活品质方面具有重要的效用,但是老年人群体内在的异质性和生活环境的差异性使得适用于老年人的辅助技术面临着一系列的技术、审美和伦理困境,例如技术本身往往缺乏易操作性、耐用性甚至安全性,远程监控等各种信息技术的使用带来个体的隐私问题等等。辅助技术产品和使用者具有“内嵌性的”亲密关系,是非中立的、负载意义和价值的,因此设计和开发有效的、能够为老年人所接受的辅助技术是一个需要由医学、工程学、信息科学和伦理学等众多学科参与的重大课题。
一、辅助技术和老年人独立性的提升
在漫长的人类历史中,深陷“自然的必然性”的大部分人类在生命有机体尚未衰老之前就已经被疾病、灾害和战争夺去了生命。人类的平均寿命在20世纪之后才开始有显著的提升,随着生产力和现代医学的进步,人类的自然寿命不断延长。在现代化和工业化的进程中,增寿的同时伴随着生育率的降低,使得老年人所占人口比例不断提升,这就是所谓的老龄化问题。人口结构的变化带来了一系列的社会问题和挑战,20世纪60年代以来世界各国都开始关注老龄化问题。中国人口的巨大基数、特定历史时期的人口政策、尚未完成的现代化和工业化历史进程,所有这些因素迫使我们必须全社会参与积极应对老龄化所带来的挑战。1999年中国成立全国老龄工作委员会,从2000年开始全国老龄工作委员会先后开展了四次“中国城乡老年人生活状况调查工作”。2015年第四次调查显示,“人口老龄化水平持续提升,从2000年的10.3% 持续提高到2015年的16.1%,平均年增长率为4%,是同期总人口自然增长率的8倍,老年人口净增长9 000万人,老龄化进程值得关注。”[2](P42)除了老年人绝对数量和其占人口比例的不断增加所带来的压力之外,老年人口还存在着男女比例失调等问题。中国传统的居家养老方式在现代社会转型中也受到严峻的挑战,第四次中国城乡老年人生活状况调查数据显示,半数以上老年人独居或仅与配偶同住,与人共居老年人已不足一半,表明当前老年人家庭结构小型化趋势突出[2](P25)。
衰老不仅是生命有机体的一种自然事实,还是人类社会所共同面临的一种挑战。老年是人生命历程中的一个阶段,如何从时间上来加以定义,不同国家、不同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划分标准。有些国家以65岁作为老年人的分界线,中国老龄工作委员会以60岁作为老年人的分界线。这种人为的在时间划分节点上的分歧其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当老龄化社会成为人类社会的常态,我们如何看待和审视老年问题。在理想状态下,人类在生物意义上会经过童年、成人和老年不同生命阶段,与此同时这个个体在社会意义上成长、工作和衰老。这种理想化的关于生命历史的设定被称之为“生命周期的准生物视角”[3](P26),其局限性在于以成人为中心来设定生命的历史,把童年期看作是成年期的预备,把老年期看作是对成人期的余音回响,把凡是不能按照这种理想预期演进的不确定性都看作是对“人生进程的破坏”。从这种准生物视角出发,会使得我们以“消极”“失败”的情绪来理解和处理老年问题,会妨碍我们对于老年问题的真正解决。以理想化的成人为中心,我们一方面期待每个人都能正常的衰老,当老年人面对损伤和病痛的干扰时,我们更多地是被动地负担,“老龄问题被理解为老年人问题,而老年人问题被理解为养老问题,以至于人们把对老龄问题的关注集中在如何给老年人盖养老院、提供相关服务这一狭小的领域,从而掩盖了许多重大问题”[2](P8)。
残障人士是和机体未受损伤的个体相对照而言的,这一对照在从童年到中年的大半段人生历程中都被突出强调,但是到了老年阶段,这一区分则显著地被削弱或淡化了。首先,这是因为在能力降低、环境障碍度增加方面,老年人和残障人士具有非常相似的地位和性质;其次,在从童年到中年的人生历程中被强化的对照还反映出了资本和市场对于机体未受损伤的个体参与工业生产的肯定以及对于残障人士通过技术和康复手段重返劳动力市场的期待。从资本和市场的逻辑来看,对照的淡化在某种程度上还意味着对于老年人生存境况的漠视。为了克服“生命周期的准生物视角”的局限,普利斯特利提出了一种新的认知和理解生命历史的“生命历程视角”,他指出人类生命历程的每一个阶段都有其自主的意义和价值,童年不是通往成人的预备阶段,老年也绝不是成年的余音回响[3](P4-5)。所以从生命历程的视角来审视老年期,“要为漫长老年期注入生命的意义和价值”[2](P17),要关注老年人的独立、自主和尊严。
辅助技术是根据适用的目标人群——残障人士来加以定义的技术集群。残障人士在学习、工作和日常生活过程中都面临着严重的社会阻隔,不能有效地独立生活、接受教育、参与工作以及进行人际交往。独立性的缺乏一方面使得残障人士往往会丧失自主性和尊严;另一方面则使得残障人士无法实现自身的潜能,创造出应有的社会价值。以新兴技术的进步为基础,辅助技术在打破残障人士所面临的社会阻隔方面变得越来越有成效。老年人对于辅助技术有着强烈的现实需求,“辅助技术研究聚焦于老年人口,因为65岁及以上老年人中很大一部分比例,接近25%,拥有一件辅助性设备,并且这些人中大约有三分之一拥有多种辅助性设备”[4](P5)。
除了生理机能本身的衰退之外,老年人所遭受的生理损伤一般可以分为四类:运动损伤、视觉损伤、听力损伤和认知损伤,这些生理损伤会使得老年人独立性减弱甚至丧失。随着科学与技术的不断进步,与老年人所可能遭受的各种有机体的损伤和机能衰退相匹配的各种辅助技术产品、设备不断被设计和生产并在实际生活中加以运用。比如当老年人遭遇运动损伤时,除了可以借助于轮椅、拐杖、助行架、手推车等辅助技术产品提升自己的运动能力和范围,未来还可以期待具有感知和探测环境状况的“智能轮椅”等新兴产品和设备来帮助老年人克服运动障碍;当老年人遭遇视觉损伤时,除了可以利用眼镜、放大镜、大字号产品等较低技术含量的设备之外,还可以利用电子放大镜来获取更好的视觉感知;当老年人遭遇听觉损伤时,可以借助于助听器、烟雾探测器、闪光灯门铃等设备,还可以利用基于新兴技术的数字化助听器、能够将声音转化为文本的智能设备进行更好的沟通与交流;当老年人遭遇认知损伤时,老年人所最可能遭受到的认知损伤就是老年痴呆症,老年痴呆会带来经验混乱、记忆力衰退、学习能力减弱等症状,进而会影响一个人独立完成日常活动的能力。在传统的技术条件下,几乎没有与认知损伤相匹配的辅助技术器具,但随着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手段的进展,在未来可以期待通过人工智能机器人来帮助具有认知损伤的老年人实现独立和自主。
当老年问题被狭隘地理解成养老问题时,老年生命的意义和价值就不当地被遮蔽了。完整生命历程的每一个阶段都有其自主的意义和价值,不止是老有所养,更重要的是老有所乐,老有所为。借助于各种辅助技术产品和设备,老年人可以克服因生理机能衰退和损伤所造成的限制,提升独立性和自主性,走出家门,进行学习、社交、休闲和娱乐,甚至进行工作和创业。其实对于老年人而言,生理的限制和阻隔可以通过技术进步来消除,然而真正将老年排除在社会之外的是更深层的社会偏见和阻隔。
二、辅助技术何以会被老年人弃用
技术中立观认为,“技术在文化上、伦理上、政治上具有中立性……技术在‘本质上’是非伦理性的,是独立于价值的某种东西,是既可以为善也可以作恶的工具。”[5]残障研究的医学模式把康复作为首要的价值和目标,认为是残障人士的生理损伤和临床需要决定着他们对辅助器具的选择,因此可以由医生和健康专家帮助残障人士选择辅助技术器具。在某种意义上医学模式隐含的理论前提就是技术中立观,从医学模式出发一方面使得我们仅仅从功能性和有效性的角度来考察辅助技术,忽视对技术使用者的主观心理体验和身份认同;另一方面则把辅助技术看作是医学治疗和康复无法完成的情况下作为“无法治愈”的补充性的技术手段,这就使得辅助技术器具反过来会成为残障的标志,给残障人士带来沉重的心理压力和负担。
事实上辅助技术的生产、设计和使用是一个包括使用者、医生和健康专家、生产者、销售者和社会公众在内的复杂网络系统。医学模式假定残障人士是“无知者”,因此认为使用者并不是这个网络的中心。在将辅助技术适配于包括老年人在内的残障人士过程中,存在着大量排斥和抵制辅助技术器具的现象,残障人士宁愿忍受痛苦和不便,甚至甘冒生理损伤所可能带来的巨大风险,也要对被诊断为临床需要的辅助技术器具弃之不用。实践中的惨痛经验和教训使得我们开始反思人和技术手段之间的关系,人们逐渐认识到技术本身绝对不是中立的,技术中立是一种“神话”。有不少学者对医学话语中的辅助技术进行反思和批评,首先技术本身是负载意义和价值的,“对于设备功能性的关注将会限制我们对消费者和意义相关的他人所具有的意义的理解,换句话说,技术不是中立的。意义经常是决定技术被采用还是被束之高阁的一个因素”[6](P5)。其次,决定一件辅助技术产品被采用或弃用的原因是复杂多样的,生理损伤和临床需要并不是决定辅助技术器具选择的唯一因素,“辅助技术减少环境阻隔的有效性(effectiveness)并不是决定这个设备被采用或被弃用的唯一决定因素”[4](P16)。
老年人因生理机能衰退和生理损伤而带来独立生活能力的减弱,各种辅助技术器具和手段可以有力地提升老年人的独立性,进而提升其自主、尊严和生活品质。老年残障人士在性别、审美体验、残障类型和生活环境等方面都存在着大量的显著差异。而从技术中立观出发的辅助技术工程设计不当地忽略这些差异,用整齐划一的工业设计来提供无一例外的产品,当这些产品被投放到市场,进而适配于老年人时,并没有产生临床诊断所预期的效果。老年人或者弃之不用,或者降低使用频率,或者选择不能充分克服限制的其它技术手段。当我们把老年人——辅助技术的使用者,当作辅助技术所涉及的使用者、技术和社会这一复杂网络的中心时,我们就会对老年人何以会排斥辅助技术有所发现。
首先,辅助技术给老年人带来沉重的羞耻感。医学模式所追求的理想是把人类所遭遇的生理损伤完全加以治愈,然而由于人类医学的局限,总有一些严重的生理损伤是无法治愈的,这会给坚持“康复”原则的医生和健康专家带来深深的挫败感,进而把辅助技术看作是治疗失败之后的选择。医生和健康专家这种挫败感映射到社会心理层面就会变成人们对于残障本身的排斥和质疑,这也是残障人士遭受社会阻隔的重要原因。绝大部分辅助技术器具都是可见的,并且和人类原本的生理构造存在差别,这就会使得辅助技术本身成为残障人士原本不可见的、私密的生理损伤外化为醒目的标志。老年人人生阅历丰富,对于社会文化心理层面的排斥和质疑有着更深刻、更敏锐的体验,因此会带来自我否定的沉重羞耻感。
要想克服老年人因使用辅助技术而产生的羞耻感,就必须克服社会心理层面对于残障和技术的偏见。有学者指出医学模式对“康复”追求的背后隐藏的是“浪漫主义的偏见”,人类在自然状态下所具有的物种典型性并不足以成为正常性的标准,要培养公众对于残障人士通过他们身体和替代性装备的紧密配合所实现的机能持欣赏态度[6](P12)。还有学者指出,我们必须建立新的康复范式(new rehabilitation paradigm)来克服医学模式的局限,不是从个体的生理损伤出发,而是从有损伤的个体在社会层面是如何面临排斥和隔离出发,因此新的康复范式所寻求的就不是生理的复原,而是在生理无法复原的情况下,残障人士如何被消除社会阻隔,因此新康复范式下,残障就不仅是残障个体的悲剧,康复的责任就从个体转移到社会[7](P9)。
其次,辅助技术忽略了老年人的性别差异。人类的性别差异以一定的生理构造为基础,同时也是社会建构的结果。男女的性别差异在青年和成年期被突显,这是人类对生育和婚配的需求所决定的。与此同时,性别差异在童年和老年期则被淡化了,英语用不区分性别“it”代词去指称孩子,这一语言现象在某种意义上就是性别差异淡化的体现。从心理发展的角度看,人类在童年期就开始建立起性别认同,并且在老年期也有着非常强烈的性别区分和认同,这本身就说明对于老年人性别差异的淡化是不合理的。在全球医疗系统中,性别不平等现象随处可见[8]。如果辅助技术器具的设计从成本的角度考虑进行通用的工程设计的话,其产品往往是没有考虑性别差异的,或者男性化的,因而引起使用者的排斥。
以轮椅为例,男性和女性老年人是存在着不同的要求和体验的。根据研究人员对使用者的采访,女性倾向于把轮椅比作衣服,并且要求轮椅的颜色要和其着装有着很好的搭配,比如“她的轮椅必须是中性的,因此她可以穿色彩鲜艳的衣服。她不想让人们注意轮椅,而是要关注她本人”[7](P60)。而男性使用者则倾向于把轮椅比作山地车,并且有男性使用者会替换轮椅原本装配的轮胎,而选择在网上购买与汽车轮胎相似的轮胎,“这些轮胎是黑色的,审美上令人愉悦,就像汽车轮胎。其中一个轮胎上还装饰有细小的银色骷髅”[7](P61)。
再次,辅助技术忽略了老年人的审美需求。医学模式认为是临床需要决定着老年人对辅助器具的选择,因此仅关注辅助技术的功能和有效性。而社会模式则指出,以轮椅为例,“轮椅的审美特性(aesthetics)对于这些使用者来说非常重要。它们甚至要比轮椅的功能性(functionality)更为重要”[7](P60)。因为在功能有效的情况下,如果不能很好地满足老年人对于审美特性的追求,辅助技术仍然有可能被老年人所弃用。在国际范围内,医学模式关于功能优先性的假定仍然占据支配地位,甚至不少国家对辅助技术进行监管的公共卫生部门也认可医学模式的这一假定,比如英国卫生署的一位雇员指出,“在英国每个病人优先考虑的是临床需要(clinical need)而不是审美外观(aesthetic appearance)”[7](P57)。其实在讨论老年人对辅助技术的选择和使用体验存在性别差异时,所举实例已经涉及到轮椅的使用者不仅关注功能,而且关注产品的装饰效果和审美外观。其实如同我们对衣服的选择,不仅仅是尺码决定我们的选择,是否与我们的审美相契合才是关键。在老年人对于辅助技术的选择过程中,良好的审美外观和审美体验是决定老年人能否与辅助技术相匹配的重要因素。
三、如何创制有效的老年辅助技术
随着生物工程技术、人工智能技术、纳米技术等一系列新兴技术的进步,我们可以乐观地期待老年人因生理机能衰退和生理损伤所造成的独立性的丧失都可以通过技术手段来加以解决。然而正如我们前文所分析,技术的进步只能提升相关器具和技术手段的功能性和有效性,辅助技术能否真正与存在临床需要的老年人的需求相匹配则是一个异常复杂和困难的问题。“将人和设备匹配要比将人和衣服匹配困难得多。令人吃惊地是,人们并不必然使用他们‘临床’需要的设备。人们会放弃设备,甘冒风险。”[7](P57)与此同时,我们也乐观地看到当技术和身体能够很好地匹配时,技术在某种意义上就会成为身体的延伸,甚至身体的一部分,有很多老年人借助于辅助技术从而实现独立生活,进而走出家门,积极参与社会交往。甚至有学者指出,“将设备和消费者之间进行匹配变成了一种科学和艺术”。[7](P11)在某种意义上,技术手段只具有潜在的生命力,当它为人所掌握,为人所使用时,其生命和意义才被激活,才可以称作是有效的。如何才能实现辅助技术和老年人的良好适配呢?
首先,辅助技术要采用安全、易于操作和使用的工程设计。安全性是所有的技术和工具都要考虑的基本要求。除此之外,在设计老年人使用的相关辅助技术器具时,除了要考虑功能性之外,还必须从人机交互的角度充分考虑老年人的生理特征、性别差异和认知局限,从而设计出用户界面友好的技术和产品,老年人更容易操作和使用的产品才能更为老年人所接受。
其次,要将老年人的审美需求和伦理关怀融入辅助技术的工程设计。辅助技术的功能性和老年人的临床需求是辅助技术工程设计首先要考虑的,但是在将辅助技术和老年使用者进行匹配的过程中,功能性和临床需求并不是唯一的决定因素。老年人对于辅助技术设备的大小、颜色、样式和装饰品等功能之外的外观形式有着非常重要的审美需求,这就要求辅助技术工程设计除了通用设计之外,还应该针对不同的老年残障个体进行个性化的设计和服务。此外,老年辅助技术的设计、使用和分发还必须遵循自主原则、知情同意原则、无损伤原则和公正原则等伦理原则。
最后,要推动社会公众认知和了解辅助技术,创造对残障和辅助技术宽容的社会文化环境。残障歧视是社会心理层面阻碍老年人使用辅助技术的最大障碍,如果从“人人生而自由,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来看待环境对人构成的障碍和限制,那么归根结底我们每个人都是为环境所阻碍的个体,都是残障人士。并且从残障的普遍性上来看,在每个人的一生中都会或多或少,或早或晚遭受有机体的损伤,因此对残障的歧视就是对每个人自身的歧视。正视残障,进而正视老年人所使用的技术手段,乐于见到在人和技术的良好匹配下老年人独立性和生活品质的提高。在这样一种宽容的社会文化环境中,老年人才会消除心理压力和羞耻感,才会勇敢采用临床需要的辅助技术产品。